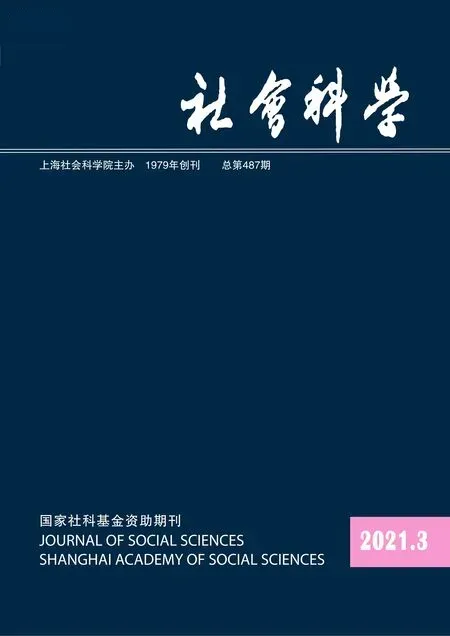论物化批判的主体间性辩护路径
周爱民
关于物化批判的研究,中国理论界已经充分阐明了物化与对象化、异化、“物像化”(Versachlichung)和拜物教概念的异同。(1)关于这方面的重要贡献,可参见韩立新《异化、物象化、拜物教和物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刘森林《物象化与物化:马克思物化理论的再思考》,《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这些比较性分析有助于人们准确回答物化是什么。由于物化现象是社会批判的对象,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继续澄清批判的规范性与可能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和霍耐特在此方面贡献卓著。在当代复兴物化批判的理论尝试中,他们所发展出的主体间性辩护路径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他们强调,卢卡奇基于形而上学主体概念的物化批判已经不合时宜了,必须另辟蹊径利用主体间性理论改造物化批判。在具体理解主体间实践关系,以及物化批判的规范性与可能性问题方面,他们的观点则大相径庭。详细分析与评价这条辩护路径,有助于推进本土物化理论的研究。
一、卢卡奇物化批判的理论困境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Verdinglichung)一词被提升到了哲学概念的高度并得到了详细阐述。然而,该书自问世以来一直饱受争议。如安德鲁·芬伯格所言:“到现在为止,卢卡奇的名著主要是通过非常消极和单方面的批评而为人所知。”(2)Andrew Feenberg, “Reification and its Critics”, in: Georg Lukacs Reconsidered,Michael J.Thompson(ed.), Continuum, 2011, p.172.在对该书“物化批判”的批评者中,阿多尔诺较有代表性。虽然阿多尔诺对这本书赞誉有加,(3)卢卡奇对阿多尔诺的影响参见Dirk Braunstein and Simon Duckheim,“Adornos Lukács-Ein Lektürebericht”, Lukács 2014/2015, Jahrbuch der Internationalen Georg Lukács-Gesellschaft, Vol.14,No.15,2015,pp.27-79。但他对物化批判的批评却极其尖锐。他的批评为后来批判理论家评论物化批判指定了方向。(4)哈贝马斯曾明确地指出,正是阅读阿多尔诺才给予他勇气以系统地讨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参见Jürgen Habermas, 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edited by Peter Dews, NY Verso, 1986, p.98。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沿此方向系统地阐述了阿多尔诺的批评,之后的霍耐特也继承了他的批评。(5)卢卡奇物化批判对批判理论传统的影响可参见Konstantinos Kavoulakos,“Lukács’Theory of Reification and the Tradition of Critical Theory”,in: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ritical Theory,Michael J.Thompson Editor,2017,pp.67-83。
阿多尔诺的批评贯穿于《否定辩证法》全书之中。概言之,他的批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6)详细分析参见Timothy Hall, “Reification, Materialism, and Praxis:Adorno’s Critique of Lukács”, Telos, 155, 2011, pp.61-82。Hall认为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它恰恰反映了现代性启蒙本身的内在矛盾,以及卢卡奇超越这种矛盾的失败。一方面,他指出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具有浪漫主义倾向,认为否定普遍的商品交换原则会为倒退到古代的非正义状态提供借口。他强调,问题不在于废除普遍的商品交换原则,而在于批判现实中的不公正交换,以实现交换原则中所蕴含的“自由和公正交换的理想”。(7)Theodor W.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uhrkamp, 1966, S.148.另一方面,他批评卢卡奇混淆了物化与事物的客观性,认为在物性中,“对象的非同一性维度和人类对普遍的生产条件的屈服交织在了一起”。(8)Theodor W.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Suhrkamp, 1966, S.190.由于卢卡奇没有正确对待非同一物,把它们与物化现象等量齐观,这导致他最终只能以观念论的方式克服物化现象,即寻找统一主体与客体的大写“主体”。
阿多尔诺的上述批判基本被哈贝马斯和霍耐特所接受。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系统地重构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他指责卢卡奇把物化发生的原因仅仅归因于抽象的商品交换,以至于忽略了经济子系统本身的独立性意义。这种忽略的结果是,物化批判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较为模糊。在此,哈贝马斯延续了阿多尔诺的观念论批判,认为卢卡奇虽然诉诸于“实践”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物化现象,但是这种实践只能是“哲学在革命中的实现”。(9)[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哲学在此比传统的形而上学具有更大的能力,它不仅能思考社会的总体性,而且还能思考世界历史的进程。无产阶级借助哲学的启蒙,能摆脱物化意识上升到自我意识的高度,进而能通过有意识的革命实践活动创造历史。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解决之道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重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回到了客观唯心主义。”(10)[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一书中,霍耐特也同样认为,卢卡奇物化批判“正式版本”的辩护基础是观念论的同一性哲学。他进而认为,“今日毫无疑问的是,随着他的‘物化’批判的这种奠基,卢卡奇失去了任何社会理论式辩护的机会”(11)[德]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译文有改动,参见Axel Honneth, Verdinglichung.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 Frankfurt/M.,2005, S.27。)。此外,霍耐特还一方面批判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太过宽泛。他认为,把物化与社会关系中的各种“去人格化”现象等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等同会导致把市场的交换行为都视作物化现象。另一方面,他又指责卢卡奇对物化的界定过于狭隘,因为卢卡奇仅把商品交换视作物化现象产生的缘由,完全忽略了固化的社会实践或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引起的物化。(12)[德]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30页。
在整合上述批评的基础上,迪尔克·夸德弗利格更为内在地批评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在规范性与可能性问题方面所潜藏的理论困境。(13)Dirk Quadflieg, Vom Geist der Sache, Campus Verlag, 2019, S.21-38.他把这种困境界定为人类学路径与历史哲学路径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在对物化现象的描述中,卢卡奇使用了诸多对比性描述。在描述物化劳动时,他使用的描述性词汇是“被肢解的”、“孤立的”、“机械的”,等等,而由物化劳动所构成的社会总体也是“机械的”、“偶然的”,具有“已经非人化和正在非人化的特征”。针对那些尚未处于物化现象中的劳动,他则使用了有机的源初性来界定这种状态,例如“人的有机统一性”、“有机统一的劳动过程和生活过程”,而由有机劳动构成的社会总体则是一种“有机必然性”(1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杜章智译,第140、148、151、136页。。结合卢卡奇对作为“第二自然”的物化现象所进行的批判,人们会很容易把与物化现象相对立的有机的源初性视作人的“第一自然”。因为只有在某种积极的第一自然概念基础上,对“第二自然”中主体与客体关系颠倒的描述才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消极现象。
显然,上述两条道路是相互矛盾的。在人类学路径中,物化批判所依赖的第一自然似乎是一种既定物,但是在历史哲学路径中,既定物本身被视为历史生成的产物,把某物视为不可改变的既定物本身就是物化意识的表现。(16)卢卡奇正是在此意义上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认为他的人类学把人推向了“固定的对象性”(fix Gegenständlichkeit),具有很大的危险,会陷入独断的相对主义中([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7-248页)。按照同情的理解,卢卡奇所描述的第一自然是在历史发展中将会实现的状态。但是,在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他已经否定了历史目的论。此外,在如何看待物化批判的规范性与克服物化的可能性问题方面,人类学路径与历史路径也处于冲突之中。如果认为物化现象的自我扬弃具有客观必然性,那么就无需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物化批判了;如果物化批判是基于人类学基础之上的规范性批判,那么克服物化就无法直接诉诸于某种客观的必然性,它必须依赖于主体的批判活动。卢卡奇在文中或许认识到了这种矛盾关系,认为尽管物化现象的自我扬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必须最终依赖于无产阶级的有意抉择,但是在他的历史哲学框架中,这种抉择意识的可能性也是存疑的。
二、作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物化批判
在改造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哈贝马斯基于主体间性理论的改造思路。在20世纪70年代写给维尔默的一封信中,哈贝马斯就已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改造物化批判的想法。他指出:“要为现代社会中异化或物化现象负责的,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交换原则或者工具理性在现代的胜利,而是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的紊乱关系,这种紊乱关系成为了批判理论的对象。”(17)转引自Dirk Quadflieg, Vom Geist der Sache, Campus Verlag, 2019, S.66。也有论者认为哈贝马斯的物化批判思路在其更早期的作品中就已有雏形了,参见Hauke Brunkhorst Regina Kreide Cristina Lafont(Hrsg.), Habermas Handbuch, J.B.Metzler, 2009, S.328。哈贝马斯的著名论断“生活世界殖民化”就是对这种紊乱关系的形象表达。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对该论题的充分阐述标志着新物化理论的诞生。(18)只有少数学者充分关注到《交往行为理论》可被视作新的物化理论,参见Timo Jütten,“The Colonization Thesis: Habermas on Reifi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9, No.5,2011,p.701。
哈贝马斯认为,用“生活世界殖民化”来界定当代社会的物化现象要比卢卡奇的物化版本更为准确。他用一种“双重社会理论”替代了卢卡奇所描述的单向度的社会合理化图景。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要更为复杂,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文化、社会和人格形成的合理化过程。在文化的合理化过程中,命题的真理性、规范的正确性以及个人表达的真诚性这三种有效性要求,逐渐成为了主体间在交往时须相互提出的规范性要求。建立在有效性要求基础上的交往行为,以作为背景和资源的生活世界为依托再生产着生活世界。此过程在社会层面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社会整合”,它保障了生活世界符号的再生产。与“社会整合”机制完全不同的协调行为的机制则是“系统整合”。尽管哈贝马斯后来曾强调要避免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把社会整合等同于交往行为,把系统整合等同于策略行为,(19)Jürgen Habermas, “A Reply”, in: Communicative Action, Axel Honneth and Hans Joas (ed.), The MIT Press, 1991, p.254.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书中所界定的系统概念与目的合理性、工具和策略行动紧密相关。(20)参见Hauke Brunkhorst Regina Kreide Cristina Lafont(Hrsg.), Habermas Handbuch, J.B.Metzler, 2009, S.376。系统可以被界定为目的合理性行动的整体,这些行动借助作为去语言化的金钱和权力媒介得到了协调。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构成了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两个维度。哈贝马斯并未停留于上述的分析性区分,他还进一步借助进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发展过程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历史考察中,他建构了自己版本的物化批判。
依哈贝马斯来看,问题不在于用社会整合去批判系统整合或者相反,而在于这两个方面在现实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不恰当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意义上的“启蒙辩证法”。一方面,现代社会文化的合理化过程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现代社会经济与行政子系统的发展被视作生活世界分化之后合理的产物。分化出的两个子系统分别通过金钱与权力的控制媒介再生产自身。两个子系统的独立化过程虽然瓦解了传统社会统一的价值观,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意义的丧失与自由的丧失,但是社会行动借助这些媒介减轻了交往行为的不确定性负担,使得整个社会的物质再生产更为高效,(21)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2, Suhrkamp, 1988, S.269-270.此外个体还可以无需考虑各种有效性要求的限制,自由地运用策略行为,从而也获得了自由。另一方面,启蒙历史过程的真正问题或者说“反讽”在于:“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使得系统复杂性的提升成为可能,这种复杂性膨胀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被释放的系统命令冲破了被这些命令所工具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力。”(22)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2, Suhrkamp, 1988, S.232-233.。换言之,物化的临界点就是:“只有当生活世界无法从所讨论的功能中退出时,只有当这些功能无法——就如在物质再生产领域中显示的情况那样——毫无痛苦地转变为媒介导向的行动系统时,转换为另一种行动协调机制并且从而转换为另一种社会化原则才会导致物化,也就是说,导致一种生活世界交往基础的病理学变形。”(23)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2, Suhrkamp, 1988, S.549.哈贝马斯以法治化为例具体地指出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病理现象。(24)对法治化所导致的病理现象的分析与批判,参见Daniel Loick, “Juridification and Politics.From the Dilemma of Juridification to the Paradoxes of Rights”,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4,2014,pp.762-764。概言之,这些现象严重扰乱和阻碍了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
在哈贝马斯通过交往行为改造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中,现代性的成就得到了更为公允的评价。哈贝马斯对市场经济系统与行政官僚系统的系统论解读,也有助于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行政制度改革时,摆脱来自教条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当批评,能够使人们在界定物化现象时更为小心翼翼,不再简单地把市场行为与服从命令行为视为物化现象。此外,对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切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物化批判的规范性问题与可能性问题。在批判的规范性方面,他能立足于生活世界批判系统的不当侵犯,这种批判无需再假定形而上学的主体概念;在批判的可能性方面,他也无需再诉诸于工人阶级尚未枯萎的灵魂,生活世界中进行交往实践的行动者都可以成为物化批判的主体。
尽管他的物化批判具有这些优点,但是他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区分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一方面,这种僵化的区分忽略了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可能内在地包含了交往潜力,即这两个子系统并非完全是价值无涉的中立领域,它们可能是不同团体通过交往实践进行斗争后的妥协产物;另一方面,这种区分也忽视了生活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即生活世界并非是权力无涉的理想之所,它的内部可能存在由种族和性别偏见所形成的权力统治。总之,就如霍耐特所说,如果把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析性区分运用到具体的社会领域中,就会产生对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双重“虚构”(Fiktion)。(25)Axel Honneth,Kritik der Macht, Suhrkamp, 1989, S.328-331.此外,在批判的规范性方面,哈贝马斯的物化批判也存在规范性模糊的问题。鉴于批判理论一直坚守内在批判,即批判的规范性要求不是来自某些社会学家或哲学家的“专利发明”,而是源于被批判对象自身之中,(26)具体分析参见周爱民《论批判理论的家族相似性:从内在批判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那么物化理论就必须要从行动者的角度澄清行动者自身批判物化现象的规范性要求是什么。如上文所述,哈贝马斯是从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陷入功能紊乱的角度批判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但是,仅从功能主义的角度难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对于具体的行动者来说,从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的功能紊乱角度难以直接推导出它在规范性要求方面就是错误的。(27)更为详细的批判参见Timo Jütten,“The Colonization Thesis: Habermas on Reific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Vol.19,No.5,2011,pp.701-727。不过,与霍耐特彻底放弃哈贝马斯的双重社会理论架构不同,Jütten主张物化论题的不足在哈贝马斯既有的理论框架中能够得到补救。例如,哈贝马斯在说明现代福利国家中的过度法治化时,认为法治化所造成的对福利分配的官僚式执行以及货币化补偿导致了对生活世界交往实践的扭曲,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说明它为何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一种规范性错误。
上述指责可惜并没有推动哈贝马斯继续完善他的物化批判。在出版《交往行为理论》之后,他基本离开了对社会病理的分析,而转向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律理论中的奠基问题,这一转向的集大成之著就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霍耐特在评论这一转向时也略带遗憾地说:“毫无疑问,伴随着康德主义传统的转向,哈贝马斯面临着失去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见解的危险,在他更坚定地以黑格尔为典范的早期著作中仍然包含着这些见解。”(28)Axel Honneth, “Unser Kritiker Jürgen Habermas wird siebzig: eine Ideenbiographie”, Die Zeit, 1999-06-17,https://www.zeit.de/1999/25/199925.habermas_honneth.xml.
②做好电子档案的存储与备份。电子档案是现代科技的产物,其生存和可读性依赖于计算机的硬件产品和软件产品。对归档的各类型文件,如文本文件、图像文件、音视频文件等,应采用通用的主流存储格式,对非通用格式的电子文件应提供格式转换功能。对电子档案的存储设备应考虑其成熟性和发展性,尤其是不公开的机密电子档案应具有脱机保管能力。电子原件的存储方式也是关键,应该提供多种方式,如数据库存储、目录存储、光盘存储等,用户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电子档案备份、恢复是档案管理系统运行的安全保障。应建立一个从系统备份、数据库备份、网络备份到电子原件备份的有效备份,保证档案管理的完整性。
三、作为“遗忘承认”的物化批判
在继承哈贝马斯早期著作见解的基础上,霍耐特重新把社会病理现象视作社会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29)参见Axel Honneth, “Pathologien des Sozialen.Tradition und Aktualität der Sozialphilosophie”, in: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Suhrkamp, 2000, S.9-69。他首先批判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霍耐特已基本形成了两大批判:一是认为哈贝马斯的双重社会理论是双重虚构,应该另辟蹊径挖掘交往行为可能包含的另外的社会秩序构想;(30)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 Suhrkamp, 1989, S.297-303.二是指出对话语原则的违背并不能构成充分的斗争动机,人们模糊的非正义感其实构成了重要的冲突燃料。(31)Axel Honneth, “Moralbewußtsein und soziale Klassenherrschaft”, in: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 Suhrkamp, 2000, S.114-115.借助黑格尔与米德的承认理论,他把这种模糊的情感冲动界定为承认遭受否定而产生的被蔑视感。经过这些理论准备,他建构起了新的社会哲学。借助这种新的社会哲学,霍耐特对卢卡奇物化批判的改造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然而,在说明物化批判的规范性问题方面,他没有利用之前所阐述的具体承认原则,反而使用了一种先验意义上的承认概念,并把它视作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32)在《为承认而斗争》的后记中就已经有这种区分的端倪了,他当时区分了人类学中的“常量”,即人的发展需要依赖于他人的承认,与历史中会发生变化的具体承认关系,只不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主体的自我实现依赖于他人的承认,而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更多强调的是主体承认他人的重要性,参见Axel Honneth, Kampf um Anerkennung: Zur moralischen Grammatik sozialer Konflikte, Suhrkamp, 2010, p.311。这种承认概念虽然使得他的物化批判更为准确,但同时也造成了物化批判陷入“无的放矢”的尴尬处境中。
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一书中,霍耐特首次系统地亮明了对卢卡奇物化概念的理解,试图让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再度现实化。他严格按“字面”(literally)意思来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概念,认为物化就是把他人仅仅视为物,“把某人视为物就是把他或她当做缺少全部人的特性的某种东西”(33)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8。遗憾的是《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的译者依据的是德文第一版,该版没有英文版中几位学者的反驳和霍耐特的回应,这部分内容对进一步理解霍耐特的物化理论至关重要。。把他人视为物究竟为何是错误的?这种错认仅仅是认知意义上的错误吗?霍耐特排除了物化仅仅是认知错误或道德错误的看法,他认为物化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实践。对物化的这种理解,使得批判的规范性问题变得更为醒目。既然物化是一种错误的实践,那么正确的实践是什么?
在界定什么是正确的实践时,霍耐特比卢卡奇和哈贝马斯都更为小心翼翼。与卢卡奇不同,他并未直接把“物化”与“客观化”等同,他认为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客观认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手段,因此不能全盘否定它的意义。与哈贝马斯不同,他并未把错误的实践与正确的实践分类划入不同的社会领域。他强调,应当在更高的观察层面上去区分物化实践与非物化实践。在此更高层面,客观认识与承认并非处于直接对立中,而是处于不同的关系中,物化是对两者错误关系的表达。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中,一极是认识的“承认敏感”(anerkennungssensitiv)形式;另一极是认识的“承认不敏感”形式,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实践行为只关注客观认识,先在的承认退入背景当中并遭到了遗忘。
在仔细区分了物化实践与非物化实践之后,还需要澄清为什么承认敏感的认识是正确的。为了回答该问题,霍耐特同时从起源(genetisch)与概念两个方面论证了承认先于认识。借助发展心理学与S.卡维尔的研究,他指出,婴儿如果在发育成长过程中没有在情感层面先承认他的照料者,就无法形成以照料者的视角客观认识对象的能力,而成人如果没有先承认互动对象作为人的存在,便无法理解互动伙伴的语言表达。既然承认在时间与概念上都是恰当地认识他人的必要条件,那么在认识他人时,就必须时刻意识到承认的优先性,即保持承认的敏感性。在承认敏感性的认识中,个体在情感层面把他人视作与自己一样具有人的特性的对象,霍耐特在文中使用了“积极的肯认”(34)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5.来表达这种对他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基本承认并不包括道德方面的规范性要求,它仅仅是一种“先验条件”,具体的“爱与恨,矛盾情绪与冷漠都可以被视为这种基本承认的表达”。(35)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2.
很显然,基本承认与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所阐述的具体承认关系并不相同。具体承认体现为制度化实践中的爱、平等与团结原则。他认为,这些具体的制度化承认原则只不过是历史地“填充”了上述基本承认关系。由于具体承认是主体间相互提出的道德要求,那么基于这种承认遭到否定的批判就是一种道德批判。与此不同的是,由于基本承认表达的是个体间最基本的社会存在关系,是个体相互恰当认识对方的先验条件,那么基于这种承认遭到遗忘的物化批判就是基于更为基本的“社会本体论立场”(36)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7.的规范性批判,即澄清社会本体论层面的正确与错误。
这种本体论批判在回答批判的可能性方面优势也很明显。鉴于基本承认在正确认识他人方面的必要性,设想整个社会都陷入到这种物化现象当中显然是荒谬的,而不难设想的是,社会中存在诸多把人视作人的制度化实践。尽管如此,这种批判在寻找批判对象时会陷入困境。依霍耐特的看法,“真正的物化案例只存在于其本身没有类似于物的属性的东西被看作或当成一种物”(37)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9.。借助于卢卡奇的洞见,他把这种物化实践的成因归咎于社会的制度化实践,他称之为“物化的社会病源学”。令人疑惑的是,社会的制度化实践真的会使人把他人完全视作物,从而忽视他人之为人的特性么?从霍耐特列举的诸多案例中可以看出,几乎没有哪个案例严格符合他所界定的物化现象,他自己也坦诚:“只有极少和例外的案例,只有在社会性的零点处才能发现对先前承认的真正否定。”(38)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7.例如他在文中所列举的打网球案例,双方仅仅关注比赛的输赢,并不意味着就互把对方视作物了,也有可能是完全出于尊重对方才在乎输赢。在遭到批评后,霍耐特坦诚该案例是一个“糟糕的选择”,甚至具有“误导性”。(39)Axel Honneth,Re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5.他又列出了自认为符合物化现象的两个案例:一个是战争中只顾歼灭敌人的士兵甚至把路人也视为应当被射杀的物;另一个是现代的奴隶制,如性交易。然而,无论哪个案例都无法严格满足他对物化的界定,例如士兵不会不知道自己射杀的是人,因为他专门瞄准枪口射向路人而不是射向视野中的其他物,就已经说明他并未遗忘人与物的差异。
T.于腾正确地指出,要摆脱物化批判“无物可批”的尴尬局面,就不能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理解物化,物化只能被视为一种“比喻”(metaphorical)的说法,即某人被视为“像是某物”(as if a thing)。(40)Timo Jütten, “What is Reification? A Critique of Axel Honneth”, Inquiry, Vol.53,No.3,2010,pp.235-256.在本文看来,霍耐特之所以一再强调要按字面意思理解物化,是因为他把物化视作对基本承认的遗忘。既然基本承认被视作是对人之为人的特性的肯认,那么遗忘这种承认就必然会导致把人视作物。因此,要解决霍耐特物化批判的难题,就必须修正对基本承认的理解。本文认为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自由”概念来完成这项工作。尽管如此,主体间性的阐释路径仍然会忽视卢卡奇物化理论中的重要维度,即物的物化问题。下文将首先阐述主体间性阐释路径对物的物化问题的忽视,最后一部分将通过哈贝马斯的交往自由概念来重新界定基本承认,并且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物的维度置入其中来澄清物的物化问题。
四、对物的物化问题的忽视
卢卡奇曾明确指出:“当各种使用价值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为商品时,它们就获得一种新的客观性,即一种新的物性,……它消灭了它们原来的、真正的物性。”(41)[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0页。洞穿这些新的物性,例如货币作为生息资本形态存在、土地作为地租形态存在,等等,把它们视为对现实的“真实抽象”,构成了物化批判的重要方面。如果对物的物化形式的固化本身是物化意识的典型表达,那么就可以说,主体间性的阐释路径把物的物化形态视作物的本来形态,也是典型的物化意识的产物。(42)已有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了哈贝马斯的物化理论对社会生产关系中物化现象的忽视,参见Martin Morris, “Capitalist Society and Its Real Abstractions: The Critique of Reification in Habermas’s Social Theory”, Rethinking Marxism, Vol.10,No.2,1998, pp.27-50.
诚然,霍耐特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注意到了物的物化问题,但是由于他固执于主体间性的阐释路径,物的物化最终被当作了次要的方面。在该书中,他明确意识到了他所主张的基本承认优先性难以说明物的物化问题,因为基本承认表达的仅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认识的必要前提。他认为,尽管在伦理方面,尝试与动物、植物甚至是无机物的互动式和承认式相处是“令人欢迎的”,但是在规范方面的偏好并不能直接证明这种相处是不可替代的。要证明这种互动模式不可替代,就必须要证成对它的替代会直接扭曲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而这又进一步要求在概念层面必须证明对自然物的承认是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前提。在霍耐特看来,不管是卢卡奇还是海德格尔和杜威,都没有提供满意的证明,而且他也怀疑提供这种证明的可能性。(43)[德]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4-96页。在此情况下,他强调必须要离开卢卡奇对物的物化问题的直接说明,转而采取一种更为间接的说明方式。这种间接的说明方式就是,物的物化表达的是对该物所承载的他人生活态度或价值观的遗忘。换言之,对物的承认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对他人的承认,“对他人个体性的承认要求着我们,就客体曾被他人所赋予之各种意义与面向来认识其独特性”(44)[德]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罗名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8页。。
在此解读路径中,自然物或社会物本身的规范性问题被彻底遮蔽了。对物的规范性问题的忽视也体现在霍耐特整个承认理论架构中。他所指出的个体自我实现所需要的三种承认关系,全部都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各种承认形式(爱、法权与团结),而对物的承认在此完全是缺场的。自然物或社会物只有在认可他人劳作成就的视域中才是在场的。物的这种“卑微”地位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二元切分中,对物的彻底工具化使用被视作现代性合理化的重要成就。在功能分化了的经济子系统中,对物的彻底工具式使用被视作是理所当然之事。在早年的《认识与兴趣》中,他甚至把技术上的认识兴趣视作人类科学认识自然的“准先验”条件。基于这种理由,他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工具和技术理性了解自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科学认识自然的方式,更不可能存在如马尔库塞所主张的那种与自然和解的“新科学”。(45)[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5页。对物本身规范性的彻底忽视直接导致哈贝马斯认为物本身的物化是正常的,无需批判。
哈贝马斯与霍耐特的上述见解早已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判。例如,J.怀特布克认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他在人的科学方面是反还原主义者(人与人之间应遵循交往理性),但是在生命科学中则是彻底的还原主义者(科学受技术上的认识兴趣引导)。(46)Joel Whitebook, “The Problem of Nature in Habermas”, Telos, Vol.40,1979,pp.41-69.R.埃克斯利则指责哈贝马斯混淆了科学中的方法论与科学作为“人类的一般工程”。她强调科学共同体可能并非出于控制自然的兴趣研究自然,例如当代生态学所强调的生态系统内在关系学说就指出,自然并非是人类自我保存和自我实现的工具,它们有其自身的相对自主性。(47)Robyn Eckersley,“Habermas and Green Political Thought: Two Roads Diverging”,Theory and Society , Vol.19, No.6, 1990.不仅在科学理论中存在完全不同的对待物的方式,而且在现实的新社会运动中,例如生态主义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以及女性主义运动等,人们都极力强调自然物以及作为自然的身体本身对于塑造健康的社会互动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在他们的批判诉求中,自然物的存在本身被视作具有一定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要求我们正确地对待自然物。例如,工人要求改善劳动环境的诉求就不是要求承认个体的劳动成就,也不是要求公正分配,而是要求恰当地考虑工人的自然身体本身。(48)从鲜活体验的角度对劳动的阐述,参见Christophe Dejours, Jean-Philippe Deranty, etc.,The Return of Work in Critical Theor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总之,如果这些基于物本身的批判要求是物化批判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而主体间性的阐释路径必定会导致对该维度的忽视,那么在当代复兴物化批判时就必须重新评价这条阐释路径。在如何对待主体间性阐释路径方面,本文主张一种温和的纠正方式,反对彻底抛弃该路径。主要理由是:从积极方面来看,该路径以阐述主体间正确的实践关系为基础,更为恰当地界定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物化现象;从消极方面来看,如果彻底抛弃该路径直接去说明物本身的物化问题,“可能会倒退到形而上学中,从而落后于现代所达到的学识水平进入一个再度附魅的世界”(49)Jürgen Habermas,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Habermas: Critical Debates, John B.Thompson and David Held(e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2, p.245.。直接赋予自然物以某种自在的道德价值从而要求我们尊重它们,在认识论上面临着独断论的危险,它必须要解决这样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即人类何以能脱离自身的认知视角去认识事物自在的价值?该问题显然是无解的,因为对价值的认知总是事先打上了人的烙印。即便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自我保存的角度来看待具体自然物的价值,从而要求人类的活动要尽量避免危及它们的生存和存在,也是事先假定了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否则不能从生态系统自我保存的事实得出人类应该要尊重这一事实的规范性要求。如果以上两个方面的理由能完全成立的话,那么继承主体间性的阐释路径将是更好的选择。现在面临的问题仅是:如何在这条路径之中成功地直接说明物的物化问题?
五、交往自由与物的构成性意义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本文将首先指出一种更好版本的主体间相互承认关系,以便解决霍耐特式物化批判无的放矢的窘境。如上文所述,为了复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霍耐特提出了一种主体间的基本承认关系,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几乎难以找出遗忘这种基本承认的实践活动。因此,为了准确地描述卢卡奇所揭示出的物化现象,就必须要修正对基本承认的理解。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所提出的“交往自由”(kommunikative Freiheit)概念可以被视作基本承认,它能够更好地说明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物化现象。
交往自由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概念之一,但是直到出版《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他才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并对之作出了简要说明。(50)更为详细的说明参见Klaus Günther, “Communicative Freedom, Communicative Power, and Jurisgenesis”, in: Habermas on Law and Democracy, Michel Rosenfeld and Andrew Arato(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234-254。交往自由是指“在以理解为取向的行动中预设着的一种可能性:对对话者所说的话和在这种话中所提出的旨在主体间承认的有效性主张,表示一个态度的可能性”(51)[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页。。在以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动中所预设的这种能够表示(肯定或否定)立场的可能性,是交往主体相互赋予的“规范地位”(normative status)。这种自由并不是指行动能力上不受阻碍的自由,也不是意志上的自由,而是交往主体在以理解为取向的交流中必须相互预设和相互承认的权利。它同时也蕴含着相互的义务,即说话者必须要准备为自己所提出的有效性主张提供理由,而听者在否定说话者的有效性主张时也必须愿意和可以给出理由。如果说话者只想让听者接受其主张而不愿给出理由,而听者在不愿或无法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否定说话者的主张,那么交往自由就遭到了否定,交往行动也就随之中止了。因此,尽管交往自由是一种规范性的预设,但是它还必须是一种有效的自由,即“一个人只有在拥有方法和能力激活它的情况下才是自由的”(52)Peter Niesen, “Communicative Freedom”, in: The Cambridge Habermas Lexicon, A.Allen and E.Mendieta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51.。如果没有实现交往自由的可能性,就不能说人们相互之间拥有采取肯定或否定立场的能力。从交往自由的这些特征来看,相比较于霍耐特所论述的基本承认,它更能说明卢卡奇意义上的物化现象。
首先,以交往自由为基础的物化批判能更好地与道德批判区分开来。如果道德是指康德意义上的把人视作目的并非仅仅视作手段的话,那么霍耐特所理解的对基本承认的遗忘仍然是一种道德错误,因为遗忘基本承认的实践活动是把人完全视作不具有人的特性的物。而以交往自由为基础的物化批判则无须把物化视作对人的特性的彻底遗忘,它只是把对基本承认的遗忘理解成遗忘或否定主体的规范地位。这种遗忘并非必然是道德上的错误行为。在以各种有效性要求为基础的交往行为中,人们可以随时退出交往行为不受“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的制约,这种随意的退出即任意意义上的自由甚至是交往自由的前提。(53)从交往自由无法直接推论出任意自由,而从任意自由角度来看,它能构成交往自由的基础条件之一,参见Albrecht Wellmer, “Freiheitsmodelle in der modernen Welt”, Endspiele: Die unversöhnliche moderne, Suhrkamp, 1999, S.15-54。
其次,它能更好地从参与者的角度说明为什么物化是一种规范上的错误。如果基本承认是主体间在以理解为取向的言语沟通行为中必须要预设的基本关系,那么它的规范约束力就体现为主体间必须相互尊重对方的规范地位。交往自由所体现的主体间的自主理念,“它们作为不可避免的、经常是反事实的假定,嵌入到了日常的交往实践中,并且因此嵌入到生活世界中;它们在政治系统的制度中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尽管以零碎的方式”(54)Jürgen Habermas,Autonomy and Solidarity: Interviews with Jürgen Habermas, Peter Dews(ed.), Verso, 1992, pp.226-227。沿此方面可以进一步指出哈贝马斯与黑格尔在看待自由问题上的相似性,Kenneth Baynes, “Freedom and Recognition in Hegel and Habermas”,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28,No.1,2002,pp.1-17; Robert B.Brandom, “Towards Reconciling Two Heroes: Habermas and Hegel”, Argumenta, 2015, pp.29-43.。如果物化实践是对这种基本承认的否定,那么人们从参与者的角度就能够利用交往自由概念内在地批判该实践的错误性。
最后,它能更好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霍耐特式基本承认所批判的现象,如战争中的滥杀无辜和奴隶制,也存在于前资本主义制度中,因此可以说以该基本承认为基础的物化批判具有非历史性,它难以具体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物化现象。而以交往自由作为基本承认的物化批判则能避免这一缺陷。正是现代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使交往自由变得可能,它因此是现代社会和文化进化的成就,对它的否定或遗忘就可以被归咎于具体的现代制度实践所致。因此它是现代社会和文化进化的成就。例如卢卡奇所描述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的物化劳动,以及以普遍商品交换为基础所形成的经济系统与官僚系统中的物化实践,就可以通过交往自由的概念得到恰当的批判。工人被迫进行琐碎的无声劳动,商人只顾以利润来衡量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官僚系统中只有执行命令的实践,等等,都可以被视作对交往自由的否定。如果霍耐特对现代社会“规范一元论”的论证在经验上是可以得到充分支撑的话,那么就可以以交往自由遭到否定来批判这些子系统中的物化现象,而无须像哈贝马斯那样把交往自由的批判潜力限定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方面。
尽管利用交往自由重新阐述基本承认能解决物化批判的对象难题,并且能更好地说明现代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但这条阐释路径仍可能会忽视物的物化问题,因为交往自由指涉的仅是主体之间在以理解为取向的言语交往时所预设的、能够有理由地肯定或否定某种有效性要求的权利,它直接排除了物本身也享有这种权利。那么,如何在交往自由的视域中直接说明物本身的物化呢?
合理的解决方式就是承认物本身对于交往自由具有构成性意义。在此方面,有两条路径可以证成物的构成性意义。一条是霍耐特指出的但并没有详细反驳的论证路径,即卢卡奇、海德格尔和杜威都曾试图论证过对物的承认是客观认识的必要前提。在未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霍耐特就草率否定了这条尝试路径的可能性。这恐怕与他和哈贝马斯共享的基本信念有关,即对物的科学认识只需工具理性就足够。这一信念限制了他们对人与物之间原初承认关系的探究。例如,霍耐特在讨论心理分析与儿童发展心理学中所争论的婴儿“全能感”时,就坚持认为它只是暂时性阶段并且仅限于亲密的照料者,(55)Axel Honneth , “Facetten des vorsozialen Selbst.Eine Erwiderung auf Joel Whitebook”, in: Das Ich im Wir, Suhrkamp, 2010, S.294-295.他完全忽视了儿童“融合社交性”(syncretic sociability,即人与物的原初承认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方面,法国思想家梅洛-庞蒂所阐发的“肉身间性”(intercorporeity)概念构成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被认为可以澄清:人在有机体方面与物的互动构成了交往自由的前提条件。(56)详细论述参见Jean-Philippe Deranty, “The loss of Nature in Axel Honneth’s Social Philosophy.Rereading Mead with Merleau-Ponty”, Critical Horizons, Vol.6,No.1,2005,pp.153-181; Talia Welsh, The Child as Natural Phenomenologist: Primal and Primary Experience in Merleau-Ponty’s Psych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hilip J.Walsh, “Intercorporeity and the first-person plural in Merleau-Pont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53,No.1,2020,pp.21-47。
另一条路径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即研究物对于主体形成主观心理以及主体之间形成社会准则方面所具有的构成性意义。在此方面,迪尔克·夸德弗利格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论物的精神》(57)Dirk Quadflieg, Vom Geist der Sache, Campus Verlag, 2019.一书中,他系统地梳理了物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以及社会整合方面所具有的建构性意义。在此传统中,有长期被黑格尔研究界所忽视的黑格尔早期耶拿手稿中积极的物化概念,还有法国文化人类学对礼物交换(以莫斯为代表)的研究成果,以及海德格尔、阿伦特和马尔库塞等人对物本身意义的研究。夸德弗利格目前还只是梳理了这些思想传统,并没有以交往自由为视角系统地整合这些思想资源,这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很多的空间。
总之,根据上述两条路径的研究成果,如果物对于主体间性的交往自由具有构成性意义,那么从否定方面来说,在以交往自由为基础的主体间互动中,物就不能仅仅被视作工具式存在,它具有“不可支配性”(unverfügbar),即要求我们不应当完全把物视作“可支配的”(verfügbar);从肯定方面来说,物化批判要能同时指出物的构成性作用,要能区分出积极意义上物的“物化”与消极意义上物的“物化”,以便能合理地批判消极意义上物的物化。积极意义上的物化是指承认物在促进交往自由方面的建构性意义,而消极意义上的物化则意指对物本身的规范性的遗忘或否认。显然,在物化批判中重新重视物的物化问题,可以使得古老的物化批判连接到当代的生态主义运动中,可以使得物化批判重新作为政治斗争的理论武器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58)已经有学者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了,参见Anita Chari, “Toward a Political Critique of Reificatio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Vol.36,No.5,2010, pp.587-606。
结 语
综上所述,主体间性阐释路径主张用主体间性的某种实践关系作为物化批判的规范性基础,试图更为恰当地回答物化批判的规范性与可能性问题,以便避免卢卡奇物化批判中人类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矛盾。这种复兴物化批判的努力,可以使得物化批判告别历史哲学的宏大叙事,转而借助具体的经验分析来澄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因具体的社会制度问题所造成的物化现象。这些理论洞见值得我们在当代复兴物化批判时加以借鉴和利用。但是,以哈贝马斯和霍耐特为代表的主体间性阐释路径也存在诸多的理论难题。除了他们各自理论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外,在复兴卢卡奇物化批判时,他们所遗留的重大问题是物的物化问题被忽视和低估了。然而,物的物化问题不但是卢卡奇物化批判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当代新社会运动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因此,要利用主体间性理论重新复兴物化批判,还要充分阐明物的物化问题。在认识论层面,可以沿着有机体之间的承认互动以及人对物的原初承认是交往自由的前提展开论证;在文化人类学方面,可以通过揭示物对于主体间交往自由所具有的中介意义展开论证。这两方面的探求并没有僭越主体的视角独断地赋予物本身以某种自在的价值,而是在承认主体间性理论成就的基础上澄清它的前提,以便为物的规范性要求留下空间。在主体间性理论之中补入物的维度,可以充分发挥该理论的批判潜力,可以使得物化批判能够合乎时宜地成为资本主义内部兴起的反抗运动的理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