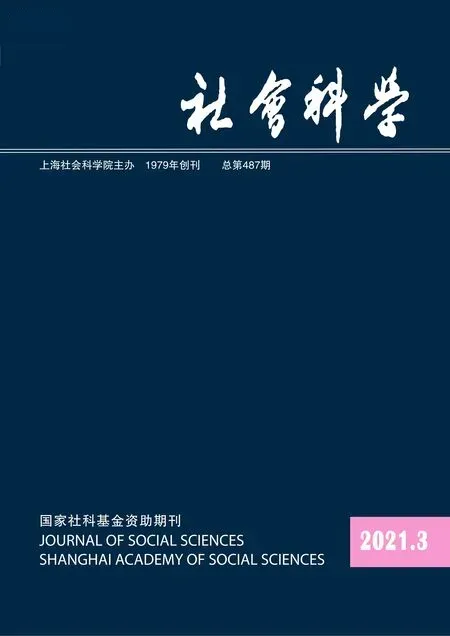化用的生活形式,还是共鸣的世界关系?
——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共识与分歧
郑作彧
一、批判理论的当代发展动力
在社会思想史上,很少有流派像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那样,一方面既有强韧、清楚明确的世代传承,但另一方面在世代的传统延续上又不断在思想研发与时代诊断上推陈出新。(1)本文以下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简称为“批判理论”。不过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 两者并不是直接等同的。本文要讨论的更多是批判理论。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可详见王凤才《如何阅读<否定辩证法>》,载[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2页。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建立起批判理论的第一个世代,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毋庸置疑地延续进第二代。哈贝马斯之后,中间沉寂了一阵子;但2001年霍耐特(Axel Honneth)执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高调地大力推动批判理论之后,批判理论便被认为正式进入第三代。由于霍耐特让批判理论发展得相当蓬勃,因此这个思想流派是否会再出现新的世代,也一直令人感到好奇。像是受教于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的弗斯特(Rainer Forst),就是备受期待的批判理论新世代学者。(2)王凤才:《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
不过,除了弗斯特之外,2015年之后霍耐特的其他弟子也开始冒出头来,纷纷有意识地打着“批判理论”的旗帜,表现出令世人瞩目的创造力。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任教于耶拿大学并执掌埃尔福特大学韦伯高等文化与社会研究院的罗萨(Hartmut Rosa),以及任教于柏林洪堡大学的耶姬(Rahel Jaeggi)。这两人不只学术成就斐然,而且也乐于提携后进或培养弟子,形成了相当热闹的批判理论研究学圈[例如甫至柏林自由大学任教的采利卡特斯(Robin Celikates),以及霍耐特退休后接任其教席的萨尔(Martin Saar),便深受罗萨和耶姬的提携,也与两人有许多直接的合作,成为今天批判理论当中相当活跃的核心成员]。也因此,近年来国际学界越来越同意,批判理论已经以罗萨和耶姬为中心,形成新的第四个世代了。(3)Amy Allen and Eduardo Mendieta, From Alienation to Forms of Life: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ahel Jaegg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8; Beatrijs Haverkamp, “Reconstructing Alienation: A Challenge to Social Critique?” , Krisis: Journal for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ol.1, 2016, pp.66-71; Esther Lea Neuhann and Ronan Kaczynski, “Rosa, Hartmut: Resonanz.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Berlin: Suhrkamp 2016.816 Seite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Literatur, Vol.4, Issue.3, 2016, pp.42-53; Christian H.Peters and Peter Schulz, Resonanzen und Dissonanzen: Hartmut Rosas kritische Theorie in der Diskussion,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7; Simen Susen, “The Resonance of Resonance: Critical Theory as a Sociology of Wolrd-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2019, https://doi.org/10.1007/s10767-019-9315-4; 郑作彧:《译者前言:一本书,两种读法》,载[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
与第二代和第三代几乎被认为就是单一代表人物在推动整个学派进展的情况不同,第四代和第一代一样,都是许多才华洋溢的学者共同参与的。这些学者共享着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怀,在相同的立场基础上各自发展出富有洞见的理论。不过,第四代学圈有一个与第一代不太一样的有趣现象: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的立场有很高的一致性,他们的研究有很大的互补性。例如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写的《启蒙的辩证》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性延伸。然而,第四代虽然在基本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当中的成员却对彼此有很强烈的批判性,研究以一种相互切磋的方式来进行。特别是第四代的主要人物,罗萨和耶姬之间的辩论。
罗萨年纪稍长于耶姬,很年轻时就以社会加速理论闻名于世,但其时间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批判潜力,是受到耶姬怀疑的。而耶姬的批判理论,则被罗萨攻击为是一种很危险的理论。这种“批判理论的内部批判”,可说是批判理论很特殊的当代发展动力,一个很值得讨论的现象。不过,探讨这种发展动力之前,有必要先厘清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共享基础立场是什么。因此本文接下来首先将呈现第四代的共享主旨。然后依序介绍耶姬和罗萨如何基于对对方的质疑以发展出他们各自的批判理论。由于这是一个还正在进行的辩论过程,因此本文最后无法对两人的论点给出最终总结;但他们至今的共同缺失,以及这个缺失可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思考方向,仍然是可以初步归纳得出的,这也是本文最后会尝试做的事。
二、第四代批判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美好生活
霍克海默发表于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无疑是很重要的批判理论奠基宣言。(4)Max Horkheimer, “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 In Max Horkheimer(ed.), Gesammelte Schriften, Bd.4: Schriften 1936-1941,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8 [1937], pp.162-216.霍克海默在当中表明,社会研究不能像实证主义那样,将社会当作与研究者和研究结果本身无关的客体对象,而是必须要注意到社会理论本身就是推动社会进展的重要元素之一。因此社会研究不能只单纯地进行描述与分析,还必须揭露社会运作的弊端,进而建立能推动解放实践的观念。在经过《启蒙的辩证》到《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之后,工具理性批判,亦即对自启蒙时代开始发展出来的支配自然的实证主义与科技,是如何地在近代开始回过头来支配人类,所进行的批判,就成为了第一代批判理论很重要的主轴之一。(5)Max Horheimer and Theodor W.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88; Theodor W.Adorno et al.,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München: Luchterhand, 1969.哈贝马斯具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关怀,还极为仰赖社会学理论,因此在研究策略上与第一代有点不太一样(6)Axel Honneth, Kritik der Macht,Reflexionsstufen einer kritischen Gesellschafts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但工具理性批判在哈贝马斯那里依然得到了深入的延续,并且他还将“解放”这个要素进一步放大,视作是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知识旨趣。(7)Jürgen Habermas, Erkenntnis und Interess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68.众所皆知,哈贝马斯后来即是致力于发展一套基于沟通理性的行动理论,以此作为从工具理性(特别是以媒介进行操控的社会系统)解放出来的手段。(8)Jürgen Habermas, “Erläuterungen zum Begriff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In Jürgen Habermas(ed.),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9, pp.571-606.
到了霍耐特这里,工具理性批判的内涵、揭露社会运作弊端的主旨、以解放作为目标或知识旨趣等要素依然受到了传承。(9)关于批判理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像是“解放”)在各世代的传承与调整的一个颇具洞见的整理,可参见周爱民《人的解放与内在批判——再思早期批判理论的“活遗产”》,《哲学研究》2020年第3期。不过,这些概念的内涵已经有了不小的转变;甚至这种转变有一定程度的偏离与转向。(10)[德]约阿斯、克诺伯:《社会理论二十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霍耐特将解放的旨趣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将批判理论的研究工作,从社会弊端的揭露转而定位为“社会病理诊断”,将“工具理性批判”转变为“承认与蔑视的批判”。
霍耐特认为,批判理论之所以要求解放,是因为人应有权利与能力追求自己所认为的美好、成功的生活;因此光是“解放”这个概念是不够的,而是应该更明确地将“美好生活”视作任何社会哲学所关怀的目标。(11)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und moralische Verpflichtung”,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Vol.51, Issue.1, 1997, pp.25-41.当然,何谓美好生活见仁见智(12)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些理论探讨,一个值得参考的文献,可参见马欣《恩斯特·布洛赫论美好生活》,《世界哲学》2019年第3期。,但人要追求美好生活必然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社会在形成过程中,许多制度的正当性,就在于承诺会将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赋予个体。然而由于各种可能的原因,社会制度常常没有尽到当初所承诺的职责,因而使个体蒙受痛苦。这种社会失能的情况,是一种社会病态,而批判理论的任务正是应该进行“社会病理诊断”。(13)Axel Honneth, “Pathologien des Sozialen.Tradition und Aktualität der Sozialphilosophie”, In Axel Honneth(ed.), Das Andere der Gerechtigkeit.Aufsätze zur praktischen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0, pp.11-69; Axel Honneth, “Die Krankheiten der Gesellschaft.Annährung an einen nahezu unmöglichen Begriff”, WestEnd—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1, 2014, pp.45-60.而整个社会自由的基础,霍耐特认为是“承认”(14)Axel Honneth, “Organisierte Selbstverwirklichung: Paradoxien der Individualisierung”, In Axel Honneth(ed.), Befreiung aus der Mündigkeit: Paradoxien des gegenwärtigen Kapitalismu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2, pp.141-158.;当代社会对承认的各种破坏,霍耐特则诊断为是一种常态性的蔑视、视而不见(Unsichtbarkeit)或“物化”。(15)Axel Honneth, Unsichtbarkeit: Stationen einer Theorie der Intersubjektivitä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13; Axel Honneth, Verdinglichung-Eine anerkennungstheoretische Studie (Mit Kommentaren von Judith Butler, Raymond Geuss und Jonathan Lear und einer Erwiderung von Axel Honneth), Berlin: Suhrkamp, 2015.
罗萨和耶姬的博士论文和教授资格论文都是由霍耐特指导的,跟着霍耐特学习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深受霍耐特的影响。(16)像前文提到的弗斯特相较起来反而没有如此深受霍耐特的影响。弗斯特的博士论文是由哈贝马斯指导的,教授资格论文才由霍耐特指导。所以弗斯特在很多时候(例如在讨论“辩护”这种明显具有沟通理性内涵的概念)会更多一些哈贝马斯的风格,例如:Rainer Forst, Das Recht auf Rechtfertigung: Elemente einer konstruktivistischen Theorie der Gerechtigkei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7。这种影响表现在他们对批判理论的旨趣与任务,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接受霍耐特的定位。
罗萨和耶姬都跟霍耐特一样,相对少提及“解放”,而是更多聚焦在“美好生活”上。但与霍耐特不太一样的是,罗萨和耶姬都对“美好生活”有很直接的讨论。由于生活是否美好常被认为是很主观的事,所以在批判理论第一、二代那里,究竟解放人类之后要怎么样,或是在第三代那里,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都常避而不谈。但这个被避而不谈了三个世代的问题,恰恰被罗萨和耶姬认为是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出发点。(17)其实不只罗萨和耶姬,就连弗斯特也将美好生活视为当代批判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不过由于主题与篇幅限制,本文不拟讨论弗斯特在这方面的看法。关于弗斯特对美好生活的讨论,可参见Rainer Forst, “Kritik, und wie es besser wäre”, In Rahel Jaeggi & Tilo Wesche(eds.), Was ist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pp.150-164。
罗萨认为,正是因为“美好生活”是一个禁忌话题,却又偏偏是所有人都认为很重要的主题,所以长期以来许多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相关讨论,都沦于“资源拜物教”的困境,亦即都只关心如何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对物质资源进行最大化的分配,至于美好生活都视为个人的事(亦即所谓的美好生活的“私人化”),不予置评。(18)[德]罗萨:《分析、诊断、治疗: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胡珊译,《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这些探讨却从来没有认真分析过为什么物质资源越多生活就会越美好。从经验现实来看,很多例子都可以指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并没有让生活真的更加美好。(19)Hartmut Rosa et al, Weil Kapitalismus sich ändern muss,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4, p.27.若对美好生活问题视而不见,批判理论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
耶姬也持同样的看法。她指出一件在批判理论,乃至于所有至今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当中(20)耶姬宣称她的批判理论是一项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的计划(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51)。不过,究竟“社会理论”和“社会哲学”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她并没有非常细致地交代。她提过,她将社会哲学视为实践哲学下的一个对社会事物进行时代诊断的哲学研究,而社会理论是分析社会事物的最重要的一个范畴,亦是社会哲学的主要基础(参见Rahel Jaeggi and Robin Celikates, Sozialphilosophie: 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C.H.Beck, 2009, p.24)。也就是说,“社会哲学”应是包含了“社会理论”的一个较为广泛的范畴,而她的研究则属于“社会理论”这个基础层面。不过,耶姬本人对社会哲学的讨论更多一些,至于“社会理论”这个概念的使用相对来说较为随意。笔者曾参与耶姬的“社会哲学导论”的讲堂课,课堂上耶姬称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等概念有很大程度的重叠;这也足见她并无意将这些研究领域之间进行壁垒分明的区分。但这些概念之间是否真的有她所谓的层次关联,也不是不用商榷的。所以,虽然她的理论就其极为强调经验面向的方面来看,无疑属于社会理论,但对她而言社会理论究竟是什么,与社会哲学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其实也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深究的。,以及在日常生活里,都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又很矛盾的事:一方面,人们常认为生活要怎么过才会是美好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没有什么好评论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常抱着哈贝马斯所谓的“伦理的节制”(ethische Enthaltsamkeit)的态度,亦即认为学者必须节制自己对美好生活下价值评论。但另一方面,人们总还是对他人的生活有各种指指点点。例如在当代中国,“都大龄了还找不到对象结婚”,是常听到的唠叨。但就人口学来看,婚姻也的确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不能仅视作私人的事。(21)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11.所以美好生活不是不能评断的。因此和罗萨一样,耶姬也断言,当代的批判理论首先必须要是以美好生活作为出发点的批判,必须正视美好生活问题,否则批判理论是无法具有当代现实意义的。(22)Rahel Jaeggi, “Objektivitätsansprüche Kritischer Theorie heute”, In Albert & Steffen Sigmund(ed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Sonderheft 50, 2010, pp.478-493.
除了“追问美好生活”被第四代批判理论当作共同的出发点之外,对于“何谓批判”这个问题,罗萨和耶姬也表现出高度的共识。在罗萨那里,批判的关键词是“可以是另一个样子的人类生活”(23)Hartmut Rosa, “Kritik der Zeitverhältnisse.Beschleunigung und Entfremdung als Schlüsselbegriffe der Sozialkritik”, In Rahel Jaeggi & Tilo Wesche(eds.), Was ist Kritik?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pp.23-54.;而对耶姬来说,可批判性的前提在于“可以转变的人类实践”。(24)Rahel Jaeggi, “Was ist Ideologiekritik?”, In Rahel Jaeggi & Tilo Wesche(eds.), Was ist Kritik? ,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pp.266-295.这两种说法其实差不多是同义的。
罗萨和耶姬都指出,虽然不论是批判理论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批判”都是很常见的一个词汇概念,但这个概念是有适用范围的。例如“今天天气很糟糕”,我们可能会抱怨,但不会因此就批判地球。因为原则上天气是晴是雨不是人为的,人也无法决定与改变。但像是“男女同工不同酬”一事,完全是人为的结果,而且明明人们可以换另外一种做法、造就另一种结果,却不这么做,那么这就是可批判的事。所以批判理论的主旨不只在于进行社会病理诊断,而更在于呈现出内在于人类实践当中各种可以改变的可能性(因此耶姬将批判理论的批判,称作一种“内在批判”)。(25)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261.改变当然可能变好,但也可能原地打转或变坏(或用耶姬近来着重发展的一对概念术语来说:我们的社会生活可以“进步”,但也可能会“退步”)。所以“批判”必然需要同时担负规范的建立与诊断的进行。在批判理论第一代那里,诊断的工作做得比较多,但也因为欠缺规范的建立而给人一种悲观的绝望感。(26)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740.在第二代那里,规范的建立是让人满意的,但也因为太过强调规范性,使得第二代的批判理论多少让人觉得与现实情况有些距离。(27)Rahel Jaeggi, “Objektivitätsansprüche Kritischer Theorie heute”, In Gert Albert & Steffen Sigmund(eds.), Kölner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und Sozialpsychologie, Sonderheft 50, 2010, p.486.第三代的批判理论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尝试,但我们可以明显发现,霍耐特最后依然走向“规范重构”,而在社会诊断方面做得差强人意而已。(28)参见郑作彧《承认的社会构成》,《社会》2018年第4期;郑作彧《批判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自由概念及其不足》,《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于是,对这两方面工作的同步进行,就被罗萨和耶姬视为新世代批判理论必须达成的任务。
从常识上来判断,照理来说规范任务应先于诊断任务,因为要进行诊断,必须要有个用于诊断的标准。但罗萨和耶姬的做法却相反。事实上,在霍耐特那里就已经指出,我们并不需要确认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健康的,也能够知道什么样是生病了。(29)Axel Honneth, “Die Krankheiten der Gesellschaft.Annährung an einen nahezu unmöglichen Begriff”, WestEnd—Neu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Vol.1, 2014, pp.45-60.所以罗萨和耶姬的批判工作都是先从社会诊断开始的,亦即探讨人们在当代社会中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点上,罗萨和耶姬基本上还是有共识的,然而两人却已经于此开始采取不同的分析路径,为双方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三、异化诊断
罗萨和耶姬都有个特色,就是他们的社会诊断工作都不是先从经典文献着手,而是从日常生活的观察出发。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许多令人蒙受痛苦的现象,都来自一种根源,就是与世界脱离开来、被排除在世界之外,这使得现代人常常感觉自己活在一个自己不存在的世界。这个现象在批判理论第一代那里被认为是工具理性的后果,第二代认为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第三代则称为蔑视、视而不见或物化。但这些概念都太过学术,并不是日常生活当中一般大众会用来描述自身苦难感的词汇,因此难免可能会有学者以超然的态度给予指导、但却脱离人们实际日常生活感受的问题。但耶姬另外找到了一个概念:异化。
异化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厚学术内涵的概念,甚至在学术界都有点被滥用了。但就像“意识形态”一样,至少在德国,异化已经进入到日常语汇当中,是一般大众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便没有什么哲学知识基础也常会用到的词汇,这让该词汇在学术讨论之外被赋予了很丰富的经验内涵。异化概念可以提供一个其他批判理论概念很难给出的好处,就是用今天的日常生活的经验表述来翻新异化的理论内涵。(30)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14.
而在日常生活各方面的表述中,耶姬整理出了用“异化”这个词汇来进行指称的七种情境(31)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21.:(1)没有基于自己的需求活出自己的面貌。(2)做着虽然没有人逼迫、也是自己要去做,但实际上并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3)与自己的出身背景(如自己所属的家庭、与自己宛如生命共同体的伴侣)脱离、断开来了。(4)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泯灭了人情味、人的性质,让人的关系变成如事物一般(Versachlichung)。一定程度上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即在指这种情况。(5)由于社会分化造成的劳动分工、生活领域碎片化,让人的生活常常只能局限在某专门领域,让自己变得破碎了,不再是整全的人。(6)制度系统的强制性太大,消灭了独立的行动空间。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的“铁笼”就属于这种情况。(7)令人感到无比荒谬、毫无意义的经历,也会被现代人说是一种异化的情况。比如我们观看一场足球赛,自己支持的队伍表现极差、被对方痛宰,那么这场足球赛就会让自己有异化感。所以德国一般报章杂志上,在重要足球赛后常会出现“异化”这个词汇。
这些情境,都让主体感觉与自己和世界相异开来,因此用上了“异化”这个词汇来描述。同时耶姬强调,由于主体必然是在世存有的主体,我就是在世界当中的我;自我关系就是世界关系。所以自我异化同时也是一种世界异化,即与我产生相异开来的关系,必然同时也是一种与世界相异开来的情况。(32)例如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37。这让耶姬进一步在学术层面上讨论异化时,不是局限在这个词汇本身来进行概念史耙梳,而是从探讨世界关系的哲学思想出发。因此耶姬接下来的讨论出发点不是一般谈到异化时首先会想到的马克思或黑格尔,而是在其导师霍耐特的影响下,从卢梭出发。(33)与霍耐特早期在柏林自由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深受挚友社会家约阿斯(Hans Joas)的影响所以专注在社会学理论工作,以及中期自随哈贝马斯工作开始多以黑格尔哲学当起点的取向有些许不同,近期的霍耐特还常常特别强调卢梭的重要性,认为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应追溯到卢梭那里去。就连“承认”这个概念,他原先以黑格尔为起点,最近更强调其概念内涵起源于卢梭。参见Axel Honneth, Anerkennung: Eine europäische Ideengeschichte, Berlin: Suhrkamp, 2018。而耶姬的理论工作在这方面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霍耐特的影响。参见Rahel Jaeggi and Robin Celikates, Sozialphilosophie: Eine Einführung,München: C.H.Beck, 2009, p.14。耶姬认为,卢梭指出了文明的发展让原本处于自然世界里的人类脱离了自身的本真性与需求的说法,就是一种标示了异化情境的诊断。这种脱离感,后来在黑格尔、克尔凯郭尔、马克思乃至于海德格尔的相关讨论中都可以看到。耶姬整理了这些理论之后总结指出,异化所指涉的不悦感,多是三种问题:(1)失去意义、无能为力的感觉;(2)蒙受不自由或他律的支配关系;(3)产生了缺乏关系的陌生性。这让异化不只是在描述一种相异开来的情况,也是一种需要批判以对的问题。(34)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44.但耶姬强调,要异化,即与世界相异开来、断开关系,同时也意味着自己与世界必须原先是有关系的,而且人作为在世存有,也必然始终都与世界有关系。但由于各种原因,当代社会的人常常与世界处于一种原本应该同一、但却变成对立且冷漠的断离关系。于是,在对当代社会进行诊断、并以此反思与充实过往的异化研究文献之后,耶姬认为异化最终标示的其实是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slosigkeit)的情境,这也成为耶姬式的异化概念定义,亦是当代社会生活遭受到的最重要、最严重的问题。(35)关于耶姬的异化理论的一个深入浅出的中文文献介绍,参见闫高洁《“无关系的关系”——拉埃尔·耶吉的异化理论述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9年第1期。
罗萨也同意耶姬的异化诊断与异化定义。不过,耶姬的异化诊断其实还不够完备,因为耶姬并没有回答为何现代社会尤其会造成异化。这无疑是一个经验的社会分析的问题,而这就是明确以社会学为主要研究出发点的罗萨可以进行的工作了。罗萨最初是以政治哲学研究起家的,尤其是对泰勒(Charles Taylor)的政治哲学思想的剖析。(36)Hartmut Rosa,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1998.他对泰勒的诠释甚至对耶姬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37)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194.不过后来罗萨转向社会学理论,并以“加速”为主题,建立了一套社会加速理论。(38)受限于篇幅与主旨,本文不拟对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进行介绍。对此一个比较完整的讨论,可另外参见郑作彧《社会的时间:形成、变迁与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180页。但加速不是罗萨真正关心的主题,他只是想从这个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现象出发,尝试通过分析加速现象掌握现代性的核心逻辑,以此作为罗萨版本的批判理论的出发点。(39)Hartmut Rosa, Weltbeziehungen im Zeitalter der Beschleunigung: Umrisse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skritik, Berlin: Suhrkamp, 2012.而在他的社会加速理论完成时,正好耶姬也完成了她的异化研究。因此罗萨便尝试以“社会加速”作为一个经验分析基础,将耶姬的异化概念加以运用,进行更具体的呈现。(40)罗萨探讨社会加速的教授资格论文与耶姬重构异化概念的博士论文,正好是同一年(2005)出版的。但这倒不是说罗萨完全是因为受到耶姬的影响所以才进行异化分析的,因为早在他剖析泰勒哲学的那本博士论文里,就有专章探讨异化,明确宣称异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病症。参见Hartmut Rosa, Identität und kulturelle Praxis: Politische Philosophie nach Charles Taylor,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1998, p.197。不过罗萨的确当时并没有对异化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且后来在讨论异化时已全盘接受耶姬的定义,参见[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4-145页。
在罗萨那里,加速意指“相同事务量的处理时间缩短”,或“同样时间间隔中要处理的事务量增加了”。(41)[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追求动态稳定而造成的现象。(42)Hartmut Rosa, “Kapitalismus als Dynamisierungsspirale-Soziologie als Gesellschaftskritik”, In Klaus Dörre et al(eds.), Soziologie-Kapitalismus-Kritik-Eine Debatt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9, pp.87-125.加速不全然是不好的,因为加速无疑为人类生活带来许多便利。但人作为一种向死而生的在世存有,如果将处于世界当中绽出的时间都缩短了,那当然就会产生自己与世界断离开来的情况,亦即造成了异化。简单来说,复印机缩短了复印文件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很便利的加速;但如果连谈恋爱、结婚这种丰富了生命的时间也缩短(而且现实情况是,真的也有缩短的趋势(43)关于这方面的经验分析,可参见胡珊、郑作彧《生命历程青年阶段的父辈嵌染》,《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2期。),那就会是一种造成异化的加速。罗萨认为,如果我们参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层层分析来区分出不同类型的异化的做法,来探讨在世存有的时间被削减所带来的异化,那么也至少可以区分出五种异化类型。(44)[德]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18页。
第一,空间异化。人的存在,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寓居于空间当中。这种寓居需要时间来熟悉这种空间。但在加速社会中,要么是自己得不断迁徙,要么是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空间不断拆组重建,因此人们越来越容易对自身所处的空间产生相异的陌生感。第二,物界异化。一旦人与空间异化开来,那么当然也会与空间当中的物相异化开来。而且在当代社会,各种物质产品的汰换速度非常快,我们往往还没熟悉手上的产品,新一代的产品就又出现了。而且,现代社会很多物质产品容易损坏,维修价格又常比买新的还贵。这迫使我们与物的世界产生异化。第三,行动异化。由于我们和空间、物都异化开来了,因此我们也常常感觉自己不能随心所欲。例如我们常不得不断换新手机,每款手机功能都不尽相同,操作方式也常有差异,因此我们总是得研究手机该怎么用,不知道究竟是我们在用手机,还是手机在用我们。第四,时间异化。正常情况下,时间流逝感与体验丰富度成反比。体验越是丰富,时间感觉就会流逝得越快;越是贫乏,越是度日如年。前三项异化,使得现代人常常体验很贫乏,但又觉得时间一下就过完了。从许多上班族对无聊但又短暂的周末的抱怨便可见一斑。最后,自我异化。当我们在前四项情境都处于异化状态,最终会造成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该做什么,觉得自己过着茫然又焦虑的人生。
罗萨的异化分类将耶姬的异化定义以很贴近日常生活的方式加以具体化,变得更丰富了。当然,这种经验的异化分析无疑还可以从各方面再进行下去,但无止尽地进行各种异化的分类学工作,对批判理论来说没有太大意义。一旦异化被一致同意是社会病态现象时,罗萨和耶姬的下一步任务当然就是建立一套能用于批判(亦即指导社会朝向进步来发展)的标准。在这方面,两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如果异化是一种有问题的世界关系,那么要批判异化,就必须思考没有异化的世界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世界关系。然而从同一个出发点开始,两人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前文已提到,耶姬根本上认为批判理论是一种社会哲学,而社会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所以她从实践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如何建立能克服异化的世界关系。而从罗萨对“在世存有”的关怀就可以清楚看到,他更多基于现象学来进行思考。于是从这里开始,罗萨和耶姬的批判理论发展路径分道扬镳了。
四、化用的生活形式
虽然耶姬清楚指出,主体与世界处于“没关系的关系”、破坏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即异化),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问题,也是批判理论最需要讨论的主题,而罗萨则用对社会加速的分析在经验层面上丰富了耶姬的异化批判,两人的研究看起来彷佛相辅相成;但实际上,耶姬对罗萨的做法是有所怀疑的。加速的确是当代社会的特质之一,但也只是“之一”,它并不是一个多么触及社会运作根本原理的概念。耶姬提到过,在罗萨提出异化加速理论之前,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其实就很深刻了;言下之意就是认为加速在异化分析上并不是一个有什么特殊优势的切入点,也很难让人想见如何从中发展出能掌握住人类生活根本的批判标准。(45)Nancy Fraser and Rahel Jaeggi, Capitalism: 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2018, p.172.相比之下,罗萨早期一篇谈论生活形式是否能有一个评判尺度的文章,还更有可参考和可发展性,因此耶姬认为更值得青睐。(46)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Berlin: Suhrkamp, 2014, p.40。罗萨的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到罗萨的一本论文集当中,参见Hartmut Rosa, “Lebensformen vergleichen und verstehen.Eine Theorie der dimensionalen Kommensurabilität von Kontexten und Kulturen”, In Hartmut Rosa(ed.), Weltbeziehung im Zeitalter der Beschleunigung.Umrisse einer neuen Gesellschaftskritik, Berlin: Suhrkamp, 2012 [1999], pp.19-59。因为罗萨指出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们要讨论美好生活是否受到什么阻碍因而无法实现,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直接去讨论生活本身要如何进行评判。于是,“生活形式”便成为耶姬建立批判准则的核心主题。(47)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耶姬是因为罗萨所以才去讨论生活形式的,而只是说罗萨对生活形式的讨论是耶姬仰赖的文献之一,因此也是耶姬与罗萨的共识之处。早在罗萨之前,阿多诺就已经在如《最低限度的道德》当中对生活形式有过深入的讨论。一定程度上阿多诺的哲学才是耶姬主要的理论养分来源。参见Rahel Jaeggi, “‘Kein Einzelner vermag etwas dagegen’ Adornos Minima Moralia als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In Axel Honneth(ed.), Dialektik der Freiheit-Frankfurter Adorno-Konferenz 200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pp.115-141。
“生活形式”在哲学里头已是一个有过不少讨论的概念,像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哲学里就在一种定义不清、但又似乎内涵深刻的情况下使用了“生活形式”一词。但耶姬一如往昔地并不直接从哲学文献去追溯,而是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思考可以被称作“生活形式”的各种情况具有什么共同的本质。耶姬指出,我们今天有很多指称生活的概念,像是生活风格、生活导引(Lebensführung)、文化等等,但这些概念常夹杂着一些非生活的内涵(例如“文化”太过宽泛,还包含了如雕塑艺术等物质实体;生活导引又太强调个体主观上有意识地积极实现目的的面向,但生活不总是那么有意识,而是也有自然态度的成分)。耶姬认为,若我们真的去直面生活本身(也就是耶姬常强调的“把生活形式当作生活形式来看待”),那么生活在本质上无非就是我们通过无数实践活动所过出来的。所以耶姬很明确地将生活形式定义为“社会实践的总和”(Ensembles von sozialen Praktiken)。
当然,“社会实践的总和”这个生活形式定义还太过单薄,所以耶姬还加上许多附带定义。(48)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94.例如实践之所以是“社会的”,是因为构成生活形式的实践都必然镶嵌在社会当中,具有规范、制度的条件。同时这种实践还要是能重复进行(而非偶然为之)的。但就算补充了许多附带定义,这种生活形式概念看起来似乎也还是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耶姬却从这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定义延伸出几个能用于批判理论的命题。
首先,不论我们在实践之前有没有先在心中有所规划、有没有清楚预设最后要做到什么事,我们的实践都是为了要实现、完成某些事。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刷牙洗脸,是为了让自己不要蛀牙、不看起来蓬头垢面;去餐厅,是为了要吃饭、填饱肚子(即便可能我们进餐厅时还不确定要点哪一份餐点)。但要完成事情,就表示事情不是本来就处于完成状态的,我们必须解决各种问题才能进行实现。生活,正是各种通过问题解决而构筑起来的实践的总和。于是,“解决问题”便被耶姬提升为生活形式的重点议题。
其次,所谓的“问题”,可以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任务,也可以意指我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在社会实践当中,这两者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中遇上各种问题本身不是什么很糟糕的事,因为生活当然会有问题,实践就是要解决问题,正是“解决问题”这种实践构成我们的生活。但耶姬提到,如果“解决问题”这件事遇上了问题,亦即她所谓的“二阶问题”(Probleme zweiter Ordnung),那可能就是很糟糕的事了。(49)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249.因为二阶问题表示我们的生活形式本身出了内部问题,这种问题自然就成为了作为内在批判的批判理论所针对的问题。
但我们的生活形式如何能解决问题,又为何会出现二阶问题呢?耶姬在这里提出第三个命题,即: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学习过程,一个学着如何把问题当作问题提出来,以及学习如何进行反应的过程。二阶问题则是阻碍了学习,使得人们在生活中无法把问题当作问题来提出并反应的麻烦。阻碍了学习、阻碍了问题的提出与反应,就是阻碍了改变的可能性,进而也就阻碍了我们朝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就像如果我们遇到了旱灾,农作物歉收,那么我们可能会学习到该如何通过建立粮仓、储备粮食,来解决问题,所以批判理论不会把旱灾本身视作问题。但如果因为朝廷奸臣刻意欺上瞒下,让皇帝不知此等大事而迟迟不作为,造成大饥荒,这就是阻碍了学习的二阶问题,也是批判理论所要批判的问题。(50)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243。“旱灾建粮仓”这个例子是耶姬自己举的。不过为了贴近中国文化,因此本文又加入了“奸臣”“皇帝”这些角色改写了耶姬的例子,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生活形式是否能发展出学习过程,便是耶姬认为批判理论判断人是否具有朝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的尺度。
耶姬既提出了异化,完成了时代诊断工作,又以生活形式为主轴,从日常生活的经验当中分析出批判理论的准则,无疑履行了批判理论第四代为自身定下的任务,照理说是一件颇值得称道的贡献。然而,在“学习”这个关键要点上,耶姬的探讨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耶姬认为,“学习”之所以能够解决问题、构筑出生活形式,是因为它是一种“化用”的活动(51)Rahel Jaeggi, 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4, p.131.;而正是化用让生活形式得以避免异化。“化用”的德文原文Aneignung有三个意思:占据、学习吸收、掌握运用。耶姬在使用这个概念时,是同时包含这三个意思的,亦即她指涉的是一种我们将世界吸收内化进自身当中,并因此能自在地加以运用的活动。(52)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56.化用之所以能避免异化,是因为如果异化是一种“没有关系的关系”,一种让我们与世界之间相异开来因此感到无能为力的处境,那么化用就是一种重新吸收世界的活动,让世界重回与自我的关系。化用让我们能够掌控(Verfügenkönnen)世界。虽然这不是说我们化用是为了要去支配世界,但化用的确可以让世界转化成有助于形塑我们自身的生活形式的资源。通过化用,我们就可以与世界具有一体性,拥有解决问题的资源与能力,因此不再异化,也能有实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化用”是耶姬的批判理论的核心关键词,在她迄今的主要著作中经常会看到她对化用概念的强调,显然她认为化用是人类朝向美好生活前进的最重要的能力。(53)参见Rahel Jaeggi, “Seine eigenen Gründe haben (können).Überlegungen zum Verhältnis von Aneignung, Fremdheit und Emanzipation”, In Julian Nida-Rümelin & Elif Özmen(eds.), Welt der Gründe, Hamburg: Meiner, 2012, pp.968-985。阻碍了化用,就是阻碍了学习,会造成异化与退步的生活形式。(54)参见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55。耶姬的批判理论,根本上就是对我们应有化用能力的生活形式进行诊断的理论。但化用概念让批判理论第四代学圈的不少人感到很不安。例如前文提过的采利卡特斯就直接质疑,世界不总是会顺从我们的化用,如果我们的化用、我们的学习过程,实质上对我们的世界产生了强制性,甚至产生了暴力和牺牲,这难道是批判理论想要的结果吗?(55)Robin Celikates, “Forms of Life, Progress, and Social Struggle”, In Amy Allen & Eduardo Mendieta(eds.), From Alienation to Forms of Life: The Critical Theory of Rahel Jaeggi,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43.除了采利卡特斯之外,对耶姬提出最尖锐批评的,就是罗萨。罗萨认为,耶姬完全弄错了人类生活的生成起源,所以才会提出“化用”这个危险的概念。(56)此处需要指出一件事:不论是化用概念,还是将化用与异化对立起来的作法,都不是耶姬独创的。至少黑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就已经提出过化用与异化的对立关系了。马克思也提到过这种概念(只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Aneignung通常不是翻译成“化用”,而是翻译成例如“占据”)。关于化用与异化的概念对立的详细概念史考察,参见Sybille De Le Rosa, Aneignung und interkulturelle Repräsentation,Grundlagen einer kritischen Theorie politischer Kommunikatio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2, pp.51-77。耶姬早先便深受马克思的提法的影响,参见Rahel Jaeggi, “Aneignung braucht Fremdheit: Überlegung zum Begriff der Aneignung bei Marx”, Appropriation Now! Texte zur Kunst, Vol.46, 2002, pp.60-69。不过因为耶姬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化用与异化,因此批判理论第四代学圈在批评化用概念时,都仅专门针对耶姬的定义。
五、共鸣的世界关系
虽然罗萨很早就对生活形式有过探讨,但他认为,若现代人无法实现美好生活,是因为人与所身处的世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出现了异化关系),那么我们应该直接考察的不是生活形式,而是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根本生成起源:世界关系。而对世界关系的考察应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人究竟是如何在世界当中生成出生活形式的。这牵涉到人如何以“在世存有”这个自身本质作为基础,发展出人类生活。在这方面,罗萨从[特别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式的]现象学和[主要是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的]哲学人类学出发。第二,人类实际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世界关系,以及这样的世界关系应如何导向成功、美好的生活,以及因为什么原因而让生活失败、蒙受痛苦。这意味着世界关系会随着不同的社会与历史背景而异,因此必须进行经验考察;这就是一个必须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问题。因此罗萨宣称,他的批判理论本质上是一种“世界关系社会学”。(57)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70。值得一提的是,罗萨现在除了是耶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之外,也同时任埃尔福特大学韦伯高等文化社会研究院的院长。在罗萨的争取下,埃尔福特市政府出资专门为韦伯高等文化社会研究院建一栋全新的研究大楼,预计2022年完工。这栋大楼届时将由罗萨命名为“世界关系楼”,足见罗萨在创建一门“世界关系社会学”方面的野心。不过不只罗萨,耶姬也在2018年获得了德国某企业赞助的两百万欧元,让她在洪堡大学建立“人文科学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心”,以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性研究为主旨。这么大笔的经费赞助也让耶姬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在当时登上了德国新闻版面。至少从所获得的研究资助来看,也可以瞥见批判理论第四代在当代的活跃程度。
人作为在世存有,首先是作为一种生物躯体而处于世界当中的;所以罗萨从对“身体”这个要素的考察出发。不过,人最初还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性的身体,而是首先作为一个胚胎,与胎盘、羊水一起在母亲子宫里。胚胎与母亲是相连的,但又不是母亲本身,可以用自己的举动与母亲对世界的各种感受进行回应(也就是所谓的“胎动”)。而胚胎,人最初的型态,既称不上是主体,但也不能说是客体。罗萨借用奥地利文化评论家马可(Thomas Macho)的术语,将之称为“既非客体”(Nobjekt)。(58)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87.“既非客体”的状态不只在母亲肚子里,就算出生后,我们首先也是被托在手中的,一双不是自己的、但却因为托住了自己的生命而与自己的手有同等意义的手。然后大口地把世界里的空气吸进自己的肺里,再把自己肺里的空气大力呼进世界(并且正是在一呼一吸的过程中形成了婴儿降生的哭泣声)。我们的皮肤会感受温度而进行毛孔收缩,耳膜会接触空气而震动。我们产生了知觉,但是正是因为我们降生进世界、作为与世界相互交缠的既非客体,所以才能够产生知觉。不只是知觉,还有感受。感受从来就不是内心凭空出现的,也不是仅停留在内心的。我们会因为环境的阴森气氛而感到恐惧,然后我们的皮肤会起鸡皮疙瘩把感受表达出来;或是因为一件事而难过或过于高兴,然后用眼泪把我们的悲伤或欢乐流露出来。
空气、环境的温度与湿度、阴森、舒服或难受的事件,都不属于我们本身,也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但正是因为它们,构筑出我们的知觉,进而构筑出我们的主体意识。我们总是因为世界而有主体意识。甚至罗萨宣称,根本上,主体与客体的差异不是所有知觉感受的前提,而是其结果。(59)Hartmut Rosa, Unverfügbarkeit,Salzburg: Residenz Verlag, 2018, p.11.主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是我们能向世界敞开,世界也向我们敞开。这种敞开不代表我们和世界真的是一体的,就像胚胎不是母亲,母亲当然也不是胚胎。但正因为不是一体的,我们才会被激起自己的反应、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且这些反应与回答也同时构成我们自己。这种相连却又相异,相异却又因各自的回应而相连在一起的世界关系,一种人镶嵌在世界中、却正因这种镶嵌而构筑出独有的自我的世界关系,罗萨称为“共鸣”。共鸣,让我们因为感受世界因而有所心动,并且被世界触动后激起对世界的回应。所以罗萨指出,共鸣,是一种“感动”(Emotion)或“刺激”(Affizierung)的过程。(60)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298.
共鸣不只是让我们与世界彼此敞开、彼此产生关系而进一步产生感动或刺激,而且也因为世界回应了我们,因此让我们在世界中的各种生活能够得到支援。这种支援不是我们支配与利用世界,而是世界用它自己的方式给予回应,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方式运用世界的回应。同时我们的运用对世界来说也是一种回应,让世界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们的回应。就像教师用自己的方式分享他的知识,学生以自己的方式吸收了教师所述;然后教师获得了学费与教学成就感,学生则获得了实现自我所需的知识与能力。或是农作物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养分,变得茁壮,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栽种与食用农作物。
为了保证、乃至提升共鸣的世界关系,人类社会发展出了许多共鸣领域;罗萨将这些共鸣领域称为“共鸣轴”(Resonanzachse)。罗萨对大量经验研究进行整理之后,认为当代社会至少可以区分出三种共鸣轴。(61)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297, 341.第一种是“水平共鸣轴”,它指的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共鸣,例如理想上美满和乐的家庭,今天主流上被认为较佳的民主政治体制,乃至于友情、爱情,皆属于此种共鸣。第二是“垂直共鸣轴”,牵涉到的是神、宇宙、永恒等超越性的范畴。就像我们在庙里拜拜,常会因宏伟的寺庙建筑、平静的诵经声而找到心中的平静,或是深夜抬头望向无涯的星空,感受到宇宙的伟大而莫名地感动;这些都是面对超越性的世界而得到的共鸣。第三是“对角共鸣轴”,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所处环境中的各种物。但对角共鸣轴还不只是物本身,而是也包含我们与物的各种相互运用。例如课堂上的理化实验让我们更了解物质世界的运作原理,或甚至各种球类运动项目竞赛(“球”当然也是一种物)让我们激动不已,也被罗萨算在对角共鸣轴的范畴中。家庭、恋爱、宗教、星空、球赛……正是这些人类当代社会发展出来的各种共鸣轴,丰富我们的共鸣的世界关系,也丰富了我们的人生,得以成就我们的美好生活。
对罗萨来说,共鸣关系既是对人类本质的描述,也可以为批判理论提供规范准则。(62)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747.因为,如果异化是“没有关系的关系”,那么共鸣就是一种“有关系的关系”(bezogene Beziehung);也就是说,批判理论的时代诊断,就是一种对共鸣关系是否良好持存的考察。(63)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305.例如,学校课堂应是一个带来共鸣的场合,但在某些社会,学习变成单纯的成绩竞逐,课堂成为老师赶进度、学生赶笔记的地方,没有任何共鸣。这就是课堂异化了,也是需要批判的现象。(64)关于当代学习情境造成的异化世界,进一步的详细探讨参见郑作彧《我们这个马赛克照片世界:当代真实的社会建构形式》,《广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共鸣轴的社会学分析,于是成为批判理论的研究任务。显然,罗萨在这里不愿采取耶姬将“化用”与“异化”对立起来的做法,而是宁愿提出自己的“共鸣”与“异化”的对立。原因在于,罗萨认为,化用恰恰就是破坏了共鸣、造成异化的元凶之一。罗萨的这项宣称基于几个论点。
首先,罗萨强调,他的“共鸣”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65)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285, 755.在共鸣关系中,人们可以进入世界产生共鸣状态,但也可以脱离世界产生异化状态。毕竟如果一直处于共鸣状态,意味着一直要拥抱与回应世界,那也是会累的;而异化状态可以提供自我反思与休息的空间,有时候不但不是不好,甚至是必要的。这同时也是说,在罗萨这里,与共鸣对立,会产生问题,因此需要批判的异化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
其次,既然具有对立性质的共鸣和异化都是一种关系,那么它们各自又是什么关系呢?罗萨指出,“共鸣”不是“回音”或“和谐音”,甚至共鸣反而还可以是“不和谐音”。他的意思是,共鸣是每个人、事物在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表达与回应。就像我们写了一篇论文,都会希望得到共鸣,但此时我们希望的不是其他人把我们的论文复述一遍(回音),也不是一味对我们歌功颂德(和谐音),而是希望读者用他们的体验与想法回应我们。这些体验跟想法不会与我们自己的体验和想法完全一致,甚至读者提出的可能会是批评,但这种回应才是让我们获得存在感、并且有可能精进改善我们论文的共鸣。
第三,所以共鸣不是、也不追求和谐,反而要以不和谐,或是罗萨所特别强调的“不受掌控”(Unverfügbarkeit)作为前提。而且共鸣关系中的状态也并不总是愉悦美好的,也可能是恐怖、哀伤、难过的,但正因为各种不受掌控的可能性,才让我们有更充实的主体性。就像一场球赛之所以刺激好看,就是因为我们不看到最后不知道胜负;一部凄美的电影我们可能看得伤心哭泣,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预料到剧情会有如此令人感到遗憾的走向,所以即便伤心哭泣我们也还是因此有一段精彩的观影体验。正是因为球赛走向与电影剧情的不受掌控,所以才会产生共鸣。不过,不受掌控并不是放任不理或任凭肆虐的意思。当我们说共鸣关系需要不受掌控时,也同时意味着“有关系”这件事本身是已被掌控住的。当我写了一篇文章,想听某人的意见时,对方的想法必须是不受掌控的,这样才会提供一种能让我有所改进的反馈;但这前提是我和对方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我们能联系彼此,亦即我们能掌控住与彼此的关系。所以不受掌控,意指不以支配对方为目的,以及不受对方支配的关系,而非全然无关的状态。
第四,反过来说,任何泯灭了差异性、任何企图进行掌控的关系,都是一种造成回音、和谐音、甚至是消灭声音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异化关系。(66)Hartmut Rosa, Unverfügbarkeit, Salzburg: Residenz Verlag, 2018, p.60.没有球迷可以忍受球员们打“假球”,因为一场胜负早已被掌控好的球赛无疑只会让球迷陷入异化状态;一部电影我们在第56次观看时想来不会在结尾处再感动得痛哭流涕了,因为我们已经对剧情的推进早就了然于胸了,可能看得都有“无聊”这种异化的感觉了。这里,罗萨联结上他之前的社会加速理论的一项诊断:社会不断追求加速,是现代社会企图“扩大作用范围”(Vergrößerung der Reichweite)的一个表现。扩大作用范围意指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想掌控一切事物,并且让掌控范围尽可能扩大。但矛盾的是,我们越是想掌控整个世界,反而因为我们消灭了世界的声音、听不到世界的回应,所以世界越来越与我们脱离关系,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失控。我们想提早获得学术成就的年龄,不断要求我们缩短读博与发表论文的时间,但却让青年人才无法静下心做学问,只能被迫不断产出平庸、毫无创新可言的作品。我们想通过基因改造掌控农作物生长速度,但基因改造食物却可能会提高我们的饮食风险。(67)[德]罗萨:《分析、诊断、治疗:晚期现代社会形态的新批判分析》,胡珊译,《江海学刊》2020年第1期。
通过一系列层层推进的论证,罗萨提出了他的批判理论的基准点:人是一种在世存有,在世存有是一种能与世界相互共鸣的关系。共鸣的世界关系,让我们得以获得各种过上美好生活的支援。没有共鸣的世界关系,首先人连主体性都无法建立;其次,任何阻碍或消灭共鸣的回音、和谐音、扩大作用范围,都会造成异化关系,要么我们因而无法获得世界的任何支援,要么我们处于各种失控的境地。如此一来,当然遑论过上美好生活。世界是人类所处环境的总和,可以是无机物、生物,当然也可以是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我们与世界相互敞开、相互回应,所以我们不会对任何事物(不只人)视而不见或蔑视。因此罗萨认为,他的共鸣概念,是一个可以比霍耐特的承认概念更加深邃、更适合作为“道德一元论”核心元素的顶层概念。(68)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p.748。罗萨这里提到的“道德一元论”,是霍耐特在和弗雷泽(Nancy Fraser)辩论时提出的术语。参见Nancy Fraser and Axel Honneth,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London: Verso, 2003.共鸣的世界关系,即是罗萨的批判理论的社会病理诊断的准则。
以此基准点视之,耶姬提出的化用概念,旨在掌控世界,这恰恰就是罗萨所批判的。罗萨尖锐地指责耶姬,认为耶姬完全忽略了早在阿多诺的“非同一性”哲学那里就已经指出化用的危险性;若从罗萨的世界关系社会学来看,化用更是会彻底地破坏共鸣。如果世界关系真的陷入异化关系了,那么,罗萨认为,我们拾回关系的做法绝不能是化用,而是“吸纳”(Anverwandlung)。(69)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100.吸纳的意思是让主体与世界在维持彼此差异性的基础上纳入关系当中。例如,一个院系要壮大发展,必须吸纳人才;而吸纳人才,就是让所有人才能发挥各自专长的情况下齐聚一堂。如果按照耶姬的论点,把人才都“化用”了,那等于是把人才都变成了院系领导的“奴隶”,那么这个院系想必就成了一个异化场所了。
如前所述,罗萨不是唯一批评耶姬的人,连深受耶姬提携的采利卡特斯也提出了和罗萨一样的质疑;但罗萨对耶姬的批评可能是最系统性的,因此也许是最为猛烈的。罗萨的批评的确也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回过头来看罗萨自己的共鸣关系社会学,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现,罗萨的理论可能也有可批评之处。
六、批判理论新走向的反思
虽然霍耐特在2018年交出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棒子,整个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了,一定程度上反映批判理论第三代已经步入尾声;但罗萨和耶姬的崛起,宣示批判理论已经进入了成熟的第四代。而罗萨和耶姬的研究既相辅相成,又互有猛烈的批评,让批判理论正是在这种切磋下愈发茁壮。厘清罗萨和耶姬的共识与分歧,无疑可以让我们更清楚批判理论的新走向。
罗萨和耶姬都同意,批判理论的目标是让人类可以朝向美好生活发展,其方式是通过内在批判来对社会进行病理诊断。而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病状之一,就是“异化”,亦即我们的世界关系处于一个“没有关系的关系”,因此蒙受着无能为力的痛苦。耶姬提出了概念定义,罗萨用此概念进行了经验分析,两人的合作一起让异化成为了批判理论第四代的核心概念。但进行社会病理诊断的判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是没有异化的美好生活,我们又该如何修复异化了的生活,两人出现了分歧。
耶姬将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划定为“生活形式”,指出生活形式应是一个可以通过“化用”来解决问题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拥有了具备化用能力的生活形式,就可以迈向美好生活。但罗萨反对耶姬的化用概念。罗萨将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划定为“世界关系”,指出良好的世界关系应是一种基于“不受掌控”的“共鸣关系”,人类社会也已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共鸣轴;但当代社会却因为各种掌控欲望或手段,造成了只有回音、和谐音,或甚至是静默的异化关系。“化用”恰恰就是造成异化关系的手段之一。罗萨认为,若要修复我们的世界关系,就必须通过“吸纳”,而绝不是化用。
“批判理论第四代”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当中的各学者的理论都还正在发展中。耶姬以“内部批判”为主旨的批判理论本身在自身学圈遭遇到的内部批判,想来对她而言并不是恶意的抨击,而是可以让她改善自身理论的养分。她后续如何回应各种质疑,是令人好奇的。同样令人好奇的是,她会不会也反过来对罗萨的批判理论继续提出批评?尤其是,罗萨的共鸣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问题的。
要批评罗萨的共鸣理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因为罗萨的共鸣理论有多完美,而是因为他在正式提出共鸣理论之前,曾数次举办学术工作坊,邀请了耶姬、霍耐特,甚至也邀请了霍耐特在美国的好伙伴弗雷泽,以及罗萨的精神导师、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加拿大哲学家泰勒等人,召集了这些世界上最顶尖的批判理论家一起专门针对他的共鸣理论进行“批斗大会”,所以罗萨早就知道他的共鸣理论有(会遇到)哪些问题。甚至在他正式提出共鸣理论的大部头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的最后,罗萨不是以总结全书与提出展望作为结尾,而是很罕见地以一问一答的方式,一一列出他的共鸣理论遇到过的批评和他对各批评的回应。许多读者想得到、想不到的问题,他都自己展示出来并给予解释了。而且绝大多数的解释,的确是无懈可击的。
然而“绝大多数无懈可击”就意味着不是全部都无懈可击,有的问题他的回应还是苍白无力的。尤其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共鸣被罗萨视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准则,但共鸣难道都是好事吗?
罗萨认为,共鸣的世界关系是人类主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所以也就是让美好生活得以可能的基本条件。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问题,因为关系社会学的研究就已经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人必然需要镶嵌在相互回应的关系当中才能存活下去。(70)关于关系社会学在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郑作彧《齐美尔的自由理论——以关系主义为主轴的诠释》,《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3期。但共鸣和关系是有边界的,一个人也许在他所属的群体可以获得共鸣,但换到另一个语言、文化、观念等各方面都相异的群体,我们很难想像还可以拥有同样程度的共鸣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共鸣有边界、世界有边界,所以一个内部充满共鸣的群体,很有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例如:为了要获得更广泛的共鸣!)去攻击其他的群体、攻击其他世界。共鸣可以让人获得支持,进而获得力量,所以当然也可以让人或群体有能力进行支配与攻击。一个恐怖的攻击场合,周边围着疯狂叫好的旁观者,对于场上的攻击者来说,他无疑获得了极大的共鸣,但对于被攻击者来说,这显然是彻底的异化。简单来说:我的共鸣,可能会是他人的异化,反之亦然。共鸣如果是一个有负面效应的概念,那它又如何能作为批判理论的规范准则呢?
罗萨的解释是,“好共鸣”与“坏共鸣”的二分,可以是一种分类方式,但不是他的分类方式。他很明确将共鸣的定义局限在“让各自不受掌控地对彼此发出自己回应之声的关系”。所以任何破坏了不受掌控、破坏了自我发声的情境,对他来说不是坏共鸣,因为在他的定义里这根本就不会被称为“共鸣”。(71)Hartmut Rosa, Resonanz: Eine Soziologie der Weltbeziehung, Berlin: Suhrkamp, 2016, p.742.但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他没有回应到“共鸣世界有边界”这个要点,所以依然无法解释“边界内的共鸣也可以是对边界之外产生破坏的力量来源”这个问题。以此而言,虽然耶姬的化用概念有明显的危险性,但罗萨的共鸣概念所暗含的危险性可能与耶姬并没有太大不同。
之所以罗萨和耶姬的批判理论都有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都将异化视为当代主要的社会病状,亦即都认为现代人的主要困扰在于无能为力,所以都在思考获得能力的途径。而这就会造成“获得的能力要多大才恰当”的拿捏问题。这其实很像“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的矛盾:我们应该要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但个人自由不能损害到公众权益;如此一来,个体自由与集体自由之间该怎么拿捏?有趣的是,其实“自由”也是贯穿整个批判理论发展的核心议题之一。批判理论第一代的重要成员弗洛姆(Erich Fromm)就以《逃避自由》一书闻名于世(72)Erich Fromm, Escape from Freedo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1.;第二代的哈贝马斯较近的著作以极重的篇幅在思考哲学对自由的讨论的变迁(73)Jürgen Habermas, 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Bd.2: Vernünftige Freiheit.Spuren des Diskurses über Glauben und Wissen, Berlin: Suhrkamp, 2019.;第三代的霍耐特也提出了他自己的“社会自由”概念(74)Axel Honneth, Das Recht der Freiheit: Grundriß einer demokratischen Sittlichkeit, Berlin: Suhrkamp, 2011;Axel Honneth, Die Armut unserer Freiheit: Aufsätze 2012-2019, Berlin: Suhrkamp, 2020.;第四代,耶姬也明确声称讨论异化问题其实就是在讨论自由问题。(75)Rahel Jaeggi, Entfremdung.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New York: Campus, 2005, p.255.如果我们直接讨论自由,自然会讨论到自由的拿捏问题(或是自由的拿捏如何可能并不是个问题),如此一来刚好就可以碰触到罗萨和耶姬错失(但又不该错失)的议题。
以此而言,也许基于批判理论的旨趣来对“自由”进行剖析,可以找到走出罗萨和耶姬所面临困境的路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像,将“自由”作为批判理论的研究主题,以此发展出更新的批判理论发展方向,加入当代批判理论学圈的讨论呢?这也许是除了从旁观察罗萨和耶姬如何继续发展他们的批判理论之外的另一个也很值得一试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