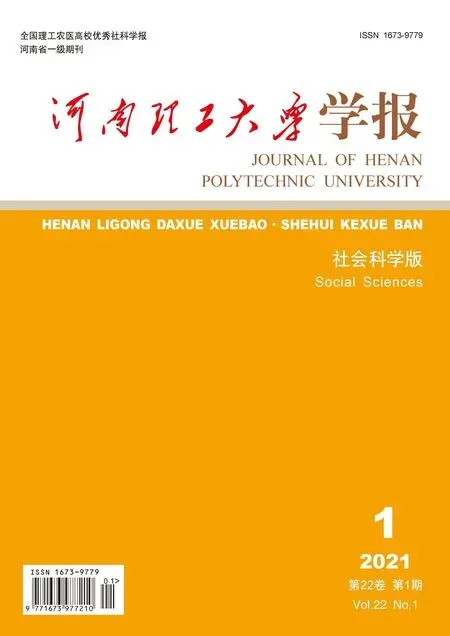叔孙通制礼再评析
——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李冰楠
(武汉大学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叔孙通,战国末至西汉初期人,曾于秦时任待招博士与博士,后于乱世中投奔刘邦,并辅佐其制定朝仪、宗庙乐,成为汉初创制礼乐的第一人。对于叔孙通及其礼制建设活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历代史书中亦有辑录,张家山汉简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亦我们提供了线索。以此史料为基础,古往今来众多人士对叔孙通及其礼制建设活动进行了探究,其评价莫衷一是:持肯定之观点者认为叔孙通以通权达变之态为汉制定礼仪,对汉初政权的巩固、发展有积极意义,如司马迁之言叔孙通为“汉家儒宗”[1]2105,后刘向[2]886、班固[2]925、王充[3]750亦承此观点,孔鲋言叔孙通“学儒术而知权变”[4]176,南宋范浚更是认为“通之有功于汉岂汗马比哉”[5]85-86,清人王夫之[6]19亦表达类似观点;持否定之观点者以叔孙通为谐俗取宠之徒,认为其制礼不过是为奉迎君主,违背了先秦儒家传统,对古礼的沦亡负重要责任,如司马光所言:“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7]128后方回[8]57、杨慎[9]105等人皆持此见。
近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多从历史背景[10]、历史影响[11]、制礼之依据[12]、制礼之内容[13]、制礼之特点[14]等方面,对叔孙通制礼进行专题性的考究、评价。孟祥才认为叔孙通是“汉初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15]275,他通过制定朝仪,使刘邦“认识到儒学的实用价值”[15]271;黄宛峰承此观点言:“儒学的复兴最早即应归功于叔孙通”,他认为叔孙通代表的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儒学”[10];罗昌繁进一步指出,叔孙通制礼著书是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仕实践”[16];而杨鑫则认为叔孙通制礼“为儒学的复兴做了准备”,但其行为模式却“背离了先秦儒家的传统”[17]。
简而言之,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叔孙通的评价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叔孙通为名副其实的“汉家儒宗”,其制礼著书并未背离儒者之基本身份;一种观点则认为叔孙通并非“纯儒”,其行为模式背离了先秦儒家之传统;一种观点则采取折中之态,认为叔孙通代表“半官方半民间的儒学”[10]。在对叔孙通进行评价时,将其与同时代之儒生进行横向对比是十分重要的。而《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描绘的叔孙通与诸儒生之间的关系则十分微妙,值得我们仔细玩味、思索。本文则拟从此角度切入,将叔孙通置于儒生群体中,通过横向比较,对叔孙通“进退与时变化”的处世之道及“度务制礼”的儒学实践进行考察与评析。
一、史料中所见之诸儒生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生群体主要有三个:其一为侍奉秦二世的博士诸儒生;其二为叔孙通之弟子;其三为鲁生。
对于博士诸儒生,《史记》有如下之描写:
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於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於虎口!”[1]2100-2101
面对陈胜领导的反秦政治暴动,博士诸儒生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极陈时务之危机与发兵之紧迫,揭示戍卒反秦之本质,却遭致秦二世的愤怒,或被降职、或被罢免。叔孙通却一改前儒之态,以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区区盗贼不足挂齿之语,凸显天下一统之局与君威之宏盛,讨得二世欢心,并受赏而拜为博士。可见,与叔孙通的“面谀”事君相比,博士诸儒生则表现出不惧君威、刚直不阿、极诚于所言的特点。
对于叔孙通之弟子,则可从以下史料得以窥见:
史料一: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1]2101
史料二: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1]2103
可见,叔孙通之弟子儒生百余人,是在秦亡之后跟随叔孙通一并降服于汉朝的。降汉之初,叔孙通并未为其弟子进言举荐,而专荐“群盗壮士”,故其弟子多有怨言。直至汉七年,朝仪首次施行并得高帝嘉赏之时,叔孙通才为其弟子进言谋职,其弟子亦大赞其为“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
对于鲁生,《史记》之描写如下:
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遂与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馀人为绵蕞[1]2102。
可见,叔孙通召集鲁生参与礼制建设时,诸鲁生对叔孙通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其中一部分鲁生选择跟随叔孙通,从而成为其制礼的重要人才基础;另有两个鲁生则对叔孙通的人品及制礼活动表现出强烈的谴责和不满。其不满原因主要有:一则,他们认为叔孙通事君众多,且皆以“面谀”上位,其行不合君子之道德风范;二则,他们认为天下初定、德化未就,兴礼起仪不合时事;三则,他们认为叔孙通所定之礼有违古制。而叔孙通亦称此两人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值得注意的是,叔孙通所征鲁生三十余人中,只有二人不肯跟随,可见在当时这样的儒生只是少数。
二、诸儒生之身份评析
以第一部分的梳理为基础,此部分通过横向对比法,对以上三个儒生群体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对比,从而为评估叔孙通之儒者身份及其礼制建设活动提供横向参考坐标。
(一)博士诸儒生与两鲁生
由第一部分的分析可知,叔孙通与博士诸儒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其差别的焦点便在于是否以“面谀”事君。面对反秦起义之政治危机,博士诸儒生实事求提出“发兵击之”的对策,尽管秦二世对此怒形于色,他们仍然坚持己见、力陈时危,丝毫不畏惧降职、罢免的责罚。而叔孙通却有惧于“虎口”之危,在捕捉到了二世的情绪变化后,马上表现出了阿谀奉承之态。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孔子便言“巧言令色,鲜矣仁”[18]3,他深以“巧言,令色,足恭”为耻,并言“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18]52;而孟子不仅在义和利之间选择“舍生而取义”[19]277,对于权贵,他更表现出“吾何畏彼哉”[19]260的态度,坚守本心而不屈服于权贵,同时他亦指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9]152,极言诚之于人的重要性。孔子与孟子此番论述,便界定了先秦儒者应遵循的道德品行与君子风范。依此为标准可知,在秦二世面前不惧君威、刚直不阿、极诚于所言的博士诸儒生,显然是秉承先秦儒家君子风范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而叔孙通之“面谀”事君显然有违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君子风范。
这种差异在叔孙通与两鲁生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实际上,两鲁生对叔孙通的谴责基本代表了历来批判叔孙通之人的观点,也是造成历代学者对叔孙通争议颇纷的重要原因。从叔孙通之为官经历来讲,他在降汉前,曾先后任秦待招博士与博士,继而又投奔项梁、怀王、项王;降汉后,先后任博士、太常、太子太傅、太常。纵观叔孙通之为官生涯,其曾先后侍奉五主,其中有两次较明显的升迁:第一次发生在秦二世诏博士诸儒生答问之时,叔孙通因“面谀”二世,得以从待招博士升为博士;第二次发生在汉七年,叔孙通迎合刘邦之要求,所行朝仪深得高祖之心,从而由博士升为太常。由此来看,叔孙通之行为确不符合古代“忠臣不事二君”[1]1917的观念,其两次升官似乎也都是因为善于迎合统治者,亦即两鲁生所谓“面谀”。在这一点上,两鲁生对叔孙通的批判与博士诸儒生达成了一致,可见在秉持先秦儒家道德品行与君子风范方面,他们都是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的代表。
除此之外,两鲁生认为天下德化未定,兴礼起仪不合时宜。对此,王夫之有段精彩论述对两鲁生之论进行了反驳:
鲁两生责叔孙通兴礼乐于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之时,非也。将以为休息生养而后兴礼乐焉,则抑管子“衣食足而后礼义兴”之邪说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信者,礼之干也;礼者,信之资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国,唯此大礼之序、大乐之和、不容息而已……然则立国之始,所以顺民之气而劝之休养者,非礼乐何以哉?譬之树然,生养休息者,枝叶之荣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润也。今使种树者曰待枝叶之荣而后培其本根。岂有能荣枝叶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驾甫脱而息贯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乐。受命已未,制作未备,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20]19。
王夫之此言打破了礼乐之兴起需以百年德化为基础之论。但两鲁生之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初社会历史现状,正如《史记》所载:“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1]2370汉初立国,其所凭籍皆武功之臣,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均百废待兴,故“与民休息”的“黄老之学”成为汉初政治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历史现状下,叔孙通兴礼起仪必会遭致非议。
而对两鲁生“公所为不合古”之谴责,也并非没有历史依据。《史记》载“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1]1024-1025,“臣(叔孙通)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1]2102皆表明叔孙通所制礼对秦仪有所承袭;朱熹亦指出叔孙通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如其所言:“叔孙通为绵蕝之仪……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便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21]3054,“叔孙通所制汉仪,及曹褒所修,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21]2208;钱穆亦指出:“而叔孙制仪,遂垂为汉家之常典。三代礼乐,徒供汉儒为慕古之空想耳。”[22]48两鲁生坚守百年德化论与古礼之规制不肯变通,与叔孙通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进一步印证了两鲁生中规中矩传统儒生的身份。
(二)弟子与受征鲁生
与博士诸儒生及鲁生相比,叔孙通之弟子对叔孙通之态度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叔孙通之弟子愿随其降汉并参与其礼制建设活动,可见他们并未因事多主、“面谀”或不合古礼等事对叔孙通的人格和行为产生质疑。这点与恪守先秦儒家君子风范的博士诸儒生,以及忠于古礼和传统儒学的两鲁生有显著差别。他们选择同叔孙通一起进入仕宦之路,又因未被叔孙通及时举荐而对其多有“窃骂”。从时间来看,当时正值汉二年,“汉王东略地”,“南渡平阴津”,北有“项王北击齐……齐皆降楚”[1]262,西有彭城、废丘之战事,天下未平、政局未定、武官当用。叔孙通正是对汉初之社会政治背景有着深刻的认识,故以“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1]2101为由,暂缓对其弟子的举荐,而特举武功之徒。相比之下,叔孙通之弟子不仅不明时局,还因自身利益未得满足而心生怨恨,其利禄之心切不明自现。当叔孙通审时度势,趁朝仪创建初得成就,顺势为其弟子谋得官职之时,他们又以全然不同之态称赞叔孙通为“知当世之要务”的“圣人”,前后之对比十分明显,更与两鲁生之态度截然不同。可见,叔孙通之弟子既没有审时度势的历史眼光,又无法恪守先秦儒家君子风范,他们在追求自身政治、利益诉求时所表现出的利禄化、官僚化特点,是十分明显的。
而对于那些跟随叔孙通的鲁生,从既有史料可知,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像两鲁生一样的强烈抗拒,但其跟随叔孙通之目的究竟为何,由于史料所限也无法进一步考辩。但可以确定的是,所征鲁生三十余人中,除了两个鲁生之不就,大部分鲁生还是选择跟随叔孙通而从事。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大部分儒生还是选择顺应时局,或为利禄之需求,或以应时之态做儒学入仕之尝试。
由此可见,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上述儒生群体呈现出了明显的分野。班固在评价大儒董仲舒时曾言“抑抑仲舒,再相诸侯,身修国治,致仕县车,下帷覃思,论道属书,谠言访对,为世纯儒”[2]2262。班固所言“纯儒”便指像董仲舒一样秉持纯粹、正统儒学的儒者。而纯粹、正统之儒学莫过于先秦孔孟之属。荀子在评析先秦儒者之身份时曾言:“儒者法先王,隆礼义……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23]75若以此为标准对上述诸儒生进行评析,则博士诸儒生及两鲁生均能坚守先秦儒家君子风范,忠于古礼和传统儒学,他们可谓当时之“纯儒”。相比之下,叔孙通之弟子则呈现出对先秦儒家传统的背离,是利禄化、官僚化儒生的代表。
三、叔孙通之再评析
由上部分之梳理分析可知,叔孙通与博士诸儒生、两鲁生存在显著差别,与其弟子亦不尽相同。那么我们该如何评析叔孙通之儒者身份及其礼制建设活动?此部分拟结合叔孙通之身份背景、汉初之社会政治环境、叔孙通制礼之原则,对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叔孙通之儒者身份
对于叔孙通这一人物的身份背景,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徵,待诏博士。”[1]2100由此史料我们可获得两条信息:一为叔孙通生于薛县;二为叔孙通擅长“文学”,并因此任秦待招博士之官。对于“薛县”一词,《索隐》言“薛,县名,属鲁国”[1]2101。可见叔孙通之生养之地“薛县”处在原鲁国范围内。钱穆曾指出,齐鲁之文化因受孔丘等人的影响而呈现出“尚文化,重历史”[22]3,以整个社会之改造为理想[22]19的特点。此处之“文化”“历史”便指上古三代之历史、文化、典章制度、人文精神,而以整个社会之改造为理想则深刻体现了儒家“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经世志邦之道。齐鲁之地所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当地成为“儒学最兴盛的地区”[24]。秦始皇东行郡县之时,曾“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1]172,及至始皇焚《诗》《书》,“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高祖围鲁之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诚可谓“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1]2370。而叔孙通所擅长之“文学”,即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正如《史记》所言:“夫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1]2370叔孙通出生于薛县,受齐鲁文化滋养颇深,又师从孔子八世孙孔鲋[4]88,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深厚的,后其任秦、汉博士之官,为汉制礼著书也印证了此点。从这个角度来讲,叔孙通儒者之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二)仕宦原则下之儒者
那么争议之焦点便在于叔孙通之“面谀”事君。本文认为分析此问题时应结合具体社会政治背景。从其“面谀”秦二世的背景来讲,当时正值陈胜起兵于山东,据《史记》所载:“山东郡县少年……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1]191而当时之朝廷,除了有秦二世这位残酷暴虐的君主外,又有以赵高、李斯为代表的官僚内部权力斗争,足可见当时秦统治之政治危机。叔孙通正是深知其学术理想与政治抱负无法在这种背景下施展,才选择以变通之态迎合二世,以求在危机情况下自保。《孔丛子》中有段孔鲋与叔孙通的对话:
秦始皇东并,子鱼谓其徒叔孙通曰:“子之学可矣,盍仕乎?” 对曰:“臣所学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鱼曰:“子之材,能见时变,今爲不用之学,殆非子情也。”叔孙通遂辞去以法仕秦[4]88。
由此材料来看,叔孙通以所学不用于今而放弃入仕,可见其对儒学与秦朝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有十分清楚的把握。而由材料亦可知叔孙通之理想并非“不用之学”,相反,其理想抱负是使平生所学见用于社会。这正是儒家“学而优则仕”[18]67经世志邦之精神的体现,只有在统治阶层获得一定身份地位,才能将政治教化付诸实践,亦即荀子所谓“在本朝则美政”[23]75,钱穆所谓“求为社会整个的改造之理想”[22]19。在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之下,他才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事秦。而对叔孙通的另一争议,便是其事多主并降汉之举。两鲁生便认为叔孙通此举有违先秦儒家君子风范。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评价管仲时,并未因其先后侍奉公子纠和齐桓公而将其视为不仁之徒,反而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8]170而叔孙通之事汉,正如管仲之辅佐桓公,表面上看,他的行为确实有违传统君子形象,但其为汉代礼制建设所做的贡献更是不容忽视。孔子评价管仲时并未因小谅而忽视其大节,可见,即便以先秦儒家标准衡量,对叔孙通都是表扬多于批评的。于此同时,《史记》中有一细节值得我们重视:“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1]2101在汉王败北之时,叔孙通仍选择跟从汉王。若其出发点为利禄,则可不必弃秦而逃,更不必在汉王败北之际仍然跟随。这可充分证明,叔孙通行为的出发点并非利禄,而是为实现儒学致用积极寻找最佳政治环境,在这一点上叔孙通与其弟子是有所区别的。梅福亦言:“臣闻箕子佯狂于殷,而为周陈《洪范》;叔孙通遁秦归汉,制作仪品。夫叔孙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亲也,不可为言也。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若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2]2198
这种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同样体现在叔孙通侍奉汉高祖的过程中。就社会历史背景而言,汉高祖以布衣为天子,又于马上得天下,文化涵养的缺失及重武轻文观念使其对繁复深奥的儒学义理甚为不屑。在叔孙通降汉之初,便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一事。叔孙通欲起朝仪之时,高祖也特意强调“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1]2101。而当时位居朝廷要职的重臣也多为萧何、曹参等武功之臣。加之当时天下初定,社会并未发展到矛盾积弊甚深而迫切需要儒学调节的地步,故汉承秦制、无为而治成为当时政治的主旋律,儒家学说、政治理论并未进入统治者视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初儒学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在这种情况下,儒学若要见用于政治,就必须与当时现实政治需求相结合。实际上,儒家礼乐文化本质上就是强调尊卑等级秩序的贵族政治文明,这一特点为叔孙通将其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积极推动儒学入仕实践提供了可能性。而汉初政治最迫切之问题便是仪法未具情况下君臣秩序的混乱,高祖便深以“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1]2101之局面为患。此时的现实政治需求使得“尊君”成为首要任务,而叔孙通正是抓住此点积极向高祖言说儒学守成之用。为使儒学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实践,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1]2102,以符合汉初社会政治现状,这才顺利推动相关礼制建设活动的展开。可见,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
与此同时,仍需注意到在此过程中,儒学以“尊君”为首要任务,并走上与现实政治需求相结合的道路,逐渐成为帝制文化建构的基础,这种转变可谓深受汉代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当然,在此过程中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的儒生,便成为坚守先秦儒学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能顺应时变发挥儒学致用之效的儒生,便成为了仕宦原则下之新儒生;为追求利禄而妥协于官场的儒生,便成为利禄、官僚化之儒生。但前两者从本质而言,并未背离儒者之身份。荀子评析先秦儒者之身份时曾言:“儒者法先王,隆礼义……人主用之,则势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23]75以博士诸儒生、两鲁生为代表的,“不用”于政治的儒生,便是“在下位则美俗”的传统儒生;以叔孙通为代表的,见用于政治的儒生,便是“在本朝则美政”的新儒生。其分野的出现,便是受具体政治环境的影响。
(三)制礼之原则评析
叔孙通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主要是因为他以杂就“古礼与秦仪”为原则而制礼。若对叔孙通制礼之依据进行考察,可知其所凭借主要有三:一则为古礼之文献典籍;二则为秦仪;三则为晓习古礼的鲁生,及叔孙通个人的礼学积淀。从古礼之文献典籍来讲,实际上,经西周末年礼崩乐坏的政治混乱,以及始皇嬴政当政时期的大肆焚毁书籍,古礼之文献典籍便十分缺失了。正如司马迁所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1]2507《后汉书》亦载“汉初天下创定,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经礼,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是以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怀愤叹息所不能已也”[25]809。杜佑更是言:“周公摄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仪礼,以为后王法……周衰,诸侯僣忒,自孔子时已不能具。”[26]857认为古礼文献自孔子时便不甚完备。孔子不足以征杞、宋也是因为“文献不足故”[18]34。可见,在古礼之文献典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还原古礼并非易事。而对于秦仪,据“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1]1024。可知秦仪来源于六国之礼,又颇采其中尊君抑臣之内容。秦本辟处西方,无文化之传统,其学术文化皆来自于东土,又以三晋功利之学为多。秦始皇虽曾征齐鲁博士七十余人至泰山行封禅之礼,然其目的皆为歌功颂德。由此可见,秦仪虽采择六国之礼,但其内涵已大不同于往昔。叔孙通曾“以法事秦”[4]88,也证明了秦仪颇有尊君抑臣之法家色彩。但在古礼崩坏、文献典籍缺失之情况下,秦仪确是吸取古礼的途径之一,那么叔孙通参酌秦仪,势必造成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的状况。从鲁生及叔孙通而言,他们都有着深厚扎实的儒学功底和礼学积淀,无疑是保留和传承古礼的重要途径。但在汉初儒学发展的夹缝中,其个人际遇和发展又不免受到当时社会现实背景的影响,故其对古礼的还原也是有限的。由此可知,叔孙通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儒学的发展以及儒生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展现的儒者群体,便体现着在此背景下不同儒者之分化: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儒生,便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传统儒者群体,亦即“纯儒”,如前述两鲁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仕宦原则入仕、发挥儒学致用之功的儒生,便成为时代条件下之新儒生,如叔孙通;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儒生,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如前述叔孙通弟子。叔孙通在坚持儒者身份的前提下,以知时而变的仕宦原则进行儒学入世实践,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其所制之礼以“尊君”为首要任务,将儒学引上同现实政治相结合的过程,这体现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帝制文化构建的过程。至于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缺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