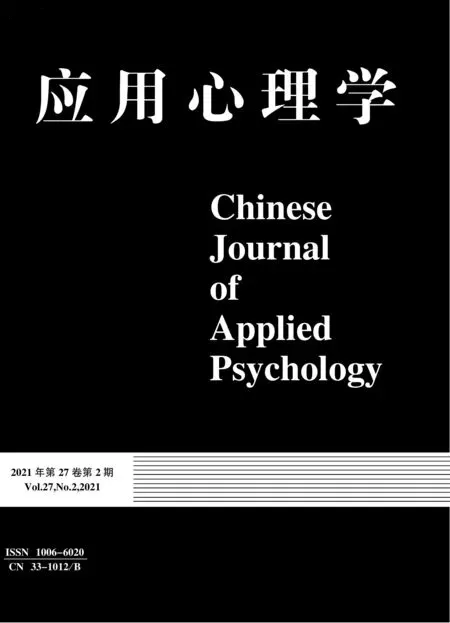第一人称视角全身错觉中的身体拥有感及应用 *
杨丽萍 麻 珂* 陈 红
(1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400715)
1 引 言
身体表征(body representation),是指身体在我们大脑中的表征(Gallagher,2000;James,1890;Kilteni et al.,2015;Maravita et al.,2003)。身体表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身体拥有感(何静,2009)。当我们低头看自己的身体时,我们就会感觉到它是属于我们的(Heydrich et al.,2013),这种“我的身体是属于我的,而不是他人的”的感觉就是身体拥有感(sense of body ownership)。从常识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以及身体表征似乎是稳定存在着的,我们每天都体验着同样的身体机能,从镜子里看到的是同样的身体外形,即使随着时间的变化,身体在脑中的表征也没有太大的变化(Llobera et al.,2013)。但是我们是如何拥有这种体验,这种体验又是否可以被改变?这些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我们(Jeannerod,2003)。
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身体错觉实验来实现对于身体拥有感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Botvinick和Cohen(1998)提出橡胶手错觉(rubber hand illusion)实验范式,通过多感官刺激(如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等)诱导健康被试错觉地认为橡胶手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这表明,身体拥有感以及身体表征是非常灵活的,容易被改变和更新。之后,研究者又陆续提出了识脸错觉(enfacement illusion,Tsakiris,2008)和全身错觉(full body illusion,Ehrsson,2007)。虽然全身错觉和橡胶手错觉及识脸错觉的研究有很大的互通之处和可相互借鉴之处,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橡胶手错觉(周爱保等,2013;张静,李恒威,2016;赵佩琼等,2019)和识脸错觉(周爱保等,2015)都仅仅是涉及到考察了某个身体部位的身体拥有感(body-part ownership),而全身错觉则是将全身作为一个整体去考察。考虑到生活中我们更多地是将自我作为一个完整的具身化实体去对待,而不单单只是身体部分的简单拼凑,因此全身错觉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正如前人研究指出,与身体自我意识相关联的基本自我是被体验为单一、连贯的全身身体表征,而非单独身体部位的多重表征(Lenggenhager et al,2007;Metzinger,2008;Aspell et al.,2009;Dieguez & Lopez,2017)。Blanke和Metzinger(2009)也通过对最小现象自我(minial phenomenal selfhood)的成分剖析支持了该观点,他们认为最小现象自我表现为在空间和时间上拥有一个身体和一个位置。
前人使用全身错觉来探索身体拥有感的研究表明,全身错觉的实现有两种方式,一是采用第三人称视角(the third-person perspective)。第三人称视角是一种离体的视角,被试脱离自己的躯体位置并以第三人的角度来观察自己的身体。例如,Ehrsson(2007)和Lenggenhager等人(2007)采用的“身心分离范式(out of body experience)”,在实验中,通过将放置在被试身后一定距离的摄像机所拍摄到的图像传输到被试佩戴的头盔式眼镜中,视觉上诱导被试以为自己是处于自己身体之后的摄像机处,然后实验者同时敲击被试的躯体以及摄像机的位置,这样同步的视觉-触觉信息就可以诱发被试产生离体感觉,错觉地以为自己离开了躯体并处于自己身体之后的位置。也有研究者利用第三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来探讨如何降低被试对于死亡的恐惧(Bourdin et al.,2017),在第三人称视角的状态下,诱发被试的身心分离错觉,这种类似濒临死亡的病人出现的灵魂出窍体验或许可以减少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的是第二种实现方式:第一人称视角(the first-person perspective)的全身错觉。这是因为,首先,日常生活中我们更多地是拥有着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自己,并在第一人称视角下经历和体验生活。所谓第一人称视角本就意味着自己是以第一人称视角占据着一个给定的位置,此时被试使用的是以自我的身体为中心(ego-centric)的参照系(Petkova & Ehrsson,2008;Preuss et al.,2018;平贤洁等,2020),也即在个人近体空间(peripersonal space,PPS)内去感受整合的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等多感官刺激信息。因此,探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实践意义。其次,多数第三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即身心分离范式)更多关注的是自我定位(self-location),即被试是否将自己定位于虚拟身体的位置(Lenggenhager et al.,2007)。如部分研究指出,正常被试从第三人称视角产生的身心分离体验或许并不属于身体拥有感范畴(Petkova et al.,2011),而仅仅是类似于个体识别摄像机中自己身体的一种视觉和位置的自我认同方式(Maselli & Slater,2013)。我们推测,研究者提出这种观点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这些实验多数是采用摄像机录像的方式来呈现,被试在心理上会倾向于认同视频中的自己。而且,有研究者将视觉、身体动觉以及触觉刺激共同纳入考察时发现,无论是在主观评价指标还是客观生理指标上,第一人称视角都比第三人称视角更能够反映身体拥有感(Slater et al.,2010)。
2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
借助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Immersive Virtual reality,IVR),我们可以轻松地实现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具体的实验设计中,被试通过佩戴虚拟现实头盔进入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中后,一方面可以通过低头看到和真实身体位置重合的虚拟身体,并且在做出动作时看到虚拟肢体的动作,此时虚拟身体与真实身体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是重合的(Burin et al.,2020);另一方面也可以在置于面前的虚拟镜子中看到虚拟身体以及对应的动作(Slater et al.,2010)。Preston等人(2015)指出,来自镜像反射的视觉信息被锚定回被试自己的近体空间,此时被试就可以依据以站在镜子前的自我身体为中心的空间参照系,将视觉与触觉信息和本体感觉信息结合最终产生较强的身体拥有感。研究发现,相比不一致的情况,当被试所做出的动作和他们所看到的虚拟身体做出的动作保持一致时,“镜子里这个正在做出一致动作的虚拟身体是我的身体”的全身错觉就被诱发出来了。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相符的,每当我们低头看自己的身体或者在镜子里看见它,并且能够同步的控制它时,我们就会产生看到的是自己身体的感觉(Schmalzl & Ehrsson,2011;Maselli & Slater,2013;Carey et al.,2019)。甚至有研究表明,在第一人称视角下,即使是不匹配的多感官刺激也能诱使被试产生较弱的全身错觉(Keenaghan et al.,2020)。
与橡胶手错觉(张静,陈巍,2020)的测量方法类似,对第一人称视角全身错觉的典型测量可以分为主观问卷评分(Petkova & Ehrsson,2008)和客观生理指标的记录,比如皮肤电和皮肤温度(Slater et al.,2010;Galvan Debarba et al.,2017;Preuss & Ehrsson,2019)。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在第一人称视角下,真实身体与虚拟身体基本重合,不存在视觉位置和本体感觉位置的分离,因此类似传统橡胶手错觉中的本体感觉偏移的行为测量方法已不再适用。
诱发全身错觉的影响因素也可以分为自下而上的多感官信息的匹配与自上而下的身体模型的调制,这与橡胶手错觉(张静,陈巍,2020)的研究结论类似。首先,研究发现,虚拟身体与真实身体的解剖结构应保持一致。有研究者在全身错觉中考察了正常情况与扭曲情况下的虚拟身体,发现被试对正常布局的身体结构展示出显著更高的身体拥有感(Romano et al.,2014),具体表现为:当身体解剖结构正常呈现时,即使在同步条件下只能看见手和脚(没有躯体),无形的整个虚拟身体仍旧可以被被试感知并体验到拥有感(Kondo et al.,2020)。其次,部分研究者发现视觉和触觉在时间和位置上被感知为同步时,才能有效诱发错觉(Serino et al.,2018;Scarpina et al.,2019;Salomon et al.,2013)。在实验中,被试通过观察虚拟身体的特定部位与自己的真实身体被同步触碰时,他们就会体验到自己拥有该种状态下的虚拟身体。也有研究通过同步的视觉、运动刺激来引发全身错觉(Kondo et al.,2018)。例如,Kokkinara和Slater(2014)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视觉-运动信息和视觉-触觉的同步刺激都能够诱发被试产生身体拥有感,但相比之下,一致的视觉-运动信息会使被试产生更为强烈的全身错觉。
对第一人称视角全身错觉的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颞顶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TPJ)中身体周围近体空间内视觉、触觉和前庭觉信息等多感官信息的整合反映了自我定位和视觉空间视角(Ionta,2011;Blanke,2012;de Borst et al.,2020;张静,陈巍,2018);腹侧前运动皮层(ventral premotor cortex,vPMC)、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IPS)等区域涉及知觉层面的高级认知加工与归因判断(Petkova et al.,2011;Grivaz et al.,2017)。
3 通过改变身体认知来影响心理
根据具身认知的解释(何静,2009;张静,陈巍,2018),当人们以第一人称视角来体验虚拟身体时,他们对自我真实身体的身体表征和对当前所拥有的虚拟身体的身体表征会发生重合,因此会从认知上将虚拟身体表征的一些内容纳入到自己的身体表征中来,从而表现出感觉、认知、态度以及行为上的改变,也就是说,通过改变感知到的虚拟身体的形态,被试对于自我真实身体的心理感知也会相应地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影响被试的自我和社会认知,以及相关的行为表现。
3.1 自我认知和行为表现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对自我认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让被试感知“我进入了什么样的虚拟身体,我变成了什么样子”来实现的。在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中,通过设计不同形态的虚拟身体,然后诱发被试产生对该虚拟身体的拥有感,从而导致被试相应的自我认知和行为表现的改变。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用于改变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比如Kilteni等人(2013)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设计了不同肤色及着装的虚拟身体,并且使用同步匹配的视觉-运动信息去诱发被试产生全身错觉,结果发现虽然被试对于不同肤色和着装的虚拟身体都产生了拥有感,但是当他们对身着舒适穿搭的深肤色虚拟身体产生拥有感时,被试能够演奏出具有更强感染力的鼓声,这与我们生活中常见的深色皮肤群体可能更具音乐天赋的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Rubo和 Gamer(2019)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让被试错觉地拥有了较为肥胖的虚拟身体,研究结果表明,接受肥胖条件的被试会报告自己的臀部周长数值更大,而且显示出更符合肥胖身体的运动行为模式,具体表现为在实验室内行走时为避免触碰到桌子而增加安全距离,或者在穿过门洞时有明显的侧身行为。也有研究者提出,因为自我的身体大小会在我们看待外部世界时提供一定的参考,那么如果成比例地放大或缩小我们的身体,就会导致我们把世界看得更小或更大(van der Hoort et al.,2011)。继而,Banakou等人(2013)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发现被试对不同大小的虚拟身体都会产生拥有感,并表现出随着身体大小的不同,对于虚拟物体尺寸的估计以及相关的态度、行为都会随之改变,比如当被试错觉地拥有了虚拟儿童的身体时,他们会高估外界物体的尺寸,倾向于选择进入儿童房间而不是成人房,而且在内隐联想测验中更快地将儿童属性与自我联系起来。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可用于开展自我心理辅导。正如所罗门悖论所言,很多人能够给予困境的他人很好的建议,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却怎么也想不通。虽然通过实验操作使被试置身于虚拟“咨询师”的身体中并不能直接改善其心理状态,但是与自我的对话却可以间接实现这一目标。Slater等人(2019)的研究营造了一种自我咨询环境,虚拟人物包括咨询师和来访者。通过对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的诱发,被试会先进入来访者的视角,向虚拟咨询师倾诉;随后又会进入咨询师的视角,产生对于咨询师的身体拥有感后,聆听自己刚才作为来访者所讲述的内容,并且帮助开解虚拟来访者,即解决自己作为来访者时提出的问题。结果表明,被试的自我批评程度降低,且情绪、幸福感以及自我同情等均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Osimo et al.,2015;Falconer et al.,2014)。
研究者还在临床的一些研究中发现,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有助于缓解患者群体的疼痛。比如Schmalzl(2011)的研究发现,利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可以诱发截肢患者对人体模型产生拥有感,从而暂时地缓解幻肢痛和收缩感觉。而针对饮食障碍和身体意象不满意群体的研究表明,如果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操纵该类被试感知到自己的身体是正常或者瘦削的,被试的身体焦虑程度会显著降低(Porras Garcia et al.,2019;张为忠,连榕,许艳凤,2020),而身体满意程度(Preston & Ehrsson,2018;Piryankova et al.,2014;Park et al.,2016;Keizer et al.,2016;Serino et al.,2019)则会显著提高。另外,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也可被用于在虚拟现实环境中对恐高症、创伤性应激障碍等的治疗(Freeman et al.,2018;张为忠等,2020;许百华,赵业,2005;柳菁,2008)。甚至最近的一篇研究发现,沉浸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后,即使被试完全静止只观看虚拟自我进行高强度动作,被试的真实心率也会提高,以及使用Stroop任务测量的认知抑制能力也会增强(Burin et al.,2020)。
3.2 社会认知和行为表现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对社会认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让被试感知“我进入了谁的虚拟身体,我变成了谁”来实现的。如果我拥有了与自我身份不同的虚拟身体,那么我记忆中该虚拟身体(或者其所归属的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表征就会与我(或者其所归属的群体)所具有的特征表征相重合,由此提高自我与他人的重合(self-other overlap),从而影响被试对虚拟身体所属群体的社会认知及相关的行为表现(Maister et al.,2015)。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会改变个体的社会认知。比如Rosenberg等人(2013)在虚拟现实环境中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诱发被试对拥有超能力的虚拟身体产生身体拥有感,结果发现被试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Yee和Bailenson(2007)的研究结果表明,当被试在虚拟现实环境中拥有更具吸引力的虚拟身体时,在自我表露和人际距离任务中会表现出与同伴更为亲密的关系。同样,拥有更高挑身材的虚拟身体的被试在后续的谈判任务中表现得也更为自信,而且这种行为的变化会持续到之后真实场景的社会交互中(Yee et al.,2009)。更为奇特的是,Ahn等人(2016)使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使被试以第一人称视角体验到自己是牛或是珊瑚来观察世界,发现无论是当被试拥有牛的身体来体验牛的日常生活或是拥有珊瑚的身体来经历遭受海水侵蚀的境遇后,他们都表达出与自然更紧密的联系并更加关心环境问题。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在社会交互中的另一应用则是通过诱发个体进行换位思考来提高其观点采择能力及共情能力,由此减少社会刻板印象的负面效应。Peck等人(2013)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诱导白人被试产生出对深色皮肤的虚拟身体的拥有感,使其拥有“我作为白人拥有了黑人的身体”的体验,结果发现被试的内隐种族偏见程度明显降低(Hasler et al.,2017)。也有实验者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对老年刻板印象进行研究,被试会分别体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虚拟身体,当被试产生对虚拟的老年身体的拥有感后,被试对于老年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显著减少(Yee & Bailenson,2013;Banakou et al.,2018)。Seinfeld等人(2018)通过将家庭施暴者置身于虚拟的受害者体内,并且通过同步一致的多感官刺激诱发其产生对虚拟受害者身体的拥有感(Botero & Whatley,2020)。在后续的测试中,他们发现施暴者识别女性恐惧面孔的能力有所提高,并相应地减少了将恐惧面孔识别为快乐的偏见。
4 展 望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张彤,纪丽红,郑锡宁,2004),在沉浸式虚拟现实环境中去实现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因此我们也越来越能够利用该技术去提高心理学实验的生态效度(张为忠等,2020)。通过设计不同的虚拟场景,不同的虚拟身体(颜色,大小,胖瘦等),我们可以对被试的身体自我及其社会认知进行广泛的研究。近些年来,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并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未来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入地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探索。
4.1 扩大实验被试群体
身体自我意识的发展贯穿人的一生,诸如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属于什么样的群体这些问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因素,因此或许可以扩大被试群体,进行更为广泛的横向和纵向的研究。比如,Cowie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6~7岁的儿童已经能够产生全身错觉,并且错觉的强度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增强。那么对于年轻人、中年人和老年人来说,全身错觉的强度乃至其反映出的身体自我的可塑性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呢?更强调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和更强调个体主义的西方文化背景,是否也会对全身错觉的强度有影响呢?此外,该范式也可用于对特定群体进行实践应用的开发,比如针对老年群体的空虚无力感以及重症患者对于死亡的恐惧等,是否可以利用全身错觉去帮助他们顺利进行过渡呢?
4.2 深入研究认知神经机制
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与橡胶手错觉、识脸错觉、甚至是身心分离范式,在实验操作以及认知神经机制上,都有很大的重合之处。对于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的研究或许可以借鉴橡胶手错觉的大量研究结论,以发现关于全身错觉的更多潜在影响因素。比如在识脸错觉(Ma et al.,2016)的研究中,作者发现当被试错觉地认为自己拥有了某虚拟脸时,也就拥有了该虚拟脸的表情,因此可以通过设置虚拟脸的不同表情来影响被试的心情。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来诱发、调控被试的心情状态呢?而且,考虑到身体拥有感和身体控制感之间的密切关系(Ma & Hommel,2015;张静,李恒威,2016;Braun et al.,2018),借鉴主动控制感的研究结论也是一种可能。比如前人研究将主动控制感理论中的唯一性引入到虚拟现实的手部错觉的研究中(Ma,Hommel,& Chen,2019),发现相比被试独自控制虚拟手的动作,当主试和被试同时操控虚拟手,且在虚拟手与被试真实手具有较低同步性条件下,被试的控制感受到显著影响,更容易认为此时的虚拟手是受主试控制。那么在虚拟环境中,我们是否可以和他人共享同一虚拟身体呢?反过来,我们是否也能够拥有两个甚至多个虚拟身体,比如像电影阿凡达中那样?虽然我们可以同时拥有两个或多个虚拟身体的论断在第三人称视角的身心分离错觉中已经得到验证(Heydrich et al.,2013),但是考虑到身心分离和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可能在认知机制上存在差异,以及自上而下的身体模型的稳定性,使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来进行验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借鉴和交叉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拓宽研究领域,对于我们研究身体自我意识的认知机制也具有较大的意义。
另外,前人的研究大部分都是行为实验和认知机制发现,鉴于实验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神经机制的研究也可以被纳入进来。比如在前文第三部分“通过改变身体认知来影响心理”中,如果可以把被试认知上的身体表征变化、心理任务或者行为表现、以及大脑相应脑区的激活联系起来,那就更能够说明改变身体是如何影响心理的这个问题,也就更具有说服力。
4.3 拓宽实验范式的应用领域
首先,根据前人的研究(Nosek et al.,2005),除了种族偏见、年龄偏见外,现实生活中还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比如男女性别偏见、地域偏见、性取向偏见等等。类比诱发对于不同肤色虚拟身体的拥有感来减弱种族偏见,我们可以在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中,通过改变虚拟身体的形态以及相应的实验操作,经由自我与他人表征的重合以及换位思考,或许同样可以减小其他相似类型的偏见与刻板印象的负面效应。
此外,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范式或许可以应用于人因工程领域(Banakou et al.,2013)。例如,有研究者提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时需要操纵非常小或者非常大的人形机器人,而一旦从第一人称视角进入这些机器人以后,对外界事物的尺寸和距离的感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外科医生可能会错觉地以为自己是在病人体内进行手术的微型机器人,或是一个工程师通过产生对作为钻探设备的巨型机器人的身体拥有感而感知到自己正位于深海海域,从而更有利于对各自特定任务的操作(van der Hoort et al.,2011)。
4.4 探讨改善机制的长时效应
如前文所述,前人探究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在自我身体意象中的应用,并发现这可以短期地改善被试对自我身体的不满意程度。而在脱离实验室环境后,被试回归自己的真实身体,这个改善效应是会即刻消失还是能够留存一定的时间呢?长期且多次的重复训练是否能起到稳定干预的效果呢?这对于特定的身体不满意个体甚至是饮食障碍患者可能具有很大的意义。同样,对于普遍存在的社交焦虑和各种恐怖症,或许也可以通过长期且多次地与虚拟人物/物体进行交谈、演讲(前人文献Pertaub,Slater,& Barker,2002已指出了虚拟现实演讲的可行性)等交互训练,来进行干预和治疗。再比如,Burin等人(2020)的研究表明,在诱发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后,即使被试处于静止状态,也能因为虚拟人物的动作而出现心率提高、认知抑制能力增强的现象,那么长期的练习是否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呢?如果可以的话,在影响人体生理的运动康复训练方面,第一人称视角的全身错觉的应用就非常值得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