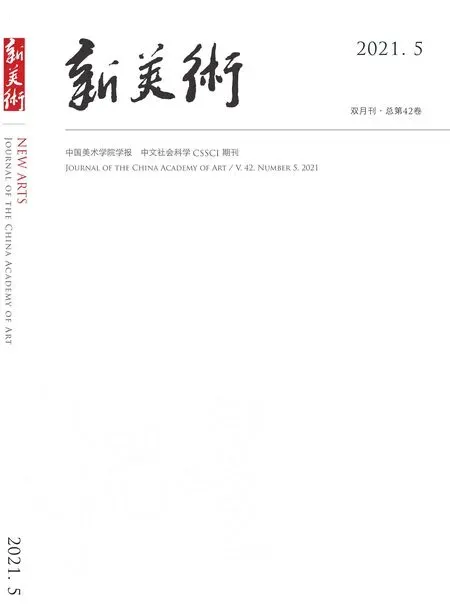黄牧甫篆刻的“断舍离”
张爱国
黄牧甫(1849―1908)是晚清印坛特立独行、别具风格的传奇人物。与吴昌硕(1844―1927)、齐白石(1863―1957)这两位差不多同时代的篆刻大家相比,他不居北京、上海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城市,而是机缘巧合地生活在岭南开放口岸城市——广州,这看似无意的“避同”选择,却似乎是艺术人生的某种“殊途”和“离断”的隐喻。与吴、齐两位诗书画印齐头并进的大家相比,虽然黄牧甫也同时兼善书画,但作为一位篆刻家的形象定位显然来得更为纯粹和强烈。黄牧甫是为篆刻而生的,他命中注定首先是一位印人,于书、画、印的对待、选择和侧重上,我们十分清晰地看到他的取舍和离断,这是耐人寻味和引人深思的。因为黄牧甫除了印谱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著作、言论留与后世,人们大都只能通过他印款中的文字以及他的朋友、弟子们片言只语的记述来推想其艺术观念和主张。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对其分析研究似乎难以命中要害,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另一方面感觉他的篆刻艺术博大超前,常读常新,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古人云:大道至简。老子曰:少则得,多则惑。在黄牧甫篆刻看似单纯的外表下,似乎弥漫着充实而美妙的意蕴,有待于我们去发现、去解读。笔者喜爱黄牧甫篆刻有年,近来对其似乎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故不揣浅陋,拟从一新的角度去探析其篆刻艺术,以就正于业内专家及博雅之士。
“断舍离”是数年前在日本兴起复传入我国及港台、东南亚地区的一种生活理念。其创始人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山下英子女士,她大学期间开始学习瑜伽,通过瑜伽参透了放下心中执念的修行哲学“断行、舍行、离行”,随后便致力于提倡以这种意念为基础的、任何人都能亲身实践的新整理术:断、舍、离,通过对日常家居环境的收拾整理,改变意识,脱离物欲和执念,过上自由舒适的生活。其核心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弃多余的废物、脱离对物品的执念”,通过对物品的断、舍、离,获得心灵的解放和自由,最终,让“断舍离”成为一种“人生整理术”。1详见山下英子,《断舍离》,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苏静主编,《知日·断舍离》,中信出版社,2013年等。
不知道为什么,当笔者第一次见到“断舍离”这一理念时,马上联想到黄牧甫的篆刻。其实,假如我们理解并认可“断舍离”的生活理念,我们就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人生整理术”而被动的接受和运用。反之,我们不得不思量“断舍离”带来的心灵震荡和思维魔力,它与我们生活中种种行为和心理活动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的动态特性。进一步说,既然山下英子也指出“断舍离就是一种动禅”2同注1,第14 页。,那么,“断舍离”或许也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人生和艺术的一种方式,这种解读和人生修行、艺术创作的行为又是合一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行合一。
现在,我们不妨看看,究竟黄牧甫篆刻是一种什么样的“断舍离”?或者说,从“断舍离”的角度出发,我们会看到怎样的一个黄牧甫篆刻呢?
一 断
断,黄牧甫篆刻断绝了以汉印为指归以外所有不需要的东西。
黄牧甫篆刻由浙派入手,进而学习清代篆刻大家邓石如(1743―1805)、吴让之(1799―1870)及赵之谦(1829―1884)等人,其间反反复复,往返肆力于诸家之间,直到汉印出现在他的视线中。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光绪八年(1882)及光绪十三年(1887)两次到广州,光绪十一年(1885)到北京,是他大规模接触到汉印的重要节点,特别是第二次在广州协助吴大澂(1835―1902)编拓二千方古印为《十六金符斋印存》期间,他经手细察了不少未经锈蚀的秦汉玺印,字口如新,锋锐挺拔,光洁妍美,这种对汉印的近距离认知深深震撼并提升了黄牧甫的审美,让黄牧甫义无反顾地植根于汉印的广阔天地。以往有许多学者曾撰文指出黄牧甫篆刻取法的广泛,所谓“印外求印”。比如最常为人引用的其弟子李茗柯所说:“悲庵(指赵之谦)之学在贞石,黟山(指黄牧甫)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3转引自马国权,〈黄牧甫和他的篆刻艺术——《黄牧甫印谱》代序〉,载《黄牧甫印存》,西泠印社出版社,1982年,第6 页。从表面上看,黄牧甫篆刻的确取资广博,举凡彝鼎、权量、诏版、泉币、镜铭、古匋、瓦当、汉简以及周秦汉魏摩崖、石刻、碑额等,无不入印,但究其神理意味,莫不以汉印平正流动、朴实厚重、挺劲闲雅的精神气息为指归。正如他自己在“师实长年”(图1)白文印章边款中所说:“此牧甫数十石中不得一之作也。平易正直,绝无非常可喜之习,愿茗柯珍护之。”4同注3,第85 页。所谓“非常可喜之习”,即是故作奇变、花哨的讨巧、讨喜的习气,这是黄牧甫极力断绝的。因此,虽然他取法上述那些文字素材,但他念念不忘的是用汉印的大美、格局来统摄它们,塑造它们,甚至改造它们,可谓源于素材,高于素材,这样一来,这些奇诡多变、意趣盎然的鲜活文字就像来到了一个管理高超的公司,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越加发挥出各自的能量和魅力。

图1 黄牧甫,“师实长年”印(出自《黄牧甫印影》,荣宝斋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
可见,汉印的审美境界是黄牧甫篆刻之灵、之魂,是黄牧甫篆刻的主心骨、总指挥。黄牧甫篆刻之“断”,表面上断绝了汉印以外的一切,实质上获得了篆刻审美的准则和高度,获得了篆刻理念上的自信和自由,让他在篆刻的天地里纵横驰骋,大刀阔斧,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与此同时,他又将这种理念和汉印之外的几乎所有可资利用的印学元素相勾连,降服之、改造之、运用之。
此外,笔者以为,黄牧甫篆刻自我风格面貌的确立亦以其“断”为分水岭。“断”之前为模仿、为借鉴、为依傍,在其印款中每每以“仿完白”“拟让之”“师撝叔”等表出之。“断”之后为自立、为发展、为创造,在其印款中几乎一概以“仿汉印、仿汉人”等表出之,其实,这里的“仿”只是个旗号、只是个号令,看其印章,完全是黄牧甫自家面目,实际上他就是晚清的“汉人”。在黄牧甫这里,几乎从未想过我们今天许多人所谓的创新,他几十年和秦汉古印、钟鼎彝器、碑版金石等打交道,长期浸淫在古物、古文字、古文化的氛围中5黄牧甫除了在北京参与重摹宋拓石鼓文的工作、为吴大澂编拓《十六金符斋印谱》外,还曾为吴大澂椎拓金石拓片及摹刻宋拓本《刘熊碑》,为端方(1861—1911)编著《陶斋吉金录》。详见白谦慎,《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 75—81 页。,心摹手追,修炼日久,沉潜日深,每有印作,古文奇字,信手拈来,如大将用兵,随意所之,神出鬼没,神龙变化,无不如志。而其对汉印的独特观察、理解、发挥等亦自然融入其中,打上鲜明深厚的黄氏烙印。
二 舍
舍,是指黄牧甫篆刻舍弃剥蚀和做作,唯光洁挺劲和自然大方是务。
黄牧甫篆刻对汉印的依归是一个十分有意味的研究话题,这种依归带来两个互为因果、互相关联的结果。一是终其一生对汉印无休止的学习、研究与开发;一是黄氏自我印风的卓立。他在“臣锡璜”(图2)一印的边款中说:“印人以汉为宗者,惟赵撝叔为最光洁,尟能及之者,吾取以为法。”6同注3,第66 页。寥寥几句就把汉印、光洁、赵之谦以及自己联系并等同起来,颇能见其志趣。而光洁的对立面是剥蚀,是他要断然舍弃的。在“季度长年”(图3)一印的边款中他明确地说:“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7同注3,第32 页。其实,篆刻界在对汉印剥蚀的审美判断上是有不同的,以浙派和吴昌硕为代表的印风对其就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我们现在无法判断黄牧甫对汉印本光洁的认知是否针对浙派和吴昌硕而发,但他在审美上这种不与人同的卓识是值得尊重的。更重要的是,对汉印的这种新解读体现了篆刻艺术发展中对整个战国秦汉古玺印认知的不断递进。而黄牧甫的个人判断恰好又与这种递进相吻合,成为推动篆刻艺术不断发展的新动力。

图2 黄牧甫,“臣锡璜”印(出自《黄牧甫印影》,第116页)

图3 黄牧甫,“季度长年”印(出自《黄牧甫印影》,第167页)
黄牧甫篆刻对剥蚀和做作的“舍”,主要是建立在刀法和对印面总体效果的高度严格的把握上的。对其刀法,马国权先生曾说:“牧甫自成家法后的用刀,也有自己的特点。他的弟子李茗柯告诉人说,牧甫刻印所用的冲刀法,完全遵照传统,执刀极竖,无异笔正,每作一画,都轻行取势,每一线条的起讫,一气呵成,干脆利落,绝不作断断续续的刻划,和三番四复的改易。我们看到钤本,可以领略到这点。如得到牧甫的原刻,将它洗干净,用放大镜仔细揣摩用刀的方法,将更证实茗柯是言之有据的。”8同注3。这段话明确的记述了黄牧甫的冲刀法及其干脆利落的特色。据云黄牧甫善用快刀薄刃,以其锋利,逞其爽洁,这种爽利猛烈的刀法,保证了线条光洁劲挺,锋芒锐利,达到一种近乎极致的冷逸,夺人眼目,撼人心眩。
在对印章总体效果及氛围的把握上,黄牧甫同样大局在手,指向鲜明,即所刻不论朱白,对印面都不做任何故意人为的敲击、残破甚至刮削磨蹭(所谓做旧),舍弃做作,达到简洁大方,明快自然的艺术境界。
三 离
离,指黄牧甫篆刻脱离对汉印外形的执念,直取其神。
笔者必须指出,黄牧甫对汉印光洁的追求,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其在“骑督之印”(图4)的边款中说:“骑督之印见十六金符斋印集。务芸爱之,属陵仿之。其光洁可及,而浑古不及也。”9同注3,第87 页。可见,光洁是其形,浑古乃其神。牧甫先生所梦寐以求者,汉印之神也。基于这一念想,他经常把前辈篆刻大家如赵之谦和汉印合并考察体味,不经意间透露其志趣之所在。在白文“欧阳耘印”(图5)的边款中他说:“赵益甫(之谦)仿汉无一印不完整,无一画不光洁,如玉人治玉,绝无断续处,而古气穆然,何其神也。”10同注3,第52 页。此处即是借赞扬赵之谦而彰其自己艺术之志趣。尽管,黄牧甫没有关于篆刻创作的理论著作传世,但有意无意地还是在他的篆刻边款中透出消息。例如白文“国钧长寿”(图6)一印的边款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述:“篆刻之难,向特谓用刀之难难于用笔,而岂知不然。牧父工篆善刻,余尝见其篆矣,伸纸濡豪,腋下风生,信不难也。刻则未一亲寓目焉。窃意用刀必难于用笔,以石之受刀,与纸之受笔,致不同也。今秋同客京师,凡有所刻,余皆乐凭案观之,大抵聚精会神,惬心贵当,惟篆之功最难,刻则迎刃而解,起讫划然,举不难肖乎笔妙。即为余作此印,篆凡易数十纸,而奏刀乃立就。余乃悟向所谓难者不难,而不难者难。即此可见天下事之难不难,诚不关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彼局外之私心揣度者,无当也。质之牧父,牧父笑应曰:唯。因并乞为刻于石,亦以志悟道之难云。乙酉秋,西园志。”11同注3,第117 页。此处,西园代黄牧甫立言,“诚不关众者之功效,而在乎独运之神明”一语,切中肯綮,无怪牧甫笑应以“唯”了。牧甫独运之神明,即在章法、字法、刀法之锤炼、推敲、精熟后之出神入化,以达遗貌取神、离形得心之境界。

图4 黄牧甫,“骑督之印”(出自《黄牧甫印存》,西泠印社,1982年,第87页)

图5 黄牧甫,“欧阳耘印”(出自《黄牧甫印存》,第52页)

图6 黄牧甫,“国钧长寿”印(出自《黄牧甫印存》,第117 页)
从表面上看,黄牧甫篆刻从未离开对汉印的模仿,他有大量的边款可以作证,甚至于他还常常在边款中不厌其烦地交待“拟汉铜印、仿汉铸印、某字取自某汉印……”,但我们如果将他所作和汉印对比,就会发现他有着纯正的汉印基因,却长着和汉印不同的模样。这就是黄牧甫绝高的地方,他脱离了汉印的形貌,直取汉印的神髓。换句话说,黄牧甫学汉印而高于汉印,师其心而不泥其迹,黄牧甫刻的汉印姓黄而不姓汉。
四 蕴含“断舍离”特质的岭南风土文化对黄牧甫篆刻的影响
在以往关于黄牧甫篆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关注到其在广州时期印艺的成熟以及对岭南印风的影响,致有“粤派”之称(吴颐人)。而笔者由此想到的,却是两次客粤近十八年的生涯,对黄牧甫人生和篆刻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如果说,黄牧甫毕生精研篆刻是推动其印风确立的内在动因的话,那么,岭南的风土文化就应该是其印风确立的外因。尽管目前关于这一话题可以看到的史料几乎为零,但透过黄牧甫篆刻的“断舍离”,笔者隐约感受到其间的勾连环绕。
笔者曾有缘于20世纪90年代在广州生活过两年,对岭南的风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也十分喜爱和关注。在黄牧甫的时代,广州是一个通商口岸,外来的新鲜事物和文化较早、较多地涌入,在和岭南本土文化充分搅拌后,形成了颇具前卫性的新岭南文化。而最具代表性并体现其风土文化的又非语言和饮食莫属,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粤语”和“粤菜”。
黄牧甫旅居广州十八载,他每天每日都要和这两样东西打交道,受其影响是必然的。那么,岭南的风土文化有何特质呢?笔者根据自身感受结合观察、思考,粗浅地概括出四点。
其一,务实。岭南的较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经济的繁荣,促使人们务实。断绝虚张声势,舍弃繁文缛节,远离虚无缥缈,这就叫断虚务实。黄牧甫在广州就职广雅书院,一干就是十几年,中间不求仕进,不慕虚名,一心在篆刻上用功,在篆刻上求发展,这难道不也是种务实的特性吗?
其二,简洁。粤语非常简洁,也更接近古汉语,但又和外来语言融合的很快。粤菜多以追求本味为主,尽量不破坏食材自身的鲜嫩,比如清蒸、白灼等烹制手法,都很简洁易行。煲汤也是,一个煲,食材统统放下去,然后慢慢煲、慢慢炖就是了。这种崇尚本味、追求简单的地域个性和黄牧甫篆刻对汉印本来面目的还原以及对汉印光洁、平正的推崇何其相似乃尔。
其三,高效。因为务实,因为简洁,人们做事自然就勤勉,效率自然就高。粤菜中的鱼虾大都活杀现杀,分分钟端上桌,分分钟落下肚。去除了许多不必要的手续、环节,直奔主题,当然高效。黄牧甫也是,认准了汉印,认准了做个印人,心无旁骛,手法简洁,有求必应,有石就刻,量上去了,质也跟着提高。据说其一生治印不下万方,可见其效率。
其四,执着。“断舍离”教人脱离对物品的执念,但并不是教人放弃执着。执着是一种坚守,是一种信念。粤语、粤菜千百年流传,满世界开花,新事物、新元素不断地加进来,可主调子始终不变,这不是执着是什么?黄牧甫也一样,执着于篆刻,执着于汉印,钟鼎、古币、权量、诏版、摩崖、碑碣、镜铭、瓦当、砖文什么的化进来,诗文、书法、绘画甚至摄影(牧甫曾在南昌供职于一照相馆)什么的融进来,再统统以黄味的汉印端出去。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风雨无悔,这不是执着是什么?
上述四者相互作用,共同铸就了岭南风土文化中的“断舍离”特质。笔者之所以费此节笔墨,实因其蕴含的“断舍离”特质和黄牧甫篆刻的“断舍离”颇能相通,于是主观大胆地推测前者对后者当或多或少有所影响。“断舍离”让黄牧甫篆刻发展到近似于西方现代极简主义的一种风格和境界。他的篆刻先是很快在岭南地区获得认可并产生影响,进而扩大到内地、港台及东南亚地区,其中不少人对其印风的学习传承是自发式的私淑,这无疑是出于对其印风的极度欣赏与推崇。他这种“极简主义”的印风,简洁、明快、生辣、时尚、超前、优雅、极致,好像永远不会过时,越是往后,感觉喜爱的人越多,读懂的人越多。他的印,可以开掘的空间仍然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还会有更多更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