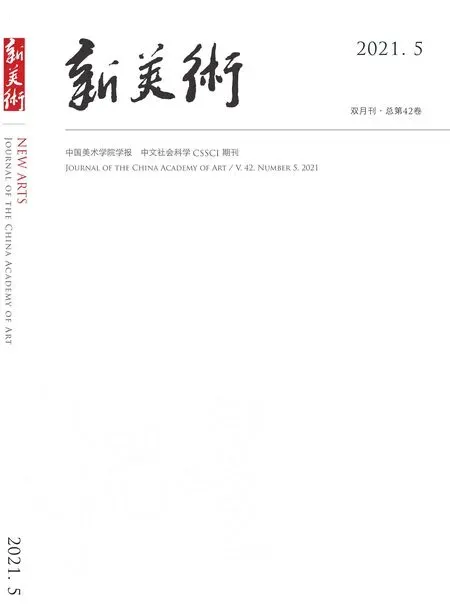论德沃夏克前期的风格史方法 以《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为中心的考察
张伟晴
德沃夏克[Max Dvořák,1874-1921]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艺术史家之一。在他于1921年去世后,他的学生将其晚年的课稿编辑出版,取名为《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Kunstgeschichteals Geistesgeschichte]。为了捍卫同时代表现主义艺术的合法性,在这部文集中,德沃夏克从观念层面重新评价了古代晚期以来的非自然主义艺术,把它们的形式归之于日耳曼民族的宗教与哲学世界观。相应的精神史阐释模式遂成其方法论的代称。德沃夏克身后,人们多是通过这一侧面来认识他的艺术史地位。例如,在梳理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历史脉络时,施洛塞尔[Julius Schlosser,1866-1938]将精神史转向视为德沃夏克跻身一流艺术史家的关键,1见陈平编选,《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8 页。包科什[Ján Bakoš]则强调,正是德沃夏克让艺术史自律且平稳的进程置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并促发了阐释学与社会艺术史的勃兴。2同注1,第191 页。精神史的影响力固然可观,但这毕竟是德沃夏克后期的取径。世纪之交,也即德沃夏克从事艺术史研究之初,他所采用的仍然是基于形式分析的风格史和艺术鉴定方法。
直到1911年左右,已发表的文章和课稿都可以证明德沃夏克的研究方法深受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经典作品的影响。3Aurenhammer,Hans.“Max Dvořák.”Karel Hruza,Österreichische Historiker,Böhlau Verlag,2012,S.185.像学派前辈那样,他着眼于档案材料和艺术品原作,关注形式要素、形式关系和品质表现,力求构建一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风格发展史。派希特[Otto Pächt,1902-1988]曾多次提及德沃夏克的风格史著述,指出他对“艺术现象的派生本质问题”的探索在当时获得了众多重量级学者的支持。4[奥]奥托·帕希特,《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薛墨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14 页。另外,从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的文章也能看出,他对德沃夏克前期和后期的研究给予了同样程度的关注和肯定。1903年发表的《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Das Rästel der Kunst der Brüder van Eyck](图1、图2)是德沃夏克的风格史代表作。在此文中他继承了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延续性思想,经由重建早期尼德兰绘画的预备阶段,有效地鉴定了《根特祭坛画》[Ghent Altarpiece]的作者身份,为人们了解凡·艾克兄弟增加了新的维度。虽然德沃夏克将传统的形式分析理论推向纯熟之境,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针对细节展开论述。5为纪念奥地利艺术史家德沃夏克的百年忌辰,捷克科学院[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 in Prague]在2021年4月15 到16日召集中欧各国的艺术史学者举行了线上会议“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影响II:德沃夏克一百周年忌 辰”[The Influence of the Vienna School of Art History II: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Max Dvořák’s Death]。由于紧扣现代主义和民族身份认同等主流话语,德沃夏克后期的精神史与文物保护工作成为会上重点讨论的议题,相对而言,他早年从事的风格史研究依然欠缺关注,与此相关的仅有荷兰绘画专家本杰明·宾斯托克[Benjamin Binstock]的一篇调查报告《德沃夏克、凡·艾克兄弟之谜和根特祭坛画》[Max Dvořák,the Riddle of the Van Eycks,and The Ghent Altarpiece],文章将刊登于2021年12月第25 期《艺术史学杂志》[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本文将以《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为中心,通过文本细读对德沃夏克前期的风格史研究进行述评,并在后半部分考察这位艺术史家对当时学界既有成果的回应。

图1 德沃夏克,《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封面,1904年

图2 德沃夏克,《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正文,1904年
一
1902年,德沃夏克从助教晋升为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的编外讲师,而后他受教育部部长委托,于1903 至1904年的冬季学期在历史研究所讲授艺术史实践课程,6Polleross,Friedrich.“Materialien zu tschechisch-österreichischenKunsthistorikerInnen im Archiv des Institutsfür Kunst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Wien.”UMĚNÍ ART,no.6,2019,S.571.《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正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此文刊载于维也纳《皇家艺术史收藏年鉴》[Jahrbuch der Kunsthistorischen Sammlungen des Allerhöchsten Kaiserhauses]第二十四卷,长达156 页,从现实意义来看,它对德沃夏克在1905年受聘为副教授起到过一定的帮助。不仅如此,文章一经传阅,随即成为关于早期尼德兰艺术的基本读物。标题虽得名于凡·艾克兄弟,但对德沃夏克而言,确定兄弟二人在《根特祭坛画》上的分工并不具有实质性的难度,需要深究的是这件作品呈现出两种不同风格的原委。德沃夏克之前,《根特祭坛画》往往被视作一件纯粹出于画家天赋的作品,中世纪艺术似乎没有为它创造任何先决条件。德沃夏克则突破以往研究范式,将《根特祭坛画》与凡·艾克兄弟的其他画作一同纳入晚期哥特式艺术的谱系,期望从中寻得有关新风格的启示。
为实现这一目标,德沃夏克构造了一个以自然主义的逐渐完善为主线的风格框架。他将凡·艾克去世前一个世纪的法国和尼德兰的绘画史划分成四个阶段,分别命名为第一意大利风格[erste italianisierende Stil]、第二意大利风格[zweite italianisierende Stil]、第一自然主义风格[erste naturalistischen Stil]和第二自然主义风格[zweite naturalistischen Stil]。第一意大利风格源于法国王室在14世纪中期接触到的阿维尼翁教会艺术,延续数十年之久直至查理五世[Charles V of France,1338-1380]崩逝,代表人物是安德烈·博纳弗[André Beauneveu]一类的宫廷画家。第二意大利风格或称勃艮第风格,主要流行于14 和15世纪之交,以法属佛兰德斯的权力兴替为节点,代表人物为梅尔基奥·布罗德兰[Melchior Broederlam]和克劳斯·斯吕特[Claus Sluter],斯吕特也因纯熟的写实技巧而被划入第一自然主义这一较为晚近的风格。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自然主义伴随胡伯特·凡·艾克[Hubert van Eyck,1385-1426]的辞世而落幕,第二自然主义贯穿于扬·凡·艾克[Jan van Eyck,1390-1441]余下的画家生涯。7Dvořák,Max.“Das Rätsel der Kunst der Brüder van Eyck.”Jahrbuch der Kunsthistorischen Sammlungen des Allerhochsten Kaiserhauses,no.24,1903,pp.264-267.
在德沃夏克的参考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布尔达赫[Konrad Burdach]的专著《从中世纪到宗教改革》[Vom Mittelalter zur Reformation,1898]。布尔达赫曾和德沃夏克一同求学于维克霍夫门下,作为一名文学史和语言史家,他的论述通常立足于一般文化史背景,对个别艺术作品不作涉及。但他对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潮经由阿维尼翁教廷传入北方的看法,显然为德沃夏克的风格框架规定了起点。按此思路,早期尼德兰绘画的自然主义便可以被历史性地推导出来。在上述风格时期里,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地理位置上看,法国宫廷都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将15世纪的北方绘画与阿维尼翁教廷的趣味联系起来。8即阿维尼翁画派[Avignon School]。西莫内·马丁尼[Simone Martini]是该画派的奠基者,他于1335—1340年在阿维尼翁为教皇服务,并将锡耶纳纪念性和古典主义的图画性传统带入当地,这与当时法国绘画的矫揉造作的线性风格截然不同。阿维尼翁画派的影响力波及法国北部的抄本小画和彩色玻璃画。在这之中相沿成习的,其实是内在于托斯卡纳绘画的图画性[malerisch/pictorial]倾向。它来自于拜占庭的艺术传统,包含了乔托式绘画与杜乔所领导的锡耶纳画派的风格特性。德沃夏克指出,法国宫廷画家在第一意大利风格时期只会原封不动地挪用托斯卡纳的设计图样,直至第二意大利风格时期方可乱真地模仿它们。此间出现过不少粗劣之作,但这都属于以图画性为目标而做出的努力。9关于意大利艺术在14世纪对法国哥特式的影响,潘诺夫斯基在《早期尼德兰绘画:起源与特征》中的论述可以作为德沃夏克文本的参考文献。潘氏归纳出乔托和佛罗伦萨画派与杜乔和锡耶纳画派两个风格来源,前者利用线性透视将人物置于纵深空间,后者发展了意大利绘画通过拜占庭手抄本了解到的“希腊手法”[Greek Manner]。14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国际哥特式是法国宫廷主题和以上两类造型母题的结合。见Panofsky,Erwin.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Its Origins and Charact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2-20.
与之相对,凡·艾克兄弟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根据宫廷艺术的先例发展出了一种完全独立的自然主义风格。凡·艾克兄弟的创作年代可被称作“后古典时期”。到此时,意大利的古典主义范式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哥特式艺术精细的描绘方式在经过改造之后重新回到历史舞台。一言蔽之,正是意大利图画性和法国线性风格[zeichnerisch/linear]的结合为经验现实的再现敞开了天地。古典艺术具有与自然现象相近的外观,却缺少像法国哥特式雕塑那样鲜明的个性和心理特征。从12 到14世纪,这些雕塑从建筑布景走向克劳斯·斯吕特刻刀下的独立形制。它们被塑造成宗教故事或传说中的古老形象,观者使用目光“几乎就可以书写出每道褶痕的历史”。10同注7,第293 页。这不禁令人想起德沃夏克在《哥特式雕塑与绘画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Idealismus und Naturalismus in der gotischen Skulptur und Malerei,1918]中的表述:哥特艺术家“尽力赋予代表了玄秘绝对的、永恒的以及神圣共同体的人物以一种实在的形象,以呈现于观者眼前”。11[奥]德沃夏克,《哥特式雕塑与绘画中的理想主义与自然主义》,陈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72 页。
这套发展逻辑最终指向了凡·艾克兄弟各自的作品及其合作的《根特祭坛画》。在德沃夏克的构想中,第一自然主义是意大利再现技巧和法国自然主义初步融合的产物。它对应于“法国哥特式绘画的最后一种风格”,作为其代表的胡伯特·凡·艾克“可能是哥特式艺术最杰出的画家”。12同注7,第297 页。第二自然主义与早期尼德兰绘画的新自然主义挂钩。扬·凡·艾克的新风格只有到他成熟时期才形成,他的造型基础可以说是植根于上一代绘画传统。尽管如此,使第一和第二自然主义彼此分立的不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某种飞跃式的突破。
借助于《根特祭坛画》的“前身”《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Trè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德沃夏克直观地解释了两种风格的共性。在这组插图中,林堡兄弟[Limbourg brothers]采用手抄本装饰的制作手法再现动植物外观,其精细程度,足以将他们从大自然获得的愉悦感酣畅淋漓地展示在画面上。但这并未背离晚期哥特式艺术的形式语汇。不过,还有一部分插图较为灵活地运用了乔托式绘画的空间透视法,如《三王来拜》(图3)。画家从统一视点描绘城堡和宫殿的结构,把建筑连同动植物与风景纳入不同的空间层次。新自然主义所要求的客观性至此才露出端倪:

图3 林堡兄弟,《三王来拜》《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fol.51 1412—1416年,羊皮纸蛋彩 29 cm× 21 cm 尚蒂伊城堡孔代博物馆
林堡兄弟《三王来拜》[Anbetung der Heiligen drei Könige]的风景效仿的仍然是14世纪的样式,不过画家对它进行了自然主义的改造。改造涉及空间再现和单个的风景母题,因此这里的风景不再像大多数14世纪绘画那样,仅仅是一个朴素的背景。三组骑兵距离观者远近不一,他们从群山之间相互隔绝的丘陵走来。与《根特祭坛画》上的神圣隐士类似,这一创造唤起了纵深的空间。背景中的城市也不再像14世纪的画作那样矗立于山脊之上,而是浮现在山峦背后的云雾之中,就像我们经常会在扬·凡·艾克的风景画里看到的。13同注7,第260 页。
德沃夏克的描述勾勒出了第一自然主义的大致轮廓,同时还使我们了解到,早在《根特祭坛画》之前,写实风格就已经在14世纪后期的手抄本插图中传开了。除却林堡兄弟的作品,许多晚期哥特式绘画也都显示出与《根特祭坛画》的外在相似性,在空间关系的探索上仍为尝试之作。《根特祭坛画》也因此被撕掉新事物的标签,成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综合以上方面可以看出,《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的重要性就在于对自然主义的重新评价。德沃夏克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风格理论,不仅深入辨析了中世纪晚期的自然主义,也有助于他在鉴定《根特祭坛画》时敏锐捕捉到了凡·艾克兄弟风格之间的张力。前文已经简要介绍了自然主义的基本特点,那么,新自然主义的特殊性又存在于何处?若想把握这一风格史概念,洞察德沃夏克前期研究方法的幽微,还需将关注点移至《根特祭坛画》本身。
二
到圣像破坏运动全面展开,《根特祭坛画》一直存放在根特圣约翰教堂的礼拜堂内,该教堂现已更名为圣巴夫主教堂[Saint Bavo Cathedral]。当时记录这件作品的文献,已经有一部分试图解答作者的身份问题,例如,16世纪的尼德兰历史学家瓦内威克[Marcus van Vaernewijck]就在他的游记中提到了画家扬·凡·艾克有一个兄弟。14同注7,第173 页。1823年,柏林一名修复人员在清理《根特祭坛画》的表面涂层时,发现了位于画框底端的四行诗铭文。文字信息证实了先前的记载,即《根特祭坛画》是胡伯特·凡·艾克着手创作,在其死后由扬·凡·艾克续作完成的。但这同时引发了关于分工问题的争议,妨碍判断的最大因素是胡伯特信息的空白。无论是胡伯特的存世作品,还是记录他言行的档案证据都并不充分,铭文却将他称作“最伟大的画家”[pictor major quo nemo repertus],他何以获此殊荣?在梳理过1823年以来的观点后,德沃夏克直接采纳了学界的普遍看法,认为胡伯特是祭坛画的最早创作者,绘制了上层的三块中心镶板,闭合状态下的镶板则由扬·凡·艾克续作,其余尚无定论。15同注7,第173 页。
《根特祭坛画》由二十四块镶板组成,内外各占二分之一。祭坛画开启后分上下两层,《三神像》[Deësis](图4)和《礼拜羔羊》[Adoration of the Lamb](图5)居中心位置。据德沃夏克考证,《礼拜羔羊》更像是在再现圣徒传记故事集《金传奇》[Golden Legend]中诸圣日[All Saints’ Day]场景,16《新约·启示录》曾二十九次提及“狮子似的羔羊”(“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以基督复活的隐喻宣告基督教的胜利。羔羊在第一次显现时,从上帝的手中拿过书卷,揭开七印。具体可参见《新约·启示录》第5 章到第8 章,《圣经研修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18年,第2106—2111 页。而不是图解《圣经·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羔羊揭开七印”[Lamb opening the seven seals]的情节。17《金传奇》由意大利编年史家雅各布斯·达·瓦拉金[Jacobus da Varagine]编写于1259—1266年,是一部关于中世纪圣徒口头传说的百科全书,每章记载一位圣徒或一个基督教节日。德沃夏克认为《根特祭坛画》打开后的镶板取材于《金传奇》所记载的这则故事: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教堂司事在巡视时不小心睡着,这时他看见了“万王之王”全能的上帝。上帝坐在宝座之上,天使唱诗班位于他的两侧,“所有天使都在他的身边驻足”,而圣母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头戴光彩夺目的王冠”,他的左手边是“身着驼毛”的施洗约翰,在这之后“无数圣女向宝座走来……之后是各个民族无尽的人群”。同注16,第253 页。德沃夏克还指出《根特祭坛画》在主题和创作意图上的矛盾之处:这件作品虽然被当作祭坛装饰,按照诸圣日的教义和内容来描绘,却不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思辨的产物,而是表现了艺术家和赞助人高度私人化的宗教感情。18同注16,第254 页。德沃夏克意识到,还原图像志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根特祭坛画》的归属问题。他将视线拉回到作品本体,把《三神像》的人物造型和《礼拜羔羊》的空间结构当作论述的中心。正是在这一点上,莫雷利以形态学特征为基础的鉴定学方法得到了深化和完善。19莫雷利的归属鉴定法受到比较解剖学和植物分类学的启发,从形式语言中提炼出三条标准:人物的姿势及运动、衣饰的褶痕和色彩组成的总体印象;艺术家惯用的表情模式;解剖的细节、风景背景与色彩的和谐构成。最早将这一方法引入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是维克霍夫的老师陶辛。见范景中主编,《美术史的形状: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傅新生、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180 页。德沃夏克先是感慨了《三神像》宏大、肃穆的精神特质:

图4 凡·艾克兄弟,《三神像》《根特祭坛画》镶板 1425—1432年,木板油画 根特圣巴夫主教堂

图5 凡·艾克兄弟,《礼拜羔羊》,《根特祭坛画》镶板,1425—1432年木板油画,137.7 cm× 242.3 cm,根特圣巴夫大教堂
乍看之下,你会感到他们具有共同的个性和同样特别的艺术情感,有的观者把这看作艺术作品中透露的神的威严,有的认为这是木偶的无动于衷。真相介于两者之间:三座圣像那超脱世俗的宁静与崇高,只有早期基督教时期的镶嵌画与之相像。似乎他们身上仍然保留了古代–中世纪教会艺术的光辉。但是他们也没有教会和中世纪的灵魂。他们面无表情,目光显露不出任何内在的生命力,似乎漂亮的头部只是偶然从人身上借来的特性。他们是神,不是人类!20同注7,第189 页。
这段文字指明了《三神像》的疑点。首先,相对于画中的群像部分,《三神像》的尺度异常宏伟,以至于当人们面对这件作品时,扑面而来的只有从中世纪圣像传统延续下来的永恒神性,而不是在《根特祭坛画》创作年代兴起的新自然主义风格。再者,以上帝右侧的圣母像为例,其“天国的女王”的高贵姿态脱胎于14世纪的拜占庭–古典母题,代表了一种理想美的范式,缺少早期尼德兰绘画的室内女性那种生动可爱的生活情趣。以上两点说明《三神像》仍被包含在中世纪晚期的造型体系内。为进一步确定作品所属的风格时期,德沃夏克又从画面上提炼出大量可资分类与比较的形式,并把它们命名为“半张的嘴”“低垂的眼睛”和“上移的瞳孔”等等。不同于画面整体的精神性特质,这些精美却千篇一律的细节无疑与第一自然主义的特色相称——《三神像》确实是胡伯特·凡·艾克的作品。
德沃夏克认为,上述母题源于日积月累的记忆图像,故而总是显得规矩,甚至呆滞,由它们组合而成的人物形象也往往流于僵化和刻板。第一自然主义画家素来把样板当作再现性艺术的基础,即便是铭文所指“最伟大的画家”胡伯特也不可能免受惯例的制约。与之相反,由于扬·凡·艾克从加工样板转向了写生客体对象,他笔下的人物摆脱了固定的程式。这一创造性的行为,需要追溯到中世纪后期以精确观察和直接描绘研究对象为基本内容的自然研究[Naturstudie]。德沃夏克声称,正因扬·凡·艾克有预先绘制素描草图的习惯,他才能在创作时迅速地切中肯綮,画其所见而非所知,“使圣乔治和圣多纳蒂安看上去像他的同时代人”。21同注7,第209 页。
扬·凡·艾克虽然不具备科学的解剖学知识,但凭借他对人体结构的熟悉以及对各个局部有机联系的把握,依然制造出了可以乱真的效果。通过举用《根特祭坛画》内外两侧圣母像的例证,德沃夏克形象地点明了两种自然主义的细微差别:扬·凡·艾克对照静态的模特写生,他的《圣母领报》[Annunciation]圣母有着“严肃、思索的目光”,而胡伯特所作的“天国的女王”“眼睛空洞无神,不是在看,而是在茫然地注视”。22同注7,第193 页。
循着《三神像》的表现手法,德沃夏克追踪到《礼拜羔羊》前景的圣徒群像,在这他提出了归属鉴定的分类依据:“正是人物的逼真自然及其在空间中的自由分布,把14 和15世纪、中世纪和现代绘画区别开来,圣徒群像就需要从这个方面加以区分”。23同注7,第200 页。德沃夏克暗示群像之中包含了两种风格,且有一部分面孔出自托斯卡纳的样板。比如聚集在羔羊祭坛左侧的《旧约》人物,它们同样是胡伯特·凡·艾克的作品。这些老者身披沉重的长袍,有着波浪般的胡须、线条分明的轮廓和傲慢撅起的嘴唇。另外,德沃夏克还提醒我们注意画家构造空间的方式。《礼拜羔羊》的群像被描绘成一个封闭单元[geschlossene Einheit],圣徒们如剪影一般,或并置或交叠,彼此之间不留任何空隙。这只能说明,为了回避表现空间层次的难题,具有仿古倾向的“空白恐惧”[horror vacui]仍在发挥作用。24“空白恐惧”指的是用细节填满作品表面或空间的创作手法,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大自然厌恶空白”是其来源。而后这一概念作为一种构图原理,在古代晚期和早期基督教艺术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在《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中,李格尔认为“空白恐惧”源于原始人装饰身体的冲动,是人类心灵在艺术创造中的自主选择。见[奥]阿洛伊斯·李格尔,《风格问题:装饰历史的基础》,邵宏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32 页。相对地,在右侧的《神圣的隐士》镶板上,另一群按透视结构分布的圣徒正有序地退向风景背景。随着类似的对偶属性不断增加,凡·艾克兄弟的风格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清晰。
三
鉴定凡·艾克兄弟在《根特祭坛画》上的角色分工,对早期尼德兰绘画的研究者来说还不够。弗里德兰德[Max Jakob Friedländer,1867-1958]更在意德沃夏克对凡·艾克兄弟风格差异的评论,并且从中看出了问题。弗里德兰德称,德沃夏克一味地夸大风格的对立,却未能顾及《三神像》中人物的宗教地位对比例的要求:“胡伯特退入阴影,仍然蒙受中世纪的束缚,扬却照亮一条光明之路,德沃夏克是把偏见和歧视带进了观察。”25Friedländer,Max J.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Frederick A.Praeger,1967,p.54.德沃夏克似乎使“最伟大的画家”胡伯特沦为平庸之辈,这使他的艺术鉴定方法遭受质疑。然而,弗里德兰德的评价其实有违他的原意。德沃夏克把晚期哥特式艺术的自然主义取向视作凡·艾克兄弟赖以共存的母体,也是他们的风格之谜的答案。他承认胡伯特是扬的引路人,同时又认为,在沿袭中世纪程式的过程中,扬·凡·艾克以自然观察为手段松动了既往的法则。26同注7,第315 页。
德沃夏克追问,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扬·凡·艾克的新自然主义是在接手《根特祭坛画》期间逐渐形成的?扬所作的《亚当》《夏娃》镶板具有超乎寻常的真实性,更接近于他成熟时期的风格,这使它们赢得的关注远胜其他。既然德沃夏克将《根特祭坛画》上第一对人类夫妇的画像称作“象征新艺术与中世纪传统决裂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它们的出色之处究竟在哪里?行文至此,有必要另行引入一个概念。德沃夏克看到,较之哥特式自然主义,新自然主义的优势在于能“唤起与现实相对应的立体错觉”。这一表达可以被替换成一个更为凝练的说法,即“逼真性”[Naturtreue]:
逼真性的新概念之所以不同以往,是因为它取代了人和物体的程式化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满足于再现那些产生于印象和概括的类型化的形象,科学精确地再现个体的造型和所描绘对象的物质特性成为了逼真性的无条件要求。我们在扬的画中发现了这种观念,而胡伯特却没有。这就是14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中世纪与现代艺术的区别所在。27同注7,第249 页。
针对这一问题,德沃夏克在后来的写作中提出,“再现性图像既要忠实于它的内容,又要忠实其存在的现实性”。28同注11,第6 页。仅就《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一文,新自然主义的“逼真性”概念也涵盖了认知和技术两个不同层面的要求。自然观察是风格转型的前提,但若仅占有写生一项专长,扬·凡·艾克可能就难以突破哥特式艺术的旧制,胜任新艺术缔造者的头衔。德沃夏克首先要我们认识到的是观念上的变革。类似于人物造型,中世纪晚期的色彩调配方式也是约定俗成且极为有限的。画家按照程式创作,几乎不会主动去观察和再现物体微妙的色彩关系。扬·凡·艾克及其画派不仅像前辈林堡兄弟一样,开始关注物体在物理环境中的位置,而且对所描绘对象的颜色做出了固有色、光源色和环境色的层次划分。事实上,无论是德沃夏克所谓的“现代绘画的本源”[eigentlich Ursprung],还是《亚当》《夏娃》镶板的逼真性,都可追溯到色彩对画面的支配和统一。
迄今为止,已经有许多材料专门探讨扬·凡·艾克领导的光色革命,像派希特就曾述及,“凡·艾克式绘画的中心问题,是通过色彩使无处不在的光线变得可被感知”。29Pächt,Otto.Van Eyck and the Founders of 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Harvey Miller Publishers,1999,p.14.换个角度看,这也相当于坐实了德沃夏克的推论。在潘诺夫斯基的《早期尼德兰绘画》中,新自然主义的成功被归结为三个因素。其中“大胆、包罗万象却又有所选择的自然主义对视觉吸引力的提炼”和油画技法的应用这两点均可与德沃夏克的观点相对应。30同注9,第2 页。
新自然主义对观察和描绘方式的推进已成共识。但对于它跟油画技法的关系,学界一向各有说辞。瓦萨里在他的天才神话中首先记录下扬·凡·艾克的传闻,“北方的瓦萨里”卡勒尔·凡·曼德尔[Karel van Mander]尾随之。他们把扬·凡·艾克视作早期尼德兰绘画的先驱人物,相信他之所以能比前人更好地模仿自然,就是因为发明了油画技法。德沃夏克不否认技法之于新自然主义的意义,但他始终认为这只是一个附加条件,扬·凡·艾克是“自然主义色彩财富的发掘者”,不是瓦萨里眼中的发明家。他用怀疑的语调来回应前人的观点:“新的绘画方法是否源于油画技法,或者相反,可以追溯到一种在艺术发展中得到证实的趋势……这是需要继续讨论的。”31同注9,第224 页。
更何况德沃夏克遭遇的是这样一个节点:19世纪中期以来,新的绘画流派层见叠出,“凡·艾克兄弟对自然主义的发现又被赋予新的内涵”。32在18、19世纪的欧洲,哥特式理想主义一度被用来彰显民族特性。自维奥莱·勒–迪克等人重新确立哥特式理想主义在法国的地位,法国中世纪艺术便与这一风格挂钩,与此同时,较理想主义更为晚近的自然主义则被视作尼德兰艺术的特色。见注7,第163 页。通过回顾自然主义发展史,艺术史家期望为这些风格的出现寻找根据。因此在评价扬·凡·艾克的新自然主义时,他们跳出了瓦萨里–曼德尔的阐释框架,着眼于当下对于艺术的关怀。在这一形势之下涌现出了诸多说法,其中,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拉波德侯爵[Léon de Laborde]和路易·库拉若[Louis Courajod]等法国学者的观点流行一时。基于丰富的档案材料和直观经验,这些人透过社会变迁的视角看待新自然主义的形成,将中产阶级的崛起确立为其前提。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里,德沃夏克也使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中世纪晚期的经济史和政治活动,以作为对风格分析的补充,他把新艺术的国际化归因于当时的法国贵族对奢侈品的强烈需求,正是这一点影响了佛兰德斯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奥地利历史研究所求学的几年里,德沃夏克曾两次接受帝国政府的旅行助学金前往法国。33同注6,第570 页。若说《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中的文化史部分出自德沃夏克对路易·库拉若和欧仁·明茨[Eugène Müntz]等人的批判继承,并不令人惊奇。
库拉若曾出任卢浮宫雕塑部馆长,1887 至1896年,他在附属美术学院开设过一系列雕塑史讲座,后题名为《法国文艺复兴在14 和15世纪的起源》[Origines de la renaissance en France au XIVe &au XVe siècle],1901年出版。库拉若颠覆了米什莱、布克哈特以来的文艺复兴艺术史观,提出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双重复兴的构想。他认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并非肇始于古代遗产启发之下的意大利,而是更早的法国哥特式艺术。34Ridderbos,Bernhard.,et al.,eds.Early Netherlandish Paintings:Rediscovery,Reception and Research.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5,pp.52-56.德沃夏克据此形成了自己的假设,与之互文地,他用“写实和个性化”来描述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然而,二人却在起源时间和地点的认定上出现分歧。在库拉若看来,哥特式艺术从理想主义到自然主义的转向得益于14世纪下半叶进入勃艮第宫廷的尼德兰艺术家,例如克劳斯·斯吕特。为此他还发明了“国际哥特式”[gothique international]这一术语,专指1390年左右在欧洲北部集中爆发的新风格。在谈及同一时期作品时,德沃夏克并没有采用库拉若的提法,而是以较为笼统的“晚期哥特式艺术”[spätgotische Kunst]来命名。
库拉若认为,12 至14世纪的法国艺术在发展上陷入僵局,只能以一种均一化的理想主义风格示人。35同注7,第250 页。对此,德沃夏克已在教授资格论文《诺伊马克的约翰的手抄本彩饰》[Die Illuminatoren des Johann von Neumarkt,1901]中给予指正。受制于单一的视觉材料,库拉若的判断必然会有偏失。而德沃夏克不仅关注大教堂雕塑,更放眼于手抄本这一在中世纪产量最多的媒材。在分析波希米亚手抄本画派的成因时,他发现空间透视法的雏形已于12世纪中期通过意大利的经文抄本[Codex]传入法国。36Dvořák,Max.“Die Illuminatoren des Johann von Neumarkt.”Jahrbuch der Kunsthistorischen Sammlungen des Allerhochsten Kaiserhauses,no.22,1901,S.118.中世纪晚期的北方手抄本与15世纪的佛兰德斯镶板画多有重合,如集中式构图、连贯的内外空间、风景和建筑母题等。在此之前,巴黎美术学院的欧仁·明茨已经注意到《贝里公爵豪华时祷书》插图与《根特祭坛画》在风格上的相似性,但他囿于证据不足,不敢贸然推论。37同注7,第282 页。为了力证这种联系,德沃夏克将当时用于装饰贵族宅邸的挂毯和壁画也纳入了考虑范畴。
可以看出,德沃夏克对不同风格交流、吸收与融合的关注,越过了时间、地理和材料的边界。在搜集第一自然主义风格的代表作时,他意识到织物底图在15世纪初商业交换中所占的比重,而后便去分析佛兰德斯为勃艮第宫廷织造的挂毯和弥撒礼服上的刺绣图案,从中识别出了胡伯特·凡·艾克的风格特性(图6)。这一思路合于他的老师维克霍夫在普遍史语境下考察艺术现象的主张。《诺伊马克的约翰的手抄本彩饰》就是作为皇家图书馆彩饰手抄本图录的导论,在后者的敦促下写成的。38同注36,第37 页。维克霍夫非常认可德沃夏克关于中世纪手抄本的课题,他曾在这位学生的简历中评价道:“他[德沃夏克]是中世纪晚期抄本小画最好的鉴赏家之一,至少在德意志的艺术领域是最好的。……对中世纪晚期手抄本的鉴定和分类归根到底源自他的研究。”39同注6。

图6 《金羊毛骑士团礼拜仪式法衣》1425—1440年,330 cm × 164 cm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底稿由罗伯特·康宾创作,其艺术风格通常被认为是对《根特祭坛画》的回应
四
20世纪初,书籍彩饰仍被视作一门次要艺术[minor art],40小文杜里曾在《艺术批评史》中作如下划分:美的艺术或美术[fine arts]用于再现人及其相关的事物,而小艺术(次要艺术)仅指装饰[decoration]。见[意]廖内洛·文杜里,《艺术批评史》,邵宏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1 页。往往是在视觉材料极为有限时,才会得到艺术史家的垂青。而像织物、彩色玻璃画等工艺美术门类,门庭冷落的程度更甚于此。在前期的风格史研究中,德沃夏克一心投入到当时不受重视的艺术时期与类型,其志趣响应了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学术传统。但正如李格尔和维克霍夫的用意,德沃夏克把古典和后古典时期的艺术一并纳入普遍史全景,所体现的也是一种目的论导向。他的目标系于“我们时代的艺术”,也就是印象主义绘画。与扬·凡·艾克一样,印象派也以外光写生和由此引发的色彩革命著称,而巴比松画派画家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在这方面曾予以印象派重要启示。德沃夏克不禁自问:“如今还有多少人能隐约感到米勒在绘画史上代表了一个与扬·凡·艾克相似的转折点?”41同注7,第315 页。与其说新自然主义是艺术史上空前的断层,不如说它是哥特式自然主义经过完善的结果。同理,中世纪艺术也不意味着倒退,而是从威尼斯画派、委拉斯凯兹、伦勃朗直至印象主义这一发展历程的预备阶段。
至于德沃夏克采用线性进步风格史观的理论依据,他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的开篇即已指出:“再现形式的发展问题是艺术史真正且至关重要的基础。”42同注7,第167 页。众所周知,现代图像学尚未普及之时,形式分析一直主导着艺术史的话语权。而在论证自然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赓续时,德沃夏克坚持主张,无论是所描绘对象的真实性,还是艺术家创作观念的先进程度,都植根于既有的形式条件。单件作品如《根特祭坛画》绝非孤立、偶然的事件,它必然与前后现象发生联系,一道构筑起艺术史的发展链条。德沃夏克曾将艺术作品间的遗传关系比作经院哲学思想:
正如经院哲学教会我们如何将一系列合乎逻辑的想法组织起来,现代科学也教会我们如何将个别事件逐渐转化成发展的链条,从真实或假定的因果关系上看,它都是令人信服的。43同注7,第166 页。
德沃夏克从事艺术史研究之初,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等新康德主义哲学家还未在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之间划定严格的边界,对于处于初创时期的艺术史学科,自然科学的概念模型仍具参考价值。即使已经阅览无数原作,如何组织现有的观察经验,理解风格的一致性,如何重塑艺术史的发展逻辑,为新作归类和命名,依然是德沃夏克与身后整个维也纳美术史学派需要面对的问题。另外,将作品的风格与归纳法结合起来,还有更为实际的考量。早在德沃夏克之前李格尔就指出,只有认识到作品之间的内在发展关系,参照创作所依据的前提来推断,才能还原单件作品的真实内容。44同注5,第114 页。个别作品是普遍发展史的一部分,德沃夏克之所以通过划分风格时期来标记中世纪晚期的艺术作品,首先一点显然是为以实证的方法对《根特祭坛画》做归属鉴定。
除风格的发展问题,探讨发展的动因也是风格史写作不可缺少的内容。为了证明新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并非一蹴而就,德沃夏克将风格演变的驱动力诉诸于内在的直观[Anschauung]和直观化[Veranschaulichung]冲动。质言之,审美主体观察经验的丰富、理解与接受能力的提高,导致了其审美需求的提升。自然主义的含义随之转型,艺术家从复制风格化的母题改为靠写生来模仿自然。德沃夏克并未就这一问题深入下去。科勒[Wilhelm Köhler,1884-1959]谈到《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时,认为它反映了李格尔的某些思想,所指大抵就是德沃夏克对文化心理学的简略涉及。45Köhler,Wilhelm.“Max Dvořák.”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no.39,1923,S.319.不过,德沃夏克同时期的其他文章表明,这时的他确实致力于为风格的自律性辩护,试图通过建立科学的体系赋予艺术史以独立学科地位,使之与历史学相区分。46同注5,第189 页。对他而言——就如对李格尔那样,外部因素如材料、技术和功能以及图像志,仅仅是干预风格内在一致性的“摩擦系数”。
施洛塞尔在〈维也纳美术史学派〉中称后期的德沃夏克将“风格史与文化史研究综合为一体”。47同注1。其实这一倾向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一文已有相当显著的体现,借此我们也可看出德沃夏克对文化史难以割舍的态度。德沃夏克反对将文化史和艺术史上的平行现象进行类比,强调一般的文化前提只是促成风格变化的间接条件。48同注7,第271 页。尽管如此,他依然为我们勾勒出了自然主义在中世纪后期从法国宫廷到阿维尼翁教廷,再到佛兰德斯城市的传播路径。在这期间,意大利的人文教育和法国贵族文化承担了风格载体的角色,扬·凡·艾克的艺术位于两条线索的交叉点。针对德沃夏克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里广泛援引文化史和文物史实例的行为,他的学生安塔尔[Frederick Antal,1887-1954]的解释是,“风格概念不等同于形式特征”,要想避免对一件作品做出主观判断,唯一可靠的手段就是掌握它的历史背景。49安塔尔指出,像《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这样,在研究起源问题时探讨佛兰德斯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做法,只在经济史著作出现过。见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封闭与开放:20世纪中期艺术史方法论述评〉,冯白帆、孟尧译,载《美术》2021年第1 期,第132 页。
透过心理学和文化史两面棱镜,德沃夏克前期的风格史方法获得了全方位的呈现。他结合自然主义的发展原理得出结论:“像扬·凡·艾克这样不受限制地展示现实世界,不是自然主义的开端,而是一种必然的终结。”50同注7,第165 页。.于是新艺术的来历便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中廓清。如果我们还记得德沃夏克对现代艺术的关照,那么可以说,他也间接地完成了为印象主义正本清源的任务。德沃夏克在文章结尾评述道:
这种“对自然的新发现”既不是他(扬·凡·艾克)个人的成就,也不是他那个时代其他艺术家的成就,而是产生于整个哥特式绘画长期发展的成熟果实。这是一种新的、更严格和科学的写实概念以及与之对应的再现手法,它们构成了新风格的基础。这两者都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在数代人的观察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扬的艺术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或许也是对他自己——既不是什么变化,也不是一场对抗历代艺术的革命。唯有当后人不再熟悉那些时期时,它才作为一种颠覆或作为新的基础出现。51同注7,第314 页。.
德沃夏克曾用大教堂门廊两侧的纪念性雕塑形容《根特祭坛画》的两种风格:一边是《旧约》人物,象征古老、已逝的中世纪艺术,一边是《新约》人物,预示着一种以胜利姿态面向未来的新风格。52同注7,第213 页。这又何尝不是扬·凡·艾克自身的写照?诚然,画家极富革新精神,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新意并不突出。若是将他的作品放在风格史中来看,不难发现它们实为哥特式艺术合逻辑发展的结果。不过,扬·凡·艾克的色彩表现力还是使他的画面效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德沃夏克认为,新自然主义的逼真性更多地源自扬·凡·艾克的观察经验,而这经验亦是仰仗数代人的实践才走向了最后的觉醒。现在应该回到由《根特祭坛画》铭文引发的疑案了:胡伯特·凡·艾克是最伟大的画家吗?可以想见,与扬·凡·艾克经常题写在画面下方的花押字Als IchKann[“尽我所能”]意义相仿,《根特祭坛画》上的铭文也只是这位画家表达谦逊的方式。53同注7,第213 页。.
五 结语
德沃夏克在学术生涯前期高度重视风格问题,这既与维也纳美术史学派的学术环境有关,也反映了他既有的研究基础和实践过程中的反思。在《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中,他以扬·凡·艾克在《根特祭坛画》上的笔迹为出发点,通过比较新自然主义与先前形式的异同,来为它在一个更宏大的风格框架中定位,利用艺术鉴定方法和对遗传关系的梳理写就了一部自然主义发展史。十多年后,当德沃夏克在他的《哥特式雕塑与绘画中的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中谈到扬·凡·艾克时,这位艺术史家并未完全放弃他早年的一些基本观点。当然这时,德沃夏克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揭示人类世界观的转变。比如重提“如我所能”这一铭文时,他指出这“不是表达了中世纪的谦逊态度,而是现代人为自己的能力所作的辩护”。54同注11,第114 页。但另一方面,德沃夏克也像以往那样承认,扬“绘画中所体现出的对于自然的感知并不新鲜,其作品中有不少东西可以回溯到久远的年代”。55同注11,第105 页。至于德沃夏克自己,他精神史著述中的某些思想是否也可以回溯到前期的风格史研究?他在风格史中对社会文化的整体观照,难道不足以成为日后重构“精神气候”的根由?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戈尔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1863-1944]指出过两者之间的承接关系,认为德沃夏克后期的方法“只能视作对形式分析的精细化,而不是一种反动”,56[德]戈尔特式密德,〈美术史〉,滕固译,载《新美术》2000年第4 期,第28 页。笔者对此说法深感认同。
《凡·艾克兄弟的艺术之谜》发表后的第二年,德沃夏克接替了李格尔生前的工作,兼任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和奥地利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主席职务,此后便将重心放在文物保护和课堂教学方面。也是从这年的冬季学期开始,德沃夏克逐渐把凡·艾克论文的思路应用到整个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去,在他关于意大利巴洛克艺术和中世纪艺术的课稿中,就流露出了这一取向。57Dvořák,Max.Geschichte der barocken Kunst in Italien.Vorlesung[WS 1905/06]608.IKW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