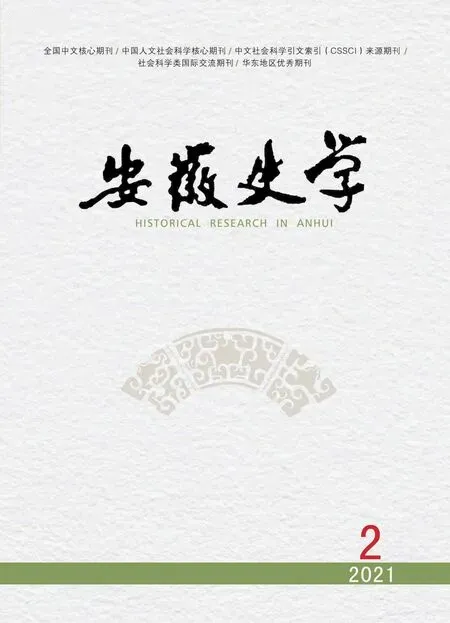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孙竞昊 佟远鹏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引言:明清北部运河城市地方性发展所蕴含的问题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是由于修筑和使用大运河所致。既然地方经济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的漕运引发和支持,那么大运河体制的运转是否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济宁作为一个运河战略要地,受到国家的格外重视,中央政府在济宁州城设置了庞大繁复的行政、军事官僚机构,不仅运河最高管理衙门在地方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卫所等的建制也制约了其作为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
同时,济宁士绅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言人,在各种权力的博弈与调和中积极作为,影响之大在地方精英势力普遍弱小的北方城市中十分突出。他们的努力和欲求可否带来被视为现代政治形式核心的某种地方性“城市自治”?有意义的探索在于,厘清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国家政治权力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如何与特定的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并充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某些变更对济宁地方社会的政治属性及其历史定位的影响。
本文从设立在济宁的官僚机构入手,考察国家如何借助体制与官员个人两种途径在地方政治生活里施展权能,及其与以士绅精英为代表的地方势力相遇而出现的一些反应。因为省级政府、朝廷、皇帝本人都系于运河管理,并把运河传输系统作为行使权力的舞台,所以有必要在以运河为命脉的全国政治经济语境里评估济宁的地位。鉴于明清时期济宁与其他北方运河城市具有相似的城市化经历和城市形态,这样的思考将有助于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理清国家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角色。
一、济宁城内外的政府机构
自秦汉以降,济宁的重要性在于它地处南北交通中的要冲位置,并在战乱时期成为各方争夺的战略要地,但经济却长期维持在一个不起眼的水平,前所未有的变革随着大运河的出现而发生。晚明济宁籍士大夫陈伯友(1583年举人,1601年进士)指出,济宁的重要性系于其在漕运中的地位:
居人曰:济当南北咽喉,子午要冲,我国家四百万漕艘皆经其地。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者又鳞萃而猬集。即负贩之夫、牙侩之侣,亦莫不希余润以充口实。冠盖之往来,担荷之拥挤,无隙晷也。(1)陈伯友:《重修通济桥记》,康熙《济宁州志》卷8《艺文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第46a页。
因为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济宁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繁复、叠加的垂直型和横向型政府机构和组织遍布济宁城内外。
(一)地方行政机构与运河管理
明清政府为了便于监控运河,在运河沿线设立州或直隶州。清代,山东运河沿线先后设置过两到五个直隶州;从1774年到1903年,有济宁和临清两个直隶州。(2)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61》上册,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45页。明代,济宁作为普通州,领三县;清代直隶州时期,也领三县。
施坚雅依中心地理论认为,传统的层级体系依据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设计和规范,然而中国社会的“自然”结构是由非官方因素所决定,诸如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那么,在“正常”的行政管理体系上的变革,是为了应对经济因素和“不规则”的政治、文化因素扮演更大作用的非“自然”结构的变化。(3)[美]施坚雅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7页。新的政区旨在与经济扩张协调,从而在地方管理中施展更强的控制和更深的渗透。如是,济宁保持了多种属性:作为一个城市中心,一个州或直隶州的治所,一个区域中心,即施坚雅所说的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功能的中心地——并不仅是沿着运河,而且是对整个腹地而言。
(二)军事机构与漕运
明清国家军事结构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运河及其他陆地运输线和重要城市均处于高度保护之下。明末济宁籍士大夫杨士聪(1631年进士)曾指出济宁防卫与运河防卫的关系:“贼之不为漕患,恃有济城在也。何不结营于城北二三十里,使贼不敢近城,则不必护漕,而漕无患矣。”(4)杨士聪:《玉堂荟记》下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2页。维系运河运转网络中的济宁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军事集结地。
明初建立起的卫所体系独立于正式的地方行政区之外,但在运河和其他水路沿线,一些军卫被佥派为运丁和护军(5)据梁方仲研究,明代山东担任漕运任务的卫所主要有:临清卫、平山卫、东昌卫、济宁卫、兖州卫、东平所、濮州所。全国163个承担漕运的卫所中,有16个每年漕粮额数超过6万石,济宁卫和临清卫即在其中。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21页。,卫所的军事功能日渐衰落。到1430年代,大多数卫所军户被用作其他职能。(6)[美]牟复礼、[英]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102、103页。至明代中期,济宁建有任城卫、济宁左卫、济宁右卫三卫,各辖5600 名士兵。(7)万历《兖州府志》卷17,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第4页。清初的济宁州志只记载“济宁卫”,参见康熙《济宁州志》卷4,第75a—79a页。清初,山东的大量卫所被取缔或合并(8)《清世祖实录》卷93,顺治十二年九月壬寅,《清实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34页。,卫所人丁几近演变成了专职漕运人员。(9)《清史稿》卷122《食货三》中载:“清初,漕政仍明制,用屯丁长运。”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565页。他们由于漕运任务而纳税较少,受东河河道管辖。(10)李继璋:《济宁直隶州拟稿·建置志上》(手稿),民国十六年稿本,山东省博物馆藏。因人员不足,清代开始有大量汉旗旗丁从事漕运和运河维护工作。清代末年,伴随着漕运的衰亡,运河沿线的卫所制度也在1894—1895年间终结。
在运河体系中使用军户,意味着济宁周边的一部分亚城市人口不在地方行政管理范畴。卫所分担地方防卫职责,特别在动乱时期卫所驻地可以成为城市防御的缓冲地带。但是卫所人口也是当地日常物资与文化财富的消费者,卫所人员时常在使用地方资源如灌溉用水上与当地百姓发生冲突。
明清时期,军事与准军事力量的管理体系非常复杂,其中一些军事机制体现在地方文官管理机构里。在济宁地区,除了正常的军事机构,运河和黄河的管理机构也承担一些军事功能。明代山东的最高军事机构是山东都指挥使司。明中期,全省6个府内共设置18个卫、27个守御所或备御所;(11)嘉靖《山东通志》卷11,明嘉靖十二年刻本,第1a页。还设有两个兵备道,分驻济宁和临清,均源自它们在运河治安上的战略位置。(12)万历《兖州府志》卷17,第1a、3a—3b页。
19世纪中叶之前,清政府在山东境内仅德州、青州驻扎有八旗兵营,但济宁在地方军事管理中的地位依旧非常重要。全省设有两标:抚标驻扎在省会济南;河标驻扎在济宁,接受总督河道御史的监督。济宁设三个河标营,在山东南部的运河码头派驻兵丁,并特设三个城守营与地方军事力量相互协作,负责济宁城的日常安全事宜。(13)袁静波:《济宁清代以来的兵营驻地》,《文史资料》第10辑,济宁市市中区政协1997年编印,第111页。还在山东运河道之下置有运河营。
正如韩书瑞所言,虽然山东地区军事力量的地域分布系因地制宜所主导,但实际的兵力部署,却因应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整。(14)[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32页。在和平时期,驻防在济宁的五个绿营与政府监管的团练、义勇等地方力量协同负责当地安全,其中一个营专责城市。(15)参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9,清乾隆五十年增刻本,第1a页。同页载:“国朝特设城守一营”。一旦周边地区出现战乱,济宁往往成为大量军队集结的指挥部。19世纪中后期,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乱期间,济宁因其地处控制大运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关键位置,驻扎了大量兵力。(16)资料来自同治四年的诏书,参见《清穆宗实录》卷137,同治四年四月丁亥,《清实录》第48册,第213—214页。僧格林沁、曾国藩、李鸿章都曾在济宁作战,僧格林沁战死山东,陵墓建在济宁。(17)民国《济宁直隶州志续志》卷1,民国十六年铅印本,第9a—10a页。由于政府视济宁为维护运河的枢纽,该地区没有遭受到类似山东西部城市通常所遭遇的战火。
(三)大运河、漕运、黄河的专门管理机构
济宁不仅作为州治,且管理或监督大运河、漕运以及黄河水利工程的其他官僚机构也设置于此,政治重要性比一般的州要大得多。在山东西部,运河的维护与黄河的治理息息相关。明清时期,至1855年黄河改道北移前,黄河下游河床在济宁城以南约100公里处。万历《兖州府志》描述黄、运关系:“国家定鼎燕都,仰给东南,惟是一线之流,以供天府。故漕渠通塞,则国计由之盈缩。而河流顺逆,则漕渠视以通塞。二者国之要害也。”(18)万历《兖州府志》卷19,第1a、1b页。山东西部的重要性在清代延续,因其“乃粮运之道”。(19)参见《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己亥,《清实录》第3册,第58页。
北宋开始形成了专门的运河管理机构(20)宋以前主要由地方民政机构负责,朝廷(如户部官员)偶尔插手,参见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4页。,但直到元朝才创设了负责运河维护和运输的水政机构——工部都水监。会通河开凿后,工部的一个分支机构驻扎济宁,负责监管运河和黄河的临近河段。不久,又在济宁设立都漕运使,还任命了闸官,设立了军营。(21)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3—58页。运河在元代南北粮运中的作用不如海运,故而运河的管理并没有一以贯之。明朝济宁的各层级官僚机构全面发展,至清朝更加完善。
《兖州府志·河渠志》记载了明代山东设立的隶属中央和省级的运河管理机构,其中一半设在济宁。例如,自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政府常以都御史出任总督河道,驻地济宁。永乐十八年(1420年),行军司马樊敬受命提兵10万镇守济宁,使运河周边成为一大战略区域。成化七年(1471年),北京派驻济宁的总理河道接掌了大运河的全面监督。(22)陆耀:《山东运河备览》卷2,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第8a页。早在宣德六年(1431年),在济宁等运河的不同河段设立工部都水分司。(23)《明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乙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861页。此后,总理河道也接管黄河及其他邻近水道的水利工程,有权协调地方官员,节制地方卫军,或由工部尚书、侍郎兼任,品阶为二品或三品。同时,省府州亦有专门官员协助总督河道管理运河事务。正德初,明廷设工部侍郎一人,兼任治河都御史,反映了朝廷对地方水利事务的直接掌控。(24)嘉靖《山东通志》卷10,第4a页。弘治三年(1490年),刑部左侍郎白昂奏请山东府州县管河官员沿河居住,管理河道,不许别有差委。(25)《明孝宗实录》卷45,弘治三年十一月癸未,第906—907页。接着,省属的治河都察院和兖州府的三位同知之一也驻地济宁。(26)嘉靖《山东通志》卷15,第1a—1b页;万历《兖州府志》卷11,第1b页。
明代专门的漕运管理机构是在大运河重新贯通后设立的。永乐十五年(1417年),朝廷在淮安设立漕运总兵官,主管运河航道和漕运。景泰二年(1451年),又在淮安设立了漕运总督,负责征收、运输和储存漕粮,与总兵、参将同理漕事。(27)《明史》卷79《食货三·漕运》,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2页。自成化七年始,河道、漕运职能被划分给两个独立机构,即“总河”和“总漕”。地方政府也负有协理漕运之职。在山东,主掌刑狱司法的按察使,也管理漕务。(28)《明神宗实录》卷283,万历二十三年三月戊戌,第5247页。此外,朝廷还指派御史进行定期巡视。(29)《明宣宗实录》卷68,宣德五年七月己酉,第1597页。由此,河道、漕运和水利工程等事宜由总漕、总河、总兵及地方官员协同处理。
清政府基本沿袭了明朝的运河管理体系,但在两方面进行了调整:一是合并了官僚体制的一些功能,注重简洁有效;二是发展了一套更为完善的监督体系,以实现中央对运河事宜的监督指导。(30)Jane Leonard, Controlling from Afar: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p.31-32.总管运、黄的河道总督,顺治元年(1644年)首先设置在济宁,康熙十六年(1677年)移驻淮安,以应对江南紧急河务。(31)《清史稿》卷116《职官三》,第3341页。山东地方官员开始负责管理省内运河、黄河事务。雍正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雍正二年(1724年)增设河南副总河,驻武陟。雍正七年(1729年),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淮安;改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驻济宁。雍正八年,增设直隶河道总督,驻地天津,开始南河(淮安)、东河(济宁)、北河(天津)三督分立。乾隆十四年(1749年),裁撤直隶河道总督,由直隶总督兼管。东河总督全面掌控河南、山东段黄河、运河及淮河以北整个运河区的河务。咸丰八年(1858年),裁撤南河河道总督,职权归于总漕。(32)陆耀:《山东运河备览》卷2,第1a—1b页。
清代总河有提督军务的权力。河督军门署辖下军队驻扎在济宁,负责修堤筑坝、防洪以及黄河和运河的疏浚。职级较低的闸官负责水闸的开关、蓄水和控制。盛清时期,运河共有闸官42名,其中山东28名,济宁最多。密集的河务机构使济宁处于高度监控之下。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途中对此有描述:“大量士兵驻守在官道、运河及河流沿岸的哨所……每三四里远有一个哨所。每个哨所不得少于6人。”(33)[英]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著,何高济、何毓宁译:《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58页。
清朝,漕运总督设在淮安。在漕运总督之下,沿运河和其他漕运线路的各省设粮道,掌监兑漕粮、督押运船等漕务。山东粮道设在德州。并有巡漕御史稽查各处,山东巡漕御史驻地在济宁。(34)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6《漕运各官》,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03页。
(四)济宁官僚机构体系设置的影响
因应大运河所引发的经济发展,济宁等运河地区的政治机构设置更加密集和具体。特设运河机构与常规军民官僚机构平行而立,职能交叉重叠。纵向与横向官僚体制的冲突为区域政治增添了新的变数,重塑了国家与地方的关系。
首先,中央政府通过设立漕运、运河、黄河等办事机构,掌控运河地区。其属员进而派遣到运河沿线和其他水路哨所。朝廷通过对漕运系统和其他运河相关工程的日常管控,将其权力延伸到整个运河和黄河区域。
其次,中央政府通过将运河管理职责划分给特设的运河机构以及地方的军民机构来增强其权威。正如韩书瑞所言,重叠的行政管理实现了朝廷分权和差别分配的目标,从而达到中央权力的集中。(35)[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第27页。同时,漕运需要整个国家机构的协调运作,在各级官僚阶层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设的运河、漕运机构和地方民政机构都承担了财政和管理责任,如兴建水利工程、定期清淤和堤坝监测等。其结果有助于增强国家的政治一体化。
复杂的官僚体制及其功能对济宁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济宁,众多的官署衙门构成城市的显著景观,增添了城市政治色彩。而地方社会的繁杂政治因素增加了济宁城市的复杂性。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的品阶一般为正二品,高于省级巡抚,代表了朝廷的意志。对大运河和黄河水利工程负有实际责任的地方官员,时常倾向于地方利益,又对朝廷法令难以抗拒。此外,卫所兵士及其他非州籍军事人员的利益与地方利益存在冲突。济宁人口密集,官员数量庞大,商人和士兵众多,给地方治理带来了诸多难题。(36)史载:“卒伍之士与齐民杂糅,往往龃龉而不相谐。”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7,第35b页。康熙中期的济宁知州吴柽认为,地方管理的困难之一就是混居人口的注册。(37)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1,第41a页。管理机构的多样性限制了济宁地方行政的效能,也相应增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二、国家事务中的大运河和漕运
漕运作为一种传统的物质与财政资源的集聚机制,正如星斌夫所言,是国家行政管理的经济基础。(38)[日]星斌夫:《明代漕运の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1963年版,第1—4页。明清时期,漕运是国家最为关注的核心事务,故而户部每十年就会汇纂一本《钦定户部漕运全书》。(39)《钦定户部漕运全书》,清乾隆三十一年刊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9年版。与此同时,大运河和漕运对运河区域的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济宁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一)大运河对国家的战略作用
为了攫取财富,实现对整个帝国政治和社会的统治,中央政府需要控制全国最富有的地区,这也意味着国家在不同地区推行不同的政策。水利工程是国家政治调控机制的一部分,“各个朝代都把它们当作社会与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有力的武器”。(40)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9—10页。冀朝鼎划出了全国的“基本经济区”,并指出这些地区通常会进行大规模的治水工程。(41)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8、9—10页。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地带也是一个基本经济区,运河虽然主要是服务于漕运,但是它是一个综合的水利系统,也会有助于水资源控制和地方农业灌溉。更重要的是,漕运体系勾连起其他经济区域,将长江中下游地区最重要的几个基本经济区的赋税输送到北方。全国性运河开凿和重建的选址也凸显了区域的重要性。元代重建大运河,北方的运河网络由中原东迁至山东西部,东部地区成为帝国的核心。明清两代通过大运河的常规运行,实现了中央集权国家统一和稳定的旨向。
然而,大运河穿越腹地的运行面临着巨大的自然和社会困难。在元代,规模不大的陆上漕运在开通后不久就被边缘化。(42)元朝大体依赖于更有效的海上航线,所谓“河海并行,海运为主”,参见李德楠:《元代漕运方式选择中的环境与技术影响》,《运河学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9—60页。海运只涉及专门的运输人员,所以是“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的“良法”,《元史》卷93《食货一》,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364页。至明清时期,通过技术进步和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大运河在大多时间都在正常运转。晚清时期,冯桂芬曾关注南方漕米运往京师的代价,“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43)冯桂芬:《折南漕议》,《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他认为魏源的四金说“甚缪”。其实,魏源也指出漕运高额成本的弊端:“通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载魏源:《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13页。漕运的费用既然如此高昂,朝廷仍重视河运而不是海运,是因为对一个大陆型农业国家来说,河运系统显然是一种更安全稳定的运输方式。明清统治者在认识到海洋世界和海运风险的基础上,采取了保守的策略,即采取了沿南北轴线的传统内陆运输路线,进而对整个国家进行财政、行政和符号的控制。
(二)运河运输与国家的经济管控
济宁等山东地区关于运河工程的大量文献记载,反映了漕运体系对当地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对本地的日常生活节奏的浸染同样深远。从地方角度而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活动通过运河被纳入全国统筹范围。运河沿线地区必须承担各种各样常规与临时的任务,如晚清丁显《运河刍言》中所述:“漕河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44)《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7《户政十八》,清光绪石印本,第37页。运河工程无论采用服役,还是雇工形式,都给当地民众带来大量工作机会,同时也限定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总的来说,虽然运河运输刺激了沿途地区的贸易,但这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供需——也为运河驱动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方向制造了瓶颈。从明中叶开始,朝廷允许漕船携带私货,但是不愿提高私货的比例。由于贡品垄断了运河运输,私人船只无法合理地规划自身运营,而“官豪势要之人”却可“恃官势”“横行其间”,一如明中期的一则评论:“至于运河,乃专为粮运而设,驿递官船亦是借行”。(45)徐陟:《奏为乞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圣治事》,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56《徐司寇奏疏》,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3829页。在运河上,所有其他用途的运输都应该让位于漕运。宣德五年(1430年)的一则奏章称:运河上下“公私舟船往来交错,阻塞河道,漕运不便。奏请遣御史等官巡视禁约”。正如晚明耶稣会士利玛窦所言:“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入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这些运河之间的人们除外。通过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不致践踏。”(46)[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5页。
杨士聪认可运军私携“土宜”的合理性,认为漕运的“祖制寓意”在于“公私两济”。(47)杨士聪:《玉堂荟记》下卷,第47—48页。关于私人利益对公众和国家的积极影响之类的申诉和评议,终究不能改变朝廷经济统制的思维。私人贸易以及整个运河经济受到限制,造成了运河商业经济的脆弱性——国家权力及其政策的任何波动,都可能意味着运河经济的重大变化。因此,运河腹地城市难以摆脱其作为港埠的特性——依赖国家政策,缺乏自身经济再生的自主能力。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漕运为中央集权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
(三)以大运河为载体的政治、军事、社会统合
大运河和漕运是否畅行,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明朝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物品运送到北方边境。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户部奏称:山东全省的税赋为170万两,其中十之九北运戍边。(48)《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第10318—10319页。而在清朝,军事物资主要是发散到全国各处的战略要地。(49)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第113页。为此,政府相应地调整了农业、商业和军事政策,并确保运河区域的安全。山东在运河网络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而在山东,济宁的安全是一大要务。
明清两朝意图利用南北地区日益增强的交流和互动,在政治和文化上规范和强化统治。明朝主要依赖三种通讯方式:驿传、驿递、递运(50)[加]卜正民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5页。,在山东西部,南北驿路与大运河平行,有些路段需要使用大运河。这种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促进了印刷品的流通(51)[加]卜正民文、孙竞昊译:《明清时期的国家图书检查与图书贸易》,《史林》2003年第3期。,带有煽动性的思想和成分在大运河等水、陆交通线上迅速传播。(52)[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2、296页。同时,大运河的交通之利还在于,可以使政府在保障安全、协调在地官僚举措、平息地区动乱等方面获得巨大优势。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和文字狱,仰赖于朝廷利用便利的交通和通讯渠道来收集信息和调度资源,从而加强了与当地文人的联系和对他们的控制。(53)参见R.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87,pp.7-8,49-56,206-208.李欧娜通过对道光皇帝处理1824—1826年大运河危机的研究表明,朝廷的大运河方略是维持大帝国的高度集权。(54)Jane Leonard,Controlling from Afar: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 1824-1826,p.2.
(四)皇帝巡行大运河和济宁
与明朝大多数皇帝严重依赖官僚机构不同,清朝皇帝则是更积极地干预运河和交通系统的日常运转。康熙皇帝曾讲:“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55)《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二月辛巳,《清实录》第5册,第701页。据《清实录》载,清朝皇帝的谕令,经常会涉及到运河及其相关的问题,时常包含诸多细节。皇帝与地方官员在运河问题上交流频繁,洞察日常事务的运行。从济宁所设的专门机构与常设衙门管辖权能的分立与交叉可见,清朝皇帝事实上已经成为汇聚和协调规划与决策的核心。
宏伟的大运河和相关的水利工程为皇帝们提供了展示威严的平台。山东是皇帝沿运河南下巡视的必经之路,在山东北部的德州码头下船,经陆路到泰山和孔庙进行祭拜,随后前往济宁码头,继续乘舟南下。乾隆皇帝一次逗留济宁时,曾赋诗感叹杜甫的命运:“可惜先生未遇时”,借以彰显其治下的繁荣和清明。(56)乾隆皇帝的《题南池少陵祠》,收录于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诗文集萃》,济宁市新闻出版局2001年印行,第237页。他的另一首诗告诫河道总督李宏:“固堤绥禹甸,输漕达燕京”(57)乾隆皇帝的《赐河东河道总督李宏》,收录于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诗文集萃》,第239页。,透露出皇帝企图集中权力和消弭潜在异己因素的巡行目的。
皇帝通过巡行得以亲睹大运河的运作,并直接行使其监督权;同时又告诫臣民,巡行不应干扰运河运输。正德十四年(1519年)春,皇帝南巡时指示北直隶、山东和河南的文武官员,不许扰乱漕运和其他公私船只的正常运行。(58)《明武宗实录》卷172,正德十四年三月己亥,第3317页。与之类似,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要求山东地方官员停止建造行宫,凸显其对民生的关切。(59)⑩宣统《山东通志》卷首《列圣训典》,民国四年铅印本,第73b、99b页。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春,皇帝到山东短途巡视,从济宁沿运河返回北京,公私船只“于两岸暂泊”,他命令“御舟”快速穿过,恢复“商贩流通”,体现“恤商便民之意”。(60)《清高宗实录》卷1349,乾隆五十五年二月辛未,《清实录》第26册,第51页。嘉庆皇帝缩减了巡行开支,十七年(1812年),他要求山东巡抚减少营建行宫的资金,将精力放在基本设施上即可,还诏令节省招待王公贵族的花费。⑩可见,明清皇帝利用了大运河相关的各种资源,巩固和集中国家权力。
三、济宁地区的漕粮征收与运河劳役
作为明清时期治国方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漕粮的征收和运输深深渗透到整个国家特别是运河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央政府以运河为轴心,积极左右地方社会生活,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城乡日常生活和权力结构。
(一)漕粮征收与运输中的国家与地方关系
在明清时期庞大而复杂的税收体系中,作为头筹的漕粮一般从比较富裕的八个省征收。所谓“南粮”,取自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和湖南等地的州县,而“北粮”则征自山东和河南。此外,还有从苏、松、常、嘉、湖等府征收的“白粮”。(61)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页;[日]星斌夫:《明代漕运の研究》,第36—37页。明代及后来学术界所谓的“江南重赋”,实际上是指这些地区的高额漕粮税赋。(62)李文治、江太新等认为,所谓“江南重赋”实际上指的不是田赋,而是一些州县征收的漕粮。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11页。
漕粮征收由地方各级政府执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与赋税表现相挂钩,他们还肩负漕粮运输的职责。明清实录中有山东官员因大运河的相关事宜受到表彰、诘难、擢升、贬职、任命、撤职的大量记载。在漕运过程中,会增添各种附加税。原因之一是地方官员必须利用“非正式的税收”来维持政府开支,这是低税收的后果。(63)[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58—260页。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行政机构的支出和官员的私利很大程度上都依赖这种不规范的征收。(64)参见[美]韩书瑞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第23—25页;[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官员征收赋税和漕粮运输的职责,为其提供了一个敛财的机会。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山东巡抚黄克缵将这种普遍的额外征税列为关税制度的弊病之一。这种“双重”税收,损害了国家和商人的利益。(65)《明神宗实录》卷432,万历三十五年四月辛亥,第8174—8176页。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罗列了运河地区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给当地居民增加的负担。(66)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9,第22a页。
漕运体系所带来的沉重赋税,影响了八省的地方政治和民众生产生活。江南地区尤其如此,扩大再生产能力严重受损。(67)参见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分配结构关系探析》,《史林》1996年第4期。然而,与南方近乎完全消极的影响相比,漕粮体系在北方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二)山东西部与济宁地区的漕粮征收与运河劳役
从明中叶开始,田赋主要以银两形式征收,可是只有小部分漕粮折银。与江南地区相比,北方地区缴纳漕粮的配额虽然较少,但山东、河南和直隶因承担运河运输、维护和治黄工程,大量的民力却被繁重的劳役消耗殆尽。
与运河相关公共工程的劳役多是强制性的,由于自然水资源缺乏,运河北段的维护变得艰巨。疏浚河道淤泥是运河地区常有的一项任务,充分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预算和计划里。(68)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65—271页。在某些情况下,政府甚至从其他地区强征劳工。济宁周边及其辖县纳税虽少,却承担了沉重的劳役。谢肇淛的长诗《南旺挑河行》,表达了他对山东西部运河役夫艰辛劳作的痛切感受:“堤遥遥,河弥弥,分水祠前卒如蚁……浅水没足泥没骭,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风天雨霜,十人八九趾欲断。……君不见,会通河畔千株柳,年年折尽官夫手。”(69)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16b—17a、42b—43a页。徐骏伟作《冬深过天井闸感浚河之苦》诗,有“岂不怀民力,何由竭地泉。村村烟火寂,洒涕办夫钱”(70)康熙《济宁州志》卷10,第16b—17a、42b—43a页。的句子,反映了运河的繁重劳役导致了农业的荒废和破坏。因为以银代役比例的增加,运河维护的体力性劳动和漕运的服务型劳动也逐渐减少。雍正元年(1723年)推行以银代役的措施:“古人救荒之策 ,有大兴役以济民食者,不若竟动正项钱粮,雇募民夫,给以工食。挑浚运河,则应雇既多,散者复聚,民资工食,稍延残喘。”(71)《清世宗实录》卷3,雍正元年正月庚戌,《清实录》第7册,第93页。这些调整客观上促进市场型贸易活动,但不能改变如济宁这样的运河发达地区高额赋役的本质。
济宁籍士人对劳役之累多有愤懑之议。于若瀛道出当地所遭受的困扰:“吾土非干即溢,困于征输。迩者扰之以矿税,纷之以河工。”(72)于若瀛:《弗告堂集》卷21,明万历刻本,第13a页。郑与侨列举了明末吏治腐败下济宁的赋役之重:“今差烦役重,尽加派于一州……是以一州两肩数省之累,济民几何能不皮骨俱尽哉?”(73)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赋役记》,山东省图书馆抄本。康熙《济宁州志》载:山东“六郡称剧困者惟兖,济宁一州又甲于兖属诸邑。故流移难复,宜议招徕,无秽莫治,当策劝劳,亦今之急务也。”(74)康熙《济宁州志》卷3,第1b页。清中期的孙扩图指出:“吾州自绅士至于庶民,均有切骨之累,曰派纳运河秸料一事,盖阅数十年来,无所告诉者矣。夫河员于冬月平价购办秸料,以预运河之需,例也。州派民纳,非例也。派纳而并供各衙署薪烧之秸,尤非例也……兼之胥役奉行不善,交纳本色,则十倍称。收折纳钱文,则一母十子。”(75)孙扩图:《一松斋集》卷1,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第7a页。
可见变本加厉的劳役,使济宁地区的官员和民众苦不堪言。历任官员在奏章和公文中为地方发声,指出沉重的赋役负担,在当地赢得赞誉。但中央政府对地方诉求几乎没有让步,强有力地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权限,特别是在粮食存储方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山东巡抚王国昌与河道总督张鹏翮因擅自挪用常平仓粮食赈济灾民,皇帝斥责他们“掠取名誉”,要求“均摊赔偿”。(76)《清圣祖实录》卷214,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清实录》第6册,第169页。这一事件显示,当地方与国家利益相抵牾时,地方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三)国家借助漕粮的均输角色
对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社会安定有序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为此,需要将一些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给贫困地区,以确保民众的最低生活水平。大运河的正常运行,保证了漕粮的稳定运输,使国家获得了社会财产再分配的能力。如饥荒救济,管控市场价格维持全社会粮价的稳定等,都是比较有效的荒政举措。为了有效地再分配,国家建立了不同等级的仓储体系。运河运输与国家的粮仓系统相关,大部分的国家粮仓用来存放漕粮,临清是全国最大的粮仓集散地之一。济宁不是国家的仓储重地,但由于富庶经常被要求多缴赋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诏令要求,运河沿线的济宁和其他港埠的商业税以实物形式缴纳,以备饥荒救济。(77)《明宪宗实录》卷262,成化二十一年二月乙巳,第4440—4441页。
国家特别重视运河地区的灾荒救济,尤其在洪涝多发的山东西部。灾荒救济多以赈济粮食等为主要形式,以15世纪初期的济宁地区为例,据《明实录》,中央政府曾于洪熙元年(1425年)、宣德元年(1426年)、宣德六年(1431年)、正统三年(1438年)委任地方官或派遣京官救济洪、旱、蝗等灾害导致的饥荒。(78)《明宣宗实录》卷2,洪熙元年六月,第41页;卷15,宣德元年三月庚戌,第48页;卷80,宣德六年六月甲辰,第1854页;《明英宗实录》卷46,正统三年九月癸未,第886—887页。清朝效仿明朝,在地方政府出现纷争或腐败的情况下直接派员到灾区赈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被派往山东西部的官员们直到秋收季节才获准返京,奏报秋收情况。(79)《清圣祖实录》卷216,康熙四十三年五月甲寅,《清实录》第6册,第188页。
减免田赋和杂税的征收也是解救灾区困境的方式。例如,明正统和景泰年间,济宁曾多次被豁除赋税。(80)《明英宗实录》卷146,正统十一年十月丁未,第2876页;卷157,正统十二年八月甲子,第3055页;卷261,景泰六年十二月戊午,第5585页。漕粮的部分减免也会舒缓灾区的压力。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山东西南部遭受水灾,皇帝减免了1/3的漕粮贡纳(济宁共6500石),并命户部拨银9812两赈济济宁。(81)《明神宗实录》卷368,万历三十年二月庚午,第6879页;卷408,万历三十三年四月己酉,第7608—7609页。清康熙初年,济宁的赋税削减了1/3。(82)《清圣祖实录》卷34,康熙九年十一月丁丑,《清实录》第4册,第466页。乾隆十年(1745年),朝廷拨调银两救助山东西部的济宁及其他地区。(83)《清高宗实录》卷248,乾隆十年九月壬申,《清实录》第12册,第197页。
饥荒救济的方式往往与粮食价格管制相结合。正如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所预期的那样,政府稳定市场价格的传统做法是运用籴粜杠杆干预市场活动,影响价格。魏丕信将“通过年度售与买方式取得的价格稳定化”视为清代常平仓的三大功能之一。(84)另外两个功能是“灾时救济”和“春季借贷”,参见Pierre-étienne Will and R.Bin Wang,Nourishing the People:the State Civilian Granary System in China,1650-1850,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1,p.137.济宁相关的资料显示,政府经常从粮仓中取出余食,以公平的价格投放市场,抵御灾荒和社会动荡时期的投机行为。(85)然而,稳定粮食价格的措施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政府不得不增加救济资金,让民众自行在市场上购买粮食,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诏令,增加对民众的救助,以应对济宁和其他四县粮食价格的上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清实录》第15册,第296页。
由于明清时期城市的快速发展,粮食等的市场需求增加,政府的商业干预并不容易奏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向饥民直接发放银钱,从而承认了商人在救灾中的作用,允许他们在流通中获利。价格管制和饥荒救济相结合的策略非常普遍,正如雍正朝重臣鄂尔泰所述:“凡地方有灾歉之处,轻则平粜,重则赈济”。(86)鄂尔泰:《遵旨议奏事》,乾隆八年七月十六日,《档案·乾隆朝户部题本》,转引自吴琦:《南漕北运:中国古代漕运转向及其意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国家储备的粮食来源于田赋征收和政府采买,主要借运河漕运抵达京城。然而,明清时期北运的漕粮,有时会被地方“截留”。雍正、乾隆年间,山东大量的漕粮直接用于赈灾和平抑市价。雍正四年(1726年)、八年、九年,朝廷准许山东撤回大量粮食,用于当地救荒。(87)《清世宗实录》卷43,雍正四年四月癸未,《清实录》第7册,第635页;卷97,雍正八年八月丙午,《清实录》第8册,第297页;卷101,雍正八年十二月乙卯,《清实录》第8册,第341页;卷102,雍正九年正月丁亥,《清实录》第8册,第356页;宣统《山东通志》卷首《列圣训典》,第50a页。乾隆九年(1744年)、十一年、十二年、四十八年(1783年),朝廷在济宁和山东西部的广大地区进行赈济。(88)《清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壬申,《清实录》第11册,第713页;卷274,乾隆十一年九月戊申,《清实录》第12册,第588页;卷284,乾隆十二年二月丁卯,《清实录》第12册,第704页;卷291,乾隆十二年五月丁未,《清实录》第12册,第810页;卷1176,乾隆四十八年三月辛丑,《清实录》第23册,第767页。赋税的重新分配是确保国家稳定和有序的关键手段,朝廷尤其需要认真对待粮食的再分配功能。国家对如济宁等重点经济区的政策倾斜,取得了显著成功,因而济宁及周边地区几乎没有因灾荒发生大规模的暴乱。
在北方省份中,山东征税之难及拖延情形尤为严重。乾隆元年(1736年),皇帝命兵部侍郎王士俊警告山东巡抚岳浚拖欠税款的严重性: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省拖欠税款多达三百余万两,甚至流行一句谚语:“不欠钱粮,不成好汉”。(89)《清高宗实录》卷17,乾隆元年四月庚辰,《清实录》第9册,第439页。以地方民生的名义请求延期、拖欠、缩减、蠲免,成为地方政府的普遍策略,也是官员筹集资金用于公务和自身开支的主要途径。此外,地方经常以赈济饥荒的名义上书乞求免除欠税,以便清除地方债务。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济宁及其周边县乡遭受洪灾,次年六月,皇帝豁免了济宁、鱼台、金乡、滕县、峄县等地累年拖欠的税款,共计地丁钱粮七万五千两、仓谷三万九千石和籽种麦本四千九百两。(90)《清高宗实录》卷537,乾隆二十二年四月戊寅,《清实录》第15册,第775页。九月,乾隆皇帝再次诏令,豁免积年所欠的地丁钱粮。(91)《清高宗实录》卷547,乾隆二十二年九月甲寅,《清实录》第15册,第963页。
(四)大运河上的国家垄断与商品化
对生活必需品生产和贸易的垄断是历朝的国策,而大运河则是国家践行其意志和决心的一个最重要舞台。
在制造业方面,江南的大型纺织工场和临清的砖窑是最为知名的官营企业。在一些运河港口,政府还成立了运河运输业。早在永乐七年(1409年),政府就为卫所船员建立了一个总造船厂,并在济宁设立分部。(92)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济宁运河文化》,第59页。官营造船厂垄断了运河上行驶的大型船舶的制造,国家对漕船的数量、大小和容量都有严格的规定,旨在控制运河上的运输和贸易规模。
在商品流通中,盐作为政府垄断的必需品,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只有持盐引的商人才有权利买卖食盐,甚至连贸易路线都有明确的规定,但盐以及其他商品的贸易垄断很难奏效。漕船允许携带和交换一定数量的盐和其他物品,但是实际上船员从事大规模的食盐走私活动。政府被迫日渐放宽了贸易限制,船员可携带私人货物配额的提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有时,朝廷甚至制定政策鼓励国家管控下的私人贸易。嘉庆十年(1805年)颁布诏书,准许山东船只在返程途中购买大米和其他粮食,并享受部分关税豁免。(93)《清仁宗实录》卷143,嘉庆十年五月戊戌,《清实录》第29册,第16页。
走私货物扩大了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正面影响。但私人商业经济所受的桎梏,也同样展现出政府所起到的负面作用。然而国家依旧坚定不移地推行传统的垄断政策,并通过些许修改实现灵活性,以适应和契合新兴的商业环境。朝廷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与国家与地方的关系相关,因为本地商人或跨区域商人都活跃在特定的地方经济环境之下。康熙中期的济宁知州吴柽认识到市场活力的积极作用,主张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他如此看待政府的垄断政策:
济宁水陆交冲之地,与他处不同,逐末之人多于务本之人。有籴济宁之谷贩往别地者,即有籴别地之谷贩至济宁者,适相等也。一来一往,贫民藉以得食者,正复不少。若下遏籴之令,贩来之人恐无他客,转买必且裹足不前,故遏籴非荒政之上策。……济宁人烟繁庶,水陆经过者络绎不绝,有文武各衙门及四营兵丁,故民间卖酒为生者甚多,若概行禁止则俱失业矣。(94)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1,第48a页。
此番言论虽然基于官方的立场出发,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社会的合理诉求,甚至包括商人的呼声。
(五)大运河体制的缺陷及整顿
在运河运输系统中,各种粮食运输方式左右着当地的经济生活。明初,以“支运法”为名,规定各地农户将税粮就近运送到运河沿岸的几个国家级粮仓。由于民役运粮耽误农时且花费不菲,自宣德六年(1431年)开始,一系列的改革逐渐减少了民运的义务。(95)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4《河漕转运》,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78—379页;[美]黄仁宇著,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1368—1644》,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67—69页;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70,pp.3-4.但允许消耗运费的规定,给官员敲诈勒索和腐败留下了漏洞。顺治九年(1652年)的一则史料显示,官僚腐败在运河运输中十分普遍:“各衙门人役皆以漕为利薮”。(96)清档,顺治九年二十六日,户部尚书车克等题本,转引自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288页。漕船携带的私货经常被各级官僚机构和人员所觊觎,在途中被侵吞。正统六年(1441年),漕运右参将都指挥佥事汤节抱怨,山东“每岁漕卒附载土物以益路费,往往为抽分司盘诘,军甚苦之”。英宗皇帝批准了“勿抽分”的请求。(97)《明英宗实录》卷81,正统六年七月甲寅,第1626—1628页。弘治元年(1488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马文升在奏章中历数“运军之苦”,突出的一项为:“军士或自载土产之物,以易薪米,又制于禁例,多被检夺。”(98)《明孝宗实录》卷11,弘治元年二月丙辰,第254—255页。
明清两朝皇帝在给地方官员的诏书中经常提到贪污、渎职、舞弊等弊端。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河道总督王新命及其属下因 “勒取库银六万七百两”被惩处。(99)《清圣祖实录》卷154,康熙三十一年正月辛巳,《清实录》第5册,第701页。乾隆元年,皇帝诏令山东,将欠税归咎地方官员、派出人员和当地权贵普遍的腐败、偷窃、滥刑和欺诈等行为。(100)宣统《山东通志》卷首《列圣训典》,第53b页。嘉庆皇帝曾感慨道:“东省官吏,图利者多,守义者少,朕甚忧之。东巡之举,断不可行,行则徒增烦恼耳。”(101)《清仁宗实录》卷212,嘉庆十四年五月丁亥,《清实录》第30册,第853页。
此外,大运河是国家的交通命脉,也是权贵们展示其权势的平台,以至于妨碍了航运。弘治十八年(1505年),一位户部官员指出,在水闸高度集中的济宁段运河,因“闸官及吏职卑微,往来官豪,得以擅自开闭,走泄水利,阻滞运舟”。(102)《明武宗实录》卷2,弘治十八年六月丙寅,第71页。清代亦有类似情况。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皇帝告诫河道总督张鹏翮:“山东运河,转漕入京师,关系紧要……有官员经过,不许徇情,擅自开放泄水,以致漕船稽迟。”(103)《清圣祖实录》卷220,康熙四十四年四月甲寅,《清实录》第6册,第224页。
总之,这些系统性的功能失调和官僚主义的缺陷,损害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虽然可以以零碎的技术手段修正,但在现存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却不能永久性地消除。
(六)在运河私人运输贸易活动上的纷争与裁决
儒家“藏富于民”信条是一种经济上的不干涉主义,尽管其行为实际上可能会呈现出相反的一面。这种理念在政治经济上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大运河上,如何界定国家在涉及商人活动方面的角色是一项主要内容。
运河运输存在官方和私人两类,故有官船和民船之分。宫廷消费的漕粮和物品大多由官船运送。许多案例表明,民船比官方背景的漕船遭遇更大的困境。朝廷在某种程度上看到私人运输对国家发展的积极作用。正统年间,监察御史李在修以“不能禁戢下人”横行运道为由弹劾漕运总兵、山东布政司参议等一长串官吏,虽然正统皇帝没有惩罚这些官员,但在诏令中严敕:“比间运粮军旗不守法度,故将船只横栏河道,沮滞民船,或逞凶殴人”,勒令“钤束军旗,不许仍蹈前非”。(104)《明英宗实录》卷42,正统三年五月庚寅,第816—817页。至清朝,卫所制度衰落,政府逐渐雇佣商人协助漕运,多次斥责官船利用漕运名义和官方身份欺压商人。乾隆三年(1738年),为了应对直隶粮价“稍昂”,要求“向有禁米出洋”的奉天、山东地方官吏松绑:“有愿从内洋贩米至直隶粜卖者,文武大员,毋得禁止”。但是,商人售卖需要领有往、返两地的官府“印票”。(105)《清高宗实录》卷75,乾隆三年八月乙巳,《清实录》第10册,第192—193页。
私人运输和贸易受益于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的目的。运河沿线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国家的干预,而济宁作为一个主要的运河商埠城市,成了这种关注所引发矛盾的聚集地。
综上所述,大运河的运行增加了治理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复杂性。对于运河北部地区的地方利益而言,国家强有力的存在有利有弊。而所谓利弊,需要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具体语境中进行审视。
四、当国家遇到社会:渗透与回应
笔者曾讨论过明清时期济宁士绅如何运用各种策略建构和加强地方认同。(106)孙竞昊:《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本文则着眼于中央如何渗入地方社会,怎样处理国家意志与士绅所代言的地方利益出现对抗的情形。济宁案例为研究国家权力与士绅权威的交集与互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试验场。而对国家权力干预下的地方主义的张力及其局限性的分析,有利于评估济宁地方社会的政治特性。
(一)国家在教育与社会领域里的介入
中国传统国家不仅干预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而且还广泛介入地方士绅精英通常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教育、文化、宗教等领域。明清时期,从为科举服务的学校,到灌输统治思想、传播知识的基层识字普及工作,国家强化了教育对当地社会的影响。
现存的济宁明清方志都列有“学校”类别,可以了解官办学校(如“州学”)的详细情况。随着大运河体制的建立,济宁的教育受到多方官办机构与个人的重视和资助,其中一个表现是创立和扶植书院。而社学则会直接涉及更广泛的人群。(107)参见Evelyn Rawski,“Economic and Social Found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 and Evelyn S.Rawski,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Los Angeles,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1.洪武八年(1375年),诏令各地兴办社学,济宁知府方克勤“立社学数百区”。(108)参见龙文彬:《明会要》卷25《学校上》,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411页;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7a—47b页。卫所也设有社学,济宁卫学的规模颇大。(109)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8,第46a页。明末,还有一些取得功名的士子来自济宁卫学。尽管这时社学在全国已经衰微,但济宁城社学的良好状况表明了当地政府和士绅合作的成功。总体而言,官学和私学在济宁这个著名的运河城市里相得益彰。
明清国家重视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嘉靖元年(1522年)的一则碑文记载了济宁的一次社坛祭祀。(110)《明嘉靖元年里社坛碑》,载徐宗干编:《济宁金石志》卷4,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第24a—25a页。在清代,官方祭祀仪式在民众的宗教生活中持续发挥着作用。(111)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10,第1a页。但是,国家对宗教活动的干预并不排斥民众的宗教实践,以流动的运河为载体的思想交流和由此形成的宽容氛围,鼓励了济宁及其他运河城市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接纳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
然而,朝廷和地方政府为确保稳定的社会秩序,对潜在的危机保有警惕。徐宗干在济宁知州任内,鉴于“济州毗连南省,素好淫祀,城乡旧建庙宇甚多”的情形,曾把一些寺庙地产划归地方书院,他还“抽查保甲,遇有外来僧道,随时查明递籍”。(112)徐宗干:《庙地改拨书院经费议》,民国《济宁直隶州志续志》卷7,第5a页。他还“毁淫祠数处”。(113)民国《济宁直隶州志续志》卷10,第42a页。地方文献还记载了其他几起类似事件。因此,在宗教和教育领域,国家和地方基于共同利益,似乎达成了某种融洽的关系,有助于济宁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运河沿线的安定局面是漕运的保证。
(二)在国家与社会冲突中的地方精英
明清时期国家权力对地方事务的渗透,遭遇到了作为地方利益代言人的精英阶层的抵制。(114)参见韩国学者闵斗基的相关论述,Min Tu-ki,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1990,p.22.日本学者用“士绅统治”一词来形容士绅地主在明清地方社会中的威权地位,而国家也不得不在税收与其他事项上与之协商。(115)Noriko Kamachi,“Feudalism or Absolute Monarchism? Japanese Discourse on the Nature of Stat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Modern China,Vol.16 (July 1990),pp.336-351.周锡瑞和冉玫铄概括出明清士绅在地方社会用于建树权威的非直接国家权力资源,包括物质财富、社会人际网络以及符号、象征性的资本等。(116)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0,p.11.他们运用多种资源和策略,取得并巩固地方霸权。例如,一些公私场所成为表达想法、交换意见、游说当局、争取地位和整合权力的渠道。同样,商人与士绅阶层联合,以保护其利益免受国家侵犯,加强了地方精英的凝聚力。
明清时期济宁文化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典型的精英能动主义。从明中叶开始,士绅精英不仅热衷从事文化、教育和经济活动,而且通过广泛而富有实质性的公共事业,诸如灌溉系统、道路、水路、城墙、护城河、城门、城楼、城池等公共工程建设、改造和修缮,几乎涉及了当地社会和政治所有内容,对维护地方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7)R.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4;Mary Backus Rankin,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5.黄、运工程为当地民众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来源,尽管士绅精英对因之承受的负担多有不满,但仍将其物力、财力和精力倾注于此。
济宁士绅在水源管理和水利工程方面总体持合作态度,但是他们对政府关于劳力和财力的配置不无争议。他们往往与当地官员协力,上疏朝廷争取减免赋役,这在地方官员的奏章以及致仕返乡士绅的请愿中均有体现。如孙扩图致仕后,对以运河为由巧立名目强加给“绅士”“小民”“工贾”的各种“派纳”“亲受其累”,曾“三诉三斥”。(118)孙扩图:《一松斋集》卷1,第7a—7b页。在任济宁籍官员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家乡谋取权益,正如康熙皇帝警告大学士等臣下所说:“山东绅矜,最称桀骜,且好结朋党。”(119)《清圣祖实录》卷142,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戊寅,《清实录》第5册,第567页。
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水源的使用。尽管山东西部的水利工程具备多种功能,但整个水利系统的核心目标仍是运河通航。故而政府派驻各级官吏对重要的河流、沟渠、水库、湖泊和泉水进行监督、管理和利用。大运河山东段依托许多水资源相对丰沛的湖泊,但与农业用水产生矛盾。清朝中后期,微山湖成为山东运河最大的水源,周围的农民时常开垦湖畔周边以种植粮食,而官员为民生计,常常听之任之,危及运道水源。康熙六十年(1721年),皇帝警告道:“山东运河,全赖众泉灌注微山诸湖,以济漕运。今山东多开稻田,截湖水上流之泉,以资灌溉。上流既截,湖中自然水浅,安能济运?”(120)《清圣祖实录》卷292,康熙六十年四月庚子,《清实录》第6册,第838页。嘉庆十二年(1807年),政府决定疏浚微山湖水系一条淤塞的旧河,遭到了“占种湖滩,视为恒产”“矜民”的抵制。嘉庆皇帝以“为国即以为民”之辞训示:“断无因尔等贪图小利,置公事于不办之理”。(121)《清仁宗实录》卷185,嘉庆十二年九月乙未,《清实录》第30册,第400页。
此外,每当治理黄河与维持运河之间发生冲突时,朝廷毫不犹豫地倾向于后者。明清时期,政府为防止黄河北徙,给淮河流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也危害了整个运河运输,这种情况持续到1855年黄河铜瓦厢改道。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士绅无法改变这一根本格局,仅能诉求减少负荷而已。
(三)地方官员的双重角色
在明清两朝的权力网中,各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纠葛。皇帝通常自居于平民和权贵之间的仲裁者位置。(122)孙竞昊:《朱元璋的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5期。清朝皇帝更广泛、深入地干预地方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纠纷。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重申了康熙皇帝要求“东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轻减田租”的“训谕”,认为:“诚切东省民生利弊也”。(123)《清高宗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清实录》第13册,第44页。嘉庆皇帝多次斥责山东“吏治废弛”的“积习”。(124)《清仁宗实录》卷293,嘉庆十九年七月癸丑,《清实录》第31册,第1021页;卷342,嘉庆二十三年五月戊午,《清实录》第32册,第525—526页;卷370,嘉庆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清实录》第32册,第895页。
尽管地方政府在当地社会中代表朝廷,但是朝廷与地方官员之间亦存在着紧张关系。士绅精英能够掌握民意,而民意正是朝廷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主要标准。在国家和地方的矛盾关系中,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国家、地方机构、当地社会和自身仕途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在国家与地方关系十分严峻的运河地区,为了监督漕运、清淤泄洪、保证堤坝的定期维护和稳定的水量供应等,地方官员常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明清时期的地方官员比以往都更需要依赖与地方精英的协作。嘉道时期的学者沈垚指出:“唐时州县兴造之事,听长吏自为。宋后动须上请,一钱以上,州县不得擅用。所请不能称所需,所作往往不坚固。于是长吏始有借助富民,民之好义者有助官兴造之举。”(125)沈垚:《落帆楼文集》卷7,民国七年吴兴丛书本,第21b页。他们需要培养与地方精英的友好关系,方能为当地大众谋求福利,并在与士绅的互动中塑造自身形象。
因为公共设施经常受到洪水、地震或人为疏忽造成破坏,故文献记载了济宁大量的重建与修缮工程。除了官方举措外,地方官员还会以私人倡议为名,捐赠和赞助公共工程,如修葺墙壁、塔阁、孔庙、桥梁、道路、学校,修缮城墙、护城河,等。此外,他们还会捐款解决当地的困难。嘉庆八年(1803年)竖立的一块石碑,就是为了纪念乾隆年间的一位知州为了缓解“粮船辐辏”时“阻滞”导致的“商民不便”,在济宁南门外的一处运河桥上,“自捐廉俸,平治码头,造大船一只,可容车马”。(126)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5,第68b页。嘉庆十二年(1807年),济宁州及卫所官员资助栖流所,使“穷丐流民”“免致沿街露处,有倒卧病毙之苦”,也符合“以靖地方事”的治安意识。(127)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4,第75a—75b页。
另外,鉴于济宁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扶植地方文教事业是树立声誉的有效途径。地方官员通过增补预算、捐赠资财、授课和主持仪式等方式,支持和督导地方教育,培育、提携年轻书生。官员与士绅在教育上的互动,增强了官府与地方之间的关联。(128)孙竞昊 :《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济宁的不少地方官员身处商业环境中,所以对商业在当地经济中的地位有着同情性质的认识,并在他们的施政措施中有所体现。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州官发布征税条规“勒石立碑”,如《剔蠹疏商记碑》《除害疏商记碑》,禁止敲诈勒索过往商贾,以维持当地经济秩序。《除害疏商记碑》专门“以苏姜商事”:“一禁坏科,一禁奸商,一禁牙蠹,一禁市弊,一禁脚弊”。(129)徐宗干:《济宁金石志》卷5,第69b—70a页。鉴于晚清船舶服务业的重要性,徐宗干严令禁止衙门的各系分支无理索要商业用地的租金。(130)咸丰《济宁直隶州志》卷3,清咸丰九年刻本,第13a页。
地方官员有时会为了当地利益而冒着不顾中央权威和权势者的风险。一个通常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为了过往船只可以在水闸开、关上予以优先权。同治八年(1869年),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在沿运河南下途中耀武扬威,在山东境内被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擅用职权罪处死。相传这起事件与宫廷斗争有关,但安德海的骄横、不法的确招致了当地士绅和官员的同仇敌忾。(131)《清穆宗实录》卷264,同治八年八月癸卯,《清实录》第50册,第661页;卷266,同治八年九月乙亥,第692页。
总而言之,地方社会政治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则是不同机构和个人纷争与调和的产物。史料表明,在济宁的税收征纳、军费协商、宗教和文化活动管理、市场干预以平衡物价、公共工程安排、社会慈善监督、地方治安组织等方面,地方官员乐于与士绅精英合作,而且在国家与地方自主性的冲突中,每每为地方利益仗义执言。
余论: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下济宁地方性发展的张力及其限制
1927年完成私修方志《济宁直隶州拟稿》的作者李继璋不认可将清末民初的“自治”归诸舶来品之说,而是认为早在晚明时期,济宁地方社会的“自治、自卫之能力”(132)李继璋:《济宁直隶州拟稿·建置志上》。已经表现出一种类似欧美经验的本土性地方主义。而当代的许多研究也揭示了,明清时期一些发达地区城市化的高涨、地方社会的壮大推进了某种城市自治性的发展。但同时,正如济宁的情形所示,国家政权不断地延伸其政治权力,抑制离心倾向和不同意见。那么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开埠前一些特定地区呈现的前所未有地方性发展进行定性,而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在运河城市济宁的演绎可以视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如何有效地渗透和管理地方社会,是大一统中央集权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明清时期,大运河虽然促进了商业活力和社会流动,有利于激励思想和社会的自由或自主性发展,但也为国家权力提供了一条便于进行有力干预的通道,地方必须在朝廷法度和准则下运行。修建大运河不是为了促进商业,保护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以农立国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的必要途径。济宁、临清等北方部分运河城市的空前发展,都无外乎是国家政策的副产品。在明清的多数时期,大运河运转良好,运河、黄河的水利系统得到合理的管控,运河沿线繁荣发展。因此,朝廷得以相对自如地将国家意志施予新兴的城市中心,使之成为政治堡垒。济宁、临清和其他若干港埠因为与运河的关系而被提升为直隶州,凸显其重要地位。以济宁为例,多重、多种官僚机构的设立,成功地规范了其地方性发展的态势和取向,使其难以突破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质的规定。
正如彭慕兰所言,帝国政治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核心和边缘,一如因运河而崛起的济宁地区的层级体系所显现的那样。(133)[美]彭慕兰著、马俊亚译:《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0—311页。以济宁、临清为代表的北方运河城市的崛起,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得区域的划分更为复杂,出现了某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宜于施坚雅模式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134)参见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3期。在济宁,运河带的出现影响了“自然”的宏观区域网络及其内部层级结构,商业化与城市化使得济宁成为经济功能突出的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而在地方社会权力网络中精英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扩张、市民文化的繁荣,标志着地方性的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区域经济、文化与政治层级制度似乎是在一个较小的空间内运作,例如一座城市或一个州,可以符合施坚雅模式的一些基本特征。但从更为宽广的维度看,视市场因素为动力的施坚雅模式的局限性也十分显著,因为官僚机器对运河地区的渗透使济宁这些城市中心的发展依旧没有跳出传统行政中心导向的窠臼。所以,大运河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官僚制度有力地遏制了地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自主发展。济宁和北方运河地区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政治和政策,但又受制于此。
国家权力的兴衰,紧密地关联着中华帝国晚期“水利循环”的命运和运行。(135)[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0—22页。正如大运河跌宕起伏的境遇一样,济宁等港埠城市也与王朝国家一起历经治乱、兴衰。明清中国,虽然在一些新兴或发生功能转型的城市出现了若干新气象,但没有产生一股巨大的社会变革力量,济宁的案例就是一个缩影。而且,像济宁这样生机勃勃的少数运河城市,孑然兀立在普遍“落后”的众多北方行政中心治所中。只要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中中央与地方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制度上没有发生质的改变,那么某些城市、地区中即便出现经济与社会的某些变迁和地方性成长,依旧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根本性突破。缺少社会演化的真正革命性动力,开埠前中国传统社会的嬗变无论如何剧烈,也无法超越王朝周期更替的轨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