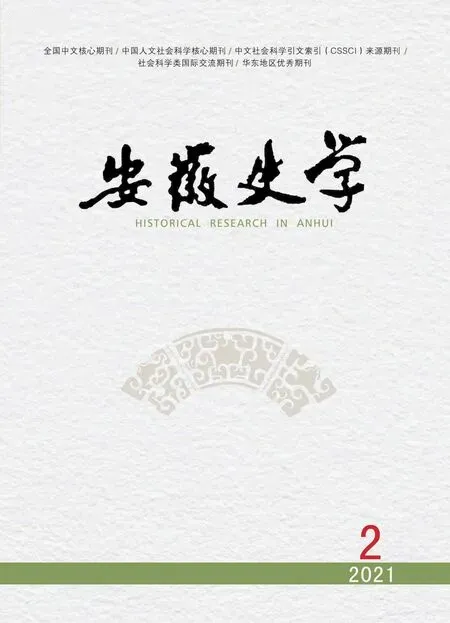历史性的体制和当下主义:弗朗索瓦·阿赫多戈的历史时间研究述评
黄艳红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近来我国理论界开始注意到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赫多戈(或译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理论(1)赖国栋:《法国当下主义历史观的兴起》,《光明日报》2017年7月28日;拙文《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他于2003年发表的著作《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以下简称《历史性的体制》)在国际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2)本文使用的是2012年版:François Hartog,Régimes d’historicité.Présentisme et expériences du temps,Paris:Seuil,2012。为简便计,本文对该书的引用将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码。在法语学界,“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 d’historicité)和“当下主义”(présentisme)已经进入史学研究的语境(3)C.Delacroix etc.,Les courants historiques en France,XIXe-XXe siècle,Paris:Gallimard,2007,p.15,pp.595-597.,英语学界则将“历史性的体制”概念运用到具体课题的研究中。(4)Diana Mishkova etc.eds.,“Regimes of Historicity” in Southeastern and Northern Europe,1890-1945:Discourses of Identity and Temporality,UK:Palgrave Macmillan,2014.本文将主要依据这部著作,对阿赫多戈的相关理论作初步的述评。
阿赫多戈在巴黎高师就学时以古希腊史为主攻方向,但他较早就对现代史学感兴趣,并承认德国历史学家科泽勒克的《过去的未来》对他的思考帮助很大。(5)[法]弗朗索瓦·阿赫多戈著、赵飒译:《灯塔工的值班室》,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18—119页。另外,阿赫多戈很早就关注人类学家的研究,他最初于1983年提出历史性的体制概念时,就得益于马歇尔·萨林斯的启发(28)。上述学术和思想背景,再加上阿赫多戈对当代法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史学发展(尤其是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的深入思考,构成《历史性的体制》一书的几个主要思想源泉。
一、多元的历史性体制与时间秩序的危机
《历史性的体制》标题中的“体制”用的是复数(régimes),意指历史性体制的多样性。阿赫多戈对“历史性”(historicité)作了一点说明:它“表达的是个人或集体置身时间中、并在时间中自我展开的历史条件和方式”;这个词首先意味着疏离(estrangement)的经验、人体验到的距离感,正是通过这类经验,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范畴才得以理解和言说(14)。历史性的体制之所以是多样的,是因为在不同社会中,时间的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合”(articulation)方式参差有别,它们各自的影响力不一样(47)。有时是过去占支配地位(历史性的“旧制度”),有时未来的考量在时间经验中占优势(现代历史性体制或未来主义)。
阿赫多戈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状态的历史性体制(259),他对一些独特个案的研究,旨在揭示不同的历史性体制的过渡。在全书五章中,前三章讨论的是“时间秩序I”(6)时间秩序一说借自法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波米扬,参阅Krysztof Pomian,L’ordre du temps,Paris:Gallimard,1984。,作者运用“远距视角”,考察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和斐济诸岛的历史和时间感知方式,随后通过对西方文学史上两个人物的分析,以纵向的视角对西方社会的历史性体制演变加以说明。
马歇尔·萨林斯批评了将结构与事实对立的传统路径,他试图解读太平洋原住民和西方殖民者早期接触时的文化互动和误解,并就土著人与西方人表述历史的差异进行了阐释。(7)[美]马歇尔·萨林斯著、蓝达居译:《历史之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萨林斯的基础上,阿赫多戈抽象出原始社会历史性的“英雄体制”:国王是共同体存在的条件,历史从结构上说是“拟人化”的,因此原始人对历史事实的理解颇为独特。在这种体制中,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被当作当下和未来采取行动的模板,它们在与当下不断涌现的事件的相互参照中获得意义。在最初与殖民者发生接触时,土著人和西方表述、理解历史的不同方式引起了很多误会,具体事件被双方以不同的方式编码和解码,例如19世纪新西兰毛利人叛乱期间对英国国旗和桅杆的误解,以及18世纪末库克船长在夏威夷被当作献祭品的神话。在这些案例中,土著人都是以延续已久的神话和仪式来解读当下的事件(54—60),事件与体系、历史与结构、当下与过去之间存在一整套的交换关系,每个社会都根据特别的体制生产历史。
在阿喀琉斯那里,“每一天都是第一天”,这里几乎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不存在当下与过去的距离感(69—73)。在西方历史上,犹太——基督教的启示彻底改造了时间经验的方式。《旧约》已经使犹太人产生了强烈的未来期待,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你要离开本地……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8)《圣经:创世纪》12:1—2。《旧约》经文还为犹太人提供了关于时间历程的完整叙事(92—93)。阿赫多戈援引了犹太历史学者耶鲁沙米的观点:希腊史学家从来没有赋予历史整体性的意义,犹太人才是历史意义之父。这植根于犹太人的信仰特征:他们是从历史经验去理解神的,历史是神的考验与人的应答的过程。(9)Yosef H.Yerushalmi,Zakhor.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6,pp.6-9.
基督教吸纳了犹太人的历史观。但基督教对西方的历史时间观有独特的贡献:它以道成肉身这一决定性事件将时间一分为二。从此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当第二个、也是终极事件,即基督再临和末日审判到来时,时间也就结束了。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过渡期是一种期望的时间,当下的每一刻都寄寓着时间终结的希望(94)。“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惟独父知道。”(10)《圣经:马太福音》24:34—42。末世论的当下就是《新约》带来新时间观。它还确立了一种紧张关系,这就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的紧张,基督道成肉身之后还会再临,一切都还没有完结,但随时会完结。作为救赎史的历史就是从这一紧张关系发展而来的。
中世纪史专家贝尔纳·葛内对基督教时间观在史学中的表现做了更为直观的揭示。在古代史家那里,时间是不断重启的,历史目睹了一个个文明的兴衰,有如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但在基督教史学中,整个尘世的历史是在一次性的时间(un suel temps)中展开的,世界历史是一场有始有终的进程:从创世到末日审判。(11)Bernard Guenée,“Temps de l’histoire et temps de la mémoire au Moyen Age”,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1976-1977,pp.25-35;pp.25-28.如果按照科泽勒克的理论,基督教的时间观似乎开辟了某种新的“期待视阈”——末日审判,这是过去的经验中所没有的。(12)参阅拙文《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这种新的期待视阈是否像现代革命观念中的理想社会一样,具有某种现代性呢?阿赫多戈的看法是否定的。基督教史学中过去的经验分量更重,如基督徒认为,《新约》的故事在《旧约》中已有提示,圣经文本中有基督降生的见证。中世纪史家还为预知未来而研究《旧约》的先知预言,他们深信整个历史进程都贯穿着神意。(13)Bernard Guenée,“Temps de l’histoire et temps de la mémoire au Moyen Age”,Annuaire-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1976-1977,pp.25-35;pp.25-28.但基督徒对未来的展望并没有新颖之处,除了末日,他们的期待视阈中不会有任何关于尘世的新鲜事物(94—95)。这与阿赫多戈所称的“历史性的旧体制”,即信奉“历史是人生导师”的理念是一致的,这里不存在新的期待视阈与过去的经验空间明显的紧张关系。
但基督教的时间秩序存在可塑性。教会总是重续和尊重“先人的习惯”和“历史导师”(historia magistra),科泽勒克也认为基督教延续了古代人关于历史为后代提供范例的观念。(14)Reinhart Koselleck,“Historia Magistra Vitae.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Topos im Horizont neuzeitlich bewegter Geschichte”,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p.38-66.基督教时间秩序本身具有一种强大的“时间性”力量,它将历史视为一次性的历程,而且有最终的结局。到近代,当对进步的展望逐渐压倒对拯救的期待时,便实现了从一种秩序向另一种秩序的转变,因为对过去的关注和末世的热忱都转向了未来(96)。这一论点与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中的看法颇为接近。(15)[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对于这个转变,阿赫多戈的表述是从历史性的旧体制向现代体制的转变。“旧体制”(ancien régime)与法国历史中著名的“旧制度”是一个词,与之对应的就是大革命。阿赫多戈的确赋予1789年以标志性的意义(32),认为这是新旧历史性体制转折的关键日期。这个观点本身并无大的突破,因为科泽勒克也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真正开辟新的期待视阈的关键事件。(16)Reinhart Koselleck,“‘Erfahrungsraum’ und ‘ Erwartungshorizont’:zwei historische Kategorien”,in 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pp.349-375.但阿尔托格的新意在于提出了“时间缺口”、“时间秩序的危机”等概念,以分析历史进程中时间经验的多样性和互动关系。
“缺口”(brèche)概念来自汉娜·阿伦特,它是“历史时间中奇怪的中间态,此时人们意识到时间中的间隔,这种间隔完全是由这样一种状态决定的:以往的面目不再存在,但新的面貌尚未成型”(23—24)。阿赫多戈说的时间秩序的危机,指习以为常的时间感知,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常态关系突然出现紊乱(27、32、38)。他选择两个案例来分析时间缺口和时间秩序的危机,并以此窥视历史进程中时间经验形式的转变。两个例子都来自文学领域:《荷马史诗》中的尤利西斯,“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
当代学者马塞尔·德蒂安认为,《荷马史诗》没有展现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分离,在古希腊人的时间观中,要将过去理解为已发生之事、将过去以别样的面目呈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17)Marcel Detienne,Comparer l’incomparable,Paris:Seuil,2000,p.76.奥尔巴赫在《模仿论》中也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荷马英雄们缺乏历史感,《旧约》在这方面要远胜《荷马史诗》。荷马的风格特点是“前景”(foreground),叙述虽然有向前和向后的跳跃,但始终表现为对纯粹的当下时空的呈现,没有刻画历史和人在时间中的发展进程。(18)[德]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等译:《模仿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29页。阿赫多戈通过对《奥德赛》第八章的分析(19)[古希腊]荷马著、王焕生译:《荷马史诗·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155页。,提出了不同意见(76—83)。当尤利西斯听到费埃克斯人的歌手唱起特洛伊的故事时,他流下了眼泪。此刻的尤利西斯已经意识到自己在特洛伊的过去,这与他在漂泊中的当下存在距离,这一距离感表明他已经获得阿喀琉斯所没有的“历史性”意识。尤利西斯落泪就是荷马英雄世界中时间秩序的危机:不过他没有概念化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危机,“泪水就是他的语言”。(20)[法]弗朗索瓦·阿赫多戈著、赵飒译:《灯塔工的值班室》,第113页。
第三章关于夏多布里昂的研究(97—139),笔者认为是全书最出色的一章。时间秩序的危机非常有力地揭示了两种“历史性体制”的转折与冲突,也是对科泽勒克关于鞍型期(约1750—1850年)概念演变研究强有力的佐证。(21)参阅拙文《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2017年第6期。夏多布里昂出身贵族,一生几乎横跨鞍型期的两端(1768—1848),经历了数次革命,足迹踏遍大西洋两岸。对他而言,旧制度与大革命既是一种实际的人生经验,也是一场新旧历史性体制的交锋。1797年,他在《论古今革命》中认为,了解过去能够理解现在和预知未来,过去的革命与当下和未来的革命之间可以类比:“手擎往日革命的火炬,走进未来革命的暗夜。”“如果你们要预知未来,那就请思考过去。”他在比较古希腊的革命与现代革命之后说:“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所谓新事物,大部分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在古希腊的历史中找到……人只能不断地重复。”这是一种典型历史性的旧体制。然而30年后,夏多布里昂几乎完全否定了当初的观念(114—120)。1826年,他在为《论古今革命》写的新序言中,时间像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一往无前:“我是在一条航行于暴风雨中的船上写作,两边的河岸沿着船舷一路飞逝消失,而我却要把它们当作固定的事物。”(22)Chateaubriand,Essai sur les révolutions,Génie du christianisme,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Paris:Gallimard,1978,pp.51,220-221,431-432,15.其时间观已经从循环论(圆圈)变成线性(河流)。在新时间观中,历史的特征随时代而改变,因此法国应“重写它的年鉴,以便与精神的进步协调一致”(130)。这是历史概念本身的时间化,阿赫多戈引述了科泽勒克对“历史”概念时间化和单数化的见解:历史概念逐步清空过去的典范特征与重复性,将其转变为单数的概念(die Geschichte),这一概念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强调事件本身的唯一性,每个事件都在时间进程中有其独一无二的位置,它没有先例可循(106—107)。(23)笔者曾以托克维尔的民主概念为例,探讨这种历史概念的形成。参阅拙文《托克维尔“民主”概念的时间化及其局限》,《历史研究》2019年第6期。
观察空间的扩展对夏多布里昂时间观的转变意义重大。他年轻时认为,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纯洁的野蛮人”之中,古典时代的风尚等而下之,但远比现代人高尚;对于新生的美国,他将之比拟为古罗马,以为华盛顿就是古罗马的共和英雄(99—112)。但当他来到美洲,寻找那种想象中的纯正自由时,他发现了两种自由:一种属于人民的孩提时代,它是风俗和美德的女儿,这就是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自由;另一种是知识和理性的女儿,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24)Chateaubriand,Oe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de,Paris:Gallimard,1978,t.I,p.873;pp.749-750;p.874.卢梭推崇的野蛮人的自由被时间化了,它处于时间进程的上游,并必将在时间进程中失去参考意义:夏多布里昂在美洲原始部落中看到的是极端悲惨的生存状态。(25)Chateaubriand,Oe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de,Paris:Gallimard,1978,t.I,p.873;pp.749-750;p.874.古代的自由和美德被祛魅了。而美利坚合众国的新自由将更有生命力,因为这种自由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只会随时间而不断发展。(26)Chateaubriand,Oeuvres romanesques et voyages,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de,Paris:Gallimard,1978,t.I,p.873;pp.749-750;p.874.
夏多布里昂的转变,印证了科泽勒克关于“历史是生活的导师”退场的论断。阿赫多戈尤其强调夏多布里昂时间经验中的危机特征,这也是该章标题的意义所在:“新旧历史性体制之间”。这位作家在1841年说:这个已经失去神圣权威的世界,“仿佛置于两种不可能之间:过去的不可能,未来的不可能”。(27)Chateaubriand,Mémoire d’outre-tome, Tome 2,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Paris:Gallimard,1952,p.922.这是身处两种体制之间的心态写照:一方面真切地感受到时间之河的无情奔流,另一方面又留恋已经逝去的往日的静止和安稳(115、131)。这个案例研究很好地将时代剧变内化为个人时间经验中的矛盾,为我们观察历史变迁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对旧体制的记忆乃至留恋,使得夏多布里昂还不能成为“未来主义者”那样纯粹的现代体制的信徒。1909年,意大利未来主义者马里内蒂(Marinetti)发表《未来主义宣言》,鼓吹“速度的美感”,一台轰鸣的汽车比胜利女神雕像更为美丽,因此应该把意大利从“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好古癖等蛆虫”的手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最彻底的未来主义。马里内蒂质问道,“向后看还有什么用?”(149—150)这种一往无前地冲向未来的热情是夏多布里昂所没有的。但法国大革命释放出的追求新事物的冲动力和对革新的礼赞之情,其势头终于在200年后走到了拐点。
二、当下主义:背景及表现
科泽勒克的研究集中于历史性的“旧制度”向现代体制的转变,阿赫多戈更进一步,试图描绘现代体制向另一种体制的转变,这种新体制就是他所称的“当下主义”。《历史性的体制》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讨论当下主义,即“时间秩序II”。他认为现代体制(或称未来主义)向当下主义转折的标志性日期是1989年。简单地说,当下主义是当下视角取代未来视角,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性体制(150)。这可以皮埃尔·诺拉在纪念一战结束100周年的访谈作为切入点。诺拉认为,法国当代的年轻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祖国至上”的情感已经难以理解,也感受不到从恺撒到拿破仑之间的那种历史连续性,而过去这种连续性曾十分强烈。这是一种非常醒目的断裂。“当下的主宰地位和对悠长的时间性的遗忘,已经造成受惠于(dette)前人的意识的消失,而这种意识才是构成传承的关键所在”。但2018年的法国人不再认为自己蒙受了先人的遗赠。(28)http://www.lefigaro.fr/histoire/centenaire-14-18/2018/11/09/26002-20181109ARTFIG00228-pierre-nora-14-18-conserve-une-place-eminente-dans-notre-memoire.php(2019年2月15日访问).诺拉的话已经指出了当下主义的一大特征:当下占据了主宰地位,法国人不再感受到历史的连续性。在1984年为《记忆之场》写的总序中,诺拉就已提出这种当下主义的特征。他在讨论当时法国的档案狂热症时说:法国人既想完整地维持当下,又想完整地保存过去。迅速而确定无疑的消逝意识,与对当下确切意义的焦虑、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结合在一起。(29)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in Pierre Nora ed.,Les lieux de mémoire,Paris:Gallimard,1997,p.30.
阿赫多戈认为《未来主义宣言》中就已包含着当下主义的苗头,因为对过去的彻底否定本身就意味着时间连续性及时间中进步感的消失,马里内蒂声称“时间已经死亡”,他所关注的只有眼前的变革(150)。但当下主义真正成为时间秩序的主流,应是二战后新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像诺拉一样,阿赫多戈也很强调1968年“五月风暴”的意义:及时行乐的口号已经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经验。(30)[法]弗朗索瓦·阿赫多戈著、赵飒译:《灯塔工的值班室》,第133—134页。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放大了当下主义的时间感知(31)参阅拙文《“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的法国史书写》,《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如战后长期经济增长的终结,追求光明未来的革命理念的衰退,失业率无法遏制地攀升,福利国家的窘境——福利国家本来是以美好明天为名而建构起来的,但面对困境时,政府的应对措施完全是得过且过的短期政策。人数庞大的失业者更谈不上未来规划,这些“没有未来的人”的日常时间经验是一种绝望的当下主义。消费主义则从另一个方向助长了当下主义:人们期待用一分钟的时间纵览几十年的历史,用几张旅游照记录漫长的旅途,时间经验被压缩在当下的体验中(155—156)。
除了罗列当下主义表象,阿赫多戈试图通过对两个核心概念的分析,来勾勒不同历史性体制的嬗递和当下主义诞生的“长时段”背景。这就是该书最后两章论述的对象:记忆和遗产。记忆是20世纪末整个法国学界的关键词,但记忆与历史研究的结合却是相当晚近的事。修昔底德曾拒斥记忆,认为记忆不可信,19世纪的“科学历史学”踵武修昔底德,“以过去与当下之间的截然两分”为研究工作的起点。当时人的看法是:“一个时代的历史只有在这个时代彻底消亡时才诞生。因此历史学的领域就是过去。”(167)集体记忆研究的先驱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一个社会的记忆是“依据现有的框架进行加工、以便能重构”的记忆。(32)Maurice Halbwachs,La mémoire collective,2e édition,Paris :PUF,1968,pp.57,73.因此哈布瓦赫记忆概念的着重点在于其当下性,且在历史和记忆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从而将历史学者打发到作为“外在记录”的档案中去了(167—168)。
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诺拉将记忆引入历史研究,不啻为一个转折。诺拉拒绝过去与当下之间的两分法,坚持当下史学家的责任在于“有意识地在当下之中浮现过去”。过去存在的方式就是它在当下之中浮现的方式,但这种浮现是学者的操控。这就是《记忆之场》的假设前提。诺拉提出的“第二层次的历史”主要不是关注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对过去在“连续不断的当下”的意义感兴趣,对过去在当下的整个运作和被操控感兴趣。(33)Pierre Nora, Présent,nation,mémoire,Paris:Gallimard,2011,p.169.记忆研究关注的是存在于当下的过去,而存在的方式就呈现为记忆。不过,《记忆之场》之所以能备受关注,同样是因为它是应对法国当下的局面而产生的。20世纪末,法国人的历史意识和时间经验发生重大转变,但与之伴生、看起来令人费解的情形是法国人对保存过去的狂热,“一切都被档案化”(160),再就是20世纪最后20年出现的数以千计的地方遗产协会(247—248)。这些就是诺拉那句著名的话所揭示的现象:之所以这么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经不存在。(34)Pierre Nora,“Entre Mémoire et Histoire: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p.23.过去的痕迹越是在现实中找不到延续下去的理由,人们就越执着于保存它——甚至像保护艺术杰作一样保存最不起眼的烤炉和乡村洗衣石。(35)Pierre Nora,“L’ère de la commémoration”,in Les lieux de mémoire,pp.4699-4710.但是,当代人对过去的记忆表现为一种连续性的断裂:今天记忆的本质“不再是应该从过去汲取的、为人们期望中的未来做准备的东西;而是让当下呈现给自己的东西”(36)Pierre Nora,“Pour une histoire au second degré”,Le Débat,No.122,2002,p.27.,记忆是一种当下主义的工具(171)。正如当代法国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为了在未来延续1914年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仅仅是为了当下的人们去了解和怀念——更何况当下的欧洲并不需要过去的爱国主义去与邻国战斗。
这就可以理解何以阿赫多戈说《记忆之场》是一部面向当下、为了当下的著作,它不是为了宣示未来而了解过去,这是与拉维斯《法国史》的根本不同之处。(37)François Hartog,“Temps et histoire:Comment écrire l’histoire de France?” Annales.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50e Année,No.6 (Nov.-Déc.,1995),pp.1219-1236.当代法国大革命史学者让—克莱蒙·马丹在讨论所谓的“记忆时刻”时说,在以前的史学中,“未来是刻写在过去的延续性中的,当下的纪念则保证了过去向未来的过渡”。(38)Jean-Clément Martin,“Histoire,Mémoire et Oubli.Pour un autre régme d’historicité”,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47,No.4 (2000),pp.783-804.正是在这种未来主义信念下,当拉维斯在1922年的满目疮痍中撰写其《法国史》的总结论时,依然认为历史将迈向一个新的阶段,而“法国仍将是先锋”(177—178)。然而诺拉不仅意识到当下的法国与拉维斯时代的严重断裂,也知道历史学者不能再继续充当“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摆渡人”了(195);不仅因为未来与当下的隔阂,也因为拉维斯式的未来理念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不论是法兰西民族的历史使命感,还是追求乌托邦社会的革命冲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终结具有象征意义:科泽勒克曾说,美苏之间的冷战可以视为对未来的竞争(39)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88,pp.5-6.,然而冷战的终结意味着人们渐渐失去了对更美好未来的关注。
《历史性的体制》最后一章讨论的是遗产概念及实践的演变(203—256)。1980年是法国的遗产年,遗产这一术语像记忆一样弥散着整个法国社会,以致诺拉说法兰西民族都已经“遗产化”了。阿赫多戈对遗产概念的探讨时间跨度很长,借此展现其在各种历史性体制中的样态。在遗产概念发展史上,罗马的再发现占有突出地位。14世纪以来,彼得拉克等人不断塑造着与monuments(历史纪念物)相关的概念,但他们经常是带着崇敬的目光看待罗马的遗址,期待复活过去的雄伟和优雅,因此很接近“历史导师”这一旧体制。法国大革命期间,遗产概念发生了时间指向上的转变。在革命者看来,对古代遗产的发掘和保存,将有助于明日的艺术呈现“新面孔”,保存过去是为了开拓新的未来。与此同时,抵制汪达尔主义的革命者发明了“保管”(dépt)的理论,认为他们有责任为后代保存过去的遗产。1816年,人们创建了“法国历史纪念物博物馆”,当时各展厅按时间顺序布置,在试图再现每个时代特色的同时展现进步的理念,尤其是通过光照变化效应来体现这一点:中世纪各展厅是半昏暗的,17—18世纪的各展厅则是耀眼的光芒。这些展品不仅见证了法国多个世纪的光荣,还呈现出时间中的进步秩序。这种呈现方式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梯叶里和米什莱后来回忆,这使他们产生了民族历史的统一性的观念。这家博物馆中的遗产所反映的时间秩序,与拉维斯《法国史》中的时间秩序是一致的:这就是展现时间中进步的现代体制。
进入20世纪后遗产概念的内涵日益繁复,甚至世界范围都是如此。与之相应的是遗产确认乃至遗产“制造”在不断加速。在法国,20世纪后期遗产的价值还在于:它植根于某种记忆,如某些群体的、地方的、社区的记忆,现在这类记忆像民族—国家的记忆一样具有合法性和保护的紧迫性,因为作为象征符号的遗产见证着已经或正在消失的过往——这就是人们要保护烤炉和乡村洗衣处的原因。
阿赫多戈的当下主义,首先针对的是1789年后曾盛行一时、但业已从欧洲地平线上消失的未来主义视角。但当下主义开启了一种没有方向的时间经验,各个领域的不确定性都在上升(260)。20世纪末的环境保护议题就凸显了这一点。保护或维护的概念,本身就有较强的当下指向,但它还暗含着对未来的新看法:未来不再必然是光辉美好的,发展已经给未来带来威胁。人们对于日益加速的变革不再持有单纯的乐观主义,转向了另一种审慎的责任感,于是责任原则平衡乃至压制了进步主义和“期待原则”(260—262)。在历史性的现代体制中,当下只是通往未来的过渡阶段,期待视阈一片光明。然而在当下主义的历史性体制中,当下不仅失去了与过去真切的连续感,未来也已晦暗不明,甚至令人忧心忡忡。在这种时间体验中,当下在焦虑地将过去和未来都吸纳进自己的关切中。让—克莱蒙·马丹则将当下主义与后现代思潮联系了起来:“宏大叙事”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让历史书写丧失了方向标,同时也在酝酿另一种历史性体制。(40)Jean-Clément Martin,“Histoire,Mémoire et Oubli.Pour un autre régme d’historicité”,p.785.
在论述从历史性的旧制度向现代体制的过渡时,阿赫多戈找到了夏多布里昂这个突出的案例。夏多布里昂的转变,与他在革命时代的时间经验直接相关。上文已经指出未来主义消退、当下主义抬头的种种迹象,如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世界进步主义信念的动摇,追求未来美好社会的革命热情的消退,以及环境危机等现实问题的冲击。应该特别强调1789年和1989年这两个标志性日期的象征意义。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实际上标志着现代革命带来的未来主义动力的消退。阿赫多戈在书中提到了著名法国革命史专家弗朗索瓦·孚雷(或译傅勒)的论点,但他并没有就此展开。在大革命200周年到来之前,孚雷有一个著名的观点:革命结束了。质言之,以革命手段推动社会和政治制度变革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吸引力。孚雷甚至认为,此时的法国已经实现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和解,法国最终实现了政治稳定。随着经济上的现代化,消费主义也使人们的视野更多地局限于当下。从国际环境来说,与邻国的和解和欧洲建设的深入,使得法国人不再需要过去的那种战斗的民族主义精神了。(41)François Furet et Mona Ozouf eds.,Dictionnaire cr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Idées,Paris :Flammarion,2007,pp.20-23.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诺拉提到的历史连续性的断裂,以及阿赫多戈引述的孚雷的论断:未来已经封闭(21)。
阿赫多戈对当下主义的探讨集中于法国和西方世界,这无疑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冷战结束后消费主义乃至后现代思潮的确可以认为是某种全球性现象,乌托邦理想的衰退随处可见。但是,20世纪末的法国和西欧有一个很特殊的境况:民族主义热情的消退。由于欧盟建设的深入和政治局面相对稳定,也由于战后殖民秩序的瓦解,西欧进入了某种后民族—国家时代,所以诺拉说《记忆之场》是一部“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历史,有关民族光辉伟大的叙说失去了过去的诱惑力。但不能认为其他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形。虽然全世界的人都日益被当下的日常生活裹挟,但各地的时间秩序,尤其是对未来的看法,与西欧不可能完全一致。
阿赫多戈把1989年视为当下主义兴起的标志性日期,但他没有关注铁幕另一边经历的时间秩序的深刻危机,这是个巨大的遗憾。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描绘了苏联追求理想社会的未来主义时间秩序崩塌时产生的深刻的精神创伤。苏联解体后的社会的确存在当下主义的表征,如追求一夜暴富取代了过去的革命理想主义。但留恋旧秩序的心态也很强烈,这与法国很不一样。(42)[白俄] 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因此,当下主义如果要成为一个普遍概念,它应该是复数的。
余 论
《历史性的体制》不是对人类历史中可能存在的时间经验模式的全面梳理,它是对研讨各种不同时间体系的一种“邀请”。(43)Pascal Payen,“Revue des Régimes d’historicité”,Anabases.Traditions et receptions de l’Antiquité,1/2005,vaira 1,pp.295-298.作者虽然采取了“远距视角”,探究了太平洋诸岛的历史性体制,也曾以日本的遗产战略作为与西欧遗产概念的参照(209—211),但其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西方。因此,历史性的体制概念是否能运用于其他古老文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文明中是否发生过演变以及如何演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但有理由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的信念,相当接近于“历史导师”的旧体制;而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前后相继的社会形态,论证某种历史道路的“必然性”,看来是以一种明显的未来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视角取代了传统的王朝兴替叙事模式。这种转换应该被视为一种时间秩序的转变。不过,在革命史观日渐式微、民族复兴的话语频繁闪现的今天,同样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期待视阈的微妙变化。
该书的一大启示是对时间秩序的危机和不同历史性体制碰撞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历史观念和历史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阿赫多戈对新旧体制之间的夏多布里昂的分析,可否运用在其他史学传统的某些转折性人物身上呢?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认为,传统史学讲述的是朝代史而非国家史,“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这可以视为他对中国传统历史性体制的描述,即一种随朝代兴替而中断和重启的时间,因而具有循环特征;当他认为史学应“叙说进化之现象”,而且这进化是要贯穿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现代历史性体制;此外,旧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缺少系统性的理念,“皆取述而不作主义”。(44)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85—119页。凡此种种,均可与18—19世纪之交的欧洲现代历史哲学的产生建立起平行对应的关系。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19ZDA2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