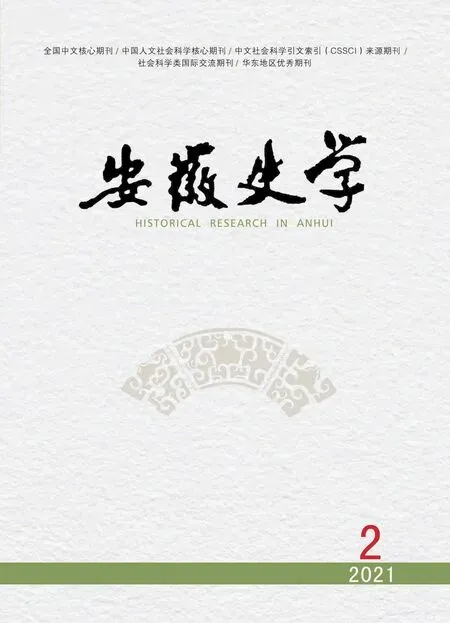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述析
张三南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在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民族主义研究领域,20世纪前叶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是备受关注的研究板块。我国学界对这一板块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梁启超、孙中山两位思想精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是中国首用“民族主义”概念之人,而后者的“三民主义”首先提及的就是“民族主义”。实际上,除梁、孙之外,曾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在其一生中对民族主义也多有论述,可谓是“民族主义”论者的又一代表人物。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长期未给予足够重视。
陈独秀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十分丰富,其思想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97—1921年的早期阶段,体现了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多方求索;第二阶段是1921—1927年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中期阶段,这是陈独秀论述民族主义最为丰富的时期;第三阶段是1927—1942年的后期阶段,这一阶段的论述既有“可贵坚持”,又有“消极意识”。在我国学界,现有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对第一阶段的关注,这实际上难以全面展现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历程的全貌,也相应“忽视”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板块的又一重要人物。(1)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陈独秀”和“民族主义”为组合篇名检索词进行检索(截止2020年12月31日),仅检索到9篇期刊论文关注的是陈独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这反映出学界对陈独秀中后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忽视”。有鉴于此,笔者拟在全面整理研读相关文献基础上,对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进行全面回顾和分析,希冀能为充实相关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一、早期的思想萌芽与多方求索
按照陈独秀本人在《实庵自传》中的说法,他的早期人生道路,并非族人所希望的“举人、进士、状元郎”的功名之道,而是他们想象不到的“康党、乱党、共产党”的革命之途。(2)参见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58页。如此人生历程形象概括了陈独秀早期民族主义思想的萌芽与多方求索。
陈独秀在回忆1897年7月到南京参加乡试时说,曾看到城里“房屋虽然破烂,好象人血堆起来的洋房还没有”。(3)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第560、563页。这句“人血堆起来的洋房”,厌恶之感跃然纸上。是年冬天,陈独秀又在《扬子江形势论略》这部他留存下来的最早著作中写道:“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4)陈独秀:《扬子江形势论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有学者认为此文措辞文雅,在显示文学才华之时,也折射出陈独秀对外患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5)参见Lee Feigon,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p.33.应该说,这一时期的陈独秀,无论是持何种文笔风范,也无论是对“洋房”的本能抵触,还是对长江形势的忧患意识,均体现出一种“反帝爱国”的朴实民族主义情怀。
南京之行使陈独秀亲眼目睹了晚清的种种腐败和怪异现象,由此走上了摆脱“选学妖孽”魔障和“天下主义”固有认识,求索民族解放和立国安邦的道路,并在康、梁影响下对“国家”有了全新认识。后来他描述道:“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6)陈独秀:《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卷,第560、563页。
此后,陈独秀四处求学,广汲新思想,充分展现了爱国救国的民族主义热情。1898年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接受新式教育。1901年10月赴日本东京留学。1902年3月,回到家乡安庆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学社”,传播新知,牖启民智,宣传爱国,鼓吹革命。当年冬天,与张继、蒋百里、潘赞化、苏曼殊等人仿照意大利人马志尼创立的“少年意大利”,组织“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的“青年会”,这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立的革命团体。1903年4月,参加“拒俄运动”,筹组“安徽爱国会”。8月与章士钊等人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创办《安徽俗话报》,影响极大,“一时儿与当时驰名全国之杭州白话报相埒”。(7)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1页。
1904年6月14日,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第5期发表《说国家》一文,署名“三爱”。从现有资料来看,此文应是陈独秀最早明言论及民族主义的文献。陈独秀在文中以白话文形式谈到国家“顶要紧”的几个要素:一是国家要有一定的土地;二是国家要有一定的人民;三是国家要有一定的主权。可以看出,陈独秀这种诠释符合现代国家学说的基本要义。
在谈到第二个要素时,陈独秀指出:一国的人民,一定要是同种类、同历史、同风俗、同言语的民族;西洋各国都是一种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他种人的辖治,这就叫做“民族国家主义”。为此,他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民族主义,指出原来是因为“民族不同,才分建国家。若是不讲民族主义,这便是四海大同,天下一家了,又何必此疆彼界,建立国家呢?”(8)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9页。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外来词语,20世纪初在中国才逐渐使用,1901年最早出现于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而陈独秀1904年便有了涉猎,实际上早于孙中山1906年12月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时正式提出“民族主义”。可见,陈独秀是中国最早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精英之一。
之后,陈独秀越发呈现出“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色彩。1905年初,他在安徽芜湖与柏文蔚、常恒芳共同发起组织“岳王会”,反对清廷与外国势力。1907年春,参加由章太炎、幸德秋水、钵罗罕·保什等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该会宗旨明确规定:“本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凡亚洲人,除主张侵略主义者,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皆得入会”。(9)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44、65页。虽然陈独秀对“亚洲和亲会”的兴趣是短暂的,但体现了其民族主义思想与“泛亚主义”(pan-Asianism)的关联,而后者又类似于他后来推崇的国际主义。(10)参见Lee Feigon,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86.
1914年11月,陈独秀首次以“独秀”之名在《甲寅杂志》发表了著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此文是陈独秀十几年来为革命救国不断奔波且又不断遭受挫折的心路总结,标志着其民族主义思想进入一个新的认识阶段。他首先强调了“无爱国心与自觉心”的严重性:“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11)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82、83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12)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文集》第1卷,第82、83页。这实际上同时强调了抒“情”和启“智”的重要性。
为在国人中实现抒“情”和启“智”,陈独秀积极投身革命实践。在《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的次年,陈独秀就把抒“情”启“智”的希望寄托在以《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为思想阵地的新文化运动上,以期“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13)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第44、65页。对此,胡适后来曾说道,“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革命的信条。”(14)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2页。
历史见证了陈独秀的功绩。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为实现复辟帝制的野心,大力提倡尊孔读经。陈独秀等人看穿了袁世凯之流麻痹国人的图谋,不遗余力通过《新青年》这个新文化运动阵地,提倡民主与科学,启迪民智。新文化运动沉重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礼教,推动了民众的思想觉悟,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陈独秀的民族主义思想从此有了新的理论武器的指导。
二、担任中共领导人期间的诠释与批判
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担任了6年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这期间是陈独秀政治理论与实践最为活跃的时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也最为丰富。他对民族主义的诸多诠释与批判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尤其是关于民族主义涵义与类型、“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论述,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
(一)关于民族主义的涵义与类型
清末民初,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从不同角度对民族主义的涵义进行了诠释。1902年,梁启超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5)梁启超:《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继梁启超之后,孙中山的诠释则经历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两个阶段。
作为中国最早论述民族主义的思想精英之一,陈独秀除了在1904年6月《说国家》一文中首次提及民族主义外,还在1924年3月发表于《向导》周报的《评中俄协定》一文中专门阐述了民族主义的涵义。他说:“我们不愿为他人奴属,也不愿奴属他人,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既然不欲他人拿帝国主义来压迫我,我们便不应该拿帝国主义去压迫人,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主义之定义。”(16)陈独秀:《评中俄协定》,《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7—588页。可以看出,相比较于国内外对民族主义或褒或贬的各种定义,陈独秀的定义更能体现民族主义不偏不倚的“中性”意涵。简言之,就是“不为他奴,也不奴人”,通俗中肯,堪为名句。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关于民族主义最为典型的分类是“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梁启超曾指出:“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1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5—76页。实际上,“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之分反映的是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道路的分歧,前者主张建立包括满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后者主张建立单一汉族国家。当时,梁启超等立宪派主张“大民族主义”,而孙中山、邹容等革命派则主张“小民族主义”。当然,孙中山等人的观点后来发生了变化,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演变为了“五族共和”。
陈独秀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分类。1924年9月,他在《我们的回答》中指出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自求解放,同时却不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民族,这可称做矛盾的民族主义;一是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皆有自决权,主张自求解放,不受他族压制,同时也主张解放隶属自己的弱小民族,不去压制他,这可称做平等的民族主义。”(18)陈独秀:《我们的回答》,《陈独秀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22页。不仅如此,在一个月之前的《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中,陈独秀就曾鲜明地阐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关于民族主义的不同态度,指出:“资产阶级所谓民族主义,即帝国主义之工具;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民族主义乃是弱小民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意义。”(19)陈独秀:《欧战十周年纪念之感想》,《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104页。可以看出,相对于梁、孙等人,陈独秀的分类彰显了阶级分析法的独特视角。这在当时是重要的理论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强调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革命的民族主义者相互同情和援助的重要性。他说:“无论何国工人,如果他们不同情于被压迫的民族运动,便是不愿意参加打破帝国主义的世界;无论何国民族主义者,如果他们不同情于工人运动,如果他们反对阶级争斗,便是不愿意成就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20)陈独秀:《无产阶级与民族运动》,《陈独秀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6页。这种认识同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的辩证统一。
此外,陈独秀还专门批判了另外两种民族主义类型。一是“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民族主义”,即“资本主义前的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这种民族主义不懂得现代民族运动特性,认不清弱小民族之敌,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实则“放过了民族运动之敌人”。他还指出,中国不脱封建时代思想的知识阶级即如此,“或极力主张民族运动(如青年党),或自以为是民族主义者(如国民党右派)”,已成中国民族运动的一个大患,“竟不看见剥削压迫中国民族无所不至的帝国主义者,……实际上做了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21)陈独秀:《列宁主义与中国民族运动》,《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240页。二是“一般高等华人的民族主义”。陈独秀指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已在中国造成一种‘民族的巴士的狱’,朘削中国人之心脏”,而“所谓高等华人亦复同一腐败,一般高等华人尚自以为崇信民族主义,但实则已为帝国主义者之奴隶”。(22)陈独秀:《打破“民族的巴士的狱”》,《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37页。陈独秀的批判用语虽略显口语化,但足以形象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现实。
(二)关于“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
陈独秀对涉及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相关议题有着诸多诠释与批判,这些内容同样成为了其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应有意涵的诠释。
1922年9月,陈独秀在《国民党是什么》中提到:他曾亲身聆听孙中山演讲三民主义,其中首讲的就是民族主义。陈独秀指出,孙中山演讲的大意是说,“满洲皇室虽然推倒了,而中华民族备受列强的压迫,民族主义仍有提倡的必要”。(23)陈独秀:《国民党是什么》,《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286页。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已由“排满”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
1924年7月,广州沙面工人举行大罢工,起因是英帝国主义颁布新警律,对华工苛加严规,肆意侮辱。陈独秀撰文声援,指出民族主义的政府和每个民族主义者都应承担起应有责任,“为民族的人格与自由权利而战斗”,“应该站在民众前面,不应该跟在民众后面,更万分不应该站在中立调人地位”。(24)陈独秀:《沙面罢工与民族主义者》,《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95页。很明显,陈独秀在此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应有意涵进行了清晰地界定。
一个月后,陈独秀在《向导》周报“寸铁”栏目中再次对“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应有意涵进行了诠释,指出:“主张民族主义的党,便应该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决不应该单是对民族运动表同情。”(25)陈独秀:《寸铁》,《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113页。陈独秀的诠释充分体现了立足于民族和工农利益的革命性。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指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参与下,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减少了前时代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增加了新的色彩——反资本帝国主义之世界革命的色彩”。(26)陈独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31页。有学者认为,陈独秀这种认识代表了以强烈的民族主义为特征的时代的一种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倾向。(27)参见Lee Feigon,Chen Duxiu: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p.6.这种认识,体现了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观的继承和发展。
其二,对国民党右派曲解“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意涵的批判。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为争夺领导权,排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多方曲解。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反击,其中陈独秀在1926年春夏连续撰文对国民党右派曲解“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意涵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
1926年3月,陈独秀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对国民党右派宣称的“打倒帝国主义,乃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势力而言”而非“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见解非常糊涂”。(28)陈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358页。
4月,陈独秀进一步剖析了国民党右派曲解民族主义的逻辑错误。早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曾明确宣示民族主义的两层意思,即“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指出其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29)《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14页。然而国民党右派后来却宣称,“本党之民族主义,主张融合此人类四分之一人口以与战胜民族抗”。(30)陈独秀:《国民党右派大会》,《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386、386—387页。陈独秀对此指出,国民党右派把人类分为战胜民族与战败民族而不是帝国主义者与被压迫者,主张与“战胜民族抗”而不是“与帝国主义抗”,这公然违背国民党一大宣言的精神。陈独秀批判道:右派的民族主义“不问是非,专与战胜民族抗,我们真不懂得国民党右派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是什么一种逻辑?”(31)陈独秀:《国民党右派大会》,《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386、386—387页。
5月,陈独秀在《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再次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反对苏俄援助的所谓民族主义,指出他们“这种形式的逻辑”实际上“不是民族主义而是闭关主义”,“不是独立运动而是孤立运动”。(32)陈独秀:《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43页。
其三,对国家主义派曲解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批判。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义派的思想源头可追溯到1808年德国思想家费希特在《告德意志国民》中所提倡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国家主义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由资产阶级政客组成的政治派别,往往特指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代表人物有曾琦、李璜等人。因其标榜国家主义,故称国家主义派;又因其创办了《醒狮》周刊,称为醒狮派。国家主义派宣扬超越个人、民族、宗教、阶级和党派,从根本上否认国家的阶级属性,实际上成为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国家主义”是国家主义派对英文nationalism的翻译。nationalism在中文语境下常译为“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派之所以放弃“民族主义”而采用“国家主义”译名,是由于他们对nationalism做出了动态的、历史的考察。国家主义派重要人物、“中国青年党六魁”之一常乃德曾称:19世纪以前,“一族一国”的国家观念非常发达,用民族主义来翻译nationalism符合时代特征,但19世纪后人类的国家组织发生巨大变化,即把单纯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变为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各原素共同组成的国家,用民族主义来对应nationalism就不能体现时代的变化了。(33)参见常乃德:《十九世纪以来国家主义在学理上之发展》,《醒狮周报》第138期,1927年7月2日。这种解释以及国家主义派采用“国家主义”而非“民族主义”来指称19世纪后nationalism的做法,貌似是学理上的创新和发展,实际上仍难以避免其在理解民族主义演进史上的固有缺陷,也难以掩盖其无法理解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本质。实际上,“国家主义”是被用来指称民族主义在19世纪以来的表现形态,仍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之内。(34)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脉络中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的1921年7月,陈独秀就在《社会主义批评》中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浓厚的德意志国家主义色彩及其狭隘的民族主义本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写道:“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而德国底社会民主党不但忘记了马格斯底学说,并且明明白白反对马格斯,表面上却挂着马格斯派的招牌。”(35)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133页。为此他得出结论:中国应走俄国共产党的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主义道路。
1926年5月,陈独秀在《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一文中,针对有人质疑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否立足于国家主义这一问题,指出这是一个根本争论点,应有明确的解答。陈独秀从两方面批判了国家主义派认为孙中山是国家主义者,其“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观点。一是认为不能浅薄地理解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陈独秀写道:“不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爱他的祖国——中国,为他的祖国——中国奋斗的,他是极力劝中国同胞要恢复民族主义来救国的,……然而因此便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那就未免对于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理论之研究过于浅薄了。”(36)陈独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29、433—434页。二是认为,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点中可以看出其与国家主义的根本不同。陈独秀指出,孙中山把民族和国家分得很清楚,一向“赞成王道而反对霸道”,其民族主义明明“属于现代殖民地国际民族运动之特性”而非“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的民族运动之特性”,因此“不能诬中山先生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也不能说他的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就是国家主义”。(37)陈独秀:《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是不是国家主义》,《陈独秀文集》第3卷,第429、433—434页。
三、后期的“可贵坚持”与“消极意识”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失败。陈独秀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7月被解除中共领导人职务,后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之后,陈独秀逐渐靠近托洛茨基主义,曾于1931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1932年10月,因托派组织成员出卖被捕入狱,1937年8月日军侵占南京前夕获释。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四川江津。在1927年7月至1942年5月这段人生和政治生涯的后期阶段,陈独秀仍有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这些论述总体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可贵坚持”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多次违背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并犯有参加托派组织的重大错误。但在民族大义以及论述民族主义方面,他仍称得上是一位爱国人士,有着诸多可谓是“可贵坚持”的论述。
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及区分不同民族主义的辩证观点。
1931年11月,陈独秀在《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中重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族主义的辩证观点,认为对民族主义不能不论时空一概采用或否拒。他说:“一切政策与口号,若不择空间和时间一概采用或一概否拒,都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民族主义运动“都曾表示过赞助或反对两种不同的态度”。(38)陈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391页。在文中,陈独秀将民主、民族联系起来,主张在群众运动中不应忽视“民主民族主义”这面旗帜对于被压迫国家的必然性与重要性。陈独秀还指出,不能拘泥于“工人无祖国”的立场,极左倾地鄙弃民族主义,单纯认为民族主义仅属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坚信中国民族主义爱国运动的大势和前景,指出传统的民族主义运动将来还会不断发生,“一直到中国民族从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压迫之下完全解放出来”。(39)陈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398页。总体来看,陈独秀这些观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其辩证认识和坚持中国民族解放前景的态度值得肯定。
卢沟桥事变后,陈独秀坚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并撰文阐述了中国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1938年8月,他在《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中指出:中国民族运动是站在民族平等原则之上,与诸如沙俄大斯拉夫主义、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希特勒大日耳曼主义等帝国主义“以夸大自己的民族为口实来侵略兼并别人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40)陈独秀:《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605页。陈独秀这种辩证区分民族主义的观点同样值得肯定。
其二,坚持反对各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径。
陈独秀坚持反对各种错误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径,主要体现在对国民党“虚假民族主义”的揭露、对日本“社会主义者”错误观点的批判及对一些极左思想、行为的批判等几个方面。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被移交南京。消息传出后,胡适、傅斯年、爱因斯坦、罗素等国内外名人纷纷发声,呼吁国民党政府善待他。在后来的法庭审理中,“民国大律师”章士钊免费为陈独秀辩护,陈独秀本人也进行了慷慨激昂的陈述,两位公众人物的表现名噪一时,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在法庭陈述《辩诉状》时,陈独秀指出,在外敌入侵、占我领土的国难关头,有的人“不加抵抗,或空言欺骗,均与卖国同科,尚何‘民族主义’之足云”。(41)陈独秀:《辩诉状》,《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476页。这实际上是对国民党政府“虚假民族主义”的讽刺和揭露。
陈独秀专门撰文批判了日本一些“社会主义者”以爱国主义为名为日本侵华战争辩护的错误行径。1938年8月,陈独秀在《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中批判他们“是站在形式逻辑的观点上,玩弄名词,而不曾考察其实际内容”,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进步是因为它打击了帝国主义,而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反动是因为它帮助自己的政府压迫侵略其它国家和民族,并强调“这是对于爱国运动之辩证的见解”。(42)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619—620页。
此外,陈独秀还对一些人的极左思想进行了批判。九一八事变后,一些极左分子借口国民党曾提出“对日宣战”的口号,便机械地“为反对而反对”。陈独秀对此进行了批判,在1931年12月《论对日宣战与排货》一文中指出这种思想实质上和不抵抗主义的效果一样。
(二)“消极意识”
当然,陈独秀晚年也曾流露出关于民族主义的“消极意识”,尤其是在1942年上半年。当时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艰难时期。在德国法西斯“闪电战”进攻下,苏联遭到重创。日本则在太平洋战场挟着成功偷袭珍珠港的余威,气势咄咄逼人。在中国,抗日战争也处于最为艰难的对峙时期。
在此背景下,1942年2月陈独秀在汉口《大公报》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后有学者在此文译介按语中认为当时的陈独秀“最为悲观”。(43)参见Gregor Benton,Chen Duxiu’s Last Articles and Letters(1937—1942),Routledge,2019,p.78.陈独秀在这篇时评文章中流露出了对世界局势的消极判断。他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世界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之“民族自决”、“民族解放”,本是一种幻想;而在两派帝国主义争着以战争裹胁全世界落后国家及弱小民族的情况下,民族斗争会受到限制。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微妙变化,认为“无论是对于轴心国或非轴心国之斗争均应从民主主义出发,不应从民族主义出发,因为专制的德意日三国之携手横行,已冲破了各个民族之最后铁丝网。”(44)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675页。可以看出,在国际国内形势极其艰难的情况下,陈独秀流露出的“消极意识”无形中放弃了民族主义这个抗击强权的思想武器。这是不可取的。
5月,陈独秀又在《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流露出类似的“消极意识”。此文是陈独秀论述民族主义的最后一篇文章,两周后他便在贫病交加中辞世。陈独秀在文中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领导的国际集团内,落后国将被吸引着被强迫着和领导国全面合作,……没有任何民族主义的英雄能够阻止这一国际集团化的新趋势;而且被压迫的民族,也只有善于适应这一国际新趋势,将来才有前途。”(45)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陈独秀文集》第4卷,第685页。可以说,陈独秀对国际集团化新趋势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他据此来否认落后国家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解放可能性的观点,却是消极和错误的。他在文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英雄”的表述显然也带有揶揄的意味,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否定民族主义重要性和可行性的“消极意识”。
结 语
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清末民初到国民革命再到抗日战争的诸多历史时期,在其复杂的人生际遇中受到了多方政治思潮的影响,包括康梁学说的启蒙、西方思想的启迪、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熏陶,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带来的顿悟,当然也包括后来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陈独秀接触的思想如此广泛,其政治生涯犯有严重错误,其民族主义思想也融合了不同的思想元素,以至于全面、准确地对其认识和评价绝非易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如有学者所言,“陈独秀自从跳出传统思想樊篱、走入现代思想世界之后,一变再变,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第三国际的社会主义到第四国际的社会主义,再到民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变化完全出于真诚,是经过深入反省、痛苦思索达成的,无论思想本身正确与否,与若干思想投机者不可同日而语。”(46)何卓恩:《民族主义内在的困境——陈独秀国家观从民族主义到自由主义的转变》,《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陈独秀民族主义思想发展历程,总体呈现的是一幅为民族解放不断求索的路线图,在维护民族大义方面是真诚的。他不愧为20世纪前叶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界中重要人物。无论是其1904年堪称中国关于民族主义的最早论述之一,还是1924年堪称定义民族主义的名句,无论是其多年围绕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诠释,还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而对民族主义进行的辩证论述,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百年重要文献整理与研究”(20AMZ0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