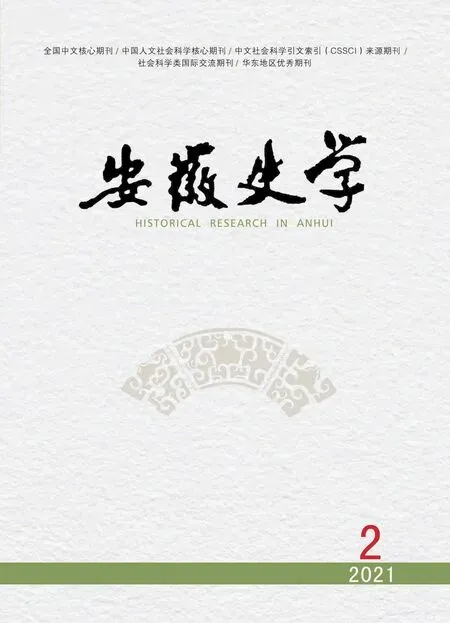抗战时期日伪的烟毒政策及其影响
——以河南沦陷区为例
谢晓鹏
(郑州大学 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抗战时期,作为日本侵华战略的重要一环,日伪当局在广大沦陷区积极推行烟毒政策。关于抗战时期日伪烟毒政策的研究,过去学界已取得不少成果(1)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日]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8年版);[韩]朴疆:《中日战争与鸦片(1937—1945):以内蒙古地区为中心》(台北“国史馆”1998年版);李恩涵:《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1895—1945)》(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曹大臣、朱庆葆:《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韩华:《罪证——从东京审判看日本侵华鸦片战争》(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这方面的论文较多,笔者不再一一列举。,但关于河南沦陷区日伪烟毒政策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且该政策对伪政权的负面影响往往被忽视。本文拟以河南沦陷区为例,主要运用抗战时期伪政权的报纸、政府公报及当事人回忆等资料,深入探讨日伪的烟毒政策及其影响。
一、日伪烟毒政策的制定
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广大沦陷区不仅实行硬性的政治高压、经济掠夺、文化破坏等活动,还积极推行柔性的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其毒化政策更是危害中国人身心健康、泯灭中国人民族意识、削弱中国人抗战意志的狠毒伎俩。“日本的鸦片政策是由以首相为总裁,外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为副总裁的兴亚院及兴亚院以后的大东亚省制定和掌握的,是作为国策,由国家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地推行的。”(2)[日]江口圭一:《日中鸦片战争》,第205页。当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允许种植、贩运、吸食鸦片毒品,是日本最高决策者的既定方针。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增加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吸食鸦片毒品的人,都是精神萎靡,缺乏斗争精神,中国人民中多一个鸦片烟鬼,即少一份抗日力量,这对削弱人民的抗日力量很有好处。”(3)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故此,在河南等沦陷区,根据日本以战养战、以毒养战的需要,受日本占领军的指导和操控,伪政权制定了一系列烟毒政策。
早在1939年5月,伪河南省公署财政厅即暂行拟定了《禁种烟苗罚款办法》,并训令伪省署所辖各县遵照执行。该训令指出:“查鸦片为害,妇孺皆知,我国久悬禁例。事变以后,本省各县治安多未恢复原状,一般民众鉴于时机可乘,纷纷私自栽种,本宜根本铲除,严厉断绝,以肃禁政……兹为顾恤民艰、寓禁于征计,暂拟禁种烟苗科收罚款办法,规定每亩缴费八元,并于土药晒成后,一并售于省署,不得零卖,以资渐近断绝。”(4)《寓禁于征:财厅颁发各县禁种烟苗罚款办法》,《新河南日报》1939年6月14日,第3版。该办法可以概括为:以罚代禁、寓禁于征、统一收购、鸦片专卖。同年10月25日,伪河南省公署又发布训令:“本省此次禁政力矫积弊,与民更始,凡已种者科以罚,再种者科重罚,若重罚而再种者,他年另定重法严厉执行。本年则姑念灾乱之后,一面救济农村,一面实行禁政,冀其自行悔悟,咸具戒心,而仍取其渐进禁绝政策。该县知事为民命所托,务对民众剀切晓谕,对于本署寓禁于征之至意,其各心领神会,遵令办理。”(5)《河南省公署训令》(1939年10月25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5号,1939年10月27日。可见伪河南省公署对于愈演愈烈的鸦片问题,采取的是“渐进禁绝政策”,即“寓禁于征”政策。
随着“寓禁于征”政策的推行,鸦片税征缴入库工作亟待落实。1940年8月13日,伪河南省公署财政厅训令各县禁种烟苗办事处,要求尽快将违种烟苗罚款催缴入库,并强调指出:“其土药(指土制的鸦片——引者)查验事项,着自结束之日起移交各该县税务局所接办。”(6)《河南省公署财政厅训令》(1940年8月13日),伪《河南省公报》第85号,1940年8月15日。这说明了伪财政厅拟将鸦片税作为一种特殊税收来管理。这一情况在邢幼杰(7)邢幼杰,字汉三,曾任伪河南省公署宣传处长、《新河南日报》社长、新民会河南省总会事务部长等职。的回忆录中也得到证实。据邢幼杰称:“河南省沦陷区特别是豫东淮阳、鹿邑等县,种植鸦片面积,与年俱增。伪财政厅见有利可图,借口禁种鸦片,寓禁于征,呈经伪省署核准。农民种鸦片一亩,科以八元罚金,实质是每亩收税八元,由财政厅委派专人到各县与县公署合组鸦片罚金征收所负责办理。”(8)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第112页。
为加强华北日伪区鸦片管理并统一烟毒政策,1940年8月3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华北禁烟暂行办法》,自当年10月1日起在包括河南沦陷区的伪华北政权统治区施行。该办法对华北禁烟的主管机构——禁烟总局及各分局,以及鸦片之制造、吸食、运输、买卖和罂粟之栽种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还公布了《华北禁烟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从鸦片之吸食、制造及贩卖、栽种及收买、药用及科学用鸦片、罚则等五个方面,更加详细地规定了华北日伪政权对鸦片的统制政策。(9)《华北禁烟暂行办法、华北禁烟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40年8月),天津市档案馆藏,档号:J0001-3-003743-028。由这两个法规可以看出,伪华北政权表面上要“厉行禁烟”,但实际上只要“经主管官署许可”,鸦片可以栽种、制造、运输、买卖、吸食等。
为进一步规范鸦片税收,1941年4月17日,伪河南省公署财政厅对所辖各县营业税征收局、所发布训令:“查本省人民狃于积习,愍不畏法,各地仍多违种罂粟,因而土药产销颇丰。前为寓禁于征计,曾查贴销毁证,酌收证费,嗣因与统税感有抵触,改贴查验证。兹为补救省库收入计,参照河北、山东等省办理情形,拟将查验证及现行土药行商营业税一并取销,改征土药贩运特种营业税一种,税率每两征收一元五角、县附加捐五角(附加捐仍直接拨县),征收手续与营业税相同,惟于特种营业税完讫之后,应于土药包皮上加盖‘特种营业税完讫’戳记,以便查验。至土药、土膏店之营业税,仍旧征收,不加变更,庶免与禁烟行政及关系机关有所抵触。当经改订上项土药特种营业税办法提经第四次省政会议议决通过,纪录在卷,特定自五月一日起实行。”(10)《河南省公署财政厅训令》(1941年4月17日),伪《河南省公报》第168号,1941年4月24日。由此可知,伪省署财政厅鉴于“土药产销颇丰”,“为补救省库收入计”,征收土药贩运特种营业税及土药、土膏店营业税等,进一步完善了“寓禁于征”政策。同年6月11日,伪省署财政厅针对土药商贩偷漏税情况,又训令各辖区营业税征收局、所,称:“惟绕越偷漏、以多报少,为奸商之惯技,而土药为尤甚。各营业税征收局、所务应督饬员司加紧查缉,以免偷漏。再贩运土药既为营业之一种,则各该局、所遇有查获土药商贩实行偷漏案件,自应适用河南省营业税征收暂行章程第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酌量情节,处以三倍以上、十倍以下之罚金。”(11)《河南省公署财政厅训令》(1941年6月11日),伪《河南省公报》第185、186合订号,1941年6月18日。该训令表明伪省署财政厅对土药特种营业税的重视,以及对土药商贩偷漏税处罚的严厉程度。
当然,日伪“寓禁于征”的烟毒政策在给日伪政权增加可观财税收入的同时,也会威胁其统治秩序,特别是容易导致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风气败坏,这一发展趋势逾到后来逾加明显。故此,1942年秋季以后,伪河南省当局尝试采取了一些比较严厉的禁烟禁毒措施。如1942年9月19日,伪河南省公署发布训令称:“查鸦片一物足以戕贼个人健康,影响社会生计,动摇国家根本,阻滞民族文化,为祸之烈令人寒胆……本省长深痛人民之沉沦,民族之颓废,已具决心,思将此种毒祸一举而廓清之。自本年秋后起,对于本省所属各道市县,无论任何区域,绝对严厉禁种烟苗,并限文到后,即由各道市县严行转饬所属,无论何人及任何地域,一概不准栽种烟苗,如敢故违,定予从严治罪。”(12)《河南省公署训令》(1942年9月19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27号,1942年10月7日。次年9月28日,由伪省署民政厅制定的《河南禁种鸦片烟苗方案令》在伪省署机关报《新河南日报》上公布,具体实行事项包括分区查禁、划段勘察、履勘复查、彻底考查、种户惩处、查禁人员惩处等。其中对查禁人员惩处规定:“一、发现在五十亩未满者,县知事记过,履勘人员记大过。二、发现在五十亩以上,一百亩未满者,县知事记大过,履勘人员撤职查办。三、发现在一百亩以上者,县知事撤职,履勘人员撤职查办。道查禁人员如有失察情形,由省公署酌量情节予以处分;道县查禁人员如有徇情隐节,包庇栽种,因而收受贿赂,或借端勒索者,依法严惩;公务人员(包括警队)如有私种,或假名栽种罂粟情事,依法从重处罚云。”(13)《澈底根绝鸦片毒氛,本省制定禁种烟苗方案》,《新河南日报》1943年9月28日,第2版。1944年10月31日,伪河南省当局再次向所属各市县发布训令,指出:“现值秋末,又届播种之期,深恐农民无知,违禁私种,误罹法纲,各市县长玩忽功令,不能切实查察,致受连带处分。兹特重申禁令,嗣后如各县农村再有发现违种烟苗情事,一经查出,定即依法分别从严惩办。”(14)《河南省政府训令》(1944年10月31日),伪《河南省公报》第498、499合刊号,1944年11月14日。
以上这些训令与过去的有关规定相比确实更加严厉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烟毒肆虐已到了不得不严禁的地步。那么,这些训令在当时河南沦陷区能否得到贯彻落实呢?我们且看1944年3月23日《新河南日报》的社论分析。该社论指出:“禁种鸦片,历年皆有明令,然禁令既发于前,又何须铲苗于后?此无他因,盖过去禁令执行之不澈底也。自表面观之,似为民众顽忽政令,仍擅自播种,致政府不得不再事铲苗,以期施策之澈底者。孰不知禁令所以据民众顽忽,竟至擅种之原因,实应归疚(应为“咎”——引者)于政府禁令之不能澈底……过去之禁政主脑,虽有决心,无加(应为“如”——引者)禁令既发,偶遇阻障,即以地方环境恶劣措辞,而易禁为罚。而种者并不见少,罚者自罚,种者自种,由是而养成民众视禁为罚之事实,对于禁令自然轻视。”(15)《社论:铲烟苗不罚款》,《新河南日报》1944年3月23日,第2版。应该说该社论虽出于维护伪政权统治秩序之目的,但其分析还是颇有见地的。
同样,出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在关系作战能力的军队中和涉及教化育人的学校中,伪政权较早采取了严禁烟毒政策。1942年1月,伪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通令所属,强调指出:“凡我军人,对于烈性毒品,务宜深恶痛绝……如有阳奉阴违者,一经查出,决即从严惩处。”(16)《刘绥靖主任通令所属严禁军人吸食毒品,如有阳奉阴违者查出惩处》,《新河南日报》1942年1月15日,第2版。同年3月,伪修武县公署奉伪省署训令,“特转饬各级学校,严禁教职员吸食鸦片,倘敢阳奉阴违,一经查出,定行撤职,并将该校长从严惩处不贷。”(17)《修武整顿教育,严禁教职员吸食鸦片》,《新河南日报》1942年3月12日,第2版。同年4月,伪睢县公署奉伪省署训令,要求所属“各级学校教职员,不得吸食鸦片,及其他不良嗜好,并附发誓约书及校长保结书各一份,限期汇报。”(18)《睢县公署转饬各学校教职员,严禁吸食鸦片及其他毒品,并须出具誓约书及保结书》,《新河南日报》1942年4月24日,第3版。然而,对于一般烟民,伪政权则以“禁烟禁毒”为名,通过收取烟民登记费,放任烟民购烟、抽烟。据《新河南日报》报道,伪省会警察署打着“禁烟禁毒强国强种”的旗号,通令下属机构协助伪开封禁烟分局办理烟民登记,并强调:“凡有烟瘾者,促其速向该分局登记,手续简单,不要像片,有居住证即可。登记费分为二元、四元两种,嗣后各膏店,凭证售烟,无证者即不能购烟,对于烟民诚有莫大便利。”(19)《禁烟禁毒强国强种,警署协助禁烟局办理登记》,《新河南日报》1942年4月22日,第2版。该报道真实地反映了伪政权所谓的“禁烟禁毒强国强种”是虚,而向广大烟民收取登记费是实,这实际上是在放任或鼓励烟民吸食烟毒。
二、河南沦陷区烟毒的泛滥及危害
全面抗战爆发前,根据南京国民政府的有关法令,国民党河南省当局自1935年开始,开展了颇有声势的“六年禁烟运动”。经过该运动,虽然河南省的烟毒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但“河南省的烟毒得到有效控制,政府公务人员、军官、商人不敢明目张胆贩卖烟土,一部分瘾君子戒除了毒瘾。”(20)霍佳佳:《1935至1940年河南省的禁烟运动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年,第41页。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先后沦陷,日伪当局为配合日本的侵华战略,在其控制区广泛推行毒化政策,致使包括河南沦陷区在内的整个日伪区烟毒泛滥成灾。
1941年3月,重庆政府内政部据河南等省报告,“现在各沦陷区内毒品充斥,我同胞之受害者,不计其数……就河南一省而论,豫北、豫南、豫东沦陷各县,鸦片遍地皆是。”(21)《敌在沦陷区施行毒化情形——内政部获各地报告》,《河南民国日报》1941年3月26日,第1版。另据《河南民国日报》报道:“豫省敌伪规定,彰德等八县为种烟区,总计彰德三万亩,汤阴八千亩,武安六千亩,临漳二千亩,浚县三千亩,孟县三千亩,清化三千亩,鹿邑七千亩,八县合计六万余亩。”(22)《敌伪推行毒化政策,定彰德等八县为种烟区》,《河南民国日报》1942年8月20日,第2版。该报还报道称:“豫北博爱大辛庄等地之敌,近设立‘忠河公司’(应为‘中和记公司’——引者),制造大量毒品,每袋万余颗,分运豫北、晋南等地推销,其价格视其销路而定,由每袋一万元至五万元不等。近复利用一切方法,向其他各地推销,敌寇此种毒化政策,实令人闻之发指。”(23)《豫北之敌施行毒化政策,设立公司制造毒品》,《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9月20日,第2版。据统计,该公司“每日夜出红丸(以鸦片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毒品——引者)5000袋,以武装运销于豫北及晋南各县,并流行于黄河南岸”,其每天的制毒收入“约计在5000万元”。(24)马模贞主编:《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年—194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2页。由此可见,豫北地区当时是日伪烟毒政策的重灾区,其中安阳县(日伪改称彰德县)、博爱县(日伪改称清化县)等地受害尤重。
实际上,除了豫北地区,日伪统治下的河南其他沦陷区烟毒问题也很严重。据报道,日军占领开封后,“毒品商店遍设街巷,而以红丸白面为最盛,廉价出售,企遂其毒化政策之目的”。(25)《敌在开封鱼肉居民》,《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7日,第2版。据郭宣文回忆,“开封沦陷期间,日本特务浪人公开贩卖并制造海洛因、鸦片等毒品,以毒害中国人并敛财,故当时毒品铺店比比皆是,中毒人倾家败产,成残或致死者,为常见现象。”(26)郭宣文:《日军侵占下开封见闻录》,《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3辑,第195页。据史啸岩回忆,当时开封“马道街、鼓楼街、南土街、书店街都有开灯供客的大烟馆。只卖鸦片不开灯的更多。”(27)史啸岩:《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毒赌娼》,《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3辑,第188页。豫东伪军头目张岚峰在大肆扩充军事力量的同时,也乘机大做烟土生意。“在他的所谓军管县中,强迫农民种大烟,实行征收强购办法,集中制成烟砖,派汽车用部队押运到砀山或黄口,向徐州、南京、天津、上海销售。”(28)《日伪时期我县商业的畸形原因》,管仁富、霍宪章主编:《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5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001页。太康县“地处偏僻,毒品流行甚炽”,以至于该县伪警察所的布告中也承认,“本县希图暴利,罔顾国法,贩卖海洛英者,到处林立,而面无血色、骨瘦如柴之吸食毒(品)愚民,触目皆是,殊属令人目睹心惊。”(29)《严禁人民吸贩毒品,太康县警察所布告周知》,《新河南日报》1943年9月22日,第3版。
豫中、豫西沦陷后,日伪“强迫襄城、宝丰、鲁山、叶县、舞阳、许昌、郑县等县人民种植鸦片,面积占耕地十分之三。”(30)《敌在河南强迫人民种鸦片》,《解放日报》1945年2月13日,第1版。当时在河南沦陷区,“城里烟馆林立,公开吸售。而且有一种新发明的毒品叫‘小磨’的,比红丸、白丸、海洛英等毒性更烈,一经吸食后,几个月内肺部全部溃烂。城郊各乡镇,鸦片罗列成市,敌伪并公开勒令将鸦片换牛羊布匹。”(31)《中原杂讯》,《新华日报》1944年12月8日,第2版。日军侵占嵩县后,“在县城特设立一个‘大昌号’,由日本人掌握,大批出售毒品大烟砖、松竹梅(一种毒品——引者)等,在城里关外,任意设立大烟馆,为数有十几户之多,在县城四关,代购罂粟种子,售给群众,任意种植。当时嵩县少壮之人,染上大烟瘾的真是无法统计,危害殊深,极大程度麻痹了嵩县人民抗日斗志。”(32)《日寇侵入嵩县后的血腥统治罪行》,管仁富、霍宪章主编:《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5卷(下),第942页。
日伪的烟毒政策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这里以豫北封丘和修武两县为例。日伪统治封丘期间,以派征烟籽为名,限定数量,迫令各乡缴纳,以致各乡不得不以肥沃之农田改植烟苗。据统计,全县种烟农田共681亩,每年产膏20430两。在封丘县城,日伪设立的烟毒售吸场所有15处,胁迫人民设立者计5处。与全面抗战爆发前相比,日伪统治时期该县境内种制运售吸食烟毒情形增至战前的15倍。经抗战胜利后调查,该县共有烟民669人,其中被诱逼吸食烟毒因瘾致疾而殒命者120人,家产荡尽者250家,总计所受直接经济损失为160万元(当时的法币,下同),因被迫种烟之农田所受经济损失达2043万元。(33)《河南省封丘县敌伪毒化罪行资料》、《封丘县抗战期间人民被迫吸食烟毒及种植烟苗所受损失调查表》(1946年5月31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省抗战损失调查(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7—359页。另据战后调查,日伪统治修武时期,伪县公署及特务机关令饬各村人民种植烟苗,并从天津、北平等地源源不断运来制毒原料,设立各种烟毒吸售场所81处,出品各种烟毒5.5万余两,敛收烟毒税款8.09亿元,致使当地烟民多达5500余人,造成各种经济损失80.23亿元。(34)《日伪统治修武时期毒化资料调查表》,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省抗战损失调查(一)》,第384页。
三、日伪烟毒政策下的吏治腐败
日伪的烟毒政策不仅给沦陷区一般百姓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而且影响到河南伪政权的吏治和公职人员的素质,这从伪政权的有关训令及处罚规定中可以得到证实。1941年3月,伪河南省公署发布惩戒令:“查彰德营业税征收局所属员役因公晋省私携鸦片一案,该局长王燮约束不周,失于觉察,自难卸责,着记大过一次,以示儆惩。”(35)《河南省公署训令》(1941年3月18日),伪《河南省公报》第156号,1941年3月18日。1943年1月,伪河南省公署发布训令:“案据滑县县知事林翼丰呈,以该县会计股长韩英杰吸食鸦片嗜好甚深,屡戒不悛,有误要公……应于本年元月二十日予以免职,以肃官箴,而儆效尤。”(36)《河南省公署训令》(1943年1月25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46号,1943年2月17日。类似的训令还有:1943年2月,伪杞县民政科技术员何品高因吸食鸦片予以免职(37)《河南省公署训令》(1943年2月24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50号,1943年3月17日。;同年11月,伪民权县警察所警务系长郭殿鹄因吸食毒品予以免职(38)《河南省政府训令》(1943年11月22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88、389、390合订号,1943年12月22日。;1944年2月,伪中牟县警察王占荣等因身着警服吸食鸦片受到免职等处分(39)《河南省政府训令》(1944年2月2日),伪《河南省公报》第407号,1944年2月12日。;同年3月,伪考城县警察所保安系长徐明因擅离职守、素行不检且染有吸毒嗜好予以免职(40)《河南省政府训令》(1944年3月13日),伪《河南省公报》第418、419合刊号,1944年3月19日。;同年5月,伪原武县警察所督察长朱殿春因行为不检且吸食毒品予以免职。(41)《河南省政府训令》(1944年5月9日),伪《河南省公报》第438号,1944年5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案例中竟有多位负有执法责任的警察吸食毒品,可以想见当时伪公务人员中吸毒问题之严重,这或许是伪政权在制定烟毒政策之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另据赵隐侬回忆,当时在沦陷区,“至鸦片一项,则以本地土产,敌方(指日方——引者)直接经营者颇少,不过作包庇运输而已。至国人之贩此业者,则分利于机关,多为特务队、特务科以及各县之伪县长、警务所等,其手段相类似……加以伪军政机关人员下乡者无不需索此物,以致各乡豪家均以此物为必需之应酬品,每逢大宴时有非此不欢之概。据闻敌人方面染此者也与日俱增,即身负宪兵之责者也受此毒。”(42)赵隐侬:《梁园沦陷前后》,毛德富主编:《民族记忆——中原抗战实录》第3卷,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304页。这再次印证了当时日伪政权中沾染烟毒恶习者人数之多、问题之严重。
鉴于日益严重的烟毒问题及由此导致的吏治腐败现象,1942年,伪河南省公署“以各公务人员染有吸毒嗜好者甚多,极应早日自醒自觉,期免害国害家,害自身,害民众,曾由省署通令各道县,自九月一日起,限两月内凡有嗜好公务人员一律禁绝。”(43)《豫北道公署严令公务员戒绝嗜好,逾期不戒者免职处罚》,《新河南日报》1942年9月22日,第3版。此外,“为澈底肃清本省所属公务员吸食鸦片毒品起见”,伪河南省公署于1942年10月24日,特制订并公布施行了《河南省公务员吸食鸦片毒品调验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调验本省所属公务员得设置调验所,由省公署延聘医师若干人办理之。”调验自1942年9月1日起,分劝告期间、调验期间、犹豫期间,各两个月。“经过劝告期间,即开始将本省所属公务员分批调验”;“实施调验时,须由各厅处长官或派员监视之。”“实施调验后,如该公务员确无吸食鸦片毒品或实在戒除者,由医师给予鉴定书,并着本人出具嗣后永不吸食切结。”“实施调验后,如调验该公务员尚有吸食鸦片毒品情事者,由省公署强迫送至开封禁烟分局戒烟所戒除之。”公务员查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概予免职:“一、本不吸食鸦片毒品竟学习吸食者;二、在劝告期间业已戒除又复吸食者;三、调验后戒除再吸食者。”(44)《河南省公务员吸食鸦片毒品调验暂行办法》(1942年10月24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33号,1942年11月18日。
随着伪公务人员中吸食毒品者日渐增多,日伪当局的禁绝措施也愈发严厉。1943年10月10日,伪河南省公署对各机关公务员发布训令:“凡染有烟毒嗜好者,统限十月三十一日以前一律戒绝,并责成各主管长官随时查明,如嗜好过深、戒绝无望者,应即予以撤换,不得稍涉瞻徇。倘逾期被人告发,或经本署派委调查,确有烟毒嗜好,仍未戒除者,该主管长官亦须同受严重处分。”(45)《河南省公署训令》(1943年10月10日),伪《河南省公报》第385号,1943年11月17日。同年12月6日,伪河南省公署“为认真推行、澈底实践公务人员戒绝烟毒嗜好起见”,特制定了《河南省公务员戒绝烟毒嗜好实施办法》。(46)《河南省公务员戒绝烟毒嗜好实施办法》(1943年12月6日),河南省档案馆藏,伪河南省公署档案,档号:M0010-002-00138-007。1944年6月17日,伪河南省政府又公布了《修正公务员限期戒烟办法第一条条文》,规定:“凡在政军机关服务之公务人员,均应自三十三年(即1944年——引者)三月二十九日起,限两星期内向主管长官出具切结,声明并无吸食鸦片或吸用吗啡、高根、海洛因及其他化合物等毒品情事,并须有同机关荐任以上人员三人出具保结,倘以后查有吸食烟毒情事,除本人应予撤职并依法治罪外,保证人员应连带受撤职之处分。”(47)《修正公务员限期戒烟办法第一条条文》(1944年6月17日),伪《河南省公报》第469、470、471合刊号,1944年8月22日。由此可见,当烟毒问题浸染了伪公务员队伍,威胁到日伪统治秩序的时候,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严厉禁绝措施。
然而,只要日伪的毒化政策继续推行,其烟毒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因烟毒问题而导致的吏治腐败也就不可能根治,甚至伪政权中一些高官竟然公开贩卖和吸食鸦片毒品。据史啸岩回忆:“日伪时期的伪军政组织大量的、公开的贩卖鸦片,已经不是什么鲜见之事。象(应为‘像’——引者)张岚峰、孙殿英、陈静斋等伪军政头子们用火车、卡车装运更是常事,不但公开装运,而且在大木箱上还贴有‘省公署’或‘总司令部’的封条。当时是官大则大搞,官小则小搞,钱多则大搞,钱少则小搞,或者是合作共办。送礼行贿是鸦片,消闲娱乐也是鸦片,真如水银之泻地,无孔不入。”而“伪省长陈静斋是有名的‘白面大王’,他常用专人专车贩运毒品于北京、开封之间。”(48)史啸岩:《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毒赌娼》,《河南文史资料》1993年第3辑,第186—188页。再据邢幼杰回忆:“当时日本人虽对鸦片毒品,不加禁止,但对伪职人员,限制颇严,不少伪职员,都因吸毒受到惩罚,只有陈静斋、孙思仿(曾任伪河南省公署秘书长——引者)、岳迹樵(曾任伪河南省公署建设厅厅长——引者)三人敢于公开吸食。”(49)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第85页。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像陈静斋、孙思仿、岳迹樵这样的高官都在公开吸食毒品,还怎么要求其下属切实戒烟禁毒呢?整个抗战时期,河南沦陷区烟毒肆虐、屡禁不绝,应该说与此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河南等广大沦陷区,日伪当局出于配合日本侵华战略、增加日伪财税收入的需要,大肆推行一系列烟毒政策。然而,该政策在当时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也威胁到日伪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影响到伪政权的吏治和公职人员的素质。抗战时期的历史事实说明:烟毒政策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日本侵华战争还在进行,日伪的烟毒政策就不会停止,相关烟毒问题就不可能妥善解决,其危害和影响也是难以消除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日伪在河南沦陷区的统治研究”(14BZS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