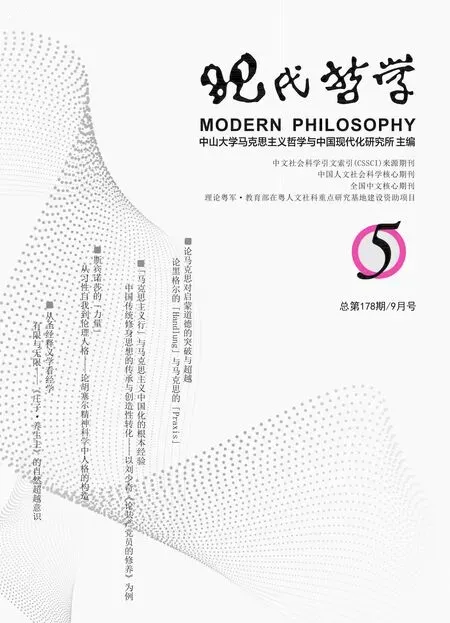有限与无限
——《庄子·养生主》的自然超越意识
朱 承
《养生主》是《庄子》内七篇中文字比较短的一篇,关于其题目和主旨的理解,历来多有分歧。有人主张,“生主”即为肉体生命之真宰,指“精神”或“性”,养“生主”即葆养精神、养性全生。如明代释德清认为,“此篇教人养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1)[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庄子〉内篇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2页。。王孝鱼采纳王夫之《庄子解》之说,提出“‘养生主’三字,意谓养生之主,而‘生主’指形神之神而言”(2)王孝鱼:《庄子内篇新解·庄子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6页。。也有人认为,此篇题应以“养生”之“主宰”为解。如郭象认为,“夫生以养存,则养生者理之极也。若养过其极,以养伤生,非养生之主也”(3)[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5页。这一条的“释文”说:“养生以此为主也。”。钟泰认为,“‘养生主’者,以养生为主也”(4)钟泰:《庄子发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张文江也提出,“庄子的‘养生’,养的是生命的‘生’,不仅养形,而且养神……‘主’,主宰,主旨”(5)张文江:《〈庄子〉内七篇析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页。。可见,关于《养生主》篇题的“题解”,历代注释者各有所重,但从这些诠注的具体表述来看,不管是“养‘生主’”还是“‘养生’主”,一般都包含有“养生全神”之义,主张通过“顺养”而达到人的自然超越。基于这样的理解,该篇提出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是“如何实现养生全神并在此基础上超越生命的有限性”。当然,这只是对《养生主》之多维理解的一种可能。在此篇中,庄子似乎在提醒人们,要想突破人生的“有涯”,就不能试图在知识上掌握世界,而应该在精神上顺应世界。在庄子看来,只有顺应天道的自然性来消解知识技能的人为性,做到安时处顺、顺任天然,才能真正的实现“葆养精神、养性全生”,通过自然而然的顺应,从而实现无限对有限的超越。
一、有涯与无涯
人生短暂,但忧思无穷,“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人的生命有限,肉身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是人们自己所不能把捉的,然而现世的人们总是意图操持着身后的事情。于是,有人强调要“三不朽”,通过立德、立言、立功,使自己的精神长存于世。如所周知,立德、立言、立功是少数精英的事情,普通人只能在自己的家族领域里延续自己的痕迹。普通人没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机会和本领,但也要追求人丁兴旺、香火不绝,通过祭祀、谱牒、庐墓等一系列方式,教育子孙慎终追远、缅怀自己,使自己的痕迹与意志长留于世。一般而言,希望超越自己肉体生命的有限性,在无限的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既代表着人的终极关怀,也是人之常情,是人们对突破生命有限性的一种本真追求。
庄子也追求无限,但他所理解的“无限”,不是对无穷世界的知识性把握或者对知识世界的没有止尽的追逐,更不是希望被人永远铭记,而是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上尽量养生全神,顺应自然,在心灵上去感知和体验无限性的超越感。庄子宣称,人的肉体生命是有限的,不能将其浪费在追逐有形世界的把握上。《庄子·养生主》说: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所谓“生有涯”就是人的肉身之有限性,而“知无涯”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及其结果,肉身有限,而世界无限。杨立华曾指出,“这里的‘知’主要是可积累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的无限性在哲学上是以世界的无限为基础的”(6)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40页。。我们认为,这里所谓的“知”除了是“知识”之外,还可以是人们对把握外部世界的心思和欲望,就是人期望把握外部有形世界获得经验知识的主观欲求,是希望认知和主宰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企图。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以有限的名言去把握无限的道,劳而无功,迷而无觉,“非所以安且久也”(7)[宋]吕惠卿撰、汤君集校:《庄子义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5页。。关于这一段,杨国荣认为,“‘有涯’意味着无法超越个体的有限性规定,个体本身有限性的规定决定了其行为方式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试图去超越这一限度”(8)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118页。。虽然世界是无限的,但个体是有限性的存在,在无限的世界面前,人必须接受其自身的有限性。关于此处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理解,崔宜明提出:
为什么有限的个体生命不能以追求无限的知识而将自身无限提升以分享无限而获得不朽的价值呢?在什么意义上,这样做反倒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迷失呢?关键在于对认识、知识的“无限性”的理解。在庄子哲学中,认识、知识的无限性并不来自于存在的无限性,存在的无限性恰恰是不可认知的。认识的无限性源自于人类认知条件的有限性,它无非是人类理性抵达认识界限时所必然呈现出的无穷类推的无限性,实质上是试图认识存在的无限性而必然导致的认识本身无意义循环的无限性,即“对待”的无限性。(9)崔宜明:《生存与智慧——庄子哲学的现代阐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73页。
按照崔宜明的看法,庄子在《养生主》篇开头所提到的“有涯”与“无涯”,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命的有限性、认知活动的无限循环性、存在的无限性。按照这一区分,我们可以认为,在庄子看来,有限的生命不足以掌握无限的存在,而认知活动的无意义之无限循环,不值得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去追逐,故而无论从存在还是认知的角度,都不应该去“以有涯随无涯”。换言之,庄子以“放弃世俗认知”的方式作为应对世界、全生养神的智慧。关于对待“知识”及“认知活动”,孔子的态度与庄子可做比较观之。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孔子强调自己无知,一方面显示了孔子伟大的谦虚,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分门别类的无穷知识和应对世界之方法的整全智慧之间,孔子选择“叩其两端而竭”的方法意义上的智慧,拥有这样的智慧,就可以在任何具体领域“物来顺应”。同样是“无知”,在孔子和庄子那里却有不同意味,孔子倾向于以整全的方法来取代碎片化的知识,希望以更明智的策略来应对世界的复杂,而庄子则选择放弃徒劳的认知活动而顺应世界,以“顺”来与世界相处。从表现来看,孔子和庄子都意图超越对于世界的具体认知,但孔子依然要把握世界为我所用,而庄子则要求顺应世界的自然性本质。从孔子和庄子对知识之态度的简单比较,大致可以看出庄子从顺应自然来体会无限的思想主张。
生命有限,但人们认知和掌控世界的心思无限,二者竟日相逐,耗神伤生,劳心悴形,于是陷人以危殆之境地。如此,有人还是要放任自己的心思愿望去追逐对于有形世界的认知,期望获得对于世界的知识性把握,迷而不觉,以至于不可救药。庄子劝说人们不可执着于对外部世界的把握与理解,不可迷信于知识领域而陷入怠妄,同样在人伦世界也无须执着于世俗的善恶。庄子认为,只要顺应自然,就是正当的,就能实现人本质上的生存诉求。《庄子·养生主》说: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在人生道路上,人的行动总要受到社会的评价与裁决,善与恶、表扬与惩罚就是这种评价与裁决。善、恶都是世间平常之事,在庄子看来,为善不要出于名利之心,为恶不要招致法律上的惩罚,因为无论是名利还是惩罚,都是人为造作而带来的后果,是因机心而非自然而成,因此对于人的全生养神多有妨碍。这里,肉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世俗的道德和法律,被庄子放在首要位置,也是其生存于世的主要目的,按照杨国荣的说法:“不是伦理和法理,而是感性生命,构成了关切的首要对象。”(10)杨国荣:《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为了养生全神,庄子要求人们忘却世俗的善恶,“缘督以为经”,即放弃人为的心思和念头,一切顺任自然,将自然而然当成法则来予以遵循。“督”是经脉,如有所谓“任督二脉”之说,传递的就是气在人体内的自然运行之义。此处的“督”是自然之理则,是人力所不得更改之“常理”,凡事任“理”而行,“顺中以为常”(11)[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上册,第117页。,将安心顺应自然之理当作“经法”,也就是当作根本原则。庄子设想,如果人们都能安心顺任天理,断绝驰求多端的念头,不让奖惩成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就可以葆养精神、养性全生、养亲尽年,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也能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进而在有限性的生命中拥有无限性的满足感。
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曰:“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人生有限而世界无穷,在庄子看来,世俗生活中“常怀千岁忧”的“忧思”与“期待”毫无意义,按此忧思,势必伤神伤生,不如忘却外在的功名、善恶,顺应自然,忘却对象世界。忘己、忘功、忘名,就像庄子提到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在庄子看来,世俗的伦理、法理都可以忽略,不能构成人们生活的依据,只有按照天理自然的安排去活动,才是“养生主”的妙道。“生之有”是有限的,而“生之主”是无限的,要超越有限之形去体悟无限之理。为了更好的说明从有限中体验无限的道理,庄子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之。
二、有限之技与无限之道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庖丁解牛”是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词语。正因“庖丁解牛”为人熟知,故而往往有多维解释,最常见的是“熟能生巧”“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之类的解读。“解牛”是日常的生活场景,从“熟能生巧”等技术层面来理解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庄子擅长在具体生活场域里阐述最本质的哲学道理,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发现自然之道,顺此之例,我们也可以继续发掘其可能的内在意涵。
“庖丁解牛”故事最关键之处不是“解牛”的技巧,而是庖丁对梁惠王阐述的“解牛之道”。梁惠王在《孟子》中曾隆重登场过,《孟子》首篇就以“梁惠王”为名,成为孟子申述其政治见解、王道理想的背景式人物。同样,梁惠王在《庄子》里再次被当作思想演示的背景人物。政治人物在先秦哲学里往往成为思想生发的背景,尤其是在庄子的文本里,其真实性大可不必刻意细究,这似乎是一种书写套路;另一个方面,这也说明了即将要表达的思想是慎重的,是在公开场合下所做的正式宣示,也是具有公共性意味的。在庄子的笔下,庖丁为梁惠王表演了一场非常细致且具有观赏意义的“解牛”表演(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可能会觉得残忍),更重要的是,他给梁惠王讲了一番道理。《庄子·养生主》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砉然响然,奏刀嚯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盍至乎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觚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诘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借庖丁之口所阐述的道理,其核心在于“道技之辩”。在庖丁的“解牛”表演活动结束后,梁惠王认为,庖丁的“解牛”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解牛技艺醇熟至极,故而发出“技盍至乎此”的由衷赞叹;而庖丁认为,“解牛”不仅仅是“技”的问题,更是合乎“道”的结果,或者说表面上看是技术熟练,实际上是合乎道之后的自然结果。换言之,庖丁的“解牛”是其“体道”以后循乎天道、物理的自然表现,合乎自然则水到渠成,已不是人力或修习技艺后的刻意而为。庖丁自述了其由技入道的历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他逐渐形成对“解牛之道”的认知,有点类似于欧阳修《卖油翁》所说的“无他,惟手熟尔”;随着经验的积累,庖丁的解牛技巧从感官认知变成心灵的默会与体认,从有形的局部熟知到无形的整体把握,也就是说不再通过能用语言来解释的技巧,而是通过心灵对于牛的整体性领会。这就是庖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体会的“解牛之道”,这种“道”不能够用语言来传递与表达。就像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庄子·天道》)。轮扁不能用语言将斫轮的技术传递给他人,甚至包括他的儿子,因为这一“技术”不能通过语言来进行精准传递,而是完全靠工匠个人在反复实践中的默会体认。一般而言,“技”可以机械地予以重复,通过语言将程序式的技巧、工作流程等清晰地描述出来,让人们按照此步骤操作即可。而“道”只能依靠个体的默会,在庖丁那里,就是靠自己长时间的摸索,体认出只有“依乎天理”才能做到“游刃有余”的“解牛之道”,以“顺”而“为”。从庖丁对其解牛历程的介绍来看,他也经历了“所见无非牛者”-“目无全牛”-“以神遇牛”等渐次变化的过程,这也符合经验积累的一般规律,“技”逐渐进乎“道”。在“技”的阶段,费神、费力、费工具;而在“道”的阶段,全神全志,保全工具,所谓“踌躇满志,游刃有余,善刀而藏”,在合乎自然之道中体会劳作之美。
“解牛”本来是一个血腥混乱的场面,而在庖丁那里变成一个艺术性的审美过程,如同在进行乐舞表演,“桑林之舞、经首之会”;“解牛”本来会损害刀具,但在庖丁的手下,刀不但没有损害反而“新发于硎”;“解牛”本来会让执行者紧张耗神,但庖丁却“踌躇满志”。这种对比体现了庖丁的不同寻常。从“养刀”到“养生”,在气氛、工具、精神都无损害的情况下,庖丁完成了本来十分费力的“解牛”工作,这对政治人物梁惠王来说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可以促使“他”思考更深入的东西。一方面,对个体养生而言,保全肉体生命也有一个“技”进乎“道”的过程,要在日常生活中总结经验,最后按照自然天理要全生养性。另一方面,由于梁惠王是政治人物,他不能只停留在“养生”,还应该将“养生”与“治国”联系起来:对于国家治理而言,保证国家健康发展也要“技”进乎“道”,从人为之治回归到自然之治,按照自然天理而行,不要将个人意志强加在治国的事务上,让国家顺自然之理而治。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效应,而是一个渐进的自然过程,即由原始状态到人治状态再到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无论是个体全神养生,还是国家治理,从“技”的维度来看都是有所局限的,只有在“道”之维度上才是整全的,才可能体验“游刃有余”(12)陈赟将“余”理解为“开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并认为“随着生命形态的转变,世俗状态下的知无涯而生有涯得以转变为生无涯而知有涯”。(参见陈赟:《论“庖丁解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的无所局限。
关于“庖丁解牛”故事所蕴含的“无限性”精神,冯契认为是人因创造性活动而获得自由:“他的德性(才能或者某种本质力量)在其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中达到自由的境界,他因‘以天合天’而感到踌躇满志,当下体验到绝对、永恒(不朽)的东西。”(13)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增订版)》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0页。顺着冯契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在“解牛”这一活动中,庖丁发挥了其自在的天赋德性,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根据对象物(牛)的自然构造予以长期的技艺探索,使其无形无限的精神意志性活动施诸于“解牛”这样有形有限的物质活动中,从而能实现对于有限的超越而体验无限。就此来说,庖丁顺应两种意义上的自然规律,一是要历经旷日持久的重复,才可能由“技”进乎“道”;二是要遵从对象物的自然构造,顺着对象的自然之理进行加工,就可能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所设计的“庖丁”这一角色在应对自然物的时候,不是去强行改变自然物的结构机理,而是在顺应自然的同时实现人化自然,终于“技进乎道”,从劳作变成艺术,从机械重复变成天道体认,从有限之“技”的养成变成无限之“道”的体验,即一种“内在的自由感”(14)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第123页。,进而在有限度的人类生产劳动中尽可能把握整全而无限的存在智慧。
质言之,庖丁解牛这则寓言试图通过“解牛”这一活动,说明人应该如何突破“应世”过程中的有限性。在人类处世、应世的过程中,所要处理的任何事都有一个“技进乎道”的过程,“技”是有限的局部性、时段性认知,而“道”是无限的整全式领会。人为的技巧虽然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毕竟是有限的。要想获得无限的整全式通透领会,还是要率性顺理,尊崇并复归自然天道,将自己的劳作与顺应天道结合起来,通过“与自然为一”中获得自由以至无限,养生如此,世事也应是如此。人应该顺应这个过程,逐渐从“有限”中突围,达到“游刃有余”的无限人生境界。
三、率性顺天而悬解
在“技进乎道”的致思中,人为的有限之“技”最终被自然的无限之“道”所融摄,人由于在生活的征程中最终顺应了自然,“以天合天”,实现了对于无限性智慧的体验。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常常是以人为的意志与行动来改变自然之天,并以此来实现人的生活目的,所谓“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然而,在庄子这里,人的意志对于“天”来说往往是多余而徒劳的,他主张“无以人灭天”(《庄子·秋水》),希望“以天合天”(《庄子·达生》),发挥人的本性顺物之自然,遵照自然自身蕴含的规律来体现“道”,即“率性顺天”,只有这样才能让人自然而然地纵浪于无限的天地大化之中,“与造物者同游”(《庄子·天下》)。为了更好地强调“率性顺天”的“以天合天”,进而超越有限以体验无限,庄子又讲了三个故事以深化之。
第一个故事关乎“人”。寻常人都四肢健全,四肢不健全往往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右师就是这样一个容易引起他人注意的“独足”之人。《庄子·养生主》说: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焉。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独足”意味着人的肉身不全,在世俗的眼光里,这样的人是残缺的“人”,为人生在世的缺憾。在一般的经验认知里,日常生活中的“独足”之人会受到很多限制,特别是行动上有着既定的有限性。然而,庄子认为,“右师”的独足是“天”使之不全,而非“人为”,乃天命所为、造化弄作,得自于性命之理,因而也是顺合天意的,只是人们不懂得这样的道理,故而以非正常的眼光看待而已。即是说,“独足”虽然有碍于日常生活,但其面貌本来如此,因此应该顺应之,不以为奇。进言之,“独足”带来的生活有限性,不足以阻挡其获得“率性顺天”的无限感。正如李振纲所言,“对于庄子而言,生命的鲜活不在于外在的形态,而在于内在的心灵自由。心灵自由是生命存在的本质,也是生命尊严的内在依据”(15)李振纲:《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5页。。形体上的缺失,既然是天之所为,就应该顺应天意,不必动摇心志以迎合流俗的评品,保持心灵的独立与自由来体现存在的意义。这与庄子“才全而德不形”(《庄子·德充符》)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天性整全、精神饱满而不为外在的形迹所干扰。虽然“右师”在形体上较之常人有所差异的,但也是顺天而非人为,因而在天德的整全性上是符合天道的,一样可以“养生全神”,即有限的形体不会影响“率性顺天”所蕴含的精神无限性。
第二个故事关乎“禽”。“禽”的习性是不受人为的约束而自在于江湖山林之中,对待飞禽走兽,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它们的自然天性让其如其所是地生活,即所谓“以鸟养养鸟”(《庄子·至乐》)。在《庄子·养生主》里,庄子提到“泽雉”养生全神之情境: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泽雉”有两种生存选择,一种是精神自由和生存艰难,一种是生存无虞而精神困顿。“泽雉”该如何选择?人又该如何评价“泽雉”的处境?按照庄子的思想,“泽稚”就应该生活在草泽中,虽然“十步一啄、百步一饮”,生存艰难,但这是其天性,“泽稚”在“率性顺天”中获得了“自适”。在草泽中自然生长,虽然获得的生存资源有限,但其精神是没有限制的,因而在庄子看来是“善”的。如果把“泽稚”关在樊笼之中,生存资源的获得可能不艰难,甚至可以获得不受限制的资源供给,但由于残生伤其本性,其自由天真就遗失了,“泽雉”也就丧失了存在的本真意义。关在樊笼里的“泽雉”,虽然看上去神态健旺,但其精神上受到桎梏而不顺应自然,因而是“不善”的。“泽雉”的两种生存处境,何者更有利于“养生全神”,更利于获得无限性的体验?庄子的答案非常明确,即顺应“泽雉”的天性,让其在自然中自在的发挥其天性。
第三个故事关乎“人伦”。日用伦常是世俗之人最关心的地方,是否按照社会认可的伦常准则来安排自己的言行,往往被当作是评价人的核心标准。比如,在儒家伦理中,丧礼、祭礼中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表现都是有所规定的,不按照这些规定来表达哀思的情绪,就会被认为是“不合礼”,而“不合礼”意味着挑战了共同体的秩序和准则,因而“不合礼”之人是要受到他人的道德批评,甚至要遭受规训与惩罚。为了展现“率性顺天”与儒家伦常的差异性,并以此来展现人在人伦事务上的精神解脱,庄子特意设计了一个丧祭之礼的场景来予以阐述。《庄子·养生主》说: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悬)解。”
老聃死了,作为朋友,秦失以“三号而出”,只是简单地表达了哀意,这在世俗之人看来显然是不合常礼的,因此受到周围人的非议。而庄子借秦失之口,讲出在人伦生活中顺天忘情的真义。在庄子看来,因为秦失知道老聃是“忘情”的真人,不能以世俗之人的情感来对待他,更不能以世俗之礼来吊唁他。与此同时,有很多人哀悼老聃,痛哭不止,如丧亲人。秦失认为,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想吊唁而吊唁、不想哭而哭,违背了天意、真情、天性,他们的哭嚎其实是一种违背天理的惩罚。通过世俗之人的“合礼”哭嚎式吊唁与秦失的“失礼”忘情式吊唁的比较,庄子凸显了忘情于世俗的超迈之意,即突破世俗的有限之“礼”而合于自然的无限之“理”。庄子主张,如果人们要真正“率性顺天”,就不要理会世俗之“礼”,而是要具有超越生死念头的“忘情”,认识到人的肉体生命虽然是有限,但不管生与死,都是在大化之中,即使肉体不再了,也只是如同老子所言“死而不亡”(《老子》三十三章),因此不必悲戚难过。一旦人们体会到“个体生命的终结并不意味着生命意义的终结”(16)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第131页。之道理,那么他们就可能超越肉体生命的局限而顺应生命状态的变化,以来去自如来对待人的生死夭寿,所谓“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那些超越了肉体生命有限性之困的人,就不再用世俗之礼来承载哀戚之情,而是进入无情、无死的无限之境,忘却生死,排除哀乐,安时处顺,安之若命。关于“顺”,宋儒张载也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17)[宋]张载撰、章锡琛点校:《正蒙·乾称》,《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63页。不同的是,张载的“顺事”是顺应伦理事务而履行人的道德责任;而庄子的“安时”则完全是要依照自然之理,连世俗之人的哀乐之情、人伦之义都要忘却,将“率性顺天”贯彻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实现解除处处受制的生存境地。所谓“悬解”,就是解除束缚。如所周知,束缚是有限性的最直接反映,而“悬解”就是要突破有限达至没有限制的境地。在庄子看来,因“有情”而接受世俗“礼法”的规约,扭曲了人的本真状态,这是人处世间所遭受的最大束缚,不利于“养生全神”;必须要做到“无情”而“安时处顺”,才能够真正解除这一最大的束缚,才是所谓“悬解”。可见,在庄子的思想里,顺应自然意义上的生死之变化,忘情忘义,顺天安命,人才能超越有限性而得到彻底的解脱。
以上三个故事,分别从人、禽、人伦事件等维度阐述了如何更好地“养生全神”,突破生存的有限而通达精神的无限,从具体的场景中展现了庄子“率性顺天”“以天合天”的思想主张。在庄子看来,“率性顺天”就是要按照人和物的本态、本性、本真去处世,庄子用人的体貌、禽的处境以及人伦交往的具体场景来说明。一般而言,无论是形体缺陷、生计艰难还是忘情背礼,在世俗眼光里都是不“好”的。但在庄子的思想世界里,只要是符合天性、顺应自然,就是“好”的。常人会认为,形体缺陷是有限的,生计艰难也是有限的,忘情背礼更表现了在人伦世界的局限。然而,庄子认为这些都来源于自然本性,是“天为”而非“人为”,因而是最恰当和本真的状态,更有利于摆脱有限性的困扰,得到最彻底的“悬解”,所谓“性得所养,而天真自全,则去来生死,了无拘碍。故至人游世,形虽同人,而性超物外,不为生死变迁者,实由得其所养耳”(18)[明]释德清撰、黄曙辉点校:《〈庄子〉内篇注》,第68页。。顺人之本性,合物之本性,才是所谓“养生全神”,也才能超脱于形体、处境乃至生死的有限之拘碍。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对于必将在世界上彻底逝去的忧思,导致世俗的人们期望通过现世的功德、思想的流述、子孙的纪念来延续自己的精神生命,超越有限的肉体生命而进入永恒的无限。庄子在《养生主》也关注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这一普遍范畴,他以“有涯”和“无涯”之矛盾作开始,以“薪尽火传”之无尽延续为结尾,展现了从有限性到无限性的智慧转换。“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人的肉体生命如同薪火,人生一世如薪燃一时,虽然有形之薪终有时尽,但无形“火”可以无限传递下去,“世间之火,自古及今,传而不绝,未尝见其尽”(19)[宋]林希逸撰、周启成校注:《〈庄子〉鬳斋口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页。。薪有尽而火无穷,个体生命有限,而宇宙大化是无限的,人通过“率性顺理”“率性顺天”就可以投入无限的天地大道之中。对人而言,超越形体、道德、生死,由个体的“技术性”存在到“合道性”存在,才是真正的“养生”。这就意味着把有限的个体融入生生不息的世界之中,也是张文江所说的“参透最后一关以见无尽之象”(20)张文江:《〈庄子〉内七篇析义》,第85页。、王博所言的“融入到宇宙大化之中,死生连成一体”(21)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8页。。“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限生命去实现个人无限的心思和欲望,是不合天道的;只有将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大化融合起来,顺应自然之天理去安排自己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无涯”,才能体验“与造物者游”的无限与自由。庄子通过“有涯”“无涯”的思想辩证和“缘督为经”的郑重宣告,通过“庖丁解牛”的故事描述,通过“独足右师”“泽稚处艰”“秦失吊老聃”的讽喻,说明真正的“养生全神”是顺应自然天道,从精神上超越人生处世的有限性,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入无限的天道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顺应自然,顺应天道,安之若素,安时处顺。这样,生命和精神能够超越有限性去体验无限,获得真正的“悬解”,也就实现了“养生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