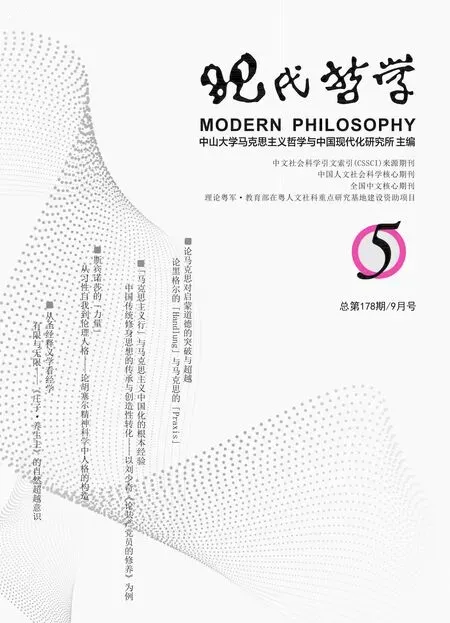互镜与融通
——从“一多关系”反思中西形而上学的特质
张丽丽
如何在比较哲学中激活和重构古典文献,是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自“西学东渐”始,学者们尝试唤醒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的生命力来回应时代问题。但由于对比较方法的选择不同,学界内部逐渐撕裂为几股力量:有的参照西方的框架建构中国哲学,有的坚持回归中国传统,有的希望藉由西方的刺激重构元典,有的运用中国智慧解决西方文明危机,有的主张积极对话。随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的日臻成熟,中西“和而不同”渐趋成为学界共识,学者们继而关注双方各自的哲学特质和话语体系。
一、中西比较的哲学困境与反思
中西相遇后“美美与共”的诉求主要来自中国哲学界,西方主流学界并未给予足够的回应。学者们曾质疑:如果西方哲学的范式像一面镜子那样照见他人,这面镜子如何照见自己?他们反对西方标准的绝对和唯一,驳斥“唯西唯是”的比较方法,强调从中国的视角反观西方。然而,西方主流学界坚信其自我批判、更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常反问“为何西方需要异质的中国思想?”在他们看来,自身理论的更迭足以解决不同时代的问题。与其花费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完全陌生的中国语言、文化和思维方式,不如专注自身的传统并发展新范式。为了弥补分歧,境外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们上下求索,在“和而不同”的共识下逐渐形成三条理论进路。
坚持“一本”的学者认为哲学有普遍的研究范式。有些学者曾将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当作普遍真理,并以此来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后来,新儒家思潮力证中西哲学“殊途同归”,即面对相同哲学问题时有各自的理论倾向。此时“一本”的内涵发生变化:从以西方哲学范式为本并用它来重构中国哲学,转变到以哲学问题为本并探讨中西各自的话语体系。学界将他们分别视为狭义和广义的“以西释中”方法。囿于两种方法都有以西方哲学为根本进行哲学研究的嫌疑,于是,学者们尝试用现代哲学理论重新阐释“一本”,使其指向生存世界本身,并力求保证其客观普遍性。森舸澜(Edward Slingerland)特别论证了如何保证主观建构的普遍有效。他指出人类在认识世界时都借助隐喻(metaphor)和象(image)的帮助,中西在认知过程中使用不同的象来把握世界及其意义,继而产生了两种概念组合模式,这两套话语体系并不影响生存世界本身的普遍有效(1)Edward Slingerland, “Metaphor and Meaning in Early China”, Dao, Vol.10(1), 2011.。然而,随着“一本”进入认知领域,普遍范式的建构便无法避免特殊因素的介入。
坚持“二本”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与历史、文化和语言紧密相关,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哲学范式。该解释传统可以追溯至葛兰言(Marcel Granet),后来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葛瑞汉(A.C. Graham)、郝大维(David Hall)、安乐哲(Roger Ames)、王蓉蓉(Robin Wang)等相继加入讨论,并揭示了中国哲学以阴阳为核心的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特质——重视对等关系、双赢共生逻辑和多元世界秩序。该解释传统有强弱两种立场:强立场认为关联性思维为中国独有,彰显中西根本的哲学范式差异;弱立场坚持该思维为中西共有,中西差异的根本在于文化和语言。这两种立场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从强立场出发,作为异质的中西思维能否理解彼此?是否会造成比较中的“自说自话”甚至对抗?从弱立场来看,双方是否会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2)Yiu-ming Fung, “On the Very Idea of Correlative Thinking”, Philosophy Compass, Vol.5(4), 2010.另外,中西哲学各自内部都有丰富多样的思想,其中不乏遥相呼应的理论主张以及互为补充的哲学旨趣。如何判定中西哲学是否存在本质差异,迄今仍无定论。
“和而不同”共识下的同异之争造成了中西比较的两难困境:坚持前者就无法避免特殊因素介入无法保证普遍的有效,坚持后者则可能陷入“自说自话”或“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一本”和“二本”的分类,意在说明中西比较中存在不同的理论倾向(同或异),并非要呈现两种互斥的立场。同异之争的价值在于试图打破西方中心主义,改变中国哲学的弱势地位,避免单边的交流模式,创建双边平等的对话机制。李晨阳、方岚生(Franklin Perkins)、陈素芬(Sor-hoon Tan)、柏啸虎(Brian Bruya)、黄勇等域外学者正在深挖此需求的潜力(3)Chenyang Li and Franklin Perkins ed., Chinese Metaphysics and Its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Brian Bruya eds., The Philosophical Challenge from China,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5.。他们在同异倾向的基础上,将哲学视为“未完成”的开放状态,专注探讨“和”的可能。以黄勇的研究为例,他分析了莫顿(Adam Morton)、斯洛特(Michael Slote)和王阳明如何回答“为何要对恶人有同感(empathy)”的问题。他指出,莫顿同感的目的在于宽恕,同感恶人作恶的外部条件继而宽恕其恶行;斯洛特的同感造成道德反对,同感主体在情感上反对其感受到的恶人的冷酷和坏心肠;王阳明的同感指向帮助,感受恶人作恶的原因并想办法帮助他不再作恶(4)Huang Yong, “Empathy with the ‘Devil’: What We Can Learn from Wang Yangming”, Moral and Intellectual Virtues in Wester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ed. by Chienkuo Mi, Michael Slote, and Ernest Sosa,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214-234.。黄勇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在于丰富了同感的范式:在宽恕、反对和帮助的基础上,同感成为感受者与被感受者共有的道德心理。以此为底本,“和”的理论倾向要求当代的比较路径应旨在以互镜的模式澄清误解、以对话的方式共谋发展、以融通的宗旨范式创新。
二、重温“一多关系”的必要
近来有学者呼吁用“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及其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价值(5)这个话题由安乐哲发起,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任博克(Brook Ziporyn)、方克涛(Chris Fraser)、王蓉蓉、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和梅勒(Hans-Georg Moeller)等从不同程度均有回应。境内新华网、光明网和人民网也都有报道,其弟子田辰山和温海明等亦撰文声援。。然而,囿于旧比较方法的影响,该呼吁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6)旧方法指广义和狭义的“以西释中”和“二本”强弱两种立场。。甚至中国哲学“一多不分”、西方哲学“一多二元”的研判常被贴上“文化本质主义”的负面标签。从普鸣(Michael Puett)对安乐哲的批评可以管窥该标签背后的逻辑。普鸣认为,安乐哲对中国古典文献做了断章取义的解读、将之放大为中西的本质差异、继而涉嫌价值高下较量(7)Michael Puett, To Become a God: 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Center, 2004, pp.17-25.。按照普鸣的说法,安乐哲用“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指称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时犯了两个错误,即将中西之间的个别差异绝对化为本质的不同,以及认为“一多不分”具有价值的优先性。如果普鸣的批评属实,那么“一多不分”的呼吁不仅无法代表中国哲学的特质,而且会削弱中国哲学的时代价值。
安乐哲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努力消除“一多不分”的负面效应。他在反驳普鸣时指出,他们二人对“本质”概念的理解完全不同:本质应该指归纳和总结某个民族具有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而不是西方传统哲学中决定物之为物的纯粹不动的属性(8)Roger T.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73.。安乐哲由此认为普鸣对自己的批评是以西方传统本质框架为依据而产生的误读。作为现代学者,安乐哲强调自己的本质概念意在用“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来概括中西既是民族又是世界的文化特征。他将关联性思维分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两种:前者指中西共有的关联逻辑;后者指中西有别的关联文化(9)David Hall and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SUNY Press, 1995, pp.138-141.。“一多关系”属于关联逻辑;“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属于关联文化。他这样区分的目的在于表明自己的立场——接受中西哲学“和而不同”的共识,反对用西方标准衡量中国哲学的同时彰显中西各自的理论特色。安乐哲通过重释本质概念,指出了普鸣批评的疏失,摆脱了西方传统意义上“文化本质主义”的标签。但是,他并未察觉到自己和普鸣对“一多不分”的不同解读亦受到比较方法的影响。他反驳普鸣时,暗示后者使用狭义“以西释中”的不合理,但他并未发现因“二本”弱立场(过于强调不同)的作用才使自己受到“文化本质主义”的质疑。
另外,安乐哲虽然通过重释本质概念驳斥了普鸣的质疑,但也因此使自己的“一多不分”面临其他难题。一方面,安乐哲提到自己的中国哲学“一多不分”是在西方哲学“一多二元”的参照下得出的结论,旨在凸显中国有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和诠释世界的模式。该提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西方“一多关系”为底本的。由于“一多问题”是古希腊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一多不分”的阐释应该与传统形而上学唇齿相依(10)参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定义,包括神(soul, spiritual, god)、本质、变化、宇宙论、同一性等讨论。。另一方面,当普鸣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概念来质疑安乐哲时,后者的回应明显受到现代语言哲学和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影响,体现了较高的反本质倾向。此时,安乐哲对“一多不分”的阐释明显又与传统形而上学背道而驰。若此,安乐哲“一多不分”似乎“自我矛盾”:既要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关又要不相关。
安乐哲可能也意识到他在传统和现代转换的过程中造成“一多不分”的解释困境,因此强调自己的“一多不分”是指中国哲学“在有感知与无感知、有生气与无生气、有生命与无生命之间并无一种最终界限。而在传统西方思想中……总是把赋予生命的‘原则’与被它赋予了生命的‘东西’设想为二元分离”(11)Roger R.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p.62.。据此推测,安乐哲呼吁关注中国哲学“一多不分”的本义应该是在中西对话中突出中国哲学的特色,勾勒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后的当代哲学样态。由于迫切想要改变单边交流的模式,他以西方熟悉的问题和语言转译了中国传统思想,同时在转译中凸显了“一多不分”的价值。这很可能是一种反格义的策略,其目的并非对中西文化作价值比较,而是尝试引起西方主流学界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和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安乐哲“一多不分”自相矛盾的问题迎刃而解。“一多不分”与希腊形而上学相关是为了突出中西面临相同的宇宙起源问题,不相关是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形上模式。但是,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比较方法的负面作用,所以在发展新儒家“一多不分”理论时无法避免广义“以西释中”带来的麻烦;在坚持中西文化有别时,由于“二本”弱立场的影响又使自己陷入“文化本质主义”的危机。即便他对普鸣的反驳在逻辑上是成立的,囿于旧比较方法的影响,他理论的核心内容(用“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及其当代价值)并没有发挥预期的积极作用。重温“一多关系”的必要就在于用当代研究进路澄清“一多不分”的形上含义,使其本义显露出来,揭示中西深层的形上关联并探索各自的理论特质。
三、感通的形而上学
当代研究进路要求在互镜与融通的视域下厘清“一多不分”概念的来龙去脉。“一多不分”最早由唐君毅提出,被视为中国人宇宙观的特质。唐君毅虽未言明“一多”是什么,但从他的论述中不难推测出以下内容:
(1)一多是数字。“一生二……三生万物”等。
(2)一是宇宙始基,多是由此衍生的万物。“万物得一以生”等。
(3)一是太极/理,多是拥有并呈现它的万物。“一物一太极”等。
(4)一是感通之道,多是感通的万物。“天下同归而殊途”等。
唐君毅引用这些内容是为了论证“中国哲学中,素不斤斤于讨论宇宙为一或多之问题。盖此问题之成立,必先待吾人将一与多视作对立之二事。而中国人则素无一多对立之论”(12)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第9页。。此处的“一多不分”有三种解释可能:中国宇宙论没有一多概念、有一多概念但无一多对立主张、有一多概念且将一多视为一体。前两种解释都需要进一步澄清:中国宇宙论应该是忽视了一多问题,但仔细研究则不难发现一多概念有迹可循。比如,理一分殊暗示了一多的对待互补关系。中国宇宙论中“一”和“多”必然一体两面、不即不离并且没有预设的宇宙秩序。唐君毅的“一多不分”虽指宇宙论的特质之一,但实则给后人留有丰富的解释空间。为了探究“一多不分”如何从宇宙论的某个特质变成中国哲学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以及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是否合理,下面将评析安乐哲等人的理论。
郝大维和安乐哲首先指出中国典籍外译时存在的问题。以天(Heaven)和帝(God)为例,在西方语境下Heaven指“超越[的]和精神的”天堂,而God指唯一的造物主;中国语境下的天没有超绝意义,而帝也不是宗教神学中的造物主。接着,他们借用维特根斯坦的“鸭兔”比喻来说明“天和Heaven”“帝和God”绝不相同,并以此为契机探讨了中西“一多关系”的差异(13)David Hall and Roger T.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p.xvi.。在他们看来,“一”在西方代表上帝或超绝的存在,“多”代表由上帝/超绝创造和支配的万物,西方“一多二分”就是指上帝/超绝与万物分属两个不同世界。据此推测,他们认为“一多”在西方的含义应该是:
(1)一是上帝,多是上帝创造的万物。
(2)一是超绝之物,多是受超绝规定的万物。
(3)一是本体世界,多是现象世界
安乐哲等人认为,天地氤氲万物一体的中国传统思想并没有预设“一高于多”的宇宙秩序,中国古人也不关心在人世之外是否存在本体世界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活泼泼地现实世界。安乐哲进一步以“心”为例来解释中国哲学的“一多不分”。他指出“心”是五脏中跳动着的感知身体和整个宇宙的“心”,而不只是西方科学意义上人体的生物器官,前者心(一)和整个身体(多)是活生生的唇齿相依,后者心身关系更像是冰冷冷的概念剖析。他继而根据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宇宙论的“一多不分”特质可以概括整个中国哲学、文化和思维的特征。
但是,安乐哲等人的论述存在几处理论隐患,迫使其给“一多不分”“既普遍又特殊”的定位不得不回到形而上学的论域中。一是,他们呈现中西差异时忽视了二者的相似之处。安乐哲十分熟悉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的有机哲学——强调宇宙是活泼泼地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但他较少提及西方的这种“一多不分”的情况。而且,当他和郝大维突出Heaven的宗教面向的时候,忽视了其精神或灵性(Spiritual)的维度。二是,安乐哲等人误将传教士翻译中国典籍时的故意曲解当作中西文化的客观差别。当利玛窦(Matteo Ricci)藉由“苍天者,抱八方,何能出于一方”质疑“帝出乎震”的合理性时,意在强调God(帝)是中西共同的造物主,否定太极、道、水和太一等中国的宇宙起源模式(14)张丽丽:《卫德明易学哲学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哲学系,2017年。。然而,当传教士将中国典籍译本带回西方,促使单数大写的God变成复数小写的gods时,又暗示他们实际上承认中国有自己的宇宙起源且该起源模式对西方产生了影响(15)Nicolas Standaert, “Don’t Mind the Gap: Sinology as an Art of In-Betweenness”, Philosophy Compass, Vol. 10(2), 2015.。只是在名称上,传教士们没有使用中国的称谓,而是沿用了神学中的God概念。这种主观曲解不该被用来佐证中西文化的客观差异。三是,他们忽视了中国“太一”的宇宙起源模式。中国古代除《周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线性创生宇宙模式外,还有以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为中心的回环复生模式,即“太一生水,水反辅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辅太一,是以成地”,“太一”能够直接创生万物,成为宇宙的开端和起点。这与普罗提诺提到“太一”是形而上学的最高本原有诸多相似之处。
显然,中西在形而上学的层面都既有“一多不分”也有“一多二元”,只是中国哲学更重视形而上学“一多不分”的一面,即安乐哲提到的“无最终界限”的理论倾向。根据经典文本的记载,这种形而上学倾向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以气为中心的“通而为一”。它强调宇宙是天地氤氲的混沌状态,万物的生化都是气作用的结果。例如,《淮南子·俶真训》中记载了宇宙的气生模式:“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万物生于气又复归于气,气的聚散主宰着万物的生死存亡。由于气无形无状无成无毁,整个宇宙遂可以被视为“一气”,也就是《庄子》所说的“通天下一气耳”。二是以心为中心的“感而为一”。它突出人的意识(心)和道德行为均是在宇宙活动的过程中产生,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宇宙的心生模式靠“感而遂通”实现,包括感乎心而成乎形的受感而生、怀天心并感于内的施感而生、尽心知性和继善成性的交感而生、人副天数天人合德的类感而生(16)李巍:《早期中国的感应思维》,《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心生的宗旨是以至诚来“通天下之志”,体现的是“吾心即宇宙”的万物一体思想。三是以虚空为中心的“一切即一”。它强调万事万物都应该是“天籁”式的“虚以待物”模式,突出中国宇宙起源的“无”的特征。而且还挖掘了佛教“诸法自性空”的“无我”思想,强调“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的形上价值。与前两种构建“一体”模式来消解物我、彼此和是非的界限不同,以虚空为起源的宇宙观彻底打破了万事万物的界限。一切和一在“常驻不灭”中实现了“一切法空如实相”。
概言之,安乐哲“一多不分”应该是强调气生、心生和虚空生相互圆融的宇宙生成模式,突出中国侧重建构“无最终界限”的形而上学特质。在互镜的视域下,以“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应该意在强调中国哲学侧重建构“感通的形而上学”。
四、超越的形而上学
澄清中国“一多不分”的形上含义及中西均存在“不分”和“二元”的深层形上关联后,重新审视并探索西方哲学“一多二元”的理论内涵成为题中之意。自巴门尼德用“一即一切”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流变说之后,西方哲学家们致力于形而上学“一高于多”的理论建构(17)Gail Fine, On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这种理论预设可以回溯至柏拉图,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之所以会被视为柏拉图的注脚,正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或反对)都与以“一多关系”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发生关联。以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为例,其议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研究应该就发端于柏拉图的“理念”思想。若此,理解柏拉图的“理念论”便等于帮助我们理解了西方哲学“一多二元”在形而上学论域内的理论侧重。
“理念”通常被学界认为是超越于现象世界的本体世界,是复杂多变背后的永恒,是超绝完满的实体。在古希腊探讨“为何一切是一”的背景下,柏拉图也要处理“理念”和“一”之间的关系。与巴门尼德直接陈述“存在是一”的规定不同,柏拉图认为“无论一存在或不存在,其他事物存在或不存在,它们都以所有事物的方式和样式,对它们本身或在它们之间,显得既存在又不存在”(18)[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06页。。这段话暗示作为一切的“一”既是“一”也是“多”,既“存在”又“不存在”。但是,具有杂多性的“一”不能作为超越世界的终极本原。柏拉图这里提到的“一”,指的并不是圆满的且具有优先地位的终极本原,而应该是整个“理念世界”(19)祝莉萍:《柏拉图的理念论与数论关系新释》,《哲学研究》2015年第1期。。这个推论的依据是,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假“理念的朋友”之口,提出了理念之上的“通种论”。他认为“是者”“静止”“运动”“同一”“差异”是比理念更深层的、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解释原则。
但是,理念论和通种论还是没有回答古希腊“为何一是一切”的问题。柏拉图在晚期的思考中重新修正了理念论,并且提出“理念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善的理念”是“最高层次的理念”,是自洽完满的“一”。善并“不像其他的学科部门一样可以进行表达”(20)[英]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8页。,它总是以“不在场”的方式“在场”,是优先的不可见的存在。那么,这种“超理念”的“善”如何同其他杂多的“理念”发生关联呢?“善”作为始基和超验的优先存在,如何保证其作为“一”的完满性呢?虽然“善的理念”出现在《国家篇》,但该篇并未给出“善”的定义,它预设了“善”是绝对的完满的“一”,但并未说明“善”如何成为理念和通种之上的更为超越的存在。即便如此,柏拉图理念世界的雏形也已经被勾勒出来,它内部显然包括了层级的次序,由低到高的排列应该是“理念-通种-善”。但是,在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中,该等级排列背后的内在逻辑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这才导致理念既是“一”也是“多”的情况发生。
那么,为何“善”作为理念的理念可以从众多其他的理念中脱颖而出?这显然涉及到柏拉图希冀将伦理学作为哲学的最终出路,也为后来康德和黑格尔等人“主体的形而上学”翻转提供基础。由于此处探讨的是“一多关系”的问题,因此上面的问题可以转化为:“一”如何成为支配且超越“多”的终极存在?这就等于是在形而上学的理念世界内部来探讨“善”(一)是如何与其他的理念(多)发生关联。为了更好地呈现柏拉图对该问题的思考,澄清其哲学中的“一多关系”,下面将引用其“未成文学说”的原话来加以辅助分析:
柏拉图……认为定义不能针对那些可以感觉的东西,而是只能给另一类东西下定义,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感觉到的东西是变化不定,不能有共同的界限。他把这另外一类东西称为“理念”,说它在可以感觉的东西之外,可以感觉到的东西都是按照它来称呼的;因为众多事物之所以与它同名都是由于分有了它……在可以感觉的东西和理念之间还有“数学事物”,是中间性的东西:数学事物与可感觉到的东西的区别在于它的永久和不动,与理念的不同在于它有很多相似的,而理念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唯一的。既然理念是其他事物的原因,他认为理念的元素就是一切事物的元素。作为质料,“大和小”是本原;作为本体,一是本原;因为由“大和小”,通过分有一,就产生出各种数来。(21)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98页。
这段话在很多方面与“对话录”遥相呼应:理念超越了可感世界,成为知识的对象而非感觉的对象,因此,理念成为超越于可感世界之外的整体的“一”。虽然“理念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唯一的”支持这样的猜测和分析,但有人可能会提出“分有”的概念是不是暗示了理念的整全性的可能呢?若理念是一切事物的共相,事物作为个体是否分有了理念中的殊相呢?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分有”和“摹仿”几乎表达同样的含义,柏拉图使用“分有”只是为了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摹仿了数”加以区分。在他看来,理念高于“数学事物”,理念的哲学任务是在数学之上提供终极的存在依据。若此,理念世界内部的层级性仍然服务于解决理念既是一又是多的问题。
同时,这段话的某些方面与柏拉图早期的思想又有不同:早期学说中强调善是本原的时候,可以将之看作是一元本体论;而在上述“未成文学说”的引文中,“大和小”与“一”都是本原,这显然是二元本体论(22)学界对于一元论和二元论亦争论不休,盖瑟尔、芬德莱、福格尔等强调“一”是最高本原,而魏伯特、克雷默和雷亚利强调两个本原。(参见先刚:《柏拉图的本原学说:基于未成文学说和对话录的研究》,第113—116页。)。那么,这是不是预示了“理念论的柏拉图”和“数论的柏拉图”在自身思想内部决裂了呢?数论的提出旨在解决理念中“一”和“多”之间的矛盾:绝对的“一”并不能作为多样性的起源,它需要“大和小”来规定“多”。辛普里丘将之进一步抽象为倍与半的关系,他认为事物的多样性均可以通过倍来增大和半来缩小两个环节实现(23)同上,第100—101页。。即便如此,柏拉图“一元论”和“二元论”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先刚提出,将“一”与“大和小”看作是最终的本原,将“一”称为最高本原;他认为一多关系不是数的关系,而是确定与不确定及同一与差异的关系(24)同上,第115—117页。。先刚结论的可取之处在于看到了形而上学内部所包含的一多的层级结构,但他忽视了作为“理念的理念”的善的价值。善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的本原,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价值的规定。
讨论至此,柏拉图以理念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架构已经完成。它并非人们所预设的“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的二元隔绝,而是在“可感世界—理念世界—通种—数(一和不定的二)—善”的五维结构中建立起来。在柏拉图那里,“一多”的含义包括:
(1)一是善,多是可感世界、理念世界、通种和数
(2)一是绝对的一,多是不定的二
(3)一是理念世界,多是可感世界
(4)一是理念,多也是理念
对柏拉图思想的回顾,印证了上文提到的中西的形而上学均存在“不分”和“二元”的情况。但是,柏拉图的理论始终维护其“一高于多”的预设,总是给宇宙以前在的规定,使其按照既定的秩序来发展。这种宇宙秩序影响了后来的宗教神学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建构。安乐哲“一是神、造物主和超绝存在”的认识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为根据的,在不断向上追溯宇宙起源的过程中,当时的学者将God(全知全能全善)作为终极的造物主。在互镜的视域下,以“一多二元”阐释西方哲学既普遍又特殊的特征应该意在强调西方倾向发展“超越的形而上学”。
通过互镜的方式,“一多不分”和“一多二元”的文化本质误会得到澄清。中西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都存在“不分”和“二元”的情况。只是西方始终有“一高于多”的宇宙秩序预设,并孜孜以求地寻找维护该假设的超越哲学范式。相较之下,中国哲学中宇宙的起源不仅有自然自发的模式,还有空无的模式;并且以气生、心生和虚空生为核心的相融宇宙发生模式建构了感通哲学范式。“和而不同”共识下的三种理论侧重,就其本质来讲都是在探索中西对话的可能,只是因为比较方法使用的不同,造成中西比较中的某些哲学困境。采用当代互镜与融通的研究方法后,中西各自的哲学特色得以呈现。而且,从学者们不同的理论建构来看,中西有诸多的对话的可能。无论是上文提到的有机宇宙论、“太一”思想、同感问题、一多问题,还是后来具体谈及的道德心理学、宇宙生生模式,中西哲学显然能够并且应该走“相互丰富”的比较路线。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理念”论的最高指向是“善”,这向形而上学与道德结合敞开大门,同时也与中国哲学宇宙的“心生”模式相契合,特别是与继善成性和天人合德的交感和类感有诸多共鸣。概言之,在形而上学的论域内,中国哲学“一多不分”与西方哲学“一多二元”难分伯仲,特别是以“和”为旨归的形上新范式建构中二者同等重要。当代的比较进路的价值是:在异同的分辨中或许可以开启“心灵”和“道德”融通的可能范式。这恰恰是用“一多不分”阐释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所在——为中国哲学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哲学建设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