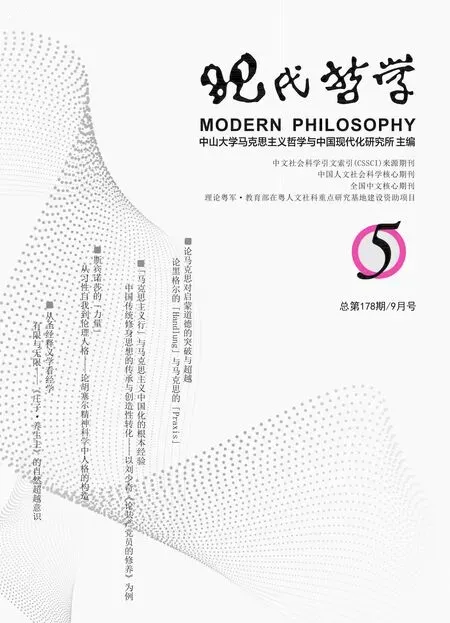形上宇宙论架构如何安放道德主体的自觉心?
——周濂溪思想解析
黄 琳
周敦颐(1017-1073,世称濂溪先生),其思想博大精深,上接《易传》,旁取战国秦汉间新儒家阴阳五行说影响,特重宇宙论思想的构建,并以“诚”作为扣合人生界“心性观”与宇宙界“天道观”的纽带。但人生界与宇宙界、心性论与天道观本非一系统,以宇宙论统合人生论、天道观统摄心性论的自由与必然之间,势必阻障重重。天道之“诚”是“本然”的必然之理,但在人之发心动念的“心动处”,又可能不依此理。心之动若依本然之理,即依循自由自律道德理性、自觉心实现价值,但是,“心”之“动”并非必然依理,故有“善-恶”两极的出现,此为“几善恶”,但“几善恶”的“善-恶”义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善-恶”义不合,后者乃就阴阳之气中见出五行之性。此性受禀于气,因气成性,非“因性而气”内蕴的道德本体当身。
朱熹以后,濂、洛、关、闽成为正统新儒家代表,被后世儒者宗崇,对宋明理学影响深远。周濂溪的思想体系,试图综括宇宙界与人生界、宇宙论与心性论。但是,当由形而上学宇宙观进入人生界中的心性论,不可避免会遭遇统而难融、融而未消的理论困境。若逆溯其流,濂溪思想与先秦儒、道之间,诸多关键性问题仍分寸不明,这些对后世儒学都产生了方向性的引导作用,待为辨析。新儒学理论在朱熹手中完成一大综合,在此综合的系统中,濂溪之学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濂溪思想也有一综合,既博大精深,又丰富芜杂,融汇了从战国秦汉间新儒家的宇宙论与魏晋玄学“因气成性”的思想特征,混同宇宙论、才性论与心性论,因此虽然谈心论性,但“因气成性”“以气为性”的气质气禀之性,终非一自由自律的道德主体与具客观性的道德实体,道德形上系统应以先天超验的客观实有为本体。
一、“因气成性”下的性与善恶
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参照孟子的道德思想,反思西方道德理论时指出,“善”本非一个由外部强加于人之上的常规,那样静涵静摄的形而上“至善”本体由上而下、超验横摄地制约着人类的天性,甚至有窒息人之情意欲念、气质气禀的危险;本体论的道德“至善”内含于人的本体自性,作为内在道德发展的起点,它内在而又超越,进而指向无限的超越界,从而使人的道德本性得以真正的发挥(1)[法]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2002年,第166—167页。。如果不能由内而外、自由自律地开出道德主体的自觉心与本体自性,那么就没有道德自由与道德选择的真正内涵,无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善恶,这也是康德道德价值理念的核心。但是,与之相对的形上宇宙论、自然界,属于因果逻辑必然律之下的独断与决定论范畴,万事万物存有的规律、性质、关系已被决定,在此哲学形态的建构之下,无从透显道德主体自由自律的自觉心与本体自性的自由选择与义务承担。人与万物皆有形上规律决定为何是如此之存在,人得何种“气”、具有何种性情与能力,都只由外在实然的形上本体决定,在此之下,内在主体的自由意志未能得以充分的展露。
在阴阳五行观的宇宙论下,人因五气配合的不同,既统具“太极之理”“共通之理”,又分有人与万物、人与人彼此之间存在差异的“殊异之理”,人由禀受之气的相异而具有“昏明厚薄”的殊异之别。无论先天“共通”的道德理性之自觉心,还是“殊异”的气质禀赋,均属统宗严密、由上至下的决定论范畴,此种空间概念化的超验横摄架构,无从透显主体自觉心、心体、性体的自由自律,并主动、奋争于其中。周濂溪《太极图说》曰: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2)[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8页。
濂溪以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构成一空间化的宇宙发生序列,又云“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可见,濂溪之所谓“性”乃强调万物的“殊异之性”与“各具之理”。万有共具的原理即无极、太极,阴阳条贯下的五行之性是“殊别之性”与“各具之理”。此性乃万物各具的不齐之性,属于具体的气质禀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加入男女,将乾坤与阴阳具体化并条贯化,化生万物,生生不已,变化无穷,遂可推至万物的化生变化,构建出一幅宇宙论下万物创生的生生不息图景。在濂溪的思想架构中,无极、太极属于宇宙论的形上本体层,由二气交感,阴阳乾坤、五行之性进入化生万物的形而下现象层。五行之性乃阴阳之气下“因气成性”所成,道德主体实然的本体之性,心体、性体之自觉心的自由自律似不突出。
《太极图》综括宇宙与人生,濂溪试图连接宇宙界与人生界,统贯天道观与人性论双重成分的形上理论体系。但是,当由宇宙界进入人生界时,难以避免统而难融、融而不消的理论困境。这种悖论、困局明白地显露在对《太极图说》“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与《通书·师第七》中关于“善恶”与“中”的理解上。
或问曰:“曷为天下善?”曰:“师。”曰:“何谓也?”曰:“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不达。”曰:“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3)[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20页。
濂溪以“刚柔”“善恶”论“性”,皆是“以气为性”“因气成性”的才性或气质之性,当落在具体的生命体上,呈现出不同的个性气质,没有明显呈露形上心性论的思想。劳思光对周濂溪此语颇为诟病,认为“刚柔”属才性、“善恶”属价值系统,故“中”与“刚柔”“善恶”的关系混乱,“中”何以成为仁义礼智信“至善”道德的最高标准?彼此关系殊不严明(4)劳思光认为,濂溪所举的“中”“刚柔”“善恶”观念,常识上似不难解,但稍加辨析,处处难通,显示其理论的混乱难明。(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8—89页。)。朱熹认为,刚柔固阴阳之气条贯下的一大分,在刚柔中,又以善恶为阴阳条贯下的细分,所以濂溪此处并非用一伦理道德层面的“善恶”义理解此语。
在“因气成性”的架构下,“刚柔”乃高一层级的阴阳,“善恶”乃“刚柔”下一层级的阴阳条贯,可以清浊、薄厚,甚至强弱替代之。所以,此处的“善恶”并非一具客观性的道德本体当身,不属于道德价值论系统,朱熹的“恶者故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正得此意(5)[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20页。。以“刚柔”“善恶”论“性”,是“以气为性”的“气质-才性”之性,又结合阴阳五行宇宙论下的条贯,“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一语,即应在此宇宙论架构之下理解。文中还偶有“善人-恶人”的分别,皆是惯常习语,而非哲学范畴伦理道德层面的论述。因此,劳思光认为,濂溪对哲学概念范畴的界定不甚严密,“大抵周氏所说之‘善恶’,只有常识意义”,即使朱熹强为之说,亦无补于事(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第89页。。
事实上,周濂溪偶一提及的善恶与心、性概念,尚不足以构建系统的心性论。濂溪的“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就“因气成性”又杂糅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五行之性立说,而被后来张载、程子称之为“气质之性”。综合《通书》文本,濂溪纵然谈“心”论“性”,但并非一具客观性的道德本体、自觉心或自觉意志。不具一普遍意义的本体自性,而只是化气为性、因气成性的才性或气质之性,亦即个别生命在具体存在时呈现出的殊别义。天道观属外在的统摄、拘定并限制义,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本体自性之自觉心是一自作主宰的道德本体,一者属必然,一者属自由,二者之间断然难融。又因濂溪的关注点本不在普遍意义的道德心体,仅就《通书》文本中关于“心”的寥寥论述,尚未“开显-呈露”出心性论中主体性的本体论观念。
因气成性、以气为性,贯注于人,即是人的气质之性,非人所能决定,心性观与天道观本身即具有张力,濂溪论“性”,既放在宇宙论架构中推衍,又将人生论直截嵌入宇宙论系统,其理论困阻,实难消融。
二、“中”的未定项与对经典儒家的偏离
周濂溪之论“善恶”,明显有别于孟子的“性善”,抑或荀子“性恶”在道德本体论视域下的“善恶”观,而只是“因气成性”的气质气禀,配以阴阳五行的宇宙论观念,在“五行之性”下细分阴阳,生出的关于清浊、厚薄的程度区分。在濂溪空间概念化的宇宙生成论架构中,“无极”居于理念层级(Idea Hierarchy)的第一层级,化生万物的“太极”居于第二级,依次为阴阳、四时顺布与五行之五性。阴阳与五行之性皆兼备体用,“理”属形上层面,“气”属形下的现象层面,在以气为性、阴阳之气贯注五行之性的过程中,“五性感动,而善恶分”,即处在由此“五行之性”的气性之下再细分阴阳的层级发用处。在先秦儒家理路中,“仁”之至善本体,出现在道德理念“仁、义、礼、智、信”的第一层级。而在濂溪的理论系统中,“善恶”竟落在气性之下。
周濂溪所谓的“善恶”,是在五行之五性化生万物的流行之“几”下呈露的。“善-恶”之“几”,亦即五行之五性在受外界境域的感发触动时呈露的端倪。即心即情而发的端倪,在这一点上,“几”颇类于孟子“四端”之“端”,即发端、端绪。“几”与“端”皆当受到外界环境的触发,双向感通性与情的过程。但是,濂溪与孟子思想中“性”内涵不同,“五性感动而善恶分”,濂溪思想中的“性”兼统善恶,性有善恶二元,犹如天有阴阳二元。“善”并非价值论意义上与“恶”相对的“至善”本体,而以是否得境域之中才性的中正偏倚作为区分。既非一“定然”价值论判断体系中的善恶,而是性情在具体境域之中过与不及的未定项,濂溪必然会强调“中”的重要地位。
“中”(去声)即中时中节之和,即在具体的境域情境中的无过无不及。在此架构下,善恶仅是一具常识义的“中节-不中节”与“无过-无不及”的未定项,而非道德本体论中一定然的“至善”本体。“中”是在灵活圆转境域之中的无过无不及,知人论世皆应中时中节,而善与恶却皆有可能过与不及。孟子思想中道德理性的本体自性,“仁体-心体-性体”所“透显-呈露”出的仁善之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即心即情即性,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系统下呈露出来、可分作清浊、厚薄、强弱、善恶之阴阳两端的气性几微,根本不同。
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论架构下,“善”乃中节之和,“恶”乃过与不及,“善”“恶”皆成一具体境域中“或然-可然-应然”的未定项,本身缺失一具客观性、实体性的“定然-实然-必然”的价值本体。既是“因气为性”的气性流行,五行之性下细分的阴阳条贯,故可以同为表示程度之偏向的未定项清浊、薄厚的描述语代替,与道德本体论下的是非价值分判不同。《通书》将刚柔细分为刚善、刚恶、柔善、柔恶,正是才性之下细分阴阳,糅合才性论与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体现,与孔孟思想以“至善”之“仁”为最高道德理想,迥然相异。
《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7)[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页。喜、怒、哀、乐皆情,其未发之“几”,端合于性,“无所偏倚”谓之“中”;情得性之正,无所乖戾谓之“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大本”乃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亦即“道之体”,《中庸》“致中和”实有“守道不失”与“无少偏倚”的两层含义。濂溪曰:“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8)[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20页。天命之性是为“大本”,情既要合于天命之性、天下之理,又要在流行之中无所乖戾,中(去声)时中节,得中(平声)之合宜,得境域之中的情之正。
既缺失价值论意义上的善恶,濂溪此处的“善恶”与“中”都既非道德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亦非一实然范畴,仅是对气质之性是否合宜之“中”(平声)并“中(去声)时中节”的描述与衡量,而非在价值评判标准下是否达成一定然目标的衡量。在阴阳五行系统之下,天为大宇宙,人为小宇宙,天人之间处于不断的禀赋、感应与决定关系。在“因气为性”的决定论、必然律系统下,阴阳之气决定气性兼两端,由气之驳杂、组合、结聚决定气性的清浊、薄厚,不同的聚合造就了“气性-才性”的善恶、清浊、智愚、才与不才。《太极图说》的形上宇宙生成论,实即一静涵静摄、空间概念化的观念形而上学独断论,由此难以生出道德主体自由自律自觉心的价值判断系统。
孟子思想是典型的心性论,其“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的志气之辨直指人心(《孟子·公孙丑上》)。老子认为万有皆法自然,“道”乃万事万物绵延俱进中时隐时没的脉络、筋骨,以去欲、归根,复归万物本体自性为关节,虽以“静”为枢纽,但在绵延流动中直观的直观形而上学,区别于空间化的观念形而上学哲学形态。与孔孟的心性论不同,濂溪之论价值又强调“无”与“静”,似近道家学说,但根本乃承《易经》而来。在《图说》中,“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此五行、阴阳、太极、无极的空间化顺布,显然有其逻辑时间上的先后之分,故“无极而太极”的“而”是逻辑时间的递进与先后。濂溪将本体称之为“无极”,代表形而上的超验统摄与静涵静摄,“太极”乃“本体”化生万物的拓展义,生生不息的创生创化之义。
总之,《通书》论“性”兼统善恶阴阳,善恶仅五行之性下一层级的阴阳两端,用以描述“五行之性”的气质禀赋是否中正不偏。“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9)[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6页。“圣人之道,仁义中正而已矣。”(10)同上,第19页。《易传》以“中”“正”定爻之吉凶,本是爻辞所依循的基本原则,以“中正”作为价值标准,非具体的德性条目,与孟子道德本体的“性善”与“四端”哲学形态不合。中(去声)时中节之和,即得境域之中五行之性之正,而或然未定项缺失一定然的本体性标准。
三、性体之“诚无”
《中庸》以“本性的实现”为“诚”的根本义,以“尽其性”为“诚”,因现实中的人不必然能实现其本体自性,此即“不诚”,亦即“非善”。凡存在之物皆有其本性,本性的实现即“尽性”,亦即客观性价值实体的“开显”与“呈露”,人若能在现实中实现本性,即可与天地参。“诚”有两义:其一,日常语言的诚实不欺,泛指充足的实现义;其二,与成性之说不可分,“诚”意谓意志的圆满与纯粹,充分实现客观性的道体,与道德本体自性的成就与实现密不可分。而周濂溪“诚”的内涵与之不尽相同。
《通书》首句言“诚”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11)同上,第13页。,又曰“圣,诚而已矣”“诚,五常之本,百姓之源也”(12)同上,第15页。。朱熹注曰:“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属,万物之象也。实理全,则五常不亏,而百行修矣。”(13)同上,第15页。濂溪以为,“诚”即实理之全,以“诚”作为人生界的“太极”“乾元”,对“诚”之重要性的描述无以复加。但是,濂溪之所谓“性”并非客观性的道德本体,而是“因气成性”“以气为性”的气性与才性,故其展露“诚”的工夫势必与《中庸》不同。《中庸》的“诚”乃“乾之健德”,积极努力求实现之意,“至诚”本是一精诚通神的纯粹状态;《中庸》言“诚”指此不息不已的变化而言,“诚”既是求实现、求符合的境界描述语,又是具体实现的工夫过程。
《通书》又曰:“诚,无为;几,善恶。”(14)同上,第16页。以“诚”释本体,又以“无为”释“诚”,亦即以无为释本体。濂溪先将“充足实现意”的境界描述得无以复加,后又将其归于一不具客观性的境界虚体。先设一“诚”的本体在变化之前,但“诚”只是一描述性的用辞,势必应有现象与物自身的符合内蕴其中。以“无”释“诚”的“诚无为”,更止于一形上之理的境界义,既云“诚,无为;几,善恶”,又曰“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15)同上,第17页。。以“寂然不动”与“无为”训“诚”,将“诚”归之于“静”。钱穆认为,“诚”无为亦无欲,绝非《孟子》《中庸》中之性,颇类于释氏所谓“涅槃性体”(16)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依孔孟下学上达,扩充四端的价值观与工夫论,处处皆强调道德本体自觉心的开显、呈露、升进并扩充,无处安顿一无为的“无”观念(1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第109页。。
但是,周濂溪天道宇宙观中的形上规律,也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不完全相应。先秦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意蕴并不止于一纯粹的虚无之境,道家将自我本性、自然之质与气融于自然生命之中,就自然生命的原始浑朴以言性,实则已将客观化的本体之性沉潜、深运其中。老子的工夫看似在虚壹而静的心上作,实则是在深潜于下的道德自性、自觉心与自然之质上用力。道家对性的态度是在养不在治,“清心、静心、虚心、一心保养原始浑朴之性而不令其发散,此即所谓养生也。养生即养性”(18)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21页。。故经典道家在心上用功,在性上收获。若就心言性,忘却了心的本体是本体自性的自觉心,一味地求虚明虚静之心,舍本逐末,既无心之可能的超越根据——天命之性,亦渐失先天本体与先天工夫。因此,牟宗三指出,惟作浮在表面、清澈见底的后天工夫,遂无从安放道德本性,这便成为道家系统偏离客观性体后思想的严重缺陷(19)同上,第21页。。流弊虽若此,但老子本非如此。
在濂溪的思想架构中,是否存在相类的问题?濂溪提出“几”与“慎动”的观念。无论是“诚”抑或“几”,本应最终落实在“心性”之上。之后宋明儒者论工夫,都强调要落实在发心动念的“几”处。“几”乃“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乃心上的一个动势,心动念发,“几”是尚未形诸事为的“势”,本是《易传》中诸事的吉凶之兆,此处皆指动静、体用之间,“几”类似于孟子的“端”,但其发诸于外的内涵迥然相异。若将濂溪思想架构理解为以道家的无欲与虚明静观会通儒家圣人的仁义中正,又会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仁义乃兼备体用的客观道德实体,中正乃一描述与衡量语,将道德的客观标准“仁义”与一境域之中求中时中节、合宜合度的“中正”合而为一,殊为可怪;其二,若理解为圣人之道是儒家的,实现的方法是道家的,势必糅而难融。
在濂溪思想架构中,因缺乏对客观性道德实体的认知,故没有真实的心性论内涵。若将“诚无为,几善恶”从《通书》全体中抽出,单独将“善恶”作为道德价值论本体理解,那么,“诚”与“几”本身在事实上已然预设了心、性、情的存在,或许濂溪未及展开。即便如此,“几善恶”的“善恶”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的“善恶”内涵又不同,濂溪在其理论架构内实预设了至少两种不同的关于善恶概念的内涵。
濂溪关注宇宙生成、化生全体,而价值论意义的“善恶”并“诚”与“几”,必在心、性、情的心性论框架下顿现。如果假设濂溪思想中含有基本的道德价值理论,需先设定一“本然之理”,此理可以是仁、义、礼、智“至善”的实体之理,预设一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明觉心体的自觉心、道德心,情、意、欲、念、物、事之道德实践、践履若依本然之理而动即得正与和,成就道德本体的“善”与“诚”,心若不依理,即反道德而为“恶”。但是,这些究竟是强为之说,还是濂溪思想并未明白呈露的内蕴架构,以《太极图说》和《通书》为据,尚晦暗难明。
四、结语:“因性而气”与“因气而性”
形而上的“天道观”与“宇宙论”,可谓一静涵静摄、超验横摄的统摄、决定与独断系统,强制形而下的情、意、物、事实现的空间概念化的哲学形态。阴阳五行宇宙论的独断与自由自律的道德理性、心体、性体之自觉心,类似于宇宙自然界的必然律与道德人生界的自由律悖论。心性论强调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亦即道德主体的自觉心与原动力。但是,内在客观性的道德实体尚未呈露,自由自律的主体性价值又如何成为可能?周濂溪思想虽博大精深,但体大难包,人性论中的价值判断问题较之宇宙论中自然世界的决定与独断复杂得多,《太极图》与《通书》中,人生界与宇宙界间的关联并未明确交代。
“至诚”本应是主体贯注本体之理时的态度,其本身并非固具的客观本然之理。“诚”即依此理,“不诚”即不依此理,“诚”本不应作为“本体之性”与“本然之理”当身,而只是贯注、贯彻“理”的“至诚”状态,故必有主客体相扣合的意蕴内涵其中。天道之“诚”是本然之理,但在“心动处”又可能不依于理,故道德价值论的善恶问题全在此“动”之“几”处说。心之动,若依其本然之理则实现道德价值,若不依理即有“善-恶”两极的出现,此应为“几善恶”的本意。若如此,“善恶”之意又与“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中的“善恶”不合,后者乃就阴阳之气中见出五行之性,此性受禀于气,“因气成性”,非“因性而气”所内蕴的道德本体。
“因性而气”与“因气而性”实属两类不同的理论进路。“因气而性”乃顺“生之谓性”的“气性”一路开出,上接告子、荀子与董仲舒,下开《人物志》气质气禀之“才性”。气性之性,是在气的聚散、组合中因禀受之气的驳杂、厚薄、清浊而成就的不同的“材质之性”与“气质之性”,亦即王充“用气为性”“性成命定”的“先验决定论”。顺气以言性,是将“性”委于“气”之下,故在“以气为性”并阴阳五行宇宙论的体系之下,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之性,阴阳之气乃第三层级,五行之性更居其后。性由阴阳之气聚合而成的气之初禀,亦即赋予万事万物的气质气禀之性,与先秦儒家之处在理念层级首位的道德本体之性不同。“因气而性”的理路,性因气禀赋之命定,属于宇宙自然界之先天、超越的必然性。一者为道德理性自由自律的自觉意志,一者为先验命定必然律的决定论,二者是不同的理论进路。
阴阳之气贯于气禀之性的“五行之性”而有的善恶之分,通清浊、智愚,此即气质、气禀、才性的具体化与现实化。这是在阴阳五行的宇宙论架构下,由天地间一气之驳杂、组合、汇聚而展露的丰富现实变化。其所谓“善恶”,实即清浊与薄厚意,在此理路的未定性下,惟具“气质-气禀-才性”合宜合度的倾向,展露因时因地的或然之善,在此境域下为合宜、彼境域下则未必合宜的或然未定项,而非一定然的客观性价值本体的“善本身”。故濂溪极重视“中”:“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20)[宋]周敦颐撰、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第20页。。“中”,发而应物之“几”、之际皆能中时中节、合宜合度,缺失一具客观定项的道德本体,其中蕴含着全然的未定项。
所以,周濂溪之论性,皆偏于气质气禀之性,缺乏一形而上客观性的道德设准。濂溪强调“中”,乃中时中节之合宜合度,得境域之中情性、气性之中正,无所乖戾,而非与一外在抑或内在的根本之“理”(“性”)相符合。天有阴阳两施,气禀之性有善恶两分,非由本体性心之善而言道德本体的定然之善,只是“因气成性”而言的气质之性、质素之性(21)“‘气性’善恶之分解的展示:诸义并立。”(参见牟宗三:《才性与玄理》,第8—11页。)。在濂溪的思想理路中,以气言性,未深见道德主体性“心”的绝对地位,故终只是浮面地说“诚”“几”“德”。若要安置心性论中自由自律的具客观性的道德理性与自觉心,必须预认心性论中客观性的道德本体。但是,无论是《太极图说》,还是四十小节的《通书》,濂溪尚未有此自觉并工夫次第,其论工夫远不如二程之学细密、系统。朱熹极力推崇濂溪,强为之说,终也评其“这话头高,卒急难凑泊”,也有理论落实处的难通之意。
综括之,周濂溪杂糅《易传》《中庸》,并受荀、老、阴阳家、汉儒宇宙论架构影响,已与先秦儒家思想相异其趣。濂溪的理论系统,混同形上学的天道观与宇宙论,未明标“心”与“意志”,即便朱熹加入一“心”字将此预认的心性观点出,实亦无法架构起真正的心性之学。“诚”与“几”惟落在主体性的“心”之上,但濂溪的思想理路难以安置心性论的主体性观念,故惟以“无”释“诚”。“诚无为”似一纯然、虚壹而静的境界虚体,但老庄,尤其是老子思想中尚有复归人心本然之理、本体之性,复归“自性-自觉心”的努力,非一纯粹的虚无静观境界可以解释。濂溪又言“几善恶”,指善恶动于人心之微,可能依于理或不依于理,但在其阴阳五行的宇宙观架构中,又与以气为性下中时中节的阴阳区分,杂糅道德价值观的“善恶”,颇难分辨。濂溪形上宇宙论架构下,道德主体的自觉心终未展露,终无从安顿道德主体的自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