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电影文字叙事
□ 李培峰 李 亚

电影《淘金记》中默片时代的文字叙事需要中断画面,以字幕的形式单独展示文字,这样不免会造成时间感的断裂
作为电影的叙事材料,文字曾在默片时期发挥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其表现形式包括位于电影虚构世界之外的字幕,以及位于电影虚构世界内部的书籍、信件、日记、报刊、档案等书写文字。在有声片中,文字的叙事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声音所取代。叙事者不必再像默片那样费尽心机地在剧情中安插文字提示信息,字幕的使用也大大减少。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复活了电影的文字叙事。新媒体的范围可以界定为:“基于计算机技术的互联网、基于通信技术的手机、基于数字广播技术的数字广播(DAB)和数字电视(包括移动电视)以及跨媒体的IPTV(网络电视)等。”新媒体是一种数字媒体,能够实现多种媒体元素,包括文字、图片、声音的互相融合和自由组合。文字是新媒体的基本媒介语言,电影一旦以新媒体进行表现,就往往需要处理文字素材,从而为电影的文字叙事带来新的契机。
新媒体在电影中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作为一种叙事的内容,即人物使用新媒体产品;其次是作为一种叙事形式,即电影镜头模拟新媒体产品的界面。本文的分析针对第二类情况,即分析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电影文字叙事。由于新媒体的特征,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文字相较于传统的电影文字,以新的叙事形式,产生了一些新的叙事功能。本文尝试从模拟功能,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以及画面与文字的组合关系等角度对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电影文字进行形式和功能的分析。
一、模拟功能
在电影中,并不是所有元素都具有叙事功能:“罗兰·巴特会提及电影的‘第三意’(third meaning),存在于外延与内涵之外:在此领域中,因果关系、色彩、表情和质感都成为故事的过客。克里斯汀·汤普森指出这些元素为‘过剩’(excess),它虽然在感知上突出,却不属于叙事,也不属于风格。”柏拉图在改写《荷马史诗》时,删掉了“海浪轻轻拍打的沙滩”等描述,因为他认为这些细节是多余的,与叙事无关。热奈特对此称:“它在那儿叙事才提及它,除此之外它不起别的作用……但这个无用而琐碎的细节是造成似乎确有其事的错觉,因而产生模拟效果的最佳媒介,是完美模仿的内涵体。”
在电影中,文字也可以做此区分。安德烈·戈德罗和弗朗索瓦·若斯特认为,无声电影的字幕可以“产生一些既是语言的,也是叙事的效果。”但叙事和非叙事的区分只是相对的,非叙事的元素在一定意义上依然具有叙事的功能,如热奈特所言,这些元素可以产生“模拟效果”从而辅助叙事。在电影的新媒体模拟镜头中,文字也具有这种模拟功能。电影可以使用文字模拟新媒体的产品界面,即新媒体与受众交互、传递信息的环境,以及在其中进行的文字交流活动,从而使这种模拟镜头成为“确有其事”的“完美模仿的内涵体”,为其叙事功能服务。

电影《羞羞的铁拳》中主人公通过斗鱼进行直播,此时电影出现了模拟直播镜头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刷屏的弹幕,文字和数字模拟直播画面,既产生了真实感,也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首先,电影使用文字模拟新媒体的产品界面。新媒体的产品界面主要由文字、声音/音频、图像/视频构成。“当前,在人机界面领域,以图形化用户界面、网页界面、多媒体产品界面、手持移动设备用户界面为主。”电影常模拟的产品界面主要包括网页和各类手持移动设备。在网页界面中,网页形象栏、导航、广告和正文内容都有很大比重的文字内容。在《解除好友》(Unfriended,2014)的一个网页模拟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浏览器标题栏上的“Chrome”“File”“Edit”“View”“History”等英文字符。在浏览器的地址栏上,显示了人物登录的网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6ihe-gnevqk”。在页面显示区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登录的视频网站“YouTube”的字符标志以及人物查看的视频的标题:“LAURA BARNS KILL URSELF”。
手持移动设备主要包括手机、pad 等数字媒体设备,这些设备往往是多功能的,既可以纪录影像,也可以传输一定的语义信息。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下,电信网和广电网的媒体界面也常与互联网融为一体。比如在《羞羞的铁拳》(2017)里,马小在手机直播中跳入了一个装满水正在加热的铁锅里,美其名曰:“铁锅炖自己”。这段情节通过一个模拟手机直播的镜头表现了出来。镜头中,出现了“斗鱼”“房间号2020202”等文字和数字信息。手机的直播可以在手机上收看,也可以在电脑上收看。因此,这个直播界面中的文字既是属于电信网的,也是属于互联网的。
其次,电影使用文字模拟新媒体的交流环境。文字是新媒体交流的主要手段,因此在电影模拟新媒体的交流时,文字会被频繁、大量地表现。新媒体的交流可以是点对点的,比如人与人通过手机短信、聊天软件、聊天网页、电子邮件、网络社交平台等进行的交流,也可以是面对点的,即多个人物同时向一个人物发送文字信息,比如在《羞羞的铁拳》中,当马小直播时,众多网友就发送了大量的文字弹幕,比如“香味满天飞”“调味品多来点”“舌尖上的美食”等。交流也可以是点对面的。点对面的交流一般表现为个人在网络上发布公开的信息,比如在《悲剧女孩》(Tragedy Girls,2017)中,一名女孩就发生于镇上的凶杀案在社交平台上的“隐瞒凶手,玫瑰谷悲剧”的讨论话题中发表评论:“谁会是下一个?”
交流者一般都有自己文字的代号。这些代号或者是交流者的真实姓名,或者是一些虚拟的以字符表现的昵称。虚拟的昵称能够提供使用者的个性、身份、欲望等信号。在《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网络》(Who Am I -No System Is Safe,2014)中,黑客的昵称是“MRX”。“MRX”为“Matrix”的缩写,意为“矩阵”。这个昵称暗示了他的神通广大和神出鬼没。在罗兰·巴特对叙事单位的划分中,这些昵称可归属于“迹象”类别,即可以表示“性格、情感、气氛和哲理”的非叙事性“象征结”。
还有一种交流活动,即新媒体界面中的关注、点赞、取消关注等操作。这些操作可以表明人物对人物的态度和情感。在《玩命直播》(Nerve,2016)中,一名女孩注册成为了一款直播游戏的主播,不断接受由网友提出的难度逐渐增加的挑战。她的粉丝数不断增加,显示粉丝数的字符就同步地出现在了画面上。
二、叙事的时间和空间
在新媒体产品中,用户以文字的形式替代面对面的对话交流。因此,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声音话语的替代。作为叙事话语的文字,既有声音话语的叙事功能,也有符合新媒体特征的时空话语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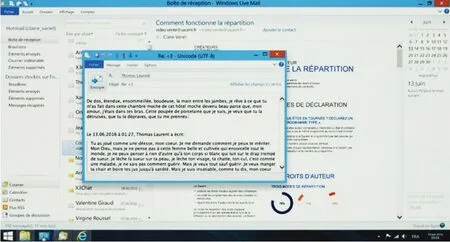
电影《快乐结局》中两位主人公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电影以53 秒的时间呈现出了这段文字输入的过程。输入以现在时态形成,没有中断,产生了类似于视听画面的叙事效果
首先,在叙事的时间上,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文字往往处于叙事的进行时中。传统的文字叙事大都是以完成时态,一次性地呈现出来。尽管在很少的情况下,电影会表现剧情中的人物书写文字的过程,但这会占据较长的叙事时间,因而大多被展示的文字都是书写完成后的。在新媒体模拟镜头中,作为交流工具的文字是像声音话语那样,在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以现在时态依次呈现的。在文字的完成时中,观众接受只需要耗费阅读时间,而在文字的进行时中,观众还需要耗费等待文字生成的时间。
在《快乐结局》(Happy End,2017)中,一对私通的男女通过一个聊天页面进行文字交流。电影模拟了他们交流的电脑页面。在镜头中,男人敲击出如下一句话:“亲爱的,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女儿在我的电脑里翻到了我们的私信。她尝试自杀,谢天谢地,她没事。我不得不删除了我们所有的信息,从此我不能再保留任何信息。我不知道她接下来会冒出什么念头。我们必须商量好一个时间。”他共花了53 秒的时间敲击出这些文字。这是在叙事的现在时态中进行的文字话语生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观众需要等待未来的文字信息,而不能像阅读字幕那样快读、略读、跳读。这种文字叙事的时间特征产生了特别的叙事效果,比如悬念、好奇等。这是传统的文字叙事所无法提供的。
其次,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的文字具有一定的空间指示作用。在传统的文字叙事中,字幕位于剧情之外,本身并不占有空间。对剧情中的文字而言,占有空间的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的载体。同样,新媒体产品中的文字也不占据空间。但不同于传统的文字叙事,在新媒体模拟镜头中,文字是由位于一定空间中的人物提供的。在对输入或发送文字的人物进行表现时,其所在的空间就可以被展示出来。而即便这个人物未被展示,但通过文字交流行为,其所在空间依然可以被推测出来。并且,观众也会主动参与这个潜在的、可能的空间的建构过程,明确或完善人物所处的空间环境。
在《快乐结局》的一个模拟镜头中,一个人用手机拍摄一名正在洗手间里刷牙的女人。拍摄者藏身于镜头之后,他/她一边拍摄一边在手机屏幕上发送文字,所发送的文字是对被拍摄者行动的描述,包括“吐”“水”“漱口”等。由于文字是以直播的形式发布的,所以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应该是处于同一时间之中,而我们也可以因此确定,他们也处于同一空间之中。
有些情况下,文字提供者的空间信息是被完全隐藏起来的,模拟镜头的画面只展示被输入的文字,却不提供任何空间信息。在《快乐结局》中,有一个模拟镜头表现了两个人物通过网页进行的聊天。聊天内容火辣,不堪入目,但我们却无从知晓聊天者的身份以及他们所处的空间位置。此时,观众会对这个被隐藏的空间产生强烈的好奇,急切地捕捉一切可以提示空间的线索。
三、画面与文字:全新的组合
作为不同的叙事素材,文字和画面各有优势和缺陷:“不过雷蒙·肯特坚持认为,以文字和以影像为形式的叙事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讲述——它是一种语言行为,需要它的对象(被讲述的)与讲述行为有时间距离……”也就是说,文字话语是一种过去时,与被讲述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时间距离”,这种距离的填平需要接受者动用复杂的思维能力。文字也具有单一性,不能在描写行动的同时又描写行动发生的环境,因而难以实现空间性。画面虽然能直接呈现空间,但却有过多的冗余信息,使接受者难以准确定位和解释。
文字和画面的结合可以互相利用双方的优点,弥补缺陷。不过在传统的文字叙事中,画面与文字在整体上是疏离的。字幕独立于虚构剧情之外,构成一个单独的镜头。而剧情中的文字位于承载物之上,但这些文字与呈现它们的镜头本身并无有机的关系。由于这种疏离,观众依然要面对文字讲述的时间距离、空间缺陷以及画面信息冗余的困扰。但是在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由于画面和文字可以同时呈现,便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的文字叙事未能尽如人意的不足。文字与画面以全新的方式进行组合,紧密而有机,自由而灵活。文字因同画面的结合而获得了一定的空间性、直观性、生动性,画面也因文字的同时在场而赢得了全新的维度和意义。
若剧情中的人物在使用新媒体,电影便可以通过模拟镜头,将文字在人物活动的画面上呈现出来。比如在《好友请求》(Friend Request,2016)中,女主角使用手机查看自己的社交账号,账号页面上的文字信息——好友的留言就在画面右侧展示出来,比如“我的胳膊现在还都是麻木的”“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你会举办一个生日派对吧?”若人物通过新媒体产品进行即时的文字交流,内容也可以显示在画面上。在《玩命直播》(Nerve,2016)中,一名女孩一边骑车一边使用手机与好友沟通。模拟镜头中,她们沟通的文字内容在画面左侧同时呈现了出来:“对不起,Vee,他根本配不上你”“去你的,不是每个人都是玩家”。
我们来分析《快乐结局》中的两个手机模拟镜头。第一个镜头中,一个人用手机拍摄一只笼子里的仓鼠。这只仓鼠在笼子里活动了一会,然后死掉了。在第二个镜头中,一个女人躺在沙发上呻吟。仅通过这两个画面,我们根本无法知晓具体的叙事信息:“仓鼠因何而死?女人是谁?她为何躺在沙发上呻吟?拍摄者和仓鼠、女人的关系是什么?”画面似乎提供了具体的信息,但这种信息却过于模糊,难以确切地解释。
两个镜头中都出现了拍摄者发布的文字信息。第一个镜头中的文字包括:“这是皮皮斯,我的仓鼠”“我养它一年半了”“我刚往它的口粮里下了点药”“是我妈妈治疗抑郁症的药”“我真受不了她”“她整天哼唧个没完”“我爸好几年前就丢下她了”。当仓鼠死后,另外一条信息发送了出来:“成功。”第二个镜头中的文字包括:“让某些人闭嘴就是这么简单”“我要打电话叫救护车了”“现在她不再是那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傻瓜了”。同样的,如果没有画面的配合,仅通过这些文字信息,我们也无法推测出具体的事件:“什么‘成功’了?谁闭嘴了?因何闭嘴?仓鼠和‘闭嘴’的人处于什么环境中?”文字信息的指向虽然明确,但却缺乏直观性,也难定位到具体的空间中。
只有通过画面与文字的组合,我们才能够接受完整的叙事信息:拍摄者有一条养了一年半的仓鼠;他/她用妈妈治疗抑郁症的药毒死了它;他/她的妈妈患有抑郁症,难以相处;他/她的爸爸离开了妈妈;他/她讨厌妈妈;他/她给妈妈下了毒。
短短的两个模拟镜头,却承载了惊人的信息含量。这些叙事信息不仅包括叙述的现在,也指向了叙述的过去。不仅有动作,也有人物的思想及评价。并且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刻画也非常深刻。这两个模拟镜头提供了一个限制性的叙事视点,虽然拍摄者始终没有露面,我们也无从知道他/她的具体信息,比如年龄、性别、外貌等,但通过这些文字和画面信息,我们还是能够推测出其人物形象:他/她阴险、无情、刻薄、残忍。同时,一个被抑郁症折磨,被丈夫抛弃,与孩子关系疏远的单亲母亲也被生动地刻画了出来。
如果是以传统的方式叙述这些故事信息,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画面。即便以声音话语的形式来讲述,也不会如这两个模拟镜头般生动而深刻。如果以字幕的方式表现,那么和这种在进行时态中叙述的文字信息相比,悬念感也会大打折扣。正是通过文字和画面的同时性组合,这两个模拟镜头才如此令人震撼,尤其是在接下的剧情中,剧情冲击力达到了高潮:我们发现拍摄者不过是一名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这就是在新媒体模拟镜头中,画面和文字的全新组合方式所实现的叙事效果,也只有在这个时代,电影的文字叙事才能实现如此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