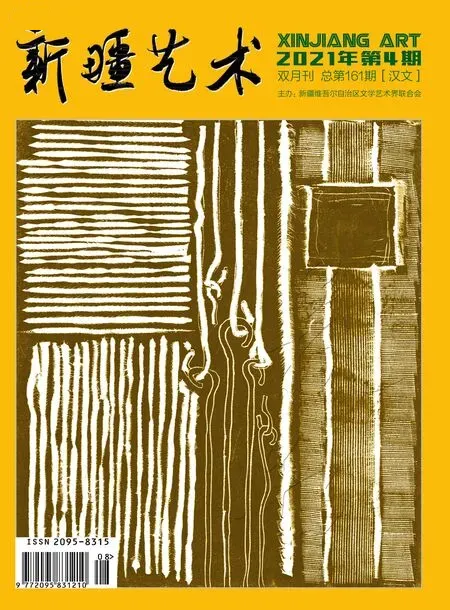村长的英雄梦
——梁越其人其事
□ 黄 毅

梁越在广西参加民族节日(左二)
在新疆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数情况下很容易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只有被人刻意提起,或者在填写一些官方表格时,不得已才想起我也是少数民族。
我是生在新疆长在新疆的疆二代,父亲是新疆的解放军,祖籍是广西都安,壮族在新疆属于少少数民族,在这里几乎没什么老乡,平日里也就把自己混同于新疆土著。
有一天,来了个瘦瘦弱弱的年轻人找我,说是我的广西老乡。其实他一开口我就听出了他的广西口音,我很奇怪我听力超常的敏锐,也许在新疆自小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太多,各种方言的耳音灌多了,自然对说话人祖籍的判断相对准确。
操着广西口音的年轻人叫梁越,大学学的是地质专业,一毕业便从最南面跑到了最西边,在伊犁的地质队呆了三年。长期的野外工作似乎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明显的印记,而潦草的长发却难掩其文气,尤其是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闪烁着柔和的光影,那是一双双眼皮的大眼睛。他当时想上帕米尔,南疆没有认识的人,听说我这位文人老乡在当地朋友众多就跑来见我。我当即修书一札给喀什文联的赵力,后来听说赵诗人给梁越提供了帮助。不觉间身边就多了位老乡兼文友。
记得大概是1995 年深秋,在库尔勒召开中国西域楼兰学与中亚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我是受邀去拍一部关于楼兰的纪录片,而梁越是参会者。在去库尔勒的列车上我们不期而遇,自然聊得很尽兴,他对车窗外天山以南的所有景物都异常新奇,毕竟这里的戈壁沙漠的粗粝与伊犁草原的柔美有太大的反差。他对我卧床长睡更是不理解,我告诉他,猛兽多睡,闻言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了。我弄了几瓶酒,有酒的神聊才显得自如,且上天入地。借着酒,他才吐露出了一些内心的真实,他说,他最崇拜的就是张骞,张骞几乎以一人之力,凿空了西域,使广袤的西域大地与中原紧密联系在一起,使丝绸之路得以贯通。
去远方建功立业,自古便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士阶层为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相信,通过个人的奋斗,可以改变个体的命运和整个家族的命运。远方意味着未知和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远方的诱惑力对门阀士族似有衰减之势,而在文人墨客中却大行其道。此风到了今人这里,已变得面目模糊,并因某些需要而被贴上了形形色色的标签。
梁越的远方不仅是地理上的远方,更是内心的远方,而张骞就是站在心中最远也最清晰的一个人。每个男人都会有一个精神的偶像,都会有一个英雄梦。
列车上几瓶酒的神侃,酒下得顺溜了,话语却开始磕磕绊绊,最终梁越大醉,好像还折腾得列车员来麻烦了一番。
梁越是一个有恒定之心的人。他立志要重走张骞之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遍西域大地。在河西走廊,在西夏王陵,在阳关、嘉峪关,在伊犁河谷,在阿勒泰金山,在楼兰罗布泊,在和田圆沙古城、丹丹乌里克,在帕米尔公主堡、瓦罕走廊等等,都留下了他孱弱而坚定的背影。
遵循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古训,梁越自觉完善着作为一名读书人的修为。他徒步进入死亡之域罗布泊,参与了人类首次中蒙国际河流——布尔根河的漂流,探幽青河三道海子石堆太阳圣殿,寻访成吉思汗最后的陵寝。这一系列高难度且充满了危险与挑战的操作,没有使他健硕起来,反而从外形上看,更显得瘦弱单薄了。
读书与他的写作实践成为他的另一种人格的完善提升,自1993 年始,他先后完成了《野天空》《寻梦飞天》《大汗的挽歌》和《西去的使节》等多部著作,其中《西去的使节》是他以张骞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是他对心目中的偶像的致敬。此书当时在新疆出版遇阻,但后来在北京出版,竟然十几年发行了近20 万册,还出了韩文版和繁体文港台版。最值得一提的是2007 年11 月列入文化部、财政部全国送书下乡工程,发行到了乡镇一级图书馆和中小学阅览室。2021 年,此书又将再版印刷。
梁越还参与和组织了多个文化项目的策划、论证,俨然扮演了文化大师的角色,他曾说,人类的智慧只有不断地聚集、穿透、飞跃、超生,人的群体所构成的民族的存在才会有可靠的保证。他在一篇题为《十年一顾西域梦》的文章中写道,西域之梦,从十年前开始,而当我几乎用双脚量遍这片大地时,我才发现,更多的文化之谜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这会导致我永远把一颗心遗落在这片巨大的荒原上。
事实上,他没有永远把一颗心遗落在这里,有一天他忽然就从新疆消失了,去了北京。在我看来,到北京是他跳出了某个地域的局限,而获得更广泛视野的开始。这时候,他于2011 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陆荣廷评传》,给辛亥帝制崩溃直到国民党北伐胜利这段历史时期中国南方实力最大的地方军事首领——中华民国勋一位、耀武上将军、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进行了全面平反,引起史学界震动。刚开始还有人喁喁私语,出版十年后再无异议。这本书让陆荣廷上将军这位曾在护国护法时期为中华民族立下大功,并扶持孙中山在广州开府,曾是南天一柱的共和功臣的铜像在他的家乡立了起来。
《陆荣廷评传》一书至今已四版五刷,还出了一版在海内外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书名《百战名将陆荣廷》。听说以此书,梁越跻身于中央民族大学壮侗学研究所研究员之列,于是他把视野投向了广西和云南,毕竟那里有他熟稔和心仪的骆越文化。骆越,意为鸟耘。洞庭湖以南直到两广地域,在舜帝时代,就是“鸟耘象耕”之地,遗落着与三星堆一样的无数人类文化之谜。
梁越对民族影像一直情有独钟,对那些湮没在历史岁月中的民族历史文化,他有着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坚信一个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况且,隐匿在远荒遐塞的那么多未知的发现,囊括了从人类起源,到人类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多个节点。民族部族的兴衰消亡,无不对今天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启示与教益作用。用纪录片的形式去完成寻找和记录正是梁越的拿手好戏。实际上他也在完成着一个伟大的凿空,试图用现代意识的关照,贯通历史与现实,甚至联通未来。
在云南,他和他的团队推动传播了很多重要文化发现:神奇的太阳鸟母、坡芽歌书和句町古国;在广西,他寻找着布洛陀和百越古道。一度他的目光延伸到了云南边境地区以外的缅北,在2015 年2 月9 日缅北战火骤起的危险时刻,与凤凰卫视团队去采访彭家声,参与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枪声再起》。2018 年4 月,作为民族影视网创始人的梁越代表太阳鸟母团队在美国洛杉矶荣获第15 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来自云南西畴县汤谷村的太阳古歌唱响太平洋彼岸,让世界电影人如醉如痴。包括《天空之城》的作者久石让这样的世界级音乐大师争相与梁越合影。

《西去的使节》一书封面
坡芽歌书经过梁越团队创作《破译坡芽密码》纪录片在全国的助力传播后,成为云南最响亮的文化名片。坡芽歌书随即在音乐家刘晓耕教授的一手打造下走进上海音乐厅,走进北京国家大剧院,甚至走上俄罗斯索契世界合唱的巅峰获得金奖。张艺谋看了坡芽歌书纪录片被深深吸引,执导创作了《歌书·蝶》进行全国巡演,坡芽歌书在演出中如梦如幻如“大片”。
这个百越僚人的后裔,目光坚定,目标明确,用他的智慧和努力证明着一个道理:任何自信,皆源自所拥有的文化的深广以及对它的理解。据说,他离开新疆后,足迹走遍了中国一千个村庄,去发现一个个村庄的灵魂并使之复活。
梁越有个很有意思的网名:村长。这个名称的来源是2006 年新疆青河县为表彰其对该县文化旅游的突出贡献,而授予他青河县查干郭勒乡三道海子村名誉村长,他似乎很满意也很受用村长这个称谓,后来,在云南的什么地方,他再一次被授予名誉村长。在中国,最小的行政序列里,一村之长也是很有些道道的人物,而我不由得也联想到,如果地球也是个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