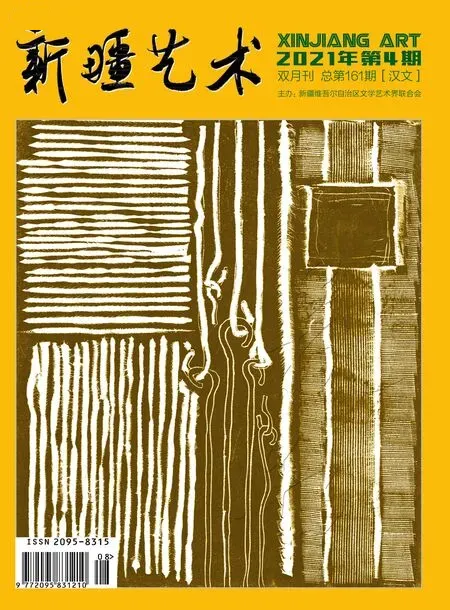中国古代桑蚕题材文学作品意象探微
□ 韩 琛

一、中国桑蚕意象综论
据考古发现推知,至迟在距今4700 年之前,中国古人就有了饲养家蚕的传统。成书于先秦的《诗经》中对于中国古代桑蚕业的描述更是多达20 余处。这些细节的描述展现了当时桑蚕业的兴盛。桑蚕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国绘画、书法、雕塑、服饰、文学中都有诸多展现,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在桑蚕文化表现形式中,桑蚕题材文学(以下简称桑蚕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绵延时间最长,辐射地域最广,可以说桑蚕文学作品在传播上已经突破了时空限制,是桑蚕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在桑蚕文化中,桑蚕文学作品逐渐有了特定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不仅增添桑蚕文学作品的意蕴,同时也是桑蚕文学最核心的概念。解码桑蚕文学作品的意象(以下简称桑蚕意象),我们就能体会到隐藏其中的文化,从整体上把握桑蚕文学作品表达的精神。
从文化角度来看,桑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桑蚕文学又是桑蚕文化的一部分,研究作为理解桑蚕文学钥匙的桑蚕意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文学作品中桑蚕意象的研究也是探寻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角度,对于理解、探求中国审美文化的多元性具有一定的学理价值。
研究桑蚕意象还有一个特殊重要的价值意义。就是桑蚕文化,对于丰赡“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桑蚕丝的发展形成了丝绸业的成熟与繁荣,进而成为丝绸之路,诞生的最重要因素。丝绸之路又成为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古代陆上商品交易路线,最终成为最早最重要的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建设“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路一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影响世界的战略举措,是新形势下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布局,也是加快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无疑将对世界经济文化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研究桑蚕文化也是为丝绸之路文明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本文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按照历代桑蚕文学作品的内容将其分为不同类型,归纳出桑蚕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具体意象。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于所引用的文献要有一个基本把握,那就是桑蚕文学意象一定是在历代桑蚕文学作品中反复使用过的,且在时间上有延续。力求避免主观臆断。
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桑蚕意象
通过对历代桑蚕诗的梳理,笔者从中归纳出以下六个意象。
(一)讽喻意象
讽喻意象是所有桑蚕诗歌中数目最多的意象表达,其沿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是历代桑蚕诗中最主要的意象表达。
《诗经》是桑蚕诗讽喻意象生成的源头,如《豳风·鸱鸮》中就有:“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此句借用桑树来阐发当时底层百姓生活之苦,通过对底层生活的揭露,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除此之外,《诗经》中的《七月》《硕人》《氓》《汾沮洳》《鸨羽》《黄鸟》等都有用较为委婉的方式讽刺当时社会的诗句。
到了唐宋时期,讽喻意象成为桑蚕诗中最重要的意象表达。唐代杜荀鹤的《蚕妇》中有“年年道我蚕辛苦,底事浑身着苎麻”;潘纬的《蚕妇吟》中有“贫女养蚕不得着,惜尔抽丝为人死”;杨修的《蚕室》有“年年桑柘如云绿,翻织谁家锦地衣”。五代蒋贻恭的《咏蚕》中有“著处不知来处苦,但贪衣上绣鸳鸯”。南宋戴复古的《闻机上妇说蚕事之辛勤织未成缣往往取偿债家》中有“缲声未断机声续,私债未偿官债催”;岳珂的《米元章蚕赋帖赞》中有“桑枯之利被天下,而不足以芘一女”;赵蕃的《蚕妇》中有“缲车响罢促机杼,盖体到头无一丝”;释文珦的《蚕妇叹》中有“无衣衣姑犹可缓,无绢纳官当破产”;周南的《蚕妇怨》中有“愿得明年蚕叶平,剜肉医疮为汝办”。到了明代,还有孙蕡的《蚕妇词》“丝成给日食,不得身上衣”;高启的《养蚕词》“檐前蝶车急作丝,又是夏税相催时”。

蚕妇
以上诗歌都是以讽喻作为其创作的主题,既是《诗经》和汉乐府的继承,同时包含着体恤民生之艰的儒家思想。可以说,讽喻意象是历代桑蚕诗歌意象最主要的表达,是桑蚕诗歌意象的核心所在。
(二)故土意象
在中国文化中,“桑梓”一词通常用来指代故土,那么在历代桑蚕诗歌中有没有这样的表达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诗经·小弁》中就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对此,朱熹在《诗集传》中注:“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由此可见,桑树的意象从农业生产的实用功能转化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再由这种亲情延伸至对故土的思念。当了解了桑蚕文学的这一意象内涵,就能理解为何《豳风·东山》中一位战士在归途中看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时,就马上产生了回归的冲动。
由《诗经》奠定的桑蚕诗故土意象在后世文学作品中还有延续,例如东汉张衡在《南都赋》中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的咏叹;西晋陆机在《百年歌》中有“辞官致禄归桑梓,安居驷马入旧里”的抒怀;东晋诗人谢灵运在《孝感赋》中有“恋丘坟而萦心,忆桑梓而零泪”的哀伤;唐代柳宗元在《闻黄鹂》中有“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的怀念;金代刘迎在《题刘德文戏彩堂》中有“吾不爱锦衣,荣归夸梓里”的喜悦。这些诗歌都是由桑梓起,而触动作者内心对故乡的思念。由此可见,故土意象亦是历代桑蚕文学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意象表达。
(三)劬劳意象
桑蚕诗里劬劳意象的生成亦源自《诗经》。《诗经·采蘩》中有:“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关于此句的解释,朱熹《诗集传》云:“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夫人能尽诚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蚕。盖古者后夫人有亲蚕之礼。”按照这种解释,此诗当是描写“诸侯夫人”为了“采蘩”而劬劳工作的场景,而“夙夜在公”则是“诸侯夫人”劬劳工作的诗意表达,“夙夜在公”日后也成为形容人们工作勤奋的常用成语。
唐宋诗人将《诗经》创造的“劬劳”意象进一步发展,比如唐代来鹄在《蚕妇》中写道:“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宋人梅尧臣在《和孙端叟蚕首十五首其十四龙梭》中写道:“给给机上梭,往反如度日。一经复一丝,成寸遂成匹。虚腹脱两端,素手投未出”;宋人钱时在《蚕妇叹》中写道:“呼奴勤向帐前看,夜卧靡宁三四起”。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劬劳意象同样是历代桑蚕文学作品重要的文学意象。
(四)田园意象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田园意象也是桑蚕诗意象表达的重要组成。关于此种意象的生成,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春日迟迟,采蘩祁祁”的田园风光中,但不得不承认,《诗经》中的桑蚕诗虽然有田园风光的描绘,但这种描绘与后世的田园意象并不相同。笔者认为,后世文学作品中的田园意象不仅有客观上的景物田园,还包含有诗人主观上的归隐意识,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称之为文学意义上的田园意象。
较早将归隐情怀注入田园风光的诗人是陶渊明。陶渊明热爱自然,同时也有归隐之心,在他的诗歌中,能读到一种恬淡的情感,这种情感的生成多是通过自然风光来表现的。在陶渊明众多的山水田园诗歌中,有不少桑蚕诗都呈现出了这种田园意象。如他的《归园田居·其二》中:“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志日已广。”陶渊明将自己内心的恬淡同“桑麻”联系起来,既表达了自己归隐之心,同时也为桑蚕注入了“田园”意象。他在《杂诗》中又有:“代耕非所望,所业在田桑”,显然,他已经将自己内心中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寄托于田桑之上,将本无情感的桑蚕注入了冲淡平和的田园意识。在《归园田居·其一》中还有这样的诗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传达出一种田园生活的质朴,成就了中国古代诗歌将自然与隐逸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这种回归田园的朴素情怀,超越了时空,不仅让古代士子们每每在失意之时魂牵梦绕,今天读来,也能够让身处繁杂世界的人们产生共鸣。
在陶渊明桑蚕诗中的田园意象基础上,唐宋文学家有了继承和发展。王维在其名作《渭川田家》中写道:“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也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上述两首诗都是通过桑蚕物象营造出一种静谧自然的氛围,这种氛围的形成其实是桑麻物象与诗人内心田园意识水乳交融的产物。从桑麻物象角度来讲,经过诗人内心的转化,为其赋予了一种“田园”意象。
唐代孕育了一大批山水田园诗,其中以桑蚕为题材的更是多不胜数,桑蚕物象也在此时被确切地赋予了“田园”意象。宋代以降,陆游在其《蚕麦》中写道:“村村桑暗少桑姑,户户麦丰无麦奴”;何应龙在《吴蚕》中说:“正是吴蚕出火时,交交窗外一禽啼”;黎廷瑞的《溪上桑叶萤食已既今年蚕事颇落寞》中有:“沿溪十亩桑,绿叶敷且腴。朝采不盈筐,暮视唯空株”;范成大的《照田蚕行》中也有:“今春雨雹茧丝少,秋日雷鸣稻堆小”。这些诗歌皆是沿着陶渊明的诗和唐代山水田园诗歌的路径进一步发展而成。
(五)爱情意象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有不少桑蚕诗是描写爱情的,自然而然的,爱情就和桑蚕诗结合起来,形成了桑蚕诗的一个重要意象。

照田烧蚕
桑蚕诗中最早反映爱情的诗歌源于《诗经》。据笔者粗略统计,《诗经》中提到“桑”的一共有20 余篇,在这20 多篇诗歌中,爱情是其中最重要的意象表达之一,比如《诗经·桑中》就有:“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此诗描绘的是当时的人在桑林幽会时激动幸福的场景。《诗经·隰桑》又有:“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此诗则以桑林为叙事铺垫,用女性视角表达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对恋人炽热深沉的爱恋。《汾沮洳》与《隰桑》类似:“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此诗亦用女性视角表达了一个少女为男友的英姿飒爽所倾倒,产生的浓浓爱意。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直接源头,其对后世诗歌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诗经》中将“桑蚕”与“爱情”相结合的表达最终形成一个文化符号:桑林成为男女幽会的象征,而桑蚕诗则成为爱情诗歌的重要载体。在唐诗中以桑蚕为题材的爱情诗歌亦不在少数。王建有诗云:“鸟鸣桑叶间,绿条复柔柔。攀看去手近,放下长长钩。黄花盖野田,白马少年游。所念岂回顾,良人在高楼。”此诗即是借用“桑林”表达了男女之间纯真的爱情。唐代郎大家宋氏《采桑》诗云:“春来南雁归,日去西蚕远。妾思纷何极,客游殊未返。”此诗则借用桑蚕之事来表达对征人的思念。陆龟蒙的《陌上桑》云:“皓齿还如贝色含,长眉亦似烟华贴。邻娃尽著绣裆襦,独自提筐采蚕叶。”此诗则以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旧事为引,表现了一个青春少女的朝气蓬勃,虽未直接涉及爱情,但全诗营造出的青春气息弥漫着一种爱恋的味道。宋代诗人楼璹在其《织图二十四首·蚕蛾》中亦是通过桑林来营造一种烂漫淳朴的恋爱气息:“蛾初脱缠缚,如蝶栩栩然。得偶粉翅光,散子金粟圜。岁月判悠悠,种嗣期绵绵。送蛾临远水,早归属明年。”此诗所反映的情感,与唐人为桑蚕诗营造的爱情意象一脉相承。

采桑图
(六)伤春意象
桑蚕诗的伤春意象与爱情意象紧密相关,多是采桑少女面对春日的生机勃勃时,自然而然产生的内心萌动,采桑女对于这种情绪波动不知如何释放,故而产生了伤春情绪,这种情绪最终也成为中国桑蚕诗歌中的一种意象表达。
最早描写伤春情感的是《诗经·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对于此句,钱钟书认为,“女子求桑采蘩,而感春伤怀,颇征上古质厚之风”,“则吾国咏伤春之词章者,莫古于斯”。由此可见,春日的明媚和对爱情的向往让采桑女萌生了缥缈忧伤之情,这种情感朴素真切,正是孔子“思无邪”的最佳注脚。
后世桑蚕文学中,以桑蚕为题材的伤春作品还有很多。比如楚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妆……于是处子怳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透过此赋可以看到一群妙龄少女在桑林采桑,她们有感于春日的明媚,不禁心烦意乱,恍惚不安。宋玉借《诗经》里的典故点出少女内心的悸动。曹植《美女篇》中亦有类似表达,采桑女面对“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的春日景象,内心萌生出“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伤春之感。南朝乐府组诗《采桑度》中亦是如此,组诗第一首就有:“蚕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此句描绘了尨茸的春日景象。组诗第六首则描写了采桑女因上述春景产生了内心的波动和惆怅:“采桑盛阳月,绿叶何翩翩。攀条上树表,牵坏紫罗裙。”
三、中国古代桑蚕意象生成原因初论
在对历代桑蚕文学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上述六条桑蚕意象。但还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上述意象产生的哲学土壤是什么?笔者认为,大体上说,讽喻意象、故土意象、劬劳意象和田园意象都源于古代的儒家思想,而爱情意象与伤春意象则相对特殊,其滋生或许源于女性意识。
(一)儒家思想
对于讽喻诗歌本质的阐释,当代主流文学史通常认为其功能主要是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例如刘大杰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讽喻诗的最大特色是广泛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与荒淫腐朽的本质,提出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具有深厚的同情和强烈的斗争力量。”从讽喻诗歌的内容来看,刘大杰先生的这段话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笔者认为这种认知应是今人思古的一种主观想象。若我们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审视讽喻桑蚕诗的思想渊源,或许儒家思想才能更为合理地解释诗人的创作动机。首先,讽喻诗的创作者多为士族阶层,他们本身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大多数士子们的政治理想,因此,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的目的并非讽刺统治者,而是希望以此引起统治者的注意,最终让社会回归正途。其次,揭露社会黑暗往往与哀悯百姓的疾苦是一致的,这种关心百姓疾苦的“民本”思想正是孟子所谓的王道思想。应该说,历代讽喻诗对现实的揭露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桑蚕诗家园意象的产生源于诗人对亲人和故土的深切怀念,如果进一步追溯这一意象的思想渊源,笔者认为,儒家的“孝”文化则是推动家园意象产生的原动力。人类何以有故乡情结?这一情结的本质又是什么?故乡情结的产生一方面与人类生存方式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故乡是父母生养之地,对父母的亲情建构了故乡情结的内核,缺乏慈孝精神内核的故乡不过是一个地理位置,很难在人类大脑中留下深层次的记忆。因此,我们可以说,游子对父母的思念(孝)是家园意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而言,这种情感只能深埋在内心,每每看到带有故乡符号的“桑梓”之时,这种情感方才被重新唤醒。
桑蚕诗中劬劳意象的生成亦与儒家传统中天道酬勤的思想有直接关联。古代士人读五经,《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劳谦君子,有终吉”。《尚书·大诰》言:“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极卒宁王图事。”对于桑蚕诗中劬劳意象的创造者而言,他们在创造这一意象时,潜意识里正是体现了对勤劳的礼颂。值得注意的是,劬劳意象的创造者和描绘主体通常并非一人,那么作为当时社会弱势群体的采桑女,她们的辛勤采桑,劬劳抽丝的行为是否也受儒家思维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弱势群体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儒家经典,但总有传道者将《五经》中晦涩难懂的道理传授给身边之人,身边之人又将这种理念散播到他的亲朋好友之间。最终,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有了儒家文化的种子,劬劳意象也因此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
提到田园意象,我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老庄隐逸思想对诗人的影响。实际上,儒家思想是桑蚕诗田园意象诞生的原因则更为合理。首先,儒家思想中并非全都持开拓进取精神,例如《论语》有:“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由此可见,山水田园诗歌所流露出的隐逸思想亦有可能出自儒家思想。此外,儒家文化亦注重亲近自然,《论语》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即是后儒乐山爱水的理论依据。

纺丝制作间
(二)女性意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男性一直主导着社会发展,但对于桑蚕一事而言,女性无疑才是主导者。《礼记·月令》中有:“是月也(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齐戒,亲东向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
根据这段文字的记载,到了三月养蚕之时,后妃要进行斋戒,然后亲自参与采桑的劳动。桑蚕农事由女性主宰的局面已经在儒家经典中得到确认。
桑蚕之事由女性主导,这一事实直接导致了桑蚕诗的爱情意象多以女性为叙事主体,诗歌书写亦站在女性角度,诗歌整体风格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由此观之,伤春意象的生成也就合情合理了,因为伤春多为少女所特有情感的表现。由女性主导某种社会活动在中国古代并不多见,桑蚕文学中体现的这种罕见的女性意识,值得我们关注。
结语
桑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桑蚕文学作品是桑蚕文化最重要的传播载体,而桑蚕意象亦是解码桑蚕文学作品的一把钥匙,因此对桑蚕意象的研究有利于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掘和传播。在国家“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桑蚕文学意象研究对于丰富丝路文化内涵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