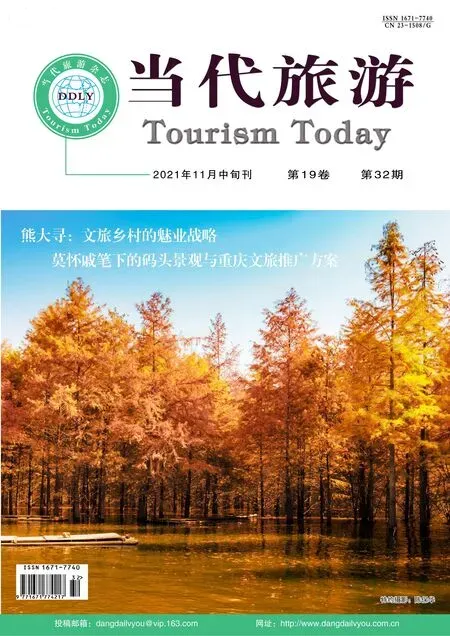女性主义视野下旅游发展对当地女性居民自我意识的影响
王 丹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长沙 410004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自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关注“三农问题”,从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到2013年的“美丽乡村”创建,再到2017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高度概括了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基础。旅游业作为新型产业形态与消费形态成了乡村振兴的重要突破口,对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明显成效,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突出。
鉴于目前乡村的空心化状态和女性的性别特质,少数民族女性往往在当地旅游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同年全国妇联下发《关于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实施意见》,妇女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少数民族女性参与村寨旅游开发中,往往受到传统文化、社会巨大变迁等因素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容易遭受社会发展的忽视,更容易陷于困难的处境。有学者认为:妇女主体性的缺失才是妇女贫困的根源[1]。促进女性主体性觉醒,有助于从根本上解放女性生产力。而女性自我意识发展,是女性主体性觉醒的核心因素。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视域,探讨旅游从业对当地女性居民自我意识嬗变的影响,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认为旅游开发有助于当地女性居民自我意识的发展。
一 旅游与女性自我意识相关理论
(一)自我意识界定
一般认为,康德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自我意识,为自我意识系统性奠定哲学基础。黑格尔援引“他者”的概念对自我意识进行深化。教育心理学认为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指人对于自己以及自己和周围事物的关系的认识,也是人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简单地说就是有关于“我”的意识。马克思指出:人的自我意识使人的生命活动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也因此而成为自觉的能动实践的主体。人的劳动过程是在人的自觉意识的支配下,改造自然并创造出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人化自然物——即劳动产品的过程[2]。可见,促进自我意识发展,是解放成为自觉的能动实践的主体生产力的重要前提。
1792年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权辩护》被认为是女性自我意识的代表之作,是对女性作为理性人类主体的权利的经典论述[3]。英国19世纪女权运动引发了社会学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促使女性自我意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学者们对女性自我意识定义多有不同,本文认为:女性自我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部分,是女性如何发现自我、树立自我、发展自我的独立意识。
(二)旅游与女性自我意识发展
旅游与性别角色变迁,是以往研究中争论较多的主题。国外旅游发展对女性角色变迁的影响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1994 年,威挽在《旅游中的性别分析》,认为性别关系在旅游发展中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国内研究也较多,多以个例研究为主,如杨文娴、林日举以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作为访谈对象,展示了当代海南黎族女性不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自我的心路历程[4]。黄燕玲、雷锦锦、罗盛锋以 4 个典型少数民族村寨为例,分别对民族村寨女性和男性居民的旅游扶贫开发有效性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性别差异对于民族村寨居民旅游扶贫开发有效性判别具有显著性影响[5]。诸玉杰等分析了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6]。主要集中在妇女对旅游发展所起到了作用,在旅游对当地女性自我意识方面分析较少。
二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地介绍
本文选择两个案例地,H村为旅游发展至相当规模,已进入旅游地生命周期成长阶段的村落,L村为尚处于旅游地探索阶段的村落。
H村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部,村里总人数为1306人,苗族占90%,女性为656人,少数民族风情浓郁,原以茶叶种植、务农为主,2010年8月开始发展民俗乡村游,2017年成立旅游公司后,将茶叶与少数民族村寨旅游融为一体,旅游业飞速发展,现已成为当地对外的窗口,并带动姐妹村寨旅游发展。
L村位于湖南怀化市,当地以务农为主,由于周边村寨的旅游业发展,当地旅游已在规划中,但由于交通等问题,目前游客稀少。
(二)研究方法
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其自我意识的状态,了解其行为背后的主观意愿,不仅仅是单纯看当地女性的行为。本文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结合部分问卷调查。2018年和2019年,研究团队先后数次进入案例地进行访谈,采访当地村委、旅游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及当地女性社区居民,积累了大量图片、访谈录音及文字资料。为保护隐私,文中受涉及被访者以字母代替。
三 不同旅游发展阶段当地女性自我意识表现
(一)H村女性自我意识表现
1 关注自我感受,认识自我
波伏娃指出“女人是以男人为参照物定义自己的,而男人却不是”[7]。当女性开始意识到“我”,“我”的想法与态度,“我的行为”时,标志着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H村为生苗村落,以往由苗王进行管理,夫权至上。H村女性在本村大多主家务活,同时参与农家乐接待、景区讲解、销售、表演等工作,同时由于茶产业的发展,也承担采茶的工作。参与旅游发展后,当地女性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开始关注到自我感受。访谈对象L在景区购物商店负责销售银器,目前收入大约每个月在3千元以上,在谈到工作缘由时,L说:“我都是自己愿意回来工作的,以前在外地打工,一个月也是这么多钱,现在家里也发展得比较好了,我就愿意回来工作,还可以住在家里。自己赚了钱,就是自己的零花钱,有时候看游客穿得什么衣服比较好看,就回来网上自己找一找,也不会和老公说,想买就买了。”在H村,男性家长仍然拥有较高权威,然而在家庭里,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女性收入的提高,其决策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有些决策依据女性自身的感受。“我回来工作”是因为我“愿意回来”,是“我”出于自身的考量而做出的决定,钱是自己赚的,怎么花也是“自己”的事,不需要再请示丈夫或公公。在某个范围内,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到自我感受,而非压抑自己的需求去顺从他人。
女性“本质论”思想意为男女有具体的、生物学上的差异的思想。惠勒夫人提出要将男女道德上的差异转换为女性的优势所在,从而证明女性在社会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这里说的女性意识,不仅仅指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指女性自身所特有的不同于男性的“气质”。访谈对象S目前是村里的文化推广员,为游客提供介绍、引导和一些表演服务。“我回来工作是因为想在家里顾小孩,家里旅游发展好了,因为家里有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生病了,还要请一个月的假,不方便嘛,在家里面,虽然钱少一点,但好一点。可以照顾孩子,就不会像有的孩子头上长满虱子。有妈妈在家,再怎么样,晚上可以给她洗一洗。”“我自己挣的钱我自己管啊,家里办事就一人出一点钱,我想买什么东西,像首饰啊,不用和他商量的,就自己买了。我自己花钱也花得厉害,买衣服呀,女人嘛。”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应该强调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强调不要用男性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主张男女平等的前提之下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在这里我们看到,S看到了自己的需求,非常清晰地了解自己,接受自己,关注自己的需求并完全接纳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能够突破被选择而建立自我的精神主体。
2 相信自我,主动寻求平等地位
女性在面对男性权力时,女性不再处于失语状态,能和丈夫商量,学会与“他者”平等交流,是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表现。访谈对象S介绍:“在家里,我也顾不太到家,小孩子上村里的幼儿园,其他时间是婆婆带,我工作收入比我老公还高一点,家里的事嘛,两个人商量一起做,像我儿子的事情,基本上我老公在管,家务活谁有空谁做呀。”在H村,被访谈家庭中大部分家庭中的女性家庭关系较为和谐,对于家里的事情,能夫妻共同商量而定,能有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对家庭事务有一定的决策权。
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当地女性能在融入外部社会的同时,尊重自己,不卑不亢,能够走出自己的封闭世界。访谈对象X说:“以前,我讲话都结结巴巴的,平常也是苗语说得多,现在我讲话很顺畅,很自信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接待。女人本来就要自信。刚开始,第一步开始学的时候,第一次带客人的时候,讲话都是抖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当时接了第二个团就没问题了,我平时脸皮也是比较厚的嘛。”“工作嘛,有的时候肯定很开心的,有的时候也不开心呐,有的时候碰到有些客人,你微笑服务,但是有的客人说,哎呀,你们这里脏死了,你们这里热死了,空调没有,烦死了,带我们到这个地方,什么话都有人说,有的人说,哇,苗家人非常热情,来的还是值得的。但那种刻薄刁钻的还是比较少,我也不会吼,也不凶他们的,跟他们讲几句玩笑。”可以看出无论是家庭这样的私域里,还是在公共领域,H村女性逐渐建立起自我的边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了自己的态度。
3 发展自我,主动寻求工作机会,争取经济独立
在H村,L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女性,她本来学历并不高,只有初中毕业,由于独生女的身份,不能外出打工。村里发展旅游业后,她在村里的培训中,学会茶艺、打鼓、驾驶等,多次代表村里前往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茶艺和鼓舞表演,为家中改造新屋,自己开车上下班,村里人对她的评价也非常高,丈夫也很支持她的工作。
另一位被访谈者L2表示:我之前普通话说得不好的,嫁到这里来也是说苗语,现在村里搞旅游以后,我就想着把普通话练好,现在做讲解员。收入还是比以前高些。“我主要是负责农家乐,女人亲和一点,好说话一点,游客也愿意和我们女的打交道 ,男的要吵架的,比较急,她(丈夫)管不好的,只有我能管好。”在当地旅游公司和茶叶公司里,女性管理者的数量比一般村庄多,并进入中高管理层。女性在物质上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基础,而能够有意识地不断发展自我,不断改善自我,挣脱父权或男权的束缚,才能争取精神独立。我们看到,在H村,由于游客带来的大量与外界接触机会和就业机会,使得村里的女性呈现出一种生机勃勃的面貌。
(二)L村女性自我意识表现
1 女性的自信心较弱
在L村,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收入较高的家庭主要收入还是来自家中丈夫或孩子外出打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该村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空心化的问题仍然存在,留在村里的多为老年人,年轻女性也不多见。在访谈过程中,被访对象D说:“(种菜)自己吃,我们这里太干了,种什么都种不出。交通不便也卖不出去。以后交通便利了可能卖得出去了。(目前)我们太封闭了,主要是交通闭塞。将来打算搞电商,卖些土特产,村里的旅游啊,民宿啊,村里搞不起,打算给村民承包。养猪呢,现在有猪瘟,也不敢养了。小额贷款这里比较少,有也不敢贷,风险大,负担不起。”“村委选举也是投票的,每个人都有票,没有女的上去讲要当什么的,我们(女性)没有那个能力”。
2 女性发展源动力不足
在L村,女性地位较之前已有很大提升,女孩子也一样进家谱,可以分地,在家中拥有一定的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权大多为“他致性”,即丈夫长年外出打工,女性不得不处理家庭事务。在访谈中,访谈对象N今年五十多岁,在村里开一家杂货店,一直以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家人因为生病,收入不高,开支大。非常希望村里能把旅游做起来,多点游客,但是对参加村里的各种活动却兴趣不高,直言村里矛盾较大,不想和有的人一起。访谈对象H今年26岁,读过大专,目前在外地打工,并已结婚生子:“在外打工,还是赚得多些,现在要带孩子,女孩子嫁了人,就跟着丈夫走。”
四 原因分析
(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旅游开发增加了培训机会
H村和L村女性都具备一定的自我意识,在村委会中,都由女性承担妇女主任一职,占有一席之位,这与我国多年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关系密切,两个村中当地女性学历都以初中居多。因而两个村庄都比较认同女性的受教育权,在家庭事务中,都有一定的话语权。但H村由于旅游的开发,客观上促使培训的数量远远大于L村,内容也更加丰富实用。如结合旅游开发的刺绣、茶艺、打鼓、讲解、销售技巧等,结合茶叶生产的茶树种植、茶叶采摘、制茶等培训,培训人次也比较多。不仅如此,旅游开发还促使了当地女性走出去,前往北京、上海等城市参加展销会、推介会等,客观上为当地女性开阔眼界、增强自信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经济收入提升,旅游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相对于较封闭的L村而言,H村每天要接触大量的外地游客,当地村民由新奇陌生已进入习以为常阶段,与社会接触范围扩大。之前在外地打工的年轻女性基本都已回村,分布在旅游公司与茶叶公司,做导游、销售、表演或采茶、管理茶园等工作。即便六七十岁了也可以从业,就业过程中虽然也不乏有旁边村庄的女性或请过来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但优先本地村民。同时,由于H村采用了公司+村委+农户的模式,使得一些由于个人原因无法从事旅游工作的女性,也可以凭借其房屋及土地入股,同样提升了在家女性的经济收入。
(三)性别优势突显,旅游开发加强了女性的自我认知
L村多以务农、砍伐竹木、打工为主要经济来源,女性在体力上远不如男性,这是造成女性在经济上依附性较强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她们不够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旅游业由于其服务业的特性,天然地更适合女性特质,这使得女性在性别上产生自豪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展自我,完善自我。
五 结语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旅游开发由于其经济拉动作用大、关联性强、服务行业特质,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女性自我意识的发展,女性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也为自己争取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等,自我意识得到彰显。但目前来看,尽管受到苗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年轻男女自由恋爱,家中老年女性地位较高等,其父权相对弱化。但其自我意识的发展仍较少体现在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等方面,在自我意识的发展途径上仍需较长时间的观察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