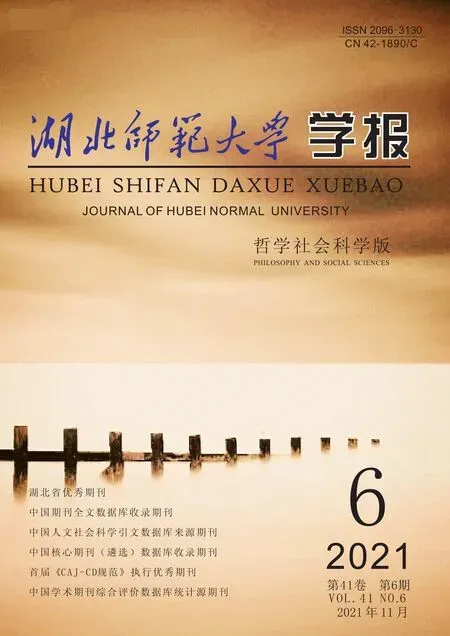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祛魅”与“复魅”
王泽亚
(南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
文学艺术的发展历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要素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当社会进入到现代时期,文学艺术的创作也相应地进入到了现代时期,本文所要讨论的现代文学艺术,更关注于时间上的现代性,即指当下的一些文艺现象,而非是文学艺术史上划定的现代主义之类的学术流派。现代的文学艺术不同于古典时期,通常呈现出流派多、流行快、消亡快的特征。随着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渗透,消费社会开始主导文学艺术的生产,交叉学科为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创作者本身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关注的题材或反映的问题也延展到了社会人生的各个领域。接受者圈层立体化,创作者身份复杂化,都将文学艺术作品推向“百花齐放”的境地。
在文艺多元化的今天,有两种主流观点在相互角力:一种是文艺“祛魅”下的反崇高、反权威、驱逐神圣性的叙事,将底层、边缘的声音纳入文学艺术创作选择的范围;另一种是文艺“复魅”下的经典重塑,以恢复传统经典和传统文化的魅力为主,通过改造使之与现代技术、新媒介相结合,与现代审美相适应,旨在提升民族自信。持文学“祛魅”观点者,常以庄子的“道在屎溺”作为其论证消解崇高的必要性或者日常化创作的理论依据。然稍有断章取义之嫌。《庄子·外篇·知北游》中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处不在。”[1],而并非仅在“屎溺”之中。这就说明,文学艺术作品不应仅停留在“祛魅”的层面,“复魅”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现代文艺的发展可以是“祛魅”与“复魅”的融合发展,而非单纯的二元对立。文学艺术作品在消解权威方面与复魅传统方面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一、消解神圣与权威:现代文学艺术的“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本义指对于科学知识的审美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它来自马克斯·韦伯的《学术与政治》一书,其中提到的“世界除魅”:“可见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2]有时也被译为“去魅”“去魔”“解魅”“解咒”。它发生于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转型之中。在文艺理论中,“祛魅”被引申为对崇高、典范的消解,破除权威与神圣,揭开事物神秘的面纱。
(一)神话新用
神话是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特殊存在,它连接着神与世俗两个世界,既反映了原始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是其精神上的支柱,也表达着原始先民的世俗愿望。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进步,掀开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神秘面纱,神话的权威性与神圣性逐渐消退,神话作为一种原始崇拜的社会意义早已不复存在。现代文学艺术对神话的“祛魅”,即当代创作对神话的态度不再是恭敬与虔诚的,不再是寄托愿望的,神话更倾向于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具体表现为对神话的拆解与重构。
1、神话意象的拆解

此外还存在着通过拆解神话意象,驱逐神话的神圣性、权威性的现象。当下都市生活挤占了神话存在的空间,人们缺乏必要的空间和仪式接触神话及其意象,这使现代人们对神本就不多的崇拜之情荡然无存。神人异兽的威力不在,他们往往被人类征服,神话意象由神主场转向人主场。例如《山海经》中的穷奇,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四大凶兽之一,喜欢吃人,极其凶恶残暴。然而在《魔道祖师》中,穷奇却被人类修士斩杀,做成了穷奇兽角鼓。这代表着上古神兽不再是权威神异的,人类斩杀穷奇是对权威的挑战。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文学艺术对于神话意象进行拆解,去除掉了神话意象原有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将神话意象拆分并塑造成更符合现代审美的形象,使其能更好地讲述现代故事,反映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对神话意象的拆解反映的是人们对世界的“祛魅”,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文艺作品中,人成为世界的主宰登上文学艺术创作的舞台。
2、神话故事的改写
中国的神话体系本身就很零散,更存在着跨地域流传多样性的特征,这就为神话故事的改写提供了历史基础。现代神话意象中的神圣与权威被消解掉以后,改写神话故事,使其表达当下的思想内容,变得更加容易。许多经典的神话故事,典型神话形象被改写进网络玄幻小说、电影电视剧,并一度成为当下的优秀作品。这是现代文学艺术“祛魅”带来的积极影响。
电影《大话西游》系列可以看作是神话改写的经典案例,它包括《月光宝盒》和《大圣娶亲》两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内容上与《西游记》没多少关联的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其中的人物却是以《西游记》中的人物为原型,这是对经典著作《西游记》中人物的戏仿。而随着新媒介的出现,网络文学中的玄幻小说直接从对神话的改写中构建了一个有别于传统神话谱系的新的神话体系。“洪荒小说”成为一个小说流派,这类小说讲洪荒大战、封神大战、佛道之争等主题。只要创作者有足够的想象力,漫天神佛皆可成为创作者笔下任意取用的素材,这类玄幻小说中的神话早已脱离了信仰、宗教等因素,成为纯粹的文学艺术的创作题材。
现代文学艺术的“祛魅”打破传统思想对创作者想象力的束缚,有利于创作者打破模式化的僵局,将故事创作延展至无限的空间,而神话故事也在现代这个去神秘化的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
(二)日常化写作的出现
反崇高、反宏大叙事,关注来自底层的声音,是现代文学艺术“祛魅”的另一个特征。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创作内容都不再是以伟大的人事作为唯一选材。这种“祛魅”的创作更关注于来自底层的、边缘的声音,是个体生命对主流社会和宰制文化体制的反抗,是由于个体未得到大众认可而释放出的野性。创作者话语立场和精神向度下移。与古典时期的作品相比,这类作品的出现代表低端者开始肯定自我,文学作品开始着眼于世俗世界,日常化写作出现。当崇高不在,平民开始登上创作的殿堂,创作内容变成那些被摒弃和排斥的异物,以及反审美的多余物和废弃物。这种现象具体反映到文学艺术作品上,就出现了荒诞派、“低诗潮”等文学流派和文艺现象。
波德莱尔无疑是这种“祛魅”创作的先驱,他奠定了现代性文学中向下的维度,让真正的垃圾以及像垃圾一样存在的被遗弃者出现在诗歌之中。就如同他在《恶之花》——《拾荒者的酒》中提到的那样:
拾荒者踉跄而至,
摇头晃脑地碰壁,
他丝毫不留意暗探的跟从,
大胆吐露心中的宏图。
他口述崇高的法律,立下誓言,
要打倒恶徒,要扶助贫弱,
在华盖般高悬的苍穹之下,
他陶醉在自诩的荣耀之中。
是的,这些受家累之烦
工作之苦,年迈所扰,
在巨都巴黎吐出的污秽之物里,
挤压得疲惫不堪[4]。
这首诗中展现着一个拾荒者的无助与绝望,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着苦难,仅能在酒醉中发泄自己的幻想。这首诗的创作表明波德莱尔关注到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他不仅在恶的世界中发现美,也能在美的体验中感受到恶的存在。创作者的世界并不是只有崇高的东西存在,现代都市的丑恶、现代文明的虚伪以及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贫乏空虚都将是创作者的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文学艺术的“祛魅”不是去除美的魅力,而是去掉遮蔽的日常化创作,现代文艺经过“祛魅”后仍具有审美性,而不会沦落为真正的垃圾。就像“‘低诗歌’所追求的‘下’其实是追求现实中的‘真’,他们揭发世间的丑恶的真面目,揭露个体生命最真实的状态,展现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已经少见的真性情。”[5]现代文学艺术在“祛魅”中解构权威,将问题的本来面目充分暴露,打破创作世界与世俗世界的界限,创作者不必再自缚手脚,接受者也能感受到文艺作品中与他们生活贴合的真实的一面。
二、重塑经典与弘扬传统:现代文艺对传统文化的“复魅”
单向度的现代文学艺术“祛魅”创作,并不能解决现代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过度的解构会破坏人们对美的体验。现代生活的平面化、同质化激发了人们对复魅传统的渴望。如查尔斯·泰勒在他的《世俗时代》中提到的那样:“这种常常是因为对那种完全困顿于内在秩序的生活的极度不满造成的,这种感觉觉得当下生活空虚、单调,缺乏更高的目标。”[6]现代社会的“复魅”不是简单的重构,我们也无需再回过头去寻求某种宗教或神的庇佑,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魅力复现,使其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周遭世界发生共鸣,是现代文学艺术“复魅”的主要目的。
(一)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再书写
网络文学是现代文学与互联网这种新媒介结合的产物,具有流行快、传播广、创作者圈层立体、接受者身份复杂等特点。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优秀中华文化浩如烟海,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已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基因之中,在集体无意识的驱动下,网络文学的创作往往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精神品质,唯美诗词歌赋的渴望。这就为身陷过度物质化、市场化的现代文艺创作,找到了一条有别于解构和“崇低”的道路,因此网络文学中隐含的对传统文化再书写的因素,是现代文学艺术“复魅”的主要方式之一。
1、对诗词歌赋的运用
由于汉语的特殊性,导致中国的传统诗歌中涵盖着情感美、意象美、意境美、阴柔美、阳刚美等众多美的特征。当现代文学艺术的“祛魅”带给人们的冰冷乏味使人颓废时,从传统诗歌中汲取精神力量、以及美的感受,成为现代创作者近乎无意识的举动。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加入一些诗歌元素,加入一些富有人文气息的,有丰富情感涌动的诗句,会给人们带来不同寻常的新奇体验。这既是对传统诗歌优秀作品的肯定,也为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发出新的创作素材。
网络小说数量众多,其中的优秀作品亦数不胜数,在众多优秀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复魅”的早期网络小说《甄嬛传》,能在众多雷同的宫斗文学中脱颖而出,就是凭借着对传统诗词歌赋的精准把握。“宁可抱香枝头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这句诗既是沈眉庄住处存菊堂的解释,也是对人物结局的暗示,这种通过诗词进行话语蕴藉,揭示人物性格命运的例证在《甄嬛传》中还有许多,并且每一次对诗句的应用都恰到好处,不显做作。这是现代文学艺术创作“复魅”传统文化,弘扬经典文学的一次成功实践。网络小说改编电视剧也是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热门话题。2021年热播电视剧《山河令》由网络小说《天涯客》改编的,由于电视剧是动感的画面,所以它在对诗句的表达上不是必须通过语言来完成。其中对周子舒退出天窗一幕的镜头处理是,一个人、一匹马、一地雪,渐行渐远,正好映衬出“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意境留白,既烘托出凄美氛围,又给观众带来无限遐想,用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画面解放观众的想象力,只在这一瞬间就能使观众感受到这部作品的魅力。
2、对优秀传统精神的弘扬
现代文学艺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复魅”,还表现在对优秀传统精神的弘扬方面。不同于西方世界以神作为精神依托,中国的民族精神从来都是以人为本的,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因此,当“祛魅”掉其中的权威性与神圣性,“祛魅”掉那些出于某种目的遮蔽事物本质的东西,保留下来的精神品质反而更加纯粹,因此,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大可不必向外去寻求精神依托,只需要恢复那些神圣与权威不在的纯粹的美的魅力,即本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就可以为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在国家大力宣传保护手工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网络文学作品《天工》从现代文明与传统工艺冲突的角度,向人们展示出一代修复师的创新与坚守,这部作品以文物修复过程中人与现代机器的对抗冲突为内容,反映出一代修复师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传统修复工艺与现代科技结合,又如何在物欲冲击下坚守工匠精神。我们的确不可能再回到自然本位的原始社会,但我们也不会因为人成为世界的中心而肆意妄为,现代文学艺术的“复魅”创作,恰恰给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将回溯优秀传统文化、优秀民族精神,与现代世俗生活、现代审美结合起来,打造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体系。
(二)现代科技与“复魅”传统的融合
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挤占了原始宗教仪式的生存空间,消解了人们对神的敬畏之心,传统节日、宗教仪式也成为了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资源之一,但同时这些古老的、散发着黄昏气息的资源,又借助现代科技,重新焕发其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魅力。智能时代和新媒介的到来,使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科技完全能够穿越时空为我们复刻千年前的视觉盛宴。现代文学艺术的“复魅”往往是在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中完成的。
在这个以科技和优秀传统为横纵坐标构建起来的空间中,现代文学艺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优秀文艺作品的形成不是某一个元素在发挥作用,而是集各家所长,形成属于现代文艺的独特的美的风格。2021年河南卫视的春节晚会中舞蹈作品《唐宫夜宴》,是以河南安阳张盛墓出土的隋代乐舞俑为创作原型,讲述唐高宗时期的一群女孩儿去宫宴表演节目的过程。其中有传统礼仪、传统节日内容的加入,也有5G、AR技术的支持,将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结合,为观众复现出千年前的盛唐景象,极具震撼的视觉效果。
而2021年端午节前夕,河南卫视再次推出国风类节目,即端午节特别节目《端午奇妙游》,其中的《洛神水赋》(原名《祈》)是一款水下中国风舞蹈,其灵感来自曹植的《洛神赋》,艺术形象来自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通过水下拍摄的方式,给人们展示出一位衣翩跹袂、身姿若仙的水下“飞天”形象。其作品原名为《祈》,是因为传统端午节有通过祭祀活动,祈盼家人祛病消灾的传统,在新冠疫情尚未完全消失的特殊时期,文艺创作者在端午节这个特殊的节日,通过这种特殊的创作方式,将现代科技与传统习俗相结合,表达人们向往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从《唐宫夜宴》到《端午奇妙游》,充分为我们展现了现代科技与“复魅”传统之间的融合,可以为现代人们带来美的盛宴,科技并非只有机械复制的作用,而传统也不是古板腐朽的糟粕,河南卫视“复魅”经典的行动,成功证明通过现代技术的加盟,现代文学艺术可以展现出审美的另一种可能——经典与现代审美的融合。这不仅反映出时代精神,也提升了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三、现代文学艺术“祛魅”与“复魅”的和解
现代文学艺术的“祛魅”创作与“复魅”创作看似是两个极端,但实际上,现代文艺创作应该有“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在选材上也应该如前文提到的那样——道,无处不在。不会因为消解神圣的、权威的体系就过分地强调底层的、边缘的以及那些被肢解的事物,从而陷入虚无、颓废之中,也不会因为回溯那些传统的、经典的事物就将神又请回到殿堂之上。儒道思想体系为我们提供着一套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的大一统融合的思想。在这种融合中现代文学艺术要实现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民主,实现资本与文学艺术性的和解。
(一)消解与重构同在
在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消解神圣与重构经典并不矛盾,一方面我们通过“祛魅”打破原有的结构,另一方面现代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又构建起一个属于当下的创作体系。仍以神话的创作为例,在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中,上古神话的庄严等级不复存在,神话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被斩断,神话的讲述者身份也从专职巫师转移到普罗大众。福柯曾经提到权力制造知识,那么当人人都有权力去讲述神话的时候,神话就成了可以被普通人制造的人话,人们可以在作品中重新构建一个与上古神话毫无关联的新的神的体系,这个体系中的神不是被崇拜的对象,这个体系仅仅作为现代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并无太多约束力的秩序。如果有人对这个秩序提出质疑,或者想重新建立一个神的体系,只要言之成理,也可被创作者和接受者接受。由此可以看出,“祛魅”去除的是人们对上古神话那个只能膜拜不能更改的权威性,去除神话的审美特权,而对其引导人们探寻神秘和驰骋想象力的方面是有所保留的。现代新神话的打造,拉开了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诸多紧张刺激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出现的唯美画面,都在被解放了束缚的创作者笔下肆意挥洒。
(二)有内涵的奇观
已经被科技与消费挟持的现代都市文化,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许多传统的仪式、节日、观念要么趋于同质化,要么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距离感,使那些经过“复魅”文学艺术作品成为一种奇观,给人带来不同寻常的审美冲击。虽然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提到,奇观是当今社会的主要产品。在乔治·瑞泽尔那里奇观被进一步解释成为铺张华丽的表演和模拟创造。他将奇观界定成为一场戏剧性的公共展示,奇观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然而要避免这种奇观沦落成为千篇一律复制品,避免奇观只注重一时的夸张新奇而忽视掉思想内容的表达,还需要在创作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合理的改造。
在这些奇观中加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改造成为符合现代审美的文艺作品,即在时空距离中为接受者呈现异乎寻常的美的体验,使这些奇观不至于落入仅仅追求刺激却空洞无物的窠臼。就像前文提到的水下中国风舞蹈《洛神水赋》,其中通过水下跳舞将原有的跳舞形式陌生化,从而形成奇观,而后又加入端午祈福的特殊寓意,形成了既华丽又有内涵奇观,而后通过观众的认可形成了经济效益。在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要坚持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主,以改造为辅,以优秀的民族精神为内核,以科技、消费为手段。在创作中既要去除权威的遮蔽,也要去除物欲的遮蔽,将那些纯粹的优秀民族文化提炼出来,改造成为符合现代价值观的文艺作品,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塑造本民族的时代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艺术的生产与消费不应该是对立的,作品具有文学艺术性并被观众喜爱,和作品带来经济效益之间并不会发生必然的冲突。以消费为主导的现代文艺生产中不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兼具艺术性与经济效益。
四、结语
目前,文学艺术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无论是在提升国民素质,还是提高国际地位方面,都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拥有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现代文学艺术创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无数优秀的传统文化,现代中国文艺发展可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祛魅”与“复魅”相结合道路。消解权威、弘扬优秀传统,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未来有着无限可能,其中“祛魅”与“复魅”的融合发展,会给文艺创作带来更多元化的选择,以科技和资本作为调和手段,为接受者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现代文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