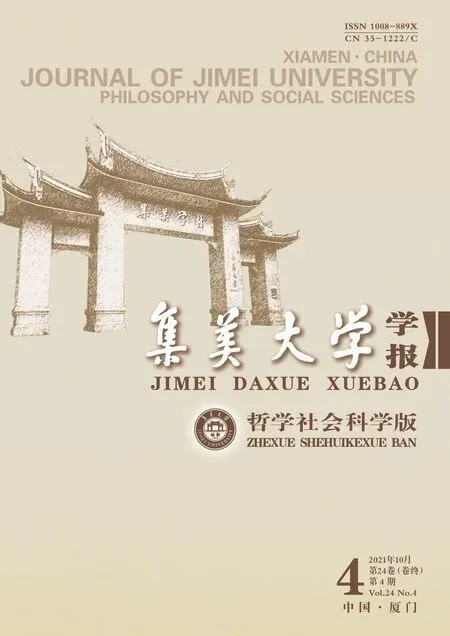汉代乐舞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探析
范晓敏,王 州
(1.集美大学 音乐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福建师范大学 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乐舞文化源远流长,史有明文的就可以追溯到西周初期制礼作乐的周公。在长达3 000多年的乐舞文化中,汉代乐舞以其张扬阔大、发扬蹈厉的强悍风格独树一帜,堪称中华乐舞史的最强音。
对汉代乐舞的研究大多是通过汉画像石去还原当时的乐舞形态,进而阐发其中的历史、考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蕴涵。这方面的研究以萧亢达的《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1]最为全面系统,近年来相关研究基本仍在其框架下进行。如刘乐乐对河南汉代墓葬中的建鼓图进行剖析并阐发建鼓所具备的礼仪功能[2];相宁和孙汉明通过对徐州地区汉画像石及动态遗存形式的研究追溯了汉代乐舞的若干特征[3];尹德锦和唐丽娟通过四川汉代乐舞画像砖还原汉代乐舞“裙摆”的范式并阐发其文化精神[4];刘冠通过米脂县历年出土和征集的汉画像石中的乐舞百戏图像对汉代陕北地区民俗进行还原[5];周仪从文献和考古两个维度论述了胡汉乐舞文化相互交融的时代背景给汉代舞蹈的形制和审美诉求上带来的新变[6];郑亚萌较为系统地回顾了近30年来汉代乐舞的相关研究,并指出在汉代乐舞研究中主要用以作为论据的文献、图像和考古材料等三个方面都存在夸饰和片面的问题,各方面的信息整合因此显得尤为重要[7]。
然则是什么样的精神底座造就了汉代乐舞的强悍外观?迄今未有令人信服的专题研究和论证出现。我们认为,是根源于时代背景的人本主义精神的崛起及发扬光大,是在这种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辉映下的自信、自立和自强的民族特质,成就了汉代乐舞独特的盛大。
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汉初人本主义思潮的勃兴
所谓人本主义,系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曾有名言“对人类而言,人是神圣的”,被视为对人本主义的最简概括。从得名角度看,人本主义固然可追溯到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但以人为本的思想,实则与东方乃至中国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1)甚至有学者提出,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整体是“神本主义”的,而源起于西周宗法制度的中国古代哲学崇尚“尊尊、亲亲、长长”,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建立于西周初期的宗法制度,就强调“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则明确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同期的孟子更将人的价值置诸国家社稷之上,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本研究的人本主义所指,即为这种以人为本、一切归结为人力的朴素思想。
秦汉之际人本主义思潮得以勃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联:神权、贵族和宗法秩序的衰落和平民的崛起,使得成就的事功和人们的能力得以勾连,从而给社会带来一种全新的、基于自身能力的价值理念;终汉之世,无不在此价值理念的笼盖之下,这成就了汉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8]的民族特质;可以说,人本主义是成就强汉之音的精神底座。
随着科技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也与日俱增,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神权逐渐衰落,与之相匹配的森严社会等级秩序也逐渐瓦解。春秋时就常有“八佾舞于庭”这种令孔子愤慨不已的僭越举动;至战国时期更是礼崩乐坏,三家分晋、田陈伐齐,下克上成为常态。与神权衰落、礼崩乐坏相对照的,则是人本主义的萌芽,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既是对基于神权的礼乐宗法制度的冲击,也是后世各种人本主义和人文思想的滥觞。
秦灭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六国贵族被极大压制,他们和原先封邑内民众的主从关系至此趋于解体,从而彻底动摇了神权礼乐宗法制度的物质基础。在秦制下,天下万民,不为官吏,则为黔首,无论是在政治待遇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一视同仁(旧贵族实则更受压制)(4)六国原本的国君后裔,基本上都散落民间和普通黔首无异,最著名的是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在为项梁所立之前,只是个受人雇佣的牧羊人,后来被项羽所杀,也并没有激起什么波澜。如项羽所概括的,“天下初发难,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力也”,参见班固《汉书》。[12]796。与旧贵族的快速没落形成对照的是秦汉代立之际平民乃至贱民的崛起。这些社会底层人士在秦末的风云际会里趁势而起,没有土地、财富、徒众或声名的依傍,基本上完全凭藉个人的努力奋斗而成就了推翻暴秦、开辟新时代的事业。《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起义时号召徒众“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侯王将相宁有种乎”[13],可谓代表了平民乃至贱民出身的秦汉代际群雄的共同心声。流风所及,不重视门第血胤,而看重个人事功,遂成为汉初的主流价值观。与汉高帝刘邦共同开创汉代的功臣们,基本上是底层民众出身;迄至汉武帝刘彻时期的名臣名将,出身微贱而凭个人事功身居高位者仍不乏其人(5)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并曾经“徭咸阳”;汉初三杰里,除了张良是故韩贵族外,萧何是小吏;韩信“家贫无行……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他诸将彭越是强盗、英布先为刑徒后为强盗、曹参为狱吏、陈平是贫穷的自耕农、周勃是编蛐蛐笼子的匠人、樊哙是屠夫、夏侯婴是马夫、灌婴是布贩、郦食其郦商兄弟是无业游民。汉武帝时期的名将名臣,如卫青起于仆佣、张汤起于小吏、霍去病是私生子、商弘羊是商人。参见班固《汉书》高帝纪及各本传。,此时距汉开国已100多年了,但在上者不以为意,在下者也不以为奇,可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理念在西汉可谓根深蒂固。
出身微贱而以个人能力或事功得居高位,这在事实上打破了先秦神权宗法礼乐制度框架下不可逾越的社会等级秩序,而代之以(尽管未必自省)朴素的人本主义理念。事实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本身,就是西汉人本主义精神的最佳写照;当然,它更多体现的是西汉人对事功的崇尚和对个人能力的推崇以及对“此时此地”的强调(这也是当代人本主义的两大特征),是一种外放性的社会思潮,而非内省式的人格特征。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居上位者就理性而言无法认同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情感而言则不会喜欢那些鼓吹先秦礼乐制度的儒生(6)《汉书·郦食其传》记载刘邦“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汉书·陆贾传》则记载:“(陆)贾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参见班固《汉书》。。这也是以“定制度,兴礼乐”为特征的礼乐制度规范,终西汉之世几乎未得以施行的原因。
人本主义在汉初的勃兴,深刻影响了西汉乐舞的发展,从乐舞的规制制度、到其具体形制、再到呈现的内容,都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征。
二、郑声施于朝廷:人本主义在乐舞制度中的体现
人本主义精神对西汉乐舞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其规制制度上。
经历了战国攻伐及秦汉代立的历史大潮,所谓“古乐”早已流散殆尽。《汉书·礼乐志》载:“汉兴,乐家有制氏……但能纪其铿鼓舞,而不能言其义。”[12]483汉高帝刘邦“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12]483。所谓楚声,相对于周公礼乐制度里需要正襟危坐“端冕以听”的先王雅乐、雅俗之比,显然判若云泥;甚至比起孔子删削过的十五国风这种民间歌谣,楚声都属于新兴的边鄙小调,如下里巴人一般在楚地属而和者数千人的流行歌曲。然而刘邦不仅自己喜欢,而且剑及履及,时有自作;“风起”“鸿鹄”都是楚声。《汉书·礼乐志》载:“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12]484此后遂成定制。至于先王礼乐那一套,则无人问津,“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12]484。
4.3 加强护士的自身建设 积极引导护士完善自己的性格,在工作中控制自己的不良情绪,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同时,鼓励护士注意休息、合理营养、规律运动、发展健康的业余爱好,使护士保持心境开阔,降低应激反应水平以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
事实上,刘邦不仅喜欢楚声,还喜欢巴渝地区的乐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刘邦自汉中伐秦时,前锋部队中有来自阆中渝水附近的板栒蛮夷,“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14]。刘邦喜欢板栒蛮夷歌舞刚健勇武的风格,这正和他伐秦灭楚的雄心锐气相契合;至于武王伐纣云云,显系攀附之说,以此将自己抬高到周武王的地位、将汉军伐秦和武王伐纣相提并论。由此观之,宫廷乐舞之存留取舍,不仅有刘邦个人的喜好因素,还有时局政治的因素,至于乐舞本身是否符合先王规制,则并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比刘邦更进一步,汉武帝刘彻不仅是楚声的爱好者(其为李夫人所作的歌和赋[12]1727-1728(7)《汉书·外戚传》:“上(汉武帝)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其辞曰:……”。参见班固《汉书》。,都是楚声),更是各地民间乐舞的爱好者,他的这一喜好甚至成为西汉乐舞制度的一个驱动(8)。
《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2]484。郊天祀地应用先王乐舞是儒家经典明文规定的,《周礼·春官》明书“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15],奏、歌、舞一一对应,可谓泾渭分明、秩序井然。然而民间乐舞爱好者汉武帝完全置之不理,他专门成立了个乐府,专司赴赵、代、秦、楚等各地采风,搜集各种民间乐歌(讴);并且委任出身平民但个人专业能力突出的人士来改造这些乐歌素材,如让音乐家李延年主管“协律”、诗人司马相如“造为诗赋”。从乐府设立到最终成果《十九章之歌》,整个创作过程体现出乐舞应为人而作的精神和有能力者居其位的原则。
《十九章之歌》的艺术呈现形态虽早已散佚不可具知,但其感染力仍能从相关的史籍记载中推测一二。《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以此十九章“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12]484。能使数百人肃然动心,则《十九章之歌》的艺术感染力大是不凡;而这数百人品类不一、身份地位各自不同,可见《十九章之歌》是雅俗共赏、能接地气的作品,而非阳春白雪那种国中仅三数人能属和的蹈空之音。
有趣的是,《汉书·礼乐志》还专门记载了另一个事例以反衬汉武帝的“恣意妄为”:在他设立乐府搜集各地民乐时,河间王刘德专门进献了雅乐;但汉武帝对之并不感兴趣,只是下发给只是备位而已的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12]490,所谓关联治道、被先儒们艳称的雅乐,对汉武帝而言也就是起到充数的作用而已。
武帝在位时基本确定的以民间曲调搜集整理并搭配当代诗人填词的乐府制度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直到汉哀帝刘欣即位后,才下诏“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12]492;而此时下距西汉亡于王莽,仅12年而已。可见乐府制度及其主导的以“郑卫之音”为郊祭乐的乐制,自汉武帝首创迄至西汉亡,连绵不绝100多年,始终是官方钦定的主流。
东汉人班固作《汉书》,推崇儒教的礼乐教化,对西汉乐制颇有微词,以为“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2]491。“郑声施于朝廷”在儒教的语法体系里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指控了,但也说明了西汉一代上至皇帝和朝廷、下至民间和百姓的一个普遍共识:乐舞是为人服务的、为当下服务的,无论是基于人们的喜好,还是政治的需要,第一要求都是要让当代之人听得下去;雅乐虽好,在为时人接受方面既远赶不上“郑卫之音”代表的民间曲调和时人之作,则被束之高阁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三、一唱众和、以舞相属:人本主义在乐舞形制中的体现
两汉的乐舞形制,并非仅作观赏或展示之用,还拥有更广泛的社交职能,而这也是其人本主义精神的一个自然延伸。
西汉主要的乐舞形制“但歌”,据《宋书·乐志》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16],因其只有清唱、没有管弦或其他乐器伴奏,也被称为“徒歌”;后来加入丝竹伴奏和节,成为“相和歌”,其特征如《晋书·乐志》所载:“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17]这种有唱有和、一唱众和的表演形制源起于民间自娱性歌舞,在汉初已成为风靡朝野的歌舞形制。汉高祖刘邦在沛作的“风起”,至其子惠帝刘盈“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12]484,就是相和歌的形制;武帝刘彻作《郊祀歌》十九章用以在甘泉圜丘祭天,也是“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12]484。张衡作《西京赋》,有句“齐枻女,纵悼歌。发引和,校鸣葭”[18],可见有歌而必有和,是为定制。

与相和歌一唱众和相对应的,是舞蹈方面的“以舞相属”,舞蹈同样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载,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交恶、灌夫骂座的一段故事:三人共饮“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13]。灌夫起舞邀丞相田蚡同舞,田蚡拒绝,在社交礼仪上被视为当面侮辱,所以灌夫会当面怒骂。尽管此时灌夫已失官,是以平民的身份面辱高居丞相之尊的田蚡,但因田蚡失礼在先,倒也并未因此发作,穷治其罪,在窦婴代为道歉之后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由此也可见以舞相属确是一项重要的社交礼仪。四川彭县出土的汉画像石刻画了主客以舞相属的基本形态。其中主人居右,高冠广袖,右手举起,左手做相邀状;客人居左,双手前伸,长跪将起,做应邀而将起舞状;主客同舞,宾主尽欢,栩栩如生。
汉代许多文献也都留下以舞相属的相关记载。如景帝子长沙王刘发益封的故事:景帝召诸王来朝,令其称寿歌舞,诸王中唯独长沙王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可见歌舞不仅是社交礼仪,舞姿不好还会被人嘲笑。刘发后来以“国小地狭、不足回旋”为舞姿不佳的理由,反而因此谥封三郡,则歌舞不仅是社交礼仪,还成为与君上进行委婉沟通的方式。由此可见,乐舞之于汉人的世俗生活融入之深。
四、志尽于诗、音尽于曲:人本主义在乐舞题材中的体现
人本主义的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汉乐舞的发展,个性的彰显和胸臆的直陈共同构成了西汉乐舞的主旋律,而这在其选题和内容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
相比此前的宫廷宴乐,相和歌的特点在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里转引王僧虔的说法总结为“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19],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之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9]。其为永歌为舞蹈,源于言和嗟叹,而追本溯源则起于“情动于中”;诗歌舞皆源于情,正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以此为发轫,以“本于情”“感人深”为旨要,最终的呈现就是汉代乐府诗歌的“乐和民声”。
《汉书·礼乐志》[12]484-490抄录了上文述及的汉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人作词的《郊祀歌》十九章的歌词,其中不同程度涉及当代时事的几乎每章都有,至如《天马》十、《景星》十二、《朝陇首》十七等各章,更完全是时事直记。郊祀是祭天地的盛典,孔子所谓“天子所祭,莫重于郊”“郊所以明天道也”;可见在儒家礼法里,郊祀是用以推明天道的至要盛典。人君自居天子,则祭祀上天无不毕恭毕敬、诚惶诚恐,以歌颂天神威灵、感谢上天恩赐为主(10)参考周祭辞: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维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祜。。而汉武帝郊天,所用的音乐是采自四方的民间曲调,所用的歌词是时人配撰的时事新诗;而诸如“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兆民反本,抱素怀朴”云云,宣扬的是四海升平的文治之成;“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云云,夸耀的则是九夷慑服的武功之盛;全无诚惶诚恐的姿态不说,还颇有与天神比肩抗行的气概。《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讨伐大宛获得千里马名“蒲梢”,作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13],将凡马上拟天马,并自夸有德威灵,还引来汲黯的指摘。后人多称汉武帝郊祀歌辞多有游仙诗风格;所谓游仙,是以凡人而与神仙游,则神仙之于凡人,就不再是高不可攀只能仰望的神明,而是可以从而游之乃至与之等筹的对象了。汉武帝郊祀歌辞的游仙诗风背后的精神支柱,实为正在崛起的人本主义思想。
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人本主义思潮在西汉乐舞歌诗中的体现是遍及朝野全方位的,高至天子重典的郊祀歌辞,低至民间传唱的杂歌谣辞,无不彰显这一特质。《宋书·乐志》记载流传的汉魏相和大曲十五,其中九首是汉人所作,分别是东门(东门行)、罗敷(艳歌罗敷行)、西门(西门行)、默默(古杨柳行)、白鹄(艳歌何尝行)、为乐(满歌行)、夏门(步出夏门行)、洛阳令(雁门太守行)、白头吟。观其命名即可知其描述的大多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形态。
在人本主义主流思潮下,汉代乐舞歌诗中的神仙形象也不再是威严肃穆、高不可攀的神明,而是可以为凡人所接近甚至可以和凡人一同狎乐的“人”。游仙诗勃兴于汉,一方面是人的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则是神的地位的下沉,此消彼长,则双方乃得以并肩同游。试取相和歌吟叹曲《王子乔》一观:
王子乔,参驾白鹿云中遨。参驾白鹿云中遨,下游来,王子乔。参驾白鹿上至云,戏游遨。上建逋阴广里践近高。结仙宫,过谒三台,东游四海五岳,上过蓬莱紫云台。三王五帝不足令,令我圣明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当究天禄永康宁。玉女罗坐吹笛箫。嗟行圣人游八极,鸣吐衔福翔殿侧。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19]。
王子乔是著名的仙人,参驾白鹿天上地下一顿遨游后,“令我圣明应太平,养民若子事父明”,仙境人世无缝对接,对仙人逍遥生涯的描述和对人世君臣父子观念的宣扬乃至“圣主享万年、皇帝延寿命”的善祝善祷,自然地衔接在一起。在这首作品里,仙人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人间上下暌隔的神祗,而是融入到人间、充满人情味乃至世故的凡人形象。
张衡《西京赋》[18]提及盛行于西京长安的大型民间歌舞“总会仙倡”(11)“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砺激而增响,磅盖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欻从背见。熊虎升而挐攫,猿狖超而高援。怪兽陆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磷囷。海鳞变而成龙,状婉婉以昷昷。舍利飏飏,化为仙车,骊驾四鹿,芝盖九葩。蟾蜍与龟,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云雾杏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东海黄公,赤刀粤祝。冀厌白虎,卒不能救。挟邪作蛊,于是不售。”参见萧统《昭明文选》卷二《赋甲》[18]。,详细描写了仙人、异兽、仙禽的各种表演形态。所谓“总会仙倡”,就是由专业演员(倡伎)扮演的各路神仙,在这样的大型歌舞集会里,仙凡杂处,人兽同乐,无复仙人殊途之隔。
五、意气相尚、悲歌厉响:人本主义在乐舞审美中的体现
人本主义思潮对两汉乐舞的影响,还在于其整体呈现出的审美趣味,是一种崇武尚武、积极向上甚至“意气相尚、一意孤行”的气质。
早在秦末群雄并立时,崇尚个人武力就已蔚为时代潮流,在乐舞形制中体现为各种执械歌舞的兴盛。众所周知的鸿门宴中,“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13],剑舞就是当时十分普遍的一种舞蹈形制;两项所作剑舞,或许是在剑法套路外添加了一些舞蹈性动作以美观瞻,介于武术和舞蹈之间,项伯“常以身翼蔽沛公”,可见其实际杀伤性并不小。西汉时,剑舞逐渐演化成为类似杂技的一种艺能展示。张衡《西京赋》记述汉代“角抵妙戏”中曾提及:“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冲狭燕濯,胸突铦锋。跳丸剑之挥霍,走索上而相逢”[18]。四川大邑安仁出土的东汉“丸剑宴舞”画像砖再现了融入杂技的剑舞的具体形态(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张衡《西京赋》提及的这些杂技形态,归根到底都是以炫人耳目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力量或技巧,它们在两汉社会中广为流行,无论是贵族宴享还是百姓的日常娱乐都喜闻乐见,可见当时主流社会对尚武精神的推崇。此外棍舞(山东藤县汉画像石)、刀舞(山东曲阜东安汉里画像石)、干舞(山东微山汉画像石)、戚舞(河南南阳汉画像石)等,也都属此类。

图1 东汉“丸剑宴舞”画像砖(12) 四川大邑安仁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
当然,执械为舞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歌舞形制,而更多是执械将士融合了一些地方歌舞形态的率性动作形态,未必与音乐有什么内在关联;两汉乐舞最具标识性的乐舞器乐当属建鼓。
建鼓原本用于战场,是鼓舞将士士气的器具,早在春秋时期就广为采用 ,在战国时期逐渐演变成为乐舞的一种乐器。两汉时期,建鼓是几乎所有乐舞形态的核心,各地出土的大量两汉石刻砖刻画像,凡涉及乐舞场景的,建鼓都处于居中的位置(见图2)。关于建鼓的形制,两汉诸多石(砖)刻画像中都有体现:上有羽褒华盖 ,下有底座(跗) ,中有立柱(楹杆)上下贯通,鼓腔悬置于立柱中间偏上,两侧各有鼓手一人,相对而击。以建鼓为核心的乐曲,其音铿锵有沙场气息,自不待言;曹植《元会》描述了魏廷的歌舞情景:“笙磬既设,筝瑟俱张。悲歌厉响,咀嚼清商”[20],魏承两汉,相去不远,音乐风尚应该非常接近,悲歌厉响亦可移为两汉音乐的基调。以之为核心的舞蹈形态,根据汉画像推测,则多为且歌且舞,姿容雄健奔放,且多为男性形象,其尚武尚力的审美取向,可见一斑。
西汉开国后一百多年,内外战争时有爆发,内有七国之乱,外有汉武开边,在此背景下,个人勇力、尚武精神和阳刚之美始终占据社会主流审美取向,无论是执械作舞还是以建鼓为核心的乐舞形态,体现的正是这一以力为美的美学取向。
六、结 语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汉初人本主义思潮的蓬勃兴起以及其贯穿汉代,是解读汉代乐舞艺术形态和特征的一把钥匙;从乐府制度的创设,到乐舞本身的形制、内容、功用和审美,无不渗透并体现了人本主义精神的光芒。强汉之音之所以能以其发扬蹈厉而冠绝华夏三千年乐舞史,正是因为其背后是一个大写的人字。当前我国正处于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如习近平指出的“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脊梁”[21],要重现中华民族强汉时代的富足、文明和强盛,就须在微观个体上建立起自信、自立、自强的国民性格,就须在意识形态上培育起“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从这个角度看,两千多年前的强汉之音,堪称当代我国大国崛起的序章和前奏了。
———史敦宇艺术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