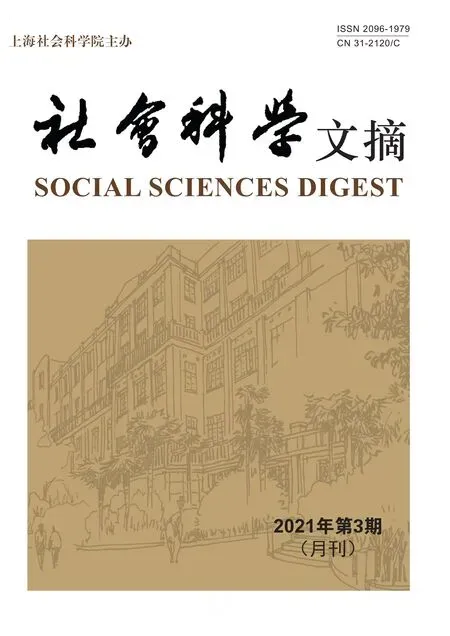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革命与建设的主从认识及其演进
“革命”与“建设”既是一对名词,也是一对概念。一般说来,名词和概念的产生是落后于历史现象的,但其产生之后又反过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且,其内涵常伴随历史的演化而可能发生变动,并影响人们对历史上与此相关现象的理解。“革命”和“建设”内涵的变化,就使得如何界定革命史和建设史变得比较复杂。
“革命”与“建设”概念辨析
就中国历史而言,“建设”的涵义争议较少。该词古已有之,表示设置、创立之意。近代以来,又有政权、党派开展自上而下规划发展之意,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等。尽管在革命时期也可进行建设,但建设更多是指和平时期的建设,其核心为经济建设。
如果说“建设”几为社会常态,而“革命”就意味着惊天狂飙,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人对此的理解是差别较大的。古代有所谓“汤武革命”,意味着改朝换代就是革命了。近代以后,到了梁启超那里,在汤武革命的基础上,增加了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几乎一切皆有革命。孙中山则将汤武革命视为“帝王革命”,而他领导的“今之革命,为人民革命……此种革命主义,即三民主义”。毛泽东认为历代农民起义都是革命,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到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如果只说“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三十年的历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他还从社会性质的巨变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革命,第一次为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第二次为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地主革奴隶主的命,第三次为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即辛亥革命。梁漱溟也认为,革命指社会的改造,像资本社会代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秦汉以后,一治一乱,改朝换代数十次,不见有革命,辛亥革命才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后唯一之革命。
可见,迄今尚无众所认可的革命史。然而,革命总有其根本特征,这就是颠覆性、破坏性、替代性,而现代革命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为激烈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及政权更替。依此衡量百年中国历史,大多会认可辛亥革命为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革命之始,其后的国民革命、中共革命也都属于现代革命。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国共两党是两个最为关键的革命主体。
由“革命”与“建设”两个概念的简单梳理不难看出,二者的涵义不仅各有其独立性,而且有一定的对立性,似乎是互不兼容的。以往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民众,恐怕大多也持此惯常的说法。然而,揆诸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的历史,无论是时人(包括革命领袖、政权要员和各界人士)的认识还是实距,革命与建设并不全是对立的,而是以革命为主、建设在革命之中的相互纠葛过程。在少数人的弄潮之下,无数人被裹挟到这一历史的激流中,无可选择,无处可逃。从辛亥鼎革到中共革命,不到40年的时间,但由于一直处于剧烈的政治巨变之中,可以划分为明显的四个发展阶段: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为第一个阶段;从1927年至193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为第二个阶段;从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为第三个阶段;从 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为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这一阶段的革命以孙中山为主导。辛亥革命虽以1911年为标志,但孙中山革命的起点是1894年成立兴中会。他一方面力主革命,推翻清朝,但另一方面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旧王朝的新政权。1897年他提出,“不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治,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不可能的”。1905年,他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这里的破与立之间,其实就是革命与建设的宏大联系。孙中山还特别强调建设的必要性,“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满洲政体“如破屋漏舟,必难补治,必当破除而从新建设”。以上论述表明,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孙中山就已经奠定了关于革命与建设关系的基调,既有二者先后相继的意识,也有齐头并进的意识,表述似有矛盾,实际上是以前者为主的。
其实,近代以来清政府并非全无作为,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都曾进行过现代化建设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然而,其现代化建设之举恰恰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它已无法阻挡辛亥革命的爆发,无法挽救清廷自身的崩溃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仅两月余,就让给了袁世凯。之所以如此,原因颇多,但如孙中山所言,一因“尽瘁社会事业。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也即他认为革命告竣,应集中精力投入社会建设,这一思想与当时社会各界的舆论是一致的。
不能不说北洋政府也是重视建设的,经济部门的领导者大多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乃至欧美留学教育,颁布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也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在政治上,由于袁世凯军阀专制愈演愈烈,孙中山连续发动反袁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又发动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并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不过,孙中山直至去世前,始终没有停止对革命与建设关系的思考。1917—1919年著成的《建国方略》,标志着其建设思想达到成熟,而且成为中国革命时期最为系统而深刻的建设思想。此时,他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仍保留了辛亥革命前的先后相继意识,将革命时期分为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宪政时期三个阶段,分别对应破坏时期、过渡时期和建设完成时期,但比以前更加强调革命与建设的并肩而进。《建国方略》中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何谓革命之建设?革命之建设者,非常之建设也,亦速成之建设也。夫建设固有寻常者,即随社会趋势之自然,因势利导而为之,此异乎革命之建设者也。革命有非常之破坏,如帝统为之斩绝,专制为之推翻;有此非常之破坏,则不可无非常之建设。是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
不是将革命与建设截然对立,而是破坏与建设为革命的一体两面,既有革命的破坏,也有革命的建设,革命的建设又分为非常的建设和寻常的建设,这是孙中山的新认识。据此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破坏的革命成功,建设的革命失败了,建设事业“简直一件也没有”,所以革命仍然是失败的。“革命要一直下去,到成功然后止。”实现三民主义,建设新世界的新中国,是防止以后再发生革命的基础。
遗憾的是,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忙,对“建设”更多的是思考,而无具体实距的机会。即便后来有广东根据地,也主要停留在政策、计划之中。不过其关于革命与建设的思想遗产对于国民党乃至共产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辛亥革命至国民革命北伐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1922年,中共受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召唤,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中共本有自己独立的革命主张,最初对其他党派采取攻击政策,但鉴于自己力量的弱小,还不能单独革命,加之与国民党有共同的敌人,随之转而采取了合作策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中,中共主要是起了配合国民党的作用。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中共还没有进行专门的思考,主要限于“建立劳农专政的统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的宏观叙述。
第二阶段:1927年至1937年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随着国民革命结束和国民政府的建立,国共由合作(或矛盾中的合作)转向对抗,台野之间展开巩固权力和夺取权力的斗争。尽管两党在反帝反封建上常有共同的表述,但在激烈的斗争中,都称自己为革命而对方为反革命。其实在第一阶段就已有了革命与反革命的舆论分野,但一般为革命者将革命对象称为反革命,而现在则是曾经的革命合作者之间互称对立面为反革命了。与孙中山时代不同的是,国共两党或为执政党或为局部执政党,都有了经济建设的舞台,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有了实距上的意义。
在国民党及其政府一方,对于建设的必要性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表达。最多见者是自称承继了孙中山的主张,认为北伐革命成功了,应该进入建设阶段。1928年蒋介石指出:“现在北伐总算是告一段落,今后就要将国家建设起来。”1931年他又指出:“在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之二大原则下,图存救亡,政府与国民实有同等之职责,而不能别其孰为重轻……故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界人士也有类似主张,如孙科指出,国民革命经过了数年间的大破坏工作,“时至今日似乎应该是开始建设的时光了……革命只是手段,只是过程,建设方是要求,方是目的……革命与建设打成一片的媒介物曰民生主义”。
如果说以上所谈是北伐成功之后必须建设,而另一种主张则是革命还没有成功,应继续进行“革命的破坏”,为革命的建设开辟道路。蒋介石曾说北伐革命成功了,但又多次表示革命尚未成功。如他在1934年指出,吾国革命“迄今尚未成功”,国民革命第一期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以后为第二期国民革命,革命事业进入更为艰巨的阶段。1936年他又表示:“现在我们革命尚未成功,总理和一般同志同学所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做了……务必赶上来负起第二期国民革命的使命。”
在此认识之下,所谓“革命的破坏”又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扫除官僚腐败,改革陈旧积习。持此主张者也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认为,北伐军事告终,但破坏工作尚未完成,官僚腐败、风俗恶习、鸦片流毒以及“心理”专制等都是影响建设的障碍,必须以破坏的精神消除阻力,否则建设就不易推行,革命就会失败。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谭熙鸿也指出:“应该下革命的决心,用革命的精神,打破各种困难,来挽救国家的危险。”他认为,尤其须以革命的手段,扫除腐败的积习。另外一方面,则是新的更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消灭共产党。国民政府参事程天放指出,共产党革命的“成绩就是破坏,单纯的破坏”,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只拆屋而不建屋,不能叫革命。国民党是为了建设而破坏,是拆屋建屋,要进行建设就必须扑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一切障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秘书邓文仪也认为,共产党“种种反革命的宣传……助长暴乱”,应集中力量尽快剿灭“赤匪”,使社会稳定,国民生活得以改善。此为先决问题,先决问题解决了,建设才能彻底进行。
在建设实距上,国民政府颁布了不少经济法规,取得一定成效,但距离期望值仍甚遥远。
与国民党相反,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背叛革命,“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自己成为唯一的革命党。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指出:“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所开始的革命。”1928年又指出,国民党说革命成功、建设开始的话都是欺骗民众的,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权才是真正的出路。不过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中共仍少有专门的阐述。如果说有所涉猎,仍主要是对革命目标或者说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关注较多。如1928年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为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1935年毛泽东也指出,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但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实,对于现时革命性质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关系是有一定的纠结的。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关于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逐步施行。中共对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主要表述为建设须服务于战争需要。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共中央也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且在革命战争的胜利中找到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
第三阶段:1937年至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
日本侵华将国共拉回到合作的轨道。两党都将对方既看成合作者,又将对方看成竞争者。两党之间,合作是主流,斗争和磨擦也没有间断过,而且越到后期越是激烈。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两党都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思路,只是在革命问题上暂时淡化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对立。
在国民党及其国统区政府一方,首先仍继续强调自己是革命者,认为抗日战争是一场革命。蒋介石做过多次表述,1938年指出:“这次战争实在是我们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的阶段,我们抗战即是为继续完成我们的国民革命。”1940年又指出:“革命虽有几十年,而至今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再不努力,还有多少时间容许我们来革命?”在《三民主义初级课程·革命建设》中,编者王沉、董德涵认为,中国的革命铲除了帝制推翻满清,是第一步;消灭军阀,1927年革命是第二步;抵抗外侮,“七七”抗战是第三步。可见,国民党所理解的革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
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如何理解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呢?前引《三民主义初级课程·革命建设》基本上可以作为国民党的代表性表述:革命不能等同于流血革命,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拆房子是为了建新房,革命必须包含建设,革命脱离了建设性仅是革命的一半,甚至变为革命的反面;抗战是毁灭侵略者毒菌的巢穴,而建国则是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以创造代替破坏才是真正的革命。1941年桂林《党义研究》杂志发表“本刊评论”也指出,革命的破坏是为了建设,只有建设才是革命大道。愈是努力建设,愈接近革命成功,建设的树立即是破坏的消灭。这一认识与此前几乎没有区别。除此之外,国民党还宣传建设服务于战争的关系。蒋介石就指出:“我们今后要完成抗战使命,得到最后胜利,不只在军事的胜负,而是以政治经济的建设工作如何,来决定我们抗战的前途。所以从今天起,我们同仁更应该从积极方面使精神物质都集中充实,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建设都能迅速发展。”事实上,国民政府在战时经济纲领的制订、经济行政机构的调整、经济法令的颁布等方面均对支持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共抗日根据地的扩展速度很快,远非苏区时期可比。关于革命以及革命与建设关系的论述比以前有所增加。首先,共产党也把抗日战争视为一场革命。毛泽东1937年指出:“中国的抗战是百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的。”1938年又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其次,对现阶段革命性质和未来社会前景的关系也大体延续了以前的思路,但有了新的概括。193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但中国将来一定要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1939年、1940年又进一步指出,现时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共产党人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真正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成为中共革命性质和革命目标的经典表述。
对于具体的建设,共产党依然将此作为服务革命战争的基础。1938年,毛泽东指出:“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1944年又指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政治、军事的确是第一的,但经济是基础。“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事实上,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减租减息、农村经济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第四阶段: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决战时期
日本投降,国共由合作转入新一轮互称反革命的决战。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国民党及其政府几乎乏善可陈,共产党则进入展望未来的阶段。
国民党仍称自己是革命的,并到了革命的最后阶段。1946年,蒋介石指出:本党革命最后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到这个革命最后的阶段,要和敌人作殊死的战斗。打破反革命的组织,摧毁反革命的势力,来达到实行三民主义的目的。到1949年6月,他承认国民党革命失败了,回顾了“民国成立以后,到今年民国三十八年为止,在这一段时间中,我们革命运动失败的经过”。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已很少在蒋介石的言论中见到。其他国民党要员偶有论及,但和以前变化不大,如国民党中央常委邓文仪指出,破坏是手段,建设是目的,革命的破坏与革命的建设工作须同时推进。革命的最后破坏工作,是消灭中共武装主力。革命大破坏亟待结束,革命大建设亟待开始,最终实现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叶青也指出,革命由破坏始建设终,破坏与建设不能绝对分开,破坏为前半段,建设为后半段,前期破坏多于建设,后期建设多于破坏。武力革命是旧时代的革命,已经过去,现在中国已到革命的建设阶段。
尽管国民党仍然强调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但实际上随着其军事失败,已陷入全面崩溃的危机之中。
如果说国民党自称革命到了最后阶段,而共产党则认为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1947年,毛泽东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由此拉开了国共决战的态势。对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共产党仍较多地描画未来的国家和社会蓝图,简单说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正如1947年毛泽东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后,要完成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1949年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在新民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仍充满着张力。
这一时期,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的思想依然持续。1948年,毛泽东指出,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才能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1949年他也指出,必须使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1948年切实提高一步,以“保障对前线的支援工作”。不过,随着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各方面建设的任务越来越重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史的结束,也降下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然而,革命与建设的命题并未随之而去。毛泽东说:“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大考已至,历史考验了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