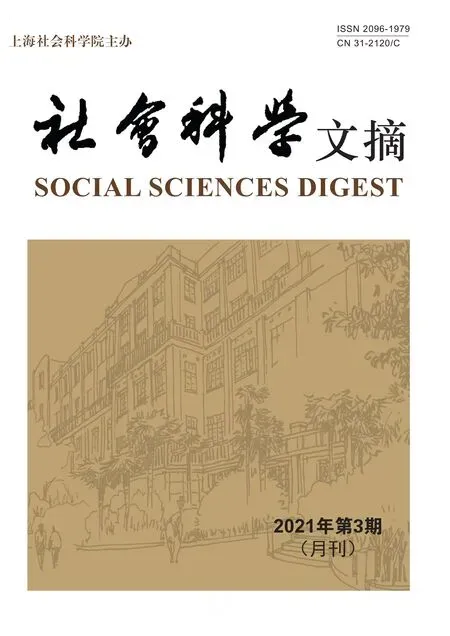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历史的假说
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说,虽然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完全是基于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战争的描述而作出的一种解读和概括。艾利森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概括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而且用这个概念来分析过去500年中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如果用“修昔底德陷阱”专指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那么未尝不可,毕竟古希腊时期的两个城邦国家的确因种种原因陷入了长期的战争。由于修昔底德详细地记录了这场战争,因此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概括,出于权威性、传播性和可接受性等原因,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艾利森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并不限于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而是用这个概念分析500年来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一个普遍现象而存在的,只要存在着“势力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就必然出现所谓的“陷阱”进而走向战争。很显然,这并不是一种客观事实。就正如艾利森自己所列举的16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并非所有的崛起国与守成国都会走向战争。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意义,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国际关系史上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退一步来说,即便“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能够用于分析所有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在使用时也不应自相矛盾。然而,从艾利森的著作来看,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有自相矛盾之处的。艾利森指出,修昔底德并不认为雅典崛起导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变得更加紧张,“让战争得以避免变得愈发困难”。既然如此,那么这个概念连用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上都成了问题,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概念了,更不可以用在分析其他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上。“修昔底德陷阱”能否成为一个概念,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本文认为:第一,战争与雅典势力的壮大没有关系,况且雅典在战争前的实力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公元前431年的这场战争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争霸战争;第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没有真正停止过,这场战争不过是希腊城邦之间长期战争的延续,斯巴达在摧毁了雅典之后,对不恭顺城邦的惩罚性战争依然在继续进行,因而当时的希腊并非只有两个势力中心,而可能是多中心的结构,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第三,认知往往是国家陷入“安全困境”的最重要原因,斯巴达对雅典乃至其他城邦的认知,对斯巴达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第四,归结起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用这个假想的概念来分析500年来国际关系史中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科学的。
“杜牧陷阱”:大国成长无法逃避的困惑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历史假说,那么艾利森用它来分析中美关系也就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会出现“不可避免的混乱”(包括爆发战争);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美两国陷入战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因为这显然并非明智之举”。退一步说,即便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很难符合国际关系史的客观实际。因为,假若存在“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则大国成长的关键是处理与外部环境(关键是与守成国)的关系问题。那就意味着,外部因素在大国成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纵观国际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内部问题才是大国成长的关键,笔者将此概括为“杜牧陷阱”。
何谓“杜牧陷阱”?这就需要研究战国时期六国为什么灭亡,以及秦国统一六国后为什么又很快倾覆的原因。唐代著名散文家杜牧在《阿房宫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这就是笔者所说的“杜牧陷阱”。它的意思是指,内部问题不处理好,必将阻碍大国成长进程,甚至导致国家衰亡。杜牧不是最早谈论此问题的文人,早在西汉,贾谊对此就有了深刻的见解。但是,杜牧这句话总结得最全面,也吸收了贾谊的思想。
当然,“杜牧陷阱”是否具有普遍性仍然需要验证,为此本文将考察古今中外大国成长的历史。首先我们以秦统一中国之前诸侯国博弈的情况来进行验证。三家分晋之时,智伯独揽晋国大权且咄咄逼人,赵襄子(无恤)何以能让赵氏不败,反而起死回生成就了赵氏立国?原因就是重视内部建设。一是重点建设赵氏封地晋阳。二是用好重要人才,使之为赵氏尽忠。上述两个方面都体现了赵国内部建设的重要性。而战国中后期,秦国攻打韩国上党,冯亭表示愿意把上党献给赵国。结果,赵国因贪图小利而轻信冯亭,让冯亭祸水东引成功,结果赵国一败于上党,再惨败于长平。长平之战,赵国因有廉颇坚守尚有胜数,但赵王昏庸临战换将且用错了人,用赵括取代廉颇,结果赵国惨败。从此,赵国由盛转衰,一蹶不振。此前,诸多谋士如公孙衍、苏秦等都积极拖六国合纵抗秦,尤其是在苏秦挂六国相印为从约长之时,使秦国多年不得出函谷关。然而,六国终究因各自偏爱本国之私而导致合纵解体,在秦国的攻击之下,六国只好割地自保。因此,六国之亡,从各国内部而言,弊在赂秦;从六国之间来说(也是另一种“内部”),在于相互之间没有信任。
我们再来考察近代国际关系史,历史也同样为“杜牧陷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首先,我们来看英国,在大多数人看来,英国的崛起源于对外的殖民掠夺。诚然,大英帝国的对外殖民掠夺为它的崛起提供了重要资源。但是,英国在对外进行殖民掠夺之前,就已经得益于自身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只是到了后来,大英帝国受内部资本逐利欲望的驱使而不断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掠夺,因而才出现了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纺织业的兴起”。大英帝国的兴起是因为工业革命,其衰落同样是因为工业革命。正是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蒸汽机的发明,使大量的民间资本都沉淀在钢铁和铁路产业之中。产业的泡沫化最终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正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了大英帝国霸权国地位的丧失,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加速了大英帝国衰落的进程。
其次,我们来看德国。德国崛起的前提是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统一虽然与王朝战争有关,但最重要的基础还是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在统一前夕,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变革开始影响战争方式,在这种技术条件下,普鲁士在19世纪60年代实现了“军事革命”。因此,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彰显的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很显然,军事制度是内部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可以从普鲁士的军队素质得到证明,即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使它拥有了高素质的军人系统和战斗部队。统一以后的20年里,德国抓住“工业革命”的“第二次机遇”,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一跃成为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先锋国”。进入20世纪以后,德国的力量进一步提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0年里,德国已经拥有了成为霸主国家的基本实力,才敢于对当时的国际秩序提出挑战。结果众所周知,德国遭到了致命的重创,德国经济雪上加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上台,对外推行武力征伐,力图改造国际秩序,尤其是要对欧洲继续“复仇”。结果,不仅法西斯被摧毁了,德国还被一分为二。很显然,德国的兴亡都因其内部因素所致,尤其是德国的灭亡,而外部因素只起到了加速的作用。
再次,我们来看苏联的兴衰。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崛起奠定了权力基础。但是,革命胜利之初,俄国的经济是十分落后的,在这种情形下进行巩固新兴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动员,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当时的苏共(布)能够用以进行社会动员的资源主要还是软实力资源,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制度的巨大吸引力、苏维埃体制所彰显出来的巨大魅力、和平外交和以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正是在强大的软实力资源的支撑之下,人们及所有的社会资源才被动员起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之中去并取得伟大成就的。而关于苏联的崩溃,认为主要是西方和平演变和两种制度的斗争的观点还是颇为流行的。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了苏联的内部,这种观点以俄罗斯自己的学者为甚,特别是有学者认为苏联经济不及美国却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最终苏联被拖垮了。更有一些学者从苏共内部体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认为苏联体制上的个人崇拜、“大清洗”运动、高度集中的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失误,以及苏共内部的特权阶层等,都销蚀了苏共的执政合法性。距离苏联解体的时间越久远,学术界的研究越集中在苏联体制问题上。
综上,无论是中国古代诸侯国的兴衰史,还是世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都表明内部因素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外部力量只是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条件,有时候可以成为推进国家发展进程的加速器。也就是说,“杜牧陷阱”是大国成长进程中具有普遍性、绕不开的困惑,只要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大国成长进程就会被打断。
“杜牧陷阱”与大国相处之道
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相处首先是要尽可能避免“安全困境”。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指出所谓“安全困境”就是指一个国家谋求加强自身安全的措施,却不经意地威胁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而所谓“不经意地威胁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安全”往往源于其他国家的认知,因为一个国家的友好与否,一般都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内政外交的认知。温特(Alexzander Wendt)指出:“无政府状态在宏观层次上至少有着三种结构,属于哪种结构取决于什么样的角色——敌人、竞争对手,还是朋友——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会引发其他国家的不同认知;同样,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也会影响本国的对外认知。鉴于此,基于信与义之上的认知才是大国相处之道。雅典与斯巴达的关系也体现了认知在大国相处之中的关键作用。
大国相处之道就应该是努力构建基于信与义之上的积极认知,这一点对崛起国而言尤其重要。因为,崛起国的任何对外言行都会引起守成国及其盟国体系的高度关注和戒备,守成国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如果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原本就没有建立信与义,那么崛起国的对外言行必然会导致守成国的负面认知。当然,一个大国如果无法处理好自己的内部问题,那么内部问题就很容易演变为一个国际性乃至世界性的问题。对于其他大国而言,内部混乱的大国对国际社会是一种威胁,也会导致大国之间产生负面认知。此外,崛起国究竟如何处理守成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既得利益同样很关键。崛起国对守成国的尊重主要表现为:一是利益尊重,二是地位尊重,三是对其既有国际权威的尊重。这就意味着崛起国的崛起方式非常关键。关于崛起国的崛起方式,笔者曾提出了两种方式:制度性崛起和工具性崛起。所谓“制度性崛起”,是指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既注重自身实力的增长与其内部制度的协调性,又注重自身实力增长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性。所谓“工具性崛起”,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成长是建立在某种或某几种实力提升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
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是消除信任赤字
艾利森在分析了500年来的“崛起国综合症”和“守成国综合症”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但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原因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潜在压力为那些偶然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引发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艾利森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历史来看,中美之间偶然性的事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都发生过,如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但都没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的冲突,这些事件都在双方的携手合作之下得到了妥善处理。这说明中美双方如果相互信任,中美关系是可以在正常轨道上驶向未来的。
那么,当前中美关系的问题究竟出在何处呢?中美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是无法克服的。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时,学术界往往都会从上述的差异性去探究原因,而且很容易找到证据以证实上述观点。然而,对任何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历史的回溯。从中美关系的历史来看,似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导致中美之间的不合作,相反在中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双方表示出强烈的合作欲望,且为寻求合作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从这些情况来看,中美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是一直存在的,但为什么那时候两国都不约而同地寻求合作并且实现了在差异下的携手合作?为什么在上述差异继续存在,且双方已经经历了深度合作,形成了诸多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却越来越大?这显然不是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所致,而是双方的信任问题,并因信任问题产生了非友好的认知。由于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客观上构成了两条方向相反的曲线,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治家都认为,美国相对衰落的原因是中国的崛起。这样的认知框架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和扩大相互之间的信任鸿沟。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信任“赤字”究竟来自何处?
笔者认为,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仍然来自各自内部,而不是外部。从美国的角度而言,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守成国对于可能丧失主导地位始终怀有担心与忧虑,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主导国都有这种担心与忧虑。即便没有崛起国的挑战,这种担心与忧虑都普遍地存在于霸权国、主导国内部,是内部一种固有的集体心理。其二,这样的心理潜藏在民众、社会之中,一旦被政治、学术、商业精英激活,就很容易转化为对对象国(可能是不友好国家,也有可能是新兴崛起国)的敌视,从而使民众对抗对象国的心理更加强烈。其三,这种心理在国家的国际地位下降的时候,往往会转化为文化和对外政策上的保守主义。美国自身的衰落和对衰落的忧虑,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且日益侵入其社会的骨髓之中。因此,美国对外界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不可能有信任感,只会强化彼此之间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性,从而使对华认知进一步走偏。这种认知的直接表现就是“中国威胁论”“致命中国论”。由此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依据不在于中国是否崛起,而在于美国自身内部问题(包括制度性的偏见、文化以及由文化变化导致的国民心理变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也是源于中国内部,其次才是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鹰派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对美国的认知产生了负反馈。实际上,在中美建交后的40余年里,无论双方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有多大的差别,至少到2018年中美贸易纠纷爆发时,中美两国的合作依然是大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美国学术界和舆论界制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问题话语。作为回应,中国学术界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活跃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诸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等著作,以及具有自负型民族主义情绪的影视作品。然而,中国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自负型民族主义则是对西方建构中国问题话语的“正”反馈,是对西方国家关于中国问题话语的一种“回飞镖效应”。当然,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原发性”民族主义,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原发性”民族主义则带有非常强烈的悲情色彩。这种悲情民族主义对外则会转变为“排外性的民族主义”。以上两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对美国认知的重要依据,也是从中国一方来检视中美之间产生信任赤字的原因。
另外,中国对美国的信任赤字也来自中国对美国的预期。中国对美国的信任预期,是建立在中国的实力和能力之上的,而不是依赖于信任客体的状况。在中美的信任框架之中,中国也是先对美国怀有信任,然后才对美国产生信任预期的。随着中国实力和能力的增强,中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眼光来认识世界,为促进世界携手合作而不懈努力。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对美国的认知目标是:美国与中国共同推进世界和平发展。然而,中国对美国的认知目标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目标产生了严重背离,大多数学者乃至政治家都情愿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去寻找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旦双方都接受这样的认知,那么双方的分歧将进一步拉大,矛盾和冲突也会加剧。假若双方都铁定要“脱钩”,或全面走向所谓的“新冷战”,那么双方就会更加强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差异与分歧。但是,如果双方内心都觉得对方是合作的伙伴或者是竞争性的合作伙伴,只是暂时无法寻找理由妥协,那么各自的智囊就应该挖掘双方过去的“深厚感情”。因为,曾经共同的经历与历史上的友好合作,也会在某种环境下重塑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最终帮助彼此消除信任赤字,走出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