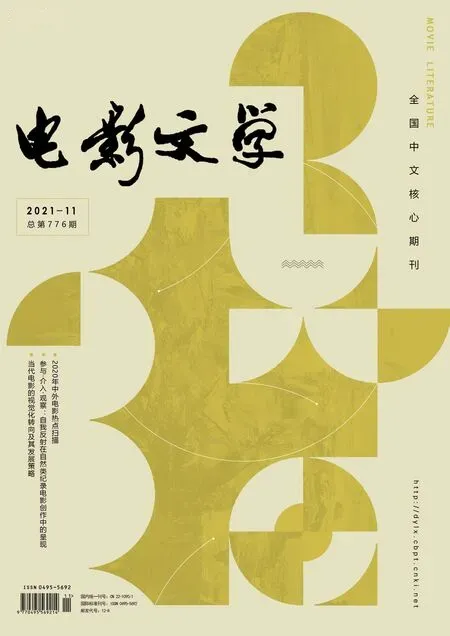2020年中外电影热点扫描
沈 鲁 徐国庆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一、国际:底层关怀、战争反思、女性困境
(一)奥斯卡的“人文关怀”
2020年奥斯卡奖的最大意外当属韩国导演奉俊昊的作品《寄生虫》拿下最佳电影、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国际电影四项大奖,成为本届最大赢家。这是奥斯卡有史以来第一部非英语获奖影片,也是韩国电影百年来结下的一枚硕果。1919年《义理的仇讨》的上映,被韩国政府公认为“韩国电影的诞生”。百年来韩国电影历经诞生期(1919—1945)、恢复期(1945—1960)、崛起期(1960—1998)和全面走向世界市场(1998— )四个阶段。以1999年姜帝圭导演的《生死谍变》为标志,多年来在韩国政府持续性的电影政策扶持下,韩国电影一举逆转了本国电影市场长期由好莱坞电影一家独大的格局,韩国电影在本国及亚洲市场的崛起,为其向国际化迈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得益于韩国电影成熟的工业体制,《寄生虫》表现“贫富差距”的常见主题,却在叙事节奏上显示出了导演相当成熟的类型范式驾驭能力。电影在两个家庭的选取上有很强的象征意义,使其跨越国界而几乎令每个观众都能从中感受到自身的困局和尴尬。电影能得到奥斯卡的青睐,除了成熟的叙事,还与美国的政治生态有着密切关联。好莱坞一直被认为是左翼电影的大本营,大批电影艺术家对底层人士和弱势群体投以深切的瞩目,如近年来的《丹麦女孩》《聚焦》《绿皮书》等入围或获奖作品,都曾以不同方式对同性恋、儿童和黑人等弱势群体进行写实关照。而《寄生虫》在贫富差距的两极对立中对社会生态的巧妙嘲讽,恰好映照了美国当下的现实环境,因此也可以将《寄生虫》看作是一部符合奥斯卡“政治正确”的作品。“贫困”主题早已屡见于中外电影作品中,但通常电影对“贫困”的书写更多是一种基于现实困境的展露和反思,而无法给出简单明确的答案,对“贫困”本身的理解也是这部电影在艺术文本内涵上最耐人寻味之处。
如果对《寄生虫》的审视更多基于魏伯·司各特总结的西方文艺批评五种模式中的“社会批评”,那么另一部由萨姆·门德斯执导并获得奥斯卡十项提名的《1917》则应当从“形式美学”角度来审视并解读。电影的最大特色莫过于伴随两位男主人公穿过壕沟、越过战区的“一镜到底”。门德斯对战争片有两处设计使其有别于传统好莱坞范式的“战争片”。首先是极简的声画处理,退去震耳欲聋的官能刺激,拍摄出一部不算喧嚣的战争电影并非易事。门德斯选择以长镜头创造沉浸感,配合着壕沟——这条非生即死的单行道,用两个小兵的故事塑造了极为残酷逼真的战争环境。在这种沉浸式的影像中,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形式带给观众的心理体验,这种形式美学也给国产电影的形式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即如何让观众透过视觉呈现进入具体的时间,而非使电影成为停留在暴力美学、官能刺激层面的消费娱乐品。其次是题材的选择。比起《血战冲绳岛》《虎口脱险》《珍珠港》等二战题材电影的繁荣创作,一战题材由于不太涉及正义与否,没有鲜明的对立双方,因此更加考验导演对战争本身的思考。只是不同于《拯救大兵瑞恩》,《1917》里的两位年轻士兵执行的是“以两人救千人”的艰巨任务。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门德斯借助人物内心不断传达“荣誉与生命孰轻孰重”“战争是否本无意义”的批判反思。人物弧光也不在于“传奇”式的个人英雄,而是小人物的生命在战争中的脆弱和挣扎,这也对国产战争片予以新的启示。
(二)柏林国际电影节:人性困局
新世纪以来的柏林国际电影节一方面延续了一贯对意识形态和严肃人性道德主题的青睐,同时也加大了对在政治底色下小人物生存境遇的关注与转向。
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的《无邪》似乎正是一部具有着浓厚“柏林风格”的影片。抛开文本本身,单就导演拉索洛夫所处的特殊环境及其自身的曲折经历,电影的存在或许已经超过了其价值本身。这是伊朗电影在《一次别离》和《出租车》之后第三次摘得金熊奖。不了解伊朗电影的观众或许会认为电影中所表达的极端个人生存状态不过是又一部迎合西方电影节对第三世界国家“他者”想象的逢迎之作,但当观众了解到以阿巴斯为首的伊朗艺术电影导演多年来大胆挑战禁忌,试图以电影冲破体制环境所做出的努力时,才会体会到《无邪》真正的价值,也会敬佩柏林电影节一贯秉持的开放的立场和国际视野。电影名为“无邪”,可恰恰讲的却是罪恶。无邪与罪恶的关键在于,面对他人的苦难,我们是选择起身反抗,还是背过身去。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用“平庸之恶”一词给出了答案,她认为比“集权之恶”更加严重的是“这种不思考所导致的灾难,比人类与生俱来的所有罪恶本能加在一起所做的还要可怕”,它体现为一种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绝对服从,并在此之下思想能力和个人自由的完全丧失。《无邪》中四个死刑执行犯的焦虑与痛苦,恰好在于如何使自身臣服于“平庸之恶”,并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自圆其说。电影中的四个人面对绝对权力,有人麻木,有人逃离,有人挣扎,四组任务群像巧妙地串联了每一个人,这是伊朗人的困苦迷茫和焦虑,或许也映照着世界上的许多人。
回顾世界电影史,每一次新运动、新思潮的兴起总离不开对女性境遇的关照、想象与关怀。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特殊时期,电影艺术的转向更加离不开对女性的摹写。导演伊莉莎·希特曼的《从不,很少,有时,总是》以未成年女性“残酷的青春记忆”为母题,以一种人文关怀和救赎意味窥视着美国未成年少女的世界。这部在柏林电影节斩获评审团大奖的作品有着传统女性主义电影对男权世界的厌恶,也涉及对“堕胎”等青春禁忌的冲破。影片并未展现出一种超乎常规体验的残酷和用力过猛的呈现,更多是在一种凝视下的温和鞭笞。如今的女性电影似乎已经告别了《末路狂花》时期对于男权社会强烈的反抗与冲破意识,这部作品中多数女性对已然成风的性别歧视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在男权侵犯之下表现出默认乃至主动迎合。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女孩在做心理咨询时,她的回答只有“从不,很少,有时,总是”,这暗示着女性在当代社会的失语,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她所面对的咨询师,也恰好是一名女性。
对“性别与种族”等公共政治话题的青睐,在二元思维之外的对人性复杂性探讨,让2020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继续保持了它基本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尊严。
(三)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华人女性艺术家的生存探索
2020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是华人女性导演崭露头角的一届。首先是由华人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获得金狮奖最佳电影(该片同时斩获2020多伦多电影节人民选择奖和2021金球奖最佳剧情片和最佳导演奖),这也是首位华人女导演的作品获此殊荣。抛开外界对导演身份的争议,从她的《骑士》开始,这位华人女导演的创作呈现出清晰的反类型倾向。《骑士》场景依然是传统西部片一样蔓延的高原、苍凉的黄土,但骑士已经不是曾经的正义使者和西部英雄,男主人公——一位脑部受伤的驯马师,因身体伤害呈现出英雄迟暮的失落感,他用摔跤、骑马、文身显示自身男性身份,同时也在挥之不去的孤独中寻找着自我身份认同。而《无依之地》延续了这种孤独感,镜头伴随着内华达州下岗女工弗恩一路开着房车横穿西部,通过弗恩的一系列所见所闻,跟随不同人物内心求索关于生命和人生际遇的答案。驯马师和下岗中年女性这两类截然不同的群体,他们自我迷失的困局和对身份认同的渴求很容易与观众发生共鸣。无论是《骑士》中驰行草原的马还是《无依之地》中不断变换目的地的房车,两部作品的人物都在迁徙中寻找着生命的归宿和意义,显示出这位年轻的华人女导演对个体生命体验的持续关注。对个体命运的存在价值和永恒意义的追问看似是电影艺术的及格线,但真正纵观中外电影发展史,不难发现许多电影还徘徊在这条及格线之外。在此高度上,赵婷作为年轻导演无疑做出了积极尝试。
(四)戛纳国际电影节:商业大片的突围
在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中,戛纳国际电影节对电影产业化发展的推动、新人力量的挖掘和各国本土艺术特色并重而使其具有相当的分量。而向来以具有深度哲理思考和艺术气质为取向的戛纳电影节中,商业类型片的突围则值得关注。
延尚昊凭借《釜山行2》再次入围戛纳,电影虽名为《釜山行》续集,但整体呈现出的更像是前作的拓展影片,由于前作在人物塑造和剧情上都有了较强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续集的拍摄难以复刻旧有套路。因此《釜山行2》选择好莱坞大片“任务主导”的剧情推进模式,显示出了韩国电影成熟的工业模式带来的优势。剧情上以在丧尸灾难中存活并流亡海外的男主角回国“寻金”为线索,剧情跟随着男主角在遍布丧尸的人间炼狱半岛中纠缠厮杀。无论是形式层面还是故事脊椎,《釜山行2》都是一部为普罗大众制作的商业大片。当观众从形式艺术的角度审视此片,必然会发现电影对叙事的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长镜头、荷枪实弹的打斗和追车戏码。而对于角色塑造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整体观感与好莱坞灾难片几无差别,尽管有延尚昊作为前作导演保驾护航,整体仍然不尽如人意。但前作当中还有开放式情节和人物走向值得发掘,这也让人对《釜山行》系列仍然有后续开发的可能有所期许。
此外,《薄暮之间》《心灵奇旅》《阿雅与魔女》等为数不多的商业电影入围“戛纳2020”,也显示出该年度戛纳国际电影节虽然在特殊疫情时期缺席线下活动,但依旧以“戛纳2020”的关注进一步标签化了自身对世界电影艺术旨趣的新转向。
二、中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蓄势待发
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曾推断:“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上的更显著的社会转型同步。”这对2020年的中国电影行业而言或许是一种启示。从2020年年初《囧妈》与西瓜视频合作创造疫情之下新的观影模式,院线放映与线上播放的复合观影形式构成了特殊时期中国电影放映的特殊景观。截至2020年底,中国电影创下204亿元年度总票房,位居世界第一,这样的成绩不仅是市场和票房意义上的,更显出2020年的中国电影在特殊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推动着国产电影在内容创作上新的表达。
(一)“国庆档”的家国情怀
2020年院线电影从暑期开始恢复,“十一档”开始全面复苏。在电影院上座率不得超过75%的防疫规范前提下,国庆档票房突破39.53亿元。与2019年相同,2020年的国庆档依旧称得上“新主流大片”的高光时刻。
在年初一预售后又撤档延期的《夺冠》卷土重来,成为“国庆档”开门之作。已经在《我和我的祖国·夺冠篇》中对中国女排夺冠的激情瞬间有所体验的观众依然显示出对这类题材的热情,这其中有陈可辛作为“后CEPA时代”中国香港导演的号召力以及女演员巩俐的个人魅力,也有故事题材本身作为家国圆梦的历史记忆在观众心中激起的持续的个人情感共鸣。电影前半段可以看作“郎平传”,随着影片推进,一个个女运动员的名字开始出现,这其实印证了不同时代体育精神的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大国精神”到如今的“个体绽放”,个人在历史体验中的真实情感得以被重视和书写。影片借助个体表现体育精神,又借体育渗入个体精神世界,与西方体育类型片有本质区别,其中传达的女排精神是一个结,以自我的绽放串起民族之魂。陈可辛在叙事上的把控功不可没,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过电影应当是一个能够讲好故事的工业产品,从《中国合伙人》到《亲爱的》,他在与内地电影人的合作中日渐熟稔于能使两地观众产生情感共鸣的制作范式。《夺冠》以两个人物、三次比赛架构起整部电影,戏剧节奏和情感高潮安排得当之余,又将人物与时代紧紧咬合,将个体生命与国家精神联结,使《夺冠》既非概念化观念输出,也未沦为一般的工业体制产品,是“新主流大片”的又一次有益尝试。
《我和我的家乡》和《一点就到家》可以称作国庆档中的“返乡题材”。相比《我和我的祖国》的历史记忆回溯,《我和我的家乡》回归现代,以五个板块涵盖农村医保、文旅、乡村教育、脱贫致富和环境治理,拼接出一幅完整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发生和即将实现的未来图景。电影人物涉及网红电商、旅美教师、普通市民等各色小人物,仍旧以《我和我的祖国》集群创作模式让观众在同一作品中感受到多种风格的艺术形象。《一点就到家》无论是剧情还是陈可辛监制都使电影带有乡村版“中国合伙人”的色彩,由三个年轻人下乡创业构建起的故事使电影在“返乡”基础上又具备了“青春”“励志”等多重元素,用年轻人的热血冲撞从乡村扶贫、电商、互联网等热点揭开乡村变迁、现代化建设的新面貌,也以新一代青年人的视角引领社会对乡野认知的重构。改革开放40年来的人口流动更多是乡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西方社会对“乡村”的概念仅是农业的产业承载地,但中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乡村”则被赋予了生态、生活与文化等多重含义。2020年是中国乡村的承上启下之年,国家第一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进一步提升城镇化比例,这个节点上重新审视中国的城乡关系则显得尤为重要。正如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终究是乡土性社会,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踽踽独行了数千年的乡土文明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乡村文明有条件在特殊的时间拐点上积极参与市场体系,并反过来实现对城市经济的牵引。《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等作品站在新型城乡关系建构的角度,通过一个个饱满的人物、鲜活的故事引导观众思考:当西方先进文明的光环逐渐退去,未来的中国故事的书写是否还会是“金融创新”“资本垄断”?或许历经岁月淘洗后的中国乡村,能够为这个故事写下新的一笔。在此意义上,以《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为代表的“国庆片”,是“政府、制作方和观众的集体合创成果,也是我们不断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产物”。
(二)“新主流大片”的范式与创新
《急先锋》《八佰》和《金刚川》无论类型范式还是家国同构的主题都是观众熟悉的“新主流大片”形式。受《我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冠》国庆档三巨头的影响,经典“香港警匪+内地家国情怀”模式的《急先锋》,哪怕有老将成龙和人气明星杨洋、喜剧演员艾伦的多重加持依旧未能成功突围。曾几何时,成龙银幕形象已经悄然实现从“功夫小子”“孤胆英雄”的个人英雄到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的转变。成龙在电影中的国际警察角色更多是“任务推动叙事”的执行者,人物光环不在于个体拯救世界的天赐神力,而是一种家国使命感的承接。即便枪战元素、跨国叙事、追车大战等常见的港式警匪片戏码依旧在电影中处处可见,但如今的受众群体已经悄然更迭,旧有的类型模式已经不再为新一代的受众群体追捧。“功夫巨星”光芒的渐趋暗淡,令人怅惘的同时,想必也会令与内地合拍的香港电影人从困境中思索出一条更符合年青一代欣赏品位的警匪片新范式。相比之下,2020年末上映的《拆弹专家2》同样是经典港片故事范式,以7亿票房进入年度票房前十。《拆弹专家2》的成功除了因为享有前作的红利,更重要的是电影在保持经典“港味”的基础上讲述的不是英雄主义执行国家任务的宏大主题,而是在惊险的警匪较量中关注个体内心与社会公序的矛盾。这种个体的矛盾性消解了英雄主义光环,从而与观众更加贴近。而电影中潘乘风“失忆”“恢复记忆”的一系列过程以强戏剧性吸引着观众,最终潘乘风牺牲自我拯救香港城市也使小人物在最后一刻完成了英雄主义的升华,这样的自我救赎过程目前看来更具有观众基础。
单从作品本身的历史存像意义来看,《八佰》与《金刚川》的确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而从电影艺术文本的角度上讲,两部作品在精神意象的构建、家国主题传达和宏大历史的架构上都往优秀战争片迈进了一步。无论是《八佰》中的白马、国旗和《金刚川》中的木桥,都能看见管虎在营造战争场面真实感和制造官能刺激的同时,从精神意象层面对主题升华做出的努力。尽管《八佰》和《金刚川》以及《紧急救援》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但无论是历史记忆还是现代叙述的“新主流大片”在口碑与热度上都较前些年呈现式微征兆。《紧急救援》尽管仍旧是以真实社会事件为基础、国家任务为主导的家国题材,却没能延续林超贤《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热烈反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电影故事“三段式”的重复续写,板块断裂感强的叙事缺陷;另一方面从《烈火英雄》开始,此类题材就已经显现出同质化的倾向。同时当下“新主流大片”题材更多局限于国内新闻事件和重大任务,“在地化”风格明显,也使得这一类型在海外传播中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未来“新主流大片”在进行题材类型多元化选取的同时,还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关注海外观众喜好。而2020年9月上映的由迪士尼改编的真人版《花木兰》,可以看出海外制作公司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兴趣,这也可以作为未来“新主流大片”的创新方向。
未来的“新主流大片”,应当在真实历史的碎片中以现实主义为原则、以集体主义和家国情怀为内核,用更加多元化的类型范式实现对历史的艺术化重构,在商业元素与家国形象传达之余,引导观众对历史及现实困境的反思。
(三)张艺谋和《一秒钟》
2020年,无论是警匪片《坚如磐石》还是充满悬疑色彩的谍战大戏《悬崖之上》都是年过古稀的张艺谋积极求变的成果。而年末《一秒钟》的上映,则让许多观众看到了一个返璞归真的张艺谋,一个阔别已久、令人备感亲切的张艺谋。
无论是视觉造型或叙事,《一秒钟》都给人洗尽铅华的凝练感。早期的张艺谋擅长为电影做减法,对莫言、苏童等小说家的作品改编都在极力去杂留纯,得益于那时的积淀,才使我们看到了《一秒钟》的极简之美。影片以西北农场的一场电影放映为开端,以一盒胶片串联起劳改犯和小女孩这两位时代的“边缘人”。简单的色彩、场景和人物,将特殊时代里小人物的卑微与挣扎娓娓道来。电影于张艺谋而言是缅怀了一个逝去的时代,于年轻观众而言,电影中的时代则是一个陌生又令人充满好奇的时代。那个年代里的人为能看一场电影狂热不已,甚至愿意贡献物资、吹捧放映员、配合放映员撒谎,严肃中带着荒诞。而电影中最吸引观众的场景不是比肩接踵的放映场,反而是躲在银幕背后或坐在影院外的劳改犯、张闺女这些“无名之辈”。一个时代值得被铭记和歌颂的只有“英雄儿女”,而小人物在历史的放映机里只有“一秒钟”,随即被掩埋在黄沙尘埃里。张艺谋重新走入黄土地,带领观众回到了充满集群仪式感的“胶片时代”。电影之于那个年代的人犹如身处黑暗的人仰望星空,他们渴望着电影丰富匮乏的精神生活,“苦难中带着希望”是张艺谋为那个年代写下的最深刻的注脚。“一秒钟”的时间概念如同一部电影之于一个人、一个人之于一段历史一般短暂。当人们因疫情不得已停下脚步,《一秒钟》在2020年末带领观众抚今追昔进行集体记忆的历史回溯,显得恰如其时。
2020年已经过去。在以“全球疫情”为最大主题的2020年,包括中外电影行业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受到深远影响,但在这深远影响的背后,不变的是观众和电影艺术工作者对电影不懈的热爱。2020年的电影行业:从不停止思考,很少耽溺不前,有时驻足凝视,但总是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