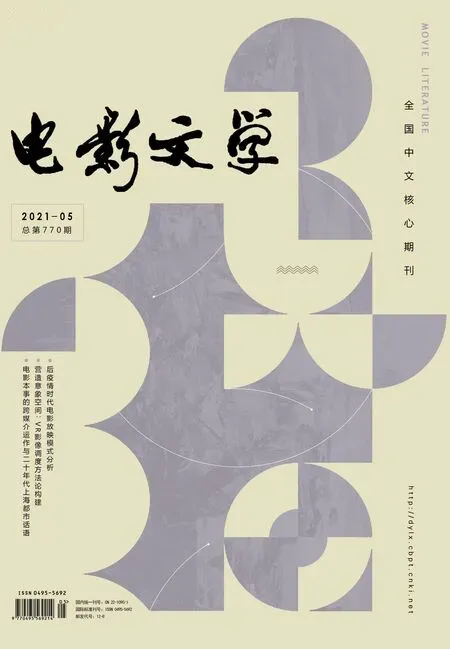《花木兰》:东方想象与文化误读
郑 敏/Zheng Min
一、文本与文本之间:花木兰的文本流变
花木兰这一人物,实际上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为宣扬女性传统道德所产生的人物。至于历史中是否确有其人或者历史中的花木兰的人生经历是否全然符合目下的再次创作,实际上还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和理解。但是不论人物与故事的真实如何,这一故事早已流传到了每一个中国家庭当中,成为一种具有相对广阔的阐释空间的叙事文本。从本质上来说,这个叙事文本本身是非常不稳定的,它甚至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性文本具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极容易受到外部阐释观念的变化影响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同的文化视野下,这一故事的改编也就更加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性。在表演形式上,也有很多关于此人物的作品问世,比如芭蕾舞剧《花木兰》、戏曲《花木兰》、电视剧《花木兰传奇》等。
从有关的作品来看,叙事文本主要重视人物的忠孝观念,实际上是试图反映出带有宣传色彩“谁说女子不如男”这一朴素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故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编文本当中,这一颇具我国民族传统生活观念的故事逐渐被赋予了更加多元的社会发展观念,相比早期的《木兰辞》,这些作品增加了很多民族之间关系的思考、女主人公在参加战争的过程中所收获的爱情以及为这一人物赋予更多的身份定义,从而使其长时间地处在个体身份困扰的过程中。
实际上,从这些文本之间的共同特点来看,这一故事的转变实际上伴随着对主要人物的重新书写和定义,这一点在任何一种文本的自身流变上都能够直观地体现出来。而花木兰的这一文本的流变最不同的是,在文本中永远都必须特殊强调出这一主要人物的最内核、最特殊的身份,那就是花木兰的性别身份。值得玩味的是:这一性别身份的特殊属性一直是在与传统的男权社会所建构的权威中对比着体现出来的,因此一定是将男性的社会属性与这一顺利完成男性社会责任的女性身份之间进行对比。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性别身份这一概念也在不断更新着其中的内涵,这也意味着传统文本中花木兰所具有的特别意义逐渐被解构,甚至丧失其原本具有的特殊性。
在《花木兰》这一电影文本中,这种改变并没有直接在故事情节和叙事逻辑上发生明显的变化,甚至从作者的实际创作角度来说,曾经改编加入的爱情故事线索也被弱化,这种弱化虽然与原作之间存在着相似的关联,但在动机上并不是试图回归到原作之中,而是试图在文本中渗透出西方的女性主义的文化逻辑。
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形象是一位在封建的男权文化中比较特殊的女性形象,按照传统的女性观念理解,是一位承袭自己父亲士兵身份,伪装成男性代父从军的忠孝的女性。按照传统的人物塑造语境来说,这一行为实际上潜藏着一种更加复杂的传统观念,那就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困境下,这一人物的塑造更加赞同的是通过孝亲来婉转地实现忠君的这一理想。因此,虽然是以女性人物塑造为主的叙事文本,但依旧是在传统男权视域下的文本创作。但是这一次改编却以当下社会思想的需要为花木兰这一女性人物赋予了全新的代表性意义。先不论这一改编最后是否真正发挥出了理想的效果,单就其创作的目的依旧是值得肯定的一次尝试,只不过这次尝试伴随创作者对中西方文化理解方式而步入了并不理想的结局。女性主义为整个叙事文本找到了一种全新的风貌,这是传统同题材文本所不具有的特点,从主题上来看这似乎是一种不容辩驳的事实,很少有文本像这样为花木兰先天地赋予了女性的优势,她天然地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元气”。虽然这一名词的出现在这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却说明了文本的一个特殊视角,那就是花木兰不再是单纯地在性别上具有一种特殊性,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这一人物就注定会完成一种特殊的使命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
二、东方与西方之间:后殖民的文化路径
在这部电影作品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能说完全来自跨国界、跨民族所带来的刻板印象,但这一因素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在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曾经被殖民的国家与曾经的殖民国家之间一直戴着一种源自现代性的有色眼镜。对于大多数被殖民的国家来说,以欧美为主导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参考范本,虽然在之后的历史发展当中,民族化又被视为重要的国家民族精神的发展路径,但曾经的影响作为一种潜在的历史语境遗存在本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从社会现象上来判断,被殖民的国家的现代化是以一种结果性的状态保存在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的,尤其是对一些在历史发展当中亟须通过西方现代化思想来解决本民族问题的国家而言,西方的现代化文明成果是一种带有天然正确性的行为;但是对于殖民国家而言,这种现代化成果在其他被殖民的国家生根发芽之前就已经在本民族社会之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因此,通过不同路径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而言,仅仅在对于现代化的态度上就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
当这种不同延续到国家民族性的建构过程中的时候,一种反叛的思维就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这种反叛一方面来自被殖民国家民族身份的认同,希望通过批判带有明显西方色彩的现代化话语来确立本民族文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则完全是来自殖民国家所鼓吹的现代化发展中带有的严重的后殖民倾向。举例来说,仅以《花木兰》这部电影而言,其中所谓的女性主义视角就是一种在本民族中也难以实现的社会发展思维,而这种过于理想的社会观念通过中国的历史故事表达出来,实际上是在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强加逻辑,并不能真正适应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这有些类似为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民族文化建构提出了一个过于乌托邦的要求,并且试图通过文本将这种不切实际的社会发展思路渗透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创作的目的依旧是源自曾经的殖民国家所内在的文化输出的唯我独尊的思维。
即使是从文本的内部来看,我们依旧可以发现我们这种论断的直接证据。比如在这部电影中,创作者一共设计了两位女性角色,这两位女性角色又都或多或少地被冠以“巫女”的身份。对于前辈的巫女来说,她自我价值的实现一直都是依赖于反面的男性角色,虽然这一人物一再强调自己并不是任何人的奴隶,但是当她面对花木兰时,则一再表现出自己对于这一年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期待。而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在电影文本中则是一位“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独立女性的代表,但吊诡的是,这位被努力塑造成为女性主义代表的主要角色,其价值的最终赋予,却是通过在男性价值主导的行伍之间实现爱情、实现亲情、实现忠义的确认,这不得不让人困惑,这部电影到底是在宣扬女性通过自我独立获得自由与幸福,还是在宣扬只有实现了向男性价值的靠近,女性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自我价值的观点。这一迷思尤其在《花木兰》这部电影中所具有的天然人物特点上集中体现出来。其实她的天赋实际上远超某些男性,但她最终自我价值的认识依旧是回归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之中,这难道不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吗?如果以此来试图证明花木兰乃至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所谓女性主义,不恰恰是一种以偏概全的努力吗?从这一角度上来看,这部电影似乎并不是在为中国古典故事添加现代的文化意义,而是以一种西方中心的角度俯视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努力。而这种努力与所谓的女性主义似乎无关,而是以西方文化的发展可以代表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一角度进行的。
三、理解与误读之间:多元化的文化发展
所谓后殖民文化,实际上一直是一个由曾经的殖民文化的倒置发展路径所产生的文化结果。但仅仅说这一现状完全是由曾经的殖民文化的影响所决定当然也不具有完全的合理性。因此,它实际上应当是以西方一些国家为主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文化殖民,而其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文化扩张,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这种现代化文化发展理路倒置的现象。但是后殖民文化虽然就其内部的文化结构来说同样同其在历史当中存在的样貌类似,但我们似乎更加应该重视的是其内部所具有的一种非常严重的解构、重构文化民族性的倾向。
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较而言是一种更具有封闭性倾向的文化特性,这一文化源自曾经的民族历史结晶,但是在其历史发展进入近代历史当中之后,遭受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社会思想内部对所谓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是持或多或少的反对态度的,这是由于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民族性的身份作为一种旧有的文化发展观念与现代性相比而言有着非常深刻的矛盾,对于旧有观念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新观念的肯定,这两种观念的交互导致一种全新思想的诞生,但是随着现代化的逐渐深入开展,很多由现代化进程导致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因此,反思所谓西方标准的现代性观念,而提倡符合本民族内在气质的文化观念成为当下社会一种非常必要的构建民族主体身份发展道路的手段。
这种在本民族内部启发民族独立发展路径的方法,并不是完全对西方的现代主义精神进行反驳,而是以一种共生的状态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进行融合和吸收。从结果上来说,这种吸收恰恰是当前全球文化发展的多元趋势。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在内部社会发展强调多元,这与这些国家曾经广泛的殖民有着很明显的联系,但是对于社会外部的文化交往来说,这些国家还抱有曾经殖民时期的观念,对这些国家和民族自身衍生出的文化传统不屑一顾。这种态度虽然曾经的殖民国家不愿意承认,但是在真正的创作行为上还有着很浓重的遗留。对于这种根植于文化交流之上的创作观念,实际上反映出了一种深刻全球化之后的文化交往隔阂。
以这部电影为例,西方的误读与刻板印象已经在文本中随手可见了。从饱受争议的人物妆容到令人困惑的空间建构,甚至对于人物身份的建构,文本中处处流露着一种倨傲的刻板印象。这种观点在文本中再明显不过,从身份的角度上来说,女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实现代父从军,甚至建立战功是因为其先天具有的“元气”,这一概念究竟是不是形容人的天赋暂且不论,仅仅说这种天赋卓绝、与众不同的个体生命观就与文本中所选取的中国人聚居的福建土楼这一处所象征的团圆、集体的文化观念有着显著的差别。
这一僵硬的文化书写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文本的结尾,在电影结尾时,花木兰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且受到了“赦免”,回归家庭之后的花木兰完成了自己的孝的文化使命,但是创作者似乎并不满足这一个人主体性的实现,文本最终还是为花木兰寻找到了权威的认可,那柄皇帝亲自赐予的宝剑与上面铭刻的字迹,并没有在电影的最后为主要人物带来任何的光辉,反而将这一人物的主体性消解得一无所有,使她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原点,那就是她的人生一定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构建自我的意义,而自己追寻独立的许多努力为自己换来的只是更高权威的认可。这种创作的思维形式,如果不是作者本人的创作观念非常封闭或传统的话,那就是源自创作者对这一民族内核的判断还保留着曾经的固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