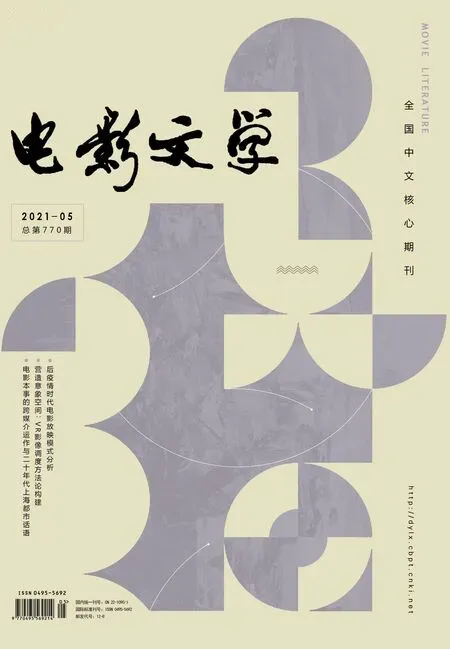电影本事的跨媒介运作与二十年代上海都市话语
刘真真(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在现有的研究中,电影本事一直被视为电影与文学文体互渗后所产生的电影文学形式之一。周晓明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与周斌的《中国电影文学的传统与贡献》都将电影本事视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电影本事兼具小说的叙事特点与电影的蒙太奇思维,它既可以是剧情梗概,也可以是电影剧本的雏形;《中国无声电影剧本选》甚至直接将电影本事作为缺失剧本的替代品。鲁勘、程景楷等人的《中国电影文学形式的形成与发展》补充了电影本事与文明戏的关系,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早期的电影本事……在情节安排上有点像戏剧,但无对话或很少写对话。”以上著作与论文都将电影本事置于文学与电影、文学史与电影史的交互与重叠之处进行研究,也有学者试图进一步分析电影本事中电影与文学互动的实践过程,如黄勇军等人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小说的滥觞与发展钩沉》,谈洁的《从本事到小说:电影剧本在早期电影杂志中的形态变迁》与李道新的《电影本事的文体互渗与跨媒介运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道新在其论文中点明了电影本事跨媒介运作的特点,这就使对电影本事的研究跨出了仅限于电影与文学这两门学科的狭隘,开始注意到电影本事与其载体——不同媒介的互动关系。他指出:电影本事是电影同小说、戏剧问题之间相互影响的产物,它一方面吸收了诸如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小说家作品中的“视觉化”与“通感”描写,又在小说文本与话剧剧本重视故事情节的影响下开始注重情节架构与人物关系。不过李道新并未就此深入下去,仍然停留在对不同媒介中文本的孤立分析上。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印刷文化的兴起密不可分,而话剧和电影的演出、放映活动同样也是都市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电影本事的文体互渗与跨媒介运作的研究必须将其置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背景之下。约翰·菲斯克指出:“在媒介文本从文化方面制造意义的过程中,互文性起主要作用。文本同时与其他相似的或不同的文本关联,通过这种方式为观众制造意义。”彼时的上海都市文化,正是东西方文化汇聚于上海时的碰撞——在旧伦理与新观念、旧文体与新文体,作为媒介的杂志、报纸与作为媒介的电影、戏剧之间的互文中诞生的。因此,电影本事不仅是“文体互渗”,更是“媒介互渗”,不同的媒介给电影本事带来不同的叙述策略:报纸与杂志上的电影本事与电影说明书上的相比更偏重宣传,有些还带有评论的性质;由于媒介间的互相渗透,电影本事的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它力图采用一种视觉化的叙述方法,既使读者转变为电影观众,也使阅读快感过渡为视觉快感。在以上的论文中,电影本事时常被视为影响的结果,事实上电影本事的叙述也在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叙述。电影本事既被上海都市话语建构,也同样是都市话语的积极建构者。
一、《阎瑞生》电影本事与上海都市想象
“文体互渗”不仅使电影本事兼具文学与电影的叙述、修辞特点,同时也使读者的阅读习惯从印刷媒介过渡至较为陌生的电影媒介。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电影本事同样是历史经验的一种表述,借由互文性这一概念分析作为史料的电影本事,我们或许可以重新审视1920年轰动一时的“阎瑞生事件”。这桩杀人案因其离奇的情节、受害者妓女身份的艳情色彩迅速成为街头小巷的热议话题。按照绝大多数论文的观点,正是靠上海纸媒大力宣传造势,才催生了一批以案情为原型的舞台剧,乃至将其搬上银幕。这些论文不约而同地将电影对原事件的呈现视为一个社会事件发酵的最高潮,其中暗含着一种历时性的、“媒介进化论”的观念——在所谓“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纪实性”“逼真性”的驱使下,各种媒介中的文本次第不断复原案情的现场,直到它从报纸新闻变为舞台剧本再进化为电影(电影显然是最具有以上几种性质的),即典型的“本原”历史主义式表述。然而《阎瑞生》电影本事并不能简单理解为“阎瑞生事件”这一历史的最终形态,可以说,从创作者们选择“阎瑞生事件”为电影素材的那一刻开始,就是以满足、还原观众的视觉性期望为目的,这也正是在该片的宣传策略中总是强调电影对真实场景高度还原的原因。因此,《阎瑞生》电影本事的诞生是共时性存在的不同媒介中文本互文的结果,所谓的逼真性、纪实性只是其表面的一种伪装,它并非要还原所谓事实真相,而是要将这桩杀人案上升为齐泽克所谓的社会征兆,且电影本身的放映也并不意味着文本跨媒介运作的结束。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指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当杨小仲创作阎瑞生电影本事之时,他无意识地将自己代入为历史学家却有意识地对原素材做了增删,他需要用一个特定模式来整合自己的叙事,从而将这件令人震惊的案件——一个类似“泰坦尼克号沉没”那样的社会征兆迅速纳入已有的文化范畴之中,当然,一部分“震惊”是必须保留的,它是《阎瑞生》吸引力的主要来源。因此,《阎瑞生》电影本事对原有报道素材的取舍正表明了作者对叙事模式与修辞形式的选择。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报道素材:《申报》在1920年6月19日开始了对阎瑞生一案的报道,它是以王莲英父母对真凶的悬赏的形式出现的。1920年7月2日,《申报》上开始出现《花国总理莲英被害记》的出版通告。1920年7月5日,《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与《莲英被害记》在《申报》上发表了出版通告,而官方审理《公共公廨审谋毙莲英案》直到1920年8月20日、21日及27日才见诸报上,尽管此案犯罪者与受害者都为国人,但会审官、律师甚至探目俱是西人,审案所用语言也为英语。自9月14日起方才在内地法庭(护军使署)审理。审案中所遇到的问题,其一是此案审理权属公共公堂审理还是内地法庭(事情的起因在租界,但谋杀行为是在非租界处发生的),其二对第二被告吴春芳的罪责的裁定究竟参考国内法律还是租界法律,其三即阎瑞生与吴春芳口供不一致(阎称自己只想麻晕王,用麻绳勒死王是吴所为,吴则称自己只是为阎等放风并未杀人)。8月28日,阎瑞生与吴春芳解护军使署,报道特别记录阎、吴二人之穿着:阎身穿麻布衫佩戴十字架,吴身着白夏布衫。11月24日,《申报》报道了11月23日阎、吴二人执行死刑之过程,因为阎瑞生的天主教信仰,执法者特别安排了牧师;吴春芳本无宗教信仰,却也和阎采用了一样的忏悔方式。在前往刑场的途中,两人状态完全不同:阎瑞生闭目,而吴春芳如传统小说中“草莽英雄”一般破口大骂王莲英复又高唱西皮二黄。1920年11月25、26、27、28、29日,《申报》连载《补录谋毙莲英案之军署判词》,对整个案件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梳理。
《阎瑞生》电影本事主要参考的应当是《补录谋毙莲英案之军署判词》,作者删除了一些与吴春芳有关的细节,并增加新的情节,从而重塑了吴春芳这一人物形象。原素材中,阎曾给吴大洋一元洗澡剃头并购买绳索,吴花完一元后又向阎乞洋四角以购买绳索,这个细节实际上充分揭露了吴的流氓习气。在行刑过程的报道中,吴口供“直爽”,前往刑场之时大骂王莲英,高唱西皮二黄,由此可见,吴春芳是个颇具江湖气的混混,他参与犯罪,未必完全是因为金钱,也可能有身为混混的粗鲁、胆大与残忍,甚至可能是出于“江湖义气”。而在电影本事中,作者让阎瑞生与吴春芳成为共同为金钱、债务苦恼之人:阎与吴相遇是在阎自跑马场赌输之后,吴向阎“狼狈称贷”,阎借吴一元。在此处,编剧将促使阎吴二人共同谋划的多种可能性简化为一致的金钱短缺,至此吴春芳的人物形象得到重塑:一个中国传奇式的草莽人物消失了,取代他的是受过西方教育的阎瑞生的跟班。这个改动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在《阎瑞生》电影本事的叙事逻辑中,原先身为江湖草莽的吴春芳成为“异质”的存在,原素材与电影本事分别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模式与社会观念。
《阎瑞生》电影本事实际上由两段叙事——欠债杀人与逃亡组成,第一段叙事最关键的两个场面“见财起意”与“谋杀王莲英”分别发生在城市(妓院)与乡村中,从而构建出充满诱惑的销金窟——现代都市上海与法外之地——乡村之形象。在电影本事的叙述与描写中,都市呈现出流动的特征,其一是金钱的快速流通。阎瑞生穿梭在不同消费场所,他从大世界出来后便直奔小花园莲英处,向题红馆借的钻戒又很快被置换为赌资并在赛马场输得一干二净,阎遇吴时吴也为债务所苦,促使二人合谋的主因正是因金钱快速流通所致的拮据,而阎瑞生杀人抢夺首饰之后又回到题红馆处(消费)。其二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主人公轻而易举地在乡村与都市之间往来,而阎瑞生杀人后乘坐轮船、火车逃亡的行动更是强调了一种独属于现代都市的时空的流动性。与城市相比,乡村显然相对闭塞,阎瑞生只在杀人和逃命时才来到这里,其岳父得知杀人之事还是靠着原始的口耳相传(派遣乳母去城里探听)。绳索不仅杀死了王莲英,更在阎瑞生逃命时发挥了重要功用,最终阎瑞生也被“绳之以法”,绳索与汽车作为勾连起两段叙事的重要符号,同时也暗示着中国/乡村不再闭塞,在现代法律与刑侦系统面前它已无法成为阎瑞生等犯罪者的庇佑。
第二段叙事明显受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大行其道的侦探片之影响,阎瑞生逃亡过程中,曾潜入松江奈山教堂向神父求救而“神父斥之”,这段情节并未出现在《补录谋毙莲英案之军署判词》中,应当是根据前文提到的阎瑞生之天主教信仰改编而成,却又呈现出强烈的道德训诫色彩。在电影本事的叙述中我们丝毫不曾感受到原审判过程中东西方在法制与语言等上的差异,也没有任何关于语言和法律的讨论,在紧张的抓捕过程后影片毫无黏滞地进入了正义审判的结局,结合前文中对吴春芳的重塑,编剧试图改写并整合东西方的生活经验、法制、宗教/道德观念,缓和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社会矛盾。通过对上海各区域的银幕再现,上海也由单纯的地理空间转变为影像中具有复合含义的文化空间,从而让观众更好地缝合进电影所构建的幻象——一个现代的上海之都市想象中。
“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本文,也不是主导本文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换言之,“阎瑞生事件”或许和真实的上海略有出入,但它构建了1920年上海的都市想象:现代性以一种不可逆的、必然的意志将整个中国连同它古老的乡村都卷入这势不可挡的洪流中,尽管令人不安的流动性带来了犯罪与死亡,但纵情声色与金钱的诱惑仍使人们对都市趋之若鹜,而这一欲望以对罪人的道德与司法审判粉饰。《阎瑞生》电影本事使观众安全地触碰到原本生活经验与文化中的禁区,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一起带来了有别于以往的新奇快感。
二、电影本事的跨媒介运作与新闻的视觉化叙述
电影本事往往被视作电影与文学相互影响的结果,事实上,电影本事也在跨媒介运作中积极地影响着新闻的叙述方式,《申报》1921年3月23日的一则新闻足以证明这一点。这篇名为《哈埠逆伦巨案始末记》的报道,讲述吉林省某团长之子因与父亲不和最终选择与弟弟一同弑父的不幸故事。虽然标题中“逆伦”一词表现出写作者仍然受到旧伦理的束缚,但整篇报道并不以传统的新闻文体写就,反而更近似于一篇惊险刺激的“电影本事”。该新闻的主人公曹佩雄在弑父之前曾前往电影院,观看了一部侦探长片,这部影片“情节戏文,均臻佳胜,唯佩雄毫不在意,坐立不安,影戏未完,即不耐坐,昏闷回家”。曹佩雄选择观看侦探片,或许是试图通过他人英勇的冒险故事来麻痹自己紧张的神经,获取胆量,但侦探片的常规结局一定是侦探侦破案件、抓获罪犯并彰显正义,因此即使情节生动的影戏与电影院构成了一个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的世界,作为潜在杀人犯的曹佩雄却对此毫不在意,甚至坐立不安(此处描写从侧面也表现出写作者对电影的观念:电影对人的心理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如果曹佩雄不是要杀人,他很有可能和其他观众一样沉浸在电影情节之中)。曹佩雄并未看完这部侦探片便离开了影院,这个“未结束”的故事在叙事中以曹佩雄本人的杀人行动继续发展着,因此,主人公从影院的离开只是情节的开端,它将一桩杀亲案与侦探电影的情节结合起来从而增加了叙事中的戏剧性,也暗示着电影这一视觉奇观最终会演化为现实世界的灾难,电影的运镜方式与叙事方式也平滑地逐渐加入后续的叙事之中。
影戏院显然是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空间,在影院中坐立不安的曹佩雄试图进入父亲的住所——一个传统、强硬的军人(随身携带一柄手枪,坐卧不离)所统治的伦理空间,这里的门每晚都要落下七重锁,并有士兵彻夜带枪守护,而曹佩雄被禁止进入这个空间,即使进去了也只能住进客房,从主人公的处境来看,他处于开放、享乐的现代生活与封闭、禁欲的传统生活的冲突当中。主人公以拿东西为借口成功进入这个堡垒一样的住所,在他进入住所之后,整个叙事伴随不同视点的切换以交叉蒙太奇的方式进行,并为读者描述一连串惊险的杀人场面:曹佩雄与弟弟持枪一前一后潜入父母的房间,曹佩雄突然心生犹豫,在弟弟的催促下开枪,仓促之下不仅没有命中,还惊醒了熟睡的父母,写作者随即转向曹母的视角,她惊叫着向丈夫求救,曹父亦呼喊求救,在一片混乱中曹结果了父母的性命。混乱结束之后写作者如此描写道:“佩雄回身时屋外廊下电灯照耀,唯屋中已熄火,佩雄回身屋外后见廊下有人影,又一枪击之中,往视则其弟佩远也。”房中并无灯光,而屋外一片光明,身处黑暗、紧张而惊恐的佩雄误杀了自己的弟弟,这个全程以曹佩雄主观视角描写的场面极富节奏感、戏剧性与视觉冲击性,对比曹佩雄击杀父母的激烈气氛,这次安静而快速的误伤重击了曹佩雄脆弱的神经,光明和黑暗的色彩隐喻也意味着曹佩雄就此滑向了命运的深渊。
在这场误杀之后,曹佩雄因子弹用尽,回到卧室取子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死了妻子和孩子。这段叙事以妻子的视角开始:因曹常将洋服和子弹放在一起,曹妻今日为丈夫取洋服时便随手将子弹放在桌上,此刻她正与女佣在房中逗弄孩子,因此置于桌子上的子弹——这一不祥的意象显然与逗弄孩子的温馨氛围格格不入,但她又是军人家庭的女眷,子弹对她而言或许只是家中常见的事物之一,当曹佩雄闯入这个温馨的空间拿起子弹填充时,曹妻与女佣因对此习以为常而并未有任何情感与动作上的变化,在“整理衣服与子弹,逗弄孩子”与“拿起子弹填充”之间形成了类似交叉蒙太奇的阅读体验,从而营造出噩运即将来临而主人公浑然不觉的紧张感,并使曹妻之死带有飞来横祸的悲剧意味。
如果我们将这一故事视为电影本事的话,以“戏中戏”存在的、未结束的侦探电影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完结:杀死家人、精神错乱的曹佩雄最终被守护在“堡垒”边的士兵们抓住,送上法庭并执行死刑。这个游离于现代与传统生活之间的年轻人最终受到了现代法律的审判,他的罪过也被旧的道德观念定性为“逆伦”。行文似乎暗指了电影这一现代媒介对人精神与心理的巨大影响,模糊自身与电影的界限,并错用这种力量会带来灾祸,但同时电影叙事的方式却足以激发具有视觉快感的阅读体验。此种观念与叙事方式在上海中西文报纸中都有体现,1913年9月7日的上海《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刊载了一则名为“Loves labors lost in the movies”的新闻,讲述德国一名渴望婚姻与家庭生活的劳工迷恋上了报纸上一名相亲女子的肖像,他不满足于简单的照片,以至于寄钱要求女子拍摄她的生活影像,甚至不惜包下整座影院只为欣赏这部自己“订制”的电影,两人见面后男子失望地发现,那张相片与影像均是女子的伪造:她花钱雇用了一名电影女演员,并让她在照片和影像中出镜。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描写女子的照片与影像,还特地为文中情形绘制插图,而这不幸人的故事看上去也仿佛是一部爱情悲剧的电影本事。甚至,上海此时此刻之风物亦可以“铭刻”进影像,并作为一种噱头在报纸上刊载,1925年1月5日的《申报》报道了一则联华电影公司的拍摄花絮:前日上海下雪,明星公司的张石川便携演员郑小秋等前往徐园拍摄雪景,这段雪景也将插入公司正在摄制的电影《好哥哥》之中。报纸的叙述强化了电影对日常的“铭刻”以及它对真实生活的“戏仿”,当下的瞬间与成为历史的永恒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正是在原创与复制、真实和幻想、模仿和被模仿着之间的虚拟空间中,人们能够挣脱疏离和破碎的现实世界的牢笼,暂时性地享受一种不同寻常的身体化感受并重新获得‘体验’的能动性。”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视觉化的叙述方式不仅使熟悉报纸媒介的市民逐渐习惯电影的叙事方式,更强化了观看电影是现代都市生活必不可少的成分。不过,一切的快感体验必须置于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统治之下。三、电影本事与电影评论
电影本事,尤其是外国电影本事并不是单纯的剧情简介,它们不以本事而是以评论的形式见诸报上,在上海特殊的都市文化背景之下,它们亦成为不同生活经验与文化体验冲突与交流的场域,在作者对外国电影本事的翻译、记录过程中也包含着对“他者”的评论与审视,以及对主体的再认识。《申报》1920年12月11日罗汉素所写的一篇观影随笔中记录了一个颇为有趣的场景:作者预备去上海大戏院看一部名为《高槐田斯》的电影(“高槐田斯”是电影名称的拉丁文音译,其本意是指“你往何处去”),并与朋友发生如下对话。
作者:你往何处去?
朋友:到上海大戏院去看《高槐田斯》(《你往何处去》)。
作者忽而发觉此言与上海人之无聊对话十分相像。他用如下对话来举例。
甲:侬来买点啥?
乙:是。
甲:买点啥?
乙:买点啥?
借由两种语言的类比,陌生的语言和生活经验并入上海都市之日常生活中,同时也划分出了都市阶层——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文化精英与普通市民。显然,在作者为弥合两种经验进行的类比中蕴含着新的分裂——文化精英的“往何处去”与普通上海人之“买点啥”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即使在作为民主之象征的公共空间电影院中阶级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正如《尼伯龙根的指环》与其中文译名《斩龙遇仙记》背后耐人寻味之不同意蕴,翻译粗略的电影本事(电影说明书)在普通观众与文化精英之间显然具有不同的意味。罗汉素认为看电影绝不是为了简单的娱乐,而是为了“读世故人情、明了人类现实生活的所在”,因为电影比记录人类历史的文学作品更浅显也更易在闲暇时观赏,有自身独特的艺术性和教化功用,他对《你往何处去》翻译粗劣的电影说明书翻译感到不满,因为它并不能完全体现这部由伟大名著改编电影的深邃内涵。罗汉素还详细记述了观看这部电影所获得的视觉享受,如罗马贵族奢侈的生活(他生动细致地描写了影片中罗马贵族早起时的沐浴与享乐)、罗马人(电影演员)强健的体魄,并希望中国也能如罗马那般“轰轰烈烈”地闹一场,诞生出如尼禄、黎基维等英雄与艺术家。“五四”的启蒙话语带来了线性的时间思考方式,在将中国和西方分为过去与现在的同时也使知识分子自身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者的身份,“在中国语境中,这一跨越国界的中介性的‘世界主义意义上的主体性’也就自然带上了几分受世人尊重的文化权力色彩,因为这种新的文化资本形式仅仅属于那些已经‘受到启蒙’的少数人”。然而在谈论到影像中作为西方文化具体表现的罗马人生活、身体与艺术之时,作者——这位文化精英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带有窥私欲、羡慕、憧憬与沮丧的复杂心态,结合克拉考尔描述在镜头前的身体呈现所用的术语“大众装饰”之双重特性——“既存在官能解放的乌托邦性质,也潜伏着对身体能量进行意识形态剥削的隐患。”这种混合着殖民地居民种族焦虑之心理与文化精英世界主义之心态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者在这篇简评中重写了《高槐田斯》的电影本事。值得注意的是,《高槐田斯》虽然充满浓郁的基督教色彩,却改编自现代波兰小说家Sienkiewicz之作品,作者在文中写道“……内容是借着基督教半神话的故事,描写希腊罗马文明衰颓时候的社会状况和基督教的精神。”或许作者自己也感知到银幕中的本事与上海当下新旧激烈交替的时势间存在隐秘的互文关系,他在文章结尾处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与疑问:“可是中国的尼禄、黎基维……一类的大英雄、大豪杰、大艺术家,什么时候可见希望产生呢?”在对电影中罗马人的描写中寄托了作者对自身与民族的想象性自我指涉,一个乌托邦幻梦,然而作者对此表示怀疑,这个问句恰好表达了“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又失去了政治解决的视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之彷徨处境。
对外国电影电影本事的“改写”或“重写”大多出现在“述评”中,即在剧情记叙之中夹杂着点评。1924年12月25日的《申报》刊载《斩龙遇仙记之短评》可视作是“改写”的典型案例,作者黄道扶直接将《尼伯龙根的指环》类比为《西游记》,而代表女性强大力量的布伦希尔德则被简化为“悍妇”:“……余应友人之约,曾一睹之,此片剧情,臻为离奇,颇类我国之《西游记》……盖此妇凶横无比,国王不敌也,后卒赖少年之助,如愿以偿。”而该片视觉奇观之刺激在于男主人公遭枪尖穿胸的场面远胜中国京戏中之武打,“剧情光陆怪离,少年为其仇人刺死时,以枪尖穿其胸,血涌而出,极逼真,远非中国京戏中之所谓真刀真枪者所可比也”。这则短评可以视作一种简略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尼伯龙根的指环》改译进中文语境的尝试。而1925年1月1日由仇湘创作的《斩龙遇仙记》影评,尽管分析角度与黄道扶不同,两者在评价的立场上却呈现出有趣的相似之处——一种基于小市民道德观念的简单解读。仇湘写道:“全篇情节,处处伏因果,雪格之刺蛟龙也,龙正渴饮于池,雪先以剑刺其右目,蛟龙乃致不敌,及后雪既行猎郊外,忽觉口渴,因就饮于池,讵为盲一右目之海根所刺,循环报复,正予以吾人以绝大教训也。”中式伦理观中的因果、报应等概念,与西方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并不一致,正如《赵氏孤儿》有别于《哈姆雷特》,如果仇湘阅读过《俄狄浦斯》或者《安提戈涅》,那么他多半不会发出此等议论。
还有一些电影本事会在叙述中加入对男女主人公之面容、装饰、表情与演技的点评,可称之为第二类“改写”案例,如1925年1月3日之《新片〈女皇艳史〉述评》。作者严月池在女演员的美貌与演技上颇费笔墨:“琶娣姄儿丝饰女皇示巴,冶艳动人,貌绝肖芭芭拉玛(演《风流债》《花情蝶义》之女主角)表情做作亦如之,允称双璧。当伊姝那米吸士遭挨马皇掳去,杏眼圆睁,握拳透爪,愤懑极矣。嗣亲爱妹遗骸,状若癫发,抚尸大恸,并立誓为妹复仇,大义凛然,使人起敬。晋宫见皇一幕,靓妆艳服,珠绕翠围,欵步轻移,拾级而登,眼含秋水,脸呈笑容,极意蛊惑挨马,俾令堕于彀中,而手刃挨时,一种勇敢果决之神气尤为佳妙。”第一类作为一种“文化移植”更多地体现出小市民阶层面对现代大都会纷至沓来的新文化、经验保守的接受态度;而第二类则更接近于导赏与宣传,在作者的叙述中,迷人的男女演员身体构成了新的都市景观,作者还教导观众如何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借助表情与肢体语言欣赏和理解外国影片,享受这种都市文化特有的新奇视觉快感,以成为一名“合格”的上海市民。
结 语
过去对电影本事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电影与文学的视域之中,从而忽略了电影本事与其诞生的背景——上海都市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电影本事见证了20世纪20年代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它与戏剧、报纸等媒介共同构建了上海的都市想象及现代性体验,让人们触碰到旧伦理中禁忌的快感,欣赏由身体、建筑所构建的都市景观,又使人们陷入新与旧、世界与民族、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茫然与无措。电影本事研究要求我们具有跨学科、跨媒介的研究视野,它的丰富意蕴依然有待更深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