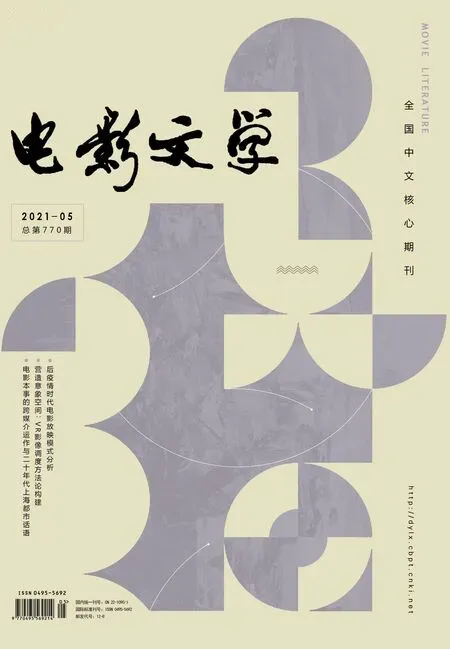告别经典叙事:用音乐表意的新动向
边岩锋(南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所谓叙事,指的是把一个或一系列事件作为故事向读者或者听众讲述出来。对接收者而言,这意味着故事是已经完成的往事,它的时态是“过去完成时”。经典叙事与形式主义及法国结构主义密切相关,一般有以下特点:人是故事的主体;叙述者是叙事的主体;文本所讲故事是有意义的;文本脱离语境,具有内在规律并有自成一体的时空结构等。而后经典叙事则对人在故事中的主体地位进行质疑和反思,故事也不再遵循确定的时空结构,叙事作品仅仅是特定文化语境的产物。但后经典叙事并不是对经典叙事的完全颠覆和全盘否定,它仍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并具有故事的完整性。比如经典叙事中作者、叙述者、故事中人物三者同一好像是讲述真实的故事,但实际上的叙事作品则往往破除“叙述者大于人物”“作者不等同于叙述者”的叙事成规,更为激进的创作者则使此裂痕愈加明显,创作者本人的态度也由此介入,文本的言外之意因此被加倍传播。总体来讲,后经典叙事以寻求新的学科范式为特征,善于利用“新兴技术和方法论”,表现出对“新兴媒体与叙事逻辑的兴趣”。就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趋势,格雷塔·奥尔森提出了三种研究方法:一是认知方法,关注“叙事被感知被识别时读者的心理过程”;二是跨媒介、跨文类和跨学科的叙事分析;三是不同语言社区和文化领域中的区域性或国别叙事学的历史重构与批判性审视。从奥尔森的观点可知,叙事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叙事学对跨媒介、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关注使得叙事学具有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作为艺术媒介,也作为电影的重要成分,音乐与故事的契合是电影叙事的基本要求。音乐不仅使电影作为视听艺术更加丰满,也能使电影叙事更加精彩。本文以程耳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2016)为例,分析导演如何借助“故事外音乐”介入叙事过程,探讨故事时空的打破对经典叙事结构有怎样的影响,揭示观众因为认知差异而接受潜在故事的心理过程。本文认为,叙事与故事分属于不同的时空层面,叙述者的叙述时间在经典叙事中总是事后行为,错位于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后经典叙事中,叙事与故事的时空则被创作者有意识地打破,从而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具体表现为叙述者对故事叙事时空的介入。创作者此时并没有退到其作品的后面,而是主动、积极地通过介入叙事媒介宣示自己的存在并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在叙述层面上,后经典叙事并没有完全抛弃经典叙事,而是挑战其表达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叙事的多元化及其方法论的突破,开启了审视叙事形式和其功能的新视角及动向。
一、故事外音乐
《罗曼蒂克消亡史》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帮派大佬陆先生(葛优饰)、交际花小六(章子怡饰)、陆先生的妹夫渡部(浅野忠信饰)及其他小人物在社会大动荡中沉浮消亡的众生相。电影的故事脚本取材于同名短篇小说集的其中三篇,《女演员》中的吴小姐影射与戴笠有亲密关系的胡蝶;《童子鸡》在电影中表现为“童子鸡”(杜江)、“妓女”(霍思燕)那条线;与电影同名的一篇则是电影脚本的主线。导演把几个故事打散,在不断的拼接过程中,将完整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虽然借助电影暗示了众多历史人物如黄金荣、杜月笙等,导演并没有特意关注历史掌故,他似乎只是借着那些慌乱时代里的社会沉浮,完成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现代视角下的个人表达。作为一部讲述中国故事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叙事间隙的外文歌曲(如Where
are
you
,Father
《你在何处,我父?》等)略显突兀,它既突兀于故事的时空结构,也游离于叙述者的叙述时间之外,间接表现为导演对故事经典叙述节奏的打破和个人观点借歌曲内容的直接表达,电影观众也因此被提醒此处叙事的非经典属性。因为导演的直接介入,《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叙事被打上了明显的个人标签,使现代语境也能在电影叙事(过去的内容)中有效地发挥作用。电影的叙事时空里,多个故事相互混合、相互冲突,突兀的故事外音乐又时不时地打破经典叙事结构,使电影的后经典叙事明显指向于导演本人的自我表达。这种“故事外音乐”之所以“突兀”,借用西摩·查特曼的说法,是因为它“没有看得见的出处,也没有隐含的出处……声音并非来自故事世界,而是来自话语世界,它的交流对象是受述者,这个受述者可以是起着框架作用的话语里的另一个人物,也可以是电影受众”。音乐此时中断了故事的叙事,观众可以确认听到的并非故事时空中的同步音乐,我们也只能假定这时的音乐既不是故事人物的,也不是叙述者的,而是电影创作者对电影的额外注解,电影观众也由此可以对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现代视角上的再思考和重新评论。这种故事外的声音,也因此被称为“评述的声音”。导演可以用它来引申故事、调整叙事节奏、解释形象或者启动情节等,产生类似“反讽”的效果。正是因为故事外的音乐,《罗曼蒂克消亡史》改变了经典叙事风格的稳定形态,打破了线性时序和同一空间的束缚,在原有传统叙事的基础上选择富有异域感的音乐来表达创作者的声音,故事也因此呈现碎片化和拼贴化,间接反映出真实生活中事件的反复无常和出其不意。导演借助外文歌曲改变了叙事走向,引发观众质疑电影中历史事件和政治话语的真实,进而启发他们自身特有的看法及感受。正如其导演同行姜文所讲,“人们生活在虚构里面,人的眼睛是有取舍的,虽然看到同一张照片,但他们看的是虚构的一面。一旦有机会去描绘现实生活,而现实本身已经是虚构的了,还有什么是可观的呢?”
现实不再只有一种,电影创作者需要重视的是当下自我的感受,用电影语言书写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识。作为艺术门类之一的电影也因此需要不断打破原有的定式和规范,来引导、启发观众对过去和现在重新思考。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也讲,“艺术电影需要古典的背景设置,因为背离规范必须是作为现实主义或作者表达来定位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电影中的外文歌曲虽然突兀,但不难理解,程耳选择的音乐语言故意脱离故事情景才突出了其表达意图。《罗曼蒂克消亡史》叙事不是围绕某个中心线索展开,而是借助故事外音乐不时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由此造成的观众认知裂隙则经由他们的想象力加以填补。
尽管有此突兀的音乐,《罗曼蒂克消亡史》故事主体仍然保留经典叙事模式,导演个人化的音乐处理手法只为提醒观众在观影的同时重新思考生活的多重意义。要明白导演的潜在意图,我们不妨再次倾听电影中小六被迫离开上海时的英文配乐Take
me
to
Shanghai
(《带我回上海》)。故事背景是小六因在剧组勾搭影帝赵先生,黑帮大老板(倪大红饰)大失面子,遂吩咐陆先生悄然处理此事。作为陆先生的得力下属,渡部连夜押送小六和赵先生去往苏州。汽车行驶在田野间,漆黑的天地被两束车灯刺破。身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越来越远,小六的前途也如夜色般暗昧不明。正是此时,带有爵士色彩的男女英文对唱介入叙事。Liberty swathes this city of shades
幽影之城被自由笼罩
Like gloves on the wings of a bird
如同双翼被束缚的飞鸟
The silken smoke of the words you spoke
昔言似烟缕雾绡
Still rises where you lay
在你安躺的地方至今萦绕
Take me to Shanghai
带我回上海
Take me to Shanghai
带我回上海
To the town where I belong
回到我的心之所向
“带我回上海/带我回上海……”歌声如泣如诉,余音袅袅,感情饱满得几乎要溢出银幕,当然前提是作为观众的你要听得懂歌曲的英文内容。正前方有奔赴战场的运兵车驶来,车灯交会中,故事的转折来临。军车刚刚驶过,身为潜伏间谍的渡部,突然杀了司机和赵先生,随后强暴并囚禁了小六作为性奴。而在随后的故事中,面对不知情的陆先生一众人等,渡部仍然是位好兄弟、好丈夫,是文质彬彬的顾家上海好男人。此处明显“疏离”于电影叙事主体的富有异域感的爵士乐,虽然暗合电影表达的主题,却因受众的主体差异性不见得能完全被观众理解和掌握。导演此时认定电影的受众是受过良好教育能听懂英文的,也因此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去思考小六的所思、所想、所为。这种叙事方法打破了电影故事的时空限制,以介入故事的音乐表达创作者的真正意图。正如袁泉饰演的明星在故事中的片场所言,“这部电影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电影此时展现给观众的是叙事外的潜在忧伤,是乱世中的华丽腔调,也是消亡中的罗曼蒂克。故事中所有个体的命运都被置于上帝视角之下,观众自然都能预知这些角色的命运,但富有情绪化的音乐介入使他们更加关注角色的内心活动,由自己语言能力和认知力补充的潜在故事则不知不觉中弥补了音画不同步的叙事裂隙。
经过导演的重新排列和剪辑,小六的故事自音乐的介入开始,演变成对感情和事实的反讽,戏剧化的人生巧合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电影的开始部分,小六在饭桌上调侃自己戏中角色的命运就能概括自己的一生。她说自己身处感情牢笼宛如行尸走肉的时候,其实还名不副实,直到她被囚禁后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她想去人少的地方,结果她真的被束缚在了与世隔绝的地下室,那里除了渡部就只有一只猫。面对深爱的陆先生,她无意间表露心声,“什么花痴啊,十三点啊,打发时间罢了”。结果后来的时间,她无所事事,都不知道靠什么来打发无聊的时间。而作为陆先生心中真花痴的小六,囚禁的日子也是对过去日子的完全反比:她的每一天,除了吃饭,就只剩下和渡部做爱。从一开始的抗拒到享受这种肉欲,小六最想要的真爱已经成为最奢侈的梦想。可她还想回到过去,想摆脱了无生趣的现在,回到与男人爱恨交加的生活。这样的推断也能合理解释当有机会时,她不想呼救也不想逃走。甚至当有机会拿起手枪,她却迟迟无法扣动扳机杀了那个兽性的男人,只是因为他承诺了要带自己重回上海。最后枪杀渡部的时候,小六不经意间流下的眼泪是悲恸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过往,也是哀悼浪漫梦想的灰飞烟灭。正如歌词形容的那样,小六的故事满是忧伤,是莺歌燕舞上海滩罗曼蒂克的消亡,也是经典叙事的特定时空关不住的现代人面对无奈人生的哀怨惆怅。
导演塑造的小六鲜活而有生命力,面对自由和尊严的代价,她才明白曾经厌倦鄙视的那一切是如此珍贵,这也是她咬牙忍受一切耻辱要重回上海的原因。所以观众也能从小六一边享受、一边流泪的样子,从音乐的变化和做爱体位的不断变化,窥探出她心理转变的前因后果。故事的结尾,面对已经毫无威胁的渡部,小六扣动扳机,那是为了告别过去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继续生存的理由,毕竟活着才有意义。小六的故事由镜头展现出来,配乐也很好地表达了角色感情的变化,但唯有歌词的英文含义才揭示了导演的态度。正如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认为,并非叙事文本中的每一个句子都可视为“叙事文”,在有些情况下,叙述与非叙述评论相互交替出现在叙事文本当中。巴尔认为这样一些非叙述评论会做出“纯粹”的思想观念上的陈述。回到《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影片叙事的克制和冷静基调中,音乐反而带动了角色情绪的流动,而英文歌词的内容则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其对疏离氛围的渲染和潜在故事的启发功不可没。尽管有叙事过程的间断疏离,电影的故事主体还要归于经典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电影是对生活的再现和反映。电影故事是“在特定空间时间因果链条上发生的有先后次序的事件”,而叙事则是对于现实生活的转述和话语表达,是在组织事件顺序并表达创作者的态度中完成的。导演通过故事的开始、发展、高潮和结尾,使观众得以确认、否定或者重新评价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经典叙事风格可以概括为“以人物为中心、封闭的结构、隐形透明的镜头语言、镜头将观众欲望的缝合、隐藏叙事人、故事一直在那里”。这样的叙事可以使观众看到有头有尾、逻辑清晰且具因果关系的电影故事。不同于经典叙事风格,后经典叙事则关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趣味。在电影的叙事层面,则增加了创作者的话语表达,即在电影作品中表现其独有的世界观和电影风格。创作者“并不表现现实,他只表现现实的表象,而对这种表象每个人则可以做各种解释。总之,他创造一种真实的现实,需要观众自己决定对待它的态度。这是一种从个人角度来对待艺术的方式”。在具体创作方式上,后经典叙事经常刻意打乱故事时空进程,利用大量跳接镜头和反复使用某种特殊技巧等随时介入故事。这类电影不再从整体上掌控话语权力,而是从个体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主观摹写。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为例,在杀戮和暴力面前,陆老板的儿子被渡部所杀及他安排手下枪杀渡部儿子复仇时,天籁般的《你在何处,我父?》悠扬响起。与和平的配乐不同,两个孩子的死亡意义不明,战争的邪恶隐藏在英文歌词内容中,这是再神圣的宗教也难以拯救的残酷现实。导演借助故事外音乐拒绝叙事的连贯性和娱乐性,大量利用长镜头、声画对立和跳跃的叙事节奏建立起独特的电影风格,故事的意义则潜在于叙事转折引发的观众想象中。
二、创意性转折
要呈现故事的具体意象,电影叙事还需要摄影、录音、美术等部门的通力合作,涉及画面、调度、表演、音乐等表达技巧,也因此使得电影叙事更具技术挑战性。具体的电影技术则包括场面调度、构图、色调的渲染及后期的剪辑、配音等。《罗曼蒂克消亡史》极具仪式感,摄影、灯光和布景的使用都是精心雕琢,而影片故事重要阶段的配乐,则更是锦上添花,推动着叙事的发展和反讽氛围的渲染。陆先生一家惨被灭门,其毫不知情满是书卷气的儿子也没能幸免。面对血腥与杀戮,屏幕外的观众耳边响起的却是田园诗一般的童声合唱:
Where are you, Father?
你在何处,我父
You’re my world, the life I know
你是我的世界,我所了解的人生
Where are you, Father
你在何处,我父
The day has given away to darkness
那投奔了黑暗的白天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带我回家,带我回家
Where are you, Father
你在何处,我父
I’m buried in your love sealed with blood
你用爱葬我,以血封棺
Take me home, take me home
带我回家,带我回家
鲜血相伴着圣洁,赞美诗中的仁慈上帝遍求而不得,观者无奈又满心恐惧。声画的不同步使得导演的态度极为鲜明:时髦的上海滩洋溢着国际化的和平格调,内里却酝酿着欲望与杀戮的风暴。影片的结尾,小六随陆先生去了菲律宾。为了逼迫渡部签字同意被引渡出去,陆先生命人当面杀了渡部的大儿子,而小六也最终枪杀了渡部。影片中的赞美诗再次响起,平和的乐声中,父辈的造孽不仅使其自身也使无辜的孩子成了罪恶的祭祀品。面对无常的人生,导演通过圣洁的音乐反复叩问:当杀戮来临的时候,万能的上帝又在哪里?歌曲的英文内容,明显打破了故事的叙事时间线,游离于中国故事的背景之外,提醒并引领观众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而反复的反讽式音乐,表现的则是特定时代的乱世众生相,是罗曼蒂克消亡之时现代人无奈的自我救赎。
美好事物的毁灭通常引起观众的共鸣,哪怕是上海滩一点点的美好,消逝了也令人抓心挠肺。电影里的故事首先是人们生活过的,然后才能被人们所讲述。正是因为在生活之中活出了故事,人们才使用叙事来理解自身的生活,所以叙事的形式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合适对象。当特定历史视野不足以表达叙事意图时,就有了导演的主动介入,比如使用故事外音乐引导观众关注命运车轮碾压下个人记忆的幻灭。当电影叙事结构不完整时,角色的自我以及社会身份也因此支离破碎,因为“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体性存在于叙事的一体性,用叙事的开端、中间至结束将出生、生活至死亡连接在一起”。一个故事要打动人心,就绝不能止于表层的叙述,破碎表象下还有更深层次的行事动机和原因。观众通过自己对叙事的阐释来感知潜在的故事,他们在超出表层含义之外了解到的真相也是叙事的一部分。以此观点来看,潜在故事的传达方法是通过“认知差异”,也就是指故事的不同参与者所掌握知识、信息的差异来实现的。参与者在电影中的主角、反面主角、其他角色、观众以及创作者等,如果其中一个参与者知道得比另一个人多些,就会有认知差异。如果观众知道得比主角多一点,也会有认知差异,而导演作为创作者,是参与者中掌握信息最多的。表现在电影作品中,创作者为了传达潜在故事,用叙事手段达到具有认知差异的效果即可。《罗曼蒂克消亡史》中,作为叙事手段,突兀异域音乐的介入引申出潜在故事,表现在观众头脑中可以被认为是叙事过程中嵌入认知差异的结果。
转折点在分析故事时相当有用,对转折点的检测会告诉我们不满意的故事中是否有重要的创造性元素不见了。转折点也可以通过叙事的冲突,引起故事受众情绪的变化。而故事外音乐的介入不仅是很好的转折工具,也是暗藏的伏笔,借以引发观众的认知差异。以《罗曼蒂克消亡史》为例,导演在电影叙事中安排了诸多转折点。身为日本间谍的渡部其实是不称职的,作为好男人的人设过于完美。认识他的人都觉得他是非分明、温柔体贴,是个彬彬有礼的上海好男人。但渡部的斯文表象下隐藏着战争狂热分子的心狠手辣,而其本性之所以暴露仅仅是缘起于某个转折点。渡部奉命潜入上海,接近帮派大佬陆先生,娶了他的妹妹并有了两个儿子,且努力地学做一个上海人。渡部非常成功,以至于他忘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日常生活中过的就是地道上海人的日子。当自己的国家需要时,渡部转变迅速,毫不犹豫地杀了妻哥全家,随后假死,换个身份去了东南亚为国征战。但作为冷血的间谍,他还是不合格的。虽然军国需要,却舍不得杀掉自己在上海的亲生骨肉。正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他又放跑了大舅子陆先生。也正是因为心软,面对妖娆的小六也没有下得去手,这说明渡部并非全无人性的恶魔。对小六的感情,源于某次家宴上,这个女人的耳坠忽闪忽闪地晃,晃得他心里本能的欲望渐渐升发。渡部听陆先生的吩咐送小六出城,导演安排Take
me
to
Shanghai
的故事外音乐介入,虽然背景音乐暗合故事情调,但突兀的英文歌词提醒观众故事将由此转折。暗夜中突现的军车,使渡部忽然记起了自己的间谍身份。耀眼车灯下的小六,耳坠一闪一闪,嘴唇也红得像他故乡娇艳的樱花。他突然爆发杀了司机,把小六抓回了家,给她裹上和服,教她日本礼仪。小六不肯,渡部就打到她俯首帖耳,直到她生生变成了一个温顺体贴的日本式小女人。就如故事中的渡部一样,生活中的人们很少说出他们真正的意思,大家过着双重的生活。人们甚至常常不知道他们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在经典叙事中,故事中的人物不仅要准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还要能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故事发展缺少合理的动机,则意味着转折点的来临,导演此时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来提醒观众。渡部杀人后,按倒小六,纵情放肆了自己压抑的欲望。他事后把女人扔在车里,自己去挖坑欲掩埋尸体,却忘记了车里还有一把枪。小六拿起枪,指向了渡部,却发现他回头的表情近乎嘲笑。历经了爱恨情仇,小六此时的想法与过往已经天翻地覆,完全没了杀他的想法。渡部趁机上前,扼住了小六美丽的脖颈。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故事外音乐再度响起,这次是日文歌曲《赤(あか)とんぼ》(《红蜻蜓》)。熟悉的乡音使渡部想起了刻骨铭心的过去:残酷的战场上,同胞们尸体狼藉,腥风血雨中却飘荡着悠扬又动人心魄的歌:
夕焼小焼(ゆうやけこやけ)の、赤(あか)とんぼ
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
负(お)われて见(み)たのは、いつの日(ひ)か
童年时代遇到你,那是哪一天?
山(やま)の畑(はたけ)の、桑(くわ)の実(み)を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们制作了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课件,并借助蓝墨云班课App构建了基础工业工程云课,实现了在移动环境下的教与学。在云课中设置一些问题以供学生进行交流与互动,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提起小篮来到山上,桑树绿如阴
小篭(こかご)に摘(つ)んだは、まぼろしか
采到桑果放进小篮,难道是梦影
十五(じゅうご)で姐(ねえ)やは、嫁(よめ)に行(い)き
十五岁的小姐姐,嫁到了远方
お里(さと)のたよりも、绝(た)えはてた
别了故乡,久久不能回,音信也渺茫
夕焼小焼(ゆうやけこやけ)の、赤(あか)とんぼ
晚霞中的红蜻蜓呀,你在哪里啊
とまっているよ、竿(さお)の先(さき)
请落在竹竿头上停一停,停歇在那竹竿尖上
思绪恍惚间,渡部想回家。在日本,他有房子也有地。他看着那个他心软留下性命的小六,希望她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返回家乡,他心里甚至憧憬着这样的话语,“我可以种庄稼,养活你们”。两个中国出生的儿子,加上大舅子陆先生还有他爱上的小六,这些他该杀而没杀的人,最后合力拧成了一根绳索,套在了渡部的脖子上。而追本溯源,真正把他缠死的,也许是心间萦绕的乡音搅起的挥之不去的乡愁。
但故事的转折只是相对的,转折点可以使主角的价值观从正面转向负面,也可以从正面转为更加正面,或从负面转为极负面。这个转折一般是相对突然并引发观众认知差异的转变。渡部的本质还是一个罪犯、一个魔鬼,他有一个中国家庭,却也隶属于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电影结尾,渡部的目标得以部分实现,却也有很多梦想被迫放弃。他悲剧的一生在故事的开始便得以注解,个人的命运在动荡的社会中是无根飘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支离破碎。对观众来讲,故事的结果一般会给人类冲突的处理方式点一盏明灯。故事外舒缓平和的《红蜻蜓》来自导演的个人表达,暴力与乡愁间杂,侵略与亲情相扰,流离奔波的人们出现在混乱的时间轴上,在罗曼蒂克消失的上海滩,通过银幕映射出的是各自安生却又无法割舍的爱恨情仇。渡部不是整个电影故事的主角,但这个角色贯穿在整个电影之中,推动着故事的合理发展。故事的情节是人物,人物也可以是情节,因为一旦人物拥有了合理的行为,他们就在驱动情节。只要发生的事件引发了主角有意义的反应,那么他的性格在观众眼里就处于塑形过程中。《罗曼蒂克消亡史》故事中揭示渡部性格的不是突发事件,也不是突然介入的日文歌曲,而是他对突发事件及其引发的脑海中乡音的反应。同样的,驱动情节的也不是事件或者中断事件叙事的故事外音乐,而是确定事件、驱动情节的人物采取的下意识的动作。在此过程中做非叙事评述的是导演本人,依靠的是故事外音乐引发的观众情绪及其相关联的诸般感觉,如兴奋、恐惧、生气、悲伤、厌恶之类。
三、后经典叙事的新动向
《罗曼蒂克消亡史》极具形式感,其后经典叙事考验观众的认知能力,故事间大幅的留白也留待观众的想象力加以填补。但在电影创造出的时空舞台上,罗曼蒂克的情感明显是多余的,故事中的人们浪漫的腔调转瞬即逝,起伏不定的动荡时局只剩下凝重和荒凉,这也许是电影英文名字(The
Wasted
Times
)的由来。人类自从解决了生存和温饱的问题,发现荒废的时间越来越多,所以人们花很多时间去消磨时间,比如电影中帮派成员慢条斯理地吃饭、悠闲自在地品茶,比如陆先生优雅地不动声色地杀人,再比如欲望之前漫长的前奏和感情纠葛等。故事开始展现给观众的是美好与浪漫,随着故事外音乐的突兀性介入,那种种美好的腔调转瞬消失,残酷的真相把虚伪的表象撕个粉碎。导演借助故事外音乐的反讽赋予了影片一种挥之不去的绝望与窒息感,人类就在这浮世繁华里虚度着年华,醉生梦死,只求现在的享受。那罗曼蒂克的气息,恰如英文歌曲中的那双手套,掩盖了那些最原始、本能的欲望,让人脱离了动物本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类的原始本能依然坚挺,那耀眼光彩下的种种残酷因为叙事的转折而暴露无遗,因观众认知差异形成的强烈对比不仅令人触目惊心,更让人扼腕叹息。《罗曼蒂克消亡史》叙事节奏缓慢,情节娓娓道来。电影原著的六个小故事被随意拼图,挑出有限的三块,经过故事外音乐造成的转折点刻意地摆放,声画分离、交叉剪辑,最终让人看到的是完全拼成后绚丽的声画盛宴。但导演在银幕上铺陈出的人间繁华却脆弱不堪,以至于几首故事外音乐就能轻易地将其撕开,露出人类最真实的一面:赤裸,残酷,却又简单纯粹。故事的情节被银幕上并不存在的外文歌曲持续性地打断又推动,几乎所有引发故事转折又触动人心的时刻,都在镜头外由观众的想象力从现代人的视角加以填补。留在观众心中的则是中国的一段历史和个人在历史大潮流中挣扎的困境,以及故事外音乐引发的从现代视角反观过去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一主题让观众耳目一新,带来了别致的观影效果,为主流的历史如何在电影中重新解读提供了新的范例。故事外音乐的富有想象力的使用,能够使话语与故事、叙述者与被叙述内容、电影与观众、想象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形成良好互动,为后经典叙事带来新的方向,叙事的内容及方式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