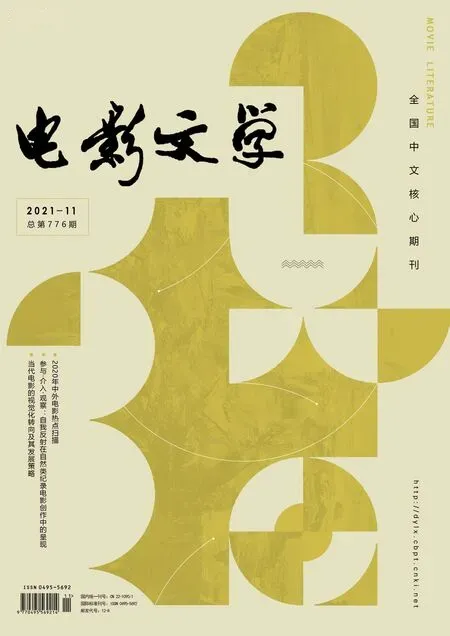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送你一朵小红花》:“伤痛美学”叙事的多维关照
王玉良
(南阳理工学院传媒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4)
2021年开年大戏《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导演继《滚蛋吧!肿瘤君》之后,又一部真实感人的精品佳作。影片以小见大,从两个普通家庭着眼,折射出千千万万个有此相似经历的社会个体。作为一位80后导演,韩延以他独特的视觉和细腻的情感,采用“伤痛式”的美学体验,为每个生活在困顿与不幸中的普罗大众,熬制了一道味美绝佳的心灵鸡汤。美国俄克拉何马大学的罗纳德·施莱费尔教授在其《伤痛美学:音乐、文学和感官经验中的符号学与情感理解》一文指出:“在音乐、诗歌和散文的审美体验中,往往有探讨伤痛极端体验的内容。一般来说,这种体验是由引导人们的注意力和期望经验图式所制约的。尽管经验的直接性是它的决定性品质,但经验本身却是间接性的。”这一论点,可以说对“伤痛美学”(The Aesthetics of Pain)的本质特征做了精准的分析。而对于电影来讲,无论这种经验是“直接性的”还是“间接性的”,都很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正是通过这种“伤痛美学”的多维叙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会层面,全方位展示了面对生死问题时普通人的两难处境。
一、个体层面: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
对生命意义的终极思考,一直是文学和艺术作品关注的永恒主题。在电影创作中,这类主题往往通过角色所遭受的重大伤痛,唤起观众对普通个体的生命关怀。韩延在《送你一朵小红花》特别纪录片(诸葛亚寒导演,2020)中曾讲道:“我觉得关于生命的表达、关于生死的表达,其实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个母题。《小红花》中有一个比《滚蛋吧!肿瘤君》里面更往前走的东西。”两部作品相较而言,《小红花》少了许多叙事和形式上的幽默,对生死问题的处理更加严肃。同样是癌病患者,韦一航的“丧”与熊顿的“豁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本片中,马小远似乎就是熊顿的化身,她身上的那种乐观、豁达在不断地感染韦一航,并把他从悲观厌世的低落状态中拉回到明媚的现实。这些不同的个体,投射出了韩延导演对生命的体悟,以及展现人在生死边缘的生活态度。在对生命意义终极思考的同时,注入了创作者强烈的同情与关怀。
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电影通过视听手段传达创作者的情感立场。韩延导演善于通过视觉语言来表达人物的内心感受,把对人物个体生命的终极思考用强烈的影像符号传达出来。比如在《滚蛋吧!肿瘤君》中,当女主角熊顿遭遇男友背叛后,我们看到,她眼中的整个城市迅速成了一个冰冻的世界,这些影像都很好地传达了当时人物内心巨大的心理波动。在《小红花》中,同样的视觉符号用来展现韦一航病发时的臆想,大有异曲同工之效。影片中不断重复出现的那个碧海蓝天,事实上是他向往的精神世界,也是超脱现实命运苦痛的理想追求。导演通过这种视听手法,建构了对生命终极的美好想象。死亡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中,有一个没有病痛、没有折磨的美好存在。
韩延创作的这两部病痛故事的电影,其最终的回归都是关于爱的主题。通过爱情拯救癌病患者的现实痛苦,《滚蛋吧!肿瘤君》中的熊顿爱上了自己的主治医师梁医生,与伟大的爱情相比,病痛的折磨似乎是那么微不足道。《小红花》同样通过韦一航与马小远的爱情,让我们看到了患病中的恋人惺惺相惜,感受到了爱情的无限力量。爱情,作为个体成长的必然经历,也是生命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爱化解病痛带给患者的折磨,这也是个体成长的重要表征。尤其是韦一航这个角色,通过他的经历,我们看到了癌病患者所承担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二、家庭层面:对亲缘结构的温情维护
与西方此类题材电影作品相比,中国电影在“伤痛美学”的叙事中倾注了更多对“家”的关注。这很明显与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有莫大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固然由历史的和文化的因素所导致。一般说来,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各种伦理关系便成了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因为每当生命个体出现巨大变数的时刻,最先受其影响的自然就是家庭结构。作为家庭团体的重要元素,每个个体都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由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所形成的这个亲缘机构,就构成了这个社会生态关系的基本单位。对于家庭来讲,任何一个成员的生死存亡定会对这个整体产生巨大影响。
与此前的《滚蛋吧!肿瘤君》相比,《小红花》把家庭关系放在了更为醒目和重要的位置。前者更加强调一种由朋友所营造的团体关系,相互间的珍视帮助,这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小家庭;到了《小红花》这里,真正把亲缘结构所组建的家庭推到了前台,父母在这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尤其在韦一航一家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个三口之家似乎是中国家庭的典型缩影。任劳任怨的父亲、斤斤计较的母亲和叛逆乖戾的儿子,形成了这种亲缘结构。为了使儿子尽快从癌病的梦魇中回归现实,父亲和母亲各尽其责,为了整个家庭不停付出,在平凡中透出了不平凡的艰辛。但创作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把这种亲缘结构的范围做了更大扩展。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家人聚会的那场戏,奶奶、叔叔、姑姑向爸爸妈妈表示,他们同样可以不惜一切,为救治韦一航的疾病施出援手。这种叙事策略,很明显扩大了家庭结构的内涵与外延,在亲缘结构的维护方面做了更为广阔的探讨。正如香港电影《新不了情》(尔冬升,1993)的处理手法一样,这种对家庭亲缘结构的温情维护,在情感表达中才能得到观众的认同,对中国传统的“家”的意义做了再次明确的诠释。
在对家庭亲缘结构的维护中,创作者主要是通过诸多细节来还原生活的原貌。中国早期电影艺术家程步高曾讲过,故事的“大情节是骨干,细节是血肉。骨干上生了丰富结实的血肉,好像一个人,生来就体态丰满,风度翩翩了”。优秀的电影作品往往在细节处理上精雕细凿,细节不仅能带给观众一种真实感,而且还往往能使我们触摸到作品的时代温度,感触人物的真挚情感。影片《小红花》最为明显的特征就在于作品对细节的大量呈现,争得观众的广泛认同。有评论者指出:“《送你一朵小红花》在国产电影中体现出难得的艺术完成度和感染力,它用大量饱满的生活细节使这个故事有了人间烟火的质感。”这些“人间烟火的质感”,更多地来源于对家庭生活点点滴滴的呈现。韦一航的妈妈为了能节省一点钱,在停车场与保安的死缠硬磨、在菜市场与小贩的斤斤计较,这些细节还原了一位真实可爱而又伟大的母亲形象;父亲为了使儿子营养均衡,在家琢磨各种菜艺文化,为了能增加收入,偷偷加班加点开出租等细节,也很好地把这种父爱如山的感情还原出来。另外,影片中最重要的细节,就是马小远画在韦一航手背上的那朵小红花,很好地契合了影片主题。就是这朵小红花,让一直活在自我世界中的韦一航,迈出了接纳现实生活的第一步,真正地敞开心扉与别人交流。“小红花”的含义在这里有了更为深层的表露:代表了积极生活的每个人。正是这些细节呈现,让影片时时处处充满着一种家庭般的温情。在展现伤痛叙事的同时,抚慰了一个个用亲情搭建起来的心灵巢穴。
三、社会层面:对边缘群体的价值观照
韩延导演在本片特别纪录片的采访中谈道:“这种对陌生人的关怀,我们从对一个家庭、一个族群的关怀,扩大到陌生人的关怀,我觉得这是整个电影表达的一个半径。”因此,电影《小红花》不仅是在讲一个人的故事,也是在讲一个群体的故事,它有着更为宽泛的社会层面的价值和意义。正如导演口中的这个“半径”,它会辐射一切周围与之有关的人和事,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态群落。以韦一航、马小远为代表的这类癌患病人,他们始终挣扎在“个体”与“社会”的边缘。一方面既希望能被社会认可并接纳为正常人,但同时自身的现实处境又往往自我设置了一道屏障。对于这个边缘群体,影片创作者给予了极大的价值观照。“影片以韦一航这个脑癌少年的视点辐射出抗癌群体和普通老百姓的社会面,医院里失去爱女的父亲、聋哑快递小哥、丢失孙子的奶奶……这些群像的闪现都对应着当下社会新闻里的生活片段,体现了主创对周遭世相的感知和关怀。”以此足以看到,影片在对边缘群体的观照方面,体现了明显的点、面结合的特征。
所谓的“点”,就是故事中呈现的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以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那位照顾小女孩的父亲为例。通过这位丧失爱女的父亲,让我们知道了这个边缘家庭的孤独和无助。这无意间与《滚蛋吧!肿瘤君》中的那个小女孩形成了对照。同样是一位未成年的小孩,同样是一位无助的父亲,同样的结局,残酷的病魔最终都夺去了他们幼小的生命,但《小红花》却给出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我们看到结尾处伤心的父亲走出医院后,有人以他女儿的名义给他点的一盒外卖,彰显了人间大爱。对于这样的边缘家庭,在社会中随处可见,他们痛失亲人的心情很多人可能感触不到。对于创作者而言,这种处理方法,无疑是希望我们能伸出友善之手,尽可能地对他们进行温暖的抚慰。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只要人人都能奉献一点爱,他们就不会孤单。
影片在“面”的处理上,设置了一个特殊群体,即那个由爱心人士小吴组织的癌病患者病友群。正是因为共同的经历、共同的伤痛,使他们走到了一起,相互抚慰、相互支持。在这个群体中,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家庭,却能相濡以沫。当群体中有人逝去时,他们一起为她开追思会,除此之外,他们还举办不定期的群体聚会、思想交流、励志讲座等。正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组织,让这群边缘人有一种家的归宿,并试图以集体的形式融入现实的社会生态中。在“伤痛美学”的点触中,创作者找到了一个支撑点。影片通过对这个边缘群体的详细描述,真正使观众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每一个普通人了解到这个群体内心的真正“伤痛”,它们不只是肉体上的,更多时候来自精神层面。因此,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一个伤感的个体故事,也是一个群体故事,更是一个社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