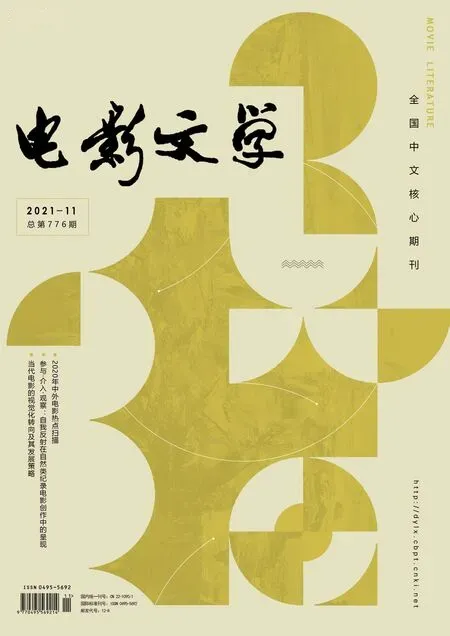科幻电影中未来城市的时空建构与具身体验
袁 强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48)
电影起源于城市,记录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重组了现代城市的文化空间,电影中的现代城市图绘展现了现代人的生活境遇。而科幻电影作为电影中的一种类型,突出了电影的虚构性、想象性,表现了对人类未来的关照。科幻电影不再拘泥于再现现实世界中的城市样貌,它可以对镜头中的城市进行任意的时间设定与空间变形,使存在于想象中的未来城市得以具象化地出现。由此,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不再仅是故事展开的背景,它能够介入科幻叙事,推动故事的发展,甚至决定故事的结局。德波拉·史蒂文斯在论及想象中的城市时指出,“城市是以一系列相互矛盾却又相互补充的方式被加以理解和体验的”,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便是在矛盾与补充、想象与真实之间表现进步与衰退、流动与区隔,以及虚拟与现实。
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在向未来行进的过程中呈现出进步与衰退两种情形,一者是科技发达、社会进步的光明世界;另一种则是荒废、破败的末日景象,表征人类未来的暗淡前景。从未来城市的空间结构来看,未来城市的空间布局中蕴含着流动与区隔之间的对立,人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打破空间区隔以实现流动的自由。另外,赛博空间的出现为人们开辟了新的精神领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城市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的乌托邦。科幻电影在对未来城市的呈现中表现出了人们对人类未来、对科技过度发展的担忧,以及对赛博空间的出现所带来的、虚拟生活过度侵占现实生活的反思。以未来城市为主场展开的科幻叙事,传达出了现代人在技术危机中的身份焦虑,在未来世界中,人类将寄身何处的问题,既关涉特定时空中的未来生存,也关涉内在于人的具身体验与存在之思。
一、进步与衰退中的时间向度
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具有时间向度,它们分列走向了进步与衰退两种不同的未来图景。对于不同时期的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形塑差异,芭芭拉·门奈尔曾指出,早期科幻电影中出现的是现代主义、未来主义的城市,它们作为乌托邦、反乌托邦的背景而出现;而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现代性的幻想破灭,电影中出现的更多的是衰落的城市,“在后期的科幻电影里,城市的环境已不再是现代性和技术革新发生的地方,而表现为现在和过去的肮脏的城市”。自21世纪以来,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的形塑更加复杂化,彼此之间在特征上甚至表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在具有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的未来城市形塑中,人们虽然面临着人与科技之间的诸多矛盾,但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将之克服。以《明日世界》(Tomorrowland
,2015)、《星际特工:千星之城》(Valerian
and
the
City
of
a
Thousand
Planets
, 2017)为代表,这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以繁荣、持续进步的形态出现;而在《银翼杀手2049》(Blade
Runner
2049,2017)、《掠食都市》(Mortal
Engines
,2018)等电影中,人在后末日时代挣扎求存,城市的衰退隐喻了人类文明的衰退。在科幻电影中,处于进步状态的未来城市以建筑群高耸有序、立体交通复杂交错、交通工具高速便捷为主要特征,城市中各类领先于影片所属时代的技术装置极具未来感与科技感。《明日世界》呈现了人类在次元外建造的科技之城,只有顶尖的、最具想象力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才有机会进入其中。这部电影将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化的科技研发之城进行了具象化地呈现,城市中的一切都服务于科技研发的需求,奇形怪状的建筑高耸交错,悬浮列车与各类飞行器在空中盘旋。电影突出表现了工业化、科技化对人类生活的积极影响,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及科技之于人类未来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同样在未来城市的图绘中凸显进步与科技的意义。在这部电影中,人类发射到地外轨道的阿尔法空间站成为外星人聚集的太空站点,在迁往麦哲伦星流四百年之后,发展成一个有着3236个外星物种混居的“千星之城”。电影在主人公韦勒瑞恩追逐缪星人飞船的场景中用俯视镜头展现了“千星之城”的外部风貌。这座建造于太空中的城市不受引力束缚,城市建筑不再是单一的垂直向上,而是向不同方向扩展,而且形态各异以适应不同种族居民的需求,各类飞船在灯光绚烂的建筑群中穿梭,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外星未来之城呈现在观众的眼前。这类电影通过对这些进步图景中的未来城市的描绘,展现了科技在人类向未来迈进中的重要作用,它们对科技的发展持有乐观态度,仍将科技的进步视为人类发展、繁衍的必要前提。
上述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以现代化、科技化的大都市面貌出现,而衰退的未来城市则指向了人类的另一种未来:资源消耗殆尽、生态环境崩溃,人类在技术统治、末日危机中探求自我救赎的可能性。以《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 1982)、《掠食都市》等电影为代表,它们所呈现的是衰退的城市。《银翼杀手》改编自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
)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到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 1968),保留了菲利普·迪克对近未来末日的悲观想象,这部电影也被解读为后现代状况的典型样本,表现了“指涉性与再现在拟仿物与模拟的大量繁衍下被吞并”,“真实性的消失与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银翼杀手》设想了2019年的洛杉矶:城市终年处于雾霾之中,不见天日,在夜幕与酸雨中,飞行器、高楼大厦与具有东方风情的霓虹灯在夜幕中影影绰绰。被限定了寿命、在外太空服役的复制人为解脱自身的枷锁偷渡回地球,人与复制人在萧条的城市中混淆难辨。这种赛博朋克科幻叙事在《攻壳机动队》(Ghost
in
the
Shell
, 2017)、《银翼杀手2049》等电影中得到了延续,电影中的未来城市有着高度发达的科技,而人们的生活质量却极为低下,而且人们在科技的冲击下难以区分真实与虚假,人类在末世消遣余生,反而是复制人在奋力追求人的身份,甚至意图成为一种超乎于人的地位的存在。不同于《银翼杀手》中的不断向外蔓生的萧条城市,《掠食都市》展现了一种孤绝化的未来城市设想。在这部电影中,21世纪的人们启用了量子武器,导致了全球性的灭世灾难。此后,幸存者们在长达一千年的末日生存中形成了新的聚居模式。他们居住在移动堡垒城市之中,堡垒城市以蒸汽为动力,在荒野中移动,遇到其他的据点,便将其吞噬,掠夺其资源,构成了一种末日孤绝的未来城市图景。这类想象以不同人类聚居点之间的联系的断绝、人类生活空间与自然生态的隔绝为特征,描绘了一种极端境遇下的人类未来生存状态,人与人之间彼此戒备,城市与城市之间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之中。
科幻电影中的进步或衰退的未来图景建立起了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未来之间的关联,蕴含着现代人对技术与人文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思考。
二、流动与区隔中的空间构成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的空间规划日益明晰,迈克尔·迪尔探究了隐含于城市规划中的微观权力,“规划与权力相关,它所取得的结果服务于一个社会中权势代理人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能使隐藏于城市空间结构设计中的意识形态或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得以浮现。
科幻电影以独特的城市地理状貌隐喻未来社会中的权力关系与身份区隔,正如爱德华·苏贾指出的,“空间化勾画出权力和政治实践的一种城市地图状貌,而这种地图状貌常常隐匿于各种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中?”。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
,1927)便是以空间区隔来表现阶级区隔,作为“手”的工人与作为“脑”的资本家生活在不同的空间。资本家们生活在上层空间,他们的孩子在运动场健身、比赛,在花园里、歌舞厅嬉闹;而工人在拥挤的地下城中冒着生命危险辛苦劳动,维持大都会的运转。电影通过上层空间与地下城的空间区隔表现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进而表现工业体系、技术专制对人的价值、情感与自由的剥夺。这种空间设计成为科幻电影中的常见母题。《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
:Battle
Angel
,2019)同样是通过上层空间与下层空间的隔绝来表现身份区隔。这部电影设想了26世纪的人类未来,在未来世界中人类的生存空间被分成两个区域:地面上的废铁城与悬浮在空中的名为撒冷的悬浮城市。撒冷城中科技发达、生活条件优越,撒冷人自视为上等人;而废铁城一片破败、罪犯横行,人们在撒冷倾倒的垃圾中寻找可以回收的科技产品。废铁城的工厂、农场为撒冷人提供生活物质,但废铁城居民不得进入撒冷生活,这种空间的区隔构成了阶级的划分。此外,区隔化的空间结构也隐喻了种族间的身份区隔。在《星际特工:千星之城》中,“千星之城”分四个区域,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地理特征与不同类型的聚居种族。城市的南部为液态区域,以从事种植业的普隆族为主;北部为气态区域,居住着感知敏锐的阿兹莫人;奥姆莱人聚集在东部区域,掌控计算机制造、金融、银行业;西部则是人类和其他物种聚集的大气加压区。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将不同种族间的生存空间区隔开来,地理环境的差异带来了个体在不同空间中流动的阻碍。每个种族固守自己的生活空间,波兰巴瑟人便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他们禁止外族进入他们的领地,闯入其中的特工被献给首领当大餐;而失去自己“根据地”的种族即意味着灭绝,具有变形能力的外星人种族流离失所,不能获得身份认证,变形人泡泡成为非法移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只能生活在“千星之城”的底层,最后在混战中丧命。
未来城市的空间构成在对流动的抵制中分隔阶级与种族,就区隔与流动的关系而言,“未来城市的空间隔离术是一种阻止流动的极端想象,是空间维度上的切割和隔绝”,而流动作为抵制区隔的力量,在构成了对区隔的反抗。在21世纪初,英国学者约翰·厄里、蒂姆·克雷斯韦尔等人推动了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流动性(mobility)的研究。流动性指涉人或物的空间移动与阶级、地位的变化。厄里指出:“流动在当代世界变得异常重要——事实上,流动的自由是21世纪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体现在各类大众媒体、政治和公共领域之中。”科幻电影通过流动的诉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来表现个体对阶级与种族身份区隔的反抗。
就《银翼杀手》而言,电影中的洛杉矶便是一个阶级固化、人与复制人对立的混乱城市。在主人公德卡乘坐飞行器穿过城区前往泰瑞尔总部的场景中,他看到泰瑞尔大厦在洛杉矶的夜幕中耸立,高耸的金字塔形建筑反射着金色的光泽,象征着财富与权力的稳固,与贫民区的破败对比鲜明。电影中的复制人从事开发外星、外星殖民等危险任务,被禁止回到地球,违反禁令的复制人会被银翼杀手处决。以莱昂为首的复制人为了获取与人类同等的寿命与权利,打破了空间隔离的禁令,来到洛杉矶与人类周旋,表现出对空间隔离、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反抗。再如《战斗天使:阿丽塔》,主人公阿丽塔的真实身份是“火星联盟”的战士,他们的使命就是毁灭所有的悬浮城市,打破撒冷人的特权地位。就像达芙妮·斯佩恩所说的,空间区隔构成了“一种强势集团对弱势集体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机制运作”,城市空间结构改变的过程也是权力关系重建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流动与区隔的角力。区隔以禁闭、安全与秩序为目的,而制约与禁闭所引发的反抗造就了城市的空间格局的改变。未来城市中的流动与区隔的冲突,也是秩序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人(或非人)在对秩序化的空间区隔的反抗中表现出来对自由、平等,以及身份认同的渴求。
三、赛博空间与现实世界中的具身差异
20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首先在他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提出了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概念,指存在于计算机网络中的由数据架构的虚拟空间,这一概念对《异次元骇客》(The
Thirteenth
Floor
,1999)、《黑客帝国》系列(The
Matrix
,1999,2003,2003)等科幻电影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近十年来,《源代码》(Source
Code
,2011)、《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
,2014)、《头号玩家》(Ready
Player
One
,2018)等计算机虚拟现实题材电影相继出现,使之成为科幻电影中的前沿题材。这类电影中的虚拟现实给电影中的人物带来了一种新的具身体验。在现实世界中,人的身体处于事物之间,人不能在身体之外感知世界,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人不是心灵和身体,而是具有身体的心灵”。而赛博空间的出现带来了一种讨论身心关系的新情景。从哲学视角来看这种虚拟现象,“当主体都可以解构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身份信息,并在赛博空间中进行流动时,人的自由的本质属性也许能在最大的可能条件下得到实现”。在《超验骇客》《头号玩家》等电影中,主体在赛博空间中摆脱了肉身的局限与现实生活中的窘迫,他们在赛博空间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另一方面,新的具身体验中也潜藏着使人们沉迷虚拟、逃避现实,甚至被计算机掌控的危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出现于1946年,在1965年上映的电影《阿尔法城》(Alphaville
)中便出现了人被计算机控制、计算机掌控城市的极端想象。《阿尔法城》呈现了人类被计算机统治的未来,电影中的城市“阿尔法城”在计算机的计算、掌控下高度发达,成为“银河系的首都”,但是市民必须完全遵从逻辑理性而泯灭感性,完全遵从计算机推算的指令,在阿尔法城的路标中标示,“阿尔法城:安静 逻辑 安全 谨慎”。整座城市充斥着压抑、紧张的气氛。在电影中,不服从指令,做出违反逻辑的行动,比如在妻子葬礼上流泪,便会被处决。这部电影在强调实用与功能性的建筑设计中凸显理性与秩序。这类城市想象在未来主义的城市图景中展现工业设施、科技对人的宰制。赛博空间的出现加剧了现代人对科技失控的危机感。科幻电影对虚拟城市的具象呈现引发了人们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思考,以及在具身体验发生颠覆性变革的未来社会中,人将如何自处的反思。《异次元骇客》呈现的便是一个虚拟与现实层层嵌套的未来城市。在电影中,科学家富勒在计算机网络中模拟了一个以1937年的洛杉矶为原本的虚拟城市,他可以通过传输设备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虚拟城市中的模拟角色身上,由此他可以从1999年回到1937年纵情声色。但是富勒发现,他认为的现实中的1999年的洛杉矶也是一个虚拟城市,由2024年的大卫和他妻子创造,而他只是一个在模拟世界中研发出同类虚拟现实技术的模拟角色。这部电影呈现了1937年与1999年的洛杉矶,以及2024年的未来城市,它们都是计算机模拟出的、数据化的虚拟空间。在电影中,当主人公道格拉斯突破路障来到洛杉矶的郊外,“世界的尽头”因算法故障而出现,显现出数据网络架构起虚拟世界的轮廓,人在虚拟世界中被“上层人”操控而不自知。在《黑客帝国》系列中也有着同类的表达:人类被矩阵系统控制生活在虚拟世界,以尼奥、墨菲斯为首的反抗组织在人类的最后领地“锡安”对抗矩阵系统,而事实上,“锡安”只是系统为反抗分子准备的另一处虚拟空间,人们在系统控制下的虚拟世界中难以回归现实世界。
虚拟现实技术赋予了未来城市以新的存在形态,虚拟世界的吸引力冲击了人们面对现实生活的勇气,科幻电影在虚拟城市的构建中表现出对现实与虚拟的关系的反思,反思人们是否还能认清现实与虚拟的界限,是否还能在虚拟世界中掌控自身。
《头号玩家》中的故事发生在2045年的哥伦布市,哈利迪开发了名为“绿洲”的虚拟现实游戏,它能实现身处游戏中的玩家的任何幻想。哈利迪在临终前宣布,谁最先通过他设置的三个关卡,集齐三把钥匙,便能获得“绿洲”的支配权与他的巨额遗产。第一个关卡以纽约城区为地图,玩家需要驱车穿过纽约城区,避开阻碍物,抵达终点的花园,首位抵达者便能获得第一把钥匙。电影将现实空间中的城市地理融入虚拟世界,在游戏世界中架构了虚拟的纽约,并赋予了自由女神像等地标性建筑以游戏的功能,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成为第一关游戏开始的指令枪。此外,《头号玩家》中还出现大量的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漫画与游戏中的场景。玩家在第一关中会遇到美国经典科幻电影《金刚》(King
Kong
)中的大猩猩金刚,它从帝国大厦上一跃而下,阻碍玩家通关。大猩猩金刚爬上帝国大厦,粗野狂暴的生物爬上纽约的制高点与人类对抗。除了金刚之外,玩家还会遇到攻击人类的霸王龙,霸王龙在城区攻击玩家的场景与《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
,1997)中霸王龙闯入圣迭戈市区的场景构成了互文,两者都在“怪物”入侵城市的场景中隐含了对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的反思,这种消解二元对立的文化观念启发了人们对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虚拟现实等高科技的发展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一种新的可能性随之出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城市可以取代现实世界成为人类的主要生存空间,而现实成为难以追寻之处。在《异次元骇客》中,人们生活在层层嵌套的虚拟城市之中,无法追溯模拟的本源,每个时空中的人都认为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而最终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模拟角色,生活在上层空间创造的虚拟世界中。《黑客帝国》也展现了极端化的人类生存境遇,人被“矩阵”控制,生活在虚拟城市中,而身体成为“矩阵”的伺服装置,为系统提供电能,“矩阵”用这种极端的方式维持系统的运作与人类的延续。尼奥、墨菲斯等“觉醒者”面临着是继续在虚拟城市中安稳生活,还是与系统抗争、为回到现实而奋战的选择。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也在系统的计算之内,重归现实的希望并不存在。在“矩阵”控制人类的未来想象中,人类完全失去了重归现实的能力。
在虚拟现实的冲击下,人们如何在虚拟世界中界定自身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头号玩家》中,虚拟现实技术高度成熟,人们可以在虚拟游戏中任意地改造世界、改造自身,游戏世界成为人们寻梦的乌托邦。人们沉迷于虚拟游戏而逃避现实生活,除了饮食、睡眠等基本生理需要,人们的社交、工作、旅游等日常生活完全在游戏中进行,电子游戏成为人们生活的主导,而现实中的城市步步衰退。主人公韦德·沃兹生活在贫民区,整片区域没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钢管架建的脚手架上排列着不计其数的集装箱,集装箱被复杂的电缆连接在一起,人们居住在这些废弃的集装箱中。哥伦布市的中心城区也是一幅混乱、衰败的图景,脏乱的街道上行驶着破旧的交通工具,这与游戏中的高科技、超现实的光怪陆离对比鲜明,人们不再试图改变现实,而是在虚拟游戏中沉浸自身。《头号玩家》虽然表现了虚拟游戏对现实生活的侵占,但它与《异次元骇客》《黑客帝国》仍有所不同,电影中的人们并未完全丧失回归现实世界的能力。韦德和同伴们通过了哈利迪的测试,在拿到了“绿洲”的支配后,他设下每周停运两天的限制,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投入更多的精力。电影所设想的未来城市虽处于衰退的境地,人们的现实生活不断萎缩,但人们仍有回归现实、重建现实中美好世界的可能。
四、寄身何处:面向技术危机与身份焦虑
科幻电影中出现了诸多不同类型的未来城市,表现出对人类未来前景的不同设想。从未来城市的未来指向上来看,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呈现出进步与衰退两种情形,《星际特工:千星之城》《明日世界》呈现了科技发达、社会进步的人类未来,而《银翼杀手》《掠食都市》呈现的则是衰退的城市,人在末世为生存而挣扎。从未来城市的空间结构来看,区隔与流动的力量并存,它们共同形构了未来城市的地理特征,在《大都会》《阿丽塔:战斗天使》等电影中,城市被区隔化,处于被压迫状态的人或非人为流动的自由而不懈努力。在《异次元骇客》《头号玩家》与《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部分觉醒者为返回现实世界不懈努力。时间向度、空间结构与存在形态构成了科幻电影塑造未来城市的三个维度。不论是进步与衰退、流动与区隔之间的对立,抑或是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在具身体验上的冲突,都凸显了现代人在面向技术危机时的身份焦虑,以及人类未来将寄身何处的存在之思。
未来城市在科技进步与人类生存危机的矛盾中显现自身,包含着现代人对技术失控的担忧。带有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的影片虽然认为人类仍能把握世界、把握自身,但也呈现了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明日世界》中,世界末日的出现正是因为人们试图研发一种预知未来、回观过去的时间装置。技术危机在衰退的未来城市图景中表现得更加直接。在《掠食都市》中,人们将量子武器投入战争,引发了灭世灾难,直到一千年之后,幸存者们才有了重新回归自然界的可能。计算机控制人类、人类陷入虚拟世界不能自拔,同样是技术危机的极端化表现,在《黑客帝国》《头号玩家》等电影中,无论是人类能否区分现实与虚拟,能否具有重归现实的能力,技术都不再单纯作为人类的工具而出现,它成为人们需要设法限制,甚至与之生死相搏的对象。
在科幻电影中,技术危机的背后隐含着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在科技的高速发展中,人类逐渐赛博格化,乃至与外星种族的混居,传统的人本位伦理失效。由此,人们的身份认同的寻求日趋复杂化,“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而这种选择在后人类的境遇下面向多个维度。它不仅指涉了空间区隔下的阶级区分,还扩展到人与非人之间的身份纠葛。首先,在诸如赛博格化、人造人等高科技高度成熟的境况下,人的概念的变化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焦虑。《攻壳机动队》中的米拉·基里安少佐与《阿丽塔:战斗天使》中的阿丽塔都是完全赛博格化的人类,她们只保留了脑部组织,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可替换的义体,身体成为不必要之物。面对着“人何以为人”的困惑,她们最终在与他人的情感连接中确认了自身的人的身份。复制人等人造个体在行为与情感上与人类无限接近,在《银翼杀手》中,人类与复制人必须通过专业的“移情测试”才能区分,他们为争取与人类同等的权利而奋战,这也影射了人类自身在后人类语境中的身份焦虑。此外,身份焦虑还体现在人类与外星种族的共处中,人类面临着对自身的重新定位。在《星际特工:千星之城》中,阿尔法空间被称为“人类智慧的结晶”,而在它发展为数千外星种族的聚集地之后,人类失去了对它的主导权,甚至有着被驱逐出城的危险。
结 语
科幻电影呈现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展望科技不断进步所带来的人类生活境遇、权力关系,乃至伦理观念变化。科幻电影中的未来预示也许都不会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但它们体现了现代人对未来世界的恒长探索,以及对当下现实生活的深切关照。科幻电影中的未来城市形塑,不仅通过呈现进步或衰退的未来图景来反思现实,还在流动性与空间区隔的矛盾、电影中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冲突中进行意义建构,现代人的技术危机与身份焦虑寄寓在未来城市的时空建构与具身体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