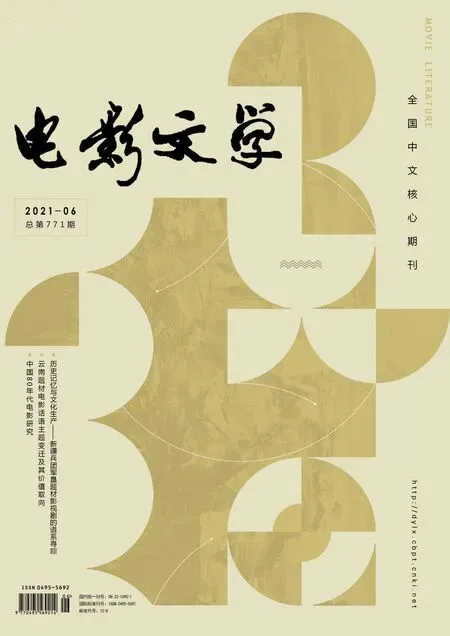新时期之初主流电影的症候式阅读
——兼谈谢晋电影的叙事伦理
段善策(海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与影视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一、艰难起步:新时期之初的创作语境
一直以来,与共和国电影史上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的身份显得暧昧而模糊。有人把该时期叫作“徘徊时期”,还有人把它叫作“转折时期”,有人把它称为“复苏时期”,还有人则视其为“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事实上,1976年10月之后到1979年看似不长的时间面临修补和接续传统断裂的历史重任,是“从一个断裂的历史边界上找到通往过去的桥梁”,为迎接“新时期”提供艺术和思想准备。尽管该时期多数影片缺乏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建树,但仍可以“《于无声处》”听到“《生活的颤音》”,看到“《苦恼人的笑》”“《并非一个人的故事》”,触到“《春雨潇潇》”里“《樱》”上绽放的“《小花》”,也曾感受到“《青春》”里的“《泪痕》”。作为社会意义与价值再生产的公共文本和文化场域,这些影像向社会激流裹挟的普罗大众提供现实的解释与精神的慰藉。对艺术家而言,如何描述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不仅关乎艺术技巧,更关乎艺术观念和自我想象。中国第三代导演的集体“返场”尤为耐人寻味。英雄人物或如赫拉克勒斯般披荆斩棘,或如普罗米修斯般茹苦领痛,是谢晋《啊!摇篮》、谢铁骊《大河奔流》、成荫《拔哥的故事》里永恒的主体。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菲勒斯”以父之名傲然挺立于银幕中央,成为创作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自我想象的投射。那些被壮志未酬的英雄泪和挥之不去的怀乡梦所萦绕的历史场景滑脱为潜意识场景。相比于再现“现场”,创作者更关心的是制造关于历史的集体记忆。一些影片的叙事时间架空而直接接续到“十七年”,比如谢晋的《青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开启了“指认他乡为故乡”的叙事模式,新时期的寻根电影(如《城南旧事》)、90年代的怀旧电影(如《阳光灿烂的日子》)乃至新世纪的历史题材(如《归来》)皆于此生发展开。总之,历史语境与自我想象形塑了影像无意识——无论是审美与教化的功能之辩,还是精英与大众的趣味之别,都跟对个人—国族关系的想象方式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在自我想象和历史现实的合围下,电影创作表现出一种审美视野下的政治无意识。
二、新时期之初主流银幕的美学特征
新时期之初的主流电影无论是表现正面战场的战争片(比如《延河战火》《赣水苍茫》),还是探索性质的反特片(比如《保密局的枪声》《熊迹》),无论是温情的革命浪漫史(《归心似箭》《啊!摇篮》),抑或传奇的个人英雄史(《拔哥的故事》《吉鸿昌》),它们都试图通过各自的书写方式再现同一个宏大叙事——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历程——的某一个瞬间,并交会成为一幅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长卷。
除了谱写汉民族的革命史诗,被整合进民族—国家记忆工程的少数民族叙述也得以复兴。官方意识形态批准在少数民族地区恢复或者增设制片厂建制。除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等老牌制片厂继续生产,天山和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恢复建制以及广西电影制片的成立有力地充实和壮大了少数民族题材的摄制队伍,诞生了《战地黄花》《祖国啊,母亲!》《连心坝》《奥金玛》《山寨火种》《瑶山春》《萨里玛珂》《火娃》《奴隶的女儿》《冰山雪莲》《孔雀飞来阿佤山》《丫丫》《雪青马》《从奴隶到将军》《傲蕾一兰》《蒙根花》《雪山泪》《向导》等近20部反映藏蒙维彝瑶等多个少数民族解放史的故事片。这些影像并不仅作为民族志而存在,更作为中国革命史的重要补充而被书写。由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特殊性,禁区红线比较明确,政治上的包袱反而较少,因而创作上取得较为可喜的成绩,出现《奴隶的女儿》《丫丫》《傲蕾一兰》《蒙根花》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的作品。然而,正如上述片名的性别指涉所表征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身份没有摆脱“十七年电影”《摩雅傣》《五朵金花》《景颇姑娘》的想象与建构——即作为意义的载体和凝视的客体,天然地与“女性”画上等号。其结果是:处于汉族叙者和观者双重视域夹缝中的少数民族电影,常常需要借助情感叙事斡旋调和主线叙事里隐含的权力结构。伴随而来的悖论便是少数民族电影里往往越是“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离“真实”越远,反映出少数民族电影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整体而言,该阶段主流电影在创作手法和影像美学方面主要有以下三大特征:一是复兴传统。这些影片“在延续英雄塑造的原则、浪漫色彩的表现方式和传奇故事的基本准则上,重现着往昔电影的路数”。它们承袭《南征北战》《上甘岭》《风暴》建构的“十七年”叙事传统——渲染战斗的惨烈,表现领袖的伟大,高扬精神的旗帜,在沙场空间重述革命导师的创业史,在敌后空间再现英雄儿女的罗曼史。二是回归现实。“样板戏电影”令人血脉贲张的理想色彩和乌托邦幻想受到压抑,新中国成立之初银幕上的豪迈自信和雄浑激昂也有所扬弃,现实主义被重新置于浪漫主义之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基调。三是焦点后置。镜头逐渐从战争前景移向革命后景,从队伍前列深入后排边缘,从英雄的面庞推至战士的内心。平面化的战场白描不再是唯一主题,硝烟弥漫、喊杀冲天的前沿阵地成为情节铺陈的背景。在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既定意识形态的框架内,银幕焦点从神圣崇高的革命世界转向平凡质朴的人性世界(例如《青春》),从你死我活的政治世界转向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例如《啊!摇篮》《两个小八路》),从禁欲主义的道德世界转向七情六欲的情感世界(例如《小花》《归心似箭》),力图向观众展现革命乐观主义在精神抚慰层面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
三、战地柔情:恋母情结与伦理焦虑
新时期之初的主流电影中,除了民族史诗,还少见地出现了讴歌战争中人性的作品。谢晋1979年拍摄的《啊!摇篮》是其中的代表作。该片通过一名女红军战士的视角展开叙述。鉴于谢晋之前的作品《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青春》都表现出对女性话题的关注,这一点倒不让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谢晋在《啊!摇篮》中延续了他在“十七年”时期便已建立起来的通过女性视角探讨某种政治议题的叙事策略。第一幕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和延安塔推镜的声画蒙太奇,宣告了这种高明的叙述技巧达到了新的高度。正如学者汪晖的观察,谢晋电影里的党的形象通常被伦理化表述为母亲的形象,影片巧妙地将返回到党的队伍中(跟党走)的核心表意镶嵌在革命后代返回母亲怀抱的伦理叙事中。
不过,汪晖的论述只选取了《红色娘子军》和《天云山传奇》,而直接跳过了它们之间的《啊!摇篮》。它成为当代谢晋电影研究的一个缩影。随后的重读和再论,几乎无一例外,将视点聚焦《天云山传奇》《牧马人》《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啊!摇篮》的独特意义和魅力则被淹没在对前者长篇累牍的讨论中。模糊的身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片在谢晋作品序列中的尴尬位置。实际上,《啊!摇篮》一方面并没有跳出谢晋的“党/母亲”的伦理政治范式,一方面又有别于后来作品的某些特质。体现出谢晋在不同时期思考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也反映其历史局限性。
该片描写了1947年前线某部女教导员李楠被派往保育院护送孩子们撤离延安的故事。在童真和肖旅长的感染下,起初对护送任务持消极态度的李楠转变了思想,最终光荣完成了转移任务,使孩子们平安到达安全区域。表彰大会上,孩子们亲切地喊她“李妈妈”。她和肖旅长也在这次任务中产生了爱情。
影片展现了谢晋以往作品中未曾表现的主题:柔软的人性和美好的爱情。但是这些伦理主题并不仅带有宣扬道德、彰显人性的意味,而且与某个政治故事相联系。影片在爱情故事中采取了性别/政治主题置换与互补的叙事策略。李楠不喜欢小孩被解释为遭受旧社会重男轻女思想伤害而留下的心理创伤,对封建男权的反抗使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一种类似娜拉式的出走。在革命叙事下,这种出走的结果必然是走上革命的道路,实现妇女向女战士的去性别化转变。
然而,谢晋却在传统的革命叙事中添加了一条性别叙事的线索以补偿禁欲的匮乏——通过肖旅长这个角色的帮助和感召,让李楠喜欢上孩子,使其在不破坏革命叙事的前提下获得一种妇女/女战士的双重身份。然而,有趣的是:源于反抗男权的斗争最终以在男性/党的感召下回归男权秩序收场,如此自相矛盾的表意逻辑似乎暗示了在谢晋的潜意识中埋藏着一种恋母情结,使他敢于冒着削弱革命话语权威的风险,固执地埋进去一条违背传统的叙事线索。
正如李楠和肖旅长之间的爱情叙事是被置于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中加以表述的一样,影片里的天伦叙事同样具有政治色彩。《啊!摇篮》开场就以一组极具象征意味的声画对位显示出以人伦散文讲述国家寓言的意图。观众首先听到孩童大声呼喊“妈妈”的画外音。在孩子对母亲的呼唤声中,雄踞镜头焦点位置的延安塔在推镜中不断被放大而逐渐占满画面中轴线。紧接着第二个镜头是延安根据地墙壁上“保卫延安”的宣传标语,第三个镜头是一个小男孩儿哭着扑倒在担架上的负伤的战士母亲怀里。这表明孩子是党的孩子,护送孩子就是保卫延安。
与“十七年”时期的《小兵张嘎》和同时期的《两个小八路》相比,《啊!摇篮》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它突破了战争儿童题材将儿童角色成人化,按照英勇无畏的小小接班人的模式来塑造人物的惯例,极力表现党的孩子的弱小无助和亟须呵护。而且对母亲的眷恋贯穿故事的始终。作为影片的重要角色,开场那个呼喊“妈妈”的小男孩儿与身受重伤的母亲分开后被送到保育院,整天茶饭不思,只是哭着嚷着要找妈妈。这种“煽情”叙事的背后绝非人道主义的解释如此简单。实际上,天真无邪、年幼无助的孩童形象承载着谢晋个人的一种自我想象。敌机轰炸下保育院孩童惊恐无助的表情和声嘶力竭的啼哭,隐含着历经浩劫磨难的谢晋内心深处的难以言说的隐痛。一个无辜的、需要呵护的弱者形象就这样浮出银幕。影片极力展现孩子的弱小无助和天真烂漫,让人觉得如此可爱的精灵理应人见人爱。而肖旅长作为党的化身所表现出的对孩子特别的关爱,则隐喻谢晋对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的主观想象和个人期待。
类似的想象还出现在1977年的《青春》里。影片中,亚妹的聋哑病是在“文革”里医疗队下乡期间被老红军战士向晖医生用针灸疗法治好的。学西医的革命老干部用针灸治愈聋哑,如此安排情节的深意在于既没有违背“文革”时关于卫生路线的基本精神,又为专业医生和老干部头上的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罪名做了委婉的开脱。谢晋电影的保守或者说对艺术和政治的平衡的细致拿捏可见一斑。他就像一名高明而谨慎的医生,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脉搏的微妙变化,但绝不贸然开出什么猛剂泻药,而是以“温养调和”的处方为主。
因此,谢晋在《啊!摇篮》开场利用音画对位以一种近乎向党倾诉衷肠的姿态为后面的个性化表述提供了保护伞。但个性化表述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反传统,精神内涵上并没有突破“母慈子孝”的德行政治的范畴。于是,我们在影片里看到的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对母亲的呼唤,一个委屈的孩子对母亲的哭诉,一个天真的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影片没有直接表述政治,却披着童真、童趣和温情脉脉的漂亮外衣,完成了一次对“儿不嫌母丑”故事的成功转述。对天伦传统的热情和画面细节的专注却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政治的批评和个体的反思。就这样,谢晋以一个还需要摇篮的巨婴的形象将自己从历史的人质中赎回。
四、个人传奇:冷战余绪与另类想象
作为战争题材的一个亚类型,反特题材在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沉寂以后在新时期初年重新在银幕上活跃起来。它们在主题风格、人物形象以及叙述结构上都打上了“十七年”时期反特片的烙印。这些影片的故事内容也大同小异,基本可以概括为:中共地下党或者特工人员与国民党反动派或者苏联间谍周旋、出生入死的斗争经历。在《熊迹》《东港谍影》《黑三角》等影片中充满民族主义的激情,故事情节常常夸张而违背实际情况。对此,夏衍曾在1979年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对《东港谍影》做过不点名的批评:“有一个造船厂工人,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他跟我说,看了一些惊险片,都是偷图纸。哎呀,我们造船工业这么落后,还有人来偷图纸?明明是假的嘛!”民族主义想象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银幕中的泛滥从反面映照出国家内部政局的动荡和人心惶惶。当一个国家的领导层发生权力斗争时,容易倾向于向民族主义索要资源,此时国际或外部的争端成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杠杆。可以看出,反特片的这种“迫害妄想症”依旧浸透着浓厚的“冷战”思维,上演的仍然是“十七年”时期《国庆十分钟》(1956)里的“冷战”故事。然而,尽管这一类型故事本身“密布冷战氤氲,但其表象系统却多少游离于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表达”,其中对主人公冒险故事和传奇经历的描述使它成为一种最具个人英雄主义的另类叙事。
其中,1979年拍摄的《保密局的枪声》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该片上映后旋即引起市场巨大反响,成为新生产的少数几部脍炙人口的国产电影之一。其成功首先得益于剧本。影片根据当时的流行小说《战斗在敌人心脏里》改编而成。故事描写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由于潜伏在军统保密局的同志被叛徒出卖并遭杀害,同样潜伏在保密局的刘啸尘决定亲自出马,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他不仅一举铲除了叛徒,还成功取得新保密局局长信任获得器重,并利用自己的地位保护学生运动和党的地下组织,最后成功掌握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密谋制订的特务潜伏计划和名单。
故事中的悬念设置非常密集,情节一波三折,人物命运险象环生,导演对于叙事节奏的把控也比较到位,除了第一幕里为同志的牺牲而感到悲愤的那场戏略显拖沓,全片没有太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结尾一段收得尤其干净利落而又留给观众足够的遐想空间,成为反特片结尾的经典范本,即使是在今天的反特影视剧里仍然被反复借鉴,比如《北平无战事》。不仅情节扣人心弦,这部影片在演员选择、布景造型和台词设计等方面也显示出超越同时代作品的眼光。这与导演常彦曾留学德国的经历有一定关系。影片基本摆脱了“文革”遗风,实属一部兼具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类型片的成熟之作。
个人英雄主义无疑是这部影片最为鲜明的风格特征。与同类题材里的主人公正统的国字脸不同,主人公刘啸尘被塑造成为一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时髦潇洒的白面书生形象。情节多着墨于敌我之间的斗智斗勇,而甚少有直接的政治口号和革命话语,地下党步入舞池跳舞一段更是史无前例的镜头。与此同时,影片花费大量篇幅描摹刘啸尘单枪匹马与众敌人周旋,凭借过人的谋略和心理素质将敌人玩弄于掌股之中的过程。他仿佛是集外形和胆识于一身的中国式的詹姆斯·邦德,不但总能化险为夷,而且总能顺利完成任务。这种带有个人英雄色彩的叙述倾向源于电影创作者的政治诉求。常彦希望通过刘啸尘这一个人主义式的英雄人物为在现实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公的曾经的地下工作者鸣不平:“我们对把所有的地下党都打成叛徒、特务,从政治上比较反感,这是一种感情因素。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当时党中央对地下党并没有定论,所以我们最初在搞剧本、拍戏时,也有些风言风语,说我们是在为叛徒、内奸、敌特树碑立传。”创作者身上的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特立独行的精神也在影片中得到体现。导演在镜头中不仅破天荒地还原了旧上海高档豪华的舞场,而且还表现了男女共产党员搂抱在一起跳舞的场景。只见主人公出入各种高档场所,熟悉各式西方礼节,享受优渥生活方式,一个反传统、非主流的共产党员形象跃然纸上。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非典型的人物却成为当时最受观众喜爱,被认为刻画得最成功的角色。该现象及反特片热潮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脉络。当人们对以斗争为使命的战斗英雄感到厌倦的时候,对禁欲节俭的生产能手感到麻木的时候,反特片作为一朵异色的奇葩受到人们关注。《保密局的枪声》将故事建构在上海这样一个远离延安文艺传统的城市空间中,工农兵电影里常见的底层生活景观被对都市摩登生活的展示置换,阅读大字报和三大报的无产阶级趣味被舞蹈、音乐、咖啡和牛排替代,男女之间的握手敬礼被直接的肢体接触省略,永远“等待首长下命令”的士兵被随机应变的孤胆英雄所解构。尽管影片结尾主人公登高上海眺望延安,将前者仍然置于后者的话语权力下,但影像中不时闪现的个人表述、性别凝视和对西方生活方式的想象,仿佛沉重的历史巨轮外壳上的裂口,成为个体精神突围遁逸的路径。
但原本在原著里没有的一个神秘人物的出场却削弱了这种突围的意义。影片结尾,当拿到敌人的潜伏计划书的刘啸尘准备撤离的时候,被突然出现的张仲年和特务“老三”截住。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千钧一发之际,“老三”突然掉转枪口,击毙了张仲年。原来,“老三”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常亮。常亮的最后现身给刘啸尘之前一系列个人英雄主义的高光表现套上了一切尽在上级组织计划之中的帽子。意味着无论刘啸尘个人如何卓尔不凡,要想最终胜利地完成任务,也仍离不开战友的力量和集体的智慧,显示出国家主义对英雄主义叙事的规训和监控;同时,这也预示着个人表达的创作突围正如影片尾声刘啸尘还得继续潜伏一样,仍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
虽然新时期之初的反特片仍流露出“不能放松警惕,周围仍潜藏着敌人”的冷战思维,但在西方谍战片尚未登陆中国银幕的年代,这种带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普通观众关于国际政治的另类想象。
结 语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运用“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和“文化操控”(Cultural patronage)两种文化策略来论述和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相对单向度的“文革”叙事而言,新时期之初的主流电影创作要丰富得多——既有表现正面战场的军事片,也有表现外围战场英雄主义的惊险片,既有表现阶级仇恨的历史片,也有谱写人性之歌的剧情片。伊格尔顿认为,“审美只不过是政治之无意识的代名词:它只不过是社会和谐在我们的感觉上记录自己、在我们的情感里留下印记的方式而已。美只是凭借肉体实施的政治秩序,只是政治秩序刺激眼睛,激荡心灵的方式。”新时期之初的中国银幕试图恢复“十七年”革命浪漫主义文艺传统,通过对英雄史诗、战地柔情和个人传奇的编码想象,引导观众不断“重返”民族国家创业坚守的艰难时刻,修复与重塑被撕裂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的同时,也寄托着创作者渴望政治秩序回归的集体无意识。新时期之初电影工作者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不同于工具主义时代的话语规则,银幕上出现的新气象并不只关涉美学问题,也关涉认识论问题。电影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工具的地位,但囿于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及历史转型等因素,电影艺术并没有变成完全独立自足的领域。不同于以往政治对电影的简单粗暴对待,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以中介的方式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