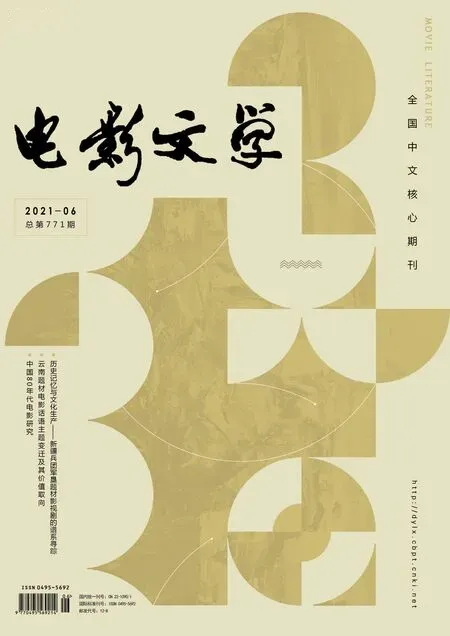80年代初大陆城市电影的叙事逻辑
袁文丽/Yuan Wen Li
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人文社科界掀起过对“80年代”命题“集体怀旧”的热潮,查建英、程光炜等一批学者围绕“重评80年代”“重返80年”,试图对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社会转型等问题进行历史境遇性地重新思考。“80年代”不仅是有关时代的个人化经验,更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不言而喻,“80年代”也成为本文思考电影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场域。本文把视点聚焦在80年代初(以1985年为界),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变化和发展中,这一时期不期然地冒出的一批具有经典意义的城市电影,回到特定的历史场域中阅读电影文本对城市的想象和表述,对社会历史变迁和文化价值的表现,具有丰富的文化症候性意味。
一、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电影的登场与历史场域中的城市叙述
对城市的叙述、想象的方式隐含着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结构性变迁的深层因缘。张英进在概括德国评论家克劳斯·谢尔普时将城市叙述分为四类模式,指出谢尔普的例子完全取材于现代欧洲文学和电影,暗示一种城市叙述从田园牧歌式(如城乡对立)到现实主义(如阶级斗争)再到现代主义(如审美沉思)的历史发展,这种发展主要因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历史发展而产生。尽管谢尔普的模式产生于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理论语境之下,在中国的文艺土壤中,我们找不到西方那样的城市叙述线性发展的痕迹,但“他者的视野”所具有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依然不可忽视。
关于城市的叙述和想象在中国现代的文艺作品中总离不开与“乡村”的比照框架。从社会历史变迁的长河中审视城乡模式的话语内涵、表达方式,我们可清晰捕捉到当代社会结构、文化话语和思潮观念的变化脉络。在前工业时代,“城乡”呈现经典的二元叙述模式,乡村代表朴素、纯净、自然、美好的人性,是和谐、理想的精神家园的表征。城市则是欲望、堕落、罪恶之都,是人性的深渊、现代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在社会主义革命政治语境中,城乡的表述机制则被置换成了阶级斗争主导下的城市/资本主义和乡村/社会主义的叙述机制;进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20世纪80年代后,城乡传统内涵又被新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取代,关于现代化(城市所指代)/传统、落后(农村所指代)的新话语内涵和叙事修辞在文艺作品中被涌现出来。
1949—1976年关于城市题材的文艺作品比较缺乏,相关作品甚至有意回避对城市形态的表现,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维惯性之下,实质上开启的是一个“去城市化”的过程,换言之,“城市”成了“社会主义文化缺席的在场者”,正如莫里斯·梅斯纳曾评述:“对于那些农民干部来说,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随着的是不信任。以集合农村革命力量去包围并且压倒不革命的城市这种做法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自然滋生并且增强了排斥城市的强烈感情。”对城市的厌恶,有关堕落城市书写的背后,既隐含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又加剧了把城市作为单一的大工业化中心的认知逻辑。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动荡之后的重要转折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中国迎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为新时期的主旋律,城市成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重镇。顺应主旋律,80年代初以反映城市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新时期电影应运而生。“第四代”导演在经历动荡和压抑的沧桑岁月,像压紧的弹簧爆发力格外强大一样,他们携着新时期一批新电影《都市里的村庄》(滕文骥,1982)、《逆光》(丁荫楠,1982)、《快乐的单身汉》(宋崇,1983)、《锅碗瓢盆交响曲》(滕文骥,1983)登台亮相,记录和表现那一社会历史阶段的主题和风貌。然而,也许受到电影人自身的知识、经验及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些电影整体上夹杂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痕迹,其对城市的叙述和表达机制,多少还残留着“十七年”“文革”中“厂矿文学”“工业文学”的影子,把城市视为大工业的生产空间,城市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不管怎样,这些文本作为80年代初中国城市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经验,同时包含着对现代城市的感觉和认识创新的一种探索。
二、都市物质性空间的呈现:现代化工业空间和民族国家想象
在上述所列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四部电影中,除了《锅碗瓢盆交响曲》以北京春城饭店的改革为线索,其余三部都以上海造船厂及其青年工人为书写对象。戴锦华精辟论述道:在当代大陆文化中,城市不时成为现代工业的代名词,城市文化不时被置换为“工业题材”。工人阶级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的历史的创造力与原动力,则成了当代文化中唯一得到显影的都市人。新时期(1979— )以来,工业题材再度成为正面表现改革的“重大题材”,工业空间成为转型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集散地,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城市和当代中国的提喻。戴老师指出新时期“城市文化”和“城市”叙述的单一性和政治符号的空洞性,但是回到80年代初的历史场域中,笔者在给予“理解之同情”时试图挖掘其叙述的逻辑和意义。
将上海和上海造船厂作为人物活动和人物身份的背景设置有着天然的现实原因。中国现代民族工业源自造船,而上海又是我国现代船舶工业的诞生地和新时期船舶工业发展的重镇。2010年上海世博会,位于浦西园区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中国船舶馆,就象征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坚强精神。船舶工业发展,对航运、海洋资源、国防事业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船舶工业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另一方面,在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笔下,上海一直以来是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多义、复杂而又暧昧的符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笔下的摩登上海,或是张爱玲笔下处于沦陷、市井生活意味中的传奇上海,或是20世纪40年代以矛盾为首的左翼作家笔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或是当代作家王安忆笔下的怀旧上海,甚至到方方、卫慧笔下的“新感性”上海,关于对“上海”的想象、叙述和建构实际上构成了一部中国现当代史。由此,可总结近现代以来有关上海城市想象的三大谱系:其一,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意识下认知旧上海摆脱殖民化获得独立的国家元叙事;其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摩登上海,表征着物质与文明的扩张及其引领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其三,上海作为凝视大都市现代性、消费性、暂时性、颓废性的现代主义感性经验叙述。本文所选择影片正是立足前两种叙事逻辑,将“上海”置于民族国家的意义上展开叙述。
把城市作为大工业发展的图景呈现和表征是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电影的主要景观,这主要表现在物理空间的镜像书写方面。为了强调和突出城市工业化的背景,影片开场镜头着力展示上海外滩大楼、高大的厂房、高高的塔吊、集体宿舍和建筑工地等,主要情节的发生也都在高度能指化的工业空间中。《都市里的村庄》开片用摇镜头对准高高塔吊和工人们愉快下班的场景。几个关键的情节都发生在工厂,如丁小亚向动力车间求援修高吊时无奈遭遇小伙子掰手腕的挑战,杜海在事故中舍命救黑子,等等。《快乐的单身汉》片头也是俯拍高高塔吊,横摇镜头依次呈现黄浦江上气派的大轮船、高大的厂房、建筑工地的掠影,最后镜头聚焦到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工人上班的情景。在影片中,除第13分钟刘铁和丁玉洁回忆起过往情感的场面,其余部分都发生在车间、工地和集体宿舍中。而《逆光》首先呈现的是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的黄浦江上的轮船、江景,电影以全景镜头横移掠影的方式展示,最后定格在正在建筑的高楼和旁边的塔吊、外滩的一幢欧式建筑的特写上。
总的来说,几部电影对上海空间的表现方式常常处理为空间的分割、差异空间的对立以及相关度空间的连接。在电影镜像中,常常把外滩建筑的掠影与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化空间衔接在一起,用破旧狭窄棚户区和现代的工业空间形成对立,淡化外滩一带建筑的殖民符号意义,突出新黄埔一带工业化空间的意义表征,通过这一带的高大楼房—工厂—黄浦江港口的空间化链条,经由造船厂、现代轮船这一具体的意义符码,体现了一个连接传统、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新上海的现代城市功能和形态。可以说,这是一种将现代性意念化了的想象性叙述。
《都市里的村庄》和《逆光》中都隐含着两个地域空间——棚户区/外滩高大建筑和黄浦江大工业空间——两个能指的对比。《逆光》开头就以俯拍横移的全景空镜头,呈现出棚户区的全貌。而故事展开的另一端又是具有高高塔吊的宏伟工业图景的船厂。棚户区是作为旧上海无产阶级的空间符号出现的,“仍然是上海滩,仍然可见南京路的建筑群,但就在这些幽灵般的影子的后面,还有一个与解放后的景色极不协调的世界——苏州河畔的棚户区。”两者的并列构成了由旧上海走向新上海的饶有趣味的镜语叙事。《都市里的村庄》和《逆光》在棚户区和船厂两个富有张力的场景交替中展开故事的叙述。这其中隐含着电影叙事的修辞逻辑:棚户区被命名为村庄/落后/此刻/传统,南京路和大工业空间被命名为城市/现代/未来/希望,正如电影中独白昭示:“一个传统中国和一个现代的中国,而这两个影子同时叠印在人们心中,希望和未来就在生活中,就在身边。”这也暗含着另一种“空间政治”逻辑(棚户区/南京路对应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历史话语中的转换。故事以面向未来的新上海的工业景观为背景,以社会主义新人——工人阶级为主体,表达出一种创造新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宏大政治愿景。
三、都市历史空间的表述策略:社会主义“改革叙事”的困境
上述四部电影在类型和叙事逻辑上有着高度的类同性:它们都上映于1982年左右,彼时中央政府正致力于两个文明的建设“两手一起抓”。电影《锅碗瓢盆交响曲》直接以国营饭店的改革为描写对象,触及改革的重要命脉、核心问题和关键举措。而以上海造船厂为背景的三部影片,探讨经济建设变革中企业制度和管理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主要关涉到无产阶级的主人——企业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的种种状况:工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知识教育和技术改进,精神风貌和效率成绩等,他们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呼唤者、实施者和创造者。概而言之,四部影片隐含“改革叙事”的逻辑和意义:以企业题材(主要是工业题材)为背景,以青年工人为男女主人公,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戏剧冲突。
程光炜曾认为“改革文学”残留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诸多因子,它所表现的生活,是高度虚构和抽象的“生活”。这种“抽象生活”常常是以“典型人物”为主体的“英雄生活”,在这里“日常”被看作是要否定和征服的对象,“日常”中的吃喝拉撒以及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都应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以服从于更高的目标。程老师对“改革文学”的深度概括虽不能完全代表改革电影的叙述逻辑,但在某些方面也是高度相似的。如电影中对“典型人物”的塑造,丁小亚(《都市里的村庄》)、刘铁(《快乐的单身汉》)、牛宏(《锅碗瓢盆交响曲》)、廖星明(《逆光》)都是有着崇高的理想与激情的“英雄”式的人物,影片对其进行大力地歌颂和赞美。虽然影片也试图表现理想主人公的私人生活——爱情,但才子加佳人式的爱情模式高度抽象化、扁平化,对于爱情生活过于浓缩和模糊。《快乐的单身汉》中对男女主人公从见面、误会、化解矛盾到结婚的过程只用了三组镜头,不到10分钟。同时通过以“社会公共性”的方式强烈消解“日常生活性”,影片常把对日常生活事件的书写放置在社会性的“公共性”空间中,放置在工厂、办公室、工地、住宅客厅的空间中。比如《逆光》中廖星明第一次带女朋友夏茵茵回家成了整个村的一个“公共事件”;《快乐的单身汉》中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风貌的“蜕变”主要上演在“集体宿舍中”。强烈的社会公共性消解了个体隐私性和日常生活性,在电影的叙述逻辑下,实际上另一种修辞话语正在被置换,青年们以爱情的名义,把美好的爱情化作理想、激情、革命,呼唤改革和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黄平说“重读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小说,大量(改革文学的)获奖作品一个核心的线索是:革命青年在‘现代化’的号召下从‘革命小将’转变为‘专业能手’”。诚然,电影的改革叙事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恐怕也是询唤“社会主义新人”的出现,让广大青年将“爱情和理想”转化为“革命激情”,将“革命激情”转化为“工作伦理”,投入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建设中去。
重返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场域中,回到改革的肇始阶段,改革的“动力”在告别“文革”的立场上是清晰的,“80年代”的某些重要共识:启蒙、改革、现代化、创新……构成了一种80年代式的“态度同一性”。上述几部电影显露了其在与主流话语、传统叙述模式之妥协、合谋和抗争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在另一个维度,电影也显示另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敏锐捕捉的时代感,影像立体多维的呈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本的新的向度和可能。如新时期人的思想解放与价值困惑、情感孤独的并存(丁小亚作为劳模被排挤),特别是物质追逐、商品经济的交换伦理在世俗社会中的暗流涌动,然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给“欲望”“财产”“商品”等以合适的位置。《都市里的村庄》精心刻画了一场知识分子哥哥(舒朗)与个体户弟弟(家林)的冲突的故事。兄弟俩的身份冲突为我们提供了多个理解的面向:精英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在“个体经济”/“发家致富”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冲突和张力,这可谓暗藏副线。滕导不只是客观冷静地书写和呈现,甚至在兄弟俩争辩的长镜头中给予“发家致富”以合理解释。在这里,影片似乎暗示个体户家林也是改革的先行者,但对于兄弟俩的态度指涉在文本中是暧昧不明的。诚如张旭东所言:“第四代”所受到的压制及其复兴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往往被低估了。以“文化大革命”为界限,充满动荡经验的时间跨度决定了他们在新时期电影生产中的潜力与局限性。“第四代”导演同更老以及更年青一代的重叠与不可避免的竞争,使得他们的作品在立场上显得很不稳定,在表达上显得暧昧,在内容上表现出自我矛盾,在影片组织上则取一种折中态度。“第四代”导演对于一切都没有太大的把握。他们依然以怀旧的追寻者的姿态登场亮相——追寻形塑了自身经验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善美。
——评《中国现代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