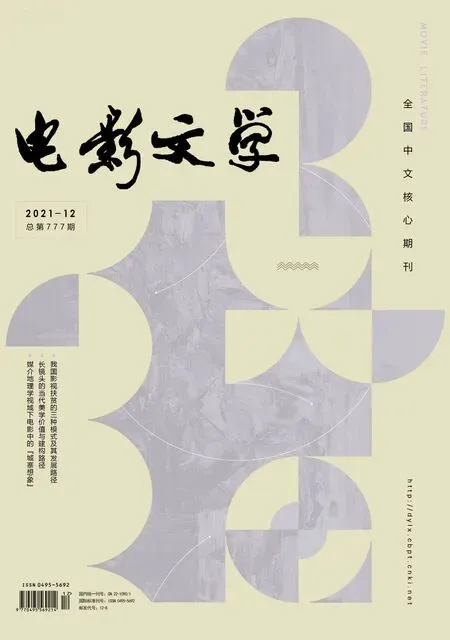影视史学视域下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的创作与传播
范瑞利(重庆人文科技学院艺术学院,重庆 401524)
20世纪初,面对传统史学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探索史学研究、史学书写的多种可能性,这种史学界的新动向在影像技术越来越发达的语境下促生了影视史学的诞生,即影视史学是新历史主义思潮下历史学与影视学的互动融合,由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也是试图通过影像媒介来“看”历史的一种方法论,且前提是认为历史也是被叙述和建构的过程,对其普世性的认定是可以用影像传达历史,也可以用影像传达对历史的见解。由此,相较于其他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历史类纪录片与历史的扭结则更为直接和显性,在历史文本化和文本化历史的互文中彰显出独特的创作与传播价值,给予历史书写和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以诸多新思考。近年来,不少的历史类纪录片在影视史学视域下被提及和关注,不少的纪录片导演更是将历史学的观念与方法注入影像的创作,但在历史的影像化书写与文本化历史的大众传播间产生了双向效应与价值的又一“现象级”作品,无疑是历史文献类纪录片《大后方》。
一、历史的影像化书写:《大后方》创作的影视史学立场
重庆,偏隅西南,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厚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被推出。其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重庆广电纪实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重庆广电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担任制作机构,全片共12集,每集50分钟,2015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重庆卫视等平台一经播出就受到了较为强烈的关注,“是同年新媒体播放量最高的抗战题材纪录片”,获得201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优秀作品奖(全球仅3部作品获得该奖项)、第五届“光影纪年——中国纪录片学院奖”最佳系列纪录片等荣誉。同时,在同年度的各种“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这是唯一一部把目光从战场向广袤的后方,从战士移向支撑抗战的四万万民众的纪录片”。由此,《大后方》可谓是近年来中国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的又一“现象级”作品,而纵观其整个创作过程,秉承学术研究的路径进行历史书写是其创作的态度,以史为基进行历史的影像化书写是其较为显性的美学风格,是秉承学术研究书写历史的创作态度,也最终成就了其的与众不同。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应用而生时的核心命题之一就是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指向的是历史的文本化问题。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甚至公开的提出,“历史就是一种文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也阐述过:“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历史是难以摆脱被叙述和被建构的事实,而且,历史通过文本才能得以显示的历史文本化问题在历史书写的长河中也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在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中,相较于口传和文字论述等手段,影像书写因其可视化、可听性则更为直接、生动。于是,随着影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历史学家开始纷纷觊觎影像,使得历史学与影像裹挟融合,影视史学被提出且愈加的引人注目。但不能忽视的是,历史学家也逐渐地注意到,影像在叙述、书写的过程中,往往具有较为强烈的艺术虚构性,影视史学的根本还是要“以史为基”,尊重历史。由此,从历史史实来看,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战时首都,无可争议的,抗战大后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与同类型、同题材的影视作品相比,《大后方》秉承历史史实,聚焦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在创作的过程中,深耕相关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挖掘,在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共同参与下,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立体的抗战的中国,且“要以人民为中心来再现大后方历史”。
为此,在12集(每集50分钟)体量的具体历史叙事中,首先,《大后方》避免历史的宏大叙述,而是通过历史核心事件及事件中的相关历史人物的经历、情感的呈现,全面展示抗战时期的物资如何运输、教育如何进行、伤员如何救护、文化如何开展等社会史、生活史以及从名人到小人物悲欢离合的个人史。比如,第一集《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介绍了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所面临的国内外的危险局势及国民政府做出迁都重庆的决策的历史经纬,直接传达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基调和政治理念,展现出了面对抗日战争中国人的历史态度和民族意志。在具体的结构叙事上,以主要线索人物(提出“对日持久战”的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相关历史活动为主干,纵横捭阖地融入辅助性人物(比如刘湘、蒋介石等)及其相关史实,阐明了形成以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的战略思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的历史,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集内容作为整个系列的开始,既是整部作品叙事的提纲挈领,也奠定了接下来分集叙事的布局结构,即每集以史为基、一个集中呈现的内容,在具体的内容叙事中,以主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为主干,融入辅助性叙事的历史人物及其历史活动,且每个段落相互独立又浑然一体,最终完整地、统一地完成了作品的整体叙事,从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等不同方面全面、立体地呈现了伤员怎么救治、物资怎么运输、教育怎么开展等战时图景,“这使得《大后方》在诸多表现抗日战争的作品中显得特别”,形成了作品在结构叙事上的形式。比如,第三集《愈炸愈强》主要讲述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的城市被日军轰炸及中国抗战大后方防空体系的建立的历史史实,线索人物及历史相关人物主要有时任重庆警备司令的李根固、重庆大学飞航学教授蒋逵、苏联志愿航空队轰炸机大队联队长库里申科等,更有陈代六、杨淑尧、陈桂芬等重庆大轰炸的亲历者及他们对历史的口述、直接的历史客体物料(重庆大轰炸现场捡回的弹片);比如,第六集《一滴汽油 一滴血》讲述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出现的石油荒及为解决石油燃料问题而开辟玉门油田、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等历史,线索人物主要有美国地质学家马文·韦勒、中国测井之父翁文波、中国输油第一人翁心源等,更有相关历史人物后代及学术研究专家学者的口述等,每集内容相互独立也又相互连接,并“重点从社会、经济、文化领域挖掘素材,关注的内容包括战时总动员、衣食住行、危机应对、伤病员护理、物资生产与运输、教育与文化传承以及战时社会心理等”。这种以亿万普通民众为主体的微观历史的书写态度,“注重由个案出发、寻觅背后的历史空间,这种方法是对传统史学宏大叙事的结构,是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观的体现”。
著名的影视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认为,用影视传达历史,必然受制于坚实的历史史料。《大后方》在创作的过程中,坚守对作为历史客体的史料的最大占有和完整运用的原则。在历史客体的挖掘上,为了保证作品的真实品格,除了极个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影像画面的处理,《大后方》在创作的过程中慎用近年来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惯用的“再现”“搬演”手法及历史影像素材的“万能画面”的利用,而是致力于真实影像素材的搜集和占有。在总时长的600多分钟里,《大后方》“60%到70%的影像是历史资料,几乎每一集都有一些此前从未跟观众见面的影像素材”。比如,每一集都大量出现的各相关历史人物的书信、日记及照片、图像;第二集《向西 向西》、第四集《战地红十字》中出现的《美国新闻影片》(1937年);第六集《一滴汽油 一滴血》中引用的当时美国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生命线》等。作品里的汽油生产量、物资运输路线图、伤员数量等数据、细节及专家学者、历史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讲述,更是渗透了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学术研究等多侧面的信息,完成了对重大历史史实的鲜活注解。如此,作品不仅在创作意图和政治理念上更加全面地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立体的抗战中国,厘清了大后方与中国抗战胜利的关系及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更表现出了亿万普通民众在强大的敌人以及艰苦严峻的抗战形势面前的挣扎、搏斗、无畏、坚强和绝不屈服的傲骨韧性,让历史客体的能指和所指助力于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止了历史被书写、叙述甚至阐释的随意性。而为了搜集和占有诸如此类的一手资料,《大后方》的主创团队远赴美国、英国、印度、中国台湾等地区,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浩瀚的资料中进行扒梳挖掘。除此之外,出现在作品中的一些珍贵的照片、图片、书信、日记等史料,是去到当事人或其后代家中进行的扫描、整理,而且,在资料的具体使用的过程中,坚守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料素材的完整性为创作原则。比如,第三集《愈炸愈强》中对《汉口谣》(1938年底,日本情报部门通过宝丽多公司发行的唱片之一)声音信息的呈现,很好地还原了日本在当时占领中国武汉后的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并开始发动对以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城市的轰炸的历史史实,令人愤恨。在《大后方》的创作过程和成片的影像文本中,对历史史料如此的挖掘和运用几乎出现在每一集的画面中,影视史学立场下对历史的影像化书写的创作态度也可见一斑。而且,少量的“再现”(特效)、大量的影像资料、口述历史、历史实物等的运用和整理,在影像画面上呈现出了一种“诗意”编排的视听节奏,增强了影像作品的细节处理,有着明显的现代叙事意念,整体上也规避了历史文献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资料汇编”的单调和单一,也更进一步升华了作品在历史书写层面上从宏大历史叙事到社会史、生活史、个体史层层细化和转换的史学观,难得地如抽丝剥茧般地实现全面的历史的影像化书写。
同时,自英国的格里尔逊派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开启“解说词+画面”的形式,解说词在纪录片中的作用日渐凸显,甚至没有解说词的辅助叙事,就很难理解画面,特别是历史文献纪录片,带有资料“汇编”的鲜明特征,更需要解说词与画面的相互配合才能较好地进行叙事和表意。但不可规避的是,解说词从被撰写的起始阶段就已是一种“主观性”的创造,经过配音的再次处理后,语气、语速、停顿等更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客观地呈现历史,在解说词的处理上,兼顾文学性的同时,《大后方》字斟句酌,而且大量地引入影像资料的原音、日记、书信等文本内容,比如,第一集《就是不要同他讲和》中,讲到蒋百里在柏林散步迷路时遇到一位德国老者的记述时,解说词说到:“我同他就谈起东方事情来。哪知道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等类。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部分解说,就来自《蒋百里全集》(第三辑),收录于《近世“我”之自觉史》(朝永三十郎著,蒋方震译);接着,作品中就是一段美国纪录片《中华儿女》的影像片段,声音也是其原纪录片中的配音(字幕翻译成了中文):“中国西部广袤肥沃的平原上,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县城——灌县。一大清早,已经有县外的农民,赶着一群叽叽喳喳的鸭子,来到了灌县集市,挑夫们推着独轮车,从附近的村庄赶来,载着粮食,挑着小猪的担子晃晃悠悠,农产品、村民、小推车,塞满去往市场的路上。”如此,在内容解说的声音处理上,采用不同的视角和口吻,不仅真实、客观地还原了历史史实,也提炼出来作品的主题表达和情感基调,富有极强的艺术表现力。诸如此类的运用,在《大后方》的每一集内容中比比皆是。这源于作品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秉承的史学态度和学术态度。其中,总策划、总撰稿周勇对重庆抗战历史的研究有着三十年多年的积淀;总制片人、总导演徐蓓作为国家一级导演,有着丰厚的、专业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的学科背景;出现在作品片尾字幕中的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有20位,都是相关领域中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作品中的每一集里更有相关领域的知名的专家、学者的访谈,《大后方》“用史实发言,为历史文献类纪录片的制作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二、影像化历史的传达:影视史学立场下《大后方》的大众传播
2010年以后,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直接扶持(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助推,中国纪录片再次焕发生机,荧屏(银幕)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甚至产生了诸多“现象级”现象,也促使纪录片逐渐地走下“精英文化”和“小众观看(影)”的神坛,趋向多元化、大众化、平民化,题材内容、制作手法、传播渠道等也越来越丰富,诸多平台(传统媒体、互联网视频、自媒体等)因纪录片而被关注,甚至成为新的影响力品牌,比如,2011年1月1日开播的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优酷着力人文,在纪录片上着力,连续八九年持续领航,被《人民日报》点赞,市场竞争优势鲜明;“二更”“抖音”“一条”等短视频(自媒体)平台自制纪录片频频亮相,引发强关注和强流量,甚至出现了“微纪录片”“手机纪录片”等新概念、新形态。2020年春节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微纪录片、自媒体平台上原创纪录片等,更是持续发力,正向赋能。在如此的行业背景下,近年来,曾在开宗立派后的短短几年就树立了鲜明的创作风格并声名大噪的“渝派”纪录片(2007年,被重庆广电纪实传媒有限公司当时的负责人雷卫提出,主要指向的是以重庆电视台纪录片创作者为主体拍摄制作的反映重庆地域文化的纪录片作品)整体上却陷入发展瓶颈,势头衰减,甚至黯然。但是,重庆地域文化鲜明且人文历史丰厚,历史上(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纪录片的创作生命力旺盛,除了大后方纪实电影外,更有《民族万岁》《抗战特辑》等极其有价值的纪录片(新闻纪录片)的出现。而在其进入新千年之后的开宗立派的创作中,历史类题材的纪录片(诸如《巴人之谜》《考古之谜》《千秋红岩》等)也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类型之一,颇受关注。于此,重庆纪录片创作主体一脉相承,在发展瓶颈中不甘落后,积极突围,特别是徐蓓导演带领的团队,在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中深耕历史史实,以《大后方》2015年的问世为一个新的起点和标志,将人们的目光重新拉回到对重庆纪录片创作的关注上,并相继创作出《西南联大》《城门几丈高》等历史类纪录片,鲜明的史学立场、严谨的学术态度、精良的影像制作,整体上给中国历史文献纪录片注入了强有力的、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并在影像化的历史传达的传播效果上产生诸多文本效用。
毋庸置疑,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千年历史不间断且被不间断记录下来的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龟甲、丝竹、棉帛、纸张、图片等都充当过记录历史史实的工具和载体,担负着历史文明得以传承的重任。影视艺术诞生后,因其直观、生动的视听优势和显性特质,迅速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文化等的各个领域,历史学将其与之相扭结,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还提出了“影视史学”的概念,用影像表达历史及对历史的见解更是被逐渐地重视。但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的世界是不可能再被逆转的真实,即便可以通过一系列史料(证据进行考证)、还原,作为一种过去时态,对历史史料丝毫不差地呈现并进而完成对历史全面的复原最终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所接触到历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转述、阐释、建构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无限地、尽力地去趋向历史并将之还原,从而让人们尽可能地认识历史并以史为鉴,是史学的良知和责任。更何况,纪录片(Docuemntaire)最早被下定义时,就被指向了“具有文献资料价值”。就《大后方》而言,由于创作过程中影视史学的观念和手段层面的大面积的介入,使《大后方》在获得纪录片表现力度的同时也尽最大可能保持了原态样本的鲜活。特别是许多大量的、首次公开的、珍贵的一手影像资料的收集和使用,还有历史的当事人及后代的相关口述及拍摄到诸如炸弹弹片、故居等文物、遗迹等,从微观历史、大众历史、个体历史、口述史等角度尽可能地还原了完整的历史,并给历史的全方位还原以公信力,这样的历史史料和创作过程中的学术标准及态度,甚至可以成为特定历史的专题研究的对象或佐证资料,助益于新历史观研究和史学新书写。这也很好地践行了纪录片的使命,发挥了历史文献纪录片的传播效能,也使得《大后方》影像本身成为有着文献价值、调研价值和进行二、三度等继续深度研究价值的鲜活蓝本。而且,区别于同题材的纪录片作品,《大后方》聚焦于抗战大后方时期的物资生产运输、教育文化传承、衣食住行运转、伤病员护理等个体、生活、社会,以史学的严谨和学术研究的标准,在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影像的镜头语言还原与解读了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的完整历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十年后,再次弥补了宏大历史叙事框架下历史书写的缺失。
同时,进入新时代,中国纪录片再次焕发新生机,历史文献纪录片作为其中重要的类型之一,虽然一直是中国纪录片创作的重心,但因其“资料汇编”造成的审美枯燥、情景再现造成的历史失真等诸多问题不容忽视。《大后方》作为一部历史文献纪录片,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播出平台的选择上,除了有影响力的传统媒体(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重庆卫视)外,顺应时代发展形势,对新媒体传播渠道进行大胆的尝试,选择在腾讯视频网站上线,且在“七七事变”当天推出了一个相关的短视频,“这个短视频上线3小时点击量就突破了100万,到了凌晨突破300万”。另外,《大后方》主创团队还专门拿出一笔做推广运营的经费,请北京的新历史合作社作为推广机构与主创团队保持紧密的合作。随着传统媒体的热播和在新媒体上被关注度的提升,《大后方》独特的叙述手法、影像资料的运用、视听语言的视听觉感染等都再创了中国历史文献纪录片审美的新高度,而其对历史主体性的观照及影视史学立场还原再现的大后方历史得到更全面深化的广度传播,在多元化和多维度的认同族群日渐泛滥的当下,唤起了历史的意识和民族的共同记忆,“成为今天我们运用抗战题材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纪录标本”,对历史在新时代的传播并借此扩大其影响力而最终塑造民族记忆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一门较为新的学科,影视史学为历史研究和影像创作都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尤其对历史文献纪录片的创作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和要求。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后方》以影视史学的创作立场,史实的基础上,秉承历史书写、专业研究的学术标准,收集和占有珍贵的影像资料、口述历史等,在主题、内容和手法上深耕于真实的全面的历史史实挖掘,打造精品,是历史的影像化书写的典范;而其站在影视史学立场上的创作,一经播出,实现了“渝派”历史文献纪录片创作的新高度的同时,影像文本语言中的大后方的历史文化又产生了还原历史、研究历史、传播历史的文本化效用,很好地反向观照了历史,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大后方》作为纪录片在创作理念和创作手法上的精深度,给当下的历史文献纪录片审美和传播诸多思考。于此,以《大后方》为代表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使影视与历史再次良性互动和扭结,无疑是对影视史学的又一次创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