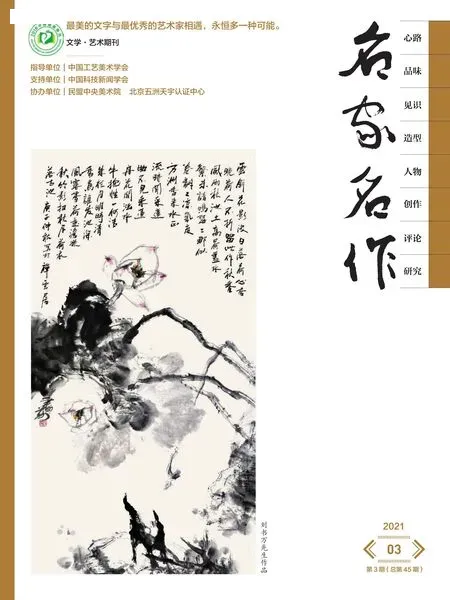衍义体的发展分期
孙先英 霍兴聪
一、创立时期的衍义体
在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完成之后,同期或稍后的人也创作了很多以衍义为名的作品,如钱时的《尚书衍义》、胡震的《周易衍义》、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夏良胜的《中庸衍义》等。然而最初的衍义作品受《大学衍义》的影响并不大,像宋人钱时的《尚书衍义》它的体例则为:
每篇之首,皆条其大指。其逸书之序,则参考《史记》,核其时事,以释篇题。复采《经典释文》《史记集解》《史记索引》所引马融、郑康成诸说,引申其义。
总的来说,宋人对《大学》的阐释,主要还是沿着程朱以来的传统阐释义理,而体例也是随文阐述,如谢兴甫的《中庸大学讲义》、熊庆胄的《庸学绪言》、刘黼的《中庸大学说》、方逢辰的《大学中庸注疏》、黎立武的《大学发微》《大学本旨》、金履祥的《大学疏义》等。
二、发展时期的衍义体
到了元朝,《大学衍义》依旧被君主所重视,并几次被翻译成蒙古文。与此同时,元朝也有很多衍义著作,像谢章的《洪范衍义》、张性的《杜律衍义》、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
在这众多衍义著作中,李好文的《端本堂经训要义》算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仿作,《元史》卷一百八十三说道:
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旨,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
此书是李好文在谕德任上时所作,“取经史传集,有关治体者”汇聚成篇,且为了方便对太子进行教育,沿袭并模仿了《大学衍义》的体例。这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对《大学衍义》的模仿之作,可惜如今已经失传。
胡震的《周易衍义》也值得一提。此书在纲目上没有遵从《大学衍义》,然而其思想内容却和《大学衍义》有极大相似性,二者皆把理学引入《周易》,并视《周易》为治平之书,胡震曾在《周易衍义》的序中说:
《周易》一经,非特占筮之书,可施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备焉。
把《周易》看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书,这种观点与真德秀《大学衍义》的旨趣如出一辙,精神实质可谓相同。
而张性所著的《杜律衍义》一书,则简选杜甫的一百五十多首七言律诗,首先解释词意和典故,继而串讲大义,故虽有衍义之名,却不属于衍义类著作。
从以上论述可知,《大学衍义》的影响在元代开始发酵,从被皇帝、大臣重视,过渡到被当作模范著述看待。然而这个时期的影响依旧微弱,也没有形成对《大学衍义》的模仿倾向,故而此阶段可以看成衍义体的发展阶段。
三、繁荣时期的衍义体
相对于宋代、元代,明代的衍义类仿作著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运用形式上,都可以说是衍义体发展的兴盛时期,现存的衍义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明代之遗留。而衍义体之所以能在有明一代繁荣发展,有多方面原因。皇帝对《大学衍义》的推崇则是原因之一,于此,吴瑞登有言:
我太祖命侍臣书于庑壁,以备朝夕观览。世宗又以日逐进讲,恐不得精,五日一进,不以寒暑废,既有所得,乃为《翊学诗》以赐辅臣杨一清等。
明代皇帝对《大学衍义》的推崇可见一斑。史载《大学衍义补》进呈之后,弘治皇帝认为《大学衍义补》“甚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于政治,朕嘉之,贲金币,命所司刊行”,礼部将书“誊副本,发福建布政司著书坊刊行”,且“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下内阁议行,帝亦报可”,并马上提升他为礼部尚书、大学士,参与机要,这为一些热衷仕途之人或留名之人打开了一条升迁捷径,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忱。
理学的兴旺发展也是原因之一。梨洲先生曾在《明儒学案》中有云:“尝谓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蚕丝,无不辨晰,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明成祖时,朝廷撰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科考用书,胥以程、朱及其门人的著作为绳墨,此举使程朱理学昌极当世,故在此背景下,凡是属于理学的衍义类著作无一例外地受到欢迎。而且,衍义体这一借经典以正君心为目的的阐释方式之所以在明代兴盛,还在于明朝政治的乖戾和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的抗争情绪,如黄训的《皇明名臣经济录》和陈子龙的《皇明经世文编》等书,皆为此背景之下的产物,由此也可知衍义体自诞生起就担有经世济民之使命。
不过,明代绝大多数衍义之作,都以《大学衍义补》的结构、体裁为范本,节略、删节丘濬《大学衍义补》,有徐栻的《大学衍义补纂要》、孙应奎的《大学衍义补摘要》、凌遇知的《大学衍义补英华》、程诰的《大学衍义补会要》、陈仁锡的《丘琼山先生大学衍义补赞英华》和不知名作者的《大学衍义补抄》等书。众多节略本出现的原因,首先在于《大学衍义补》的内容博杂不精,这就让人们对《大学衍义补》有了正反两种意见,支持者如明人何歆有言:
《大学衍义补》其考据精详,议论宏博,且为文温润典雅,不怪不华,比之韩柳欧苏,是各自成一家之言。……要亦韩柳欧苏之俦,与丘公《大学衍义补》,俱世不可无者也。
反对者如明人陈龙正则贬《大学衍义补》书,说道:
观《大学衍义补》,益觉《衍义》之精简动人,真经筵之善物也。丘书泛漫冗杂,殊无启沃,使人主刘览至此,岂不虚费心目之力哉。欲当类书备稽问,又嫌未详,正晦翁所谓记诵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者,惜哉。故儒者无反约之功,不可以著书,不足以事君。
清代强汝询在《〈大学衍义续〉自序》中说:
今夫《大学》之道,万世之常道也。真氏所衍亦万世之常道也。丘氏之书乃杂取后世功利苟且之政,津津称道,而其大旨则在推尊明制,夫明制岂果可垂之万世耶?以是为一代之书则可,而欲以衍《大学》之义继真氏之作,殆有间矣!
清代纪昀在《〈大学衍义补〉提要》中评论说:“濬闻见虽富,议论乃不能甚醇。”接着批评丘濬《大学衍义补》中,主张海运和没有批评宦官,“明之中叶,正阉竖态肆之时,濬既欲陈诲纳忠,则此条尤属书中要旨,乃独无一语及宦寺。”纪昀虽有垢评,但也承认“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原原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抵”且认为“其书要不为无用也”,张志淳在《南园漫录》中评价道:
诋其有所避而不书,殆亦深窥其隐。以视真氏原书,殊未免瑕瑜互见。然治平之道,其理虽具于修齐,其事则各有制置。此犹土可生禾,禾可生谷,谷可为米,米可为饭,本属相因。然土不耕则禾不长,禾不获则谷不登,谷不舂则米不成,米不炊则饭不熟,不能递溯其本,谓土可为饭也。真氏原本实属阙遗,濬博综旁搜,以补所未备,兼资体用,实足以羽翼而行。且濬学本淹通,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
有根柢。其人虽不足重,其书要不为无用也。
四、衰落时期的衍义体
到了清代,拟作或节略《大学衍义补》的热情消减了,又回归到对《大学衍义》进行增删改补的路子上,徐桐、庆恕、强汝询等人的作品就是此类代表。与明代衍义类著作的繁盛景象相反的是,清代有关衍义的著作大量减少,以至于最终消失。清代的衍义之作有两个特点。
第一,对《大学衍义补》的研究热情明显下降。仅有陈宏谋的《大学衍义补辑要》,而推衍《大学衍义》的著作增多,如有徐桐的《大学衍义体要》、庆恕的《大学衍义约旨》、夏震武的《大学衍义讲授目次》、何桂珍的《大学衍义刍言》。表明清代学者们接续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而对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有所矫正的意图。深究之,清代衍义作品回归《大学衍义》这个趋向,与清初盛行的经世思想不无关联。李颙曾说:“《大学》是明体适用之书……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灭裂于口耳伎俩之末,便是异端。”魏际端也在回答友人时务之急的问题时说:“救今之急,无过于用古方。古方之效莫捷于《大学》用人理财之政。”陆世仪与唐鉴的认知则更具代表性。陆世仪就认为,《大学》之大不在于文字训诂,“大在心性,不在语言文字。今者读书之人,借径于语言文字,所以复其心性也,若不识字之人,识得自己心性,何不可与言《大学》之道。陆象山有言,若我则不识一字,亦须堂堂地还我一个人,正是此意”。把《大学》定义为心性之书,这是理学家的基本共识,而陆氏重提居敬穷理,更多的是强调实践。另外,陆世仪也重视治平之道所应有的天文、河渠、地理、兵法等实用型学问,他曾有言:“凡古之专家,伎术如天文形胜、兵农水利、医药种树、阴阳伎巧之类,皆儒者所不废,但当以正用之耳。”唐鉴则认为,“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离此者畔道,不及此者远于道者也”。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以强汝询《大学衍义续》为代表的衍义著作有回归学理探讨的倾向。
第二,学者个人著述发展到官方衍义,皇帝不再是衍义著述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组织者。这时,出现了两部衍义著作,即《御定内则衍义》和《御定孝经衍义》。顺治十三年(1656 ),承皇太后训用《礼记·内则》篇推衍出《御定内则衍义》,认为家齐而后国治,而家齐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内修。《内则衍义》全篇分为八纲三十二目,并充以古今经传之言及诸多行为事例,对妇女言行进行规范,以此维护清王朝统治。《御定孝经衍义》始修于顺治十三年(1656),成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书对《孝经》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总结。全书模仿《大学衍义》的体例编排,提倡大义忠孝,并倡导全民教育,以期维护社会稳定。这两部衍义类著作,一改明代经世致用之风气,实际上成了移风俗、正人伦的德育读本。清朝皇室除了编撰这两本衍义著作外,据《清会典》记载,光绪五年(1879),景皇帝还曾下诏仿《大学衍义》之例,推衍四书五经:
古今治乱得失之原,圣贤身心性命之学,莫备于经。君临天下者,所当朝夕讲求,期有裨于治理。着倭仁、贾桢选派翰林十数员,将四书五经择其切要之言,衍为讲义,敷陈推阐,不必拘泥排偶旧习,总期言简意赅,仿照《大学衍义》体例,与史鉴互相发明,将来纂辑成书,由掌院学士装帙进呈,以备观览。
清朝前期,官修衍义类作品的编撰目的是为了笼络人心、招揽士人,利用文化政策来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到了清朝后期,传统学术走至尽头,风俗颓败,内忧外患,衍义类著作也失去了继续推进的动力,转归为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