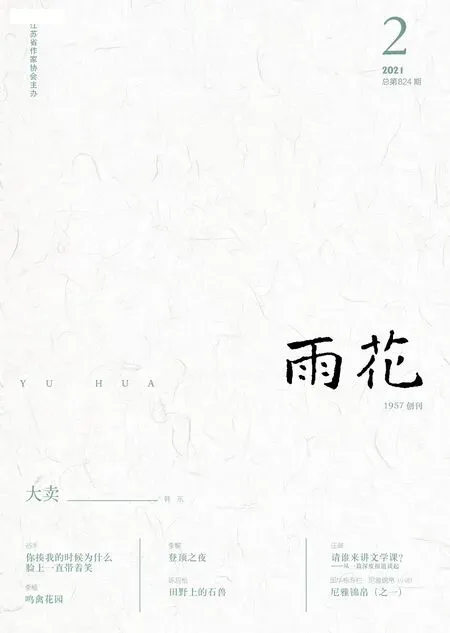雨霖铃
乡下黄昏时太阳的金色很像那尊弥勒佛的金色,不过弥勒佛的金色比在洪荒时期就有的太阳的金色还要持久。弥勒佛已经掉了许多金漆块,不细看像是泪珠。崔影有时看到,它在抽屉里,混在杂物中,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会看上那么一眼。他们家的房子早就重砌过,她小时候的痕迹已经不多见,弥勒佛竟被她母亲留到现在,像有鬼祟似的。
乡下黄昏时的金色太阳把铝皮包门上用铜钉钉出来的“家居黄金地,人住富贵屋”十个大字照得亮灿灿的。崔吉甫今天晚饭吃得有些晚,然而是在六月里,犹能看见天上的云是白色的。桌上摆了六个白瓷碗,碗里黑乎乎的,也看不清楚是什么菜。院门大敞到底,路过的人脚上的一双拖鞋拖天扫地,捧着只碗就踅到那门底下来。“呼哧呼哧”吃着碗里的稠粥,眼睛快要埋在碗里,却还向上翻,望着对面——对面是一间屋,屋里有三张电动麻将桌。里头几桌麻将刚散,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他回过头来笑说:“一直没看见你,崔老板原来在家吃鱼吃肉呢。”崔吉甫虽然吃得晚些,还是用块老姜烫了碗上海石窟门。他原不是个 于醇酒的人,一个人坐在上首,穿着四角小裤,已经喝了很久了,等崔太太上桌吃饭。他痩塌塌的光膀子叠在玻璃桌上,不时用手“啪啪”地打着脚间的蚊子。
然而等了许久,崔太太还没有上桌。他喝得两只眼睛红红的,忽然告诉她,下午在去菜市场的路上他拾到了一百元。崔太太马上过来笑问:“真的假的?”“屁,钱能被你拾到?那你也是走狗屎运了。”崔吉甫“嘿嘿”两声。崔太太怔了怔,心里直发烦,过了一会儿又问:
“你当真拾到啦?”
“没有一百元罢,有多少?你快告诉我。”
“婆娘,我是骗你的呀。”
崔太太叹了口气:“我就知道你骗我。”
忽然,她把筷子一横,举手就要抽他:“你要骗我干什么哩?”崔吉甫一面笑,一面往后避让不及。
“钱能被你拾到,我也能见到鬼了。”
不过见他不说话,她心下一凉。
她匆匆忙忙地泡了碗冷饭,从这只菜碗扠到那只菜碗,碗里的菜饭堆到她的鼻尖。匆匆忙忙地走到大门处,看见电线杆那里已经三五人攒聚过来,她要忙着一个个笼络。
“小茗香呢?又很久看不到她人了。”她伸手去揉眼睛,有只虫子飞进了眼睛里,她嘴里还含着一口饭。
“你原来竟不知道么?她去上海做了佣人呀,说她儿子一天大似一天了。”来人摇摇头说道,手里已是拿只空碗别在背后。
“我不晓得她呃——”她唱念起来。一旦涉及外面,便与她不相干。她现在光麻将就会打广东麻将、上海麻将、北京麻将,别的更不必说,在淡季便去补一补缺。
“她要生儿子哩,好了,现在早提倡男女平等了。在深圳,生个丫头先摆十桌酒。生个儿子,几天不见笑容哩。”崔吉甫插嘴,嘴里有块骨头,他闭着眼睛剔来剔去,脸上马上就少了点精彩,眉目不甚清楚。
“浪——”嘴里掉出一粒,他拾起来放嘴里,“我养的不过是个丫头!”
她听不得这句话,他家一门上兄弟两个,养的三个全是丫头宝。当初生崔影时,老大崔吉良坐在医院外,听到婴儿啼哭,搓着大手说:“怕又是个丫头呀。”她调过筷子头又要来抽他,他一面挡一面往后让:“嗳,打得人不疼么!”
“儿子你不是已养了个么,现被你藏在深圳!”她忽然停下来咬牙切齿地笑说。他只不理睬。其实心里怎么不恨,开玩笑的话,她倒当真了,在那里颠来倒去地说上多少话来。说你怎么不把她带回来,把我打到冷宫里去。说我又没拿刀子跟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是丫头,你也是一个。”她闲闲地坐下去,浑身大大地哆嗦一般。单听这句话,不知是可惜,还是后悔。
时候已经不早了,门口已经空荡荡,只有那穿鞋拖的人还站在那里。他本来是来看她的,不过没想到崔吉甫在家,心里计算着时间,多延挨一会儿,又不想让人觉得异样。本来那乡下的黄昏与夏夜是前后颠倒了来,一节长,一节短。于是那夏的半夜是舟过桥洞,仿佛走了会儿神,只朦腾一暗;黄昏却是轻绡远行,是上帝的视线,静下了心,多远也不算远。那树上的蝉鸣直钻进人的脑袋,仿佛泼了盆水至通红的炭上,激起了一层炭灰,噪剌剌的,多晚也不算晚。
于是云里“霍霍”地响了几声,像是颗石头从什么地方跌将下来,搓着。果然落了几滴大雨。“下喽!下喽!”隔壁邻居怪腔怪调地叫着,今晚看也没看成,又没有牌打,十分失望。
路过窗户,他特意略住了住,到底是不能一走了之。他闻到一股陈仓之气,其实是夏天的汗味。里头传来一个电视上的女人呜咽的哭声,只觉得画面切换跳闪得太厉害,看不大清楚。
他只很诧异:“怎么,你女儿也在家的么?”他觉得她大了后就没见过她,印象里她小时候脸黄怏怏的,嘴凶。照理说,女大十八变,现在也该秀起来了。他敲了敲窗户:“出来,出来呀,下喽,下喽。”里头的人在暗里,眼睛亮晶晶的,看了眼窗户,骂了句“猪猡”。他见她不出来也就走了。她坐起来,头有些发昏。她一双脚在底下捞来捞去地找拖鞋,鞋没捞到,倒蹭了一脚底板的灰,索性就赤在地上。
她挡在客厅门口,当胸抱住半只西瓜,用小钢勺对准瓜心挖出无籽的一块。嘴里塞不下那一块,吃得西瓜汁从嘴角漏下来。
“爸爸你喜欢姑娘还是喜欢儿子?”她斜眼看了他一眼。
崔吉甫眼睛一睁,说:“嗳,只要是我自己生的,我都喜欢。”
崔影在心里冷笑一声,心里想:“你喜欢么?你喜欢么?”
崔吉甫叫她快吃饭,她竹竿似的两条腿吊着条短裤站在影子里,衔着只勺子头仰得高高的,让那西瓜汁顺着勺柄流至嘴里。她没看见母亲,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她母亲就嚷起来:“你晚饭不吃,吃西瓜。你这叫人怎么吃,这叫别人怎么吃?都是你的?吃不完就剩在那里,大夏天的,糟蹋人罢了。”她母亲不忘用她的拖鞋在她的小腿上打一下。
“咦,你在哪里找到的?”她笑着把脚套了进去,走了出来。
她的脸这才清楚起来。
她的五官在脸上漾开来,像长在水上似的,虚无缥缈。然而脸还是黄怏怏的,很瘦。
因为是一只爆炸瓜,瓜底不知什么时候碰裂了一道口子,她明显感到瓜汁流到了手上。
她走近父亲:“看,一只大蚊子。”一张黏糊糊的手拍打在她父亲的四角小裤上。坐下来吃饭,才吃了两口,就说:“今天这晚饭实在难吃。”
“菜都热过几回了,等你们都不来。”崔吉甫说。
“你爸爸明天就走了,你不跟你爸爸坐车去?”她母亲出来问。
“你是早也要去,晚也要去,我是随你呵。”她坐在那里用一只空的豆酱瓶子喝开水,因为总有股豆酱味,喝得是蹙眉闪眼。
“你现在跟你爸爸坐车去不方便么?我是随你呵。”她重复着强调。曾经也有个仿似的场景,神气也是如此,她便把她顺手推进了深渊。哪里随得了她?她在家,她就得一日三餐地服侍她,跟她怄气,零碎地给她折磨,就是打麻将也不能打得痛快。只想到这一点,就使她暴怒。
因为他们家还未开灯,只看见一个个黑黢黢的脸影,也不知是什么表情。外面的路灯亮倒是亮着,弯腰呵呵地笑,照亮一切。因为背对着,所以脸色昏昏的。
“那你打我出去呀,我早哩,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打我出去呀。”
“我是打不得你了,万一打死了你,我还要给你偿命哩。”陆梁娥并不生气,只“咯咯”地笑了起来。
她转眼看崔吉甫,脸立刻凶起来:“你看她这是说的什么话!”
“我左说方,右说圆,我说你人不去,把东西给你爸爸带过去也好哇。人是为你打算,你倒这样瞎眼无情,该是我这样的?”
“你不该这样么,你不该这样么!”崔影在心里胡乱地一遍遍这样想。
“你明天确定开车去?你这杯酒难喝哩!”她到底在他膀子上狠狠地抽了一下。他斜定定地看她,让人害怕。他要是真打起人来也是能够下得去辣手的,但他只是用手抓抓,把眼一闭。
她父亲起得早,要与她吻别,她滚到床里去了,他还当她害羞。他也就去N 城了。
N 城的猪肝粥八块一碗,别的城也有得卖,倘使说出点别样来,N 城司机的脾气是最坏。
廊桥与鸡鹅庄各属一条街的头尾。那街尾的地势倾折而下,扩开一片。而街头的几处高楼的脊线便趁势而上,仿佛就更高似的,形势复杂,已经看不清楚。在这形势之中的突变与向上,更是一种压迫;不像鸡鹅庄,紧张也是紧张的,然而是曲折的,啰里啰唆的。那边的日脚就要比这儿的长一线,那边月色上来,这边太阳还是毛茸茸的。车辆还大段大段地淤积在下面,急起来的明知过不去还在那里失魂落魄地按喇叭。公交车也夹在里面,大个子,左右掣肘,作那尺蠖之屈。一旦顺通,便直驱出去。据说住在廊桥的人常常就这样坐过站,坐到鸡鹅庄那边去。
女人先是住在廊桥的,可是现在她连鸡鹅庄也坐过掉了。她惊醒地在人群中站起来,叫着:“司机,您刚才鸡鹅庄怎么没停?”车子还在自顾自轰轰地往前驱驰。“您叫我怎么走回去呢?”她一面急一面说。“你走回去嗳——你往后门走嗳——”司机拖着长腔,十分不耐烦,让人讨厌。“你刚才怎么不往后面走,你自己不会走么?”他还在那里呶呶不休。
她刚才看见一个矮个子妇女上车扔了硬币,听了有两声响。那司机看见那矮个子女人扔的是两枚五角硬币。“我扔五角干什么?我没有钱么?”她把钱包掏出来给他看,“我没有钱么?”“我看见你扔五角的。”“我扔五角?!”她一直不承认,往后走。司机骂起来:“好嘞——谁扔的五角谁是狗娘养的。”火气这么大,她只好等车停。
女人两手交握着,皮包的长带、装饭盒的帆布包带挽在一寸来厚的阔手腕上,往回走。刚才语音一定提示过了,司机见没人往后门走那还不开过去?是她没听见那语音提示。
未到鸡鹅庄就已听见地上排开的喇叭重复着的录音传过来——“不得了,不得了,海南芝麻蕉。不得了,不得了,海南芝麻蕉……”“西瓜削价一块一斤,西瓜削价一块一斤……”
小孩子嘴里吃着香蕉,在灌饼摊前站着,摊主是个安徽女人,冬瓜大脸,红赤赤的脸腮,扁扁的下巴,像北方人。“我这里马上就好。”她麻利地把那大饼掀过来,那清脆的油滋使人听不见她说的是什么。城管撸起袖子来,一双手撑在大腿上坐在旁边等她做完最后这一个。小孩子拿了鸡蛋灌饼,又把大人拉到油炸摊子前。那炸好的鸡锁骨垒在铁丝网上,小吊扇剥掉扇叶系了根红绸飞旋着赶苍蝇。那苍蝇在空中架着两翅踉踉跄跄地在别处停落下来,不一会儿又飞回去了。小孩子流着涎,大眼盯着摊主与锁骨,手指着要拣哪几只。
大人想起来要去买几双袜子,便去旁边的店,当门柜台上成捆的袜子叠得直抵天花板,袜子底下垫了一张美元图案的大鼠标垫子,非常触目。店家蹲在地上整理货物,一路踏着地上的睡衣睡裤就过来招呼。
第二天她又坐过掉了。她不是故意的,只得又往回走。
她刚搬来不久。房东韩老太就住在对过,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她家房子多,只有一个儿子,但不跟她住。她每天都乘公交车坐三四站路到隔壁菜场去跟别的老太买菜,她以为那里的菜是菜地里种的。
她拎着菜走了没多远,看见传芝,笑眯眯地问:“传芝下班啦?”她头发染过不久,顶心倒新长出一圈白色,像个太阳光圈。不过远看又很像头皮屑。
传芝略含笑点了点头,马上就预备进去,不愿多谈。她也觉得韩老太心里对一个在城市的独身中年女性有些偏见。其实她何尝不想多多巴结点,然而有一次搬完东西时,韩老太正好遇见她,就问她:“你丈夫已经走了?你自己一个人搬?”她马上就警觉起来,含糊说:“还有一两只小箱子,其余的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她急忙掩饰过去,因为她也是一个好强的人,不愿把自己的身世说得多么凄惨。
天这才一步一步晚下来。这里面积比先前小得多,摆设还没展开来,几个大的箱笼在旧处,很有些四面环堵之感。她搬至这里虽是为俭省房租,但对于买“每周一花”这样的事情,她也跟办公室其他女人一样。那花还不能够立即死去,便带几株回来培植着。老太太锁了门,手里摇着蒲葵扇,含着笑进来,说她这些花养得好,问她住这里可有什么不习惯的。“煤气有问题没有?”说着便用扇子掩着下半边脸踌躇着往厨房那边移动,仿佛会有什么危险在那里,一扭身却又倚住了门跟她搭话。她忽然注意到老太太的眼睛不时借故往对面的房间看,虽然用扇子不时地打着岔,还是被她发现了。房间里黑漆漆的,里头要是有个人躺在那里也不是不可能。袁传芝心里不禁诧笑,连着敷衍了几句,便笑着把她捧走了。
韩老太上次见过崔吉甫一次,所以总觉得男女团圆是另外一层意思。想到这里她皱了皱眉头,走近窗户,一个人拨弄一盆长得像草的植物,有些植物就是这样,在开花之前与草无异。但人又不是猪,又不是狗,一旦团圆就能“送做堆”的。这老太太可恨的地方也很可恨,总是一肚子的“总则我红颜薄命,一心待嫁刘彦明,偶然间却遇张瑞卿”。她没有丈夫很久了,所以对于这类事情的认识永远还停留在她自己年轻的时候。
她年轻的时候——那次她要跟他回去的,不过现在想来是个梦中笑话,因为自己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因为自己记得,所以也怀疑别人是否也同样记得这样清楚。这次见面也是她说话的时候多,热闹地把那窘态掩过去。大概他以为她后来过得一定很凄惨。
她特意周五下午请假叫了辆车去廊桥,想着周五应该是遇不到他的。因为N 城的白天里,除了周末外,都是十室九空。她虽然自己这样盘算着,倒还是碰见了。因为他就住在这附近。他像是刚从一个会议上下来,白色的西装裤,米白色短衫勒在裤子里面。脚上一双红棕色的皮鞋擦抹得晶亮,折痕却很重,衬得那酱黄的脸油腻腻的,使人觉得那白色的领圈有了层油汗的污渍。
他走近了问:“咦,你还没搬干净么?”顺手帮忙抬了抬。把手掸了掸,跺跺脚把那裤管顺了顺。她笑着说:“已经搬完了,就这几只箱子。上次车装不下,为这几只箱子再叫一辆总不值似的。”他旁边站着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异样地沉默,没有什么动作,头发从耳鬓两边垂下来,遮住了脸。她因为一直跟他讲话,也没顾得上仔细看。她的眼睛也不朝传芝看,站在那里,远远地看来往的车,并不看手机。她浑身并不发出一点声音,连眼睛都很少动,却并不古典,反倒是荒芜中的静。
“这是我女儿崔影,才十九岁,去年考进了这里的科大,来我这里拿点东西。”这样的铺陈并无溢美之嫌,可是让人听了,在心里总不免觉得毫无谦虚涵养可言。他仿佛拣了个现成的便宜,还面有得意之色。
传芝一旦把眼神转到她身上,她就马上走开去了。她父亲一定认为她是装佯,心里不由得起了一股恨意。
传芝因为过意不去,自己爬上爬下,抢着把箱子搬进房间。她其实也不愿意他多留,因此处处显得格外留心。这时候韩老太大约她随时随地都能遇见。她拿着一把钥匙,叮当作响。她这里到一到那里到一到,叮当之声就代表她森森细细的快乐。他若被看到了,老太一定也觉得奇怪,不是说走了么,怎么又回来了,那也就心下肯定了他不是她的丈夫,把它意译过来就是:那么你丈夫呢?允许你一个人在外面,莫不是家庭有了什么变故罢?
她在那里唱一支歌,什么“也曾”什么,“只为”什么,“又不为”什么,音调诙谐,很是热闹。想必是她天天都要来这么一支的,熟极而流,没看见他们。
两人看了眼菜栏,随口选了两笼烧卖、两碗猪肝粥。这里的猪肝粥做得没有一丝儿猪肝气,价格还要比那深圳的便宜。深圳的猪肝粥,他们大概忘不掉,因为太难吃,不知道是不是当时初到深圳吃不惯。他们十多年前在深圳时就认识了,那时两人太熟,所以倒不用天天去见面。以至于她什么时候彻底地离开深圳他也不大清楚。只是后来听崔长海提过一次她好像回老家去了。
“崔长海现在做了老板,把外贸公司开到北京去了,上海、深圳都有分公司,他现在是好了。”他说道,末了一句说得很轻快。他现在虽然没他阔气,但是也不见得就比他差。他摊子铺得太大。
“他那时就坏!”她说,明贬实褒。她也看出崔吉甫是一辈子也阔不了,虽然现在他各方面都是给人“吾生足矣”之感。
她那时为什么要对他说那些话?她只记得她说过,过年要跟他一起回来。一定还说过许多其他的话,不过这句话记得最清楚。像回忆一个人,永远只记得那人在那一两个场面里。他以前一直疑忌,看不上她是个外地女人,那就有许多潜在的危险。像一个人得了暗疾,不知道哪天就会爆发。她倘使真的有个不成器的丈夫,日子过不下去,那倒也好解决,可以拿一笔钱出来一劳永逸地把婚给离掉。他这时候却又不论她是真是假了,他总一定是不会怎样的。
“他回回都要喝一杯,酒量好。那时候去吃饭都各付各的,大家都没什么钱。”他笑着说,很愉快似的。两人说着一个不相干的人,等于把他们自己的过去草草说一遍。两人吃得很快,也是她避免提到各自的切身境况,其实两个人都想到了。
传芝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机会再碰面。崔长海有次到N 城来,叫了他去吃饭,他一直想把他拉拢过去。他去的时候,不曾想她也在那里,可见他们也一直有联系。
“听说你现在做到财务总监助理的位置了是不是,什么时候也替我把账管管?”他笑着站起来一手揽着衣襟,跟她碰了个杯。那崔长海一脸重肉,与年轻时候的浑胖不同,笑起来便也让人觉得只有七分是笑,三分藏着,深不可测。
“怎么能跟你说,我们是野路子出身,崔总走的是国际路线,不怕我把你的账管乱了?”传芝有说有笑。抬头便把那酒一饮而尽,她涂了口红,仔细留心杯口可有红印子。“我还怕就乱不了啊。”他觉得她这话不对。她当没听见,接着说:“虽说是总监助理,那也不过是虚名。你知道凡是‘助理’,做的都是人家不要做的。等哪天我扶了正,一定厚着脸,投个门帖到崔总那去。”他笑了起来,用舌头舔了舔嘴,不知道要怎样再开口,站起来又跟她碰了个杯。
她不得不哄着点。她脸有些烫,但该有把握的时候她是很有把握的。女人的这种抗力对于男人有时候有着非常的吸引力。她不怕他以后不来找她。对于吉甫,似乎早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吸引力。他也许觉得,这世上哪个女人不是女人。
“这么晚回来,她是你的情人?”崔影坐起来乜斜着眼恨恨地问。
“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崔吉甫咕哝一句,疲倦地往沙发上一坐,头往后仰。
“我在等你!”她又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脸窝在双臂里。他把她丢在这里这么久!他俯下身来要靠一靠她的脸,她把他肩膀往后推,手缩回来差点扫到他脸上。
“早点睡觉,你明天还要到学校里去。”他站起来泡了杯茶,打开电视看战争片,正好看见一场战役中两军对阵,机枪“特特特”扫来扫去。
“我问你,她是你什么人?”她又问。
“是我以前一个相识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就不肯对我说句实话,我就这样让你看不起,听不得你一句心里话?!”她弹跳起来揪住他的领子,直问到他眼睛里去。她时不时地怒起来,心里大概长久地匍匐着对他的恨。其实她也知道,他不过是无能。他不嫖不赌,不打人,这在中国算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她自己却常常觉得这样冤无头,债无主。跟他发脾气,他也不会怎么样。
“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使你这样不快乐么?”他握住她的手,她还是不放他的衣领。他也就随她去。他坐下来,脖子歪在一边喝茶看电视,退攻为守。
两人僵持了有许多时候,他终于守不住把那脸色黯下来,神色因为这种黯淡而近于肃穆。
“我是不快乐,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快乐,你是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我也不准备告诉你。”她终于放开了手,视端容寂,身子旋过去伏在沙发把手上,脸对着灯。她说虽是这样说,心里却滚油似的号着:你知道么?你知道么?而那炙热的灯光透过枫叶红的灯罩浴着她清呆呆的脸,照不了她的心。剖腹明心么,不见得他就能懂得。
“你衣食无忧,我供着你考完中学考大学。将来毕业如果想工作就替你安排,如果不想工作也随你,你这样活着不好么?还不知足么?”他果然也望着她。
“听你这话,你很不知足似的。因为你的童年饱受饥饿,你就看不得我们这一代享福。”
“我现在很知足,我很快乐。”他表情轻松地说。
“我不好骂出来的,你的知足不过是你拣了一个便宜,你天生养的是个丫头不是么?你还有脸说你很快乐。你哪有点人心哪?即便你是快乐的,你的快乐也不过是‘慰情聊胜于无’,‘有’也强如‘没有’。”
她就是这样一次次清醒地刺激他,使他痛苦难堪,因为适当的痛苦可以让人变得严肃认真,而这些品质可以促进人痛苦地奋进。
“也许你说的都是对的。可你看我现在有不如意的地方么?我没有。也许我是不快乐,但这世上过得不如我的有千千万,我不如的也有万万千。”他又来了。讽人的话现在说的还少么,已近于明骂还嫌不够么,不听则已,听之也则已,不如打嘴巴。
“你不快乐,你有我不快乐么?你有我不快乐么?”她残酷地盯住他问。
他就是好脾气也被她折磨得不耐烦,关掉了电视机,转过面来对着她急了起来:“那你要我怎么办呢?”
他这一说,她倒不知道说什么了。“你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你长年在外,你以为你有一个幸福家庭么?”她说。
“你还不知道罢,我那会在深圳,猪肝粥吃不惯,要死了,被人当面骂‘你就是每天三担六斗米也不会养活得像崔长海’。”
“小时候,数九寒天里我跟你姑姑、你大伯单衣单裤就那么在田里溜来溜去抓麻雀。那时候小,也不怕冷。用根棍子支着竹匾,等那三五只鸟钻进来吃遗在地上的粮,等得人跳脚却又无可奈何。”
“想着去树上抓知了卖钱,一抓抓到一条大蛇,你姑姑那时命都吓送掉了。”他罗缕着他过去的悲哀给她看。
“我为什么要出去?不出去就是个死。”他缓缓地道来,吹走茶叶呷了口茶。脸色没有先前阴沉了,只是十分地老了下去,像一个快乐的人忽然听到悲惨的消息。她想起过去所看到的一个心理实验,那暗影里用张网罟挡着许多猛兽,上面架座独木桥,人看不见可以大摇大摆走过去。若用灯照上去,便看清了那网下的恐怖,反而再也走不过去了。她懊悔这样戳穿他过去的痛苦来刺伤他的自尊,使他不像个男人,使他胆小。
“姑妈借的钱……‘今年卖完小麦,把钱还给你们’,她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
“她的钱她会还的。”他告诉她。
她不信。
“你为什么不去开那个口,你一开口,她准得还。”她可以想象她姑妈的难堪,算是为她报仇雪恨。
“就不要了罢。”她忽然又改口,眼朝空中望去。她惦记了很多年,明知道就是还回来也不是当年那个钱了。钱是借给他们家的,许多年前,崔吉甫第一次被崔长海带到深圳去赚了一笔。一大家子尝到了赚钱的好处。不过从此她就失去她的父亲了。她怎么看他都恨。
在这时代的巨轮下,一刹那,她想到那尊弥勒佛——无论遇见什么,它都能从她脑子里冒出来。她姑妈来借钱,她表哥也来了。他要把她弄出家门,他要把她诱拐了,她母亲陆梁娥同意了。是陆梁娥跟他合谋的?其实不是。那不过是注定的,是有宗教般的迷信。仿佛也是个阴天?她总觉得那是刚下完雨不久,屋檐还有雨滴,像鬼宅里的时钟“嘀嗒嘀嗒”。太阳神出鬼没,窗前一团团的蠓虫,像龙吐出来的金的绿的云。她表哥上完厕所回来了,低头在看什么。回到房间,他就要她把裤子脱下来,她坐在椅子上扭捏了会儿。他就问她,你要什么?她一时回答不上来。他随手拿起一个金链子吊着的弥勒佛给她。她隐隐觉得不够,便要了其他东西。她那时不觉可悲,但她始终记着此时,一直记到她感到此事悲哀为止。那她就再也忘不掉了。知道“诱奸”这个词时,她马上就想到了这个场景。她就那么坐在高椅上,在一个男人面前。
“外面下雨了?”崔影问。
他站起来去关窗户,“没有下,是外面风刮梧桐树上的叶子。”
“其实……我是不会告诉妈的。”她喃喃地说。她恨父亲,不过是因为她更恨她母亲。她母亲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原宥。这种原宥不是神佛的品质,是最为卑劣的隐瞒——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诱导她只能忘记。
现在,她父亲是个可怜的人。时代的巨轮“咯吱”地动一下也是寻常人的几十年,“可怜的人啊——”是的,全都是些可怜的人。
“时候真的不早了,去睡觉!”他催促着,她也就听话地进房间去了。那女人是她父亲之前相识的,她相信这话。
是有那么几次她来这里吃饭,起初不过是崔吉甫偶尔翻看手机里的电话簿翻到了她,想到有这么个熟人在这里。那情形就好比她吃过饭要走了,他预备送送她,便说:“不坐了?你这就要走了?明天还来?”她这样的到来并不使人为难。
因为崔影对袁传芝总算有个存心,已然近于一种天然的暗示,况且她对传芝的初次印象并不坏,便不可理喻地有种狂想,她会爱她的,像一个母亲般爱她的。
她来的时候把她培植的吊兰也带了一盆过来,因为是崔吉甫暂住的地方,临时找的房子的种种不便渐渐显了出来。这里没有花盆与珍珠泡沫,她便用剪刀剪掉可乐瓶子的屁股,把吊兰的根须泡在那屁股里摆在阳台上;用件蓝布旧衣裳围在腰间,站在那里切菜,把莴笋切得长长的再耐心地一片片叠起来,手握菜刀拿捏尺寸再一腰,大小便很均匀;倘使路过楼底,顺手从花圃里摘几朵栀子花上来,用线扣在衣橱的门把手上。诸如此类的这些富于生活气息的小动作使她颇显得是个女人,崔影更有几分神往。
那栀子花时间一长便生了铁锈色,她下次又换了簇新的,那大些的早被攀折光了,连未待开花的桂树也被人撅断了叉根。她分枝拨叶,找着了几只花骨朵,用水先养着。崔吉甫跷着腿在那里看电视,崔影挽着他的胳膊跟他并排倚在沙发上,陪着他看。之前的一部战争片子看了一半不看了,转换谍战片子,看了一半又换别的片子,仿佛总定不下心。她捧着花在他们爷儿俩前走过去,这父慈子孝的场景,俨然一个模范家庭。
“这花可真是香。”崔影站起来把那花从水里拎出来,“你闻闻。”
“我不要闻。”
“人家要你闻嘛!”她把花瓣一瓣瓣摘下来往他头上掷过去。
他抖动着身体把身上的花瓣全部抖下来。她觉得很好笑,大笑个不停。
“这才像话嘛,要这样笑。”她听到后马上就不笑了。
袁传芝看到这一幕场景反而先忍不住扑哧一笑:“我家最大的一个女儿也已二十了,明年结婚。十九岁的二儿子也已出来打工,那细的才八岁,还在上学。”
“上星期我回去了一趟,那细的就跑过来跟我说‘妈妈,妈妈,昨天我看到只麻雀受了伤,它……它很可怜’,赖着不肯走。”她只说着她孩子,不说她丈夫。
“我小时候给一只受伤的鸽子灌白酒,想到要做醉鸽吃。”崔影礼貌地打着岔。
“还有一次,他要一个变形金刚,我说你已经有个了,不能再买了。他一双眼睛望着我说:‘妈,我那是手动的,这是电动的,这个很高级’。”这些没有意思的她也能够看到:真聪明,什么都能够懂得呢。
“我小时候可以把空的八宝粥瓶子堆出十八个花样来,就那几只空瓶子,我没别的玩具。”这话明显地带着点吹嘘,然而,似乎还不够。
“也就是前一段时候,我把室友的一个面膜当糖吃掉了,我怎么看那小圆球也像颗糖。我那室友大喊大叫,其他人都在笑话。”她穷形尽相地把自己说成一个孩子,一个天真的小傻子。然而传芝也只管笑着。她由这源头,信口道:“我那最小的一个也喜欢吃糖,牙齿都蚀光了,可不允许他再吃了。”她听着实在有些讨厌,越来越不耐烦,借故站起来去拉开客厅的窗帘看外面。阳台上的那盆吊兰已抽了长茎:“你看,阿姨,这吊兰已要结花了。”她顿了顿,又说下去。她也就不再理会。那长茎萦着绳子一直绞到了屋顶角,再也伸不过去了,骤然一个回马枪,摇着病绿像条竹叶青蟠在半空里探着头。
看得出来她很爱她家的孩子,她家孩子又多,她仍固执地爱着每一个,那么,倘使她做了自己的继母,当然也是能够这样爱她的。要爱她,她就得做个孩子,一个天真的孩子。做自己的继母?她不能够明白自己的心理。让一个陌生的女人做自己的继母又有什么好处?
崔影看了眼她的父亲,她父亲瞌睡得眼睛都睁不开来,把头慵懒地仰在椅背后,艰难地张着嘴,也不知道睡着了没有。外面太阳的气焰还很盛,照在白墙上、红木家具上,久久地,动也不动,仿佛还日当正午。他们这阳台是独独地凸在外面的,车子在尘海里刮起尘帘兴冲冲地来来去去,紧贴着这四周,狂飙震耳,使人不能够消停。然而,这里面依旧是个真空的气泡,裹着这里的一切起伏在海的深蓝里,女人子宫里未育成的婴儿,全然未知。传芝要走了,她拦不住,站起来说:“爸,你看阿姨要走了。”他愣愣怔怔地站起来:“唔?你不坐了?时候还早,喝杯茶再坐会儿。”她笑说:“不坐了,明天要回去一趟,今天要先准备。”他也不再坚留。崔影送她下楼,他这才跌跌撞撞往房间里去。
廊桥站的站台就在大门口不远处。“阿姨再来玩啊!”她一路挤进去,不知是否听得见,车子拐个弯就不见了。原来不见也很容易。通红的太阳都已在鸡鹅庄那边,呵,已是傍晚的时候了。
传芝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崔影又不便问她父亲。她父亲模棱两可,她就更不能够禀明态度。她果然也没告诉她母亲,不告诉,就是一种小小的报复。
她决心要去看她,事先打了电话,说她父亲因为不放心,问候她。临了那边说让她有空过去走走。好在不算远,就在鸡鹅庄。路过鸡鹅庄水果摊,摊上的苹果绿、草莓红、山竹紫,纷纷杂杂全堆在外面,有种静物的美。她买了三十颗大草莓、四只苹果、四只橙子。传芝没想到,一句客气话竟使她真的来了,忙着去菜场买菜。菜市场离这有些远,她坐在那里安静地等着。
传芝一回来,便去厨房做菜。厨房太小,她进不去,便用小刀切苹果,切成许多块,每块都插一根竹签。把那草莓蒂一只只掐掉。但是她发现这样跟她大段时间隔着,像是白来了一趟。
“有苍蝇!”她大叫起来,捞起一件衣服便一路打,打到了厨房里去,便停住了脚在那里用眼睛找来找去。
传芝今天穿件黑色的蕾丝镂空前后挖V 形领的长袖衫,后面用根黑绳横在那V 字上。她想起为什么日本的女人穿和服总要把后领拉得低低的,像有只小手拉住往下拽,后脖颈抹得雪白,齐整地再横刀一切。然而现在传芝的后脖颈是赭黄色的,杂色的,那镂空里密密麻麻的肉点子,像孩子的红嘴吮吸着那肉,恨不得把她整个人吸进去……
窗外的光荧惑着那苍蝇,一头撞在了玻璃上,舞了一阵,还要去撞,她把窗户打开,它便顺势飞远了。因为个子比传芝高一些,挤在一个局促的空间里让她发现这也是一个佻达的优点,可以夷然地俯着头颅与传芝说话。“我就看不得家里有只把苍蝇!”将来她还要高,比传芝高出一个头来。而传芝家的那些孩子像一只只灰色的大老鼠似的。大女儿早就出来了,明年就要嫁人,时间长了只能是一个乏味的妇人;大儿子目光短浅,经不住眼前的诱惑,似乎也是没多大出息。将来她读完大学,读研究生,出国再读博士。她这时想到了她家的钱,她要把它们全部花在这上头,把它们全部花完,作为补偿。想必她母亲在这一点上也无可排訾。她有一种奇异的胜利的感觉。
“阿姨,您今天这衣服穿在身上……我想起一句话来。”她俯仰开阖,不时注意她的脸色。
“我母亲也有一件差不多的,但是她人胖,穿起来可没有您这感觉。嗳,您要是我母亲就好了。”她几次试探着,如果要把她这话当个孩子的话也完全可以。
“我做不了你的母亲,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看得出来你爸爸爱你。”
“我得承认他是个好人。他不过是老了才想起来他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已经老了,他或许是爱我的,不过,他的爱已经不值钱了。”
“真的,你爸爸,我看见他那时一个人……”
“我知道。”
她想起她自己的丈夫是个美男子,起先她也仗着自己年轻,在人后要怎样便怎样,后来便仗着有人在的胆子,只骂了。她也看重过他个子是否高,皮肤是否白,这都是蠢人的行径。到底重要的还是他的负责与否。
然而,她离不了婚。尽管这次回去跟家里闹翻了。她回去跟她的丈夫吵了一架。他把她刚替他买来拉货的面包车卖掉了,换了几个钱,去吃喝,去嫖。她气得要打他。她让几个孩子跟着他,暂时地要他照顾,使他不得不努力振作。至少撑过这几年,等孩子们都大了,上完学自己出去独立。这次她仿佛是彻底灰了心,因为平时她跟他吵也吵,他并不还手,似乎已经是一种认错态度,指望着他能够好上一阵,她也就可以把日子挨下去。可是这次,他不仅掼东西,还动手打了她。她婆婆就用手捶着他,骂着:“我把你这畜生,我把你这畜生绑起来狠狠地打一顿。”那老太婆凭着多年的经验似乎也觉出了危险,所以虽然这样不给儿子留情面,也希望儿媳妇能够再站出来说几句话,那么这件事也就囫囵个儿过去了。她冷冷地站在一边,不置一词,把自己化妆的镜子也带走了。几个孩子是一直袒护母亲的,所以也就不作任何表态。最大的那个女儿表示可以在家里看护妹妹,每月把钱寄到一个亲戚那里,让妹妹每个月秘密地领用。她似乎对她的奶奶也失掉了信心,因为把钱寄给她,他儿子马上就咻咻地嗅过来了。她从纷乱的思绪里理出一个念头,就是要把婚离掉。然而时间一长,这个念头渐渐也变得不可靠起来,以前没有离,拖到现在再离,那也就是证明过去是她一直做错了。这样一桩冒险的事,在她,不大可能。所以她情愿就这么忍受着,仅仅是忍受下去。
“我也老了,再怎么穿也不过这么回事。”她不由得沉默下去,“倒是你,你又不缺钱,少年青春,要打扮起来了。”她笑说,“改天去陪你买几件去。”因为过去的一切使她形成一种单纯而狭隘的苦楚,她是不缺钱,然而她听不得这话,因为她的钱应该最是不受人妒忌的。
“我是不缺钱。可我还是穿不了高跟鞋,涂不了口红。”她继而叹口气道,往远处看了眼,望不多远便被对面的楼挡住了。倒是看见楼上的月亮正对着她们这厨房的窗户,仿佛就只有她们这一扇有,别处没有,白凄凄的。她不能穿上高跟鞋,涂口红,否则她就做不了孩子了。她就得做个女人,要去爱人,不,她爱不了人,她都没有得到过爱,凭什么她要去爱别人?
“我……我还在上学,这……恐怕太早些了罢。”她低声解释着。
两人吃完晚饭,就着茶几吃水果,有说有笑。崔影用脚勾住那椅子,那椅子一搠一搠的,并不倒下去。她调皮地把头枕在传芝的肚子上,她的子宫上。传芝也就用手抚摸着她的头。
中秋节那天,她跟父亲回去了一趟。透过玻璃她看见母亲正用两只手指钳着痰盂出来。她从城市回来,看见这一幕,她母亲的脸上微微笑着。
邻居看崔吉甫回来了,都来围着她家门往里看。也不知为了什么小事,她就跟他吵,众人都劝她看开点,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她就跟人说:“将来,我总有一天要跟他离婚的。”他们都劝她不要犯傻。他们说起崔吉甫一个人在外可抵得上家里几个大劳力哩,她便说:“啊呀,他岁数大了,再挣也有限了。将来他老了,托人给他找个看大门的事做做,他要再老些了呢,就回来放鹅。”她现在那刘海新烫成细细的密圈贴着圆脸,十分富态。不过还是因为他痩,跟她趋于两极,她又天天坐在那里,便给人一种正在发胖的印象。人都说她命好,年纪不大就在家做了菩萨。所以对于她说的这些话,也就当个笑话来听。
中秋一过,日子仿佛蓄极则泄,马上就要到了年尾似的。她父亲更忙了。她也就经常去传芝那边,有次去的时候,她的两个子女也在,她先是奇怪。那大女儿长得跟传芝很像,传芝客气地给崔影倒茶,问吃过饭没有。袁传芝夸她那位女儿说:“她嫁的人好,在外资企业里。她自己现在也要升职,她工作勤奋。”她的大儿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似乎很害羞。她不便多坐,冷着脸盘算着时间差不多了,立刻就告辞:“我以后永远不会再来。”突兀地,直接地,一颗炸弹扔在了那里似的。她知道自己做得不得体,不上品。
她走在路上,人直往下溜,她后面的整栋楼也往下坍,瓦砾快要埋了她。她站不住,还要往前跑,路上结了冰,她又不能快,心都急烂了。这次明显是来替她介绍朋友的,把她的儿子介绍给她,因为知道配不上,就把他的姐姐说得一枝花似的。一个可怜的母亲,真把她当一个天真的小傻子似的。
全不值得,全不值得!研究生,博士,爱,全都不值得。她父亲说得对,在这太平世界里就这么知足地活着不好么?廊桥的住所,她父亲不多久也搬走了。她一毕业后就去工作赚钱,很是吃了些苦,时间久了,她也渐渐疑心她过去的不快乐不过是个梦。这是个轰隆隆的时代,把她脑子里的一切暂时地震出去,那是救了她,不能由着她痛苦下去。她觉悟过来就好了。电影中那些异形怪物,需要一个什么刺激就会变回原形。她现在觉悟着,暂时可以做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