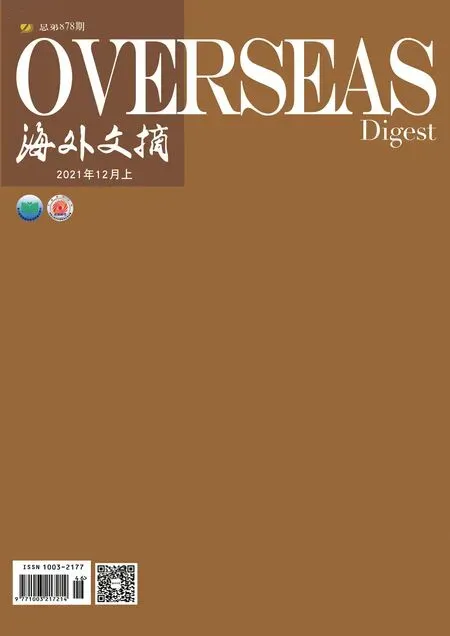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雅”在张培基中国近代散文译作中的表征
戴蕴仪 姜占好
(东南大学,江苏南京 215123)
0 引言
古汉语中,“雅”的常见意义是“纯正的”,“合乎规范的”,有“正”的含义,因此“雅言”即为“正言”,“雅声”即为“正声”。无论在艺术界还是翻译界,对于“雅”的讨论从未停止。在严复提出及后世学者逐步完善“信达雅”翻译理论的过程中,针对“雅”的讨论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1)“雅”是“古朴典雅”,“雅”文常与句式、修辞结合。(2)“雅”的内涵是变化的,自然流畅的译文也可称之为“雅”。其中第一点常见于传统译论对“雅”的理解,第二点则更多见于传统译论现代化转化过程之中对“雅”的不同理解,本文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所提出的“雅”的内涵不够完善,还有待进一步理解和深化。本文拟结合张培基散文译著,对“雅”的内涵进行三方面的补充,填补文学翻译理论中“雅”的内涵中现存的空白,并且结合译例探讨如何将“雅”更好地运用于文学翻译实践当中。
1 文献综述
“雅”与“俗”的问题首先是艺术思想领域的问题,罗丹认为:“在艺术中,有性格的作品,才算是美的。……在艺术中,只是那些没有性格的,就是说毫不显示外部的和内在真实的作品,才是丑的。”(《罗丹艺术论》第25-26 页)将大众对“美”与“丑”的定义运用于专业艺术鉴赏显然不合适,与之同理,在翻译领域,对“雅”与“俗”的定义也应给予更加开阔的视角。20 世纪末就有学者认为:“译文必须服从于原文的真实——原文粗俗还其粗俗;原文文雅还其文雅……此即严复所谓‘雅’的本义。”同时期,还有学者认为:“作为翻译标准的“雅”则是指“能被读者广为接受的语言美”,并且对“雅”的定义需做到因时而异。语言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此与之有紧密联系的翻译理论不能是固定不变的死标准,而应做到与时俱进。与之理念相同的还有著名翻译家沈苏儒先生,其在《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中指出:“比继承更重要的是发展”,因此“‘信达雅’不可能是一种完整的翻译理论,……必然不限于几条空洞的原则。”学界对“雅”的内涵的理解还有待继续深化。在《水浒传》第三回鲁达痛打郑屠章节中有这样一句原文:“直娘贼”,有观点指出若忠实于译文译作motherfucker 会使译文失去美感,译文的“雅”在这种“本就不雅”的原文中自然难以实现,因而得出结论:“‘雅’之作为翻译标准都是不能成立的”。还有同时期学者表示:“‘雅’就是‘典雅’,是再现符合原文文体语言的‘典雅’风格”。此观点放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是成立的,但还缺少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分析。译文不仅要考虑原文文体语言,对译文的目标群体及翻译目的也要进行思考。对于严复在《译例言》中提到的“信达雅”,陈福康和马祖毅也分别站在严复的角度对“雅”进行了解读,陈福康认为严复的“雅”是“偏重于美学上的古雅”,马祖毅则认为是“鄙薄通俗文字及口语”陈福康与马祖毅对严复所提“雅”的理解有据可依,但放在现代视角来看,还需继续丰富其内涵。
综上可知,对于译文“雅”的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各不相同,本文认为:(1)基于受众及社会环境的变化与发展,学者应多变,灵活地解读“雅”在译文中的运用;(2)“雅”不只局限于修辞与遣词造句,随着时代的发展,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引起目标读者阅读兴趣的译文均可称之为“雅”。(3)译文既要遵循翻译的基本理念,又要有本民族文化的特点。本文将结合《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部分译文对上述三点做进一步解读。
2 动态的视角
翻译理论要动态地定义及理解。咸丰年间,人们推崇的是古雅的文言文字,古朴典雅的文字风格深受士大夫阶层的青睐,因此知识分子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常以“古朴典雅”为标准。同时代的严复所提倡的“雅”的翻译理论便是顺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严复所写的《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信达雅”原则做这样的描述:《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因此从这样的表述中可以推测严氏所指的“雅”更着重于句法与修辞,也算是顺应了时代背景的需求。但在其致梁启超的书信中,他这样说道:“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
也就是说,单单行文语言上的“雅”是不足够的,做到意思明确观点鲜明才是译文的核心。但到了白话文盛行的今天,依然恪守清代对“雅”的定义显然已经不合适了,应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即以动态视角重新定义“雅”。
本文从张培基先生的散文译著中摘取了这样两句,加以佐证:
例1:对于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
While you are in the prime of life, why not devote yourself to a special field of study?
例2:我又不比人家高贵。
Why should I think it beneath myself to travel by wooden boat?
若要以明清时期对“雅”的定义为标准去评判这两个句子,译文语言显然与“古朴典雅”的文风相距甚远,既没有复杂句式,也缺少修辞手法。但从现行白话文角度分析,译文整体通顺流畅,结构简单却成功塑造了作者鲜明的性格特点。若要将译文按照“典雅”的文风去修改,当代读者再去读译文反而会感到生硬。此外,一些译者倾向于大量使用抽象性词语以及复杂的句式来使译文看上去更为“文雅”,但仔细阅读其内容便会发现译文所表达的不过是十分浅显的道理。因此,古人所崇尚的“雅”并不一定适用于现代著作,其推崇的文风也不一定能为大众所接受,译者还需以动态的视角看待“雅”原则,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其内涵。
3 目标读者影响下的“雅”原则
目标读者是译者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分析何为“雅”研究过程中值得考虑的环节。
清朝末年(1644-1911),翻译家梁启超将拜伦的诗歌Giaour 介绍到中国,创作这首诗旨在呼吁希腊人民觉醒,为民族独立而战。那时的中国正受到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残暴的剥削与压迫,梁启超便翻译Giaour,以此鼓励年轻人为国家和民族危亡而战。考虑到诗歌的抒情性和激励作用,梁启超将诗歌译如下:
...
Clime of the unforgotten brave!
Whose land, from plain to mountain-cave
Was Freedom’s home or Glory’s grave!
Shrine of the mighty! Can it be
That this is all remains of thee?
……
呜呜,此何地猗?下自原野上岩峦猗,
皆古代自由空气所弥漫猗,皆荣誉之墓门猗,皆伟大人物之祭坛猗!
噫!汝祖宗之光荣,竟仅留此区区在人间猗!
译文用语固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译文的“雅”不仅体现于译文的语言风格。梁启超翻译Giaour 的目的在于激发青年人为国家民族而战的斗志,因此译文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在其影响下保留了甚至更加突出了诗歌的激励作用。通过此例能得出,若译文语言符合目标读者的审美需求,达到翻译预期目的,那么即可将此译文纳入“雅”的阵营当中去。
严复的译文面向的目标读者是知识分子,为了扩大译文影响力,达到预期翻译目的,译文语言需要迎合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标准,因此严复所追求的“雅”即为以译文表述清晰为前提的典雅文风。而在现代,自然流畅的文风则更为大众所接受,因此若译文的目标读者为大众群体,“雅”的内涵便不能再以明清时代的著作风格为标准进行定义。受当代目标读者的影响,“雅”也应被赋予全新的时代内涵,即为自然流畅,朴素饱满的语言风格。
因此对于“雅”的内涵,其定义不应只由学者规定,读者的审美与阅读习惯应同样起到指导作用。
4 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影响
若译文语言风格能够体现当地的语言文化,那么也应将此类译文纳入“雅”的范畴。在张培基散文译著中有这样一例:
例3: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
...what little I know about it is probably a mere drop in the ocean.
在汉语中,“牛的一毛”一词取自中国家喻户晓的成语“九牛一毛”,为在译文中译出其含义,采用直译法固然不可取,注释法可以达意但会使译文显得呆板。因此张培基先生将其灵活转译为“a mere drop in the ocean”,译文虽无复杂结构及华丽词藻,但原文本意不仅得到完整表达,而且符合译入语的用语习惯,体现了其语言的文化特点。本文认为如此译文可完全纳入“雅”的范畴。
此外,较为典型的例子还有严复对《圣经》的翻译。在严复看来宗教是外语中最难翻译和理解的部分。为了使译文通俗易懂,他充分考虑本民族文化,使用中华文化典故和《史记》中的人物进行翻译:
例4:And, though one cannot justify Haman for wishing to hand Mordecai on such a very gibbet, yet, really,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Vizier of Ahasuerus, as he went in and out of the gate, that this obscure Jew had not respect for him, must have been very annoying.
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军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
这样译来,译文不仅便于目标读者理解,还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语言文字的特点,使译文更具“中国味道”。可以说,在对“雅”的理解上,除了需考虑随着时代背景变化需采用的动态的视角及其目标读者审美趣味的转变,还需考虑译文是否能够合理体现译入语的语言文化特点,给予“雅”的内涵以更加全面的理解。
5 结语
本文对于“雅”的内涵提出了三点补充,同时结合张培基散文译著及其他译者的经典案例对上述三点补充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实证对理论予以支持,具体总结如下:(1)对“雅”的内涵的理解需根据时代背景进行调整,及以动态视角看待“雅”;(2)不同目标读者对“雅”的理解并不相同,“雅”的内涵不能单由学者进行规定,也应顺应目标读者的审美进行调整;(3)体现译入语文化特点的译文同样符合“雅”的翻译理论,即使译文不使用精妙的句式与多变的修辞,语言风格不符合“古朴典雅”之标准,但若体现译入语(如中华文化语言文字)特点,也可将译文纳入“雅”的范畴。以上三点结论的主要对象是文学翻译实践活动,但“雅”的翻译原则能否或怎样运用于科技类文章还有待结合具体案例作进一步分析讨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对于“雅”的内涵依然具有探讨价值,这需要译界以全新视角进行分析论证并运用于翻译实践活动当中,希望通过以上讨论分析,“雅”的内涵遂得以进一步深化,同时,对于在科技文章中“雅”的实现问题,期望学界也能予以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