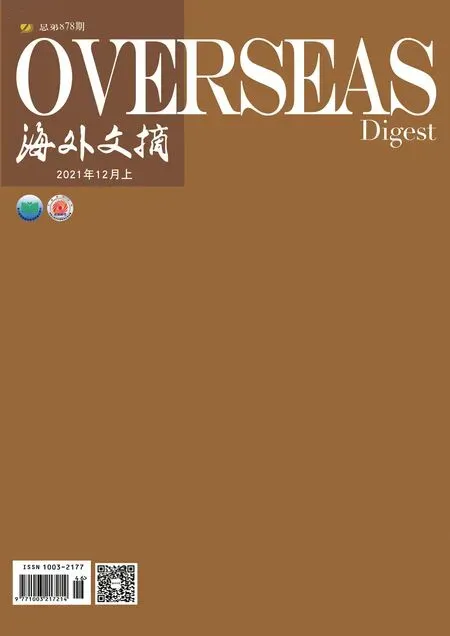论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应为含义
夏铭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200042)
在我国刑法法条与司法解释中,共规定了具有三种不同意义的逃逸行为,其性质、含义错综复杂,不仅在理论上引发了重大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莫衷一是,甚至发生同案异判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面对此种困境,分析有关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辨析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含义、明确定罪量刑时逃逸行为的性质与影响,对于改善现状,确保司法的公平公正,促进法院正确适用法律,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1 解释“逃逸”的体系限制
交通肇事后逃逸由两个行为构成。第一个行为是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是在构成交通肇事罪后,进一步实施的逃逸行为。只是由于法条的特别规定,才在特殊情况下将肇事与逃逸行为结合成一个加重的交通肇事罪。将肇事和逃逸看作当然的一个行为的观点,“根本上是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场合所涉及的行为个数作了错误的判断,没有看到逃逸行为具有独立于交通肇事行为的性质。”同样,也可将司法解释所规定的逃逸入罪分解为过失致人重伤行为和逃逸行为的结合。
那么,法律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三处逃逸行为的含义是什么?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吗?很多学者通过有力的论辩主张几处逃逸的含义各不相同:“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三种情况而言,立法目的各不相同。”“……一是单纯交通肇事后逃逸,这是基于行为人逃避法律责任而加重处罚;二是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这是基于行为人对被害人不及时救助而加重……”也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作为义务的位阶性:不仅各个逃逸之间的含义不同,甚至同一规定中的逃逸含义,也要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有所变化。例如,根据此种主张,肇事产生受害人死亡风险时的“肇事后逃逸”,和没有产生死亡风险时的“肇事后逃逸”的含义是不同的,构成逃逸所需的行为方式也不同。
此类对逃逸含义进行多样化解释的观点,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兼顾了逃逸行为可能涉及的各种作为义务,符合防止被害人损害扩大的规范保护目的,但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法条的实质解释必须限制在形式解释的范围之内。具体到交通肇事罪,就是对“逃逸”进行目的解释时,不能逾越“逃逸”通常含义的界限。遗憾的是,许多理论观点一味关注立法目的的辨析,而无视了过度强调救助义务的“逃逸”早已突破了形式理性的界限,无怪乎被人批评“规范目的解释论者以实质解释名义,抛开文义解释而径直采用了规范目的解释方法。他们往往不是讨论逃逸本身的问题,而是在猜测和推知立法者或者法律想达到什么目的。”想要对“逃逸”的含义作出正确解释,就不能直接诉诸于立法目的,而应该先从对相关规定的形式入手。
首先,在解释逃逸含义时,不宜对数个逃逸作不同解释。确实有对刑法中同一词汇做不同解释的情况,但那是以同一词汇处于不同法条、不同语境下为前提的。交通肇事罪的特殊之处在于,《刑法》第133 条直接连续规定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刑罚加重,“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再次加重,中间以分号间隔。法条规定明显呈现出一种肇事-肇事逃逸-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递进式思维。“第2 档规定的‘逃逸’,是没有致人死亡的逃逸,它专指‘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的说法虽然在逻辑上更加合理,但恐怕不能为社会常识所认同。两条互有递进关系的规定中,作为递进关系中介而存在的两个“逃逸”意思却大相径庭,这种解释路径未免过度关注实质,而忽略了词语可能含义的形式界限。这里的形式界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对词语内容的形式限制,而是根据前后文与法条结构,对词语关系的形式限制。刑法第133 条的法条结构,蕴含着“两个‘逃逸’的解释须协调一致”的隐性形式界限和要求。
2“逃逸”规定的应有之义
就“逃逸”词语含义本身而言,本文认为,基于三方面理由,“逃逸”应当解释为“逃离现场以逃避法律追究”。
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解释中清晰阐明了肇事逃逸所包含的两个关键要素:逃逸的动机应当是“逃避法律追究”,逃逸的表现形式应当是“逃跑”。如果说“逃逸”尚有一丝争辩的空间,那么司法解释中明确化了的“逃跑”则没有任何歧义的余地,只能是指物理性地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
这里引用的是最高法于2000 年的交通肇事司法解释,由于存在许多与刑法理论冲突之处,遭受诸多批评,甚至有学者直接拒绝承认司法解释中某些规定的有效性。虽然这些批评正确指出了司法解释无权立法,相关规定没有理论基础、不应在实践中适用等问题,但就其性质而言依然是“立法论”层面上的批评,而没有司法层面上的意义。这是因为学理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与德国司法人员高度重视学习法学家的意见,法学家能对法律作出权威解释的“精英话语体系”不同,中国学者的意见,在基层司法活动中完全无法抗衡国家机关的权威指导。自顾自地否定最高司法机关的指导文件,把希望寄托于基层法院在实践中主动推翻的司法解释而听从学理意见,是不现实的。应当在尊重司法解释的基础之上进行法律解释,唯此才能真正起到指引司法实践的作用。基于上述理由,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对“逃逸”作出的定义虽名义上不具法律效力,现实中却具有接近刑法条文的权威性,实际解释条文时应当将其视为教义性的解释基础。
另外,认定“逃逸”为“逃避法律追究”,并不排斥救助义务的存在。解释“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时依然可以兼顾肇事人救助伤者的义务,尽量实现督促肇事者履行义务、防止危害扩大的立法目的。
3 “逃逸致人死亡”中的“逃逸”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如前文所述,交通肇事后逃逸由肇事行为和逃逸行为两个行为构成,而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了两个行为之间的关系。首先,肇事者应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其次,“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应当是肇事者的逃逸行为导致的。问题在于,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不可能引起任何人身风险,怎么可能导致被害人死亡?按照这种思路思考下去,自然得出的结论是:既然逃避法律追究无法导致死亡,那么逃逸的含义就不该是逃避追究,而应当是不履行救助义务。但这种思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忽视了形式理性的藩篱,为了追求实质合理性而“深深陷入了法律实质主义的泥坑”,不足以为信。
实际上,“为逃避追究而逃跑”的定义和“致人死亡”的规定之间不是非矛盾不可的。如果逆过来看,可能的解释路径会更清晰地显示出来:“逃逸致人死亡”逆过来,就是“如果行为人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被害人就会得到救助而不会死亡。”可见逃逸致死的因果联系不应是“逃逸”导致死亡,而应当是“逃逸”导致“不救助”,“不救助”继而导致死亡。由于逃逸致人死亡的肇事人对死亡结果罪过形态必须是过失,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过于自信的逃逸致死”和“疏忽大意的逃逸致死”。
就肇事人因疏忽大意而没有注意到被害人面临死亡风险的情况而言,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可以转化成“为逃避追究而未能认识到其救助义务,没有发现被害人面临死亡风险”的问题——因为刑法当然地期待并预测认识到救助义务的肇事人会履行其作为义务,所以肇事人未认识到救助义务可以视为致本应获救的被害人死亡的根源。疏忽大意的肇事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的方式也就可以概述为“因为逃跑而没能意识到救助义务”。在肇事人不逃跑就能意识到自己的救助义务的情况下,肇事人逃跑了,因而未能意识到自己的救助义务,被害人因缺乏救助而死亡,此时肇事人构成逃逸致人死亡。逃逸者构成这种逃逸致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比如,肇事者在冬天夜间醉酒驾驶,将行人撞成重伤,以为人已撞死,遂未停车查看而立即逃离现场。如果肇事人未逃逸,社会一般人的做法应当是及时停车察看并报警,被害人死亡的结局本可避免。而肇事人为了逃逸而放弃了与逃逸冲突的“本可救回被害人”的选择,因此构成“逃逸致人死亡”。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肇事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逃跑行为导致的。
对于过于自信的肇事人而言,达成逃逸致死的条件十分苛刻。因为肇事人此时对于被害人的死亡风险已有认识,只是自信被害人不会死亡。此时肇事人的逃逸行为和报警救援在客观上并不矛盾,可以同时存在,所以被害人得不到救助死亡的结果很难与逃逸行为建立联系,而只能定性为单独的过失致人死亡。虽然理论上肇事人依然可以因“害怕被追究,所以没有报警”而构成逃逸致死,但是这种心理状态是绝难证明的。可以说在种种前提限制下,过于自信下的逃逸致死是几乎被“虚置”的。当然,也有逃逸行为与救助行为直接冲突,肇事人过于自信被害人不会死亡而逃逸的情形,但这种形式的交通事故太过罕见,条件之苛刻只能在理论中实现,所以并没有多少讨论价值。
4 入罪型逃逸中的“逃逸”
入罪型逃逸,即根据司法解释规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且负事故主要责任,肇事人逃逸的,构成交通肇事的基本罪。入罪规定本身并无太大争议,然而主要的问题在于:如果肇事人的逃逸造成了被害人死亡,能不能构成逃逸致人死亡?本文认为,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不能构成逃逸致死的加重情节,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排斥了入罪型逃逸中加重情节的成立。《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构成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情景限于“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而“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被规定在了第二条第六款,入罪型逃逸被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排除在外。同时,如上文所述,刑法第133 条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具有递进性:“构成交通肇事-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第一档肇事罪与逃逸行为结合构成第二档肇事罪,第二档与导致的死亡结果结合构成第三档肇事罪。三档肇事罪层层累进,构成后一档肇事罪必须以前一档的成立为基础。司法解释排除了入罪逃逸后第二档交通肇事成立的可能,自然也就使得第三档的“逃逸致人死亡”不可能成立。
第二,入罪型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可以用过失致人死亡来评价。特殊的过失致人死亡根据法条的特殊规定与交通肇事罪结合为逃逸致人死亡,而一般的过失致人死亡就不需要纳入到交通肇事罪中考虑,可以单独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并与交通肇事罪基本罪数罪并罚,量刑幅度在3 年以上有期徒刑和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考虑到肇事行为本身较轻,远未达到交通肇事的入罪标准,数罪并罚后的量刑幅度较轻是可以理解的。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回答对“肇事致人轻伤”情况的忧虑:这种观点认为,如果逃逸致死以构成前层次的交通肇事罪为基础,会使得“肇事致人轻伤后,被害人被后车撞死”时,只能以交通肇事的基础刑处罚肇事人。这种担忧是没必要的,因为肇事人引起事故致人轻伤的行为,本身就可以作为先行行为,给予肇事人以救助被害人的义务。肇事人逃跑导致被害人被后车碾压而死,被害人的死亡不是交通肇事导致的,而是交通肇事产生风险后,肇事人的不作为导致的。将死亡结果归因于肇事人的不作为,理应直接构成故意杀人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会构成任何形态的交通肇事罪。解释者需要谨记,交通肇事罪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维护公共安全的诸多法条之一。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包罗万象、解释一切的罪名。遇到交通肇事规定可能语义之外的行为,就应该放弃交通肇事罪、而用其他适宜的罪名涵盖。失去这个观念,就会不自知地陷入“交通肇事万能”的圈套,无限地扩大化、实质化法条的含义,试图将一切涉及交通事故的行为都纳入到交通肇事罪的范围之内。万能论不仅损害罪刑法定原则,更会引起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与混乱,遗害于司法法治、公正司法,损害法律的庄严与正义,必须为法律解释者所警惕。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
(2)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