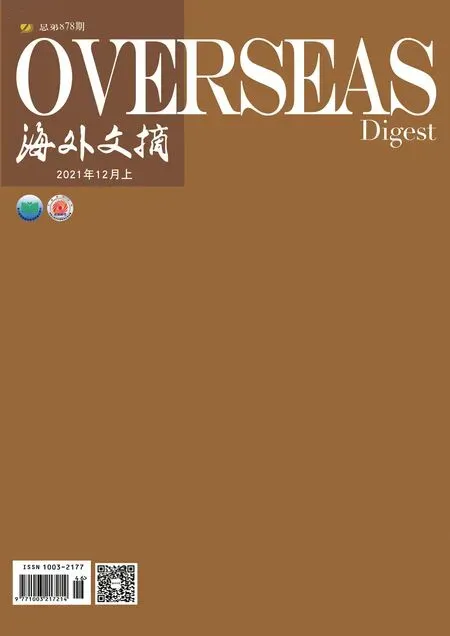道器“法”则之老子哲学
尚泽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道”是老子哲学中最根本的范畴。《易·系辞上》中描述:“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陈大明老师说:“在老子心目中,天下是一个神圣的器物。说它神圣,是因为它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的自然之物。”王爱品老师提出道—母—器的程式,他说:“道为本,显所有能说与所说以及能说之性与所说之性;母为形,为能说之性和所说之性的规则法则;器为型,为能说和所说之用。”简略一下就是:“道”的“无”性,“形”的“有”法,和“器”的“型”象。《易·系辞》又说:“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这里,象器法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上述道—母—器的程式有异取同工之处。然而,在道器法的关系问题上,古今的学者们的看法有:
第一,孔颖达等注疏《易·系辞》“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时说:“变化的结果显现出来就叫做象,变化成为有形之体叫做‘器’,从有形之器物裁制出供人使用的抽象道理叫做‘法’。”面对“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玄曰:“化变刚柔而财(裁)之,故‘谓之变’也。”)推而行之谓之通”时,他这样说:“抽象的超出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叫做‘道’,在形体之下,有具体形体的可见的称做‘器’,道器作用变化而裁制的以致用,就叫做‘变’,顺着变化推广而发挥实行叫做‘通’”。
第二,孔梳:“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
第三,司马迁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透过其微妙的帷幕,揭示其内在的思维逻辑,就成了客观认识老子哲学的必要前提。李言诚老师认为,老子认识自然、社会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发展进程的出发点和根本尺度是三大法则,即对立相生法则、反向原道运动法则和相反相成法则。
以上的3 种看法,表达了古今学者们对道器法三者关系的观点以及对老子哲学法则的理解。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道”,混沌又清晰。天下万物在“道”循环往复的运动中“顺其自然”而生长。老子哲学“道”的思想往往体现在事物发展的状态、运动过程和结果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之“道”也是在一系列特定的法则之中运行着的。那么,本文想谈谈这一系列道器“法”则与老子哲学两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也许,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道”开始。
1“道”的外延与内涵
《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据此可知,“道”的原始意义是指具有一定方向的路,即“道”的外延意。《道德经》开篇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特别提出“常道”的概念,来指称其作为哲学范畴的道。如第一章“常无欲”“常有欲”;第二十七章“常善救人”“常善救物”;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等之中的“常”字,即为“恒常”“永恒”之义。而第十六章“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中的“常”包含“变”的意思,是一种运动变化的过程。再如《文子·道原篇》说:“反者,道之常也。”正是常变统一的观点。为此,“常道”之“道”具有两种意义:一是永恒存在的道;一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的道,也即“道”的内涵意。
《说文解字》:“器,皿也”,“器乃凡器统称”。据此可知,“器”的原始意义是指器具、器物,即一个有口的,盛放东西的物体。《韩非子·十过》说:“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其中之“器”就是用的其原始意义,即外延意义。再如《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器”上升到与“道”相对应的高度。把居于形体之上的精神因素叫做“道”,居于形体以下的物质状态叫做“器”,既指出了“器”的物质属性,更指出了“道”与“器”两者的相互对应、相互依存的关系。在《道德经》中,“器”字确实有常识意义的使用,如第十一章“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第三十一章“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第八十章“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等中之“器”字,即为“器皿、器物”之意。
《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这里,“天地”有名有相,而“混成”因为有相可观,所以“有物混成”有相,但是无名,据此可以知道先于天地而生的是无名有相。那么是“有物混成”生了天地吗?不是。天下生于“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运转天地和有物混成的本质,此本质“可以为天下母”,以“母”喻孕育一切的源泉。此独立与周行无可捉摸,我们是通过天地、有物混成的相,而知运转它的根本,得母法。通过物之相的对比,了解运转物相的本质。正如王爱品老师提出的“道—母—器”的程式。母的实质是以孕育和发端天下万物的“器”的规则与法则,显独立不改和周行不殆的特性,以“器”(天下万物可见的形象和可名的事物)的有名有相,而入无名无相的真空实有。王爱品老师说:“‘道’者,‘字之曰道’却又‘非常道’,说之即落入语言与文字的形与象,以及思维见识之断见中,极不可取,我们只能借老子之言,从俗理和所说与能说的层面,展开对“道”的认识。此外,“道”独立不改。此“不改”为“不易、变易、简易”三易体证与“有无、终始、阴阳、体用、藏相、顺返、生灭、色空、方圆”九易法则作用于任何宏观、微观、盈虚变化的事物,就如九易法则中的阴阳法则主持于宇宙、生命、万物,而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为“道”之能说与所说之性,是独立而不改其常度,是无所不包的终极对待,更是在圣的如如不动。”这正是“道”的形而上的指称,也是“道”独特的内涵意义。
“道”周行不殆,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易·系辞》:“生生之谓易”说明天地阴阳生生不息地转化就叫做变易。易,日月为易,阴阳交替也。王爱品老师说:“在变易中,九易法则主导一切变量之规则,在特定的所指的阶段,某一法则为不变之法则,这个时候的“易”变,就是某一法则在某一阶段所主导,以此法则的不变来“易”变,不用再参考如如不动的自性真如和其他法则如何作用相互关系的复杂,而是直入这一法则规律的简易中。”我们知道《周易》是“大道根源”,究其具体内容则是,易道为万物大道之源。王爱品老师说:“易道,万物大道之源,为九易法则主万物一切变量动态之规则,即不变应万变。此不变非九易法则不变,乃道体自性真如的不变,万变为九易法则主一切变量之“易”变。”《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思想正是以不变应万变,此乃天下万物大道之源。
归纳起来,“道”的哲学范畴意指清静至极的状态,无所不包,如如不动,此乃“不易”。器,除具有器皿、器物的常识义,其哲学意义与“道”的形体之外的精神因素相对应,指一种形体之下的物质状态,此乃“简易”。“道”独立不改的特性与“生生之谓易”的易道,使得“道—母—器”的程式应运而生,此处“母”法即为“变易法则”。
2“道—母—器”程式顺承与返证“道”体
《道德经》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朴。”“道”处在真朴状态,道之本体混沌;第二十八章说:“朴散则为器。”这里,“真朴的道”可以说就是“一”,“器”就是“万物”。据此,“道”与“器”的顺承关系跃然纸上。而《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源。又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里,“道”可以做为天下万物的本原,亦使产生天下万物有“母”法。据此,道—母—器的顺承关系应运而生。在老子哲学中,“无”“有”均指称“道”,是老子表述大化流行所由来时所提出的一对重要概念。第十六章说:“天道圆圆,各复归其根”,第二章说:“有无相生”。这一系列论断,均说明了“无”与“有”相融相合,“无”乃包含“有”之“无”,“有”乃包含“无”之“有”。“无”并不是指绝对的一无所有,而是指《易经》所说的乾坤演变的刚刚开始,宇宙万物尚未形成的混沌无辨的状态。
《道德经》第十四章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里,对混沌的描述,老子将整个过程称之为“恍惚”,实际上是对比“有物混成”来说,“恍惚”更具备马上就要有生万物质变的临界状态。老子对“视”“听”“搏”三个具体世界的型与象给予了内涵延伸,为“夷”“希”“微”,即无色,无声,无形体,此“夷”“希”“微”即是恍惚状态的微在表现,但是仍无法“视”“听”“搏”,从世间人对型与象的著相角度来看,更是可以等同于“复归于无物”,且无型,为“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为“无物之象”。当无法从型与象上去捉摸,老子告诉我们这里面的状态就是“夷”“希”“微”的真空实有的“有物”,即“故混而为一”。“故混而为一”的“一”是在描模“道”,用来形容“道”的特性,在这里,“道”即是“一”,“一”即是“道”。“夷”“希”“微”,“无状之状”和“无物之相象”均是“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似无若有,似有若无的特性。
老子通过对大道本体的直接描述,说明大道似有似无完全不同于实在物的特性,并提出了体验大道的方法,即世间人无法直接通过感官感知“道”,而是通过“夷”“希”“微”“三者”,描模作为宇宙本体与始源的大道超越人类视觉、听觉与触觉的特征。“无”,即“有”之“无”,“有”,即“无”之“有”,“无”与“有”相融相合,揭示了“道”的特性又隐含了天下万物由来的根源。
至此,我们对于道器“法”则在老子哲学中的体现可以做出一个比较明确的表述了:在老子哲学中,“无”和“有”均指称“道”,但是,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广义上讲,“无”乃“有”之“无”,“有”乃“无”之“有”,“道”是有是无、即有即无,不在任一处落脚,却能达任一处。“无”和“有”均指称形而上范畴;狭义上讲,“无”和“有”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以“道—母—器”的程式来说明,则表现为“道”与“器”的顺承关系,“器”指天下万物,“道”为产生天下万物的本原,“母”为“道”产生天下万物遵循的法则。也就是说,在这一关系中,“无”为形而上,“有”为形而下。在具象世界中,人们往往对于形而下的事物更容易理解和把握,老子常常从具体的、简单的事物入手,分析它背后的规律,从规律找到法则,从法则入道体,以“道—母—器”的程式来说明的话,表现为“道”与“器”的“返”的关系,这一“返”的关系亦在“母”法范畴之内,本文中体现为由“视”“听”“搏”到“夷”“希”“微”直至入“道”。这就是老子哲学中道器“法”则的具体表现之一。
本文的基本思想是:“道”作为天下万物的本原,“道—器”这一顺承关系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但以世间型和象的角度来反证“道”,不免有些难度,但是还是可以证得的,而“母”法在证“道”的过程中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道—母—器”这一程式乃“易道”体的显用。除此之外,“易道”抽象于老子之“道”,亦能够解释老子之“道”。如果说老子之“道”为天下万物的存在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那么“易道”之法则则为“道”的认识提供了方法论,进而为老子哲学方法论的探索及其智慧的解读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