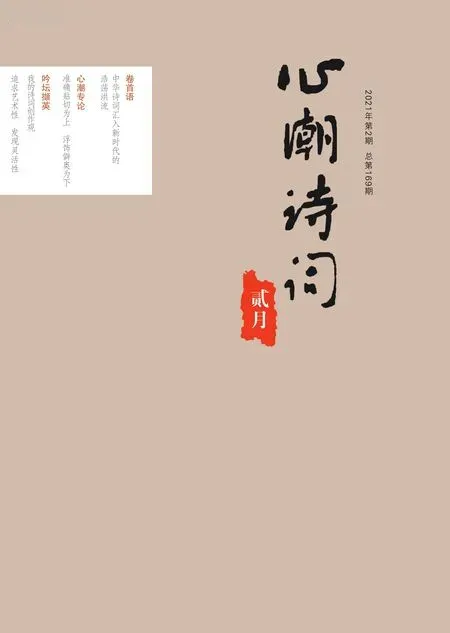回望中的热土
——段维故园诗词探微
李昊宸
回望田园故土,抒发乡居情思,是古今诗词常有之义。如今,旧体诗词蓬勃发展,不少诗人词家致力于开拓田园诗的当代书写,诗人段维即其中一例。近年来,诗人回望英山县,借清辞俊笔,所作佳制颇多。其作胎息古人,含茹田园诗之妙趣,自铸新意,描摹英山田园,绘就一幅回望中的英山故园图景,自名为“故园诗词”。本文即通过综括段维故园诗词,详论诗中独特的设喻手法与语言风格,从而萦前吐后,评估诗人该类作品之优劣,窥探其为当代旧体诗词提供的宝贵写作经验。
一、回望者的姿态——段维故园诗词概览
(一)故园诗与田园诗
段维故园诗词写作,根植于古代田园诗的深厚基础,故本文首先须对田园诗传统进行简要的梳理。“田园”一词与诗首次产生联系,见于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田”“园”二类诗部收录陶渊明诗作,后经唐李白、皎然、白居易以及部分宋代类书之手,陶诗渐有“田园诗”之名,后世类书,将陶诗及唐宋相似诗作,归于田园之流。迨及明清,钟惺、王士禛等诗评家始拈出“田园诗”这一概念以品藻诗艺。
在研究内容上,目前学界以时代整体研究(唐代成果最多)及重要作家个案研究(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成果最多)双线推进为主。近年来,研究热点渐转向先秦、晋朝、宋元、明清时期田园诗研究,对唐代田园诗则进入微观透视,以挖掘田园生活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为主。在研究方法上,由传统的知人论世的单一化研究,逐渐过渡到多种研究方法并举,特别是吸收生态学、心理学知识,关注诗、画等不同艺术门类的关系,甚至是比较中西田园诗差异,可谓形式多样,视域广阔。
21世纪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传统的田园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更新与改变。受城乡发展不均所带来的冲击,早年闲适、淳朴的生活情调,越来越变成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下,催生了一批“新田园诗”,此类诗或是怀缅儿时乡居时光,描摹一幅幅故园剪影,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情思,以曾少立(李子)描写赣南山区的早期试验词作为主;或是捕捉眼下田园生活的一瞬,使作品浸润“耕者的汗水,土地的清香”,从而绘就城市文明夹缝中的田园风情,以蔡世平所致力创作的“南园词”为主。可见,无论是描写昔日,还是醉心当下,回忆性的笔调,精巧别致的语言,时而流露的感伤情绪,都是这些作品的共通之处。在诗人不断的回望中,“田园”的内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移,由最初的清新自然,转为单薄、飘摇却依旧温暖、醇和的“故园”。因此,这种异质文化夹攻下生长出来的“新田园诗”,或称为“故园诗”更为合理。
(二)段维故园诗词概览
湖北省英山县是诗人段维之故乡,该地民彝醇厚,英才辈出,北宋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清代举人萧宏梁、王铁珊,当代作家姜天民、熊召政、刘醒龙,均为一时文士名流,足见英山人杰地灵,洵为文府胜地。同乡熊召政为段维诗集《竹太空心叶自愁》作序曾云:
吾乡于自甘淡泊的境界中,亦有可资夸耀之处,这便是旧体诗词写作的普及。无论勤于稼穑的村夫野老,还是案牍劳形的公门中人,大都以吟诗作赋为乐事。
段维前后居此约有二十余年,耳濡目染,深得乡中民风浸润。且诗人青年时,长期劳动、学习于此,丰富的青春记忆,多年绵亘胸中,使其对故园情思愈发浓郁,为日后自铸韵语、抒发故园之思奠定深厚基础。
纵览段维十余年旧体诗词创作之路,所作故园诗词共八十余首,最早的《故乡纪事八首》见于2009年,此后间有试笔。2017年至今,创作量持续增多,特别是2020年初,因避疫居家,诗人围绕着抗疫、乡居、亲情等主题,创作大量故园诗词,命意、作法俱可谓渐臻圆熟。从内容上而言,段维故园诗词具备现场性与非现场性两种特质,前者淳朴自然,深得田园之乐,正见作者依恋故园之情,并及乡中人物景事;后者则或通过网络遥见,或追忆往事,往往情味俱见,题旨遥深,微见怨讽,体现着作者身上浓郁的文人气质。从体裁上而言,诗人早期所作,均以律诗为主,后偶有长篇宏制(长调、古体等)。2017年后,多作以绝句,捕捉故园景事于瞬息之间。
段诗此类作品所长,在于其精致的语言策略及自成一体的语言风格:一者,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多样化的比喻技法,构象精巧,随物赋形,写幽细之景,成圆足之境;二者,诗人所操持的语言,极度贴近生活,时而糅杂口语、俚语,符合日常语言的节奏、思维以及说话人的身份气质,能够还原语言自然、生动的本来面目,部分诗作兼含暗示、象征意味,言多剀切,寄慨深微。下文拟对此二者作详述。
二、构象精巧,造语独特——英山故园的构建
(一)精巧的譬喻方式
譬喻,是采象构境重要的艺术手段,一个准确、生动的譬喻,往往能令全诗境界全新、耐人涵泳。段诗所构建的喻句,往往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或以最精简的设喻方式,传达最丰富的意旨;或把握本体与喻体间复杂多样的联系,抽丝剥茧,建立本、喻体独特而极具个性化的连接方式。
1.借喻
“借喻”一词,始见于元人范德机《木天禁语》一书,亦有“隐语”“譬况”“暗比”之称。20世纪上半叶,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依形式繁简程度,首次分譬喻修辞格为明喻、隐喻、借喻,以借喻为形式之最简、语义之最深。从明喻到借喻,陈先生认为:
譬喻越进了一级,用做譬喻的客体就越升到了主位。……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
换言之,选取最适宜、最精巧的喻体,令喻体独立构成“自给自足”的喻指系统,藉此传达深刻幽微之义,是借喻之精要。段维故园诗词中,即时常运用借喻,既涤除文字芜杂之累,又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早期作品《故乡纪事·养鸭人》颔联云:“独把月宫肩左右,常将画戟赶东西。”其中“月宫”“画戟”实有所指,作者自注云:
月宫指放鸭人流动住宿的半圆形鸭棚。画戟指放鸭人手持的长竹竿,一头还套有小铁铲,常用来铲土抛向远处以驱赶鸭子或给鸭子喂食。
二者想为乡中常见景致,作者日后忆及,信笔写就的是故乡一幅生动剪影。诗人本意在贴合养鸭人,但“月宫”与“画戟”皆为古典意象,具有强烈的陌生化特质,用二词于此,自然别有一番韵致。“独把月宫肩左右”一句,既点明时间,又深得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之闲适情味;“常将画戟赶东西”则比竹竿为画戟,以画戟之锋锐,而为赶鸭之役,既有大材小用之戏谑意味,又隐约能见赶鸭人之特立威武,宛然有将军之风。二句一气读来,近似聂绀弩“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用大手笔稳摄小境,以郑重语反说细节,诙谐滑稽之中,支撑生计,行走江湖,自有一种苦中作乐的“江湖气”与“阿Q气”。上述数层意思,俱“月宫”“画戟”二喻词透出,诗人以二词说出这许多意味,省却无数笔墨,足见其选词之道,在于以精致准确为尚,务求一击中的。
段诗使用借喻,屡见于近年乡居所作,每每于描摹物态、体悟乡音中,透露出对故园的深深眷恋。《观老父并栽红薯种》云:“就中偶有调皮蛋,脑袋偷偷冲出来。”《观老父为并栽红薯种保暖》云:“一群混蛋谁知晓,安乐窝终非梦乡。”二诗题材相似,比拟方式亦相似,盖以“调皮蛋”“混蛋”喻红薯种,切合其形,亦暗含机趣。杜甫秦州以后诗中,常以“尔”“汝”称呼草、木、虫、鱼以及没有生命的事物,弥见与物共情,段诗此处脱口而呼之,似长辈怜称儿孙,别有一番亲昵之情,较杜诗更为细腻,似不遑多让。
此外,如《上巳节习》有“壳破白云生”,以白云喻溢出之蛋清;《老父开鸡笼》有“一时膝下多争宠,呵斥声中喜上眉”,以绕膝儿孙喻出笼之鸡;《洞仙歌·乡居自我隔离》有“院外小筠溪,独拨青弦,宫商调、千回百转”,以宫商调喻泉流之声……作者诗中诸多精妙的借喻,均作于今年年初,似乎是因居家避疫,作者反而能潜心属文,咀嚼涵咏,锻炼文辞,故而篇中借喻有新意,符合作者乡居时的感受,以最节省的语言,达到了执简驭繁、举重若轻的效果。诗人在借喻中,以精致的语词,传达对故园细微的感受。这种真而不枉、实而不浮的故园诗词,实得益于诗人始终追求打磨“内家功夫”,通过安排语言巧思,在当代同类诗词中,别开精巧一路。
2.喻之多边
钱锺书《管锥编·周易正义》提出比喻的“两柄多边”理论,论“喻之多边”云:
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fi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
钱先生此论,在本体、喻体、喻词三方关系网络之上,别立一说,对本体、喻体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透视与剖析。盖比喻之成立,有赖于本、喻体间特性之相契,方能建立由本体至喻体意脉上的联系,然本体与喻体各有诸多特性,取其一则舍其余,着眼于二者哪点特性,是衡量、检验作者眼界的重要尺度。且古典诗词根基深厚,常见如明月、松竹、秋雁、杨柳等意象,经过无数诗人的使用,其新鲜度已大大折损,如何在譬喻中发掘常见意象的新特点,是横亘在当代诗人词家面前的巨大难题。
段维故园诗词中,多有佳喻,其中即屡见发明喻之多边者。前人诗中提及拐杖者,如“归来倚杖自叹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倚杖听江声”(苏轼《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杖藜扶我过桥东”(志南《绝句》)、“曳杖寄彷徉”(陆游《曳杖》),或倚杖独立,有感于侧身天地之寂寥;或曳杖徐行,见舒徐容与之态,盖皆以杖作为陪衬,绝少专咏拐杖者。段诗不仅专咏拐杖(《题老父用“黄泥杂”依形自制的拐杖》),更自出新意,将拐杖能支撑人躯干的特性发挥至极致,引申出陪伴之意,将之比作母亲,云“训示敲山能震虎,衰颓搀拽似吾娘”,以示老父凄凄酸楚之独身生涯中,每每摩挲此杖,自有些许暖意。在拐杖与母亲二者之间,人为地建立连接关系,可谓巧思毕见。诗人在巧思之外,更以沉郁深婉之情覆之,如此写拐杖,则情思俱见,不会陷入构思纤巧,以至于情味寡淡之弊。与拐杖相反,古诗中写月者则林林总总,有借月抒情叙理者,有专摹月象者,有关月之譬喻更是姿态各异,不可胜计。到了段维《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一诗中,诗人不依傍前人,不作陈词滥调,不作“如洗”“如银”“如轮”“如盘”之比附,而是以“如婴”二字,摹写一潭月色。圆月与婴孩,二者初似绝无关联,然只作此一喻,而婴儿之稚、幼、小,正与月色之新、柔、净、纯,相映成趣,惹人垂爱。结合诗中暮霭横斜、泉声疏荡之景,复有此如婴之月色,诗人所居之境,真幽邃可想,有山村小隐之味。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数峰无语立斜阳”(王禹偁《村行》)、“此山不语看中原”(龚自珍《己亥杂诗·其八十二》)……山有人之情感,于古人作中屡见不鲜。段诗则一反其意,《偕妻回乡避暑》云“白头相守望,如对敬亭山”,以人比山,借敬亭山之肃穆、静默,形夫妻无言相望,似乡居生活中之一帧剪影。无亲昵之语,止如此静默中,见多年相扶相守之情,以无声胜有声,情亲毕见。老杜《羌村》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段诗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彼则悲喜互见,见乱世相逢之不易;此则吐属温雅,见相濡以沫之深衷。
此外,如《齐天乐·推自制小车陪老父打年货感赋》:“满月新丸,残阳老饼,人在其中吞吐。”《夏日桃花溪》:“泉依山绕舌,逗趣似乡音。”《观老父为并栽红薯种保暖》:“破竹弯如父脊梁,撑开地膜挡风霜。”《重九寄故园菊》:“篱边金簇拥,绕膝似儿孙。”诗中所及本体如残阳、泉流、破竹、金菊等,皆已是“诗中常客”,诗人却别出心裁,将其分别喻为“老饼”“乡音”“脊梁”“儿孙”,不仅巧思毕见,且所比喻体无不与故园息息相关,采象设喻之外,复能使读者涵咏之余,喉舌之间浸润乡音乡情。纵览以上多边之喻,本体、喻体本身皆属常见,所见巧思者,乃在二者关系的把握上。且诗中或以亲属为喻,或以乡间事物为喻,这种独特的喻象选择,可见这些故园元素,已了然内化于诗人胸臆之间,信笔写来,渐次流淌,一派纯真绝假之韵味。
(二)独特的语言风格
段维故园诗词不仅擅用譬喻,在喻句的建构上独具巧思,其整体语言风貌同样别具一格,一则通过暗示,拓宽语言的内部张力;二则使用极具生活气息的口语入诗,令全诗别有一番质朴、醇厚之韵味。
1.暗示特性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谓好诗当“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梅圣俞亦谓诗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注重言外之旨,充分挖掘语言的暗示性,是旧体诗词重要的命题,段维此类故园诗词同样继轨前人,注重韵外之旨、味外之味的营造。由于诗人曾任职于高校新闻传播、政治国际关系专业,对时事政策的敏感与其理性、广阔的学科视野高度融合,使得其诗幽默、诙谐、新巧的语言背后,时时隐含着深沉的时政关怀,与国家政策、社会民生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出深广、丰富的语言暗示性。
首先,段诗擅以个性化视角,反映国家、地方政策在英山的实施情况,如“绿苔如叶捧红字,精准扶贫示范园”(《老家见闻》)、“八秩父亲何有幸,脱贫报表曰完成”(《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借助一家一户的微观视角透视,反映在国家建设全面小康,推动脱贫事业的大环境下,乡中生活的发展与改观;《老屋二章》则通过故居的拆迁,从微观角度,透视在乡村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始终伴随着个体的酸辛与无奈。相较于一昧唱颂赞歌,这种独特的写作切口,更能够体现出作者作为一个“小写的人”,在时代洪流中的真切感受。
其次,诗人作有《除夕劈柴感记》《老瓮坛遐思》两首长篇,诗中屡次提到“封资修”“新时代”等政治语词,可见是诗人通过反思六七十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以重构当下生活,借回忆往昔,从而在特定的角度,拓宽时间的延展面。同时,诗中回忆性笔调的渗入,使得个人话语不断穿插于宏大叙事中,从而一方面消解了历史的郑重宏大,另一方面营造出一种冷峻的幽默感。特别是《老瓮》一诗,句式长短错落,气脉纵横,洪峰叠起,从家中老瓮视角,串联起自己的无数个历史剪影,融亲情、家国情、历史评议、个人沉思于一体,数百字间,可作一篇故园小史读。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初(2020年),诗人因居家避疫,写作了大量的故园诗词,其中不少作品即反映了家乡乃至国家的抗疫形势,如“昼里太阳空晒背,圈中微信滥吹竽”(《庚子新正乡村景况》),正讽刺疫情期间,朋友圈、公众号上各类真伪信息的爆炸输出,淆乱群众视听,致使信息不畅,人心不稳;“桃橛驱邪红未发,山岚挽幛白权宜”(《诗兄八卦掌付疫中寄诗勉慰,步其韵答之》),借写“桃橛”“山岚”,既说明抗疫形势严峻,更深为受难者哀恸下泪,深见民胞物与之情怀;小令《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谓“截断城乡通道,隔离疑似车尘。若有红缨枪在手,敌后盘查形逼真。村村尽可军”,着眼于前期乡中严控疫情、排查患者,以类军事化的语言,渲染乡中紧张的抗疫形势,正见隐忧时局之心。
所谓“语非惟创始之为难,乃中的之为工也”,能令常语饱含暗示、象征意味,当以创意为先,不求作浮藻之饰,务求有中的之语。当今旧体诗词创作量与日俱增,牵连时事,聚焦社会之作不在少数,然泥沙俱下,作古人陈腐语者多,情辞空泛者多,以称颂为美者亦多,绝少自具面目者。段诗此类故园诗词,无论是借写乡间景事以怀缅旧时,还是因小见大,管窥时政国事,包括最新的着眼疫情百态之作,不以用事为博,不以虚美为务,始终注意延伸语言的内部空间,以简约、含蓄为胜,含而不露,自得谐趣,暗含机锋,使读者获得多重阅读体验。
2.自然质感
自民国以来,传统的诗词语言受到白话、俗语的极大冲击,胡适为白话文学编史,钱锺书专论“俗语出诗句”,归根结底,乃是为了剔除古奥、陈腐的语言范式,凸显其自然质感,还语言以“本来面目”。这里提到的“自然”,并非描写大自然,而是指体现语言真实的、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即还原其“自己如此”的本真状态,不作过度的人为矫饰,田园诗之祖陶渊明诗中即有此特质。段维的大多数故园诗词立足于描摹故园风物、乡民生活,从内容上来讲,与传统田园诗差别不大,惟多以俚语、方言入诗,脱口而出,不假藻饰,符合乡人的口吻与身份,较古人更为贴近生活,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语言的自然质感,可谓是对陶诗的效仿与致敬,是对田园诗传统的反刍与重新确认,戴建业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中对陶诗语言的自然质感曾有详细论述,此处可引为注解:
“自然”就是不刻意地拼凑獭祭,随手拈来、脱口而出,来自天然的“直与”而非人为的“强得”;……是泯灭了任何针线痕迹,给人的感受就像花开花落那样自然而然;……是指句法、节奏接近于日常口语,没有人为地颠倒正常语序,结句清通而又顺畅。
从语言内容上讲,段诗的故园诗词是充满烟火气的写作,诗中绝不故作高深,专务生字、僻典,而是大量使用现代语词,增强生活气息,拉近与读者距离。诸如“霸座”“兜售”“家 长 里 短”“电 风 扇”“中 暑”“小 哥”“跑火车”“萌萌犬”等,这些源自生活的口语化词汇,用近聊天的语气娓娓道来,不仅通俗晓畅,且画面感极强。此外,段诗时而夹杂一些近乎俚语、方言的语辞,更加凸显语言的自然质感。《双调南歌子·儿时》云:“唇濡红纸代胭脂,多怎桃花散我白鹑衣?”以“多怎”表示“何时”之意,纯是俚趣之笔,是乡中小儿口吻,与追忆儿时的主题十分贴合;《偕妻回乡避暑戏题》:“啰苏两不厌,都当听评书。”《老石磙感忆》:“咿呀磙框语,哼唧自家腔。”二诗所用“啰苏”“哼唧”,近乎纯粹的口语词汇,消解了书面语严肃、整饬的特性。
从语言节奏上讲,诗人打破了古诗传统五言诗“2—3”、七言诗“2-2-3”的节奏链,以符合日常口吻的断句方式,形成疏散自然的语言节奏,读来明快如话的是乡人声口。“狗打滚和猫闪扑,看如小伙伴回归”(《题老家门前水泥地中间小草坪》)完全打碎了传统的节奏型,以“3-1-3”和“2-3-2”的节奏对诗句予以重组,极为符合日常闲谈、说话的自然语言节奏。诗人《窖酒歌》云:“某某和某某,对对又双双。言罢微鼾起,皱褶了月光。”在诗句中直接使用“和”“了”这类语助词,且不避甚至有意的语意重复,质朴而别具韵味,真如对酒小酌后,信然赋作;《种豆歌》开篇云:“陶令种豆南山下,父亲种豆小院中。”显是有意对照靖节《归园田居》而作,然较陶诗而言,更见语言的弹性与活力,诗中“沙土虽干犹松软,遇少许水板作铁”“怪底前者草盛豆苗稀,后者勃勃惟见豆苗丰”等句,随意而断,节奏多样,最大限度地保持了乡村语言的自由度与自然感。
朱光潜在《诗论》中专论古文与白话一节,认为,作诗文应当用“活的语言”,主张使用流行语言,不专事佶屈聱牙,所谓:
现代人有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特殊情思,现代语言是和这种生活方式和情思密切相关的,所以在承认古文仍可用时,我们主张做诗文仍用流行语言为亲切。
段维故园诗词即如朱先生所言,在以古文为基的前提下,通过大量的实践,将日常语言打碎、重组,熔铸为自然诙谐的语言体系,从而部分解放了旧体诗词中语言的桎梏,使其既符合故园人、故园景,也令读者乍读之下,倍觉亲切、新鲜,是其最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类诗。
三、自然的尺度——段维故园诗词评估
(一)去模式化的立场
当下旧体诗词写作持续蓬勃高涨,旧诗创作群体与数量逐年扩大,特别是在互联网的推动下,不仅人们日常诗歌阅读的习惯被改变,旧体诗词创作更呈现出井喷之势。然而,庞大的创作量,只能说明诗词的普及,并不能反映艺术水平的成熟。恰恰相反,当代旧体诗词质量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真正能够比肩古人之佳作仍是少数,大多以陈词滥调自名,空泛的议论、抒情,使得诗词深陷古人窠臼。田园诗作为中国诗歌传统,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当代田园诗词,有着非常深厚的发展基础,经过长年累月地积淀,该类题材写作具有独特的意象群、成熟的写作范式以及广大的读者受众群体。然而,这种过度成熟,使得部分当代田园诗词,经常表现出一种模式化的创作“套路”:一方面,溪水、鸣蝉、榆柳等经典田园意象,不分节令地出现在诗中;农妇养蚕、耕夫劳作、老少自得其乐,模式化的桃源语境,恰恰消解了桃源的深广内涵;闲适、忘情、身远尘嚣,常见于古人诗中的情感基型,经反复重提后,渐渐失去了动人心弦的力量。另一方面,叙写新生事物、图解时代政策,也是今人易犯的毛病。比如,古代没有现代耕作机械,没有发达的交通运输工具,没有便捷的通讯设施等等,部分当代诗作中,试图将这些新的生活元素揉进诗里,以打造所谓的“新式”田园诗,却破坏了田园诗本来恬淡清新的气息,这是当下部分田园诗日趋“老干化”的症结所在……总而言之,田园诗固然可写,但如何使已趋近饱和的田园风情重焕活力,是对当代诗人词家的一次重要检验。
段维一贯主张作诗要有“增量”,而形成“增量”的基础,即是在熟稔于诗词传统后,对模式化写作“套路”的祛魅与超越。段维故园诗词就内容而言,以书写故园所见所闻者居多,如写故园池塘、愿景、庭院,专题乡中菊花、园葱、红薯、豌豆、油菜花等农作物,虽较传统田园题材更为细致,但大体来说,与古人同类之作区别不大。所异者,乃在诗人站在回望者的立场,回溯故园经历,重忆故园景事,却能以情理度之,擅于对乡中素材加以整合、重构,运用独特的譬喻手法和别具一格的语言策略,有节制地表达,做到“言人人心中所有,道人人笔下所无”,进而重新建构作品中的英山故园。
具体来说,在技巧层面,段诗呈现出精致、新颖的特点,或采取借喻,或发掘喻之多边属性,使得许多譬喻往往别具匠心,能令读者瞬间领会其意,反复咀嚼之下,更是极耐涵咏。在语言风格层面,段诗的语言贴近生活本来面目,自然、活泼、清新,保留了田园诗“真”的宗旨,即使读者并非英山本地人氏,也能通过诗中所描绘的某一帧画面,在各自故园中,找到相似的时光剪影,最大限度地消弭了作者与读者间不必要的语言壁垒,实现“共情”效果。当然,这种“共情”是建立在描绘故园独特景象基础上的共情,而非单纯复刻古人诗胚,表达千人一面的“泛情”。
(二)回归自然的尺度
按前文所述,段维故园诗词着意突出语言的自然原貌,以大量日常语词入诗,并以语言的自然节奏打破了古诗的惯有节奏链,总体来说,可谓是一次具有示范意义的试验。然既曰“试验”,则成功者可供人取法,粗疏者亦自当引以为戒。段诗部分作品引入生活用语,虽旨在还原生活的本真,然细加品藻,则稍嫌无味,仅为了凸显语言的生活化,缺少诗词的含蓄蕴藉之美,似乎是为用而用。如“嗓子比锣还要破,叫应家家深闭门”(《破阵子·乡村严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鸟雀亲人,未觉周遭有危难”(《洞仙歌·乡居自我隔离》)“闭门陪父度元宵,满嘴火车听我跑”(《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六》)等,虽有新词新语入诗,乍读之下,确能见作者用语巧思,能使人会心一笑,但似乎缺少真正值得咀嚼之韵味,难以令人唇齿留香,频频回味。这类直白而缺少加工的语言,在诗人今年作品中出现比例较高,是其凸显语言自然的同时,疏忽语言加工而暴露的微瑕之处,当为之一警。
当代致力于旧体诗词语言试验者不少,其中不少诗人已卓然自成体系,别具一格,段维即其一耳。其故园诗词中偶有语句稍嫌随意直白,须注意“语言回归自然”的尺度,在凸显语言试验性的同时,进一步注重语言纯度的打磨。不过,对作者的评价,既要立足微观的作品个案,更要从宏观着眼,纵览当代诗词的发展轨迹,从而对其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故总体而言,段维此类故园诗词虽有微瑕,但瑕不掩瑜,整体精致、独特的语言策略已足以示范当代作手,为此类诗词别开生面。
总述前文,段维近年所创作的故园诗词,以回望者的视角、精致的语言策略,勾勒、描摹其故乡英山县,其中对譬喻修辞格的使用以及自然、新颖的语言风格,体现了诗人驾轻就熟、举重若轻的语言能力。这种新巧的作品,虽仍有疵病,时而伤于直露,但在当代良莠不齐的旧体诗词创作环境中,不仅是在形式上对传统田园诗予以更新,更是对淳朴、自然、天真的田园精神的呼唤,可谓别有创意,足为当下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写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