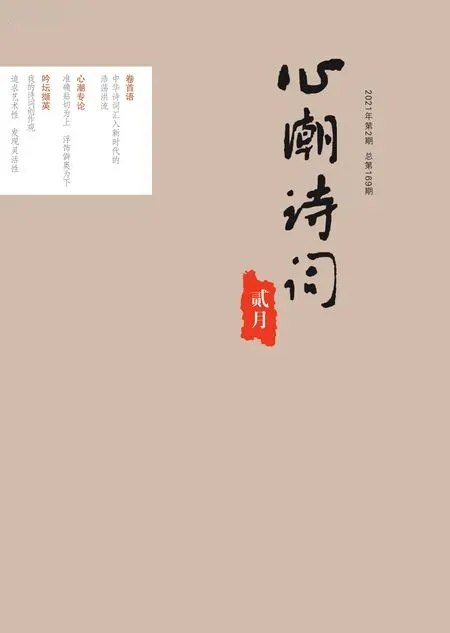准确贴切为上 浮饰僻奥为下
——诗词修改的“三条心法”和“一点灵光”
高 昌
古人说过:“改诗难于作诗,何也?作诗,兴会所至,容易成篇;改诗,则兴会已过,大局已定,有一二字于心不安,千力万气,求易不得,竟有隔一两月,于无意中得之者。”正所谓“富于万篇,窘于一字”“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诗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则心浮;多改,则情窒。
清代诗人方扶南三改《周瑜墓》诗的故事,就是“愈改愈谬”的例子。方扶南年轻时说:“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这样写晓畅沉郁,挺有味道的。可是方扶南自己不满意,到了中年时把这两句改为:“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这里加了一些修饰,绿红对比也鲜明了些,只是比原稿少了些气魄和思想分量。方扶南自己还不满意,到了晚年又改为:“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这样改到最后一稿,雅则雅矣,却“真乃不成文理”了。据说方扶南的同族兄弟方敏恪苦劝他不改少作,但是方扶南坚决不听。诗人袁枚谈到方扶南这样修改诗歌时,感叹说:“方知存几句好诗,亦须福分!”方扶南对《周瑜墓》诗的这三次修改,留下的是一个悲惨的教训。
秦代吕不韦曾经把《吕氏春秋》书稿挂在咸阳的城门上,“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也就是谁能够在上面修改一个字,就赏赐千金。这是文化自信,也是一种高明的广告艺术。宋王禹偁在《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郎》中,写了几句很爽的句子:“醉挥拔萃判,一字不复改。传写遍都下,纸贵无可买。”这里的“一字不复改”五个字,多么牛气啊。沈德潜说:“诗到真处,一字不可易。”情到真处,确实是一字不可改变的。今人诗词作者中也不乏自称“一字不易”的人物,这就要拿出文本认真掂一掂分量了——前提是做到果真文从字顺、精准恰切。而倘或没有足够斤两的文本支持,所谓“一字不易”的自信,就不过是笑话而已。
律诗的修改,大致有以下五个步骤:
第一步要检查格律。调换部分不合平仄的字词。
第二步要检查对仗。是否失对?是否工稳?是否有合掌?
第三步要检查重字。有不必要的重字要调换一下。
第四步要检查词汇。是否有不合适的?太直白的,太粗俗的,太生涩的……可以进行调整。
第五步要检查整体效果。多吟诵几遍,看看是否还有更好的词句。对于一些不合适的生硬字词,古人还有一种换字和代字的方法可以进行矫治。
词的修改也大致分为以下这么几个步骤:
第一步,对照词谱检查格律。一首新作写出来之后,先对照词谱检查一下格律,修正调整不合格律的地方。力求使自己的作品符合这一词牌的音乐和形制特征。
第二步,对照例词检查句式。对于词调的情感特色和字句、对仗等词体的特殊要求做到合体符情。
第三步,检查文字是否准确。词人总要用最合适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要有本事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字眼。我们来看李白的《菩萨蛮》的下阕:“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作者为什么在这里选择了“空”字这样一个看似平常的字来表情达意?用“长”好不好?用“惊”字好不好?用“方”字好不好?用“闲”字好不好?从格律上来说,这几个字都还符合要求,语义上也大致说得过去,但都不如“空”字更符合特定的语言环境。“空”在这里既有“白白地”的意思,也有“长久”的意思,还有孤独惆怅和失望的意思,比其他的字的内涵更加丰富和准确。
第四步,检查文字是否风雅。诗词分疆,词的味道和诗的味道是有区别的。古人提出作词要协音、字雅、字隐、意柔的主张,其实也就是强调词要打扮得更漂亮一点。
关于诗词修改,除了以上一些常识性的操作之外,我认为还有“三条心法”和“一点灵光”,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第一条心法是:“不能失真。”前些时,我有机缘读到叶圣陶先生20世纪70年代与其子叶至善之间的几封书信。我们来看叶先生对一首词的具体修改过程。
1972年2月15日下午,叶圣陶先生为几张孙儿叶永和的照片题写了一首《醉太平》:“菊科野花,缀枝雪花,何输烂漫春花?赛桃花李花。 古人插花,今人佩花,永和别样怜花,竟藏身入花。”这首词采用别致的独木桥体,“花”字一韵到底,空灵活泼,生趣盎然,温暖亲切。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代语境下,能呈现如许细腻温馨的情怀,真是令人称道。叶圣陶先生随后把这首词寄给了在河南潢川黄湖团中央“五七”干校劳动的叶至善。叶至善先生随即回信提了意见:“第一句:‘菊科野花’,这种花四周的唇形花冠为紫色,中间管状花冠为黄色,名叫‘紫菀’,根可入药。在诗词中,不知可以简称为‘菀花’否?如果简称为‘菀花’,可否把这一句改一下,最好能表示地点是陕北,如用‘原’‘梁’‘沟’等字眼作这一句的第二个字,第一个字用个适当的动词。”的确,“菊科野花”直接借用植物学名词,一方面失对,另一方面也缺少典雅风韵。叶至善先生委婉提出的修改建议,确实慧眼独具。叶圣陶先生接着在2月23日回信说:“来信中提及小词的第一句,我知道你辨出一二两句不对称,所以要我改。……若确是‘紫菀’,第一句不妨改为‘连坡菀花’,与第二句对称。若确是菊科花,那就把第二句改为‘琼枝雪花’也对称了。你看如何?”
3月2日,叶圣陶先生又致信叶至善:“今天翻看了《辞海》,紫菀有一条,现在抄给你看看。你说的完全对,那照片里一定是紫菀了。紫菀,菊科。多年生草本。须根多数簇生。基生叶丛出,大形,长椭圆状,秋季开花时脱落。茎生叶互生,较狭小,上部叶线形。头状花序密集生于茎顶,边缘舌状花蓝紫色;中央管状花黄色。……中医学上以根入药,性温味苦,功用温肺下气,化痰止咳,主治咳嗽气喘等症。”经过这样严谨的考证之后,“菊科野花”最后定稿为“连坡菀花”,就像一位乡野粗汉瞬间变成了花间玉人,修改之功,善莫大焉。原来的“菊科野花”有点“直拔直”的感觉,修改之后的“连坡菀花”形象鲜明,对仗工稳,冲而不薄,淡而有味,感染力也更强了。诗词的修改,一定要记得删掉那些概念化的、生硬的词汇,也要避免人们用熟用滥了的腔调,调换上有温度的、有形象美的新鲜典雅的语言。
通过“连坡菀花”这样的修改例证,我们可以想见叶圣陶先生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叶家良好的家风。父子俩像在一起饮酒聊天似的通过书信探讨诗词创作,平等交流互相探讨,娓娓道来无拘无束,在一段难得的诗坛佳话中也给我们在诗词修改的“不能失真”心法做了一个形象的“实场演示”。
我国古代诗人对待创作,常常刻苦铸字炼句,反复琢磨修改,苦吟不辍。诗坛上流行不少关于苦吟的故事,比如杜荀鹤说“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卢延让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贾岛说“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诗人这种艰辛的艺术劳动和追求严谨的创作态度值得尊重,但是苦则苦矣,也要注意两点,一个是不能造假,一个是不能失真。有意造假实为欺世,无心失真则为枉情。比如贾岛“推敲”故事中的“僧推(敲)月下门”,究竟用“敲”字还是用“推”字?据说最后在大文学家韩愈的参与下才定为“敲”字,说是敲字更响亮。这个故事非常著名,不过我觉得惊异的是,古往今来,人们都没有提到过诗的题目《题李凝别居》,没有考虑过题李凝别居这个具体题目所规定的实际语言环境。“敲”字和“推”字的事实基础是有很大区别的,李凝别居晚上插不插门栓?锁不锁门?如果插上了门栓,锁上了门,就用敲字,如果不插门栓,没有锁门,就用推字。这才是取舍的故实关键。题目既然用的真名实姓和真实地址,就证明不是虚构的。这就要以真实语境为基准。我们虽然无法上溯追寻,而贾岛自己应该非常清楚取舍。僧推还是敲,不能脱离事实依据。否则,就是故弄玄虚了。
第二条心法是:“要能增美。”古往今来,诗人们在诗词修改方面下了很多功夫,这也是写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房子盖好,总要装修之后才能入住。我们来看姜夔的“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里的“吹”用得多么美妙,仿佛阵阵寒意从角声中透了出来。再请看苏轼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一个“挂”字,一个“断”字,前者把静景写出了动感,后者把平静写出了尖锐。再请看周邦彦的“风老莺雏,雨肥梅子”,把“老”和“肥”这两个形容词变成动词来用,既添加了灵动的韵律,又突出了意象的质感。再请看辛弃疾的《临江仙·探梅》:“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全有雪精神。
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着句清新。竹根流水带溪云。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这首词里的“态度”“精神”和“破”字、“剩”字、“带”字的韵味和魅力,值得细细体味。前两个名词不动声色地把花和雪全部拟人化了,后三个动词营造出一种奇特的流动美,突出了探梅人的愉悦惊喜,也渲染出以动衬静的丰赡绵邈的独特风致,让平凡的山间景色有了不平凡的灵气和情感。
据周笃文老师回忆,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曾就“鬼灯一线,露出□□面”让大家填空。“□□”填哪两个字呢?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狰狞面”的,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血盆面”的,有的学生说“鬼灯一线,露出獠牙面”的。然而最后夏先生提供的答案却是“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桃花二字虽美,用在这里却举重若轻,更铺垫和反衬了惊悚的感觉,而且增加了想象的余地。
所谓“增美”,就是根据内容和意境的需要,对于诗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部分精心推敲锤炼,并进行创造性的搭配,挑选其中最合适、最生动形象的字词来抒情达意,从而获得简练精美、形象生动、含蓄深刻的表达效果,使全句或全诗准确鲜活,凝练优美,新颖灵动,神采飞扬,熠熠生辉。比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生”字的美妙,常常误写作“升”字。“升”字如果用在这里,仅仅是一个现象的描述。而诗人精心锤炼的“生”字,则是生长的意思,诗人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了明月与大海相伴相生的壮丽图景,使明月和大海似乎也都有了美丽的生命。再比如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悦”字就用得非常好。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是用拟人的手法,写的是鸟的喜悦,但是从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反映了人的喜悦心情,这就使诗歌的意蕴更加丰盈了。李白的几首诗中,对“挂”这个动词用的就非常美妙,比如“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读者朋友不妨仔细对照体味。
为了“增美”,可以用经过锤炼的动词来为全诗增色。可有时候把动词“炼”没了,竟然也能增加奇妙的表达效果。最著名的就是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仅仅是罗列了几个名词,根本不用一个动词,却比用动词更加生动和鲜明,意境清新,情趣宛然,格韵轻灵。这其实也是一种“炼”字的方式。
诗词的修改,或曰炼字,或曰推敲,除了注重检查格律、句式等等技术性的因素和优美生动等辞藻性效果,首要的是使文字表达得更鲜明、准确,要用最合适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要有本事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字眼。
第三条心法是:“不能过力。”钱锺书先生曾经说过:“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令人欣赏的作品常常是淡而有味,文从字顺,简洁明了,最后才是文笔才情。炼字重在更好的达意表情,主要的还是贴切和自然为上,并不是越奇险越雕琢就越佳妙,不能过分用力。
叶嘉莹先生曾经在学生们中间做过一个小测试。她问道:“先来看这句诗:‘鱼跃练川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再来看另一句:‘群鸡正乱叫。’你说哪首是好诗,哪首是坏诗?”
“鱼跃练江抛玉尺,莺穿柳丝织金梭”的作者是晚唐一位不知名的诗人,诗的意思是说银鱼儿在白绸缎一样的江面上跃动,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抛掷的玉尺。黄莺儿在金色丝线一样的柳条中飞翔,就像织布的金梭在穿来穿去。这两句诗对仗工稳,色泽艳丽,意境优美,很多人会选这两句。“群鸡正乱叫”的作者是著名诗人杜甫。这句诗是个大白话,初看起来平平无奇,如果不提杜甫的名字,单独提出来与前面那两句比较,很多人会认为差了不少成色。
但实际上,“鱼跃练江抛玉尺,莺穿柳丝织金梭”没有什么情感寄托,工于雕琢,失于真切自然。就像精心打扮的塑料娃娃,最缺少的就是活气儿。“群鸡正乱叫”是安史之乱后饱经离乱的真实场景描绘,真切表达了凄凉和惊惧等复杂心境下的情境,用语虽然朴拙,高明在于具体和鲜活。
“莺穿柳丝织金梭”诗句中的莺和柳,虽然刻意求工,却反而有点死气沉沉。其实并非玉尺、金梭、柳丝之类“诗词类书”中常见的现成的词句不可用,而是不能像搭积木一样堆砌和展览这些所谓的“好词好句”。请看唐代诗人施肩吾的诗句:“万条金线带春烟,深染青丝不直钱。又免生当离别地,宫鸦啼处禁门前。”作者也用了金线、青丝、春烟之类的大俗词,但都不是机械的套用,而是渗透了人生的苍凉和感慨,其中有体温,有岁月,以俗化雅,死词复生,点铁成金,给读者留下了很多回味和联想。
前面我讲过,清代诗人方扶南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周瑜墓》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到了中年的时候,他又把这两句诗改为“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到了晚年,他再次改为:“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对比三次花了大力气的改动,我们就会发现,这两句诗逐渐由清淡到浓艳,由精警到滥俗,由明白到朦胧,由天趣到人工,也终于由鲜活到死板了。诗句首先是表达内心的生活触动和思想感悟,不宜刻意追求人为雅化。方扶南这两句诗的修改,可以作为雅化失败的例证。
叶至善先生在当年寄给叶圣陶先生的信中曾经批评过张先的“云破月来花弄影”。他说:“七个字中三个主词,挤得够呛,与所表现的那种悠闲的心情也不相符。‘太直’就是直拔直,没有联想、比喻等”,“读起来有迫促的感觉,这与声调大有关系,‘破’‘来’‘弄’这三个动词,都是仄声,好像赶什么似的,来煞勿及。”叶圣陶先生回信中也表示了批评意见:“我现在随便想,这一句做作,不自然,‘破’字硬用,‘来’字勉强,而‘弄影’也有做作的毛病。说简单些,这一句不能一下子给人一个活泼鲜明的印象。”“我看‘云破月来花弄影’之毛病还在不自然,不真切。说云‘破’,似新鲜而生硬。说月‘来’,也比月‘现’月‘露’勉强(当然,‘现’与‘露’都是仄声,不合用)。说‘花弄影’,有趣,但是太纤巧。”我很赞同叶圣陶先生和叶至善先生的观点。“破”“弄”“来”不过就是几个修辞上的小特技,但是妨害到的则是作品表达上的准确和自然。“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这样风格下的“破”“弄”“来”之类的局部雕琢,影响了作品整体的洒脱和顺畅。
南宋《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曾经写道:“先君尝言,坡词‘低绮户’当云‘窥绮户’,一字既改,其词愈佳。”意思是说他的父亲认为苏轼的《水调歌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中的“低”字应该改为“窥”字。但是一字之改,把单纯的月亮变成了一个“偷窥犯”,完全曲解了作者的感情脉络,不知道“佳”在何处?词中已经有了“转”和“照”两个动词,换一个低字这样的形容词作动词用,把月亮的行踪交代得清晰明白,也使文字更多了一份波澜,有什么不好?另外,如果改成“窥”字,那么就和下文的“照”字产生了语义冲突,反而前后错乱,不知所云了。
贾岛还有一首《宿山寺》:“众岫耸寒色,精庐向此分。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绝顶人来少,高松鹤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闻。”我喜欢后半部分,对前半部分却比较淡漠。耸字、精字、透字、逆字,都过于雕琢了。由红尘起,反而冲淡了那种超脱凡俗的清雅散淡。就像经过整容手术,总不如一张天然纯朴的脸庞更加真实生动。
鲁迅讽刺崇儒师古、缺乏创新的腐朽文风时说:“于修辞,也有一点秘诀:一要蒙胧,二要难懂。那方法,是:缩短句子,多用难字”“夹些僻字,加上蒙胧或难懂,来施展那变戏法的障眼的手巾的。”鲁迅强调写文章要“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这十二个字对于诗词写作,其实也是一些基本的要求。
三条“心法”之外的“一点灵光”是:“点破节奏。”诗词修改,我认为最后还是要追求给读者留下一些深刻印象,实现这一目的也是需要一点灵光的。这里的所谓一点灵光,指修改过程中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点破节奏,打破惯性思维。
比如好多人在台上表演集体舞之类群体性的节目,如果整齐划一,观众不会注意到其中的某一个个人。但是如果有个人掉了道具、甩了跟斗、错了步伐,反而观众会立刻注意上他。这就是打乱了别人的节奏,把观众直接带入了自己的节奏,引起大家的关注。这就是一种传播学上的技巧效应。
一般作者作诗,不懂得这种控制节奏的技巧,一味地平平仄仄、也就只能是一直地平平淡淡。我读到过周信芳演《清风亭》的一个故事。
周信芳先生在这部剧中有个精彩的“摔僵尸”,他在表演时就非常注意控制节奏。当时别的演员正在剧烈的戏剧冲突中,他的表演要立刻引起观众注意,把观众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其实是很难得。他使用三个很普通的、有合乎人物性格和生活规律的动作来打破原有的戏剧节奏、步骤来完成这次表演的。一,先把手拉开,把观众的目光聚拢过来。二,把手中的拐杖丢掉,这样让观众心弦一震,继续跟从自己的表演节奏。三才是摔僵尸的精彩表演。每到此时,剧场必定是一片掌声。
有的演员很卖力气,拼命表演,甚至完全发自内心,让观众看他面部怎么痛苦,与孩子的交流怎么动人,眼泪鼻涕都来,还能看到他的身体和语言的配合等等,但给得越多,观众的注意力越分散。这说明表演在于懂得节奏、玩弄节奏来控制全场,而不是用做戏吸引观众。
诗歌修改也是这样道理。一些诗人结伴采风。面对同一题材,怎样写出自己的感受,又要让读者觉得和别人有不一样的东西?佛教临济宗有偈语说:“青天轰霹雳,陆地起波涛”,作诗其实也需要有这种“脱罗笼,出窠臼”“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卷舒擒纵,杀活自在”的勇气和追求。
改诗的灵光,就要点破原来的节奏,寻找既平顺又精彩的奇句奇字。不能仅仅满足于四平八稳,字正腔圆,还是要在模式化的抑扬顿挫中,展现个性化的风格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宋朝有位名叫王仲的人在应试之后写了一首诗:“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王安石读到这首诗,把第三句作了以下修改:“日斜奏赋长杨罢。”他说:“诗家语,如此才健。”他在这里运用字序颠倒的技巧,增加了诗句的陌生感和思考空间。诗家语其实就是经过诗人锤炼、加工、删削之后提纯出来的语言,经过转义、变性、省略、错位、夸张、通感、双关、互文、反讽等等诸般手段,打破原有的语法规则和惯性的思维逻辑,变幻出一套充满陌生感的语言密码,反常而合道,而且更加准确、生动、活泼、深沉,更加富有艺术冲击力。
清代诗人袁枚曾经引用过当时的名医薛雪的两个诗例。《嘲陶令》云:“又向门前栽五柳,风来依旧折腰枝。”《咏汉高》云:“恰笑手提三尺剑,斩蛇容易割鸡难。”别人赞赏自号五柳先生的陶渊明不肯折腰的气节,薛雪却嘲讽陶渊明寄托理想的五柳本身却惯于在风中折腰。别人赞赏汉高祖斩蛇起义的英武,薛雪却嘲讽他斗不过吕雉。这都是打破既有思维定式,从惯性思维中跳出来之后获得的佳句。
牡丹花被称为国色天香,历来受人赞叹。唐代诗人皮日休在诗中写道:“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这首诗极力抒写牡丹的王者之风,确实是群芳失色,力道十足。但这还只是正面描写,略有些直白。白居易说“惆怅阶前红牡丹,晚来唯有两枝残。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这种侧面描写,就显得更有韵味了。宋代王溥则对牡丹之艳丽不屑一顾,反其意而咏:“枣花似小能成实,桑叶虽粗解作丝。唯有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他通过枣花和桑叶来与牡丹对比,表达了自己摒弃浮华、崇尚务实的理念。这其实也是跳出固定模式,另起炉灶、重带节奏的一个成功例证。
诗词修改的这“一点灵光”,就是点破节奏。这种点破节奏,也就是敢于从群体舞的集体画面中“跳出来”,这种跳出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开拓一条新路,引领读者到自己的节奏里来。另一种是打乱自己的固有规律,让读者在惊异中重新改变注意力的方向。这种灵光在诗词构思和写作时也需要提前留意,当然在诗词作品修改过程中更需要注意和强化。
诗词修改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老话题。以上“三条心法”和“一点灵光”,是我个人的一些初步的思考和感受,愿和诗友们进一步切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