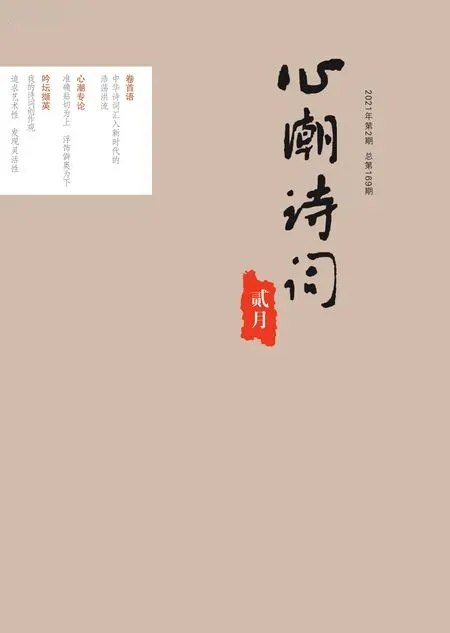传统诗学命题漫议
王国钦
(河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这不仅表现在浩若星海的诗歌(词)创作,而且表现在传承有序的诗学理论“命题”等方面。“诗言志”最早见于文字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尚书·尧典》)其后,又有“诗以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诗以道志”(《庄子·天下篇》)、“献诗陈志”、“教诗明志”等理论的陆续出现,更使得“诗言志”的命题影响至今。
东汉文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鉴于汉乐府创作而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的观点,应该是与此比较接近的另外一种说法。
西晋著名文论家陆机的《文赋》,是我国最早、最系统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赋体论著,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命题”。陆 机 对 当时“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十种文体进行了分别论述,而今来看,只有“诗”“赋”“颂”等文体的生命力最为顽强。
“诗缘政”的“命题”,源于唐代孔颖达等人对《诗经》的研究性著作《毛诗正义》:“风雅之诗,缘政而作。政既不同,诗亦异体。”由此可见,他在理论上是将《诗经》作品都看作“缘政而作”的。
在笔者看来,以上几个“命题”之间最主要的联系,就是以“诗”为原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命题。具体到当今诗词创作,笔者自己的感悟是:
其一,根据笔者《“诗言志”之言在“当下”》一文分析,“诗言志”作为最简单也最经典的主、谓、宾句式,其完整意义可理解为:“诗”(主语)是作者“表述”(谓语)个人“情志”(宾语)的一种文学作品。“诗”,必然是其中的主体、重心。
其 二,“诗 缘 事”“诗 缘情”“诗 缘政”三个“命题”,都属于被动句式,即“诗缘之于……”。若分别理解就是:
(一)“诗歌”因为“事物”而生发,不同的“事物”产生了在内容上“哀乐”不同的诗歌作品——言“生发”所至之格调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作者所表达出的一种高尚情怀,与此并非一样。
(二)“诗歌”因为“情感”而绮靡,不同的“情感”产生了艳丽、浮艳、柔弱等风格不同的诗歌作品——言“情感”所至之风格也。而“绮靡”,也仅仅是诗歌众多风格之一也。
(三)“诗歌”是因为“时政”而述作,不同的“时政”产生了在体式上各不不同的诗歌作品——言“时政”所至之体式也。诗歌体式因“时政”而生?介于是与不是之间也。
由此得知,只有“诗言志”才是真正简洁、准确、经典的传统诗学“真命题”。其余的“诗缘事”“诗缘情”“诗缘政”之说,只是以偏概全地道出了诗歌“缘何而起”的一个方面而已,若谓之“伪命题”应不为过。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缘何而起”的“伪命题”,无疑也为历史上的诗歌发展产生了种种影响与作用。
对于“诗言志”中的“志”,理解则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诗人“情志”“心志”“意志”“才志”的表述,也可以是诗人“立志”“励志”“告志”“矢志”的过程。根据作品的不同情况,“志”又可类分为“天下之志”“众人之志”“君子之志”“小人之志”,还可以细分为“高远之志”“谦卑之志”“宏大之志”“微小之志”“典雅之志”“庸俗之志”等。而“情志”之不同,诗人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大我”“小我”“有我”“无我”之形象,自然已不言而喻地体现了作品及人品之高下。具体到当下的诗词创作,诸位诗家必将各有自己特殊的感悟与选择。
杨子怡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授):“言志”与“缘情”是诗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言志”较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说法。“诗缘情”较早由陆机提出,其《文赋》有“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话。先秦时期“志”与“情”是有区分的,“志”是属于理智的东西,常指的是思想、志向、抱负,应该是不包括“情”的范畴。但是到了汉代有所变化,“情”也囊括在“志”中,如《毛诗序》就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很显然在此把情志并称了。后来,甚至有人把“言志”与“抒情”划上等号,“情动于中而言以导之,所谓诗言志。”有人索性说“志也者,情也”。到了宋,人们甚至把“志”“情”与“事”相关联:“何故谓之诗?诗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邵雍《论诗吟》)显然,“心中事”也纳入“志”的范畴。甚或把“志”扩大到“政”,如顾炎武就有“故诗者,王者之迹也”(《日知录》)的话。可见,“志”的外延逐渐扩大。“言志”与“缘情”成为中国的诗学传统。我认为两者仍然有不同的侧重点。“言志”主要说的是诗歌的创作问题,是诗歌写作的内容与方向,也即诗歌应该表达什么,应该写些什么,它为诗人指明创作方向。这里的“言”即是“述”,表达与抒发的意思,诗人应该表达或抒发自己的志向、意图、思想、抱负,甚至对社会的看法及对时事的感受。如白居易就把自己的“讽谕诗”看成是“兼济之志”,把“闲适诗”看成是自己的“独善之义”。总之,不管写怎样的诗,诗人都得有想法,有观点,这就是“志”,把这些“志”表达出来就是诗。当然也一定程度包含诗人情绪,诚如陆游所说“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曾裘父诗集序》),“缘情”侧重的是诗歌的发生,即诗是如何产生的,《毛序》所说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就是对“缘情”的一个最好的注脚,它描绘了由情感的冲动而产生诗的创作过程。因此,“缘”字可作姻缘、缘由解,诗因情而发,汤显祖所说的“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就是说的这个道理,没有情感的冲动是不能产生诗的。没有情感的诱发而“强觅愁”,自然会滑到无病呻吟之中,写出哼哼唧唧的无生命的作品。也正因诗是情酿就的,因此也就规定了诗必然有情,情真也就成了评定诗作好坏的最高标准。可见,“言志”与“缘情”涉及到诗歌的创作内容与诗歌的情感发生两个侧重点不同的问题,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中有一段话可资我们参考:“是知怀其时则谓之志,感其物则谓之情,发其志则谓之言,扬其情则谓之声,言成章则谓之诗。”诗人对其所处之时,有一定想法和思想,带着情感去观照它,把它表达出来,把情感宣泄出来,自然就形成诗。这样,诗中自然会寓含诗人思想与情感。
“言志”与“缘情”这一诗学传统仍是我们今天诗词创作应恪守的经验。它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言志乃诗之本。诗人思想、倾向、观点及对时事、社会之看法宜寓于诗中,做到言之有物。如明吴宽《中园四兴诗集序》所言:“古时人之作,凡以写其志之所之者耳。或有所感通,或有所触发,或有所怀思,或有所忧喜,或有所美刺,类此始作之。”当今诗坛之失就在于:应景者多,写实者少;闲吟趋奉者多,寄托有志者少。尤缺思想,一首下来,莫知所云。其二,情动于中始作。宋人胡仲孺《简斋诗笺叙》云:“诗者,性情之溪也。有所感发,则轶入之不可遏也。”他告诉我们:情到不可遏时才作诗,诗才真。“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刘熙载《诗概》中这句话仍值得我们深思。当今诗坛,很多诗人忘记了这个道理,只求数量,不求真情,不管冲动与否,不管感动与否,有节必颂,有饮必吟,有唱必和,有寿必贺,有喜必歌,有风必跟,应景趋时,忘记了诗歌发生的艺术规律,也忘记了诗人的责任与担当,假语套话连篇累牍,看不见诗人的情感所在。因此,我们应该回归“言志”“缘情”的传统,杜绝假大空的东西,永远记住:诗本述志,诗缘性情,诗道性情。
罗积勇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关于“诗缘政”说及其对当代诗词创作的启示意义,经查核文献和对比诗词曲创作现状,我得出了如下几点体会。一、不应过分夸大历史上“诗缘政”说对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众所周知,孔颍达等人是秉承“疏不破注”的原则来做正义的,因此,其在《毛诗正义》中提出的“诗缘政”说主要是对《诗经》大、小序和郑笺的阐释、弥合,如果对唐代诗人和诗论有影响,那也是依附于《毛诗序》和郑笺的。事实上,学者引来证明“诗缘政”说之影响的陈子昂、李白、杜甫、李益、元结等人的话语,都没引用“诗缘政”说,都是直接指向《诗经》大、小序和郑笺的,或者指向《礼记·乐记》的。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批判性地继承“诗缘政”说。
二、《毛诗正义》提出“诗缘政”说有对抗“诗缘情”说的意味,今天则宜兼收并蓄。“诗缘政”的“缘”应与“诗缘情”的“缘”同解,即理解为“诗因为政治(影响)的缘故而创作。孔疏为何不用“言”而一定要用“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诗经》“风”诗反映社会风俗、男女情爱的诗并未直接言政(但它被看成是政治影响的结果,并且在上者可以通过这些诗观察政治的成败得失);二是有以“诗缘政”对抗陆机以来“诗缘情”说的意味,因为孔疏中有“情志一也”的论述,试图将“情”归诸于“志”,其依据是《诗大序》所言“发乎情,止乎礼义”。魏晋以来言情过头,至于“横陈”,唐代要纠偏。我们今天应辩证对待“诗缘政”说,因为“诗缘政”说还有一个重要论据,就是人们的喜怒哀乐的产生都与政治有关。而我们知道,当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非全是政治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有比较明确的“小我”“大我”之分,“诗缘政”与“诗缘情”并非处处对立。
三、“诗缘政”的“君子作诗”说启示当今诗人要以主人翁姿态来创作。为了“诗缘政”的证成,孔颖达提出了“君子方可作诗”和“诗述民志”的主张,这些个主张尽管不能涵盖《诗经》所有篇目特别是国风中的诗篇创作情形,但雅、颂之作者确实大多是当时“国人”或“国人”中地位比较高的“士”所作,这部分人是懂历史且预国事的。所以,今天弘扬“诗缘政”理论,诗人就也应学习历史和了解政事,深入实际,植根人民,以主人翁姿态来写作。
四、《诗》对政的功能不仅仅是“美”“刺”两项,还有“群”这一项。诗序、毛传、郑笺、孔疏将《诗》跟政的关系归纳为“美”“刺”两项,是不全面的。《诗经》中还有《秦风·无衣》等表现积极参与政治的篇目,这一类诗在今天就更多了,抗击新冠疫情的诗词有不少是属于这一类的。对照《论语》中孔子诗论所说兴、观、群、怨,这一类功能可称之为“群”,即在关键时候激起民众的集体主义情怀,应该说,这也是表现“大我”的一种方式。
五、今日“美”“刺”的标准不可尽依“诗缘政”说。诗序、毛传、郑笺和孔疏所讲以诗美政和以诗刺政,是以“政”是否符合礼制、是否符合“旧贯”为标准的,这一点在今天肯定要扬弃。今天宜以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准,党中央确定的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识。
六、“刺政”是诗的重要功能但并非独占功能,中华诗词的刺政仍宜遵守比兴原则。客观地讲,今日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其“刺政”的作用远较中华诗词发挥得好,刘醒龙的一部小说促使政府下决心解决了乡村代课教师待遇问题,中华诗词现在还不能与之比肩。不过,我们在急起直追的同时,还是应该坚持诗词的比兴传统,《毛诗大序》在解释“风”时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毛诗正义》对此加以认同,《毛诗正义》还认为“美、刺俱有比、兴者也”。婉曲的表达也能感人至深,同时更能为人所接受,揆之人情,古今当无大异。
蔡世平
(一级作家、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讨论诗歌写作中“大我”与“小我”的问题,需要搞清楚两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一个是五四前期的中华诗歌社会文化背景;再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中华诗歌社会文化背景。中华诗歌产生于上古时期,茁壮成长于春秋战国时期,诗歌体式成型于魏晋南北朝(我认为“古风”亦是一种重要的诗歌体式)、唐宋及元,体现汉语言文字特征的格律诗、词、曲是其重要标志。
大体说来,《诗经》是春秋时期的作品,“楚辞”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诗经》是中华诗歌现实主义源头,“楚辞”是中华诗歌浪漫主义源头。
五四前期的中华诗歌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意识深植于诗人的头脑,甚至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基因,作用于中华诗歌创作。漫长的中国农耕社会,虽然也有强调个体的“小我”写作,但其主流还是“诗言志”——言儒家思想文化之“志”。近现代虽有不少讨论文章认为,孔子的这个“志”其实是“志意”,是诗人心里面的一个小小想法,是乡情、友情、爱情,亦或是悠哉游哉于自然山水什么的,与江山社稷无关。即便当时孔子真是这么个意思,但是,也被汉以后历朝历代的“注经师”们拉到了忠君爱国的儒家文化“正统”轨道上去了。他们认为这才是诗歌写作的“大我”和“大理”,诗人就是要有放江山社稷于心中的理想抱负,时刻准备着效力朝廷,建功立业,然后是封妻荫子,衣锦还乡。
那时候的诗歌写作者一般都站位很高。无论是乡下的私塾学子,还是县衙当差的吏员,提起笔来写诗就先端正了态度,洗了手脸,正了衣冠,有了“庙堂”之思,应是今日谓之的“高大上”“正能量”写作吧。这也是中华旧体诗歌的一个重要传统,对今天的诗词写作仍有较大的影响。当然啦,那时候的诗人大多是士人,是朝廷命官,与今日之人民大众的诗人还是有不小的“身份”区别的。
以上说的是五四前期诗歌写作的社会文化背景。
再来看五四后的诗歌社会文化背景。
我们应注意到五四后的文学创作是白话文生态己经形成,这一客观现实的要害在于,首先它从语言、语境上颠覆了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言文写作传统。新的筐子便要装新的东西,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如何从旧体诗歌的桎梏下突围出来,创造新的诗歌体式,就成为五四时期诗人的时代使命。于是,自由体新诗应运而生。自由体新诗带来的不仅是诗歌语言、文体的变化,而是写作思想、写作思维的变化。
其次是国家政体的根本性改变,人民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诗人的自主意识增强,再也不像封建时代文人写作的那种小心翼翼了。
再次是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艺术是西方文化全面进入,或者说是中西文化合流形成的文学艺术观念和文学艺术文本。欧洲中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思想迅速发展,“人”的全面解放,生命个性的张扬,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今天的中国文学创作。那么“小我”的诗歌写作便成为时代之必然,这在自由体新诗写作中尤为显眼,它也当然地渗透到今天的旧体诗歌写作。
当新、旧诗歌写作的小情调、小情绪、小感伤成为一种“小时髦”的时候,那么问题来了。它虽然感动了自己一阵子,但却没有能感动读者哪怕是一阵子。诗歌还能担负起净化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吗?诗人、诗歌没有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那么文学的价值何在?而当这种“小我”写作成为“常态”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一种“病态”。我想这也是《心潮诗词》给诗歌写作“疗伤”,专题来讨论“大我”“小我”的一个时代背景吧。这种讨论无疑是切中时弊,很有必要的。
好了,当我们对诗歌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大我”与“小我”的答案似乎也就蕴含其中了。从艺术创作这一层面说,我无法给出是“大我”重要还是“小我”重要的价值判断,在我看来他们的写作都无可厚非,这是诗人的个人选择、个人特点、性趣使然。扬“刘”抑“曹”,以维护刘氏江山正统地位的《三国演义》好,表现中国封建社会必然走向衰亡的《红楼梦》也好。
“小我”也好,“大我”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的立场与态度,文字里有没有民间烟火、天下苍生、人类关怀。有它“小”亦是“大”,无它“大”亦是“小”。文学创作不是码几个社会大词,唬唬人就可以的。诗歌也不是秀场,诗人都来“秀”一把自以为得意的聪明漂亮文字。切记:文学是对作家灵魂的考验。
如从生命至上的观点看,“小我”亦“大我”,可能还是更大的“我”。谁能说一只小鸟、一株小草就不重要呢!没有了它们,地球还会是地球吗?人还会是人吗?天、地、人,鼎足而三,撑起了这个世界。从一定意义上说,“我”,是世界的主体,亦是“美”的主体。是“我”感知了世界,并且参与了多彩世界的建设,人类灵魂的建设。没有了“我”,万物即不复存在,天地归于“无”。
当然这个“我”是要把他人、家国、天下放在心上的“我”。于此,才是写作的意义,诗人的意义。
沈华维
(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长期以来,诗论家们在讨论诗歌的抒情方式时,总会提到“小我”与“大我”这两个词。清袁枚性灵说指出: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续诗品》专辟《着我》一品。突出“我”,既是强调诗人特有的秉性、气质、审美能力等的个性化和独创性。从诗中有“我”的概念提出后,又生发出有我、无我、小我、大我等命题。诗因“我”而有感生情,进而形成与别人相异的独特的个性化的感受。诗中的有我与无我、小我与大我,都是诗人抒情言志的一种方式,“志”无轻重,“情”无先后,“我”无大小,他们既属个人的,又是大众的,很难截然分得清楚。就诗人所处的“大我”环境而言,诗人是时代的、人民大众的代言人,诗人的立场、观点,应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但创作时,仍需充分投入个性,即“小我”情感,不能以公众化的共性情感,来置换诗人抒情主体地位。自然,将孤立地抒发个人情感和抒人民之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有时候,纯粹的个人情感也有时代的烙印,有时代色彩的折光。只强调“小我”或只强调“大我”,都未免偏颇。现代著名诗人艾青曾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中,而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和欢乐中。”实际上,“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是通过个性来反映共性,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杜甫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不仅抒发了自己的苦难和哀愁,而且大声疾呼“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代表了天下穷苦百姓的心声。使自己的感情具有了“大我”的普遍性。
我们以今年的抗疫诗词为例。庚子年初,当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突发后,广大诗人词家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觉拿起手中的笔,投入这场防控疫情的阻击战,讴歌抗疫英雄和感人事迹。其作品数量之多,作者之众,意想不到。其中许多作品都偏重于“大我”的展示,即大视野、大场面、大胸怀式的展现抗疫局面,宏观描写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驰援湖北,白衣逆行,八方支援的场景。如武汉诗人四维先生《定风波·致敬武汉金银滩医院》:“谁料过年如过关?金猪银鼠陷泥潭。 风展红旗齐领命,问病,小家在后大家前。封路封城封感染,武汉。仁心妙手着先鞭。橘井灵泉千万眼,化险。争来春意乱云边。”作品以局部观全局,刻画了疫情就是命令,各方领命出征,白衣战士舍生忘死,不顾小家为大家,妙施仁术,化险为夷,终于迎来春意无边。作品彰显了诗人的家国情怀,也印证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早在千年前就提出的好诗的主张:“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于言,莫切于声,莫深于义。”
我们再看一首以“小我”的视角,来抒发抗疫经历和体验的作品。武汉诗人泉名先生不幸染疫中招,被隔离治疗。当他从方舱医院出来后,曾经写下一首《核酸转阴性作》,向友人们报平安:“东风入幔琐窗晴,一纸报如天下宁。连日自羞贪食饭,巡床医嘱罢悬瓶。楚江尚禁可怜丽,春疠犹存未觉馨。应许离人皆似我,归期已近暂伶仃。”诗人以自己特殊的经历,探究自身心理活动状态,真实的记录被封锁隔离的无奈,饮食治疗的过程。在那个唯核酸谈“阳”变色、畏之如虎的特殊时刻,病人得知自己核酸检测转阴,已脱离险境,重获平安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希望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成为方舱医院的“离人”,“一纸报如天下宁”,寒冬已过,春意将临,传递出守望命运,共担苦难的云水襟怀。此诗以鲜明的“小我”之境说明,对平凡的避疫生活的提炼,同样可以折射出浩荡的时代潮流。
从以上两首作品(我暂且把它们归于一大一小之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小我”与“大我”,只是诗中表现情感的一种手段,一种视角方式,本无孰优孰劣,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表现好主题,写出好诗才是目的,才是硬道理。作品中的小与大是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大中含小,大气磅礴,这是诗词的特性,也是诗人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