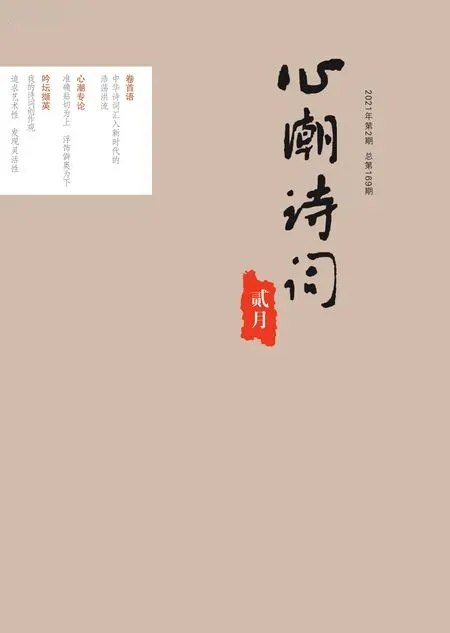褚诗的风格与法度
李俊儒
一
自元白大倡新乐府以来,诗歌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而褚宝增先生的作品正是这种风格的当代式反映。
先生的诗风在诗坛独树一帜,最大的特点是致力于以时语、时音入诗,这正与千载以上的元白相契合,先生也从不隐瞒自己革新诗风的志向,有与刘庆霖先生唱和之作为证:“久妒公才今始平,同开乐府用新声。诗坛宣告呼刘褚,从此吾朝有并称。”
二
先生既欲开今世“新乐府”之诗,所提倡的诗风自然是和元白一样妇孺可解。但这绝不意味着先生的诗是不加锤炼,脱口而出的。恰恰相反,“捉对工严非炫巧,析辞坚稳必能精”(《贺阮诗雅〈桂斋七律集〉付梓》)。先生对自己以及门下弟子,时时皆以精工为准绳,“宁可不作,不可不工”。兹以炼字、对仗、用典、结构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1.炼字
炼字是作诗的基本功,古人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而褚宝增先生虽然不雕镂饾饤,但诗中却总能见到清警可人之句,如“斜阳怂恿波光起,巨塔要挟鹊影逃”(《玉渊潭中堤桥上春末观景》)。“怂恿”“要挟”,皆是现代白话的用词,也是诗论家所谓的“熟语”,但用在此处反而令人耳目一新,这正是锤炼的功夫。而这种以生法道熟语的炼字之法,也是褚诗的秘藏之一。此外如“任由弱柳频撩我,莫问新花又对谁”(《小暑午后游颐和园》)、“铁塔频摇难抗树,金风群起愈开腔”(《登京西百花山》)等,对动词的锤炼和熟语化生,皆可慕也。
2.对仗
对仗看似容易,而作好实难。褚诗的一大特点就是出句对句之间大开大合,似离实即,而在对仗上却能一丝不苟,如“欲使八旗夺九鼎,觉应五岳拜千山”(《游赫图阿拉城》)、“醉中时有千年梦,剑外终隔万里途”(《游成都琴台路》),皆用数字成对,却天然浑成,气势磅礴。
近体诗贵在一字千金,因此重复字乃是近体诗中的大忌。但是如果能善于运用,便能收获出其不意的效果。褚诗对仗另一大特点便是善于在一联对仗中运用重字结构,即前人所说的“复字”。如“明知不可终仍可,大化众流成巨流”(《酹酒祭孔子墓并序》)、“不思霸道宗王道,总用仁心守义心”(《中国哲学》)、“腰生杂木顶生草,山下浓阴山上晴”(《从长白山西坡上观赏火山口天池》)、“四墓四瓶同样酒,千年千里共鸣心”(《谒巩义杜甫墓》)等。无论是写景或是议论,皆是平中见奇。此外,褚诗中甚至有用数学用语入诗对仗的尝试,如“最高义是赴国难,极大值为赢自尊”(《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亦可作一新法参看。
褚诗也善于运用律诗的当句对之法,如“放浪形骸存气韵,殷勤知古为从新”(《贺本门十弟子李俊儒汉仪获“聂绀弩杯”大学生中华诗词邀请赛冠军并次其作品原韵》)、“滥背诗徒俗欲雅,真知音者百难一”(《忆九年前游洛阳白园谒白居易墓》)等,同样可以倍增诗的张力与灵气。
3.用典
褚诗不以用典为能,但一旦用典便必求精准工稳。而如果在对仗中用典,则遵循“事对必基于言对”的原则,并不因为用典而放松字面上的对仗。如“枉有飞扬三礼赋,终成老病一沙鸥”(《谒平江杜甫墓》),出句用典,杜甫在天宝九年曾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并得到了玄宗的赏识,而对句则是化用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及“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之句。不仅用典妥帖,而且对仗纤毫不爽。这正是褚诗的精工之处。同样例子的还有“放荡曹参酒,悠闲晁错头”(《闲居》)、“以龟换酒情谊定,呈卷呼仙去就分”(《步张桂兴会长〈红树林〉韵并答谢知遇之恩》)等。
再看《感怀》一首:
也曾直自荐,不逊鲍参军。
未遇临川主,仍如负芥身。
富能超五柳,名岂共三辰。
但借一杯酒,增添枕上沉。
一首连用五个典故,却无堆砌之嫌疑。“临川主”应是指南朝临川王刘义庆,刘义庆广罗文士,曾编写《世说新语》;“负芥”则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语句;颈联中“五柳”即五柳先生陶渊明,“三辰”则是日、月、星。鲍参军和临川主的典故,表达除了先生期许遇到如刘义庆一样爱惜文士的知音,可惜事不遂愿。“富能超五柳,名岂共三辰”,更是自嘲中的无奈。品析此诗中胸怀与志向的同时,临川、负芥、五柳、三辰在对仗上的精工,也是值得注意的。
4.结构
对于诗词而言,辞句如肌肤,结构如骨骼。白居易在《金针诗格》中曾把律诗的结构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联谓之“破题”;第二联谓之“撼联”,“欲似骊龙之珠,善抱而不脱”,或者“雄赡遒劲,能捭阖天地,动摇星辰”;颈联谓之“警联”,搜索幽隐,哭泣鬼神;第四联谓之“落句”,如“高山放石,一去不回”。律诗结构安排如此,则可谓至矣。兹以先生《谒秭归屈原祠并屈原墓》一诗稍作分析:
万古诗宗此地生,煌煌日月总陪同。
心才暗痛即来雨,树便低垂不敢风。
本分无邪难大怨,基因纯正必孤忠。
而今荡荡三峡水,随意濯缨濯面容。
首联破题而入,务在引出下文,“煌煌日月总陪同”更有非凡气势,如此开篇方可以免于平弱凑泊之病。颔联做到了情景融合,心方暗痛,更兼来雨,将此时屈原祠之氛围烘托备至,对句的“风”字更是活用为动词,顿收神奇之效,作者对屈原的缅怀与敬仰之情亦呼之欲出。第三联转入议论,既是对屈原的论定之语,又有自身感怀于其中,可谓警语。尾联跳脱开来,意在言外,确能收“高山放石,一去不回”之效。
当然,诗无定法,结构亦不能拘泥于一式。但唯有善于安排结构者,其诗方能避免有句无篇,并支撑起一篇之立意。这也是成为佳作必不可少的要求。
三
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情感的真挚与极强的震撼力也是褚诗的一大特色。如《闻吾师许永璋先生今夏于南京仙逝两章》:
入理亲文整廿秋,百家六艺世风喉。
进身有幸宗和仲,学业无成逊少游。
曾为圈红一字喜,岂因易墨半篇羞。
而今再向吾师问,渺渺云间万鹤楼。
初闻平静转而惊,递涌悲伤占尽情。
逐字删扶诗赖正,开篇讲解意方通。
由心是梦连非梦,任月三更到五更。
留下德操被岳麓,一生文笔续桐城。
先生年少时就读于南京大学数学系,但是却因机缘巧合在文学课上结识了中文系的桐城许永璋教授,并从许先生学诗。这两首是怀念许先生的作品,笔触真挚,令人读来不胜唏嘘。而同样的写怀之作在集中不占少数,如“无诗总感活如死,有酒仍能暮至朝”“一心仍似火,两鬓渐成秋”“古月同于今月亮,今人胜却古人孤”“偶观北斗觉无愧,每遇东君总有情”等,都是难得的性情佳句。
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的诗词风格虽然以雄豪见长。但集中婉约之作同样缠绵悱恻,令人百转千回,如《无题》一首,相比于当代任何以婉约见长之大家,皆无逊色:
尚未别离心已愁,料知明夜月成钩。
一朝南浦一生恨,两扇西窗两处楼。
花落花开因起雨,且行且止若浮舟。
为能不怕人相问,借故思乡让泪流。
先生几十年来,所作诗篇已有六千余首。在浩如烟海的作品之中,如果要我选择其气力最盛,著意最深,最能代表褚诗之风格者,应当是《谒杭州岳王庙三章》:
终能亲见岳王爷,八百余年情未绝。
受我屈膝三叩拜,愿君上马再集结。
忘其痛饮黄龙憾,代以清除倭寇邪。
一曲满江红唱响,吹平东海浪千叠。
战罢郾城逼旧京,金人再败已无兵。
渡河轻可收幽蓟,放马犹能下会宁。
耻辱羞仇积抑郁,精忠智勇待喷腾。
大唐疆域将重现,毁在君王敕令停。
江山半壁瞬间丢,都号临安觉记仇。
殿上君臣甘苟且,阵前将帅枉追求。
正邪稍忍奇冤酿,忠逆急衡大恨留。
于此做为埋骨地,英雄死后再蒙羞。
读罢三篇,怒目拍案之景象犹在眼前。尤其其一,韵脚全用古之入声,而属对之精工,情感之激烈,寄意之深厚,当能得集中诸篇之冠冕,即使称之为新韵阵营中的扛鼎之作,我想亦不虚忝。
四
先生多年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在不断的探索中,又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这在先生《论诗绝句百首》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故而分析褚诗之法度,自然可以在论诗绝句中寻找蛛丝马迹。
1.诗外工夫胜
或许是先生理科的出身,决定了先生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式。先生为诗,很少用力于雕琢文字,更重要的是书写自己的思想与胸怀,也就是“诗外工夫”。先生曾在论诗绝句中批评当下大学校园里崇尚同光体的现象:“酷似宋初宗贾岛,甚于元末拟飞卿。自知诗外功难济,专卖修辞搏令名。”也是这一论点的侧面映证。
对于诗外工夫的修养,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天才无物总文迟,出塞岑参始有诗。送客雪中辕阵外,梨花开遍万枝时。”而除了阅历与年齿的增长外,保持思想和立意的理性与中正,也是重要的一点。如《与褚门弟子说》:
思维休偏激,偏激险象环。大道行中正,中正道自宽。莫以一己私,浪发臧否言。臆断近无知,招惹笑柄传。示长并藏拙,居后为成先。是非及俗雅,岂尽分两端。时常作鬼语,鬼语必伤年。奇诡摧李贺,幽苦损纳兰。无有大气量,将淤肺与肝。力求融百家,可随日月悬。
“大道行中正,中正道自宽”,堪为至理名言。
2.立意当为先
历来古人有关诗中立意的争论很多,曹丕在《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词为卫。”而明代谢榛则认为:“诗以一句为主,落于某韵,意随字生,岂必先立意。”(《四溟诗话》)事实上诗为志之所之,徒以炫耀文字,雕琢一词一句而惑人耳目,终究不是诗之上乘。例如晚唐的贾岛、姚合,其得在于佳句,其失则在有句无篇,如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除了“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联外,皆人尽能道之语,乏善可陈。虽有名句,卒不能与真正的名作相比。这在古今已有定论。
褚宝增先生始终认为“阅世、读史、仗义、怀仁,此诗人之必备”(《褚宝增诗文选集(2005—2015)》自序)。过分雕琢文字之精工,自然不可能是先生所追求的作诗法门。褚诗真正动人之处,便在于诗中高超的立意。
先生认为立意有四个要点。即立意在先、立意须明、立意须新、立意须高。这四点在先生的咏史诗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如《访海瑞故居》一诗的尾联:“世人反谤沽名誉,皆去沽名世自清。”立意既高且新,令人折服。而“卷土重来知不能,断然一刎出声价”(《说项羽》)则在杜牧、王安石之后又从另一角度推陈出新,不失为翻案之良作。至于评宋徽宗赵佶的一联:“潜心所创瘦金体,瘦剩江山半壁穷。”立足一瘦字,机巧之外,又发人深省。诸如此类,在先生集中不可胜数。
此外,褚诗善于以小见大,即使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也能发掘出独特的立意,如:
自京举家驾车去海口驿湛江一夜
满眼斜阳生好风,着衣不必再肥臃。
江山万里炎凉异,无碍人心向大同。
说旅游
腿尚轻灵腰尚纤,不妨偏爱访名山。
为能战胜恐高症,绝顶仍需向上观。
当今诗人往往生活中逢一小事辄下笔成“诗”,但往往缺乏的便是精到的见解,内容不过是流水账而已,这等诗即使作千首万首,又有何益?陆游《示子遹》曾写道:“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可为此症之良药。而褚诗则堪为师法之范本。
而即使是诗人日常的酬赠之作,先生也绝不虚与委蛇,精警之立意触手可拾,如:
待到千军同奋起,便无恩怨便无门。
(《答李崇元先生〈读褚君弟子诗〉并用其原韵》)为使天涯知己晓,吹箫再上凤凰台。
(《贺北京诗词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举起金樽一放眼,唯公分走我诗名。
(《与诗人刘庆霖先生于京痛饮》)全才仰仗才间济,大艺因图艺外求。
(《福州拜见赵玉林老并获自书诗文集签赠》)
3.诗律需精细
先生在2017年初夏时曾作过这样一首论诗绝句:“不悔轻狂是少年,曾呼屈宋作衙官。老来诗律足精细,堪补当初放胆言。”可见先生一直以来从未放弃对诗律精细的追求,具体可以从对仗与反对拗体两方面来探讨。
当代最为盛行的诗体,便是七言律诗。而二联对仗则可以称之为律诗的“中流砥柱”。因此对于对仗的要求,自然不可以等闲视之。故前文虽然已讨论了褚诗对仗的风格特点,此处小括先生于对仗之法度,以为补充。
先生认为,中二联对仗必须追求工稳,不得从宽而对。如先生曾指出一场诗赛的获奖作品中,存在一些不够精工的现象,如“玉树”对“东山”、“南浦”对“曲栏”,皆是词性上的对属宽泛,而“月夜”对“春秋”,则甚至犯了平侧之病,即以并列结构对偏正结构。这些都是先生对诗律之“精”的要求体现。而先生对用典的要求则是“事对必须基于言对”,即用典的同时,对仗上依然不可有丝毫放松,这是先生对诗律之“细”的要求体现。为此先生也曾专作绝句论述,可以一并参看:“看似无情却有情,空间张大复充盈。必须事对从言对,巧又能工算上乘。”
律诗的拗体自老杜形成,在宋代被黄庭坚发扬,继而形成了一种“宁拙勿巧,宁朴勿华”的风尚。用诗的拗变,追求语意的艰深雄健,以此避俗。而褚宝增先生则明确地指出:“质文并重质先行,变体实为病体征。”拗体非变体,乃是病体。诗律在唐代形成,自有其发展的规律存在。拗体原本也是相对于正体而言,既然这种音律之拗是已经被正体大浪淘沙后的产物,再度标榜拗体,岂非逆势而为?事实上,拗体在杜甫集中也并非多数,实非正调。如《白帝城最高楼》一首,通篇皆拗,然而实乃身临此景,周遭险恶的泣血而发之作,兴到如此,骨骼愈加峻峭,自不可以格律拘之,料老杜当时未必以律诗视之。但这种变化偶而为之尚可,自有其兴会之妙,但如果以此为标榜,另成一体,则是刻意求奇,不足为训了。总而言之是在“质文并重,质先于文”的原则下,难以做到“质文并重”的无奈之举。
4.崇时拒泥古
关于先生追求时音时语入诗的观点,在前文已有论及。但应该如何创新,先生的看法是:“不仅翻新敢创新,求新首要立精神。前七子又后七子,重在今朝拟古人。”明代前后七子以标榜唐诗创立门户,他们的问题在于拟唐人之辞藻,而空有浮响,了无余味。读来不过是唐诗的仿体,而很难见出作者的真实性情与历史环境。这一点,在清初已经有了论定。而今日之社会革变,其剧烈程度又远胜于唐代到明代的变化,针对今日诗坛涌现的拟古之风,先生的这一论点,无疑是一剂苦口的良药。
不过先生并不反对传承古人。相反,先生历来力主诗由古入,“殷勤知古为从新”。我们所学习的,应当是古人的法度与精神,而不是辞藻上的仿古。因为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人的生活方式相比于古人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于当代诗歌中一些仍然充斥的拟古且不符合实际生活情况的意象或者辞藻,先生的态度是否定的。如这首论诗绝句所言:“不失法度继先贤,当解时光只向前。天下男人多短发,是谁仍卖汉唐冠。”诗当然是需要美感的,但并不需要脱离现实的虚假美感。
五
褚宝增先生在当代是一位极具探索精神的诗人、诗论家。这在褚诗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先生也不仅限于小我,多年来坚持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开创诗词创作课程,将自己形成的诗法金针度人。在先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加入了诗词复兴的阵营。我们有理由相信,诗词一道必将在未来散放出不可小觑的全新活力。文章的最后,引先生2005年结集自序的赞言作为本文的结尾,并与诸读者共勉:“生也有涯,无涯惟智;傲岸泉石,咀嚼文义;诗载精神,我心有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