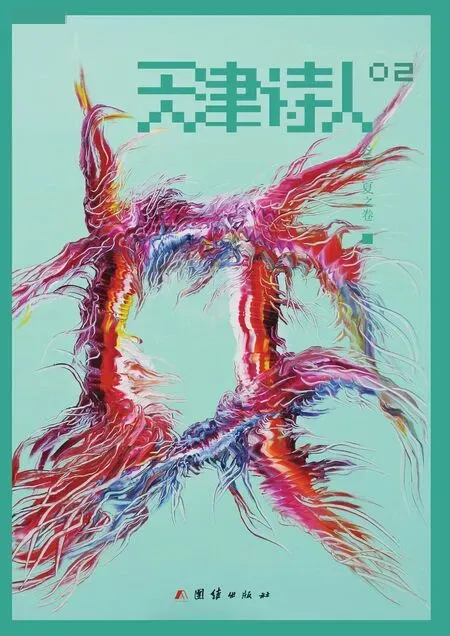文化突围,生命的突入之诗
蔡超
“荒野之声”“蝗群变调”“大漠风沙”……单从《段光安诗选》的目录与选辑即可看出,诗人之诗的主体风格与审美偏向——悲壮苍凉,雄浑辽阔,带着生命的沉郁,却有一往无前的力道。
开篇的《荒野黄昏》,荒野、黄昏、乌鸦、日落、喘息、腐烂,所有的意象构建出萧索衰败的意境,却在近乎原始的氛围中突显生命的轮回不息之力。这让笔者想到艾略特的《荒原》和《死者的葬礼》,只是又有所不同。艾略特的诗中,万物复苏,生命在死亡的腐败上野蛮生长,诗人在肯定生命力量的同时哀悼逝去的一切,感叹四月是“残忍”的季节。而段光安不像艾略特在诗中呈现生死纠缠的暧昧、对死亡的回眸,更像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带着一种更为朴健的向前的生命力道,“云杉倒下腐烂/再重组生命”,生命在此处得到更无挂碍的彰显与更新。也由此,诗人更进一步地进入对自我生命的探寻。
世界的更新乃在于自我的更新,“时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熟悉的先人智慧在这里得到新的阐释。来时的路已苍茫,灵光飞出是“万路之后无形的路”,在万路上下求索中才得到顿悟的此刻。天地人交汇相通,诗人这一感触一定难与人言,却隐含着传统“天人合一”的智慧。
段光安的荒野不只是一个诗歌意象,其中更含有自身的生命意蕴,荒野的野性是对自己被文化遮蔽的生命的重新开启或救赎,这里就有了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对生命本源的接近和皈依,一种精神的依靠和救赎,而荒野的野性和生机勃勃在这里恰好暗合了生命的本源。它突破了文化上的复杂纠缠,孱弱精致,段光安更钟爱荒野,钟爱粗砺意象和生命不羁的野蛮生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段光安笔下的高粱茬儿、拉拉蔓、青麦、蜣螂、螳螂、鹰、老马、母豹、残狼、残碑、残石、古城……它们都有一种不屈的力道,生命是不屈的,石头、挺立的碑更是不屈的,这和诗人的生命历程或精神向度有关。
段光安的诗积极地从原野的生命中汲取养料,磨砺诗,更磨砺自己,并形成自觉,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