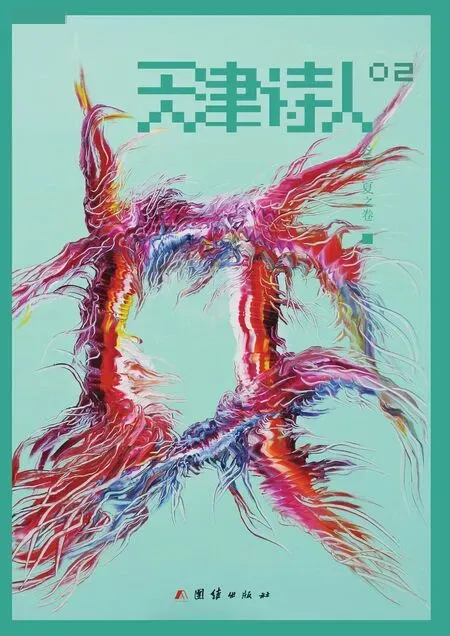为生灵叹,为生命歌
谭笑
“生命的深刻才是诗歌意义的深刻。”正如诗人段光安在《觉诗》中所言:“我认为对诗而言,生命至关重要,即使是一句有最微小生命的诗,也胜过与我们生存无关的厚厚诗集。”整部诗集浸透浓烈的生命意识,最打动笔者的也恰恰是诗人笔下那些卑微弱小却又不屈不挠的生命。
“只有简化,才能把有用的东西从大量无用的东西中萃取出来。”段光安的诗大多短小精炼,语言平实质朴,没有过多华丽辞藻的修饰却将鲜活的生命意识熔铸于诗歌之中。比如:“静/潜入湖蓝/几朵白鹭悠然/灵翼扇动/几行诗句漫上苍天”(《湖上白鹭》)。诗人用精炼的笔触,近乎白描的手法,三言两语就让几只在湖上悠然戏水的白鹭跃然眼前,最为点睛的是“几行诗句漫上苍天”。这些小生灵的怡然自得、这静谧和谐的意境又随着诗人灵动的思绪而诗意盎然,成了漫天的诗行,诗行间弥漫着清新自然的生命气息。仅有两句的《再步老桥》:“行人是缺氧的鱼/待活儿的民工锈成桥头的铁钉”。经年沧桑的老桥,没有活力、呼吸困难的行人,还有铁钉一样常年固守着零活儿的民工。现实的场景,简单的画面却映射出深刻的“城市病”。诗人以日常生活为切口,以生命意识洞察着现实问题,从更深层次反映生活,再现生命。这也有力地印证了诗人霍俊明的话:“诗歌的体量与诗行的长度无关,而是与精神和智性、思想的体量有关。”
段光安认为每个生命都是艺术家,呈现着生物体中的艺术方式。哪怕是一朵野花,一片落叶,一声鸟鸣只要用心感悟,在某个瞬间都别有动人心处。因此,他善于捕捉身边的一景一物,从平凡的自然意象挖掘不凡的精神意志。“静穆/收割后的高粱地/干硬的根/支撑着剩余的身躯/在凛冽的风中/站立/锋利的梗/执著地望着天际/大雁远去”(《高粱茬儿》)。干硬的根,剩余的身躯,凛冽的风,一幅秋收后高粱地里荒凉残破的景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但诗人笔锋一转,转向那锋利直指天际的梗,它迎风而立,凄凉中透出刚强,那是一种强烈的对生的坚守与渴盼;而远去的大雁是寒凉、是眷恋,更是一份来年春必归的希望!又如被砍割后的沙柳茬儿、戈壁被风沙侵蚀的树根、狭缝中生长的树、被锯去枝叶的光秃树干……诗人选取的意象并不华美惊艳,相反很多都是残缺破损的,但就是在这悲美的意境中,每个微渺的生命体内都蕴藏着一股不屈的力量,虽处于困厄之中仍顽强地生存,使读者感受到振奋人心的生命活力。
诗人笔下的动物意象也大多如此。如《蟹蛛守台》,“日夜厮守/只剩下干瘪之躯伏居于台/把自己撕碎/蛛丝延伸且不断展开/一张硕大的网/把贫瘠的土地覆盖/其实那张网/早已在我们的体内存在”。一只小蟹蛛,诗人却能从它身上发掘坚守不渝的精神,可见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的生命都有它的崇高之处。诸如此类的意象在段光安的诗中还有很多,如在雨夜中坎坷前行的老马、举步滴血仍回洞喂奶的母豹、地震后逃离动物园的残狼等。诗人描绘了这些个体在饱受磨难后展现的坚韧的生存意志,悲悯其苦难际遇的同时将生命的张力和炙热表现得淋漓尽致。
“诗需要真挚,真挚到深入根本,向自然或自己汲取或深入,返璞归真到本质。”正所谓探索自然的本质即探寻人性,所有对自然万物的描摹刻画最终总要回归到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思考,向着人类深层的生命意蕴贴近。“每天走向衣镜/由风华正茂剥落成一块奇石/瘦/陋/皱/饱经沧桑/看不清/是云/是雾/是霜/昏花老眼审视/一片苍茫”(《衣镜》)。更衣照镜是平日里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我们每天重复着这样的小事,却没有发觉时光就在这平凡的日子里匆匆流逝,岁月无声无息地流走却在人们的身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痕迹。韶华已逝,诗人看着衣镜中的自己已不像从前那般风华正茂,苍老的容颜、瘦弱的身躯好似一块剥落的奇石,破碎,丑陋。在《某时》中诗人说,“我不敢看时钟/因为秒针不断地割着我的生命”。秒针形如针、状似刀,不停地切割着生命,这样形象、巧妙的比喻,表达了诗人对时光易逝的痛惜。如果说子在川上曰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豪放豁达之风,那么段光安的这首诗则呈现了细腻、深切的痛,让人触目惊心,思绪万千。
谈及时光,死亡这一生命现象便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段光安在《门》中写道:“祖父进了一扇门/父亲也进去了/我突然发现自己站在电动扶梯上/正逼近那道门槛/黄昏融入玻璃/门虚掩。”诗中的这道门便是死亡之门,当祖辈都相继走进那扇门后,诗人意识到自己也在向它逼近了。同时,诗人选取黄昏这一深沉的意象,玻璃中的黄昏,更平添了生命的虚幻和不真实感,表现了深沉悲凉的生命意识。
《段光安诗选》让人深切地体会到诗人对生命的敬畏、对生灵的赞美和对生命本质的挖掘与探索。也正是因为怀揣敬畏之心、赞美之情去创作,段光安笔下的诗行才有了生动的情感、鲜活的意象和不屈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