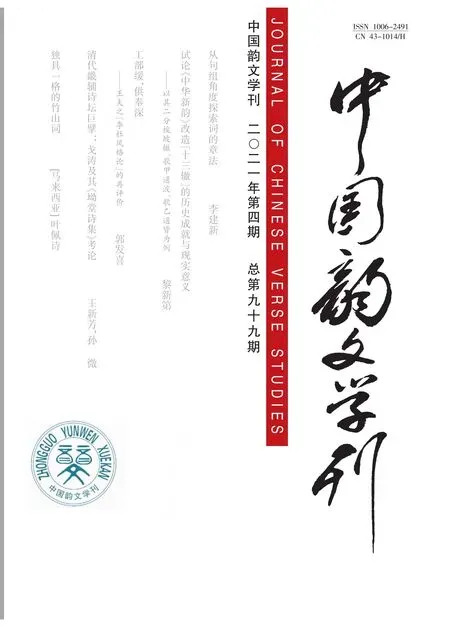会通与会心:论姜书阁的古诗学
雷 磊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古诗,从现代学术的眼光来看,一般指中国古代的诗歌,系取其广义。但是,从传统学术的眼光来看,一般是指汉魏六朝(即汉至隋)诗歌,取其狭义。若以传统学术古诗概念而论,它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唐诗,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时代特征,即主要指汉至隋代的诗歌,往往简称为汉魏六朝诗,古诗也可包括逸出《诗经》《楚辞》之外的先秦“古逸”诗,但并非通例;二是体裁特征,主要指汉至隋代的四、五、七言诗,尤以五言诗为大宗,而唐及以后的五、七言古诗不与焉。所谓唐有唐之古诗,而古诗亡。唐代古诗与古诗是性质相异的两种诗体,明清诗家多分别而论,而将前者称为唐古。因此,古诗不完全是与律体诗(近体诗)相对的古体诗概念,而是其时代特征与体裁特征相结合而成的概念。古诗(即汉魏六朝诗)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中国古代诗歌继《诗经》《楚辞》之后的又一兴盛期,同时启导了唐诗之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巅峰期。唐诗之巅峰并不能掩夺《诗经》《楚辞》的辉煌,同样,唐诗之巅峰也不能掩夺汉魏六朝诗之光芒。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诗歌。现代学术,有成熟的《诗经》学、《楚辞》学、唐诗学,但是没有古诗学。我们认为,可以提出古诗学这一概念,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汉魏六朝诗歌,以入于《诗经》学、《楚辞》学、唐诗学之序列,当有其充分的理据。若无古诗学,则无唐诗学和宋诗学,此当为古诗学之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姜书阁先生(1907—2000)有古诗的创作、理论和批评,三者结合当可构铸其古诗之学。姜先生幼冲学诗之蓝本即为《古唐诗合解》,当于古诗有极深之体悟,后出版自选诗集《松涛馆诗集》,其中有不少古诗。姜先生可称为文学史家,著有《中国文学史四十讲》(1982)和《中国文学史纲要》(1984),后者初稿78万字,撰成于1962年3月,不久即油印300部以作教材,为新中国最早个人独立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之一。此两部文学史均于古诗及其发展颇有论列。姜先生又可称为文体学家,先后著有《诗学广论》(1982)、《先秦辞赋原论》(1984)、《骈文史论》(1986)、《汉赋通义》(1989)、《说曲》(1990)等。《诗学广论》是其诗歌理论之结晶,亦为其代表作之一。姜先生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汉魏六朝诗三百首》(1992),虽为选本批评,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姜先生古诗学的“晚年定论”。
姜书阁先生也是较早使用“诗学”术语的学者,其《诗学广论》自序云:“过去论诗者,很少有人用‘诗学’一词,而作为诗的支流的词、曲,皆以附庸蔚成大国,却老早就有人称之为‘词学’‘曲学’,这好像有点奇怪。其实,诗论、诗说、诗话、诗律、诗史,乃至诗纪、诗笺、诗选之类,也都属于诗学的范畴,若把这些内容加以概括,便是诗学,而且只能名之为诗学。因此,本书以‘诗学’为名,实际上就包括了上述这些方面的内容。”因此,《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当然属于诗学论著。古诗学、唐诗学、宋诗学,系以时代划分诗学。就姜先生之诗学而言,其古诗学之支撑论著更为坚实,提出姜先生古诗学之问题,理由也更为充分。姜先生的古诗学论著,已如上言,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文学史,如《中国文学史四十讲》《中国文学史纲要》;二是文体学,如《诗学广论》《先秦辞赋原论》;三是古诗选本,即《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三者之间是先后发展,又互为补充的关系。因此,本文即结合上述姜先生所撰古诗学相关著作,探讨其古诗学思想,而论述则以其最晚之古诗学著作《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为中心。以下即从文体论、作家论、作品论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
姜书阁先生的古诗学论著具有强烈的辨体意识,而其《汉魏六朝诗三百首》的编选思想和编选实践是其古诗辨体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理论总结。
其实在《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之前,虽未明言,姜先生已经基本确定了古诗含义即汉魏六朝五言诗的观念。如他的文学史论著和文体学论著均认为五言诗在东汉成熟后成为文人诗歌的主要体式,又认为古诗是律诗产生之前的诗歌形式,又认为古风(即古诗)可专指五言古诗,综合起来就是上述所言古诗的基本含义。而《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主要是序言)对古诗内部的各种体式辨析更为精密。
姜先生在编选《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之前,“遍读明清以来古诗选本”,探讨古诗(主要是五言诗)的源流演变,其序一则曰:“向来言古诗或选古诗者皆并先秦两汉与魏晋南北朝为一,而泛称‘古诗’,(如《古诗选》《古诗源》)或舍先秦而径以‘汉魏六朝’为目。”即汉魏六朝诗可代表古诗之意。再则曰:“自西汉之兴,至隋代之亡,八百余年间的诗歌,主要是完成了五言诗的全部发展过程。”即汉魏六朝五言诗可代表古诗之意。最后说:“本书所选的时代是五言体代替《三百篇》四言体而萌生、发展、成熟的历史阶段。”明确了本书的编选宗旨,即主要选评汉魏六朝五言诗,以揭示其发展的全过程。
最初,出版社系请姜书阁先生编选《魏晋南北朝诗三百首》。显然,若以五言诗发展视角而论,汉、魏难以分断。姜先生认为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诗”,已是完全成熟的文人五言诗,钟嵘《诗品》“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的说法,早已为后世学者所推翻,定其为东汉末年作品。若未入选,则非合理。与此相类的,还有托名的苏李诗,亦为东汉末年作品。因此,姜先生商改为《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今选即收入“古诗十九首”,又“古诗七首”,又“托名苏武李陵赠别诗七首”。
既以揭示五言诗发展为选录宗旨则可不必选录先秦诗歌。汉魏六朝之前的诗歌尚有上古歌诗、《诗经》、《楚辞》、周秦楚歌、周秦歌谣等。上古歌诗,其序认为:“世所传《击壤》《康衢》之类,本不足信,亦无须选。”其两部文学史著作也是少论此类诗,即非为文学史发展之重点。《诗经》为成熟之四言体诗,又已成书,也不必选。《楚辞》也为成书,且系汉赋之近源而非汉魏五言诗之近源,则亦不必选。至于楚歌,姜先生认为:“楚辞之为体实源自楚歌,其势至西汉犹沿袭不衰,以故若选先秦诗歌,自可以楚歌当之。”不过先秦楚歌虽为《楚辞》之源,却非五言诗之源,且存世颇少,又曾经姜先生选出结集出版,就不必再选了。至于周秦歌谣,姜先生认为:“战国至秦,散见于经子百家的风雅歌谣可视为诗者,实亦极少,从明人冯惟讷《诗纪》、杨慎《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及近人逯钦立所辑的《先秦诗》来看,至多不超过百首。”其乃转相杂抄,颇为丛残,多有异文,亦不尽可信,难为先秦诗歌之代表,不选可矣。总之,姜先生从揭示五言诗渊源这一选录思想和文献之性质(是否成书,可靠性)来看待和处理先秦诗歌,其与汉魏六朝诗各为独立之文学段落,予以截断,理有当然。上古歌诗、周秦楚歌、周秦歌谣,明清古诗选本,多统称为“古逸”,或选或不选,非为必选者。汉魏六朝诗径称为古诗,以上接《诗经》和《楚辞》,在学理上,也就成立了。
同样,基于揭示五言诗发展的选诗宗旨,四言诗也在非必选之列。姜选序明确了“不再选录四言诗”原则,因此,于前人普遍称赏的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韦孟《讽谏》、嵇康《赠秀才入军》等名篇,皆在割爱之列。但是,对于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和《步出夏门行》(云行雨步)两首四言诗,因成就极高,无法忽略,“则破例选入”。
五言诗既非直接渊源自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那它的直接源头何在?姜先生认为,从文献来看,五言诗起源于汉代民歌(包括民间歌谣和乐府民歌),史书载有成帝时五言歌谣《尹赏歌》《黄爵谣》,而汉乐府民歌多有五言诗,且代表了汉代民歌的艺术成就。东汉班固《咏史》为第一首完全的文人五言诗,但艺术上并未成熟。其后,东汉文人五言诗增多,有名氏者如秦嘉《赠妇诗》三首、郦炎《见志诗》二首、赵壹《疾邪诗》二首、蔡邕《翠鸟诗》、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等,而渐趋成熟。《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和“苏李诗”七首,均公认为东汉末年文人之作,且艺术特色相似,可统称“古诗”,标志着文人五言诗已完全成熟,并成为后世五言诗的典范。而上述文人五言诗明显学习和模仿的是民歌,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五言诗起源于汉代民歌。此后,五言诗不断发展,成为汉魏六朝诗歌的首要体式,甚至超过辞赋,代表了汉魏六朝文学的最高成就。以上论述参见姜先生的两部文学史论著和《诗学广论》,不详引。
但是,《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限于体例(按作家作品时间先后排列,无名氏作品附后),将汉代“古诗”和民歌均冠以“无名氏”而排列于汉诗之末。其中,收“古诗”十九首,又“古诗”七首,“苏李诗”七首,共33首,占入选汉诗64首的51.6%。又收汉乐府民歌和民间歌谣15首:《白头吟》、《怨歌行》、《饮马长城窟行》(青青河畔草)、《战城南》、《有所思》、《上邪》、《陌上桑》、《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古歌》(高田种小麦)、《古乐府》(兰草自然香)、《古绝句四首》、《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占比为23.4%。这15首民歌,除《战城南》《有所思》《上邪》三首外,均为五言诗。我们绝不能因为上列48首“古诗”和民歌置于汉诗之末,而忽略其源头或典范的意义。姜选于此48首“古诗”和民歌之小传、解题和评说,表达了同其文学史论著和文体学论著一样的观点,且更为丰富和具体。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选东汉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10首:秦嘉《留郡赠妇诗》三首、赵壹《疾邪诗》二首、孔融《杂诗》二首、辛延年《羽林郎》一首、宋子侯《董娇娆》一首、蔡琰《悲愤诗》一首,占比15.6%。它们大致呈现出民间五言诗向文人成熟五言诗发展的轨迹,共同托举起五言诗的巅峰和典范——“古诗”。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选了6首汉代有主名的楚歌(或具有楚歌特征的诗歌):项籍《垓下歌》、刘邦《大风歌》、刘彻《秋风辞》、刘细君《悲愁歌》、梁鸿《五噫歌》、张衡《四愁诗》,冠于汉代主名五言诗、佚名五言诗和乐府民歌之前。如果说乐府民歌是五言诗的直接源头,那么楚地民歌似可以说是五言诗的间接源头。汉初上层统治者学习楚地民歌而推动民间楚歌发展为文人楚歌,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此后文人楚歌五、七言句增多,最后汇入五、七言诗的发展大潮中了。
五言诗在汉代产生和成熟后,魏晋南北朝仍继续发展,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不详论。总之,姜书阁先生的多部古诗学论著,互为补充,共同深刻揭示了五言诗与各体诗歌的互动及自身发展的全过程,具有强烈的辨体意识。
二
姜书阁古诗学作家论具有强烈的优劣意识。文体论离不开作家论,后者是前者的坐标点,具有标识和定位的意义。姜先生三部分论著均有丰富的作家论思想,且先后发展、互为补充,构成作家论之体系。我们仍以《汉魏六朝诗三百首》为讨论的中心,而以其文学史著作等为佐证。作家优劣的批评方法有定量和定性两种,而以定性批评为主,定量批评为辅。定量批评主要是选录多寡,定性则为文字评说。优劣评说一般遵循三段论:一是综合评述或具体评述作家作品的思想性或艺术性,综合评述就姜选而言一般出现在小传或题解部分,具体评述则一般出现在选诗(往往是代表作)的评说部分;二是通过纵向比较或横向比较指明作家作品的创新性;三是由此确立作家的成就、地位、影响等。本节的目标是通过分析姜选的定量批评和定性批评勾连出主要作家排行榜,以揭示姜选的作家优劣论及其独特见解。因为同类型或同时代作家的可比性强,故此一排行榜具有同类型和同时代排行的特征。但也存在特出的作家跨类型或跨时代排名的情况。
就类型而言,汉魏六朝诗的作者有的是无名氏民歌、无名氏文人诗和有名氏文人诗三类,因性质不同,需分别排名。首先讨论无名氏民歌。姜先生极为重视民歌,认为是文人诗发展的原动力。姜选收录汉代民歌有15首之多(其中五言12首),与汉代有名氏诗16首(其中五言诗11首)相当,可见在五言诗发展的初期,民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代民歌不仅有源头的意义,其代表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姜先生基本认同“古今第一长诗”和“长诗之圣”的定位。民歌此后仍有发展,姜选于魏代未收录民歌,晋代收录13首,占晋诗73首的17.8%,其代表作《西洲曲》“写一个女子对她的爱人的思忆”,“以自然优美的自然环境烘托出真挚而细腻的感情,有情景交融之妙”,其艺术特色“表现在回环相续,摇曳生姿上”。因此,它“标志着南朝乐府民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千余年来,长为选家所重,学诗者莫不熟诵焉”。其评说遵循思想论、艺术论、成就论、影响论等之逻辑线索而展开,虽为一作品而发,但其为南朝民歌代表作之一,即为民歌创作群体中优秀者所创作之诗歌,仍体现出其强烈的作家优劣意识。晋代民歌中《子夜歌》四首、《子夜四时歌》四首、《懊侬歌》二首共十首,均为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相似,如语言通俗、情感真挚、五言四句、男女恋歌、多谐音双关等,同《西洲曲》一起奠定了南朝民歌的基本特征,对此后的南朝民歌影响极大。由此可见,代表作代表作家(就民歌而言,则为民歌创作群体)的创作水平,那么代表作批评也是作家优劣批评的重要方法,其特点是由点及面。姜选于宋代选录民歌13首,占宋诗56首中的23.2%。均源于晋代吴声和西曲,体制、内容、艺术适相近似,如皆为五言四句,写男女相爱相思之词,多有双关谐音、借物取譬等艺术手法,热情深挚,语言浅近,是南朝民歌之通体,强化了南朝民歌之传统。齐、梁未选民歌,陈选1首,隋选1首。北朝选民歌8首,占北朝诗24首的33.3%。同南朝民歌相比,北朝民歌有了新的发展,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其代表作是《敕勒歌》和《木兰诗》。《敕勒歌》最具草原本色,可谓“民歌中的绝调”,“洵为千古不磨之名篇”,颇能体现北朝民歌雄伟奔放的气势和刚健质朴的风格。而代表北朝民歌最高成就的则是《木兰诗》,它虽经文人加工润色,但基本上保持着北朝民歌的特色。它的主题思想很明确,“反映人民对于战争的厌憎和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决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什么女英雄的赞歌”。而语言朴素自然,节奏鲜明,运用了反复吟咏与排比烘托的手法。因此,《木兰诗》“当视为北朝第一名篇”,与《孔雀东南飞》一起成为汉魏六朝南北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双璧。经过上述梳理,汉代民歌的最高代表是《孔雀东南飞》,北朝民歌的最高代表是《木兰诗》,南朝民歌的最高代表是《西洲曲》,三星辉映,群星闪烁,由此可以窥探民歌的总体艺术成就。
汉代无名氏文人诗均为五言诗,其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其实姜选所收《古诗》七首和《托名苏武李陵赠别诗》七首,风格与前者相近,则无名氏文人“古诗”共选录33首,可作整体而论。其占汉诗64首的51.6%,而汉代收录有名氏诗最多者为秦嘉的3首,可见,“古诗”的入选率绝高。公论亦如此,姜著也认为“古诗”抒发和表达了作者的真切情感和深刻思想,且具有相当普适性。而其艺术形式更是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和突破,如比兴手法、朴素语言、景物烘托、形象刻画等。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甚至认为是“五古”的最高典范。即给予了《古诗十九首》等“古诗”最高等级的评价。“古诗”取得如此高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充分汲取了民歌的养分,姜选认为“古诗”“正是文人诗的色彩,而又带有民间味”,它是“摹仿或学习民间歌谣(乐府)的”。无名氏文人“古诗”深刻影响了五言诗的发展。汉代以后无名氏文人诗不复名篇,未再选入。民歌往往经过无名氏文人的修饰和润色,则无名氏文人诗与无名氏民歌混而为一了。因此,汉代无名氏五言“古诗”是极为独特的现象,这也成就了其经典性和普适性。
有名氏文人诗,姜选于魏晋至隋每代都有收诗数量迥高同代诗人者,如魏代,曹植15首,阮籍14首,曹操9首;晋代,陶渊明22首,左思12首;宋代,鲍照18首,谢灵运9首;齐代,谢脁9首;北朝,庾信8首。据姜著评说,以上九家确为本时代诗人名列前茅者,也为汉至陈代名列前茅者,且无人能出其右,可谓一流诗人。魏诗中曹植当为第一,录诗最多,姜选小传认为“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都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曹操和阮籍何者在前,恐怕不能完全由选诗多寡论定。姜选往往于小传中说明作家作品存世数量,如曹操存诗24首,则入选率为37.5%;阮籍《咏怀诗》82首,则其入选率为17.1%。就入选率看,曹操高于阮籍。评说也是如此,于曹操诗,姜著认为它以旧题乐府写社会现实和个人情志,语言质朴简约,风格气韵沉雄,思想性和艺术性均极高,“开了建安诗人的新风气”,“不愧为魏诗之祖”。而于阮籍诗,姜著认为它是“继承‘建安风骨’优良传统的‘正始之音’的主要代表作品”。因此,就开创性而言,阮籍不能望曹操项背。姜著且对阮诗略有批评,认为他的诗开始完全脱离民歌,而成为纯粹的文人诗了。魏诗三甲即为曹植、曹操、阮籍。晋诗,陶渊明排第一位,不仅如此,姜著还认为他是魏晋南北朝诗歌第一人,仅为汉代“古诗”留出了一头之地。陶诗兴到自然,悠然意远,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契合,似未着力者,而有“质真”风格,独立挽回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雕琢、玄言、声病、宫体等颓风。晋诗第二则为左思,其代表作为《咏史》八首,姜选认为其诗“借古抒怀,鸣所不平,壮而不悲,最为名篇”。总之,左诗继承“建安风骨”,有“俯视千古”之气概,绝非注重形式之美的陆机、潘岳等诗人所可比拟,是太康文学也是西晋最有成就者。宋诗,成就最高者为鲍照,他是自汉魏七言诗产生以来第一位写出成熟七言诗的作家,而直到陈、隋才有继起者,可称为汉魏六朝七言诗第一人。又他的诗向汉魏民歌学习,不避险俗,反映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姜评为“陶渊明后第一人,而为南北朝最伟大的诗家”,地位同陶渊明一样超拔于时代之上。宋诗第二为谢灵运,姜选认为他“扭转东晋玄言诗风,开创了宋、齐山水诗派”,“极貌写物,穷力追新”,“自是晋宋一大家”。齐诗首席为谢朓,他继谢灵运之后写了不少清新秀逸的山水诗,而无其过分雕镂之弊,近于陶渊明之自然。他的五言小诗向南朝乐府民歌学习,刻画入微,意味深长,已开唐人绝句、律诗之端。梁、陈、隋,宫体诗盛行,轻靡柔媚,格调不高。北朝诗人中由南入北者,其诗风颇有新变,代表人物是庾信,他后期的诗由绮艳靡丽转为清新刚健,音节和谐,情调苍凉,凄切动人,开辟了诗界新境,为唐诗(尤其是律、绝、七古)之先驱。可谓“南北朝最后一位最有成就的大作家”。
以上所论是作家优劣大体与收录多寡相应之情形。但是收诗数量不多,且相差不大,选录多寡就难以反映作家优劣。更重要的是需依据评说,继续排名,于此也往往能见出姜先生的独到看法。汉诗,秦嘉3首,赵壹2首,但是,成就更高的为均收诗1首的蔡琰和张衡。蔡琰《悲愤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写实创作方法,是汉末最长也是最成功的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的完全成熟。其次是张衡,姜选小传云:“更重要的是他创立了最早的七言诗《四愁》四章和文人五言诗的早期重要作品《同声歌》,都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应该特予标举的。”魏诗三甲(曹植、曹操、阮籍)以下当数王粲,姜选小传认为 “《七哀》诗‘西京乱无象’一首亦为代表汉魏风骨的典范作品”,将“汉魏风骨”这一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为一首诗,点亮了读者的认识,见解颇为新颖。以代表作而论作家之成就、地位,这也是作家优劣论的重要方法。前论民歌是如此,此论王粲也是如此。姜选收录王粲诗3首,排名第四,实符“七子之冠冕”的地位。与王粲并列第四位的是曹丕,亦有三首诗歌入选,其小传力破“鄙直”旧说,认为:“他在形式上颇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自有‘清越’之致,无宁说这倒是他的优点。”而且,他的两首《燕歌行》,“情致委婉,音节美妙,为世所重”,是“最早的文人所作全篇完整的七言诗”,“具有一定的开拓性,对七言诗的形成有贡献”。可以说,姜先生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曹丕诗歌的文学史地位。可见姜先生古诗学论著并非人云亦云之作,而颇有自得之见。晋诗两雄(陶渊明、左思)以下,当数刘琨、郭璞,他们是西晋永嘉文学的代表。虽然,姜选仅收录刘琨诗二首,但其诗存世者就只有三首,而其中《答卢谌》乃为四言,因体例所限(原则上不收四言诗)而未选入,因此并不影响其晋诗第三人的地位。“他的诗写国家民族的危机,而抒发自己救亡济时之诚”,“悲凉酸楚”,“风格雄峻”。郭璞的诗,姜选收录4首,均为《游仙诗》,小传认为“其诗乃借游仙咏怀,并以曲折隐晦的方法反映现实,近于阮籍的《咏怀》”,颇有诗体创新之功。但他的诗“向往绝世遗俗,作离尘之想”,有消极性,“终不能上继建安、正始”,也比不上刘琨。其余西晋诗人,虽有好诗,但均不免雕琢之弊,略少雄健之气,则均在陶、左、刘、郭之下。即如古人盛称之陆机、潘岳,尚远不如张协,张诗“情与物会,非由心造”,是其高明之处。再以陆、潘而论,姜先生亦反传统之见,认为潘岳“《悼亡》三首感情深挚,凄哀动人,比陆机还高一筹”。宋诗二豪(鲍照、谢灵运)以下,则为颜延之,姜选收录4首。虽“颜谢”并称,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他远不如谢灵运。姜选意见则略有不同,其小传认为,颜诗“雕镂太甚,堆砌典故”,“艺术上自不及谢”,但“在思想上却又有与谢异趣而高于谢者”。他举了两个例子以作证明:一是颜延之与陶渊明为友,曾诔渊明,极称其品德之高;二是《五君咏》对“竹林七贤”中嵇、阮倍加赞扬,即可见其怀抱。以上为元嘉三大诗人,实际上也代表了刘宋诗歌的最高成就。
我们可以列出上文所述汉魏六朝连绵起伏的诗人“高峰”:无名氏“古诗”、曹操、曹植、阮籍、左思、刘琨、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等。而这些耸立的高峰其基石则为汉魏六朝民歌,《孔雀东南飞》《西洲曲》《木兰诗》《敕勒歌》等是它们的代表。汉魏六朝民歌是五言诗产生、发展、成熟、转变的源泉和动力。当然,基石与高峰之间还有庞大的山体:众多优秀诗人诗作,共同支撑起秀美的峰林。姜先生的作家论时有所得和创见,构建起其作家论之体系。
三
姜书阁古诗学的作品论具有强烈的审美意识。文体论和作家论离不开作品论,作品论是前两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姜先生的文学史论著当然富于作品之论,但限于篇幅和体例,难以全面、深入分析作品。其文体学论著,如《诗学广论》九篇中有两篇专论比兴手法和形象思维,分析了大量的作品,但均有特定的视角。姜先生古诗学的作品论主要还是体现在《汉魏六朝诗三百首》。此选体例主要有六:序言、选诗、小传、题解(即题注)、注释、评说。而评说是其精华,最能体现姜先生的审美意识、鉴赏心得和诗学思想。评说用语简洁,但并不面面俱到,而是点破诗心,引诗韵汩汩溢出,令读者击节叹赏。其评说中的作品论同作家论一样是兼重思想性和艺术性。因评说往往是击破一点,则或思想性,或艺术性,每诗多仅言其一。评说亦多有所本,而尤以沈德潜《古诗源》评点为最,有肯定,但也有阐发,甚至批评。今取其颇为自得者分析如下。
首先是论作品的思想性,又分两点。一是思想深刻。思想深刻主要源于批判现实。有批判官场的,如赵壹《疾邪诗》二首,姜选认为作者所抨击之奔竞世风“却一直延续于整个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意义”,趋炎附势是人性之弱点,世风之痼疾,至今亦难根除。其思想之深刻性和普遍性不容置疑。有批判战争的,如汉乐府民歌《战城南》,姜选评云:“极写战争的残酷、战地的凄惨与连年战争的无休无止,深刻地反映出人民厌战的情绪。”有批判行役的,如《古诗十九首》(去者日以疏),姜选解说诗意云:“久客异乡,年已老大,偶过墟墓,感叹人生无常、沧海桑田,不禁哀伤思归。”评论曰:“这是一个失意者的作品,所表达的感情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代表性。”失意者悲叹的是王事靡盬而“欲归道无因”,其无法破解的困境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代表性。
思想深刻还源于政治抱负,如《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姜选认为是劝人及早立身,勿贻后悔,因此“这首诗是《十九首》中思想内容比较积极的一首”。诗中“立身苦不早”“荣名以为宝”等数语确已成为后世励志的格言了。又如曹操《短歌行》,姜选评云:“说者往往将此篇分为数段就其字面逐段理解,谓叹息时光易逝,慨慷忧思,借酒销愁,怀念朋友,感伤乱离,思得贤才,建功立业云云。果尔,杂乱无章,何以成为名篇?其实全篇只是一意,即:‘人生几何’,‘去日苦多’,‘悠悠我心’,‘忧从中来’,‘越陌度阡’,‘何枝可依’,‘忧思’‘沉吟’到最后,唯有广揽贤才,共图大业而已。”曹操之豪雄形象借此评而树立,此评又正可体现其点破诗心之特点。
思想深刻还源于人生态度。关于陶渊明《和郭主簿》末二句“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究之白云与古何涉,则颇难索解”,众说纷纭,姜选评论曰:“其实,诸家解说皆为辞费,但得其悠然意远,便已足矣,何烦更细加剖析?”“悠然意远”正是陶渊明自然人生观的反映。又如陶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姜选评论云:“诗从‘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说起,而以长此躬耕结束,具见认理真而行事果。”由此活脱出真隐士的内心世界。
二是情感真挚。上文所论思想深刻者,往往寓有深情。同样,情感真挚者,其思想也不无深刻。如曹操《薤露》,姜选评曰:“指斥何进沐猴而冠、董卓荡覆帝基,忿怒悲伤,若不可遏。这不仅是‘汉末实录’,且已表现了诗人闵乱之情与救世之志。”情志实难区别。但因各有侧重,则予分说。古诗有的是感叹身世。如甄后《塘上行》,由“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可知,此诗大概作于被废之时,姜选评曰:“淋漓恻伤,情至之语。”当得其情。
有的是感叹爱情,此类尤多。姜选评《有所思》曰:“这是一首以大胆泼辣而热烈多情的女子的内心活动写成的情诗。”又评《上邪》:“这首诗和上首一样是热烈多情女子的爱情诗。”“上首”即指《有所思》。以上是欢快的情诗,但更多的是夫妇分离或永诀的悲恸,如评旧题苏武《诗》四首其二曰:“以征夫别妻论,这诗确是极其沉痛。开头说夫妻恩爱,正为即将远别增悲。……末数句实在是强抑悲愁,劝慰爱妻,然而一说到‘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吾知其必哽咽不能再吐一语矣。”还原当时情境,颇能诱发读者之感同身受。又如评潘岳《悼亡诗》(荏苒冬春谢)曰:“安仁所长固在抒情,其悼亡之作真挚动人,千载推重。”姜著正以此组诗而力压陆机。
有的是感叹亲情。如孔融《杂诗》二首其二(远送新行客),姜选先解说其诗意云:“诗先言想看爱子,却被告知爱子已亡,埋在西北方墟丘之上。去瞧瞧孤坟吧,但那又能怎样呢?‘生时不知父,死后知我谁’呢!”然后评论曰:“真是凄怆已极,令人堕泪。”悲莫悲夫丧子之恸,何况此子还从未见面呢。
有的是感叹友情。如评《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云:“知音难遇,千古同悲。”又如旧题苏武《诗》四首其一,姜选评说首先认同沈德潜“别兄弟”之说,然后评其“昔者常相近,邈若胡与秦。唯念当乖离,恩情日以新”四句云:“写亲人离别时的真实情感,自来诗人很少写出此境。”抉发亲人离别前后之变化甚细微入情。
有的是感叹苍生。如评梁鸿《五噫歌》曰:“嗟叹沉郁,格调苍劲,前无所承,后莫能继。”“沉郁”“苍劲”的风格当缘于作者对民生“未央”之“劬劳”的深挚悲叹,因此姜选给予其极高评价。又如评《古诗》(十五从军征)云:“极凄凉、极惨痛。道尽战争与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残酷灾难。不独当事者泪落沾衣,两千年后的今人读之,亦不免为之泫然。”点提出此诗强烈的反战情绪。又如傅玄《豫章行·苦相篇》,姜选评曰:“说尽封建社会女子一生的痛苦。然而控诉无门,唯有忍受而已。”这位女子伤痛具有普遍性,是思想深刻和情感真挚的交融。
可见,姜评特重作品的情感要素,其共同的要求是真情实感,发自肺腑,感动人心。情感真挚和思想深刻一样是判定作品审美性的必要标准。
其次是论作品的艺术性。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技巧繁杂,但是,古典诗歌最为重要、也最为核心的是比兴手法。姜先生就认为“比、兴之为诗不能不用的两法”。本节仅论比兴以觇姜先生作品论之艺术论。比兴可分比、兴、比兴三种艺术手法,此三种艺术手法可细分出多种手法,统称为比兴手法。
比法易明,不论。先谈兴法。兴既为发端,又或有喻义。而有喻之兴,“在诗中最为重要”,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喻义,而这喻义又是隐喻,比较婉曲,用之于讽,耐人寻味。因此,姜选特别重视对汉魏六朝诗兴法及其喻义的阐发和鉴赏。如《古歌》五言四句,首二句“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沈德潜评曰:“兴意若相关,若不相关,所以为妙。”姜评不完全认同此说,以为此诗之兴既是发端,喻意也显然:“前两句为喻,后两句为主体。男儿远走他乡,有如种小麦在高岗上,如何能不枯槁憔悴、结出果实来?此至为分明。”而认为沈说“未免是故作深解”。又如汉乐府《白头吟》起二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也是兴法,姜选评曰:“诗的开端两句完全可以视为对这女子精神面貌的概括。”则揭示其譬喻之意。此诗第十三、十四句“竹竿何嫋嫋,鱼尾何簁簁”不在首部,但也是兴法,即兴起其下两句“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此为特例,姜选并未放过,于“竹竿”两句注释云:“此二句喻男子爱情不牢固,见异思迁。”则揭示其喻义。又汉乐府民歌《艳歌行》首二句“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姜选评曰:“开头两句兴辞,兴亦有比意。”此二句注释又曰:“以燕起兴,引出兄弟流落他乡,来去不由己,不如堂前燕的下文。”解明了喻义。又汉乐府民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首两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姜选注释云:“乃兴全诗”,“正是‘三百篇’兴诗的遗制,也是几千年来直到今天还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并继续使用的民歌开篇方法”。由上述各例可知,自《诗经·国风》以后,兴法传统在民歌中承续不绝,是其诗歌艺术性的重要体现。
民歌的兴法后为文人所学习和模仿,如《古诗十九首》第二首首二句“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第三首首二句“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第八首首二句“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均为兴法。“冉冉”两句,姜选注释云:“首二句用孤竹结根泰山起兴,暗喻女子欲嫁一个可靠丈夫的心愿。”揭示其喻义。曹植最善兴和比兴之法,下文论其比兴,此论兴法,仅举一例,如其《野田黄雀行》首二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与下文并无直接联系,姜先生认为“也是兴辞”。汉魏诗歌多用兴法,不详论。因此,姜先生认为这也是构成“汉魏风骨”的重要因素。晋、宋以后,总体来说,兴法少见了。但是左思和鲍照则是例外,如左思《咏史》八首其二首四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既为发端,其喻义又显然指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句意。其第八首首二句“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也是兴而有比。因此,从兴法来看,也可证明左诗上承“慷慨多气”的“汉魏风骨”。鲍照《代放歌行》首二句“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姜选注云:“首二句以蓼虫食苦蓼而不食葵堇起兴,引出下文。”下二句为:“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显然与首二句意义关联,则此诗首二句也是兴而有比。又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四首二句“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与下二句“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意义关联,亦是兴法。又《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八首四句“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阳春妖冶二三月,从风簸荡落西家”与下二句“西家思妇见悲惋,零泪沾衣抚心叹”相关联,当为兴法,且颇有创新。又《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九首二句“锉蘗染黄丝,黄丝历乱不可治”也是兴法。沈德潜评鲍诗:“抗音吐怀,每成亮节。其高处远轶机、云,上追操、植。”善于运用兴法也许是做出上述评价的重要依据。可以说,“古诗”、曹植、左思、鲍照之所以成其时代诗歌的最高代表,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下文续有论述)是重要的原因。
再说比兴手法。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讽兼比兴”,即谓“《离骚》诸言草木,比物托事,二者兼而有之”,将比、兴合一了。比兴手法在后世衍生出多种形态,若以诗歌之整篇或整章而论,有比体诗、寓言诗、象征诗等;比体诗又可分为拟物诗、拟人诗,而尤以拟物诗为多。甚至情景交融、景意交融等都可归入比兴手法之列。正如姜先生所云:“就景中写意,托物以寓情,这也便是兴。”推而广之,凡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者,即有比兴精神,可称比兴手法。比兴的特点同样在于含蓄委婉,耐人寻味,富于诗意。晋宋以后,纯粹的兴法减少了,但扩展化的比兴往往而在。可以说,兴和比兴成为汉魏六朝诗歌最重要的艺术手法。姜选同样重视对比兴这一诗艺的审美。
汉魏六朝文人有学习和模仿《离骚》的比兴手法者。如张衡《四愁诗》,沈德潜评曰:“心烦纡郁,低回情深,风骚之变格也。”但何谓“风骚之变格”?似在于“纡郁”“低徊”,但何以“纡郁”“低徊”呢?沈氏并未言明。姜先生评说先引《文选》卷二十九录此诗之序云:“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然后论断云:“其序虽非张衡所作,但颇能得衡作之本心。”亦未明言,但实已肯定此诗系运用所引诗序前三句所言之比兴手法而寓以后三句所言比兴之意。“纡郁”“低徊”指向比兴手法,“心烦”“情深”则指向比兴之意,这正是“风骚之变格”。点破比兴手法,比兴之意则易明,比兴手法显然是此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
其实比兴手法亦源于民歌。如《古绝句》四首其四:“南山一树桂,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庆不相忘。”全诗写鸳鸯,是拟人比体诗。姜选评曰:“语言和取喻之物都是古今民歌所习用者,足见古绝句便是古代歌谣,是长期在民间口耳相传的优秀通俗作品。”实认为《古绝句》是运用了比兴手法的歌谣。又如《古乐府》:“兰草自然香,生于大道旁。十月要镰起,并在束薪中。”全诗咏兰花。姜选评曰:“言才智之士处于混浊之地,不为世用,终与草木同朽。短短五言四句,寓言至为著明。”点明其通篇为拟物之比体诗。又如《古诗》(四坐且莫喧),姜选论曰:“诗的开头三句完全是歌唱艺人开场白的口吻,可见这诗实系乐府民歌。”推测此诗即为乐府民歌。虽难论定,但其与民歌之关系显然。姜选解说其诗意云:“此诗明写富贵人家在精雕细镂的铜炉里烧着熏香,香风入怀,四座赞叹。但香风不能持久,转瞬散尽,白白糟蹋许多香草。”论断其主旨云:“这实是比喻世人追求浮名,徒耗精力,终无益处。”全诗写铜炉熏香,亦拟人之比体诗。因此诗仅末二句“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影射主旨,颇为深隐,经姜评提点,才豁然贯通。
民歌之比体诗后为文人所研习,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全篇是以天上牵牛、织女离别之情比兴地上夫妇离别之情,也创新了比兴手法。姜评曰“无疑也是拟乐府民歌的佳篇”,则揭示其比兴手法亦源于民歌。又如论刘桢《赠从弟》曰:“全用比体,亦赞亦劝。赠诗佳构,可谓独创一格。”因其以比体赠答而获致激赞。又如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也是全篇用比体,“将自己比作西北的一片浮云,不由自主地被暴风吹到东南吴会之地”,以此表达言外之“无穷悲感”。汉魏六朝诗人中曹植最通比兴之法,如其《野田黄雀行》全篇用比,由末二句“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可知为拟人法,《文心雕龙·隐秀》赞此诗“格高才劲”“长于讽谕”,姜选评曰:“两句话已尽其妙。”此两句不仅可赞此诗,也可移于称赞曹植所有的比兴体诗。又姜选评其《美女篇》曰:“美女以喻君子,亦植以自喻也。以如此盛德美才而不获展布自效,盛年一过,何可追攀?此所以中夜起长叹也!论者或谓此篇以华缛胜,实则极写美女形质服饰之艳闲动人,正所以言君子品节之可慕也。”虽有承袭前人之处,但姜选所论更为细密精确。又《七哀诗》(明月照高楼)是以思妇自比,姜选评曰:“明写闺怨,实寓讽君。……性情之作,不须华饰,自成建安绝唱。”评价极高。又《白马篇》则是以游侠自比,遂自然而发出末二句“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之誓言,悲壮莫名。又《杂诗》(转蓬离本根)是自比转蓬,《杂诗》(南国有佳人)则亦以美人自比。《七步诗》则是“托喻煮豆”,可谓“事近义切,本乎至性,词质理达”。可见,曹植比体诗比比皆是,形式多样,有以人比物者,有以物比人者,有以人比人者,且艺术成就极高,不愧为“汉魏风骨”之最高代表。其次是鲍照善用比兴之法,如其《拟行路难》(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全篇咏铜香炉,是拟人之比体诗,姜选评曰:“此诗既是后世闺怨诗所宗,亦是仕官失意者常所取拟。”可知此诗艺术之高,影响之大。《梅花落》全篇咏梅花,姜选评曰“讽意可取”。鲍照《拟古》八首其三以游侠自比,全仿曹植《白马篇》,姜选评曰:“言幽并少年骑射之精、意气之壮。隐示自己有守郡防边、为国立功之志。诗句俊逸奇警,与内容相称。”若以比兴而论,鲍照就不愧为南北朝诗第一人。姜选评析比兴体诗者还有不少,不详论。可见,比兴手法是对兴法的发展,兴诗虽有减少,但比兴不乏其作。因此,兴和比兴可以说成了好诗的标志。
景而与情、志交融者,若就广义者而言,也是比兴手法。如旧题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其一,沈德潜评曰:“一片化机,不关人力。此五言诗之祖也。”极力推许,但所论过虚,难得要领。姜选于此诗中“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四句注释云:“以上四句以风吹浮云喻人生多变、身不由己。”又有“触景伤情”之评。则读者自可意会此四句及此诗之妙处。此四句浮云失所之景物与送友远行之离情化成一片,似不关人力,须玩味乃识,正可谓比兴之精神,而为古诗之至境。又如张协《杂诗》(秋夜凉风起),全篇十四句,前十二句写景,末二句抒情。姜选评曰:“写秋夜思妇感时怀远之情,从室内到室外,动物有蜻蛚、飞蛾、蜘蛛;植物有萋绿的庭草和依墙的青苔,都给人以凄凉寂寞之感。故结曰‘感物多所怀,沉忧结心曲’,盖情与物会,非由心造也。”全诗以写景为主,但无非抒情,非如后世模山范水者可比,所以可泛称为比兴手法。姜著即由此诗之评而移评张诗总体风格,遂越潘、陆而上之。又评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云:“题曰‘玩月’,自当有写景语,前半篇便是。然而景不徒写,必以寓情,……弹琴唱曲,饮酒玩月,聊以自遣耳。”由此评可知本诗颇有比兴之精神,也可归于比兴之列。
最后是综合评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自难分隔,上文论述比兴手法,往往关联比兴之意,也是综合评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但重点还是论述艺术性。本小节所论与思想性相关联的艺术性则将比兴除外,仅略举数例,以见思想性与艺术性之交融乃为姜选评说之主流。如姜选评刘细君《悲愁歌》云:“真情实感,不假雕饰,便是千古至文。”则前两句一句评思想性,一句评艺术性,两者交融而不可分隔,第三句则给予了此诗成就最高的评价。又如评《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先解说诗意云:“这首诗是写思妇怀念久别远人的。短短八句,却从庭中奇树说起,由树及叶,由叶及花,再说折花将以赠给所思的远人。然而路远不可能送达,无可奈何,只有罢了。其实一枝花有什么值得远赠的呢?不过是因离别太久而发痴想吧。”然后引陆时雍《古诗镜》语以论断:“诚哉,‘深衷浅貌,短语长情’,在《十九首》中亦是不可多得者。”可知,全诗八句乃“浅貌”“短语”,但念兹在兹的却是“深衷”“长情”,是以浅近语言、习见物象、平常行为、烦乱思绪表达真挚情感,思想情感与艺术形式深度切合,所以是“不可多得者”。又《古绝句》四首其三云:“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别。”姜选一句评曰:“一喻到底,语简意切。”也是既评艺术又评内容,并形成因果之关系。又如评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西京乱无象)曰:“《七哀》闵乱,一读便知。中间特写饥妇弃子一段,顿使读者为之落泪。此古所谓举重赅轻之法,亦即今所谓典型概括之道,不可仅视为一种小小的艺术手段。”典型概括之法造成了哀恸落泪之艺术效果,可谓一语中的。又评陶渊明《读山海经》曰:“盖在于心有所会,自然流出,平和安雅,不费力气,更无半点斧凿痕,故能入妙也。”欲表达自然入化之哲思,必借自然入化之语言。评《子夜歌》(怜欢好情怀):“多用谐音、双关语辞,是民歌的特征之一,而情歌尤甚。把要说又不好说的字眼改用隐语道出,往往愈见多情。”用谐音双关则愈见多情,此评可当南朝民歌之通论。再举数例,不必一一解析。评潘岳《悼亡诗》(皎皎窗中月)曰:“篇中三用顶针续麻的艺术手法,益增其缠绵重叠、回肠荡气的效果。”评左思《娇女诗》曰:“写娇女娇憨之态,极尽形容。妙在观察入微,造语恰切,而绝无雕饰,真白描绝艺也。”评陶渊明《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云:“而‘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二句只用两对叠字,遂使村里景色顿入化境,洵千古妙文。”均是艺术性、思想性一一对应而论。
《汉魏六朝诗三百首》的评说继承的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评点方法,有强烈的审美意识,言简意赅,极少旁骛,直捣黄龙。当然与小传、注释的配合也让评说简省了不少笔墨,这样更好地发挥了评说一语道破的审美效果。评说于会心鉴赏中也往往有引申性和提升性的议论,表达出作者关于古诗学的学术观点,可为其学术专著之补充。其中最有价值当为比兴观。
总之,姜书阁先生首先是一位文学史家,其次是文体学家。经过上述的论证,他还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他的古诗学就是上述三者的结合体。会通意识是姜先生学术思想的底色和根基,必然贯穿于其古诗学之文体论、作家论、作品论,而有强烈和鲜明的辨体意识和思想、优劣意识和思想、审美意识和思想。因其文学史著作、文体学著作并非专论古诗学,《汉魏六朝诗三百首》则可谓姜先生古诗学的代表和集成之作。因此,姜先生古诗学自有其特色,即审美性、批评性。文学批评当会于心,得于见,有感而发。可以说,姜先生的古诗学是会通与会心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