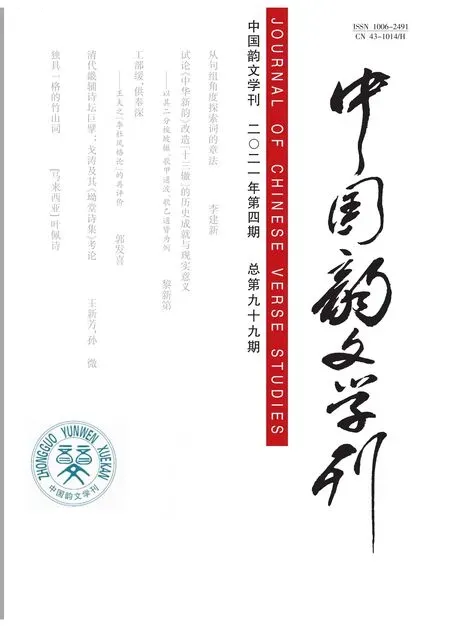工部缓,供奉深
——王夫之“李杜风格论”的再评价
郭发喜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李白和杜甫是活跃在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二人作品取材多样,风格各异,共同代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最高成就。中唐以还,李、杜诗歌作品的优劣高下成为唐诗研究领域的关注度最高的争论之一。尊杜贬李者有之,扬李抑杜有之,二家并称者亦有之。王夫之显然属于扬李抑杜之列,其《唐诗评选》卷一评《远别离》,认为“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供奉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李、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必提,王夫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春秋笔法”褒贬二人讥时诗风。“工部缓,供奉深”应当作何理解?李、杜讥时诗风究竟如何对立?目前,这些问题尚未有学者讨论,今试为抛砖引玉,以待方家。
一 “工部缓,供奉深”之原义考释
“工部缓,供奉深”一语,源出自王夫之评李白《远别离》诗下,原诗云:
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言尧幽囚,舜野死。九嶷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痛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此诗亦见殷璠所编《河岳英灵集》卷上,大抵作于安史乱前。诗寄兴深远,以娥皇、女英二妃和舜帝生离死别之事,表现远别离的悲哀。论者以其诗有影射时政之意,如清人陈沆《诗比兴笺》曾云:“《长恨歌》千言,不及《远别离》一曲。”王夫之将此诗为“供奉深”的代表作,但“深”字具体的含义,却并未展开论述。
不过,在评杜甫《野望》诗时,王夫之又提及《远别离》,注云:“诗有必有影射而作者,如供奉《远别离》,使无所为,则成呓语。”按照此处解释,“深”字即“有影射而作”之意。
在中国古代文论语境中,“深”字通常可作三解。一是见识、意义或感情的深刻、深远、深厚,如钟嵘《诗品》评应璩诗,称其“祖袭魏文,善为古语,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刘勰《文心雕龙》所谓“阮旨遥深”等。二是指程度上的大或高,如钟嵘《诗品》评班婕妤《团扇》诗,称其“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刘勰《文心雕龙》评曹植《魏德赋》,讽其“劳深绩寡,飙焰缺焉”等。三是精通、善于或擅长某种文学题材、风格或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谓“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皎然《诗式》所谓“诗有四深”等。
联系《远别离》“有影射而作”的特点,则王夫之笔下之“深”,意应稍近于“雅意深笃”与“阮旨遥深”之类,指李诗寄兴深微,含蓄蕴藉。回到“工部缓,供奉深”的上下语境中,“缓”字对应“工部讥时语开口便见”,而李诗“有影射而作”则正是“供奉则不然”的绝佳注脚。如此,便可以解释王夫之所谓李、杜诗风对立的原本含义。
然而,新的问题再次出现:如果“缓”指杜诗题旨“开口便见”,“深”指李诗“有影射而作”,那么王夫之为何不直接用“工部浅”与“供奉深”相对应呢?这样岂不更加准确?另外,王夫之评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扁舟欲往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句时,又注云:“‘杳杳’句住得好,于急故缓。”“缓”字在此处,并不作“浅”解,而是与“急”相对,指节奏迂缓。如此看来,“工部缓”应当还有其他含义。
从字面直接破译“缓”字确有一定困难,王夫之于老杜此类诗歌之下,正好有与“缓”字本意相近的批注。如评《新婚别》,注云:
《出塞》《三别》以今事为乐府,以乐府传时事,胎骨从曹子桓来。意韵婉切,其或伤于烦缛,而至竟与白香山有雅俗之别。当于其开合生活求之。
再如评《无家别》,注云:
《三别》皆一直下,唯此尤为平净。《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崧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邪!
《出塞》与“三别”等诗,正是杜甫讥时诗的典型代表。从上引批注可以看出,王夫之对这些作品颇有微词,因其“伤于烦缛”,不够“平净”,且“尽有可删者”,使读者有“言有余则气不足”的观感。
可见,王夫之认为“缓”字应至少同时包含“浅”和“繁”两层涵义。他所谓的“工部缓,供奉深”,一则指杜诗用事“开口便见”,浅显直露,不及李诗“有影射而作”,委婉含蓄;另外则指杜诗语言“伤于烦缛”,思力迟缓,不及李诗言辞省净,“深于义类”。
应当承认,王夫之的看法在整体上大致符合李、杜讥时诗的面貌,“工部缓”与“供奉深”也比较准确地概括出李、杜此类诗歌的特点。但是,这个观点不够全面,大有可商榷之处。
首先,李白讥时诗并非皆“影射而作”,亦有大量“开口便见”之作。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数句;再如《古风其十五》中“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等句,皆直指时政之弊,无所回避。所以,李、杜都有“开口便见”的特点,只指责杜诗,显然有失公允。
其次,杜甫讥时诗并非不能达到类似“供奉深”的艺术效果,如《曲江对雨》中“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等句,以“龙武新军”“芙蓉别殿”之景暗讽玄宗、肃宗父子失和之事,用“金钱会”典故,委曲自然,不显突兀,契合整体诗境,《杜诗详注》评其“叙时事处,不露痕迹。忆上皇处,不犯忌讳”。可谓“有影射而作”,绝非“开口便见”。上元二年(761)九月,肃宗“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杜甫感于此事,作《石犀行》。此诗表面以“今年灌口损户口”的事实,强调秦太守李冰作石犀厌水精终于事无补,实则暗讽肃宗群臣“黩礼不经”,有违“先王正道”,亦属“有影射而作”,可谓“工部深”的代表。
所以,杜甫并非不能达到“供奉深”的境界,李白也并非没有“讥时语开口便见”的作品。王夫之“工部缓,供奉深”的评价,虽然大体符合李、杜讥时诗的特点,但是这一概括,并不完全正确。
王夫之之所以会提出“工部缓,供奉深”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扬李抑杜的重要理论支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明代诗坛风气的影响。中唐之时,李、杜并称,然以诗歌传唱度和接受度而言,则李在杜前;宋代而后,风评骤变,杜甫被时人尊为“江西诗派”之祖,推崇备至,李白则广受贬低和批评;至于明代,前后七子等标举“诗必盛唐”,李、杜两家平分秋色,各有拥趸,彼此常展开激烈的论争。针对当时诗坛上宗杜学杜的种种弊病,王夫之对杜甫及杜诗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杜甫的负面评价,如讥讽杜甫“摆忠孝为局面”,“装名理为腔壳”,多“门面摊子句”等,“工部缓,供奉深”也是其中一例。虽然王夫之的评价不够全面,但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读者应当回到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下,对这个观点进行客观评价。
二 “工部缓”与“供奉深”的对立统一
中国诗歌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如《诗经》中的《七月》《氓》,汉乐府《东门行》《陌上桑》,左思《咏史诗》,鲍照《拟行路难》等,皆为讥时之作。这些经典之作,或“缓”或“深”,或既“缓”又“深”,都深刻地反映和揭示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此,并不能将“缓”或“深”作为评判诗歌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工部缓,供奉深”是王夫之对李、杜讥时诗风格的分别概括,在整体上也大致符合李杜讥时诗风的面貌,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诗歌表现方式,“缓”和“深”并无高下优劣之别。
明清以来,杜诗的主要风格被普遍概括为“沉郁顿挫”。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则进一步解释道:“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受时代因素的局限,王夫之只关注到杜诗用事直露、音节顿挫的外在特点,在有意或无意中忽略了杜诗思力深邃、悲慨沉郁的精神特质。然而,学者却不能因此苛责古人。实际上,直至清代以后,学者才广泛用“沉郁顿挫”四字形容杜诗的主要风格。对于杜诗风格的体认,从“工部缓”到“沉郁顿挫”,经历了传统两种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交锋。从后世的传播和影响来看,显然后者更加全面且深入人心。所以,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讨论“工部缓”,还应该赋予其“沉郁”的内涵。而“沉郁”者,即“思之深”也。
王夫之所谓“供奉深”,不仅指李诗因“有影射而作”的特点,同时也有构思深邃的特质。他曾评李白《长相思》云:“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一以为风度,一以为淋漓,呜呼,观止矣。”其中“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正是诗人“思之深”的写照。他评《登高丘而望远海》又说“后人称杜陵为诗史,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内”,也是称赞李诗构思深刻。从杜甫讥时诗的创作来看,“工部缓”也具备同样的特点。杜诗之“沉郁顿挫”,不唯体现在音节“顿挫”之“法”,即“表达方式上的波澜起伏、反复低回”,更重要的是表现诗人“沉郁”之“意”,即“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杜诗音节“顿挫”之“缓”,只是诗人为表现“沉郁”之“意”而惯用的艺术手法,不能将其作为攻击杜不如李的依据。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缓”也能“深”。
首先,李、杜都有“缓”而“思之深”的诗歌。除却上文提到李、杜作品之外,再比如二人同样有描写战争题材的讥时诗。开元天宝年间,朝廷征伐无度,数起边战,百姓深受其苦,在表现战争的残酷时,李白《战城南》有“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之语;杜甫《兵车行》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之句。李、杜这两首反战诗,主题鲜明,叙述和议论都比较详细,丝毫没有“影射而作”的意味,句句都是“开口便见”,最终都深刻地反映出反对不义之战的主题。同样的还有二人反映安史之乱时,哥舒翰潼关惨败之事的作品。如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诗人以沉痛的口吻历叙当时“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函关壮帝居,国命悬哥舒。长戟三十万,开门纳凶渠。公卿如犬羊,忠谠醢与菹”的惨象;杜甫《潼关吏》中也有“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的悲呼,此二诗皆笔触大胆,直抒心中悲愤,令人触目惊心,印象深刻,竟似出自一人之手。
其次,李、杜都有“深”而“思之深”的作品。安史之乱时,李白目睹肃宗兄弟手足相残,杜甫则耿耿于玄宗晚年落魄失位,故对当时朝政皆有讥讽。如李白《上留田行》中“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等句,用“田真兄弟”和好如初的典故,暗讽肃宗兄弟不相容,以至刀兵相见之事;其《树中草》亦以寓言故事的形式,感叹肃宗兄弟“如何同枝叶,各自有枯荣”的悲剧。杜甫《石笋行》则借益州城西门石笋之态,暗讽肃宗纵容李辅国等奸佞小人欺凌上皇,批判当时“政化错迕失大体”,痛斥群臣“坐看倾危受厚恩”;其《杜鹃行》中“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等句,则以“蜀天子”典故暗指玄宗失位之事,讽肃宗不孝、群臣不忠。以上诸诗,皆“有影射而作”,用事委曲含蓄,笔锋犀利,议论深刻。
总之,“工部缓”和“供奉深”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无高下之分。“工部缓”亦有深的内涵,受制于时代因素的局限,王夫之只注意到杜诗音节“顿挫”之“缓”,忽视了其思想“沉郁”的一面。“工部缓”与“供奉深”固然在艺术效果呈现上有所不同,但相互之间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存在着一定共性,统一于“思之深”。
三 “工部缓”与“供奉深”的诗歌史分野
王夫之所提出的“工部缓,供奉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杜作品的特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启发意义。从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说,“缓”和“深”不仅存在于李、杜诗歌之中,而且在其他诗人的讥时作品中也有广泛体现。同时,李白、杜甫作为诗歌史上的关键人物,“工部缓”和“供奉深”还深刻揭示了古典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分野问题。
中国最早的讥时诗应属《诗经》中的“变风变雅”。西周末期,王室衰微,礼崩乐坏,“颂美”不再是公卿列士献诗的主流。针对社会的丑恶现象,部分诗人一改先前温柔敦厚的心态,其诗直斥时政,“讥时语开口便见”,如《十月之交》《民劳》《板》《荡》。这些讥时诗,用事立意皆无所顾忌,多以“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抒发愤懑,可谓“缓”也。另一些诗人虽不出恶言,但却指桑骂槐,用嘲讽挖苦的方式抨击执政者,如《新台》《墙有茨》《鹑之奔奔》等。这些诗常用比兴,多“影射而作”,用事曲折隐约,主题深刻重大,可称为“深”。可见,王夫之所谓的“缓”和“深”除了内涵的差异,同时也分别指代“赋”与“比兴”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
杜甫晚年“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之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其中尤以“三吏”“三别”等讥时诗最为时人所称道。杜诗“推见之隐,殆无遗事”的诗史性质,决定了诗人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会更加偏重“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不过,正如钟嵘《诗品》所说:“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读者之所以会形成“工部缓”的印象,其原因正在于杜诗虽未专用赋体,但其致力于叙事抒情毫发毕现,不免会给人以“意浮文散,文无止泊”的观感,即王夫之所谓“工部缓”也。
与杜甫不同,李白同类诗多用比兴,务在寄兴深微。又因他天才杰出,故虽“专用比兴”,亦无钟嵘所谓“意深则词踬”之患。王夫之给李白以“供奉深”的评语,主要是由于其独特的风格追求所决定的。李白承陈子昂之后,以兴复风骚传统和建安风骨为己任,他曾直斥建安以来的作品“绮丽不足珍”,又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为了实现这种文学理想,李白不仅作有《古风》五十九首,同时还经常宣扬自己的创作体会,他“常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种诗歌思想与杜甫截然不类,故而有“工部缓,供奉深”之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工部缓,供奉深”的评价,也涉及诗歌发展史的分野问题。如上所论,李、杜皆有“思之深”的特点,杜甫并非不能达到“供奉深”的艺术境地。作为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杜甫诗歌风格多样,牢笼百家,正如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所述,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其讥时诗之所以会形成“缓”的主导风格,主要是因为他在继承李白等诗人的前提下,对诗歌表达方式有自觉的取舍和侧重。
实际上,杜诗不仅异于李白,即便与其所师法所有前代诗人相比,其风格也有根本性不同。在杜甫之前,诗歌被赋予了一种神性,儒家认为其不仅具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治功用,甚至还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之效。因此,历来诗人诗兴之感发者,多是君国政治、王化民风等严肃庄重之事。《诗经》而后,屈原《离骚》重在规谏,其诗怨以刺;汉赋之所作,意在劝百讽一;三曹七子、竹林七贤,其诗兴所发都偏于军国大事和群体命运;至于六朝,诗坛虽整体朝着浮靡方向发展,更加重视声律和技巧,但是《诗经》以来的“言志”和“兴观群怨”传统,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唐代以来,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的诗坛革新者,高举“复古”旗帜,在继承汉魏六朝题材发展和技巧革新的基础上,使传统诗歌创作逐渐进入繁荣期。盛唐之时,诗坛名家辈出,先代“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诗教理想最终得以实现。然而,这种建筑在开元天宝盛世之上的诗坛繁荣,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便因失去存在的经济基础,气象日渐萎靡。在此前后,杜甫凭借其反映现实的讥时诗,与李白等盛唐诗人逐渐分化,并形成了“工部缓”的主体风格。可以说,唐诗发展之转折在于杜诗,从“唐音”到“宋调”之转变也始于杜甫。杜甫于诗歌最重要之新创,既不在于其炉火纯青之技巧沾溉后世,也不完全在于其熔铸前人作品之精华而自出心裁,而是由杜甫开始,诗歌不必再背负沉重的“诗教”负担,从而获得了创作自由。所以在杜甫笔下,诗歌感情兴发不必再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之事,卜居借物,种菜除架,朝会值班,题画写生等日常琐事皆可入诗。
诗歌之形成,在于诗人之感于事,动于情,行之于言。杜甫之前,诗人或背负着“诗教”的责任,或自觉地以“摇荡性情”为追求,几乎很少将生活琐事入诗。因此,在传统中国诗歌的情感表达模式中,虽然佳作如云,但同质化也相当严重。如果说在杜甫之前,在传统诗教要求下,诗歌被默认为具有一种神圣的地位,承载着“不朽之盛事”等庄严的使命,一般表现为历史视角下的宏观叙事和固定情境下的典雅抒情。那么,从杜甫开始,诗歌逐渐消解了它的神性,下降到凡间,成为普通诗人情感的附属物和抒情达意的工具,更加趋向于日常化的个体叙事和平凡化的通俗抒情。正如袁宏道所嘲笑的那样,“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宋人周紫芝曾惊叹于苏轼“街谈市语,皆可入诗”,实则自杜甫以来,这种写法便已不算新鲜。王夫之所痛斥“《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之类,即取材于唐人之“街谈市语”。
李白则不然,与杜甫相比,作为陈子昂的忠实信徒,他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诗人。朱熹曾说:“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故李白讥时诗仍然偏重于“风雅兴寄”,而杜甫则不拘泥于此。在杜甫讥时诗中,不仅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名句,更多的是“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等琐细记录,而后者是绝不可能出现在李白诗中。杜诗感事兴发之具体实在的特点,极大地丰富和扩充了诗歌的材料来源,使诗歌的功能从传统“兴观群怨”进一步扩展到记录个人的衣食住行,使后人作诗有规律可循,有章法可依。在杜甫之前,用这样的手法写作诗歌是很难想象的,也是前代诗人很少采用的。杜甫的创作为后世学诗者提供了可供复制的模板,正如王夫之评杜甫“老夫清晨梳白头”句式所说的那样,这种做派“正令人人可诗,人人可杜,宜天下之竞言杜也”。从“供奉深”到“工部缓”,不仅揭示了诗歌在发展过程中由雅变俗的内部关节所在,昭示了中唐之后诗歌演进的新方向,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后人学诗乐意从杜诗着手的真正原因。
因此,之所以会出现“工部缓,供奉深”的文学现象,除了李白和杜甫个人在主体选择上对表现手法的偏好不同,同时也受到诗歌自身内部发展规律的深刻影响。
结语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作为我国诗歌史上的标志性符号,李白和杜甫代表了古代诗歌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反思诗坛上学杜宗杜的弊病,曾提出“工部缓,供奉深”论点。在王夫之看来,工部之“缓”首先在于杜诗用事太直,“讥时语开口便见”,其次在于其语言“或伤于烦缛”,且“尽有可删者”;供奉之“深”一则指其诗用事不直,“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内涵深刻,二则语言省净,无“芜蔓之累”。“工部缓”与“供奉深”确实反映了李、杜诗风的一些特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和启发意义。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工部缓”与“供奉深”并无高下之分,不能将其作为扬李抑杜的依据。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缓”和“深”并非完全对立的,二者还存在着共性,统一于“思之深”。“工部缓”与“供奉深”还深刻揭示了古典诗歌在发展中的重大分野问题。李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诗人,重在寄兴深微,故多用比兴。而杜甫则致力于叙事抒情毫发毕现,故多用赋法。杜甫所开创的个体具体年代化叙事和主观化抒情模式,打破了传统宏观化叙事和群体性抒情模式的限制,使诗歌不必再承受“诗教”的负担而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工具,将个人生活琐事写入诗中,稀释了传统“诗教”指导下中国诗歌的厚重感,不免给人以“缓”的观感。所以,在评析王夫之“工部缓,供奉深”之命题时,需要回归到古人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探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