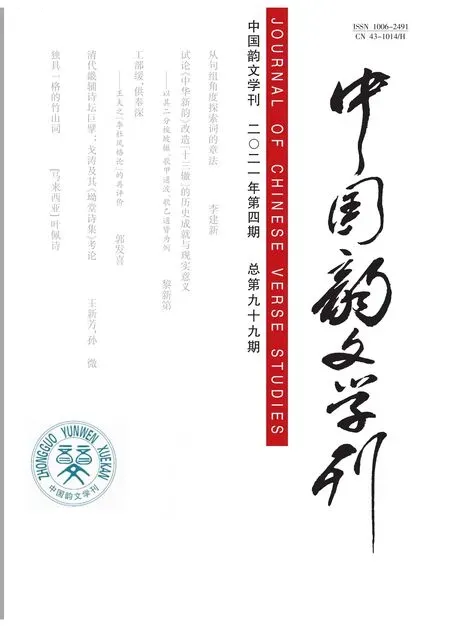论翁方纲对王士禛“神韵说”的解构
宁夏江
(韶关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0)
翁方纲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对王士禛“神韵说”的研究和评论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整理、批点过多种王士禛诗学著作,合刊为《小石帆亭著录》,其《复初斋文集》《复初斋诗集》也有大量涉及王士禛诗学的文字,《石洲诗话》对王士禛“神韵说”更是做了多方阐说。翁方纲通过批评王士禛“神韵说”,提出新的诗学主张。他的“肌理说”是对王士禛“神韵说”进行解构而建立起来的。
一 对王士禛“神韵说”的消解
翁方纲最初接触王士禛“神韵说”时,对其极力推崇,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王士禛许多诗学观点与自己的龃龉不合,且不太合“时宜”,于是转而对王士禛“神韵说”进行消解式的批评。
(一)翁方纲批评王士禛偏爱“冲和淡远”之神韵。本来,王士禛的“神韵说”就有“偏向性”,就是以盛唐王(维)、孟(浩然)派之“清远冲淡”为基本的艺术旨趣。翁方纲出于自身诗学理论的构建,不顾王士禛的诗学旨趣,批评王士禛偏爱冲淡清远之“神韵”,轻视或排斥其他风格之“神韵”,“先生于唐贤独推右丞、少伯以下诸家得三昧之旨。盖专以冲和淡远为主,不欲以雄鸷奥博为宗。若选李、杜而不取其雄鸷奥博之作可乎?吾窥先生之意,固不得不以李、杜为诗家正轨也;而其沉思独往者,则独在冲和淡远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矣”。即王士禛偏爱王、孟派冲和淡远之诗,却漠视李、杜的“雄鸷奥博”之作。他对盛唐诸家的艺术取向剑走偏锋,遗弃李、杜等大家,很明显是不恰当的。他所推赏的“神韵”(即“三昧”)的审美范围很狭窄,所说的“神韵”“非神韵之全也”,“渔洋意中,盖纯以脱化超逸为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实际,岂容一概相量乎?”“阮亭《三昧》之旨,则以盛唐诸家,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而诸家各指其所之之处,转有不暇深究者”,“渔洋于三唐虽通彻妙悟,而其精诣,实专在右丞、龙标间”。
翁方纲还批评了王士禛因为执于冲淡清远一种风格,所以在诗歌用语上“多择乐府中清隽悦目之字……如是诗人止当用清扬、婉娈之字,而不当用籧篨、戚施之字矣。说诗正不当如此也”。
(二)翁方纲批评王士禛“神韵说”与明七子派泥古论同调。他指出王士禛有意为七子派泥古论调辩护,他的“神韵说”思想实际上是在代七子派“下转语”:
李沧溟之纯用《选》体者,直谓唐无五言古诗矣。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者,正谓其无《选》体之五言古诗也。先生(笔者按:指王士禛)乃谓讥沧溟者不合其下句观之,而但执唐无五古一句以归咎于沧溟,沧溟不受也。岂知沧溟之咎,正专在此唐无五言古诗一句乎?彼谓唐之古诗,皆不仿效《选》体耳,岂知唐古诗正以不仿《选》体为正,而后之为诗者转欲《选》体之仿耶?此所谓舛也。……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在后,乃有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之说,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选》体之说,五言不效《选》体,则谓之唐无五言古诗。然则七古亦将必以盛唐为正矣,则何不云宋无七言古诗?而彼不敢也。是以渔洋代为下转语曰:“苏诗七律不可学。”是则直曰苏无七律而有其七律,夫然后可以继李沧溟之论耳。
翁方纲批评明七子派以《选》体之五古为高,唐之五古不效《选》体之五古,于是否定唐之五古的价值而“直谓唐无五言古诗矣”,“岂知唐古诗正以不仿《选》体为正”。而王士禛认为七律应宗唐,苏轼七律不学唐,于是说“苏试七律不可以学”,这不是与明七子派泥古同调吗?
翁方纲指出王士禛“神韵说”同明七子派的观点换汤不换药,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王士禛只是变七子派之格调说为“神韵说”,其“所云神韵,即李、何所云格调之别名也”,即王士禛的“神韵说”实际上是变相的七子派格调论。王士禛“不敢议李、何之失,而唯恐后人以李、何之名归之,是以变而言神韵”。翁方纲带着揶揄的语气说:“李空同、何大复之伪体,渔洋唯恐人讥议之,此则渔洋先生之好买假古董,实不能为先生讳矣”。
(三)翁方纲批评王士禛“神韵说”轻视诗中之学问事理。他在《志言集序》中说:“杜云:‘熟精《文选》理。’曩人有以杜诗此句质之渔洋先生,渔洋谓理字不必深求其义,先生殆失言哉!”在《神韵论上》中也说:“其误曰‘理字不必深求其解’,则新城一叟,实尚有未喻神韵之全者。”翁方纲指出王士禛不但轻视诗中“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等伦理,也不重视诗中学理,“如咏焦山鼎,只知铺陈钟鼎款识之料,如咏汉碑,只知叙说汉末事,此皆习作套语……盖渔洋未能喻‘熟精《文选》理’理字之所以然,则必致后人误会‘诗有别才’之语,臻堕于空寂”。“自王新城究论唐贤三昧之所以然,学者渐由是得诗之正脉,而未免歧视理与词为二途者”,“目空一切,不顾涵养之一莽夫所为,于风雅之旨殊远”,他们的诗歌或弊于虚空,或流于高腔,诗中欠学,诗中乏理,虚而不实。
(四)翁方纲批评王士禛“神韵说”对诗法避而不谈。他说:“愚曩者固已于藐姑神人之喻,微觉渔洋拟不于伦矣。”指出王士禛把诗之“神韵”比做庄子寓言中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藐姑之神,这是故弄玄虚。又说:“(渔洋)第知以澄迥淡泊为超诣,则犹未深切乎后学所应历之阶、所日履之径也。此事岂可不问何时、何地、何人而皆以禅寮入定,山磬清圆为悟入者也?”即王士禛遇人向他请教神韵诗法,不管何人何时何地,皆笼统地以“入定”“悟入”等禅语加以指授。翁方纲这一意见基本上代表了清代诗坛以来对王士禛“神韵说”的批评。吴之振就对王氏的“神韵说”表示异议:“近世主领骚坛之人,每对学者讲三昧,谈神韵,问其所以,则曰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作诗久自能了悟。学者闻其语,虽不甚解,亦不复问,比于禅宗,则棒喝之微旨也。其真与伪,学者且不能知之,又安能学之。吾谓大抵袭沧浪之绪语耳。”现代学者钱锺书也说:“(渔洋)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
(五)翁方纲批评王士禛“神韵说”不“切实”。他指出王士禛不问何情何景,作诗以同一格调加以套用。他举例说王士禛《黄子久王叔明合作山水图》:“长林巨壑来畏佳,飞鸟流云去寥廓。空堂白昼生风霆,飞瀑千寻竞喷薄。老松撑突夜叉臂,怪石纵横鹅鹳啄。”诗中“‘空堂白昼生风霆’,此七字似乎先生集中处处皆有之”。在《苏斋笔记》中翁方纲再次揶揄王士禛道:
渔洋集有《冒辟疆水绘园修禊》十首,众所称也。一日有友读此诗,议其不工。予闻而竦然,意此友必知者。乃叩其所以不工,则曰:“此题须切如皋冒氏之园,不可与他处景事相似,乃工耳。”予笑曰:“君误矣!渔洋篇篇皆然,何尝有某一诗切其人其地,而独议此为不工耶?”盖渔洋通集之诗,皆若摹范唐人题境为之者耳。
王士禛“神韵说”不切实,导致诗歌失“真”。如王士禛有送别诗《送吴天章归中条山六首》,题中吴天章(笔者按:即吴雯)在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宏词科没有被取中,王氏以诗送之。翁方纲评云:
人之相别,必有因时因地悲愉欣戚之殊,而诗之词气因之。即如吴天章此归,乃其应召试不遇而归也,虽于秀才下第不同,然与他时之归自不可同语矣。乃渔洋先生之诗,则不问其何人、何时、何情、何事,率以八寸三分之帽付之,尚复何诗之有?
翁方纲指出吴天章在博学宏词科应试中名落孙山,虽与科试下第有所不同,但并不是潇洒惬意之事,然王士禛送别诗所写的却是吴天章归隐中条之趣,很不切合吴氏召试不遇而归的心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王士禛作诗不切诗中人事,一概以“淡远冲和”的腔格加以套用。这种缺乏真情实意的诗歌没有价值(“尚复何诗之有?”)。
翁方纲还指责王士禛的神韵诗本来就显得空淡玄远,再加上诗中堆垛典故太多,愈加使人不知诗歌旨意之所在。徐珂《清稗类钞》载翁氏评点王士禛成名作《秋柳诗》曰:“诗以数典神韵欺人者,其弊竟若此!文简以盛名之下,颠倒一世豪杰,吾终不为之屈服也……似此用典,可谓堆垛甚矣,有何神韵可言乎?”翁方纲罕见地以凌厉之辞,不留情面地抨击王士禛“诗以数典神韵欺人者,其弊竟若此”,“有何神韵可言乎?”
二 “神韵说”的重构
正如上述所言,翁方纲不顾王士禛神韵说的审美旨趣,也不顾王士禛之诗学旨归,而按照他自己的诗学理论框架,一方面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另一方面重构他所体认的“神韵说”。他阐发的“神韵说”思想当然“已不是王渔洋神韵的真正内涵”。
(一)针对王士禛偏爱“清远冲淡”之神韵,翁方纲认为神韵是指一切诗歌所具有的审美特征。他指出“神韵”远非“清远冲淡”一种风格所能涵盖,“神韵乃诗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神韵者,彻上彻下,无所不该”。在翁方纲看来,诗歌只要符合儒家“诗教之绳矩”,各种审美标准、审美风范、审美趣味,如果运用得当,都可说是“神韵”,也即“神韵非诗品中之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他明确提出“然则神韵,是乃所以君形者也”,即“神韵”是各种审美标准、风范、趣味的泛称,而不是某一具体的格调法度。(笔者注:“君形”意谓统帅形貌之物,即“神”。)
杜甫、韩愈、杜牧等人已从不同的角度对“神韵”进行了阐述,“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神字即神韵也。杜云‘精熟文选理’,韩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杜牧谓李贺诗‘使加以理,奴仆命骚可矣’,此理字即神韵也。……其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镜花水月,空中之象’,亦皆神韵之正旨也,非堕入空寂之谓也。”自古以来诗歌体现出来的“神韵”也各不相同,“有于格调见神韵者,有于音节见神韵者,亦有于字句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有于实际处见神韵者,亦有虚处见神韵者,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情致见神韵者,非可执一端以名之也”,“以其义言之,则圣人一言蔽之,曰‘思无邪’;以其音言之,则曰‘乐不淫,哀不伤’,曰‘各得其所’,曰‘洋洋盈耳’,未有一言可以该其所以然者”。
翁方纲进而指出神韵并不是王士禛创造的。他在《神韵论上》中详述道:
盛唐之杜甫,诗教之绳矩也,而未尝言及神韵。至司空图、严羽之徒,乃标举其概,而今新城王氏畅之,非后人之所诣能言前古所未有也……自新城王氏一唱神韵之说,学者辄目此为新城言诗之秘,而不知诗之所固有者,非新城始言之也。
翁方纲认为自古以来诗人都意识到了“神韵”是诗歌本来特征,杜甫虽没说,但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诗歌之“神韵”。司空图、严羽等人虽然没有用“神韵”一词,但他们已经大致说出了“神韵”的意蕴。然而“古人盖皆未言之,至渔洋乃明著之耳”,即王士禛明确用“神韵”来标举诗歌的审美特征。在《神韵论下》他再一次申述道:“诗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之也,是乃自古诗家之要眇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他进而分析了世人对“神韵说”的误解主要是对古典诗学缺乏了解,“昔之人未有专举神韵以言诗者,故今时学者若欲目神韵为新城王氏之学,此正坐不晓神韵为何事耳”,“盖未熟观古人集,不知神韵之所以然,唯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如果对古典诗学有全面的了解,“知神韵之所然,则知是诗中所自具,非至新城王氏始也”。
(二)针对王士禛“神韵说”与明七子派泥古论同调,翁方纲认为诗人当自具面貌风格。他指出今人和古人各不相同,“今编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拟古、感兴诸题而又徒貌其句势,其中无所自主、其外无以自见者,谁复从而诵之?夫其题内有拟古、仿古者尚且宜自为格制、自为机杼也,而况其题本出自为其境、其事属我自写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面,非古人之貌而袭古人之貌,此其为顽钝不灵、泥滞弗化也。可鄙可耻,莫甚于斯矣!”诗歌是要以“古人为师”,但必须推陈出新,而不是唯古是从。他在《格调论中》说:
然则学之汲古师古何为也哉?曰:圣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礼不能于杞、宋征之。凡所以求古者,师其意也,师其意,则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于《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于《韶》《武》之意,岂《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节奏乎?抑且勿远稽《三百篇》,即以唐音最盛之际,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属,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谢、颜之作者乎?宋诗盛于熙、丰之际,苏、黄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
翁方纲从古典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列举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苏轼、黄庭坚等人皆能如孔子师古,师其意而不效其体,皆能从学古中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从而铸就唐诗、宋诗各领风骚。翁方纲进而指出:“诗无貌古之理。古必天然神到,自然入古,亦犹平淡之不可以强为也。岂可云诗必求其古欤?若学者相率而效为貌古,则蹈袭之弊,竞趋于伪体,是乃诗之大蠹。”
(三)针对王士禛“神韵说”轻视诗中之学问事理,翁方纲把学理作为诗歌的根本。他认为“性情与学问,处处真境地……且莫矜忘筌,妙不关文字”,劝勉“后之学人若不殚治经籍,实求心得,而徒执渔洋拈出之迹,即使人人皆味《三昧》之味,诗《十选》之诗,犹未必其真知,况于随声倚和,弗思其源者乎?”翁方纲特别指出:“诗自宋、金、元接唐人之脉,而稍变其音,此后接宋、金、元者,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乃有明一代,徒以貌袭格调为事,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至我国朝,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他断言宋、金、元以后的诗人,如果想探寻诗歌新的天地,“全恃真才实学以济之”,这是诗歌发展的大势,学无根底的诗人,绝没有立足之地。他相信有清一代诗人会以明代诗人空疏不学为鉴,“况在今日,经学日益昌明,士皆知通经学古,切实考订,弗肯效空疏迂阔之谈矣,焉有为诗而群趋于空音镜像以为三昧者乎?”
(四)针对王士禛“神韵说”对诗法避而不谈,翁方纲认为诗歌大到脉络条理、结构布局、行文笔法,小到句法、字法以及音调都有基本法则。“(诗歌)大而始终条理,细而一字之虚实单双,一音之低昂尺黍,其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都有章法可循。尽管诗人在创作时不必拘束于具体的法度,但诗歌创作又不能没有法度,所谓“忘筌忘蹄,非无筌蹄也”他在《神韵论下》中云:“射者必入彀,而后能心手相忘也;筌蹄者,必得筌蹄而后筌蹄两忘也……是故善教者必以规矩焉,必以彀率焉。”指陈王士禛的“神韵说”如同还没有教会射猎者如何射猎,就要求他射猎时要心手相忘;还没有教会渔猎者如何使用筌蹄,就要求他渔猎时要筌蹄两忘,确实有空言之弊,让学诗者“无可着手”。他认为只有先教会学诗者熟练掌握“规矩彀率”(“筌”“蹄”),然后才能达到言为心声之境(忘“筌”忘“蹄”)。他在《石洲诗话》《杜诗附记》《七言诗三昧举偶》《苏斋笔记》《五言诗平仄举偶》《七言诗平仄举偶》《芸窗改笔》等著述以及他对朱彝尊、厉鹗、曹振镛等人诗歌的评点中,向其门生及世人阐明了诗歌的规矩法度以及诗歌创作如何才能达到“细肌密理”。
(五)面对王士禛“神韵说”“不切实”的之弊,翁方纲提出诗歌要切实“事境”。“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几于化也。未有不有诸己,不充实诸己,而遽议神化者也。”“一时有一时之阅历,一家以一家之极致焉。”诗人面对特定的“事境”,就有被其激发的特定情感,相应地就应对“事境”做“正面铺写”。“妙悟”式的抒写所采用的程式化的意象、泛化的语句,是绝对表达不出对具体“事境”的真情实感的。即使诗歌抒写的是古淡清远之境,也应是从“实处”得来的,“予尝论古淡之作,必于事境寄之。放翁有言,绝尘迈往之气于舟车道路间得之为多”,也就是说即使诗歌意境高古超迈,也是为当前具体事境所激发。
翁方纲还认为诗歌唯有切实,才能存“真”,“真也者,即己之谓也。夫人所处有时有地,彼不可代也,后不能以移前,老不可以为少壮之言,贵不可以作贫贱之语,处乎今日,不可以说昨日之语,不论登临咏物、论古赠友,唯其中间有我在,有我之时地在,所以真也”。
三 解构的逻辑策略
翁方纲对他所体认的“神韵说”的重构,实际上就是对其诗学理论“肌理说”的建构,这是承接对王士禛“神韵说”批评而来的。一般说来,一个新理论取代一个旧理论,就是“破”与“立”的对立。但翁方纲不同,他没有走这一条老路,他走的是“不破”而“立”的新路径。他在解构王士禛“神韵说”的过程中,非常讲究逻辑策略。
翁方纲对王士禛“神韵说”进行重构颇费了一番心计,主要原因是他欲弃置王士禛的“神韵说”,却心存顾忌。王士禛在康熙一朝被尊为诗坛圭臬,“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其“名位声望为一时山斗”,弟子门生众多,在乾嘉诗坛仍然颇有势力和影响。再加上他与王士禛有师门之谊,翁氏的父亲翁大德曾入王士禛弟子黄叔琳门下学习,后来翁氏自己也向黄氏问学,他是王士禛再传弟子。在如此背景之下,翁方纲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像对待明七子的“格调论”简单地一棍子将其打倒,他得小心翼翼地来处理王士禛的“神韵说”。在这种心态下,他所采取的策略是抑扬结合,模棱两可,不把话说尽说绝,尽量不引起王士禛追随者的强烈反感,避免世人对他的指责,表现为:
(一)他批评了王士禛偏爱冲淡清远之“神韵”,却又说王士禛倡导的“神韵”并非专指“冲淡”。他说:“平实叙事者,三昧也;空际振奇者,亦三昧也;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者,亦三昧也,此乃谓之万法归原也。若必专举寂寥冲淡者以为三昧,则何万法之有哉?渔洋之识力,无所不包。”指出以王士禛之眼识才力,“神韵”不但包括“寂寥冲淡”,也包括“平实叙事”“空际振奇”“浑涵汪茫”等艺术旨趣,可谓“无所不包”。
(二)他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是变相的七子派格调论,却又说王氏之“神韵说”是为纠七子派之弊提出来的。他指出明七子派之诗多模拟“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等盛唐气象,误导世人以为这就是盛唐之诗,王士禛于是选编了《唐贤三昧集》,“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翁方纲进而指出,王士禛“专举空音镜象一边,特专以针灸李、何一辈之痴肥貌袭者言之,非神韵之全也”,“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此特亦偶举其一端,而非神韵之全旨也”,“则皆举隅也,奚又择诸?曰:‘择其最易见者,择其隅之最易反者’而已”,即王维、孟浩然“空音镜象”之诗最能反证七子派侈言盛唐格调之论,所以被王士禛特别予以拈出。
(三)他批评王士禛“神韵说”缺乏学问事理,却又颂扬王士禛才识超群,功力深厚。赞扬王士禛“呜呼三昧旨,充实万钧力”,“天挺秀骨,无论何等语言,入其咳唾,皆成珠玉。此窦臮述虞秘监书,所谓层霄缓步,高谢风尘者也,若无其秀骨而习其套言,非其天资而步其熟径,将奚存于中,将奚发于外耶?昔人云:日临《兰亭》一纸,终不成书。盖渔洋一人,提倡神韵,山辉川映,一时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聪明涵盖中耳”,“先生诗如海佑拣取明玑紫贝作仙子五铢之服,随手凑补,皆合五城十二楼中装饰,但寒者不可以为衣耳”。意谓唯王士禛有此功力才识,方能言“神韵”,一般人岂能挦扯神韵!
翁方纲评论他人之诗好“骂詈”,但批评王士禛的“神韵说”却一改常态。他不但很少骂王氏,还高度肯定了王士禛“神韵说”在清代诗坛的影响,以回应康熙对王士禛的褒扬。他指出明代诗人“无一人具真才实学以副之者”,无力接轨宋、金、元诗,却企图步唐诗之“兴象超妙”之后尘,结果只是“徒以貌袭格调为事”。清代诗坛一变明代空疏无学之弊,“然当其发泄之初,必有人焉,先出而为之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气复于冲淡渊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经术实之也,所以赖有渔洋以涤荡有明诸家之尘滓也”。即明诗流毒已深,要纠治扭转它不能过猛,必须要有一个缓冲和过渡,为它“伐毛洗髓,使斯文元气复于冲淡渊粹之本”。王士禛作为康熙诗坛耆宿,承担了这一使命,他提出“神韵说”,以“涤荡有明诸家之尘滓”。翁方纲高度评价了王士禛在引导“貌袭格调”的明代诗风(主要指七子派诗风)向“冲淡渊粹”的清代诗风转变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然而翁方纲话锋一转,指出以王士禛为首的康熙诗坛已完成了对明诗“伐毛洗髓”的任务,王士禛的“神韵说”起到转移明诗风气的作用,是“过渡阶段净化思想和心绪的一剂药石”,其作用就此而已。乾嘉诗坛应承担的使命则是对受明代诗风影响的清代诗坛“徐徐以经术实之”,在翁方纲看来,这个任务该由他本人所引领的这一代人来完成。清代是经术学问集大成的时期,“国朝景运日新,经义诗文,并崇实学,是以考证之学接汉跨宋,于此时研精正业者,盖必以实学见兴观群怨之旨,得温柔敦厚之遗”。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已无法胜任时代的要求,清代诗学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崇实学、兴考证的风气。特别是乾嘉之世,“文治之光,乃全归于经术。是则造物精微之秘,衷诸实际,于斯时发泄之”,“士生今日经学昌明之际,皆知以通经学古为本务,而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士生此日,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诗学大醇”,因而更应有与乾嘉学风相适应的诗学。这当然不能是王士禛时代的“神韵说”,而必须是新的诗学,这就是他所重构的“神韵说”。他说:“方纲若不为之剔抉源委,俾读者知其立言之所以然,其于甘辛丹素经纬浮沉之界,所关非细。”
翁方纲接着指出鉴于“神韵”已被世人所误解,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名称,而代之以“肌理”,“今人误执神韵似涉空言,是以鄙人之见,欲以肌理之说实之”,翁方纲由此而顺势推出他的“肌理说”,明确提出以“肌理说”取代“神韵说”,以便更好地与乾嘉实证学风相适应,“士生于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乾嘉士子要“以实学见兴观群怨之旨,得温柔敦厚之遗”,当“先于肌理求之也,知于肌理求之……又奚必其言神韵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