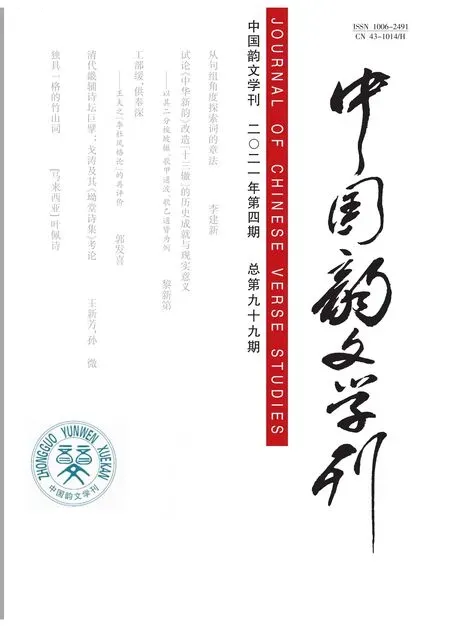明代诗人陈白沙诗的地位与评价
章继光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00)
陈白沙(1428—1500),名献章,字公甫,别号石斋,出生于广东新会,后迁居江门白沙里,世称白沙先生,明代著名思想家、诗人。在明代诗歌史上,陈白沙诗歌在精神内涵、美学素质、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同时期诗人相比,白沙诗歌的成就是许多人所未能达到或超越的。然而历史的评价并不尽如人意,部分文学史家因循旧说,对白沙诗歌的价值一度有所忽略,甚至产生误解。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陈白沙兼有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在传统学术史和文化史上其理学家(心学家)的名声盖过了他的诗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白沙后学关于“白沙诗教”的设定,其门人湛若水出于传播白沙学说的需要,将陈白沙的部分诗作,附上他自己的解释,编成《白沙子古诗教解》,使后来的一部分读者将白沙误读为一般的“道学诗人”(“性气诗人”),从而影响到人们对白沙诗的内容与美学特质全面、深入的认识。笔者以为,对白沙诗的评价必须放在明代前期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认真考察,才会得出可信的结论。
明代前期诗歌的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严峻、保守的,面临着学风(朱学)和诗歌本身的双重阻力。
从学术风气看,从明初至成化初年的一百余年中,思想学术风气都是保守僵化的。出于强化封建专制的目的,最高统治者采取了定朱学为一尊的文化政策。朱元璋多次昭示“尊朱子之书”,成祖朱棣敕令撰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五经大全》颁行天下,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源。正如学者所言“自考亭(按:朱熹)以还,斯道以大明,无烦著作,只需躬行耳”,有明学术一度沦为“述朱”之学。定朱学于一尊的思想统治,以及以“四书”取士的科举政策使天下士人思想受到严苛的控制,也使他们诗歌创作的欲望和内在活力受到严重的压抑。
从诗歌创作风气看,明代前期诗坛适应专制统治需要的歌功颂德的台阁体诗风盛行。
清代学者蒋重光在《明诗别裁集》序言里曾对明代前期诗歌的发展勾画出一个基本轮廓,指出:“国初诸臣,青田(刘基)、青邱(高启)两雄并峙,开风尚也。永乐以还,体崇台阁,……成、弘之代,茶陵振兴,绍先启后,标引导也。”所论虽较简略,但与明诗发展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明初诗坛以高启、刘基为代表,曾经掀起了诗歌发展的第一个小高潮。但这种局面很快便结束,随着永乐时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登台,高、刘开创的局面便逐渐失去光彩。“三杨”在永乐后期先后进入内阁,他们在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为维护皇太子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受到倚重。杨士奇在内阁时间43年,杨荣37年,杨溥22年,三人同为历经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三杨”雅好诗文,他们以位尊权重的身份执掌文坛,揄扬风化,要求诗歌发挥鼓吹、颂扬承平之世的作用。作为四朝元老,他们德高位显,安富尊荣,所作诗文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饰,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在他们的示范和提倡下,“雍容典雅”的台阁体诗风迅速流播,左右诗坛,影响到明代诗歌发展数十年至百年之久。针对台阁诗风的恶劣影响,不少学者提出尖锐的批评,如沈德潜指出:“永乐以还,尚台阁体,骩疲不振。”出于对台阁诗风的厌薄,他编选的《明诗别裁》除杨士奇外,于杨荣、杨溥二人诗作一篇未选。
当台阁体诗风盛行之际,李东阳步入诗坛,李东阳诗宗杜甫,博采众长,出入唐、宋、元、刘长卿、白居易、苏轼、虞集诸大家,钱谦益说:“西涯(李东阳)之诗,原本少陵、随州、香山,以殆宋之眉山,元之道园,兼综而互出之。”李东阳在成化、弘治两朝十五年内以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讲习艺文,主持文柄。尽管东阳有台阁重臣之名,但他关于诗歌的见解与“三杨”却是针锋相对的,他论诗既重风教,也重诗歌特质,在声律、格调等艺术方面提出了不少迥别于“三杨”的可贵见解,表现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气度与风貌,他的出现标志着明诗发展的转机。
在李东阳的提倡和影响下,明代诗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学者对他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沈德潜说:“茶陵(李东阳)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后何、李继起,廓而大之,骎骎乎称一代之盛矣。”
李东阳论诗以“台阁”“山林”判分高下,两者之间,他偏向后者,他宣称:“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李东阳的所谓“野”是指山林诗的在野之气(“山林气”),所谓“俗”是指朝廷典制之诗的雍容典雅之气。李认为“野可犯,俗不可犯”,表现出对台阁体“俗”气的明显不满。虽然李东阳并未能廓清台阁余风,但以他为代表的茶陵诗派继承、发扬了盛唐诗人比兴感事的传统,从而开了明代前七子宗唐的先河。学者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李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李、何,厥功甚伟。”“西涯宏才硕学,汲引风流,播之声诗,洵足领袖一时。”陈白沙与李东阳有着深厚交情,成化十九年(1483)白沙应召入京期间与时任翰林学士的李东阳相识,谢恩还山时,李东阳并赠诗送行;后两人在较长的时间里一度保持联系,多有唱和,李东阳对有岭南隐士之称的白沙及其充满山林气息的诗歌颇为欣赏,评价甚高。
作为受李东阳肯定的山林诗人,陈白沙远离庙堂,面对炎凉熙攘的世态,他选择了一种终身讲学隐居的生活,在岭南圭峰山下写下了两千余首诗歌,其中与田园、山水有关的占半数以上,他的这类散发出在野气息的山林诗,表现出与居庙堂之高的台阁体诗迥然有别的美学风貌。它们有的直接描写农家生活和农事劳作,有的抒发登山临水的逸兴,有的吟咏自然草木,不少作品具清新潇洒、高逸绝尘之风,是自然美与诗人超脱世俗心灵契合的结晶。其中田园诗中的《和陶诗》以人们熟悉和喜爱的陶体,对田园生活做出了别开生面的吟咏,它们在内容、体裁、格调上与陶诗相似,名为和陶,实为创新,其闲远的意境,古淡、自然的语言,朴素、单纯的色调,是白沙淡泊守真、追求自然美学理想精神的诗化:
流连晡时酒,吟咏古人诗。
夕阳傍秋菊,采之复采之。
采之欲与谁,将以赠所思。
所思在何许?千古不同时。
四海倘不达,吾宁独去兹。
愿言秉孤真,勿为时所欺。
(《移居》其二)
我始惭名羁,长揖归故山。
……
东篱采山菊,南渚收菰田。
游目高原外,披怀深树间。
禽鸟鸣我后,鹿豕游我前。
闲持一杯酒,欢欣忘华颠。
逍遥复逍遥,白云如我闲。
乘化以归尽,斯道古来然。
(《归田园》其二)
前诗(《移居》其二)表现了白沙对陶渊明追求自由、逃禄归耕古代高士的由衷思慕与向往,表达出自己面对世俗洁身自好、独抱孤真的人生理想。在后首诗(《归田园》其二)中,白沙一开始就表白自己归耕是为了摆脱功名的牢笼。诗中随之充分展现出诗人归田以后丰富多彩的生活与自得其乐的感受:既有采菊收菰的农事劳动,也有游目骋怀的休憩,更有禽鸟、鹿豕的追随之乐与山林云岚朝夕为伴的愉悦。在这令人神往的田园生活与自然胜境中,作为诗人的他享受到了委身大化,与之融为一体的乐趣,结句“乘化以归尽,斯道古来然”便是对陶渊明“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辞》)服膺自然之道的体认,与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赠答》)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主旨如出一辙。全诗表现的是一种乐在田园的隐者、智者、达者的心态——对逍遥自得、超旷襟怀的表白,对自然、宇宙与人生之理的彻悟,对乘时委运精神境界的体悟与追求。
有的田园诗表达出诗人参加农事劳动的乐趣:
一蓑费几藤,南冈砺朝斧。
交加落翠蔓,制作类上古。
吾闻大泽滨,羊裘动世祖。
何如六尺蓑,灭迹芦花渚。
举俗无与同,天随梦中语。
今夜不须归,前溪正风雨。
(《藤蓑》其二)
迟明向南亩,疏星在檐端。
夫出妇亦随,无非分所安。
道旁往来人,下车时一观。
……
逻苗远峙夕,濯足荒沟寒。
……
齐声鼓腹讴,永谢攒眉欢。
(《庚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前首诗写白沙亲自采藤制蓑的过程与感受,全诗趣味盎然,襟怀旷达、格调高古,结尾耐人寻味;后诗展现出白沙与百姓耕种田园、自得其乐的生活,描摹丰富多彩的田园生活与隐居乐趣。
对白沙的这类诗作,王船山评价较高,他说:“陈正字(按:陈子昂)、张曲江(按:张九龄)始倡《感遇》之作,……朱子和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唯白沙能以风韵写天真。”又说:“此十年中别有《柳岸吟》(按:船山隐居衡阳湘西草堂自编的咏物感怀诗集),欲遇一峰、白沙、定山于流连骀宕中。”揄扬之意,溢于言表。王船山《柳岸吟》诗作不满九十首,其中和陈白沙诗达三十八首之多,可见他对白沙诗的偏爱。
白沙的山水诗有的清淡、简洁,颇得唐人王(维)孟(浩然)风致与意趣,如:
冬眠不觉晓,开门见白云。
云中何所有,童子两三人。
(《晓起》其三)
不难看出,这样的小诗糅合了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和贾岛《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的笔致与诗意,诗人以疏淡、飘逸的白云渲染出一种隐逸之气,自成一格,耐人寻味,是情景(境)合一、饶有意境的佳作。
但作为心学家白沙笔下的山水诗,更多表现出哲人对自然山水的观照与体认,诗人在流连林泉,以自然山水为观赏对象的同时,追求和体味着一种心凝神释、与物同流的意趣,挥洒出一种超旷自得情怀:
天际有山皆古色,水边无处不秋声。
一春桃李风吹尽,万里乾坤雨洗清。
(《南海祠下短述》)
担头行李但书囊,选胜寻幽到上方。
身与白云同去住,客从何处问行藏。
(《游白云》)
有的山水诗表现出诗人由这种胸次悠然的意趣升华出的潇洒自得:
江流东与海潮通,江去潮来古今同。
岩洞风光诗卷里,天涯岁月钓船中。
(《赠同游马玄真伍伯饶甥舅》)
柳渡一帆秋月,江门几树春云。
来往一时意思,江门万古精神。
(《六言》)
蜻蜓短翅不能飞,欸欸随风堕客衣。
此是天人相合处,蒲帆高挂北风吹。
(《上帆》其一)
这些诗中所表现出的白沙优游、徜徉于自然造化或历史沧桑的精神状态,已不仅仅是对山水的流连,它们使人联系起诗人所津津乐道的鸢飞鱼跃、浩然自得的状态与宇宙生生不息的精神,体现出白沙心灵与自然的同构、诗境与心学的融通。这些充满诗意的画面与其说是诗人忘情于自然美景的山水意趣的抒发,毋宁说是白沙获道境界的诗学延伸与心灵图像的呈现,它们以活泼自然的姿态凸显出昂扬自得的主观精神和美学张力,展现出白沙作为心学家的独有的“心境”与心学气象,这是十分可贵的。毋庸讳言,白沙这类诗作拓展、丰富了明代山水诗的意境和美学品格,闪烁着心学的光辉和哲学品位。享有明代心学开山地位的陈白沙,以所倡导的心学向因循守旧的朱学发起挑战,他以立心为要务,以点亮心灵之灯作为精神使命,致力于追求 “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的“自得”境界;这种境界就是让个体生命进入到真机活泼,与大化同一的状态,无适而不可,无往而不能,“鸢飞鱼跃在我”的境界,让心灵与思想的羽翼飞翔在宇宙无限广阔的时空。追求本性真实自然的表现与精神的自得,是白沙心学的根本点,也是白沙诗歌和诗学的亮点。白沙的自得精神进入他诗歌创作的领域后,就实现了哲人与诗人的同一,他的诗歌就具有了可贵的精神内涵。在这些诗中,白沙不仅用心去感受充满活力的自然山水,同时也用心在体悟大化、自然之道,从而使这类诗成为心灵对自然的体验,成为诗人心灵连同心学精神与自然山水契合的结晶,它们凸显出白沙作为心学诗人对“心”的致力追求。此外,白沙集中的部分哲理诗(论道诗)由于体现、流露了白沙超然独悟的心学思想,带给人们关于人生、自然的理性思考,具有浓厚的哲理性、趣味性和文化气息。白沙诗的这一整体特征使得它从内容、形式到语言风格上表现出高蹈于理学压抑和左右诗坛的台阁流风迥然不同的美学风貌和心学境界,更使得它与左右世俗的宫廷文学——台阁体绝缘,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清逸拔俗、轩昂自得的美学品格,从而在明代前期诗坛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占有重要地位。前人赞白沙诗“流连骀宕”,“以风韵写天真”(王船山语);“出于自然”,“在勿忘勿助之间,胸中流出而沛乎,丝毫人力亦不存”;“脱落清洒,独超造物牢笼之外,而寓言寄兴于风烟水月之间”;“潇洒有度,顾盼生姿,腐风为之一扫”,如此等等,都揭示出以心学为价值取向的白沙诗歌在明代前期诗坛独标流俗的格调与美学风貌,展现出白沙诗歌的生命精神。此外,白沙诗论重视以涵养虚静作为审美观照的条件,以及关于性情说的有关观点(重悟入、情真、自然等)等,这些都是对先秦以来中国古典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白沙诗是心学与诗的融合,它对抒情主体与真情的高度重视,它对人格独立、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诗中所凸显的自然、自得的生机与物我合一的境界,所包含的道机、理趣,等等,均不同程度地显示出心学对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渗透及正面推动的力量,并预示着明诗和明代文学价值观的转变,以及一场新的文学思潮的酝酿与发动。笔者以为,这是站在时代高度,兼有诗人和心学家身份的陈白沙对包括诗歌在内的明代文学和思想文化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我们在以陈白沙为首的江门学派学者的著作和诗文中不难看到心学与诗歌创作的重要联系,他们以道入诗的吟咏唱和在明代前期的诗坛形成了一道颇具特色的心学诗派的风景。在明代后期王学左派及徐渭、李贽、袁宏道、汤显祖等人的诗文或戏剧中,在吴承恩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中更不难感受到心学精神元素所显示的巨大活力,它们以本心、真情、性灵递相标榜,高扬自我主体意识,使宋明以来的朱学价值观与旧的思想体系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不能说这些人都受到白沙的直接影响,更不能说这股思潮是白沙一手带动的,但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之所以形成,的确是明代心学力量推动所致。而究本推源,自然要上溯、追踪到对明代心学有发轫之功的陈白沙。
白沙不重著述,其思想学术精华主要体现于所存的两千余首诗中。白沙诗歌是岭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明珠,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数百年后的今天 ,它所包孕丰富的思想、美学内涵仍带给我们跨越时空的通灵共感,文化、美学的启示与沉思。
毋庸讳言,白沙诗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作为理学家兼诗人的白沙,他的诗中的确有一部分偏于理性的论道、悟道之作,这些诗有的平易自然,富于理趣,将深刻的哲理与生动的形象融为一体,让读者获得诗美和哲学的启迪;有的则限于演绎理学名词或经义,枯燥乏味,主要关乎宇宙大化、性命之理的思考、探求,近乎玄谈,缺乏诗性和诗的美学价值。但这类诗在白沙集中的总量并不多,不至于影响对白沙诗的整体评价。当我们对某一时期的作家或诗人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围绕他所生活的时代、社会文化思潮以及整个诗坛的情况做出全面的考察与分析,既要尊重前人的结论,又要具备宏观与独立的眼光,这样才能避免主观和武断,同时避免陷入前人的成说不能自拔。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周汝昌先生在谈到兼有宋代诗人和理学家身份的杨万里(杨是被列入《宋元学案》的学者)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是理学家兼诗人,学诗不肯死在‘黄陈’江西诗派的篱下,敢于自出乎心眼。他讲理学(听见这个名称不要怕),他讲的话头大抵来自周、孔、程(听见这些人,也不要怕),但是,看他对他的先哲们并不一味膜拜,一味迷信,一味盲从,却敢提出异议和新见解,……在他所处的那等历史阶段的局限下,他能如此,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周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对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杨万里诗的武断批评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在对兼有类似身份的白沙诗的研究中,这种评价对于今天的读者多少应具有启发和借鉴的作用。但陈白沙与杨万里还是有区别的,白沙不是一般的理学家,他是宋明理学心学一翼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明代心学的开山。对具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诗人就必须从一个新的维度细心考量了。
如前所述,心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和学术思潮,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宋明以降讫至近现代近千年中,心学对包括政治、学术、思想、文学(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等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系统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点已逐渐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共识。三十多年以来,随着这种认识的深入,以及传统研究模式和方法的突破,学者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审美认识的深化,等等,学术界在理学与文学、心学与诗学的研究中已取得明显的进展。可以预期,随着研究的推进,整个心学诗派及心学诗论的美学价值将会得到更深入的发掘,学界对陈白沙诗歌的认知度和接受度将会不断提高,闪烁着心学光彩的白沙诗歌及其诗学将会进一步增值,中国文学史、美学史将会为它书写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