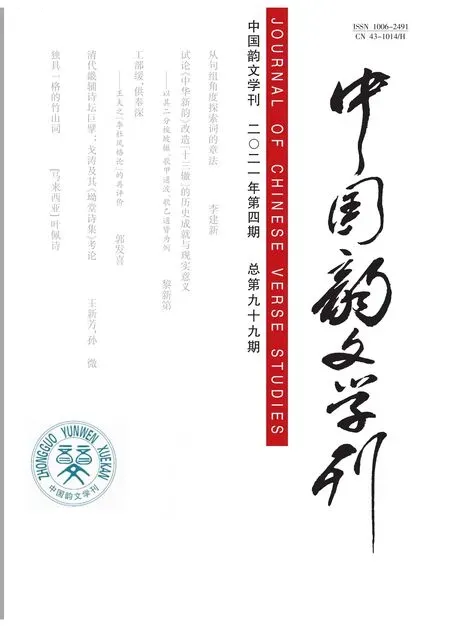清代畿辅诗坛巨擘:戈涛及其《坳堂诗集》考论
王新芳,孙 微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200)
戈涛(1717—1768),字芥舟,号蘧园,河北献县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授湖广、山西、河南道监察御史,充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福建乡试正考官,终刑科给事中,著有《坳堂诗集》《坳堂文集》等。戈涛是乾隆诗坛的代表诗人,早年与戈济、戈源、李棠等结“香泉诗社”,又与边连宝等人结“续真社”“慎社”,同边连宝、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纪昀并称为“河间七子”,又与边连宝并称“瀛洲二子”。戈涛诗文兼善,诗名更著,然因其诗文集屡遭灾厄,流布甚稀,故而学界对戈涛诗文的研究极为少见,目前所见者仅有刘青松先生在《清畿辅诗人边连宝、戈涛诗歌理论初探》(《华夏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及《坳堂诗文集》整理本“前言”中首次对坳堂诗文进行了总结,具有导夫先路的意义,然其论尚属椎轮大辂,对坳堂诗文的研究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鉴于目前学界对戈涛研究的薄弱现状与其在清代诗坛的重要地位极为不符,兹不揣谫陋,试对戈涛的诗学理论倾向及其诗歌之创作特色进行初步总结,以期就正于海内方家。
一 “欲拔新城帜”:戈涛对王渔洋“神韵说”之反拨
在“河间七子”中,戈涛和边连宝都是王渔洋“神韵说”的反对者。戈涛《坳堂诗集》前本来有边连宝之序,然而由于边氏在序中对王士禛的“神韵说”大加挞伐,以至于翁方纲后来为《坳堂诗集》作序时删去了边序,如今我们要讨论戈涛的诗学理论倾向,就必须首先厘清这段公案。边连宝《坳堂诗集序》虽已被翁方纲删去,不过此序的片段仍存于《病余长语》之中,其云:
自严沧浪以禅喻诗……其为风雅之祸者甚烈,而近世之劫持文柄者复宗其说而改其面目,谓诗当以神韵为主。于是天下学者靡然趋风……于是乎诗道至此而大敝。夫诗以性情为主,所谓老生常谈,正不可易者。不主性情而主神韵,得无影之掠而风之扑乎?杜甫氏千秋宗仰,求其所设神韵者,不过曰“浣花溪里花含笑,肯信吾兼吏隐名”而已,再则曰“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而已,外此无有也。善乎周珽氏之评杜也曰:“绝脂粉以坚其骨,贱风神以实其髓。”神韵家不磕自碎矣。
边连宝认为诗以性情为主,而王渔洋倡导的神韵说偏离了性情之轨,天下竟靡然趋风响应,遂导致诗道大弊。并且他还举出杜诗为例,认为杜诗中表现神韵之处不过两句,可见神韵说在诗道中所占比例极小,实不足道也。然而翁方纲却极力反对边连宝此说,其《坳堂诗集序》云:
献县戈芥舟《坳堂诗集》,不蹈袭格调之滞习,亦不必以神韵例之。顾其稿有任丘边连宝一序,极口诋斥神韵之非,甚至目渔洋为“神韵家”,彼盖未熟观古人集,不知神韵之所以然,唯口熟渔洋诗,辄专目为神韵家而肆议之。且又闻其尝注杜诗,其注杜吾未见也,第就此序举杜诗“浣花溪里花饶笑”二句、“巡檐索共梅花笑”二句,谓杜集中只此二处是神韵,不通极矣。“神韵”者,非风致情韵之谓也,今人不知,妄谓渔洋诗近于风致情韵,此大误也。神韵乃诗中自具之本然,自古作家皆有之,岂自渔洋始乎!古人盖皆未言之,至渔洋乃明著之耳。渔洋所以拈举“神韵”者,特为明朝李、何一辈之貌袭者言之,此特亦偶举其一端,而非神韵之全旨也。诗有于高古浑朴见神韵者,亦有于风致见神韵者,不能执一以论也。
按,翁方纲是渔洋再传弟子,故对边连宝贬斥渔洋“神韵说”极为不满。平心而论,边连宝对诗歌神韵的理解过于偏狭与质实,其对神韵说的批评也显得过于偏激,而翁方纲之说又明显带有流派之偏见,二人所云均非公允持平之论。戈涛对王士禛神韵说的态度,虽然没有边连宝表现得那么激烈,但他在诗序中亦多次批评神韵说因复古而失真之弊。其《默堂诗叙》曰:
诗道歧出久矣,自瓣香沧浪者以“神韵”为解,于是尽举济南、竟陵、公安互角,争树之帜而摽之……然而论者犹或疑其有流而失真之弊。夫至于失真,则于济南、竟陵、公安诸派,卒无以相胜。而所谓真者,又非可假老妪能解之言,以自文里陋也。诗之为道,固何如哉!固何如哉!
此外,戈涛在《随园诗序》中曰:
明之盛,何、李最著,信阳温文都雅,诸体俱具美,似无可议;然试取唐之拾遗、供奉、襄阳、次山、苏州、昌黎,以及东野、乐天、长吉诸人之作观之,虽途分派别,而各留性情面目于数百年之后,与读者相见于蓬窗土屋之间。东坡、山谷、放翁宗杜,欧阳宗韩,而不得名之为杜、为韩,无他,各有真也。信阳兼收并采,循声体貌,规规然惟古人为步趋,诗则美矣,曰此自成为信阳之诗,吾不谓然。北地才加纵,而一于尸杜,厥失则均。于鳞、元美而下,流滋滥矣。故余尝谓宁为钟、谭,勿为王、李,非好诡趋,故有激云然也……杨诚斋诗数变其体,一旦取而焚之,遂自成一家之言。学者仰天俯地,作为文章,不尽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不尽去古人之书,亦不能自成其文……近日新城之学遍天下,余以为一信阳而已。信阳画自唐以上,新城则兼泛滥宋元以下,故每作一诗,胸中先据有一成诗,而后下笔追之,必求其肖而止。所作具在,可一一按也。余非敢瑕疵前人,然恐诗道坐敝于此,则明七子不独任咎。
戈涛指出,历代诗歌均能自具面貌,只有明代诗歌不然,这是因为从前后七子以至于竟陵派“唯古人为步趋”,诗歌虽然写得很美,却迷失了自我,失去了性情之真,不能像唐宋诗人那样“各留性情面目于数百年之后”。而清初王士禛倡导的“神韵派”同样有此流弊,只是其学习模仿的对象由唐以上改为宋元以下罢了,故诗道大弊的责任不仅在于明七子,神韵说同样也难辞其咎,其批判的矛头直指王渔洋。边连宝《酬芥舟为作生传,并叙诗稿,兼索杜、苏二家诗注叙》称其“愤然欲拔新城帜,舌锋笔阵争翻腾”“孤军锐卒捣窟穴,百年壁垒失完坚”。《寄呈芥舟》云:“一自新城张伪帜,百年坛坫走滕邾。定知感慨今犹昔,敢道英雄君与孤。”可见戈涛和边连宝一样,均是神韵说的反对者。刘青松先生指出,戈涛看到王渔洋过度强调“神韵”最终陷入自相矛盾,从而失去性情,属于知本之论。在王士禛“神韵说”笼罩诗坛的情况下,戈、边二人以大量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不同的文学理念,在北方诗坛上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二 戈涛的诗学途径:由韦应物而入,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
戈涛早年从沈阳戴亨学诗,又受知于嘉兴钱陈群。戴亨(1690—?),字通乾,号遂堂,与陈景元、长海并称为“辽东三老”,有《庆芝堂诗集》十八卷。金兆燕《庆芝堂诗集跋》称戴亨之诗“上自汉魏,下逮初盛唐诸大家,皆撷精取液,如金入冶而镕铸之,不肯稍降一格以狥时目”,《清史稿·文苑传二》曰“其诗宗杜少陵,上溯汉魏,卓然名家”。戴亨与戈涛之父戈锦为同年友人,作为戈涛的诗学启蒙者,其兼取众长、自成一格的诗学路径无疑对戈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戈涛的诗学途径,边连宝《刑部掌印给事中芥舟戈公传》曰:
其少作风怀疏逸,绝似右丞,时而穆然玄淡,则直探左司之奥。迨其后,两游豫章、滇南,尤得江山之助。演迤涵泓,闳大以肆,汪茫浩衍中其风骨仍复稜然可揣,盖不可以一家名矣。
所谓“左司”,即唐代诗人韦应物,因其曾任检校左司郎中,故称。边连宝指出,戈涛早年诗歌学习主要模拟王维和韦应物这两位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崇尚“穆然玄淡”的诗风,在其游历江西、云南后,因得江山之助,诗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周蒌亭诗序》中,戈涛亦曾提及自己早年对韦应物的钦慕,其曰:
余幼学诗,窃慕左司风格,已而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虽极力驰逐,出之终不免于艰蹶,其率然有得,虽不敢谓阑入陶韦之室,然每恍然自悦于心。
他交代了自己从幼年学陶渊明、韦应物进而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的诗学过程,并指出之所以对陶、韦应之诗“每恍然自悦于心”,是因为性之所近。戈涛在《苹果诗》中曰“于诗韦苏州,于人林处士”,也可见其对韦应物之心仪。边连宝《赠芥舟》诗云:“我爱子戈子,华年慧业深。吟诗学古淡,直抉古淡心。萧萧松竹韵,泠泠琴磬音。音韵岂徒古,性情实匪今。坐令浮竞者,浩叹空弥襟。”诗中也提到戈涛早年“吟诗学古淡”的经历。由于性喜陶渊明、韦应物之诗,戈涛早年诗作确实多有平淡清远之风,如《访东涧僧不遇》曰:“我闻东涧僧,能诗似齐己。策杖一寻幽,潺潺两涧水。深院闭无人,微闻落松子。”深得陶、韦诗淡远之风神。又如《别盘山》云:
青沟住独久,珍重别髯髡。
石订重来约,山留昨夜魂。
东西分涧水,次第下烟村。
回首从前路,天城近石门。
《自玉石庄达天成寺五首》云:
步步泉声急,层层石色分。
入天无寸土,横路有孤云。
野鼠时惊客,林猿各觅群。
郁然深处望,岚气晓氤氲。
稍缘一径仄,渐逼万峰齐。
曲折藏幽处,人家过涧西。
数惊石欲堕,回讶路全迷。
几日桃含蕊,残红流满溪。
余寒犹中客,知是入山深。
踯躅花迎路,栗留声出林。
偶随渔者去,或负钓竿吟。
小坐莲池北,萧然净我心。
云壑都回转,峰峦互带缨。
于山为曲室,有寺号天成。
绝壁宸章迥,高峰佛塔声。
老僧谙旧迹,指点涧泉名。
树影沉沉合,山光簇簇浓。
苍烟来绝壑,落日在高峰。
晚饭抄云子,香泉芼鹿茸。
耽吟殊不寐,卧听上方钟。
这些描摹自然的山水诗平淡自然、清新如画,都酷似王孟韦柳之作。纪晓岚《曹绮庄先生遗稿序》曰:“芥舟戈太史前辈则山水清音,翛然自远。”说得大概都是戈涛此类诗歌。
除了早年醉心于陶、韦之外,戈涛中后期的诗歌则“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至于其原因,边连宝已经指出与其游历西南的经历有关。戈涛在《默堂诗叙》中也曾述及典试云南的经历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丙子夏,余与默堂先生典试云南,往返百八十余日,舆相踵,舍相接,每过名山大川,幽奇隐怪之境,晦明风雨,朝夕变幻;以及荒墟废迹,骚人逸士之所留遗,予往往有所述作。”为西南地区奇丽的山水所激发,戈涛诗歌开始由陶、杜之平淡转为奇崛恣肆。另外从个性气质来看,戈涛亦不喜绮靡而喜雄奇。陶梁《国朝畿辅诗传》曰:“其论诗也,绮语、理语、剽窃语、糜弱语皆所切戒,故所作格律峻整,气力磅礴,于高、岑、李、杜、王、孟、韩、苏诸家均登其堂而哜其胾焉。”边连宝《刑部掌印给事中芥舟戈公传》也称其“居恒谈议以及诗歌,从不作绮语,余尝为小词示之,辄颦蹙曰:‘何必为此?’余为之竦然”。也就是说,戈涛在审美类型上,不取绮丽柔靡,而取李杜韩苏之雄浑壮丽、大气磅礴,当然这也是慷慨悲歌的燕赵诗人中最为常见的风格类型。
戈涛诗歌学习李白的痕迹相当明显,如《天姥峰》曰:“天姥插天势奇绝,灵峰自古压瓯越。下瞰方城拱赤城,举头夕阳乍明灭。遥见无边青色变,巘崿峦岗纷折叠。兀然拔起四万仞,不知乾坤何郁结。”明显是模仿李白的同题名作《梦游天姥吟留别》。此外,《破石崖》《庐山》等诗模仿李白乐府的痕迹也相当明显。如《破石崖》曰:
忽然突兀二万八千丈,疑是西华玉女之芙蓉。南望海天黝然黑,不知大道何冥冥。光收电影暗,雨洗岚烟青。庞眉老宿有时拄杖而独立,时有松鼠无数上下跳跃松林中。
《由隘口入归宗寺历开先观瀑布过三峡至栖贤禅院》曰:
瀑布挂天七万八千四百尺,银河乱落明珠跳。逡巡却立不敢逼,寒风飒飒吹鬓毛。坐我漱玉亭,我怀南唐朝。万金之堂易彼万乘国,对此令我名心消……雷霆砯訇三峡斗,九十九水汇此回塘坳。溯流上层梯,鸟道摩秋毫。回首宫亭湖,波光动林梢。松林趺坐耸肩息,时有松鼠跳踯衔人袍。
其宏大豪迈的气魄、大胆的想象和夸张、腾挪跳荡的句式和音节,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白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诸篇。此外,戈涛诗中有些字句也有模仿李白诗歌的痕迹,如《九日偕周挹源、李召林荇洲登瀛台集香泉社四首》其四“大雅久不作”直接用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成句,《西川行送吴右襄》“短衣长剑缦胡缨”亦化用李白《侠客行》“赵客缦胡缨”。
在“河间七子”中,戈涛和边连宝均师法杜诗,边连宝著有《杜律启蒙》,戈涛曾为之作序。和其友人边连宝一样,戈涛对杜律亦极为推崇,在其诗中化用杜诗之处很多,如《望盘山》“忍向尘埃没”,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自洛阳寄随园》“魂来昨夜隔枫林”,化自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手把新诗细细吟”,出自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卢生祠》“疏帘清簟应无梦”,化自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九日偕周挹源、李召林荇洲登瀛台集香泉社四首》其四“风竹娟娟净”,出自杜甫《狂夫》;《送周觐光》“况当俦侣稀”,化自杜甫《归燕》;《自玉石庄达天成寺五首》其三“萧然净我心”,出自杜甫《刘九法曹郑瑕丘石门宴集》。戈涛学杜能够加以变化,自成一格,如《天姥峰》“俯而一望众山小,荡胸云生眦鸟决”,明显化用杜甫《望岳》之成句,却进行了凝缩,句式也由五言变为七言。又如《自玉石庄达天成寺五首》其五“晚饭抄云子,香泉芼鹿茸”,句法出自杜甫《与鄠县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饭抄云子白,瓜嚼水精寒”,“入天无寸土,横路有孤云”,句法出自杜甫《别房太尉墓》“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但戈涛能在继承中加以变化,故能学杜而不似杜。另外,杜甫七律中多用“当句对”,戈涛对杜诗中的这种特殊句法也曾进行模拟学习,如其“东家篱借西家竹,上阪泉浇下阪田”二句明显是学习杜甫七律中的“当句对”,可惜该诗仅剩此残句,若非边连宝《杜律启蒙》征引,恐怕后人已难以窥知其模拟杜甫此种句法之痕迹。
此外,从戈涛某些诗句打破自然节奏、诗句的散文化、用字的生硬以及诗风的横放来看,其诗歌亦有学习韩愈、苏轼的痕迹,然杜诗也是韩诗、苏诗之源头,故而宗杜学杜无疑是戈涛诗歌的主要倾向之一。
三 “上下沿溯,归于自得”:戈涛诗歌之艺术风格述略
戈涛的诗歌虽由韦应物而入,进而泛滥于李杜韩苏诸大家,但由于他秉持以性情为主的诗学观,故能转益多师后自成一格。李中简《芥舟先生小传》称戈涛诗“上下沿溯,归于自得,体气苍凉高洁,类其为人”。“归于自得”之评乃知己深契之言,在戈涛看来,学习模仿前人诗歌只是手段,其目的仍是表达个人之真性情,故他论诗强调“自得”和保持自我个性。其《随园诗序》曰:“不尽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不尽去古人之书,亦不能自成其文。”又曰:“今读随园诗,纵横排奡,不可方物,而各有一随园者存。即其晚年深造自得,其刚果之气不能尽没于冲夷澹寂中,此随园之真也。其骨近韩,其神近孟,其气近李,其情思近卢……至谓某篇学某、某篇学某某篇,则断断无有。”此外,边连宝《病余长语》曰:“芥舟论余诗风……所谓‘随园之诗,自成其为随园而已’。又曰:‘各有一随园者存’,则非知余之深者不能道也,故余《酬芥舟》有云:‘敬取一语敢拜受,行间字里皆随园。’”戈涛指出,边连宝“深造自得”后仍保持自我的个性,并不随人俯仰,所谓“行间字里皆随园”,这才是“随园之真”。戈涛《边徵君传》曰:“故其率然有作,直吐其胸中所欲言,倏如风樯骏马、快剑长戟,奔流激湍,粗沙乱石,悬崖绝涧,瘦竹枯木,丫杈万状,不可睨瞩。”戈涛认为边连宝能直抒胸臆,表达真性情,并不屑在古人门下求活计,这才是其诗歌最可宝贵之处,这虽是在称赞边随园之诗,其实又何尝不是夫子自道呢。戈涛诗歌中虽有模拟前人的痕迹,但他更着意于抒发个人的真情,如《奉使过河间夜宿》云:
五更钟又动,梦断自沉吟。
一作京华客,栖栖直到今。
荒庐门径改,老屋雨风侵。
何意邮亭宿,居然是故林!
诗人奉使途中经过故乡河间,夜宿馆驿之中,慨叹自己多年来宦海浮沉,竟至故园荒废,有家难回。此诗前半乃用偷春格(即首联对仗,次联不对),便将这种感慨之情强烈地表现出来。又如《上谷归途避雨夏调元村居》云:
伏雨动浃旬,积潦忽成川。
驱车何所适,始叹行路难。
泥沙湍未穷,云雷方遘患。
仆者嗟沉瘁,客子衣裳单。
故人居道左,停鞭叩松关。
跣足倒舄履,握手捐温寒。
呼儿具茗荈,斗酒萦襟颜。
苦云命不易,莫辞酒杯宽。
往者暨边子,乘春来追攀。
壁上有遗句,蠹蚀半凋残。
春雨杏花白,秋风槲叶丹。
撚指六七载,历历思前贤。
与君共郊牧,晨夕阻往还。
美人况已远,秋水生寒烟。
人生感聚散,暌隔在中年。
顾我颔须满,悲君鬓发斑。
儿女累须毕,功名志宜闲。
庶当理袯襫,从子桑麻间。
这是一首叙事诗,写途中于友人村居避雨情事。从篇章结构、情感线索、遣词造句来看,此诗都明显有模仿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痕迹。但戈涛抒发的是“人生感聚散,暌隔在中年”之慨叹,与杜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又明显不同;而从表现手法来看,此诗过滤掉了杜诗“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那样的人间烟火味,用“春雨杏花白,秋风槲叶丹”“美人况已远,秋水生寒烟”抒发了对时光流逝的怅惘之情,意象清新明丽,富含盛唐韵味。可见虽源于古人却能自铸新词,这就是戈涛诗歌的“自得”。
总的来看,戈涛诗歌除了具备自然平淡、清新明丽之风外,亦多有雄奇豪迈之音。如《入滇歌》云:
娥嫏坡袅双髻鬟,石虬尾掉江沧烟。一声长啸万山顶,此身真落天南端。玉虚九阙呼吸接,天风泠泠吹昼寒。回首下视云漫漫,海色灭尽黔中山。鹰崖狼箐稍倔强,蚁蛭破碎中躜岏。青丝辔头黄金缠,玉踠不惜石子弹。远山离立如静女,翠螺窕窈刚齐肩。北溟客到南溟天,六月正御扶摇旋。平生壮游差一快,浩歌抵当逍遥篇。我闻四极八度九万里,日月不到无穷边。此于天地万万一,安得侈语周人环。夏虫春秋朝菌朔,委蜕欲往从群仙。浮邱拍手洪崖笑,挥斥六合骖龙鸾。不然弄笔老牖下,俯仰斗室何其宽!
诗中描摹了云南奇丽的山水景物及其对诗人产生的强烈心灵震撼。此外,《庐山》《天姥峰》《破石崖》《荆门行》《老鹰崖》诸篇,也颇能代表戈涛五、七古雄奇豪迈、清旷超逸之诗风,如《老鹰崖》曰:
有仙超超越八极,我亦千载腾高空。长啸四山应,立久心自清。君不见老鹰崖相对,终古人难行。
《天姥峰》曰:
浙江潮声八月来,鞭打雷霆走冰雪。伍胥一去钱镠住,百万神兵弩飞铁。渺渺水影东南流,十丈长帆鸟一瞥。扶桑指点日出处,遥闻雄鸡天欲白。云为车,风为马,徘徊俯仰灵岩下。李白一梦又千年,瑶草灵芝更谁把?
《庐山》曰:
熊虎叫啸绒狖啼,蛟虬怒蟠赴深穴。远树叠远峦,远峦乍明灭。五老苍颜耸肩立,岌岌峨冠拱揖客。大笑风来飘翠带,影落鄱阳半湖碧。
这些诗歌超凡拔俗,想落天外,充满雄奇奔放的浪漫主义色彩,既是出入李杜韩苏诸大家的表现,同时也是戈涛独特个性的诗化体现。
四 戈涛在清代诗坛的地位及其影响
戈涛的诗歌在清代颇受推重,钱陈群是其最早的赏识者,翁方纲《坳堂集序》云:“乾隆辛未,予始从香树钱先生论诗,先生于北方学者首推宋蒙泉、戈芥舟二君。”戈涛是纪晓岚的同里前辈,故纪晓岚对其人其诗极为推崇,其《赠戈芥舟二首》曰:
长鲸跋浪出,万里沧溟开。
三山岌欲动,倏忽生风雷。
夫君振高节,早岁驰雄才。
胡为久蹉跎?幽郁使心哀。
绿草春离离,感激黄金台。
饥鹰思掣鞲,疲马思疆场。
壮志虽不遂,猛气犹飞扬。
缅怀古烈士,抚己多慨慷。
不有辛苦人,焉识劳者伤?
长铗发哀弹,恻恻沾衣裳。
另外,纪晓岚《镂冰诗钞序》曰:“雪厓以后,北士之续其响者,唯景州李露园、曹丽天,任邱边随园、李廉衣、献县戈芥舟,寥寥数人,惜其遗集皆在存亡间,不甚著也。”法式善《试墨斋诗集序》云:“我畿辅之地,沿燕赵遗风,悲歌慷慨,使酒挟剑,奇气郁勃,皆能摇撼星斗,镂刻肾肝也……李文园、边秋崖、戈芥舟诸先辈,余皆获侍其杖履,闻所议论,东南人士无不奉为依归。生平著述,脍炙人口,惜无人发凡起例,勒成卷帙。”陶梁《国朝畿辅诗传》引《红豆树馆诗话》曰:“乾隆中,畿辅诗人盛于河间,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为巨擘。”范凤鸣《愚仙吟草序》云:“夫献陵为日华故壤,我朝二百年来,名流辈出,馆阁钜公如纪文达、戈芥舟,皆以燕许手笔,鼓吹休明。”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戈涛“诗格律谨严,气势浩瀚,兼有高岑、王孟、苏陆诸家胜概”。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之《坳堂诗集》提要曰:“边连宝与戈涛互作序言,共同驳斥神韵之非,于乾嘉诗坛独树一帜。”总之,戈涛在清代诗坛占据着重要地位,可惜的是,由于《坳堂诗文集》流传甚少之故,当代学界的诸种清代诗学史均未提及戈涛。王长华主编,李延年、江合友撰《河北古代文学史》第三卷第二编《清代河北文学》部分,于第一章第三节“任丘边氏家族及其河北籍友人诗歌创作”中首次提及戈涛诗歌,然其所论过于简短,显然只是将戈涛作为边连宝的陪衬看待,且只涉及戈涛山水纪行诗的地域特色,尚未能对戈涛诗歌的整体特色进行全面分析。2016年,刘青松整理的《坳堂诗文集》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刘青松辑校的《戈涛、戈涢诗集》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相信随着戈涛诗文集整理本的相继问世,学界对戈涛诗歌成就特色的认识会愈发深入,对其在清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当会有更为精准的判断。
总之,戈涛为“河间七子”之翘楚,清代中期的代表诗人。在“神韵说”和“格调说”此消彼长的交替期,他和边连宝共同反对“神韵说”机械拟古之流弊,强调抒发真性情,保持个性独立,并以丰富的创作实绩践行了自己的诗歌理论。戈涛的诗歌由陶、韦而入,泛滥于李杜韩苏诸大家之间,形成了清旷超逸、雄奇豪迈的独特风格,被清人推为畿辅诗人之“巨擘”,其在清代诗学史上理应占据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