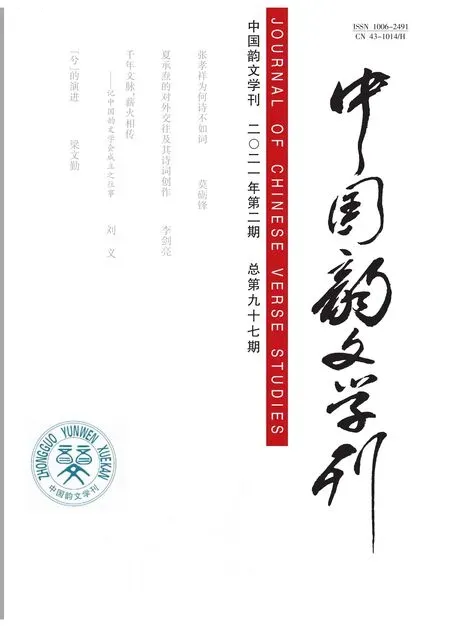汉魏六朝离别诗的主题演变及其内在动力
毛若苓
(北京工业大学 国际学院,北京 100124)
离别是古典诗歌中最常见的描写对象之一。汉魏六朝时期的“祖道”活动,既是专门为远行之人举行的告别仪式,又是人们集会和社交的场合,其中往往会出现众人赋诗的情形,这正是《文选》中“祖饯”类诗歌出现的现实条件。它们集中描绘告别时的情形和感情,可以说是专门的“离别”诗,然而,对离别的描绘显然不仅存在于“祖饯”中。《艺文类聚》中的“别”类就囊括了一部分被《文选》归入“赠答”或者“公宴”类的作品。将这些作品一起考察就会发现,早期诗歌各类题材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离别”主题也常和其他题材内容杂糅一起。而到了南朝,“离别”与其他题材之间的界限变得清晰起来。因此当代学者普遍认为,“离别诗”作为一种诗歌的题材类型是在南朝形成的。
哪些诗人在作为一种“题材类别”的离别诗的形成过程起到了关键作用?“离别诗”又有什么共同特征?它们和同样展现了离情的赠答诗与宴会诗的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不乏讨论。日本学者松原朗准确抓住了六朝离别诗的主要特征,指出了鲍照和以沈约、谢朓为代表的永明诗人在“离别诗”成熟的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过,若将其他题材中对离别的表现一起纳入考虑范围,这个过程以及鲍照、沈约等诗人在提炼主题方面起到的作用尚可详加讨论。
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诗歌的情感内涵通常是被重点考察的对象,而诗歌体式的演变及其与离别主题提炼之间的关系却很少被提及。如果将离别诗的演变放到整个五言诗体式演变的视角下考量,可以发现,齐梁诗人在诗歌体制上进行了有意识的、自觉的创造,而这种追求与诗歌对情感和主题的提炼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新题材成立的内在动力之一,这也正是本文将详细讨论的内容。
一 汉魏晋赠答、祖饯、公宴类诗歌中的“离别”
《文选》中“祖饯”类诗歌,从曹植的《送应氏》到沈约的《别范安成》,一共只有八首。此外,有大量写在离别时刻、抒发离别之情的诗歌是以“临别赠言”的方式表达的,被《文选》归入了“赠答”类。还有一部分,因为具有“祖道”活动强烈的社交色彩,被《文选》归入了“公宴”类。因此,讨论诗歌如何书写离别,就需要把赠答、公宴、祖饯等几类作品一起纳入讨论范围,它们之间的交错离合也可以帮助我们确认“离别诗”与其他题材之间的界限。
赠答诗的传统源远流长,邺下文人与曹氏兄弟的诗歌往还,是这类题材第一次在文人群体之间大规模出现。在诗歌往还中,建安诗人抒发彼此的情谊、抚慰和劝勉,真诚袒露自己的处境和内心忧虑,展现自我形象与人生追求。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此时赠答诗的基本底色是乱世之中的生命忧患和立功、立言以求不朽的精神追求。因此,在文人互叙交谊、君臣之间表达提携之意和知遇之恩的社交性之上,建安赠答整体笼罩着一层生命忧患感。赠答之中,多有“赠别”。它们通常将离别与世道艰险、人生忧患联系在一起,包含了大量铺叙交谊、劝勉人生、哀叹命运的内容,离别之情只是友朋赠答多层内容中的一个部分。如王粲的《赠蔡子笃》,是送友人离开荆州时的告别之作,“风流云散,一别如雨”的离别之悲,背后是“悠悠世路,乱离多阻”的乱世忧患和“人生实难”的生命哀叹。
在明确题名为“送别”的诗作中,也有与赠别相同的精神底色,例如《送应氏》二首。第一首全篇哀叹登高远望时所见洛阳宫室的焚毁和乱世之中变化的无常,基本与“送别”主题无关。第二首诗则描写了一个送别宴会的场景,诉说朋友离别的悲伤和深厚友谊。在“天地终无极,人命若朝霜”的忧患当中,宴会自然也是“难屡得”和“不可常”的。将之与王粲之作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所以被《文选》归入“祖饯”类,是因为第二首诗的主体描绘了“告别时刻”的场景。诗歌由宴会场景与离情共同构成,二者并存,才是这个主题区别于其他临别赠答的关键。
西晋的赠别诗以二陆之作为代表。诗中充满了“家邦翻覆”以及生者“凋落殆半”之际的远离亲族之痛,还有与其他西晋诗歌相似的玄学观照——如“六龙促节,逝不我待”和“天步多艰,性命难誓”这种“天”与“人”相对视角下的人生哀叹。诗人们不仅提及离别时刻的“临觞”与“饮饯”,还尤其突出“牵世婴时网”这种“不能由己”的游宦之苦。与建安之作相比,二陆之作的“离别”主题更加明确,他们选择以对句来展现对方和自己在地理空间上的分隔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南归憩永安,北迈顿承明”。这种对地理分隔的强调在后来的南朝离别诗中反复出现,成为构成离别主题的重要元素。
然而,在《文选》的分类中,二陆展现沉痛离情与游宦之苦的作品并没有被划分在“祖饯”类。《文选》在这个时期的选诗依然十分看重对送别宴集和送别时刻行为的描写。入选的两首是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和潘岳的《金谷集作诗》,它们描绘的是饯别活动以及告别的惆怅。然而,孙诗除了开头提及“饯我千里道”之外,主体并非抒发离情,而是西晋诗中常见的凶吉难测之叹和达人悟道之想。潘诗中有“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的离愁别绪,诗歌的主体却是“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的社交活动。比起陆氏兄弟的告别,这类作品中的作为“宴集”的社交性要远远大于离情本身。
实际上,西晋诗歌中与“祖饯”活动关系更加密切的是大量应诏而作的“祖道”诗,这类作品多为四言颂体,为应诏、应制之作,更接近西晋的“公宴诗”,而非抒发离愁之作。总体来说,西晋诗中深刻的“离情”主要存在于以陆氏兄弟之作为代表的赠答诗中。大量的“祖道”诗是无关离情的,即使是被《文选》收入“祖饯”类的作品,“离情”往往被玄学思考或者宴集描写所覆盖,离“公宴诗”只有一步之遥。实际上,东晋义熙年间刘裕组织的戏马台送别宴集,其中谢灵运、谢瞻的“送孔令”之作,写的是饯别宴会,却被《文选》直接划入了“公宴”类。
东晋诗几乎完全笼罩在玄风之下,赠别之作也不例外。“离别赠言”的内容高度相似:双方的交往是“友以淡合,理随道泰。余与夫子,自然冥会”,情谊则“如彼清风,应此朗啸”。这些作品呈现的是士族权贵交游的仪式感以及玄风陶冶之下的理想人际关系和精神意趣,即使是离别赠言,“离情”也远不是诗歌所要抒发的重点,而全篇写离别时刻的作品几乎不见。
晋宋之际的两位大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也有赠别之作。陶诗大多是书写友人来访之乐与临别赠言,例如《答庞参军》(五言)、《赠羊长史》和《与殷晋安别》。比起描述离别,陶诗更侧重描绘双方的深厚交谊,展现其中稠厚的人情味道和诗人守节生活的志向。即使中间有“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这样表达分别的句子,重点也始终不在倾诉离情。谢灵运的赠别诗多写给谢瞻、谢惠连等同族昆弟,如《赠从弟弘元》《答中书》《赠安成》等。他们在告别中追叙家族史的荣光和自身仕途经历,回忆往昔亲族往来,哀叹后来的四散奔波。比起陆氏兄弟,谢氏虽无家国翻覆的血泪之悲,却同样有世路奔波的倦意,还增加了东晋以来返归山林、以求自然的玄学理想和趣味。诗中“凄凄离人,惋乖悼己”的离别之情被完全笼罩在复杂的铺叙之中,最终一切情感都以“守道顺性,乐兹丘园”的精神追求为终结,离别的哀伤也归于平静。此外,谢灵运的《邻里相送至方山》被《文选》纳入了“祖饯”类。它确实是一首集中描绘“告别”的诗作,叙述了离别发生的原因、告别时刻所见的景物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感,最终表达劝勉之意。然而,诗歌中的“离情”重点并不在人的分别上——谢灵运不仅是要告别一系列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将要迎来“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的“幽栖”生活。这和谢灵运在行旅诗中展现出来“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精神追求一脉相承。
经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从汉末到宋初,个体之间深刻的离情始终包含在“赠答”之中。临别赠言并没有固定的内容,大部分时候,离愁别绪并不被单独书写,而是在诗人铺叙双方交谊的过程中与其他复杂内容融合在一起。分别时刻的不舍、双方的地理分隔、对离开者处境的想象、与自己处境的对比以及离别带来的痛苦,常与对人生、时代乃至整个天道运转中人的命运的哀叹密切关联,与自己的精神追求关联。“离别”始终没有被单独提炼出来,没有固定的展现方式,也始终和同时代的其他题材作品一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共同精神底色。与此同时,较为纯粹的对“离别”事件的描写存在于“祖道”类作品当中,而这类作品一直与“公宴”界限模糊,它们有相当强的社交性,“离情”反而不是被集中展现的内容。可以说,一直到刘宋前期,“离别”还没有被诗人单独提炼出来而成为一种题材,没有成为被特意描写的对象,也还没有相对稳定的“别诗”的表达方式。
二 故人情谊与别后相思:南朝诗人对“离别”主题的提炼
刘宋中后期,鲍照的作品对离别的展现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它作为一种诗歌“题材”的范畴也逐渐清晰起来。鲍照的赠答除了如《日落望江赠荀丞》等少数作品外,大多是明确的“别诗”。与此前的“祖饯”类作品多以宴集为核心不同,鲍照虽也提到宴会,但更倾向于用符合心境而又新鲜写实的山水描写来构筑离别的画面。以《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为例:
风起洲渚寒,云上日无辉。
连山眇烟雾,长波迥难依。
旅雁方南过,浮客未西归。
已经江海别,复与亲眷违。
奔景易有穷,离袖安可挥。
欢觞为悲酌,歌服成泣衣。
温念终不渝,藻志远存追。
役人多牵滞,顾路惭奋飞。
昧心附远翰,炯言藏佩韦。
作为“赠别”,诗歌并没有铺叙自己和庾中郎的交谊,而是开篇就用山水描写构筑了风寒日昏、雾远波长的离别环境,这是鲍照尤为擅长描绘的秋冬阴暗凄冷的水上风景。本身就带有悲戚感的山水又更加触动了友朋的离别之悲和自己的羁旅之思。除了山水之外,诗歌中的一切也都围绕着“离别”构筑,宴会是“悲酌”,本该让人感到欢乐的歌舞也沾染了悲戚之泪。整首诗歌可以说是对离别的集中描写。
在鲍照其他的赠别诗中,《送盛侍郎饯侯亭》题目是饯别,但宴集在诗歌中并没有明确出现,反而是“高墉宿寒雾,平野起秋尘”的凄寒之景,衬托了“君为坐堂子,我乃负羁人”的憔悴悲情。《送别王宣城》用“广望周千里,江郊蔼微明。举爵自惆怅,歌管为谁清”的山水和宴会描写来突出离别的时刻以及其中的悲哀。《送从弟道秀别》中,离别发生在“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的时刻,而这一刻诗人见到的是“浸淫旦潮广,澜漫宿云滋”这样昏暗的风景,正衬托了“天阴惧先发,路远常早辞”的告别带来的阴郁心境。一方面,正是将笔墨分给了对离别时刻风景的描写,鲍照在宴会之外为刻画离别时刻找到了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山水描写塑造的环境氛围与离愁别绪相互呼应,让笔墨集中在离别的氛围和情绪之上,而非对具体的交谊进行反复铺叙,这又集中凸显和提炼了“离情”。
鲍照笔下的离别主题常与“行役”主题结合。由于鲍照终身位沉下僚,一生都在不同的主君之间辗转漂泊,对仕途始终怀有极大的恐惧和疲惫。他各种题材的诗歌都会带有明显的寒士孤苦的精神色彩。诗中人以“役人”、“游子”、“负羁人”的身份出场,“劳舟厌长浪,疲旆倦行风”的孤独与疲惫,“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的寒士生活的无望,和离愁别绪一起,共同构成了鲍照笔下的离情。这一点与陆机兄弟的赠别有相似之处,不过,与建安和西晋的离别展现相比,鲍照离愁背后的人生感叹,不再建立在对天地人生运行规律的整体思索上,而是下层士人在世俗生活中完全无望的常态性孤独与悲哀。
总之,鲍照笔下的“离别”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对“离别时刻”的描绘重点在山水而非宴会,这使得对于离别的书写摆脱了此前“祖饯”类中以叙述社交宴集为主的方式,走向了以风景和情境暗示、象征情感的方向,更集中抒发离情,也就和“公宴”真正区分开来。其二是诗歌对告别氛围的烘托、对别情的提炼,使得离愁别绪开始从包含了告别、言志、铺叙交谊、哀叹人生等种种复杂情感的“赠答”中抽离出来。这些特征让“离别”本身成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共同形成了“离别”与其他题材的界限。到了南齐永明年间,永明文人的一系列告别宴集之作,使得对离别的书写进一步与其他情感抽离,并带有了类型化的色彩,让“离别诗”成为一种独立的题材类型。
永明九年春,谢朓离开京城西上荆州,在告别宴集上,永明诗人进行了集体赋诗。此外,还有一场为同是西上荆州的萧衍饯别的宴集,与宴者也进行了集体赋诗。根据现存的诗作可知,参加送别谢朓宴会的人有沈约、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人,参加送别萧衍的人则有王融、任昉、宗夬等人。这些诗歌在数量上构成了南齐离别诗的主体。由于南齐文人频繁担任宗室幕僚,多在地方辗转为官,范云、沈约、谢朓等人相互之间也多有送别之作,可以一起纳入讨论。
永明年间文人交游的场合多是王俭、萧子良组织的文化活动,交往中包含了大量自觉的、带有文艺才华和技巧的游戏与竞争意味的内容,往来之间最被突出的是个人的才学、技艺和风度。永明文人的友朋情谊正是建立在这种交往方式的基础上。双方彼此的赞美不全是社交辞令,还带有“知己”之情和对后辈的“提携”之意,共同构建起参与者的文化声望和地位。因此,告别宴集上集体赋诗的场合兼具社交仪式、友朋送别与切磋文义三层意味。在这类场合完成的诗作,从性质上来说,首先是对“离别”这个题目进行的“同题赋诗”,其创作场合、方法与永明时期诗人集体创作的赋题乐府和咏物诗并无太大区别。三者的情感内涵也有明显共通之处:赋题乐府和咏物诗倾向于对“怨情”与“思情”这一类没有明确指向性的情感进行吟咏,“相思离别”尤其常见,而“别情”经过合适的处理,也正能够符合“怨”与“思”的特征。然而,由于与宴者之间确实存在个人情谊,告别宴会上的创作也就并非只是诗歌艺术的同台竞技,其中的情感也不能只用赋题乐府和咏物中最常见的男女怨思来表达。总之,永明时期的文人关系和诗歌的创作场合使得这些离别宴集之作具有多重意味,也使得它们在创作方法上高度相似,倾向于集中展现没有具体指向性的、类型化的“离别之情”。这种情谊具有一定的社交和文辞游戏意味,但其中包含的个体情谊,又远高于一般“祖道”场合的社交辞令和应制赋诗。这与建安具有抒情言志性质的赠答诗、二陆的赠别诗、两晋的社交辞令乃至鲍照充满了寒士身份感的作品都截然不同。这正是永明诗人提炼离别主题的外部环境条件。
既是“同题赋诗”,凸显题中之意就十分重要。比起前代诗人,南齐诗人前所未有地重视以各种方式提炼、集中突出“离别”主题。典型的例子就是谢朓本人的《离夜》:
玉绳隐高树,斜汉耿层台。
离堂华烛近,别幌清琴哀。
翻潮尚知限,客思眇难裁。
山川不可梦,况及故人杯。
谢朓描写的是一场主题为“告别”的夜间集会,与其说诗歌在写宴会,不如说是在用“离别”元素突出主题:宴会的厅堂是“离堂”,帐幔是“别幌”,思是“客思”。为诗中出现的事物贴上离别的标签,是突出主题最简单的手法,其他诗人也在使用:烛为“离烛”,歌为“离歌”,酒为“别酒”,唱是“别唱”,弦为“分弦”。这些用语的反复出现说明,诗歌的重点并非精心描绘一场宴集,而是想要充分展现“离别”的概念和氛围。
这只是一种比较初级的强调主题的方式,更能够提炼“离别”的手法是强调地理空间的分隔。虞炎、谢朓、刘绘均强调了荆州与建康的东西分离带来的哀愁:“离人怅东顾,游子去西归”,“叹息东流水,如何故乡陌”,“不见一佳人,徒望西飞翼”。展现空间的阻隔在二陆赠别诗中已经出现,南齐诗人在这种分隔上又加上了一层“关联”,从而为分别加入了新的情感内涵:沈约之作以与荆州相关的典故来暗示对方所去之地,将汉水、巫山、云梦泽等属于楚地的“风景”带入眼前的告别,“瀄汩背吴潮,潺湲横楚濑”既是分隔,又保持了联系,最终,“以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的绵长情谊,超越了地理的分隔,将身处异地的人心联系在一起。王融的“寸心无远近,边地有风霜”、萧衍的“眷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均有这层含义。友人情谊跨越山川河流的阻碍而与对方同在,这使得南齐的“离情”与类型化的男女思怨之情有所区别,显得尤为绵长悠远,这种写法也为后来的唐诗继承。
这样集中而反复的强调,使得南齐诗中的“别情”集中在“分别哀愁”与“故人相思”上,很少夹杂其他感情。比起前代诗人,鲍照已经提炼了“离情”本身,但他的“离愁”之下始终铺垫着行役之苦。南齐诗人则进一步去掉了“行役”这种较为具体的、个人化的因素,而留下了“客思”“故人”这样类型化的内容。这些诗歌展现出一种单纯的、非特殊性的人际关系:它基本无关告别双方的人生志向、政治命运、亲族关系、阶级地位甚至过去具体的交往过程和情感深浅,与对天地人生的整体思索和哀叹也没有关联,只有纯粹的、单一的离别带来的哀愁、孤独与相思。双方的关系被提炼为普遍意义上的“故人”,这代表着经历过时间洗刷而存留的普遍性的人情。
在非集体创作的情况下,南齐送别诗继承了鲍照的山水与离情结合的创作方式,创造了新鲜细腻的送别场景。如小谢《临溪送别》中“叶下凉风初,日隐轻霞暮。荒城迥易阴,秋溪广难渡”带来的衰颓摇荡之感正与告别时“君子行多露”的艰难和疲倦相配;《与江水曹至滨干戏》中“花枝聚如雪,芜丝散犹网”的轻盈纤丽也正适合“别后能相思,何嗟异封壤”这样能够克制哀愁的悠长情谊。但这些作品与集体饯别之作一样,并不会让读者窥见双方关系的独特性,不夹杂任何别的感情,被强调的依然是具有普遍性的“故人情谊”和“ 故人相思”。正是这种强调,使得故人绵长情谊在南齐离别之作中显得格外突出,也使得“离别诗”产生了强烈的类型化色彩,从而彻底与赠答、公宴等同样以人际往来为基础的题材区别开来,确立了它独特的内涵。
三 南朝离别诗提炼主题的内在动力
论及南朝离别诗创作的演变,创作场合、人际关系等外部环境对创作方法的影响一般是被较多考虑的因素。然而,如果将离别诗和同时期其他题材作品一起观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与诗人对新体诗的尝试密切相关。
永明时期,从汉魏延续而来的五言古诗的体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至于被明代诗论家评论为“古意尽矣”。除了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四声之外,诗歌篇制变短,结构方式、造语琢句也随之发生了明显改变。汉魏以来,五言古诗基本保持了以叙述性的笔调,用顺叙的方式来呈现一个比较完整的单一场景的结构方式。西晋以来,五言古诗篇幅普遍增长,形成了多层次叙述、写景、抒情的“太康体”。到了晋宋之际,谢灵运的山水大篇常以“移步换形”的方式,展现出一个观景、兴情、悟理的完整过程。虽然描写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依然保持了五言古诗传统的叙述体制。南朝之前,“祖饯”类诗歌几乎都是集中描写送别宴会的场景,而赠答诗则多在告别场景里层层铺叙交谊,这正是诗歌情感内涵和体式特征结合的表现。
在鲍照的部分作品中,五言古诗中这种叙述线索和结构明显弱化。西晋以来常见的叙事、写景、抒情多层结构在鲍照笔下简化为景与情的结合,诗歌篇幅也明显变短。在不少行旅诗中,鲍照以突兀奇险的景物描写,将诗歌直接带入阴暗悲凉的抒情氛围,省略对赶路、登临或日常所见所闻之事的叙述,也不直接描绘情感产生的过程。这种方法也同样被运用在赠别中。叙述性降低、结构简化以后,诗人变换了情与景的勾连方式,强调风景与情感的共通之处,山水不仅是眼前告别宴会情境的组成部分,还成为集中烘托和提炼情感的载体。体制的简化显然也让诗歌的情感内涵相对集中,起到了提炼主题的效果,这一点也为南齐诗人所继承。
鲍照诗歌在体制上尚未超出汉魏以来五言古诗的框架,永明诗人则开始大量尝试篇幅短小的八句体和十句体,并对整首诗歌的结构方式做出巨大的改变。这些尝试主要分布在赋题乐府、咏物和离别这三类题材当中。由于本质上是如出一辙的“同题赋诗”,立意构思求变求新,就成为这三类题材创作的需求。由于新体诗篇幅短小,不适合进行完整的叙述或者长篇的物象铺陈,永明诗人普遍不再使用五言古诗传统的叙述性结构,也不像谢、鲍那样铺写山水,而是试图以比较巧妙而相对集中的构思立意来作为抒情核心。与此同时,在失去了较为完整的叙述线索后,如何建立诗歌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组织全诗结构,也是永明以来诗人需要处理的新问题。不少诗人继承了鲍照那种山水与别情两层结合的抒情结构,另一方面,他们也有意追求比鲍照更具新意的结构方式。这些使得南齐以后的离别诗在艺术风貌上有了更本质的改变。虽然有时这些尝试在结构上并不十分成功,但它们让诗人集中提炼离别主题,尝试以新巧的立意和构思去书写离别,使离别诗脱离了对临别赠言的铺叙和对离别时刻的场景描绘,呈现出新的情感内涵和艺术风貌。
仍以永明年间的几次告别宴集之作为例。刘绘、范云、沈约之作都可以分为景与情两个层次。在鲍照笔下,风景的阴暗与情感的忧愁相匹配,情感的共通感是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南齐诗人笔下,二者的关联则建立在“距离远而重逢难”这个核心立意上。对风景的描绘不仅是为了烘托眼前宴集的环境和情感,还要集中凸显这个构思并以此组织全诗。刘绘的《饯谢文学》中,前四句写景,每一句都在强调空间之远:水中的小洲是“千里芳”,天上的朝云有“万里色”,这些景色都在“天隅”,而这正是友人要去的地方。后四句抒情中“无与窥”、“共谁陟”、“不见”和“徒望”每一句都在集中强调往后时间中的“不可见”。范云和沈约之作则都用和荆州、巫山有关的典故,将对风景的描写建立在对荆州的想象和对距离的强调之上。范诗中隐约可见的远山和断续连绵的沙地,突出的正是远望的距离感,最终“尔拂后车尘,我事东皋粟”则用人生前途的分歧暗示了重逢之难。沈诗中“一望沮漳水,宁思江海会”,要凸显的依然是距离带来的会面之难。诗中风景看起来似乎是饯别宴会场景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它们的核心作用是与典故一起强调空间距离之远进而凸显离别主题。这意味着,在构思立意相似的作品中,宴会场景中的风景描写甚至可以完全被对距离的强调所取代。例如沈约的《送别友人》,王融的《萧咨议西上夜集》,范云的《送沈记室夜别》等,已经不能说有以山水烘托情感之意,而是全以空间距离之远去凸显别后的不可见。正是这种对集中立意的追求,使得诗歌由描绘送别场面完全转向了新角度、新构思呈现“离别”之题。
强调空间之远和会面之难,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常见构思。而优秀诗人沈约和谢朓,则有更为新巧的构思。谢朓的《新亭渚别范零陵》整体虽然也是常见的以典故构建空间距离对比再进行抒情的两层结构,但它将抒情凝结在“停骖我怅望,辍棹子夷犹”的时刻,让诗歌的情感高潮集中在这个将要分手却又停留的瞬间,使得诗歌的层次更加清晰且富有曲折意味。更典型的例子是被选入《文选》“祖饯”类的沈约名作《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在《文选》的“祖饯”类中,这首诗与排列在它之前的同类诗歌有极大差别,它完全没有描写饯别宴会的具体情境,也不曾提及眼前的山水。而与其他南朝离别诗相比,它虽涉及空间距离的对比,但更强调的是时间维度。诗歌的基本立意是以少年和衰老进行对比,凸显重逢之难。八句诗全部围绕这一立意进行组织。诗中虽然有“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暗示饯别宴会,但句意重点是时间的变化而非告别的场景。这类作品的出现说明,南齐诗人对离别的书写完全跳出了对“祖饯”场景的描写,而对集中立意、巧妙构思的重视,又使得诗歌的情感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提炼,从而让别情更加纯粹。
永明之后,无论篇制长短,立意集中、寻求巧妙的构思以组织全篇,都成为组织诗歌成篇的基本方法之一,而离别主题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展开。沈、谢之后,何逊是又一位集中描写过离别的南朝诗人。
和永明诗人们一样,何逊的大部分离别诗抒发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故人离别相思之情。他擅长以山水描写烘托别情,也同样会以空间距离遥远的对比来凸显会面之难。此外,他进一步将“离别”事件提炼为一个无言而饱含情感的分手瞬间,将抒情放置到别后相思之时。这样,“相思”不是举杯饯行时刻对双方感情深度的肯定和对未来的设想,而是被留下的孤独者对“离别”带来的情感体验的长久回味,与短暂的告别瞬间正好形成对比。以此为核心构思,何逊还为离别主题提炼出了“别后相望”这个抒情画面。如《赠韦记室黯别诗》中,“故人傥送别,停车一水东。去帆若不见,试望白云中”,送别时刻是短暂的,离愁别绪包含在无言的、暗示着空间距离的凝望之中。这个时刻结束之后,诗人才开始独自细细体味无人与共的哀愁。《送韦司马别》虽然长篇铺叙离别之悲,重点描写的却不是告别的场景。抒情从告别结束的时刻才开始,在“悯悯分手毕,萧萧行帆举,举帆越中流,望别上高楼”之后,诗歌的主体是“独愁”之人如何在回家的途中以及入夜之后辗转反侧。而名作《与胡兴安夜别》的构思特征更加明显:
居人行转轼,客子暂维舟。
念此一筵笑,分为两地愁。
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方抱新离恨,独守故园秋。
前四句,何逊将告别活动凝结为即将分手却又停留这样饱含感情的时刻,这也是谢朓曾经描绘的画面。饯别的宴席是“一筵笑”这样飞快流逝的瞬间,而“两地愁”则是这瞬间结束之后的长久结局。前四句已经暗含了告别时刻的短暂与别后相思长久的对比,因此诗歌后四句就重点描绘了孤独之人面对惆怅别情和凄凉秋景的画面,诗中的山水风景也不再属于告别的宴集,而属于那个“被留下的人”。从这首诗里就能看出,何逊继承了永明诗人在革新诗歌体制基础上对集中立意和构思的追求。而比起前人,他的构思更加新巧凝练,不仅能够集中表达离别主题,还能够提炼出本身饱含着充足感情的抒情画面。无论从情感内涵还是从诗歌体制两个方面来看,“离别”这一主题在何逊的手中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成熟度。
综上所述,汉魏以来,诗歌中对离别的描绘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既有创作场合、创作群体演变乃至时代精神变化的外在动因,同样也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动力,就是五言诗歌在体制和结构方式上的革新。在南朝之前,对离别的描写散布在赠答、祖饯、公宴等几种不同题材的诗歌中,对别情的抒发常常和其他不同的情感杂糅在一起,共同展现出诗人所处时代的整体精神特质。因此,“离别”作为一个主题,还没有被提炼出来,也没有相对固定的对离别的展现方式。进入南朝以后,鲍照对五言诗的结构进行了简化,对离别之情进行了提炼,使得对离别的描写集中在对告别场景中引发悲情的山水描写和离愁别绪本身上。山水和别情的结合使得离别这一主题第一次真正和赠答与公宴有了明显的界限。此后,南齐诗人对离别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提炼。从情感内涵上来说,他们集中描写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类型化的“故人”离别相思之情,让诗歌的情感内涵具有了类型化的色彩。从诗歌体制上来说,他们极大地改变了汉魏晋以来五言诗的结构方式,选择以立意和构思为核心去组织全诗,这使得他们笔下的离别诗完全脱离了对饯别宴集的叙述和描绘,变为以新颖的角度去集中呈现“离别”感情本身。在“离别”被高度提炼、成为诗歌的描写对象之后,作为一种诗歌题材的离别诗,才真正从和其他题材的交融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题材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