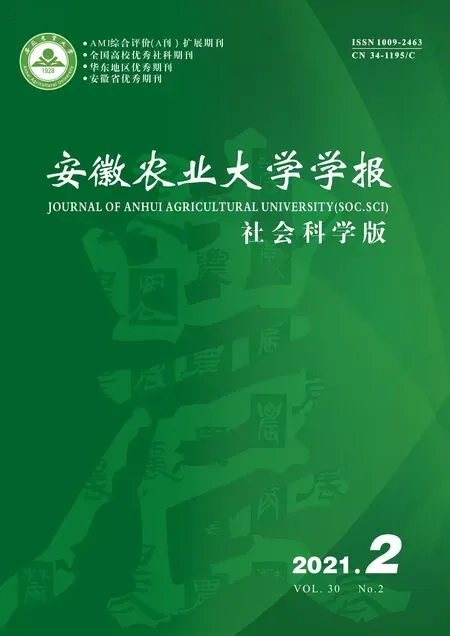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魏吴战争
崔旸菁菁,胡阿祥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三国时期,曹魏在巢湖东北岸居巢屯兵屯田,并于西北岸建设合肥城,巢湖成为与孙吴对抗的重要军事堡垒。同时,巢湖下游的濡须区域,成为孙吴沿江防线的重要据点之一,也是孙吴与曹魏长期争夺的热点地区。自建安十七年(212)孙权筑造濡须坞,至嘉平四年(252)东关之战,四十年间魏吴在巢湖区域发生大小数十次战斗。较大的战役如公元213年曹操亲征濡须坞、222年魏大司马曹仁率步兵数万攻濡须、228年魏攻东关和252年东关之战等。一时间,巢湖地区群雄争霸、烽火硝烟不断。
巢湖位于江淮交通要地,北有南、北淝水通合肥,达淮河,南有濡须水连接长江,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得以贯通,便利军队出入江淮。魏吴双方在江淮一带的战争问题,是汉末三国政治军事史研究的热点话题,有关巢湖—濡须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少历史地理著作中都有论述。
一、相关研究综述
著作方面,胡阿祥主编《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从战略地位、山川险要、军事重镇三个方面对苏、皖一带的军事地理进行分析,点出了江淮间存在合肥、寿春、盱眙等军事堡垒;陈金凤《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以斗争局势为主题,讲到吴魏江淮之争、南北朝淮河流域战争局势等问题;宋杰《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论文集,重点讨论了“合肥与曹魏的御吴战争”“孙吴的抗魏重镇濡须和东关”“孙吴武昌又称‘东关’考”“东晋南朝战争中的寿春” 等主题,对魏吴、南北朝对抗战争局势进行解读,指出巢湖区域及濡须东关地区为魏吴战争的重要枢纽,并对巢湖一带的具体战争进行了考证。
论文方面,史念海指出,守江之计,必得淮南以为战地,如曹魏控制江淮防止孙吴北上并伺机南下,孙吴争江淮以保守江东,其中巢湖一带便是孙吴与曹魏交锋争夺的“中间地带”;孙新文《三国时期吴魏濡须之战研究》,详细讲解了魏吴几次濡须之战的过程与结果,强调了濡须口的重要军事地位;崔兰海、周怀宇《曹魏政权在合肥的攻防战略》讨论了曹魏如何通过迁移合肥城址,应对沿巢湖北上的孙吴的威胁;金家年《濡须水流向的历史考察》讨论了濡须水的历史演变及流向问题;吴立、王心源等《巢湖流域新石器至汉代古聚落变更与环境变迁》则从考古成果出发,探究了文题所示问题。
又有从自然地理角度,研究巢湖沉积历史、流域演变以及区域地理景观的,如王传辉、郭振亚等《基于遥感的巢湖流域景观格局变化研究》利用遥感图像、沉积物孢粉分析,讨论了巢湖流域在地质历史当中的环境变化过程;高超、王心源《巢湖崩塌岸成因初步研究》通过分析沉积物分布状况、湖区土壤类型,分析了巢湖周边地质条件的变化以及古代巢湖湖岸崩塌问题。
由上所述可见,学者们对史料的挖掘解读已甚详细,研究多沿着传统军事史的路径,从魏吴战略决策、军事部署等方面展开,而相形之下,对巢湖区域历史自然地理的关注较少。战争是对抗双方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发生的冲突,而相关各方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对战争的过程与结果都会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如果说历史是一台大戏,那么每幕情景都有属于自己的、由时间与空间编织而成的独特舞台。换言之,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如何影响魏吴战争,仍然存在较大的探讨空间。
二、巢湖地理概况
巢湖位于今安徽省中部,流域北临江淮分水岭,西依大别山,东北接临滁河流域,东南连通长江,属于长江下游左岸水系,是我国现今第五大淡水湖,流域面积约14 203平方公里。湖泊状似“鸟巢”,东西两端向北翘起,中间向南凹曲,湖泊长度54.5公里,最宽处可达21.0公里,平均宽度为15.1公里。流域内地形总体向湖体倾斜,呈现出明显的阶梯状分布。根据地面高程可分为山地、丘陵、阶地、平原、湖盆五种。本文所指“巢湖区域”,包括巢湖湖体、上游数条入湖河流以及下游唯一的通江水道,还包含了湖区周边丘陵、平原等区域。
巢湖流域处于热带和暖温带过渡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年均温在15℃~16℃,流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 100毫米,降水呈现时空分布不均的特点,集中在流域西部,夏季常有暴雨出现,主导风向为东南风,冬季则为东北风。
巢湖从形成上来说属于断陷湖泊,根据变迁过程,可分为古巢湖时期和新巢湖时期,两阶段以全新世地壳抬升古巢湖面积缩小为分界。汉晋之际,中国整体气候较为干冷,长江水位下降,巢湖面积进一步缩小,进入现代发育时期。在湖体面积缩小的同时,巢湖周围还出现了大量的湖漫滩。流域内河流湖泊众多,水网密集,入湖水系包含了上游注入巢湖的数条河流,如杭埠河、丰乐河、派河、南淝河、店埠河、柘皋河、兆河、白石头山河等,多条水流汇入巢湖后,又经裕溪河、牛屯河等流入西河并注入长江。《水经注·卷二十九沔水》记载,长江东经濡须口、栅口连接巢湖,东流经乌上城北、南谯侨郡城南、绝塘、农山北与清溪水汇合,又从农山西南流注栅水。可见巢湖水系是一个开放的、与长江联通的天然水系。
史籍关于巢湖的记载自古有之。早在《尚书·仲虺之诰》中,便有“成汤放桀于南巢,惟有惭德”的记载,《春秋左传》中也多次提及“楚人围巢”。夏商到东周该区域被“巢国”统治。秦时巢湖区域设居巢、历阳、襄安等县,属九江郡,汉代属淮南国,王莽篡汉后改九江郡为延平郡。东汉撤销橐皋县,历阳县属扬州九江郡,居巢、舒县、临湖县、襄安县属庐江郡。三国时期,魏吴长期在巢湖地区交战,郡县置废频繁,魏吴皆置庐江郡,曹魏以六安县为郡治,东吴以皖县为郡治。
中国古代中原通江南有五条道路,分别为商山武关道、南襄隘道、“义阳三关”、江淮运河以及连接淮河中游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巢淝通道”。巢淝通道位于江淮丘陵中部,北部南、北淝水流量较小,且因季节性降水不均等因素水位变化大,但由于流经区域多属平原,尚可通航。南部裕溪河沟通长江,沿河多为平原,行军打仗可水陆并进,可以极快从西北进入江淮区域,故在南北政权对峙时期,沿巢湖濡须一线发生的战例数不胜数。
三、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对魏吴战争的影响:作战方式与作战时机
建安十七年起,魏吴双方在巢湖区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对抗活动,巢湖的自然地理地形、气候水文等状况对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战争策略的制定、战争过程的发展以及战争最后的结果。
(一)魏吴的作战方式
巢湖地区水网密集、湖面广阔,南北多丘陵,陆路交通不便。巢湖区域的地形特征决定了魏吴双方在该区域采用以水战为主的战争方式。
对于曹魏来说,巢湖流域是进攻孙吴的重要途径。宋杰在讨论孙吴江防部署时提到,若曹魏军队沿着陆路行军,需要用车载或者担负物资,且途经山地丘陵众多不易交通,极大地消耗了士兵体力且效率低下。若能控制巢湖及下游水道,利用水力、风力运输舟车粮草,便可事半功倍。
曹操明白水军对作战的重要性,因为就算陆运物资南下,没有水军力量,魏军对孙吴的沿江防御工事也是望尘莫及。自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便作轻舟治水军,此后四越巢湖进攻孙吴,皆是率领庞大船队南下。可以说,巢湖地区是曹魏进攻孙吴的重要路径。曹魏的基本经济区在中原冀、兖、司、豫四州,南攻孙吴便要考虑战略物资的南运,巢湖区域是长江下游水路的重要枢纽,即《孙子兵法》所说的“衢地”。
另一方面,巢湖流域下游水道是孙吴防卫曹魏的天然屏障。对不善水战的魏军来说,孙吴的水边坞堡近乎坚不可摧。建安十六年筑成的临江要塞濡须坞,即是拱卫建业的一个重要堡垒,建兴元年(252),孙吴又在濡须城以北东关地区筑东兴堤来防守曹魏。孙权对江淮地区的经营,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后,孙权命令周瑜在西线荆州地区,协同刘备进攻江陵,自己则在以扬州为中心的东线,沿着濡须水、施水、中渎水,通过巢湖流域水道,对曹魏合肥城发动进攻。第二阶段,建安十五年(210)周瑜病逝,孙权无力同时控制荆州与扬州,遂听取鲁肃的建议,将荆州借与刘备,自己将防线收缩到扬州,次年又将主力西迁建业,以迎击曹操在濡须流域的进攻。此后,孙吴主要是以从濡须水道通过巢湖攻打曹魏合肥城,以及在濡须口夹岸筑堤防守为主。第三阶段,黄龙元年(229)孙权自武昌还都建业,孙吴中军主力便转移至建业附近,而直到吴亡,曹魏、西晋的军队再未主动经过中渎水南下进攻,孙吴此阶段的经营转以进攻为主。
由于吴魏兵力差距,孙吴在该区域的作战大部分以防守为主,巢湖及濡须区域的自然水文条件也经常被运用到防守战略中。孙权黄龙二年筑东兴堤,建兴元年十月诸葛恪作东兴大堤。《三国志·诸葛恪传》中筑堤以“遏湖水”的记载,容易被误以为是筑堤防治巢湖洪涝灾害,其实该时期未见明确的巢湖洪涝的记载,因此孙吴专门修筑大型工程、治理巢湖洪涝的可能性很低。进而言之,孙权“筑东兴堤”、诸葛恪 “更作大堤”,很可能是一种利用巢湖水文地形,把修建陂塘的方法运用到防御作战中的案例。如宋杰即认为东兴堤的修筑是为了在濡须水和涂水航道的狭窄处截断水流,淹没沿岸陆路,从水、陆两面阻挡曹军深入。另一方面,濡须坞易守难攻,每年长江春潮时水位激增,水流湍急,成为防御魏军的一道天险,一旦气温升高水涨流急,对不谙水性的魏军来说非常不利。在水深的情况下,孙吴军队吃水较深的大船便可投入使用,硬件上更是超过魏军。因此魏军往往知难而退,孙吴便可以守代攻,以逸待劳。
(二)魏吴作战时机
巢湖区域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盛行风向随季节变化,全年降水差异明显。既然水战是魏吴双方重要的战争方式,那么巢湖河道的通航能力,自是影响双方作战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末三国时期,中国整体气候处于一种逐渐变冷的趋势,巢湖区域的气温也较汉初有明显的下降。黄初六年,《三国志》中有淮河结冰的记载,曹丕至广陵亲自检阅十余万士兵,由于冬季淮河突然冻结,不得不取消演练,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淮河结冰的记录。巢湖位于淮河以南,气温自然相对温暖,即便是在较今更为寒冷的魏晋时期,也未见巢湖冬日冰封的记录。也就是说,冬季的巢湖及下游河道依然具有通航能力,而且冬季气候干冷,水位较低,水流也较为平缓,通行比较安全,这样,冬末春初就往往是曹魏进攻孙吴的良好时机。如建安二十二年二月(西历3月末到4月),曹操进军屯江西郝溪,将在濡须口筑城拒守的孙权逼走;然而等到三月,曹操还是“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何以如此呢?应该就是季节变化导致水情变化的缘故。
在季春以至夏季,江淮之间来水既多,降雨也逐渐频繁集中,于是经常出现河湖水位暴涨、水流湍急的状况。如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攻吴濡须的战争中,两军对垒相拒月余后,孙权即在战事上开始取得一些胜利,所谓“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战局遂有扭转之势。曹操坚守不出,孙权便主动挑衅乃至挑战,并威胁曹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此处“春水”便是指长江春潮。三四月份,气温回升,长江流域的降雪开始消融,冰雪融水通过支流汇入长江;等到四至六月份,长江水位上涨,江水倒灌巢湖,巢湖及其区域内河流水位上升,河水流势凶猛,而这对于魏军来说,不仅增大了作战难度,物资补给也有中断的可能,所以孙权以此威胁曹操退兵,曹操也果然退兵了。
曹魏利用冬季较为良好的水运条件进攻孙吴,但随着气温回升春日水涨,却又往往无法持久作战,这就是地理条件施加在战争上的影响,类似的事例颇多。如黄武二年三月,曹仁遣将军常雕等领五千兵,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与吴军作战,紧接着,“是月,魏军皆退”,可见若双方久持不下,补给困难,曹魏方面便会逐渐失去优势,又受到水涨流急对作战的威胁,只好暂且退兵。至于孙吴一方,则抓住曹魏此时不便久战的机会,常筑堡垒坚守不出,以此化解危机。
影响魏吴双方作战的另一自然地理因素,是巢湖的大风。俗语有“巢湖吹八面风”的说法,这描述的便是巢湖区域的风向多变,小气候特征明显,难以预测。同时,受到季风气候的影响,整体上巢湖2月至3月吹东风,4月至7月盛行东南风,8月至10月盛行东北风,11月至次年1月为西北风,其中东南风与西北风风速较大,对于魏吴双方的军队都有很大的威胁。如史书中有大风致兵船倾覆的记录。吴将董袭率领的五楼船在濡须口遭遇强风,“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从而导致作战失败、董袭死难的结局。又吴将徐盛领兵时也曾遭遇强风,“时乘蒙冲,遇迅风,船落敌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兵,上突斫敌,敌披退走,有所伤杀,风止便还”,受到孙权的赞扬。由此可见,巢湖大风对魏吴双方作战都十分不利,而哪方能更好地适应巢湖的气候,就更能在战斗中取得优势。
四、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对魏吴战争的影响:曹魏屯田选址与军事重镇迁移
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对魏吴战争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具体的作战方式、作战时机两方面,也表现在牵涉更加广泛的曹魏屯田选址、军事重镇迁移两方面。
(一)曹魏屯田选址
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屯田居巢,并留派夏侯惇、张辽等人率兵屯田,在选择屯田位置时,出于攻守孙吴的战略考虑,选择了靠近通江水道的巢湖东岸,而未选择汉代开发较多、聚落更为密集的巢湖西岸。靠近巢湖唯一的通江水道,巢湖的东南岸与东北岸似乎都能成为曹魏攻打孙吴的战略物资补给据点,曹操选择东北岸而非东南岸屯田,主要原因在于巢湖的气候、地形、地质三个方面。
首先是巢湖大风问题。巢湖流域受到季风气候影响,4月至7月及11月至次年1月盛行的东南风、西北风风力强劲,东南岸受到大风影响较大,屯田选址在东北岸则能有效避开风口,农业及军事活动受湖风影响较小。
其次,曹魏屯田选址受到了巢湖湖岸崩塌的影响。巢湖区域降雨分布不均,湖水丰枯水期水位变化大,湖岸受到含水量高低变化影响,部分湖岸经常发生风化与崩塌。巢湖湖岸不同区域的崩塌程度,与巢湖湖岸地质条件有关,巢湖流域的主要轮廓在中生代燕山运动和新生代喜马拉雅运动时期已经奠定,流域内可分为北部剥蚀丘陵区、东部构造剥蚀低山区以及西部剥蚀壑丘区。经地质勘测,巢湖湖岸按组成岩性质可分为基岩石质湖岸、砂土质湖岸与黏土质湖岸,其中湖岸崩塌多发生在二级剥蚀阶地的黏土质湖岸类型中。
根据王心源等人对现代巢湖湖岸的地质勘探研究,发现巢湖严重崩塌湖岸主要分布在以黏土质为主的巢湖南岸的齐头咀、夏塘咀及罗大郢至陈家户的巢湖西北岸,次严重崩塌湖岸主要分布在李家洼到大魏家巢湖东南岸。而在以砂岩为主的巢湖东北岸龟山、大院子至李家洼、孙家凤至中庙一带,崩塌较为轻微。根据古今巢湖范围,可推断靠近今巢湖东北龟山的古“居巢”地区,很大可能属于砂岩基底,崩塌较为轻微。而巢湖东南岸砂质湖岸分布广,更容易发生崩塌。再者强劲的东南风、西北风掀起的拍岸浪,对西北和东南两侧湖岸不断冲刷和淘蚀,加大了对湖岸的侵蚀,导致这两侧湖岸较其他方位更容易发生崩塌,对曹魏的屯田非常不利。
第三,巢湖东北岸较东南岸地形更为平坦。巢湖东南岸有银屏山、蜈蚣岭等广阔的低山丘陵区域,大部分海拔在200米至400米之间,少有平坦的土地。东北岸凤凰山以东、汤山以南有一片较为广阔的平坦土地,适合曹魏军队进行农业生产和军事活动。
曹魏屯田选址居巢,还有着土壤因素的影响。历史上巢湖虽然易涝,但在东汉三国时期却较少发生洪涝灾害。同时,历史时期洪水留下了大量富有营养的淤泥沉积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此时屯田巢湖岸边能够利用较为肥沃的巢湖漫滩进行耕种,而无需过多考虑洪水的影响。
然而曹魏的居巢屯田,既使此后居巢成为魏吴战争中曹魏的重要据点,其屯田策略也体现了古代农业生产经验的阶段性特征。在汉末三国时期,气候较为干冷,湖泊水位较低,巢湖地区的农业生产以利用肥沃平坦的湖漫滩进行耕种为主,而不是选择开垦高地来避免洪涝灾害。在现已被湖水淹没的肥西县牌坊郢遗址中,便出土了汉代水井,这侧面证明了当时湖泊水位较低,遗址距离湖泊远,居民需要打井取水。随着南北朝后期气温逐渐回升,公元五世纪开始,中国整体气候偏向温暖湿润,而包括巢湖流域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区域,洪涝灾害再次成为影响该区域农业生产的重要问题,利用湖漫滩肥沃土壤进行耕种的现象逐渐消失。
(二)军事重镇迁移——以合肥城为例
巢湖区域复杂稠密的水网,对于争战的魏吴双方来说,既带来了敌方的威胁,又提供了进攻的便捷道路,孙吴水军便曾多次从濡须通过运河进入巢湖区域,对临近巢湖岸边的曹魏合肥旧城进行军事袭击。至于魏晋时期新旧合肥城的来回迁移,则与巢湖的水运条件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合肥”一词首见于《史记·货殖列传》:“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由于靠近南楚中心城镇寿春,又临近巢湖与淝水,合肥成了皮革、鲍鱼、贵重木材等物品的交易市场,繁荣的贸易也带动了合肥城经济的发展。秦末汉初,“合肥”便是作为一座“输会”,凭借其优越的交通环境,同大都市寿春共同发展起来。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为了抵御孙吴,在江淮一线占据有利的战略位置,建安五年,曹操任命刘馥为扬州刺史,命其修筑合肥城,这就是著名的曹魏合肥旧城。《三国志·刘馥传》载:“馥暨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雷)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灌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这段记载显示:刘馥修筑合肥城,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诸如兴修水利、募民屯田、安抚百姓,甚至创办学校来推行教化,又建设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拨兵屯守。可见曹魏是将合肥城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要地进行建设的,合肥城也由此成为屹立于巢湖之滨的军事堡垒。
合肥城由于处于南北交通要道,曹魏时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开始逐渐突出,如自曹魏开始,即频繁见于史料记载。论其形势,清初顾祖禹有言:庐州“府为淮右襟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宋杰《合肥的战略地位与曹魏的御吴战争》则对208年至278年间有关合肥城的战役进行了统计,包含主动出击但未发生交战的军事行动,孙吴军队对曹魏发动过34次作战,其中合肥—寿春方向便占了12次,占总数的35%。
然而问题在于,上述的合肥城虽靠近巢湖,水运便利,但也极易被吴军上岸包围,如《三国志·刘馥传》记载:“孙权率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以破走。”这样的合肥城虽建造坚固,防备充足,可以抵挡吴军百余日而不被攻克,但其临近巢湖的位置,仍然带有隐患,如青龙元年(233)魏将满宠即上疏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贼大辈,然后围乃得解。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所谓“南临江湖”,应指南部靠近巢湖。
合肥旧城既然如此,于是有了合肥新城的建造。合肥新城的建造,首先应从满宠与蒋济的辩论谈起。在这次辩论中,征东将军满宠依据上引理由,认为“宜移城内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即西迁三十里立城,以据奇险为守;护军将军蒋济则认为迁城属于示弱,应以淮北为守。满宠则再次上表,言以诱贼远水之计谋:“今贼未至而移城却内,此所谓形而诱之也。引贼远水,择利而动,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矣”,终被魏明帝曹叡采纳。
事实证明,满宠移建合肥新城的建议乃至计策是成功的,迁城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如《三国志·满宠传》记录了合肥迁城后发生的两场魏吴战争:先是青龙元年,“权自出,欲围新城,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宠谓诸将曰:‘权得吾移城,必于其众中有自大之言,今大举来欲要一切之功,虽不敢至,必当上岸耀兵以示有余。’乃潜遣步骑六千,伏肥城隐处以待之。权果上岸耀兵,宠伏军卒起击之,斩首数百,或有赴水死者”。又青龙二年,孙“权自将号十万,至合肥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孙泰。贼于是引退”。据此可知,迁移后的合肥新城远离巢湖岸边,孙权欲攻打新城,无法再次据水为势,只得上岸跋涉进攻合肥新城,结果或遭遇埋伏,或下风被烧,损失惨重。
近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合肥三国新城进行了勘探考察,合肥三国新城遗址被发现于今合肥市西北郊15公里的庐阳区三十岗乡陈龙行政村陈大郢自然村,其地南临淝水故道,西据鸡鸣山约2公里,北部是连绵起伏的岗地,新城遗址则坐落于岗地顶部。而对照嘉庆《合肥县志》对曹魏合肥新城遗址位置的记载,“在今鸡鸣山北,有故址,围三里,共一八墩,在城西北”,可知嘉庆《合肥县志》对曹魏合肥新城位置的记载有误,北应为东之误。又司马氏的晋朝代魏初期,合肥新城还一度被使用,及至西晋平吴之后,来自巢湖方面的威胁不复存在,合肥新城远离巢湖的特点,便由易于防守变成了交通不便,于是逐渐被废弃了,西晋重新使用了刘馥建造的合肥旧城。
据上所述,魏晋时期合肥城址的两次变迁,主要便是由于受到巢湖地理条件的影响。优越的航运条件,给合肥城带来了物资运输的便利,但也带来了敌人的威胁,而曹魏迁移城址,则是在特定时局下积极适应地理环境、转守为攻的成功案例。
五、结语
若谓历史是台戏剧,那么巢湖区域便是魏吴战争演绎的绝佳舞台。汉末三国乱世,战火连绵,或许围绕巢湖的诸多战例,只是其时战争大戏的几幕场景,但其复杂情形、精彩程度,仍令人击节赞叹,也向后世的读史者鲜活展现了何为用兵的天时地利。
说起用兵的天时地利,前此胡阿祥在《中国大智慧》之“军事智慧”中,专门有一讲“借力打力:水火无情却给力”,其中讨论到赤壁之战的一个关键细节,即老谋深算的曹操怎么会遭遇到孙权的火攻。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赤壁一带在冬天里偶会出现气温升高的日子,继而会刮起临时性的东南风,这种短暂的地形风,或一两天,或数小时,既极难被人把握,也很少受到外人关注,所以即便是军事天才曹操,也不明此中奥妙。然而,作为孙吴水军中最熟悉长江尤其是赤壁一带小气候的老将军黄盖,却知道这是稍纵即逝的黄金战机,周瑜对此应该也是心知肚明,于是两人合作导演了这场精彩绝伦、传诵千古的“火烧赤壁”。看来,真如兵圣孙武所说的:“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懂得天时、地利的运用,对于取得战争的胜利,往往起着重要作用。
换言之,理解赤壁之战,风是关键的因素之一;同样的道理,理解魏吴双方在巢湖地区的作战方式、作战时机、曹魏屯田选址、曹魏军事重镇迁移等方面,全面把握巢湖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前提或基础所在。进而言之,本文虽然仅仅讨论了汉末三国时期巢湖区域的战争案例,但也绝非以偏概全之论,因为巢湖区域在其后千余年的南北对峙战争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诚所谓争夺天下之兵家必争之地。
注释:
①《三国志》卷二《魏书二·文帝纪》记载,黄初六年(225),“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
②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对应公历一月末至二月,由于该年存在闰一月的情况,该年二月应对应公历三月末到四月。
③《三国志》卷9《魏书九·夏侯惇传》载,“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三国志》卷17《魏书十七·张辽传》载,“太祖复征孙权,到合肥,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乃增辽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④吴立《巢湖流域新石器至汉代古聚落变更与环境变迁》根据考古材料统计汉代遗址分布区域发现,到汉代,原本分布于巢湖东北岸柘皋河流域的14处文明聚落全部消失,而在南淝河中上游地区遗址增长20多处,可以大概推测汉代巢湖流域开发程度较高区域为巢湖西岸,东岸开发较为落后。我们可以初步排除曹操选择居巢,是出于居巢地区经济、农业较为发达的原因,应是主要出于军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