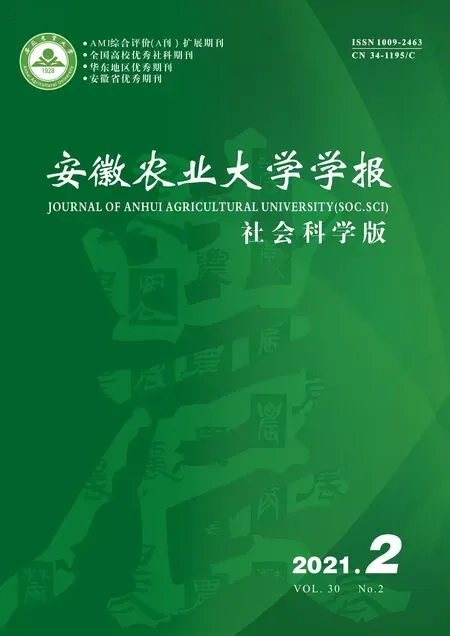“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
江守义,支瑞瑞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文艺大众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潮流,从晚清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新小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平民文学”“民众文学”,再到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学创作的大众化趋向不断增强,文艺不属于少数人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文艺界开始了对“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探讨,20世纪30年代“左联”有组织的讨论将“文艺大众化”推向高潮。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的发展来说,“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可以说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左联”的“文艺大众化”探索,既体现在实践活动中,也体现在具体的理论建设中。经过三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左联”的探索在左翼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一
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就已经开始。1928年2月,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提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这里的“大众”已经和左联“文艺大众化”的“大众”内涵相去不远。1928年,郁达夫创办《大众文艺》,其“大众”的内涵来源于日本,缺少革命文学的阶级要素,因此受到了许多作家的围攻,引发了人们对于“大众”内涵的探讨,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大众化”的发展。1929年3月,林伯修在《1929年急待解决的几个关于文艺的问题》中正式提出“普罗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他意识到“文艺大众化”不能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还要落实到实践中。同一时期,干釜在《关于普罗文学之形式的话》中涉及到大众化的形式,指出“普罗文学底形式,第一需要大众化。听闻大众化,有二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需要‘深入大众’,一方面是使‘大众理解’。”就林伯修、干釜二人的观点看,他们实际上为此后“左联”的相关讨论提供了基本方向。
“左联”期间,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30年的局部讨论、1931年末到1932年的组织性讨论、1934年的回应性讨论。
第一阶段的讨论主要是《大众文艺》组织的讨论。“左联”1930年3月成立之初,并未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左联”的成立宣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和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都未提及“文艺大众化”。“左联”成立时虽然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但这个研究会一开始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并没有实际贡献。“左联”成立后很快在4月29日和5月29日召开了两次全体大会,在这两次会中都没有提到“文艺大众化”问题,并且“各研究会,在这一月中,也只有‘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举行过一次讨论会”,说明“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根本没有开展工作。但3月份之前,在左翼内部,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却如火如荼。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后,于1930年组织了两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第一次时间不详,但肯定在“左联”成立之前,因为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上刊发了《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的现场记录,同期还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标题下,刊发了冯乃超、陶晶孙、郑伯奇、沈端先、鲁迅、郭沫若、王独清的文章,冯乃超、陶晶孙、郑伯奇、沈端先也是座谈会的参加者。第二次在3月29日,《大众文艺》第2卷第4期上刊发了《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的现场记录,其中心议题是少儿读物的大众化问题。第二次座谈会虽然在“左联”成立之后,但和第一次座谈会是连续的,与“左联”领导层并无直接关系,只不过3月2日“左联”成立后,《大众文艺》也成为“左联”刊物,这次座谈会通常被归入“左联”的名义下。
或许是受《大众文艺》讨论的影响,1930年5月,“左联”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开始明确地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议题之一,当然,这里的“文艺大众化”更多的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大众化”的相关内容,相关讨论也只能是局部讨论。此后,这种局部讨论慢慢向全局性的组织性讨论转变。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上发表了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已经击破资产阶级文学影响争取领导权的阶段转入积极的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组织活动的时期”,“左联”已成为“领导文学斗争的广大群众的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者。决议“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认为通信员运动、平民夜校、工厂小报、壁报这些形式都有利于使文学“从少数特权者手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大众的所有”。决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艺大众化”的口号,但不仅在理论上带有“文艺大众化”的色彩,在实践上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大众化”形式。这意味着“左联”领导层从总体上开始重视“文艺大众化”工作,此后,“左联”所发布的一些决策中出现了“文艺大众化”的相关内容。1930年10月25日《左联秘书处通告》(发表在1931年10月23日的《文学导报》第6期、第7期合刊上)第二条就明确提出:“‘大众文艺’及‘文艺大众化’问题为联盟目前十分注意的工作。”《通告》要求:对大众化的问题,“务必提出书面的意见,论文式、通讯式、杂感式,均无不可。此项意见,除交大众文学委员会参考外,亦将择要在本联盟机关报上刊布”(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大众文学委员会”,它应该是“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改组后的名称)。这些都为第二阶段的全局性讨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的讨论是“左联”领导层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1930年11月,“左联”在第二次国际革命作家代表会议上被纳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国际联盟的“中国支部”。此次会议上,国际联盟确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目标和任务,要求“左联”积极扩大无产阶级文学在工人、农民中间的影响,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深入到工农大众之中。在国际联盟会议精神的指引下,1931年11月“左联”通过了著名的“十一月决议”,开启了“左联”对“文艺大众化”自觉的组织性讨论,“文艺大众化”也成为“左联”1932年的一个工作重心。在瞿秋白主持“左联”工作后,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明确将“文学大众化”作为当前“第一个重大的问题”;1932年3月9日,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将“文艺大众化”看作是“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同日通过的《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要求“左联”的每个小组“从各方面去进行革命大众文艺的运动”,并在秘书处下设立“大众文艺委员会”;为促进“文艺大众化”,“文总” (左翼文化总同盟)、“社联”(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还联合创办了一个工农大众的小周刊《白话报》。除了在这些组织层面对“文艺大众化”的重视外,瞿秋白、洛扬(冯雪峰)、何大白(郑伯奇)、寒生(阳翰笙)、起应(周扬)、止敬(茅盾)、鲁迅、方光焘、田汉等人还发表了各自对“文艺大众化”的见解,瞿秋白(宋阳)和茅盾(止敬)还就相关问题进行商榷。《文学》《文学月报》《北斗》等期刊都加入到“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之中,尤其是《北斗》第2卷第3期、第4期合刊还刊发了“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发表了陈望道、魏金枝、陶晶孙、郑振铎等11人的文章。
第三阶段的讨论集中在1934年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的讨论上。这一讨论源于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遵守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在此背景下,汪懋祖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批判“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主张尊孔读经和复兴文言,反对白话文。汪懋祖的极端观点和国民政府并不一致,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张尊孔,但反对读经和文言教育。这样,在文化复古潮流中文言和白话之争又被重新提起。当这种争论传到上海,陈望道等人决定对“文言复兴”进行讨伐,但这种讨伐不是重复“五四”时期的文言和白话之争。作为策略,陈望道提出通过反对白话文来保护白话文:“要保白话文,如果从正面来保是保不住的,必须也来反对白话文,就是嫌白话文还不够白。他们从右的方面反。我们从左的方面反,这是一种策略。只有我们也去攻击白话文,这样他们自己就会来保白话文了。”1934年6月16日,陈望道等人以《乒乓世界》副刊《连环画周刊》征稿为名,在“一品香”茶馆聚会,乐嗣炳、夏丏尊、傅东华、曹聚仁、黎烈文等12人与会,会上提出“大众语运动”,进而引起理论界关于“大众语”和“大众文学”的讨论。由于这一阶段的讨论从反拨文言复古开始,它不是“左联”领导层的组织行为,主要是一种对复古思潮的回应性讨论。同时,这一阶段的讨论不局限在“左联”内部,也有不少非“左联”人士参与,即使是参与讨论的“左联”成员,也是以个人名义参与,换言之,这是一次知识界的公共空间内的自由讨论。由于参与讨论的人员中不少是“左联”成员,这次自由讨论也被认为是“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第三阶段的讨论。讨论的阵地不限于“左联”期刊,在“一品香”聚会时或许由于黎烈文(时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在场,与会者决定将《申报·自由谈》作为讨论阵地,此后,《中华日报·动向》《社会月报》《太白》《申报·电影专刊》和一些左联刊物(《春光》《文学季刊》《新生》《新语林》《文学》《文艺月报》等)也成为讨论阵地。8月,《文学》第3卷第2期和《社会月报》都刊出了《大众语问题特辑》,大众语问题一时成为讨论热点。
“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讨论之后,“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热度逐渐冷却。期刊杂志上很少再看到有关“文艺大众化”的文章,“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基本让位于“两个口号”之争。
二
由于“左联”的党派性质和革命性质,“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探讨,也是一种工作中的实践。从实践层面看,“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讲究策略,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二是通过多种途径,将文艺真正“大众化”。
就第一个方面看,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左联”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左联”期间继续这种讨论,就需要和“左联”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其活动要统一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党的革命事业不能只停留在口头的讨论上,实践更重要。作为一般知识分子,只要对“文艺大众化”进行理论探索,而作为革命工作者,则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左联”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将“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成一种运动。具体途径如下:
其一,翻译国外的相关理论,让“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有坚实的理论支撑。“左联”作家翻译了不少国外文献,其中一些与“文艺大众化”有关。这与“左联”的政策引导分不开。“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总纲领”,“理论纲领”要求“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行动总纲领”将“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作为“左联”的工作方针。“左联”下属的国际文化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也为国外理论的引入提供了渠道。据《论“左联”期刊的翻译作品》一文统计,“在‘左联’期刊发表的2 951篇署名文章中,有564篇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翻译作品数约占作品总数的20%,也就是说,在“左联”期刊上发表的每五篇文章中,就有一篇是翻译作品”,而“在‘左联’期刊登载的翻译作品中,理论作品的翻译有275篇,约占翻译作品总数的48.8%,文学作品约占51.2%,二者可谓是旗鼓相当”。《大众文艺》《北斗》《春光》《文学季刊》《文艺月报》《拓荒者》等期刊都翻译了相关的理论文章,尤其是列宁文艺思想的翻译和介绍(成文英以《论新兴文学》为题,翻译了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发表于1930年2月《拓荒者》第1卷第2期;同期还刊登了沈端先翻译的列裘耐夫的《伊里几的艺术观》),为文艺大众化讨论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引。周扬后来在纪念“左联”5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继承和发扬左翼文化运动的革命传统》中总结了这一点:“‘左联’根据列宁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文艺应当属于人民的观点,提出了‘文艺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口号,发出了全体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众当中去’的号召”。
其二,以刊物为阵地,发表论文和作品。“左联”的主要活动在上海,由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当时国民党对于文化的围剿,“左联”创办的期刊动辄被停刊,但是“左联” 不断创办新期刊,或者将一些期刊改头换面。期刊是“左联”的主要阵地。“左联”成员不仅利用“左联”自己创办的刊物表达观点,也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左联”对于“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主要也是通过期刊来完成的。据不完全统计,“左联”出版的期刊有46种,其中很多期刊都曾经发表过“文艺大众化”相关论文。比如《大众文艺》作为“文艺大众化”第一次讨论的阵地,1930年组织过两次大型的座谈会,举办过两次“我希望于大众文艺的”笔谈,征集了众多作家对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意见。除《大众文艺》外,很多杂志也为“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提供了平台,如《拓荒者》上刊登了阿英的《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化》、阳翰笙的《普罗大众化的问题》,《北斗》上刊登了郑伯奇的《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阳翰笙的《文学大众化与大众文艺》,《文学》上刊登了瞿秋白的《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冯雪峰的《论文学的大众化》,等等。第三次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涉及的期刊更多,《时代公论》《申报·自由谈》《申报·教育消息》《申报·读书问答》《中华日报·动向》《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大晚报·火炬》《社会月报》《文学》《新语林》《新生周刊》《独立评论》《新中华杂志》等都发表过相关文章。通过期刊上发表的众多文章,“左联”基本控制了舆论,让“文艺大众化”问题成为热点。“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除了发表理论文章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形成呼应。相对理论文章而言,“左联”期刊发表的文艺作品更多。以1932年6月出版的《文学月报》创刊号为例,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文章只有瞿秋白(宋阳)的《大众文艺的问题》,文艺作品则有蓬子(姚蓬子)的《诗四首》(分别是《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颂歌》《血唇》《决心》)、茅盾的小说《在火山上》(《子夜》第二节)、金丁的《孩子们》、冰莹的《抛弃》、蓬子的《雨后》、芦焚的《请愿外篇》、田汉的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巴金的散文《马赛的夜》等。
其三,成立研究会,组织论争。“左联”成立了众多研究会,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诗歌研究委员会、小说研究委员会、漫画研究会等,与“文艺大众化”直接相关的则有大众文艺研究会和工农兵文化委员会。在大众文艺研究会的组织下,“左联”有意识地开展了“文艺大众化”的第二次讨论,《北斗》第2卷第3期、第4期合刊还刊发了“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让“文学大众化”问题成为一个热点;《文学月报》创刊号、第1卷第2期、第3期连续3期刊发瞿秋白(宋阳)和茅盾(止敬)关于大众文艺的争论文章,也是《文学月报》有意为之。《文学月报》1932年6月创刊,正是“左联”号召走“文艺大众化”路线的时期,前两期的主编姚蓬子和第3期的主编周扬都是“左联”成员,周扬1933年还成为“左联”党团书记。第三次讨论虽然是回应性讨论,但有了第二次讨论的基础,第三次讨论中的“左联”成员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已有一些默契,尽管表面上不是“左联”的组织活动,但讨论中还是体现出较强的组织意识。
就第二个方面看,“文艺大众化”由观念变为一种运动后,就需要通过合适的形式,将这种运动落到实际工作中去。鉴于当时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和“左联”为革命服务的宗旨,“左联”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尝试将文艺真正“大众化”。
其一,鼓励知识分子到大众中去。30年代的中国,只有少数人识字,无论是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都不是真正的工农大众。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中提出,“大众文学应该是大众能享受的文学,同时大众也能创作的文学”,“大众文学的作家应该是由大众中间出身的,至少这是原则”。但根据当时的条件,这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他在下文中又给予了智识阶级出身的作家创作大众文学的机会,但同时要求他们走进大众的生活,向大众学习。1930年8月通过的“左联”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也号召“‘左联’全体联盟员到工厂到农村到战线到社会的地下层中去。”
知识分子到大众中去,主要是通过到工厂和农村体验生活以及实施教育工作等形式实现的。对大众文艺委员会来说,它主要的任务是将文艺大众化落实到位,如“创办通俗性刊物,创作民歌民谣,改编名著为通俗小说,建立工人夜校,组织工厂读报组、办墙报,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办蓝衣剧社等”。据吴奚如回忆,“文艺小组、夜校,是‘左联’大众化工作委员会活动的主要形式”。多种形式的深入群众,不是停留在规划设想中,而是落实到盟员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比如,“为了了解上海群众文艺活动情况,‘左联’曾派丁玲和何谷天(周文)去大世界游乐园进行调查研究”;为了培养工人通讯员,“‘左联’在杨树浦工人区办了一所弄堂小学,名‘涟文学校’,‘左联’诗人风斯(刘芳松)和作家艾芜都担任过这所学校的教员”。这些实践活动有利于“左联”成员进一步了解人民大众,贴近群众的生活,从而实现真正的“文艺大众化”;深入群众也有助于知识分子创造出更多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让大众满意的作品。
其二,鼓励大众进行创作。从苏联、日本等国引入的工农兵通信运动是这一政策的集中体现。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工作的决议》,提出“左联要‘向着群众’……尤其要加紧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工作,以及工农兵读书班、读报团、说书队的工作,加紧从这些工作中教育出工农作家及指导者”。“文艺大众化”是让文艺面向大众,面向大众的文艺也应该是大众创作的文艺。潘汉年在《大众文艺》的征稿中提出“尽量征求大众——被压迫的工农斗争生活的记录,不管通信、随笔、日记,并且一定要注意识字的工农的通信”。郑伯奇在《文学的大众化与大众文学》中则认为,“大众化的任务,是在工农中造出真正的普罗作家”“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工农作家简单地表现出自己的生活——斗争生活和日常生活”。丁玲在主编《北斗》时就特别注重发表工农作家的作品。“慧中(彭慧)的小说《米》、白韦的小说《夫妇》《墙头三部曲》和戴叔周的报告文学《前线通信》在《北斗》第2卷第3期、第4期合刊发表时,丁玲又在《编后》中加以‘特别推荐’,‘希望读者能加以注意’,因为这些作品的作者是‘拉石滚修筑马路的工人’‘从工厂走向军营的炮兵’,‘以及努力于工农化教育工作而生活在他们之中的慧中君’。”虽然“左联”利用各种形式鼓励大众创作,但这些工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收效并不大。
其三,借助左翼阵营内的各类联盟,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工作的重心,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左翼电影小组、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等组织,也用各自的方式来实现“文艺大众化”的目标。1932年3月15日《秘书处消息》就刊登了《和剧联及社联工作竞赛的合同》,“左联”和“社联”“剧联”就“文艺大众化”等相关问题签订了竞赛的合同。中国新闻研究会则思考了“舆论的权威如何在大众中建立”这一问题。1932年11月15日的《文学月报》发布了中国诗歌会成立的消息,刚成立的诗歌会同样关注到了“文艺大众化”这一问题,“他的目的是研究诗歌理论,制作诗歌作品,介绍和努力于诗歌的大众化”。由此可见,“文艺大众化”不是仅仅局限于“左联”内部的一个活动,“左联”还和左翼阵营中的其他组织合作,将“文艺大众化”落到实践之中。
具体而言,诗歌领域、戏剧领域、绘画领域、电影领域、文学领域、歌曲领域,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当时鲁迅、瞿秋白等都写了一些通俗歌谣。瞿秋白创作了《上海打仗景致》(无锡景致小调)、《英雄妙计献上海》等脍炙人口的说唱作品,鲁迅连续发表了《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通俗歌谣。以革命文学名著如《毁灭》《铁流》等改编成的通俗化的“大众本”在这一时期受到群众欢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群众戏剧运动如 “蓝衣剧团”就很活跃,他们演出的《工厂夜景》《活路》《S.O.S》等剧反映了工人生活中的困难和不幸,在当时广为流传。蒲风等发起中国诗歌会,提倡用俗语写民谣、小调、儿歌、弹词,杨骚的《乡曲》、蒲风的《六月流火》《钢铁的歌唱》《茫茫夜》、任钧的《战歌》、穆木天的《流亡者之歌》等,都贴近时代,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很受群众欢迎。“左联”在文学实践中积极响应“文艺大众化”,在创作的形式、方法、内容及题材上都体现了贴近群众、面向大众的特点,使大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这些作品。
三
“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最大的成就在其理论建树上。与三次讨论相对应,其理论建树主要表现在对文艺大众化的初步认识、对“大众化”文艺如何创作的探讨、对“大众语”的讨论。
首先,“左联”在对“文艺大众化”理论探索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文艺大众化”的初步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众化与政治的关系,二是大众化与艺术性的关系。就第一个方面看,“左联”达成了共识,即大众化以政治为先导。由于“左联”强烈的党派意识,它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自然而然从政治角度展开,文艺大众化不是单纯的文艺问题,它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将大众与无产阶级挂钩几乎是“左联”盟员的一致看法。在《大众文艺》召开的第一次文艺大众化座谈会上,参会者基本上认同蒋光慈的观点:“不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说他是无产大众,这问题就用不着说。”大众就是蒋光慈口中阶级倾向鲜明的无产大众。陶晶孙在《大众化文艺》中认为“大众乃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冯乃超的《大众化的问题》一文认为大众包括“从有意识的工人以至小市民”。陶晶孙是《大众文艺》的主编,冯乃超是“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他们的观点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左联”领导层的看法。大众既然是政治意识强烈的无产阶级大众,文艺大众化也只能以政治为先导,如陶晶孙所言:“文艺大众化的本意不是找寻大众的趣味为能事。还要把他们所受的压迫和榨取来探究。”“左联”探索“文艺大众化”符合左翼文化运动的本质要求,“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文学——就连一切艺术——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应该属于从事生产的大多数的民众”。如此,在阶级和政治的视野中来解读“文艺大众化”的意义也就顺理成章了。王独清在《要制作大众化的文艺》中认为,大众文艺的任务就是“结合新兴阶级的感情、意志、思想,更予以发扬光大,使得以加赠他本身实际斗争的力量。同时再推动一般能与新兴阶级联合的人类”。王独清的说法相对含蓄,没有把“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直接置于政治之下,但对阶级的关注最终还是无法远离政治。钱杏邨《大众文艺与文艺大众》则直接认为“文艺大众化”的探索是为政治服务的,“它的积极的任务是扩大新兴阶级的政治影响,完成新兴阶级的解放运动”。明言之,即“左联”进行“文艺大众化”探索,其意图是为了扩大左翼阵营的政治影响。
就第二个方面看,“左联”没有达成共识。大众化是否意味着失去艺术性,这个问题在“左联”内部,见仁见智,观点不一。郭沫若在《新兴大众的文艺的认识》中提出“无产阶级的通俗化”,认为“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不要丢开无产大众”。与郭沫若相反,鲁迅则反对为大众而妥协,在他看来,“文艺若设法俯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俗大众。迎合和媚俗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华汉在《普罗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中的见解则较为独特,艺术性对他来说是玄妙的、可变的,因此“只要在各阶级层中能够宣传和教化千百万勤劳大众的作品,那这种作品就是有色有香的艺术性十二分高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反之则不是”。这三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代表性,表现了“左联”初期“文艺大众化”探索的复杂性。
其次,“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不仅体现在对“大众化”与政治、“大众化”与艺术关系的理解上,还体现在对“大众化”文艺如何创作的探索上。在第二次讨论中,瞿秋白作为“左联”的领导者,他发表在《文学》第1卷第1期上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带有导向性意义。该文从“用什么话写”“写什么东西”“为着什么而写”“怎么样写”“要干些什么”五个方面对“文艺大众化”做了系统的阐述。对“大众化”而言,“用什么话写”是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瞿秋白主张“普罗大众文艺要用现代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听得懂的话来写,这是普罗大众文艺的一切根本问题”,就此论述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在论述的过程中瞿秋白彻底否定了五四运动的功绩,他认为“这‘五四’时的白话仍旧是士大夫的专制,和以前的文言一样”,“这种白话变成了新式文言”,字里行间都表达出了他对五四运动时期欧化白话的不满。这种态度在瞿秋白之后的文章中也有体现,他化名宋阳发表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认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旧小说式的白话,和‘五四’式的新文言比较起来,却有许多优点”,“新的文学革命不但要继续肃清文言的余孽,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瞿秋白这种否定“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态度得到冯雪峰、郑伯奇、周扬、张天翼、欧阳继修等人的支持。冯雪峰(洛扬)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认为:“现在的作品是过于投合智识份子读者的脾胃的,用语和文字组织是过于奇难晦涩,过于隔离群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的,作品的体裁也是如此。”阳翰笙(寒生)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指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革命也是失败了的,而由这一运动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欧化文艺,结果仍为少数的绅商和买办和欧化青年所独占所专有,广大的工农大众简直没有享受到半分儿实惠。”
茅盾应《文学月报》的要求发表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他对瞿秋白全盘否定“五四”时期白话文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认为欧化文艺还是存在受众的,对于接受过“五四”时期白话文教育的人来说,“五四”时期白话文比旧式文言白话更容易接受。沈起予也与瞿秋白持不同意见,他在《〈北斗〉杂志社文学大众化问题征文》中说:“不应当因此拒绝引用欧美和日本的特长的(为我们所无的)的文法和构造来丰富我们的‘国语’。我们应该随着大众化的水准之成长而将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复杂起来,将我们所表现的感情纤细深刻起来的。”瞿秋白和茅盾等人的观点各有其道理,茅盾后来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由于二人讨论的出发点不同,才走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李长夏在《文学月报》发表的《关于大众文艺问题》同时对瞿秋白和茅盾的观点给予辩证性的批评,算是为这个问题划上了句号。
“大众化”文艺的创作与其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有关。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论述“写什么东西”时,认为这是“作品的体裁问题”,“普罗大众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歌曲小调和对话剧等”。对旧形式的利用成为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的重要话题。洛扬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主张,“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即内容是革命的小调、唱本、连环图画、说书等等”,“为了引进大众到新的文艺生活,从旧的大众文艺形式中创造出新的大众文艺形式”。寒生在《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第一须运用大众所爱好的体裁的各种要素创造出新的形式来;第二我们须用新的内容去注入旧的形式或用新的描写方式逐渐去修改旧的形式;第三我们适合着大众的文化水平去创造出一些新的形式来。”
再次,是对“大众语”的讨论。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左联”发起的,而是由当时的“文言复兴”运动发起的,但其实和“左联”第二阶段瞿秋白等人对白话文的认识也有关系。瞿秋白和茅盾的争论显示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在20世纪30年代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欧化白话文较之文言文是一种进步;另一方面,欧化白话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又有脱节,甚至有点格格不入。瞿秋白甚至说:“‘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了胃口的鱼翅酒席,劳动民众是没有福气吃的。”正是由于“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尴尬处境,加上“文言复兴”的时代敏感性,“大众语”问题才得到热烈的讨论。“大众语”问题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大众语”的内涵、建设和文字拉丁化这两个方面。
“文艺大众化”对语言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在第一次论争中,鲁迅就意识到了语言对于“文艺大众化”的重要性,他指出:“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所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来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在第二次论争中,瞿秋白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中着重讨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文艺大众化”的作品“要用现在人的普通话来写。——有特别必要的时候,这要用到现在人的土话来写(方言文学)”。这已经和“大众语”的内涵相近了。在瞿秋白的影响下,阳翰笙、郑伯奇、冯雪峰等人也对“文艺大众化”的语言问题进行了思考。但“大众语”真正成为人民关注的重心,还是要到第三次讨论时期。
“大众语”在1934年6月18日《申报·自由谈》上由陈子展提出。他在《文言——白话——大众语》中认为,文言、白话的论战已经过去了,应该提倡大众语文学,并对大众语、大众语文学的内涵等方面做出规定。在他看来,“所谓大众语,包括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的语言文字”,“大众语文学,一方面要适合大众用的语言文字,一方面还得提高大众语的文化水准”。次日,陈望道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正式提出“大众语”口号,并对大众语的实践提出要求:“建设大众语文学,也须接近大众、向大众去学语言。”“左联”人士参与大众语讨论多是以个人名义,涉及的话题有大众语、大众语文学的定义和建设问题,以及方言、文言是否可以纳入大众语之中。任白戈在《“大众语”的建设问题》对大众语的定义同陈望道一致,他认为,“‘大众语’就是一种拿来传递大众的思想感情与情感而且很适宜于传达大众的思想与情感的语言。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使大众写得出,看得懂,读得出,听得懂的语言”。除了定义之外,任白戈还从“为什么要建设‘大众语’”“‘大众语’的建设是可能的吗?”“怎样建设‘大众语’”几个方面对“大众语”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他的“大众语”在反对文言文、“五四”时期白话的基础上要求切合大众的口味,“要单纯、明确、简短”。魏猛克的《普通话与“大众语”》质疑把土话加入大众语的合理性。王任叔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鼓励作家们到大众中间去,通过实践发展大众语,通过大众语文学教育大众反过来推动大众语发展。“大众语”讨论可谓众声喧哗,参与者不限于文学界,地点也不限于上海,观点纷呈。总体上看,“大众语”讨论促进了“左联”的“文艺大众化”探索。
“文字拉丁化”这个问题在“文艺大众化”中也是瞿秋白发起的,他在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罗马字和现代普通话,甚至在1932年完成了《新中国文字草案》一书的写作,瞿秋白的研究对第三次讨论中的“文字拉丁化”问题影响重大。在第三次讨论中,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张庚在1934 年 6 月 24 日在《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上发表《大众语的记录问题》,文中提出:方块字“实在记录不了大众语这丰富活跃的语言,否则必会把大众拖回僵尸的路上去”,“苏俄创行了一种中国话拉丁化,推行也很广,而且出版了很多书报,这我们可以拿来研究的”。7月 10 日,同为“左翼”阵营的叶籁士在《动向》上发表《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介绍了拉丁化新文字,在他看来“‘拉丁化’也许尚有许多小缺点,然而它既成为一种大众运动,一定能在实践中得到解决的。”鲁迅1934年8月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认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因此“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在《门外闲谈》中则主张:“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左联”对文字拉丁化很重视,1935年的《新文字月刊》和1936年的《中国语言》都是“左联”“文字拉丁化”的实践场地。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左联”所进行的“文艺大众化”探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说,“左联”在进行“文艺大众化”过程中一直强调深入群众,创作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探索还是远离大众的,“文艺大众化”活动所影响的范围也是十分有限的;“左联”内部对于“文艺大众化”的意见也难以统一;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容易走向极端。不过,“左联”的“文艺大众化”探索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它将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融为一体,上承“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下启 20世纪40 年代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在近现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理论得到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左联”对“大众化”的内涵、创作形式、语言等方面的探索对于此后的文艺理论建设、文学批评和文艺发展都产生了影响。“文艺属于大众”的观念也在“左联”探索“文艺大众化”的进程中深入人心,“左联”时期所建立的“大众化”观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左联”的部分探索在新中国成为现实。大众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普通话,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也从封建时期的王公贵族变成了普通大众。应该说,这些变化多少得益于“左联”对“文艺大众化”的探索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