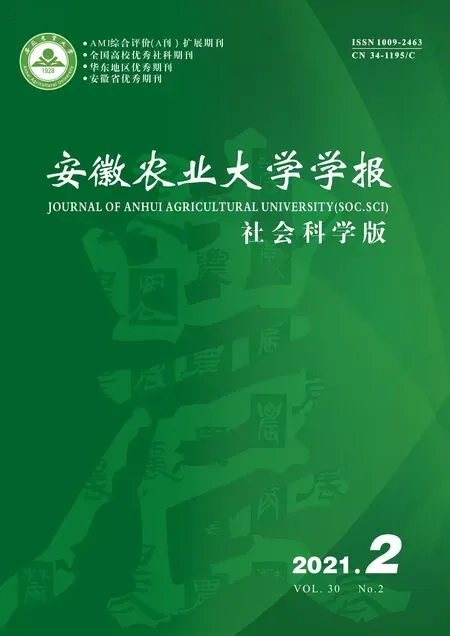逸人·逸笔·逸气*
——论倪瓒诗画创作风格的互通
戴欢欢,任声楠
(1.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子,无锡人。梁溪倪氏始祖为宋建炎二年(1128)扈从宋高宗南渡的倪师道,倪氏家庭历经数代经营,至元末为东南巨富。倪瓒幼年失怙,其兄长倪昭奎为道教名贤,对其思想影响较大。倪瓒自幼好学,家中筑有清閟阁,阁中藏有书画数千卷,可供其赏玩、勘定。倪瓒交游甚广,与文人、官员、乡绅、方外之士、书画名家皆有交往。倪瓒一生未仕,元末时家道中落,流寓他乡,晚景凄凉。倪瓒以画名世,工于书法,兼有诗名,可谓诗、书、画兼善。倪瓒在诗、画上均有自己的创作主张,其诗画作品皆有独特风格。《全元诗》收倪瓒诗歌1 151首,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艺术水平很高,为时人所推重。
一、身为逸人,隐迹山水
倪瓒家族富甲一方,“家雄于赀”,居所清閟阁藏书数千卷,且“古鼎法书,名琴奇画,陈列左右”。此阁是倪瓒精心营造的一片精神净土,倪瓒常常在此博览群书,增长学识。清閟阁周围“四时卉木,萦绕其外,高木修篁,蔚然生秀”,倪瓒时常与友人唱和其间,论诗作画。倪瓒一生淡泊名利,纵情山水,被后世称为“逸人”。明人顾起纶曰:“倪隐君元镇,高风洁行,为我明逸人之宗。”倪瓒交游甚广,“名傅硕师,方外大老,咸爱知重”。励志为学,但他的目的不是获得荣华富贵,而是期望能够留下美好的名声。正如其《述怀》诗所言:
嗟余幼失怙,教养自大兄。励志务为学,守义思居贞。闭户读书史,出门求友生。放笔作词赋,览时多论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富贵乌足道,所思垂令名。
他不求富贵、励志求学,发出“富贵真可羞,功名竟何物” (《次韵别郑明德》)的感慨。元至正(1341—1370)年初,倪瓒晚年时“忽散其赀给亲故”,抛却功名富贵,醉心于山水之间, “容名非所慕,登览竟忘归”(《赠沈文举》)。倪瓒虽然鄙弃世俗功名,但是他交往对象中不乏各级官员,如总管、县尹、府判、秘监、同知等。倪瓒并非出于对官场生活的厌恶,而是志不在此,正如其《答陈参军》诗所言:
世故纷纭自纠缠,南山修竹老风烟。陈公怀抱政如此,清影萧萧月满川。
倪瓒家境优渥,不曾遭遇过元廷压迫,所以他没有反抗元廷的行为。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倪瓒依然拥护元朝的统治,如其《上平章班师》:
金章紫绶出南荒,戎马旌旗拥道傍。奇计素闻陈曲逆,元勋今见郭汾阳。国风自古周南盛,天运由来汉道昌。妖贼已随征战尽,早归丹阙奉清光。
倪瓒称起义军是“妖贼”,称元朝出征的将军是“元勋”,由此可见他对元廷的态度。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倪瓒一方面对黎民百姓寄以深厚的同情,另一方面主张“仁让自家国,士民知孝忠”(《薛常州让田诗》),将国置于家之前,强调孝与忠。可见倪瓒在“自幼读书史”时所受到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倪瓒这一思想还在他的行为中有所表现,其《至正乙未素衣诗》云:“《素衣》,内自省也,督输官租,羁絷忧愤,思弃田庐,敛裳宵遁焉。”至正乙未(1355)年,此时已至元末,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使得农民苦不堪言,而倪瓒家中田产甚丰,荣华富贵建立在对农民的压榨上,他感到痛苦乃至忧愤。最终,他摆脱一切物质所累,乘夜逃离家庭。
散尽家财后,倪瓒纵游山水,隐迹江湖。此后他广交方外之士,这对其思想影响颇深。倪瓒受道教影响颇深,特别是道教的清净无为思想。其《玄文馆读书》一诗有引:“余友玄中真师在锡之东郭门立静舍,名玄文馆,幽洁敞朗,可以闲处。至顺壬申岁六月,余寓是兼旬,谢绝尘事,游心淡泊。”倪瓒来到其道教友人所立静舍寓居二十天,在这段时间里,倪瓒摆脱了尘世的烦扰,坚守清静,获得内心的淡然。他每天只是“潜心观道妙,讽咏古人书”,以至“怀澄神自适,意惬理无遗”,甚至希望能够“愿从逍遥游,何许昆仑墟”。清净无为是倪瓒的人生理想,其病中有《卧病》诗:
旱忧命觞斝,抱疾忽经旬。止酒却腥腐,端居谢喧尘。粗秽除内滞,清虚以怡神。江云载飞雨,飘飘洒衣巾。矫首咏玄虚,精思候仙真。道园游恬淡,心兵息狂狺。泠然风涛尽,鼓枻银河津。戒哉贪饕子,病原果何因。
倪瓒抱病多日,拒绝尘世纷扰,力图排除内心的烦恼,以求清净虚无,从而怡悦心神。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纷纷扰扰,倪瓒颇感乏累,他需要借助一种力量,使得自己放下尘世中的一切不顺意,寻求精神上的超脱。
除了受道教思想影响,倪瓒也会在佛教思想中寻求精神的解脱,获得六根清净。其在《至正十年十月廿三日余以事来荆溪重居寺主邀余寓其寺之东院凡四阅月待遇如一日余将归乃命大觉忏除垢业使悉清净乃为写寺南山画已因画说偈》一诗中写道:“根尘未净,自相翳晦。耳目所移,有若盲瞆。心想之微,蚁穴堤坏。辴然一笑,了此幻界。”倪瓒希冀在佛教圣地涤荡心灵,诗题中所提到的“除垢”,一是使得耳清目明,二是做到心无旁骛。倪瓒在现实生活中有很严重的洁癖,其居如有“俗客造庐,比去,必洗涤其处”。他所喜欢的地方必定也是干净整洁的。倪瓒的洁癖不仅仅表现在对环境要求上,同时也表现在其精神上。他要净化内心,摒除杂念,杜绝“心想之微”,在思想上实现虚空、宁静。在释、道两种思想的影响下,倪瓒散尽千金,远离世俗喧嚣,纵情山水之间。“厌闻尘世事,缅邈不相关”(《题渔樵友卷》),这是倪瓒与世俗生活的彻底决裂。从锦衣玉食到归隐山林,这并非是倪瓒对元末社会动乱的无奈,而是他顺从内心的自由选择。所以,时人周砥对其评价是:“我识云林子,亦是隐者流。一生傲岸轻王侯,视彼富贵如云浮。”
二、画为逸笔,简远空疏
倪瓒在《答张藻仲书》中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倪瓒作画不追求工拙与否,只用飘逸、简单的笔法随意勾勒。他说:“写竹切不可求精,精则便有工气。”“松最易工致,最难士气。必须率略而成,少分老嫩正反,虽极省笔,而天真自得,逸趣自多。”倪瓒写竹、松力求避免“工气”,通过“率略”“省笔”之法来实现其画作的士人神韵。这跟赵孟頫所提出的绘画作品需追求“神似”是一脉相承的,是元代画坛的一种总体倾向,也是文人画发展较为成熟的体现。倪瓒论画强调“率意为之”“草草而成”,认为这样才能“韵亦殊胜”。倪瓒目前所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如《古木幽篁图》《梧竹秀石图》等,尤其是写竹图,用笔比较简单、随意,不拘泥于笔画的工整,但是却体现出了一种幽远萧瑟的意境。倪瓒追求“逸趣”“不求形似”的主张一以贯之,与其诗论互通。正如倪瓒在《秋水轩诗序》中称赞陈惟允诗歌“如风行波生,涣然成文,蓬然起于太空,寂然而遂止,自成天籁之音,为可尚矣”。他又反对“祖述摹拟,无病呻吟”的诗句。倪瓒在绘画上提倡“不求形似”,其目的在于不作简单的刻画和描摩,而是将主观所感的物予以表现,以实现自己独特的风格。倪瓒作诗反对一味模拟,强调表现个性,尤其不能一直对前人的意境、意象等进行简单的加工和模仿,注重融入诗人个体的感受,写出符合时代特点、能体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作品。倪瓒存世的一千余首诗歌,不论是送别赠答之作,还是题画、咏怀之作,都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感受,因此不会给读者生硬以及矫揉造作的感觉,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更能打动人。
元代画坛一直有“师古”和“师心”之争,而到元末,“师心”之说尤为盛行。倪瓒是“师心”说的主张者,其《跋画竹》云:“以中每爱余画竹,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但不知以中视为何物耳?”倪瓒所画之竹,没法用似或不似、繁茂或稀疏、倾斜或笔直进行评价,他往往率性涂抹,甚至难以辨别为何物,但是依然受人喜爱,其中原因就是倪瓒笔下之竹,并不以形似为工,而是追求表达超脱世俗的逸气。倪瓒的《梧竹秀石图》,将梧与竹进行交织表现,梧叶用墨熏染,不甚细致,秀石亦难见其形貌之秀,但是颇得幽淡之趣,简中寓繁,梧、竹、石三者分布紧密,但丝毫没有拥挤、逼仄之感,各得生长姿态。
倪瓒画作的重要特色是具有简远空疏之美。其画作多取材于江南一带的风物,常作疏林坡岸、浅水遥岑景象。缓坡林间常有幽亭或茅屋,沿坡而下一般是一片水潭或者湖泊。倪瓒笔下的水,水域宽阔,大多水平如镜,体现出画家宽广的胸怀。沿坡而上一般是缓缓升高的山峦。倪瓒爱写远山,朦胧缥缈,起伏连绵直到天际。偶尔也写近山(如《水竹居图》),也不巍峨,缓起缓落。总体而言,倪瓒笔下的山水常有幽淡萧瑟的意境,具有简远空疏之美。如其画作《溪山图》,在图的上、左中、右下只绘了几株树木,颇显稀疏,图的中下方是水面和岸地,所占面积也甚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近一半画面的高山以及高山脚下平缓的岸地,这就凸显了高山的陡峭与巍峨。整个画面布局较为疏朗,没有拥挤的感觉,使用淡墨,显得意境幽远、疏淡。《图绘宝鉴》评其画:“画林木平远,竹石殊无市朝尘埃气。”倪瓒所画竹、木从来不喜茂盛,一幅画中竹木屈指可数,而且其竹石姿态各异,自然生长,没有丝毫人工痕迹,这正是其人生态度的反映,即希望远离世俗社会,追求闲适不受拘束的生活。因此,他的绘画虽然不以工整细密见长,仔细欣赏,能看出其画中所蕴含的深意。倪瓒不喜尘世的纷纷扰扰,喜爱山水之间的简淡闲远,如《松林亭子图》,亭在长松下,在岸边,远处有层层叠叠的山峦;亭子背后有几株长松可倚,面前是宽广的水面,远处有山可欣赏;亭子前后的物体同时也起到了阻隔尘世的作用,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世外桃源,没有战争,没有苦难,更没有喧闹,给欣赏者带来悠闲、自然的审美体验。
倪瓒画作的“空”是一种艺术留白。留白有助于画面的和谐,使构图简而不陋,比浓墨重彩地渲染更有诗意,避免画面太满给人带来压抑之感。留白可让观者充分发挥想象,可以更好地实现画家与观者的交流。善于留白的画作,展现在观者眼前时,就不单是画家一人的作品了,观者不仅可以根据画中的山水、屋舍、林木等景物及其布局去揣测画家的心境,而且可以借助留白在心中对绘画进行再次加工。这种加工因人而异,留白的艺术价值正在于此。倪瓒是处理留白的大师,其画作常有一半以上都是空白,画面布局主要有两种:第一,近景有竹、荆等植物,是画作主体,写远山往往寥寥数笔,中间是一大片的水域,两处景物上下相对,如《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古树茅亭图》《安处斋图》等皆是此类作品,这种布局方式是倪瓒山水画的主流。第二,写植物的近景偏居画面一隅,在图的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与远山隔水遥对,两种景物左右居之。如《小山疏林图》《疏林图》《平林远岫图》等。无论是哪种布局方式,倪瓒的留白总能起到“此处无物胜有物”的艺术效果,如其《紫芝山房图》,此画分近、中、远三景,近处林木挺拔、幽竹纤劲、怪石高大、茅亭悬于江边,远处山丘绵延,倒映在湖水中,中间的一大片空白就是湖水,水平如镜,不泛涟漪。用干笔淡墨、点染皴擦,湖光山色,空灵澄净。此画幅上还有优美的楷书写下的一首五律自题:“山房临碧海,碧海紫芝荣。云上飞凫鸟,月中闻风篁。术烟生石灶,竹雪洒前楹。谁见陈高士,熙夷善养生。八月廿日为叔平画紫芝山房图,并赋五言。瓒。”很好地将诗、书、画三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起。诗歌前三联描写眼前之景,尾联“谁见陈高士,熙夷善养生”则为联想的情景。
倪瓒之画,不求形似,以逸笔写眼前之景,不为景物的形态所羁绊,重在写胸中“逸气”,在画作中表达自己超脱世俗的意趣。他常以简单的笔墨勾勒图景,留下大量空白,给观众以想象的空间,形成简远空疏的画风。
三、诗有逸气,冲淡萧散
倪瓒指出:“诗必有谓,而不徒作吟咏,得乎性情之正,斯为善矣。”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徒作吟咏之态,而要发乎性情,“然忌矜持不勉而自中,不为沿袭剽盗之言,尤恶夫辞艰深而意浅近也”,不喜欢那些拘泥于表达、抄袭前人之言、辞艰语深而没有内涵的诗作。与其画“不求形似”相一致的是其诗歌的“不事雕琢”,他十分推崇“遇事而兴感,因诗以纪事”之类的诗作,因为这类诗“不为缛丽之语,不费镂刻之工,词若浅易而寄兴深远,虽志浮识浅之士,读之莫不有恻怛羞恶是非之心,仁义油然而作也”。在诗歌语言上不过分雕琢,不费力于对语言的精雕细琢,虽词语浅近但寄兴深远,这样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倪瓒的诗论观点是其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如其《十二月十七日过与之洛涧山居留宿忽大雪作及明起视户外岩岫如玉琢削竹树压倒径无行迹飘瞥竟日至暮未已雪深尺余因赋诗留别》:
世途萦荏苒,岁晏不知归。密雪竹林夜,挑灯共掩扉。萧条尘虑净,讽咏玄言微。遇此岩中赏,心事怅多违。
宴席已近尾声,诗人仍然不想归去,大雪悄悄降落,夜晚如此静谧,引得诗人思绪良多,往事幕幕闪现眼前,内心不免惆怅。诗句虽浅显易懂,但语言的自然简洁使得诗人情感的表达更加真挚,似缓缓流水激起心头的涟漪。诗中简短的语言是诗人情绪渲染与表达的需要,没有丝毫的生硬。倪瓒作为画家兼诗人,他的内心世界是极为敏感细腻的,外界细小的事物也能引起他的关注,并在其内心里掀起一片波澜。因此,他的诗歌是其抒发内心情绪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倪瓒之诗不论记事之作,还是写景之篇,都蕴含了深厚的真情实感,如《偶成》:
积雨不为休,萧条使人愁。哀吟四壁静,病卧百虫秋。开门望原野,江湖漭交流。谁能载美酒,为我散烦忧。
诗人开头便写了无休无止的雨天,萧条的景象触发诗人心中的愁绪,推开门,放眼一望无际的原野,诗人烦不胜烦,只能用美酒来暂时忘掉烦忧。此诗只有第二句和最后一句写愁绪与烦恼,但是所有的景象都是为其抒发烦愁铺垫的,让人读罢不免也随之苦恼起来,这就是真情实感的魅力。又其《送友仁之京师》:
春风吹兰茝,佳人将远游。远游何当还,神京郁云浮。睠言英迈志,飞辔不可留。岂无金闺彦,与子结绸缪。河山风气雄,江水日夜流。遥瞻云中雁,庶以慰离忧。
诗人欲挽留即将远游的朋友,但是理智告诉他是不可强留的,所以诗人将离别的忧愁寄托在云中的大雁身上,希望借此获得安慰。诗歌前十句写其友远去,句句透露出不舍。两个“留”字,将离别的忧愁直接抒发出来,表达了诗人内心的不舍与难解的“离忧”。倪瓒主要生活在元末,当时诗坛盛行“师心”说,即注重对于内心情感的抒写。在战争频发的年代,倪瓒选择隐居,面对好友的远行,内心不免担心,不舍的情绪始终萦绕心中,这就需要抒发的渠道,对于倪瓒来说,这个渠道就是诗与画。
倪瓒在元代画名与诗名并举,其多幅画作中均有自题诗,这是诗歌与绘画的完美融合,也实现了诗境对于画境的补充。如其《古木竹石图》,右上自题七绝一首,首句“古木幽篁春淡淡”,就给此幅画作定了一个平淡飘逸的感情基调。此外还有《秋亭嘉树图》,右上方自题诗文六行。又《梧竹秀石图》,右中侧偏下自题诗文七行。《幽涧寒松图》,左上方自题五言诗一首,首句便是“秋暑多病暍”。另《水竹居图》《竹石乔柯图》《溪山图》《吴淞春水图》等图上皆有倪瓒的自题诗作。由此可见,倪瓒并不是偶然进行诗与画相结合的创作。元人谢应芳称倪瓒:“诗中有画画有诗,辋川先生伯仲之”,认为倪瓒与唐代诗人兼画家王维不分伯仲,都能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元人张端赞其“所作诗画,自成一家,潇洒颖脱,若非出于人为者”。倪瓒的诗画创作在当时就已得到很高的评价。
倪瓒的诗歌体现了其淡然处世的人生态度,具有简远空疏的意境风格。拙逸老人周南在《元处士云林先生墓志铭》中说:“处士之诗,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萧散,尤负气节。”与其简远萧瑟的画风相似,倪瓒的诗歌风格是冲淡萧散的。他的生平与思想决定了其诗歌中没有抑郁不平之气,情感表达往往平和冲淡。他在《徐良夫耕渔轩》一诗中写道:“林庐田圃,君子攸居。载耕载渔,爰读我书。”他远离城市,住在自然之间,以庐为居,以耕田与捕鱼为食,以读书为乐。他 “厌闻尘世事”,而喜欢远离尘世的生活:“汲泉以煮茗,遐哉遗世心。”遗世而独立,倪瓒感到十分惬意。倪瓒在诗中较为直接地表达了他的归隐之心,描绘了闲适平和的隐逸生活,表现了其纯净、恬淡的心理状态。凡尘琐事,都在倪瓒思想中进行了调整和转换,最终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平衡,趋向洒脱,避免了矛盾冲突。倪瓒的送别寄赠之作,感情表达也同样是冲和平淡的,如《赠张韩二君》:
张仲情何厚,韩康谊亦深。赋诗论宿好,聚首契初心。阮籍惟须酒,陶潜不解琴。与君忘尔汝,萧散鹤鸣阴。
张、韩二君与倪瓒交谊深厚,他们在一起饮酒赋诗,不亦乐乎,感情深厚,但最后诗人希望忘却彼此,将不舍之情消散在离别之后。
倪瓒身为画家,对景物的观察颇为细致,其诗歌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对景物的描写。如《荒村》:
踽踽荒村客,悠悠远遁情。竹梧秋雨碧,荷芰晚波明。穴鼠能人拱,池鹅类鹤鸣。萧条阮遥集,几屐了余生。
首先,倪瓒交代自己是这荒村的客人,远离城市,来到此处,并有远遁之想。第三、第四句写荒村的自然环境,有竹、有树、有水、有荷,一切都充满着生机与诗情画意。第五、第六句用穴鼠与池鹅的活跃突出了寂静,最终目的是表现荒村的萧条与荒凉。
倪瓒还有大量的题画诗作,这些诗歌是对画面的无限拓展,如其《题画》:
甫里林居静,江湖远浸山。渔舟冲雨出,巢鹤带云还。漉酒松肪滑,敷茵楮雪间。春风一来过,似泊武陵湾。
前两句给全诗定下了基调,即寂静与远旷,这也像是笔墨的初步勾勒。第三、第四句中,“冲”和“带”在静中寓动,具有灵动、洒脱的特点。画面是静止不动的,观者无法看到动态之景,而诗句“冲雨出”“带云还”之类的动态,就补充了画境,使得画面灵动起来。第五、第六句对画中细节的描写,对整个画境有补充说明的作用,“春风一来过”句,画龙点睛,平添了诗意。倪瓒在其题画诗中,重现了绘画的构思、布局及运笔的整个过程,还将静止的画面运用简单的动词将其灵动化,动静结合,画面充满灵动之美,实现了诗与画的融合互通。
四、结语
倪瓒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遁隐山林的人生选择,对其诗画创作都有重要的影响。其画作写意传神,其诗强调抒发性情,冲和平淡,情味悠长,是元末诗学“师心”论的体现。倪瓒诗画兼擅,形成了其诗画创作的独特思维与视角,使其诗中有画的意境。其诗是对绘画可见的内容与不可见的运笔的展现,而其画中亦有诗的韵味,不重形似,将主观情感融入画中,形成简远空疏之境。倪瓒将诗与画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融会贯通,实现了诗画艺术创作风格的交融互通。